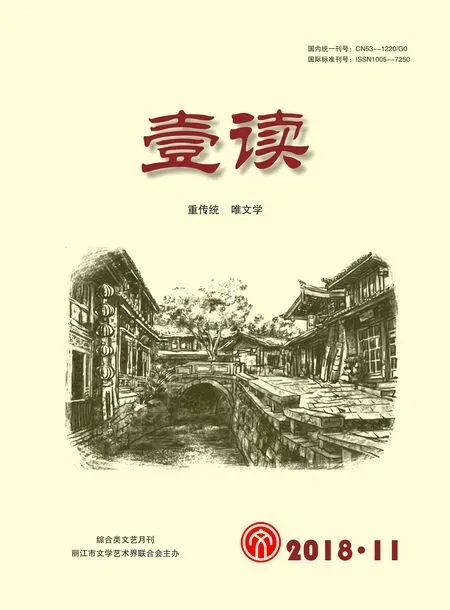束河情怀(外一篇)
2018-01-24罗燕萍
罗燕萍
初见美丽,自然,古朴的束河古镇,我的心一下子陶醉了,古老的大石桥立在那里,不悲不喜。
坐在石头桥栏上,闭目静静晒着暖阳,任清风抚着发梢,似乎听见在细诉经年的往事∶马帮驮着各种货物,皮革,酥油,茶与盐。从他身上经过。一走经年,马蹄打磨着桥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使得石板光洁润滑。穿着羊皮卦的英俊少年,赶马过束河,遇见蹲在三口井边浣洗着蜡染的美丽姑娘,吹着三弦暗诉情意,姑娘羞红了脸颊。穿着羊皮披肩的满脸慈祥的纳西阿婆,坐在门前石磴上纳着厚厚的鞋底。
在大石桥上待了一阵后,我信步走进古镇的小巷,一幢幢沉寂在时光深处的民居,全实木装潢,雕梁画栋,刻窗雕门,吸引你凝眸停足,细细品味工匠的精巧技艺。传统手艺是有温度的,其中所蕴含的人文思愁淋漓尽显。无处不令我迷醉其中。
青瓦屋脊上蹲着瓦猫,将古城鸟瞰,守护永久的安康吉祥。
在束河,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去寻找一条僻静曲折的小巷,用平平仄仄的脚步,去贴近一堵堵斑驳的土墙,立在它面前,看着它被岁月侵蚀苍老的面客,却依然慈祥地矗立在小巷深处,在当前的滚滚洪流中,如此安静、美好又沉默的地方已经越来越稀有。静立在它的面前,似乎能从那斑驳的痕迹里寻见束河变迁的历史画面∶
束河曾以发达的文化教育和皮革加工闻名于世。早在清朝乾隆年间,束河就开设了由政府公助的义学馆,还有三所私塾,近、现代又创办小学、中学,使束河成为著名的人才之乡。
由于位于茶马古道的要塞,以前束河村从事皮革业的很多,各种皮货远销西藏、西昌、青海等地,有的商人甚至到达印度、尼泊尔等国,故有“束河皮匠,一根锥子走天下”之说。
在束河,我任由脚步和目光漫溯。进入眼帘的,最美是那九鼎湖龙潭的水,在房前屋后田边地头流淌,滋润古填,养育了束河儿女。清冽冽的池塘,倒映着美丽纯洁的雪山。云朵在水中荡漾,和着像丝绦一般的水草流淌。垂柳安祥,鸟儿歌唱,鱼儿悠悠伴茶香。倘徉于龙泉之畔,漫步于束河古街,总能让人感受到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时光在这里流逝得很慢很慢。
有许多游人闲坐在大石桥上,看桥下水流,倒映蓝天白云随水流走,似自然风景画,似一首历久弥新的歌,丝绦飘逸,灵动诱人。
再见她时,很多铺面新开张,迎来四方客欢畅。雨后春笋般的客栈,各具特色的食府各自为岸。夜晚红灯绿茶清风相伴,还有那根雕雄鹰欲振翅翱翔。曾经马帮的驿站,如今变心灵的驿站,供来自四面八方疲累的灵魂歇息休养。
找间特色咖啡店静坐,不说话已十分美好。“你有故事吗?我有酒。”“来丽江束河我卖凉粉粑粑养你。”各种诙谐的语录成为一景,悦愉着你俗世的心。卸下所有伪装,静听四方街的洞经古乐,让身心放松沐浴在时光里,与自然同在。也可选择去朝拜三圣,跪下,梵音里涤净尘垢,回复本真的纯洁。
若遇雨天,赤脚走在光滑的石板路上,脚心贴着凉凉的石板,会寻到些许儿童的乐趣。有那么一刻,作为自然人的我似手也融进了古镇的骨血里,成为一体。深刻感知到她的喜怒哀乐,历经过的种种磨难与荣辱,繁华与颓废。
每次走进她,她都有惊人的变化,若一位清纯的少女,慢慢变化成优雅的少妇,一点点丰润起来。
四季不同,她给予你的感受也各不相同,冬天是寂寥的,然她却是温热美好依旧,寂寥与她无缘,暖阳轻泻下来,驱走寒意。走得累了,可以租匹马来乘坐,悠闲地穿巷过街,马儿温驯,蹄声得得敲碎时光,有种穿越而来的感觉。
来到四方广场,找条石凳闲坐,边晒太阳边观察行人,有只胖猫咪也来树旁石头上晒太阳,目光傲娇着告诉你它是常住户,是属于古镇的一抹风景,要多惬意就多惬意,你却只是匆匆的过客。
祖母的记忆
读了陈洪金老师《祖母的记忆》一文。我也开始怀念我的祖母了。祖母是一九二四年生人,在今年,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已驾鹤仙去,令我痛彻心扉。
祖母“从某个遥远的时刻开始活到现在。在漫长的岁月里”,沐浴在阳光里,神性又温馨,在她娓娓叙述的陈年往事里,我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很多细节,一些我们及以后的所有人都只能在电视文学作品里才能感受的生活经历。
我与祖母相处的时光多是在幼时。祖母讲述的许多美丽故事,一些乡间口口相授的传奇,丰润了我幼时贫乏的岁月。那时年幼无知也没记下什么,等回头来问祖母,年事已高的她也模糊了记忆不再说得出来,这无疑是深深的缺憾。
祖母的一生,是甜蜜与辛劳的一生。甜蜜的是祖母赖以生存的手艺——麦芽糖小作坊。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滤麦芽糖水,糖渣用来喂猪,然后是熬制糖水浓缩成糖稀,这是个辛苦的工作,要调好火候,人不离锅地用柳木棒搅动,懒一下或火侯不好,都熬不出好糖稀,熬制好后起锅舀到铺有豆面的簸箕里冷却凝固成型,这就是勤糖,忙完这些,祖母吃过早饭便背上昨天制好的糖上街去卖,卖完糖又去买碎米背回家,(熬稀糖都用碎米的)到家也就撑灯时间了。饭后又将早上冷却的勤糖一端挂在柳树枝干上,柳树枝杆必须用直且有小碗口粗的,上端剥去皮,很光滑,下端用绳子固定在房柱上,用麦杆引火加热拉址成白糖。勤糖闪着金黄油亮的光泽,在拉扯中一点点变成奶白色,糖依旧是糖,口感与味道就大不同呢,我一直没想清楚是怎样引发的变化。一般引麦杆火的工作都交给家人来完成,这也是需要技巧的,火近了会飞落上燃烧后的黑灰,远了又烘烤不到糖,祖母则用力拉扯勤糖,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则相当累人。这一做就是一生。
祖母年轻时应是相当美丽,温婉贤雅的女子。从末听她说过粗鲁的话语,声音极好听,与人说话总面带微笑,轻言慢语。祖父是马帮出生,脾气暴躁,祖父母是怎样认识结成夫妻的是个谜,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祖父母便不在一起生活,祖母带了幺叔幺孃过。父亲是来上门的,祖父与我们一起生活。
祖母一生勤劳惯了,在去世之前都从未止息过劳作,她将院子空地种上各种菜蔬,没事就侍弄侍弄,有时吃不完,会采了送给左邻右舍,因此人缘极佳,这点在她中风躺倒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周围远近的乡邻都来看望。
祖母对我们几个孙女极好,爱清洁的她总是会百忙中烧一大锅水,将我们一个个清冼得干干净净,与众不同的洁净,让我们与乡村邋遢孩子的形象远离。在我记事至祖母去世前最后的时光,她都是个清爽干净的人。哪怕中风躺下,大小便失禁,在她神志还有些清明时,都会用手拍打被子提示我们给她清洗干净,换上新的尿片,我亲手给祖母换洗了三次,祖母只躺倒两天便永久离去了。没受太多折磨。
回忆一旦拉开闸门,便一发不可收拾,不可截止。祖母站在另一个世界,与祖父一起看顾着我们,那里应该没有疲累,终可停止劳作休息了,那里也应该是山清水秀,花香鸟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