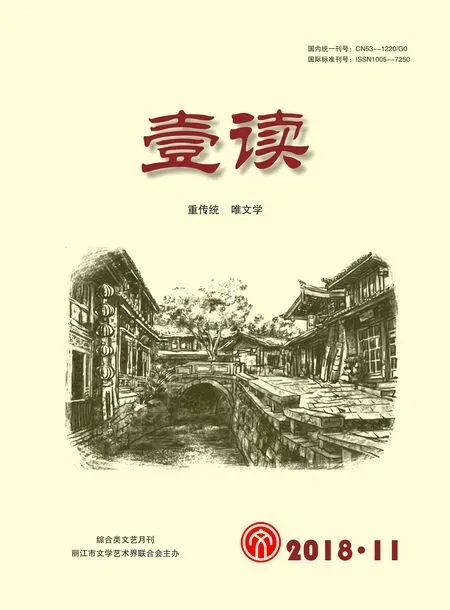向阳的烟草
——丽江青年写作者杜向阳诗歌印象
2018-01-24黄立康
黄立康
烟草需要向阳,“向阳”需要“烟草”。
这是我阅读杜向阳这组“烟草诗”的第一印象和最终概括。
烟草生长需要大量阳光,而诗人杜向阳需要借“烟草”突围人生。
植物、作物、药品、商品,烟草身份众多、身世复杂,而在诗歌中,“烟草”是一个意象。无论“向阳”指代环境或人名,还是“烟草”指代植物或诗歌,“向阳”与“烟草”这两个汉语词汇间存在着的天然、互生的内在关联,让诗歌有了宿命的意味。
“绿色的一件衣裳/你我穿上了它”,“烟草”成为诗人对自己审视和采摘的媒介,“烟草”,是解读诗歌、破译诗人的密码。现在,就让我们从“烟草”的形象开始,回到诗歌开始的地方,去解读烟草的隐喻和向阳的诗心。
痛:关于烟草
“向阳”“没有香味”“又白又紫”“吹着喇叭”“烟草叶/翻卷,白如铅铁”“金色烟叶”,杜向阳用简笔为我们勾勒出“烟草”的形象,而在烟草、烟草地的外层,包裹杜向阳的是烟草所代表的生活。
烟草代表一种生活的常态。路过烟草地,我看到的烟草向阳、茂盛、翠绿,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烟草让生活充满希望和动力。如同阳光只抵达河流的表面,局外人的目光也只能抵达烟草生活的表面。对于常人,烟草是生活的饰品,对于烟农来说,烟草就是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像我这类的旁观者所理解的烟草生活仅仅是烤得金黄、累叠整齐的烟叶,以及人们点上精致的过滤嘴香烟、惬意吞吐的场景。对于真正的烟草生活,我能知晓、理解的其实很少。杜向阳的这组“烟草诗”为我们呈现出烟草生活的真实状态,呈现的过程像剥洋葱,充斥着模糊的血肉和清晰的疼痛。
我们不断尝试脱困的计策
这么多年
一直在这条路上冒险
别人吟诵秋风时,我们
在碎石地上作业,打埂,喷洒农药
在山腰
在金沙江边每一寸有价值的土地上
望眼山谷,全部土地
归属于烟草
白天,太阳烧烂我们的皮肤
睡前,一碗酒,我们用酒
麻木这贫穷的火灼烧命运的痛感
全部活计,只为这金黄烟叶的美梦
而早在四月之前我们就开始栽种烟草
——《烟草》节选
这是诗歌的现场,也是生活的现场。杜向阳为我们呈现出“烟草生活”内在的矛盾——虚幻与真实、理想与现实、奢华与贫瘠、安闲与困苦——在诗人的生活中尖锐地对立着,对立赋予了诗歌张力、深度和立场。烟草向阳的光鲜背后是劳累艰辛的烟农生活,当烟草生活色香俱全的表面被揭开,呈现出血肉模糊的真实时,我们或许会认同诗人对美的理解、对人生的定义——“我理解的美/就应该是悲壮的美”“痛苦才是我们的礼物/这一生的圆心”。
我曾和杜向阳谈到“绝望”,他说:“绝望不就是我们的终极思考吗?”正是这份悲壮,让“烟草诗”呈现出震撼人心的力量,让我想到了滚石的西西弗斯、鹰啄的普罗米修斯和伐树的吴刚。人生苦役,活着,像一支驼队。我看到的是身为烟农的杜向阳,同时也是身为诗人的杜向阳,他将自己沉入到深深的绝望之中。我想他并不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他是在绝望中寻找自己,试图看清自己的现状与命运。这便是烟草诗对他的意义,也是他写作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写作的意义。)文学是一个人的宗教,皈依与拯救,相信才会有希望。小说家胡性能在《小说杂感》中评述:“每一个写作者的写作,可以说都是一个走向彼岸的过程。史铁生曾说:‘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而文学,则是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让我们的灵魂一直保持走向天堂的前行状态。”
写作,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杜向阳一直在路上,他的道路是回归。如诗所见,杜向阳将自己变成一株烟草,回到他的烟草生活,回到他的烟草地,回到他自己。圣奥古斯丁说:“别想着向外求索,返回你自身。真理栖居于灵魂之中。”杜向阳将自己化作一株烟草,然后,往烟草深处走。
自我是杜向阳对烟草的第一层隐喻。
“你我肉身的全部构件/也会开出轻盈又粘稠的烟花”,烟草诗的第一句,杜向阳物我合一地写出了他与烟草的血肉关系:我即烟草,烟草即我。如同对烟草上瘾,诗人杜向阳执迷于对自己剖析和追问,甚至是鞭笞,写烟草就是在写他自己,这让诗歌具有了视觉感、血肉感和疼痛感。烟草是诗人的化身。从这里开始,烟草与杜向阳互为镜像、互为敌友、互为释义,诗歌是烟草的话语。
但杜向阳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比喻之上,而是进一步对“我即烟草”进行描述、挖掘。“我”的特质赋予“烟草”,“烟草”的现状同时也传递到“我”身上,烟草轻盈、柔弱、向阳的特质对应着诗人敏感、易悲、奋进的性格。杜向阳在诗歌中巧妙地运用“偷换指代”的方法,加强了“我即烟草”的血肉关系:“我们身体上/也长出黑茎病,一阵轻风就吹垮掉我们/我们扛起的日子也生满了迟星病,那儿/一大块一大块地烂掉了”。
烟草的病,传染到诗人身上,同根同心,同病相怜。杜向阳将疼痛浓缩为疾病,疾病是疼痛的外在表现。“烟草”和“我”都带着病,都处在疼痛之中。病因来自杜向阳自我认同的身份。一个人如果要认清自己,势必要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追问和确认。之所以将自己比作烟草,我认为杜向阳是将自己的纠缠、焦灼的身份一分为二,烟草代表他“烟农”的身份,而与“烟农”对立的是他“诗人”的身份。“烟农”与“诗人”身份的对立,是杜向阳隐藏在烟草身上的第一组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杜向阳将自己的“烟农”身份形象化为“烟草”,将某一部分、某一身份剥离开来,细细审视。“杜向阳”即是烟农,也是诗人,“烟草”即是植物、作物,也是诗歌。“诗人”身份是“烟农”身份的寄生和反叛。两个不相融的身份纠缠、撕扯、分裂又重合,这种焦灼的状态让诗歌呈现出多层次的寓意和向两极的对立,使得诗歌流露出一种撕裂的痛感。
杜向阳在诗歌中隐藏的第二组对立——“我”和“父辈”——来自他对“身份”的进一步追问:源头,源头象征着生命的起始,也隐喻着既定的命运。杜向阳有两个身份——“烟农”和“诗人”,如果说“诗人”身份来自自我,那么“烟农”身份来自于他以烟草为生的“父辈”。
“我和父亲抽着烟草,这个/我没有再回来的家园”“我的父亲们/又黑又丑”“让我贩卖它们吧/父亲的心血全部献出去/我的青春全部献出去”“父辈们/手工业者/为之搏命”。
“我”与“父辈”的对立统一,是杜向阳“诗人”与“烟农”对立又统一的身份的延续。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是父辈生命的延续,父辈的生命是我们继承的财产,生命带着固有的冲力和惯性,从父辈抵达我们,要追问“我是谁”“我从何处来”的问题,必须要回溯生命,回到父辈,看清父辈的命运。“我”与“父辈”之间存在着妥协与对峙,杜向阳用人称代词“我们”表示与父辈的同属关系,同样的“烟农”身份,同样因烟草而悲喜的命运,父亲的心血和我的青春都献给了烟草。
杜向阳也认同自己的“烟农”身份,但“诗人”的身份带来自我的觉醒和反抗,青春代表着激情、希望、不甘与未来,而“父辈”却带着老去、认命、墨守和过去的阴影。父辈是故乡,青春是世界。父亲既定的命运是我们反叛的道路,我的青春与父辈的心血矛盾尖锐,“我和父亲抽着烟草,这个/我再也没回去过的家园”,种植烟草的人抽着(消耗)着烟草,拒绝命运安排的人试图逃离,却总是轮回到命运中反刍着命运,在对待烟草的态度上,“我们”却默契地达到统一。烟草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烟草能够治疗“我们”各自的病痛,能够挽救父辈的灵魂和我的青春。对于诗人来说,烟草到底意味着什么?烟草能够给诗人带来什么样的人生?烟草除了代表烟草苦役的生活,代表自我,更重要的是,诗人笔下烟草象征着人们对生活的极端化的美好想象。
杜向阳往烟草深处走去,经过烟草所代表的苦役生活,经过自己,也经过了父亲与故乡。像是寻找病痛的源头,最后,杜向阳站在“烟草”的核心前,长久地伫立、审视。烟草是生活,是自我,是黄金。
诗中多处提到一个意象——黄金。
“被称为黄金叶的烟草可以摘收了”“全部活计,只为这金黄烟叶的美梦”“仓房里挂满金黄烟叶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至今一身病痛”“让绿油油的烟叶变成金黄的钱财”“黄金之梦/一种瘟疫”。
黄金,是杜向阳对烟草的第二层隐喻,这是一个神形兼备、内涵丰富的隐喻,一方面烟叶烘烤变金黄,另一方面烟叶有着极高的经济价值。卑贱的烟草具有了黄金的价值,使烟草散发出黄金的魔力和致命的诱惑。在烟草所背负的所有隐喻和对立中,“黄金”是最为核心的内容。黄金为烟草带来了财富、身份和权力的喻义,在这一层面上,二者是统一的。烟草驱动的人生,黄金之梦是源动力。但黄金与烟草又有着本质的区别,黄金坚硬、珍贵,烟草柔弱、普通,特质暗示了二者不同的命运,无形中增强了诗歌的张力,扩大了诗歌的阐释空间。
在黄金与烟草貌合神离的统一中,存在一个对立面:贫穷。杜向阳在诗歌中并没有将它隐藏,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诗句:“黄金之梦/一种瘟疫”“你我穿上了它:那些痴心症/那些治疗贫瘠症的药丸/发家致富的妄想症”“烟草治疗土壤/和穷苦之病/治疗七月和八月生育的空荡”。贫穷是对强悍命运的描述。杜向阳同样通过对立关系来加深“烟草”的矛盾关系——黄金与贫穷。代表着富贵与贫穷、虚幻与现实、灿烂与苍白、锋利与麻木的两极对立,矛盾不可调和却又统一在“烟草”身上,让诗歌充满撕扯的痛感。更有深意的是,杜向阳将“贫穷”进一步形象化为疾病:“痴心症”“贫瘠症”“致富的妄想症”。如果黄金是富贵的象征,那么疾病便是贫穷的外显。诗人以“病态”的方式呈现生活的现状。对富贵生活的追求,被形象化为对黄金的痴迷,病越重,痛越清晰,而这种痛的矛盾,被附在“烟草”柔弱的肉身之上,承载着沉重的希望。杜向阳继续向“烟草”深入,在某个时刻,烟草代表的对美好生活的期许,甚至超越了“黄金”,直抵灵魂:“一朵朵雪白的烟草花/你以为花的象征是驱走魔鬼和病魇/是父辈们寄放灵魂的仙境”。烟草成为了“灵魂”的寄托,“灵魂”是杜向阳对烟草的第三层隐喻。从“肉身”到“灵魂”,杜向阳借烟草完成了对自我的追问,触摸到了生命的深层意义。当然,诗人并没有试图升华主题、强行赞美。在这一点上,我认同他的做法,有时候,我们所理解的灵魂,其实跟物质、现实、欲望和苦难有关,而并没有善美的内涵。
症:关于烟草地
疼痛源自病症。对于杜向阳来说,所有的病症、疼痛都源自烟草。烟草是内里的病因,而病症的具体表象则显现在烟草地上。像止痛治病,必须剜掉腐坏的部分,对症下药,才能生出新肌,杜向阳必须回到烟草地,去审视侵蚀他生活的炎症。
烟草地向阳、广阔、密集,但当我们走进烟草地,身处其中,化为一株烟草,我们扎根的烟草地会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带给我们怎样的体验?于坚在《棕皮手记》中写到:“只有进入《圣经》内部,才有善与恶的区别。如果站在《圣经》之外,那么它是无所谓善恶的。它无非是‘这样的一棵树’罢了。而诗人和世界的关系,也是如此。”诗人也需要进入自己世界的内部,去尝试着解释他与世界的关系。杜向阳需要进入烟草地、进入烟草、进入自己“烟农”的身份,才有痛与乐的区分。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在烟草地之外,那么烟草无非是“一株烟草”而已,让我们跟随杜向阳的烟草诗,一起走进烟草地的时空。对于烟草地的刻画,杜向阳并没有停留在片面之上,他的叙述克制、简洁,因为他想要表达更多的内容。杜向阳选择了几个点来对“烟草地”进行塑造:坐标、时空和意义。
“烟草地”作为一个诗歌中的地域意象,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具体实在的对应:
“凋败的故乡大地”“烟草地尽头的河流/真美。金沙江你真美”“旷野在呼唤我们,那些浩劫/在护佑我们”“我们在清晨抵达山边”“别人吟诵秋风时,我们/在碎石地上作业,打埂,喷洒农药/在山腰”“我们还在日夜开荒,直抵山脊”“成片的烟草田”“我们走到田尽头的水沟边,蹲在那里/搓手上的烟油”“一些烟叶在地里腐烂”。
在杜向阳零散的记述中,“烟草地”的形象在我们脑海中逐渐清晰,我们得以确定“烟草地”首先出现在诗人的故乡。每个人都有故乡,为此杜向阳将故乡的坐标进一步确定到“金沙江”,然后是“旷野”“山边山腰山脊”“烟草田”“田边”“地里”。烟草地有了一个存在的坐标,也有了一个具体的外部环境。而针对诗人的内心世界,杜向阳写道:“烟草地占据了要塞”。烟草地占据了故乡的要塞,占据了父辈命运的要塞,占据了诗人青春的要塞。“要塞”一词让烟草地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烟草地中一年一季的烟草种植,如同一场决定成败的战役,杜向阳(烟农和诗人)将自己放置在“哀兵”的位置之上,步步为营地坚守自己生命的要塞。
在我们确定了“烟草地”的坐标和环境之后,“烟草地”以“平面图”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杜向阳并没有点到为止,环境变化催生的心境变化,让诗歌显示出更深的层次和意蕴,体现出烟草地的“要塞”意义,杜向阳进一步挑选关于烟草地的细节,通过空间和时间的变化,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变化、流动、无常中的烟草地。
杜向阳的诗歌有着很好的时间感,时间的流动为烟草地带来变化,同时也为我们呈现烟草的一生、烟草地的一季。
“全部活计,只为这金黄烟叶的美梦/而早在四月之前我们就开始栽种烟草”“六月末到七月,大雨不停/一些烟叶在地里腐烂”“想必,你也热爱这些/反复循环的寂静/和短暂的疯狂的七月”“我们松开喉舌,爽朗大笑/我们为金色烟叶重现的七月/感到有尊严”“烟草治疗土壤/和穷苦之病/治疗七月和八月生育的空荡?”“七月,八月,九月,十月/雾袋里的烟草地/肥厚的烟叶/摘尽它们!摘完它们!”“不要过多的雨水/不要九月深入时/贬低烟草价值”
时间的变化让烟草地之上的时空开始流动。四月之前种下烟草,之后的六、七、八、九月,需要大量阳光的烟草却时时迎来雨季,牵动着诗人的悲喜。“破坏土地,终结青春”的烟草却有着柔弱的肉身,烟草几乎什么都怕,脆弱的烟草使烟农的生活也变得脆弱,让诗人的心变得敏感易痛。“在普通话诗歌中一般看不见诗人何时空现场、更看不见与私人生活、具体时空的关系。”(于坚《诗学随笔》)但杜向阳强化了他与时空的关系,除了赋予烟草地时间感,杜向阳也不断地深化了烟草地空间的细节。
我在诗中看到的“烟草地”是这样的:
“凶险的静谧的富饶的荒凉的高地/是不归之路”“布置在石头间,山岩间的”“在烟草地白炽的云浪中”“太阳如铁水的季节”“烟草地已经开花/瘦弱的烟叶/恐怖的冰雹”“风和雾在吹打烟草地”“麻布袋一样的雾里面”“雨水冲刷出血红的泥土,冲毁/刚刚建造起来的美好”
脆弱的烟草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中——“凶险的静谧的富饶的荒凉的高地”——烟草的特点(脆弱、多金)对应着烟草地的特点(凶险、富饶),烟草地的状况就是病症的状况,烟草地的状态也就是诗人存在的状态(凶险、荒凉)。围绕着“烟草”,杜向阳将自己的感情意图以“烟草地”的“状态”呈现——亲近与排斥,迷恋与厌恶,熟悉与无常,回归与游离,安稳与颠沛——烟草地即是杜向阳的生活环境,也是诗人的内心环境。
烟草似乎处在极端的自然环境中,总是猝不及防地面对自然的侵害,风、霜、雨、雾如同敌军一次次的攻城冲击,烟农的生活因烟草地而草木皆兵。烟草地的高山大江、山脊河沟,所有可以依赖的环境与烟草地连成一体,被杜向阳提取、凝练、重塑,形象化为一个“要塞”。足见烟草地的重要性,烟草和烟草地都是杜向阳存在的重要证据。
烟草地占据了要塞。要塞,在杜向阳的进一步书写下,细化为“凶险的静谧的富饶的荒凉的高地”。词语的变化为我们带来了更多更细的感触。“要塞”意味着固守,也意味着囚禁。为了将“要塞”的双刃性表现得更明晰,杜向阳对“要塞”做出解释,和烟草的隐喻充满矛盾一样,烟草地也充满着矛盾:凶险对静谧、富饶对荒凉。自然现象让脆弱的烟草地变得凶险。除去“金色烟叶重现的七月”,多数时候烟草地静谧、烟草孤独。黄金之梦来自烟草,而黄金之梦也是一场瘟疫,刺痛贫困,留下荒凉,席卷父辈的命运与我的青春。一切荒诞的统一都来自杜向阳的生存状态、真实情感。同为烟农与诗人的杜向阳总是处在一种焦虑、悲痛、忍耐、心悸和无力之中,正如他在诗中写到的那样:“烟草地,谁耕耘它/谁就一生重如铅铁”“我们把自己还给烟草地/吞噬的/不止这些”。
从“故乡”到“要塞”,杜向阳还在不断地深化“烟草地”,最终,烟草地变成了诗人的“记忆”,包含了诗人过往和未来、时间与空间、付出与收获。烟草地是记忆。
反复记忆起这私人的领地
这土地的圆弧
也请记忆雨量,风速
那些无影人奉送的:心悸,草种!
请记忆我们如何带走它们
带它们上路
疗:关于烟草生活
“没有任何划定的道路来引导人去救赎自己;他必须不断创造自己的道路。但是,创造道路,他便拥有了自由与责任,失去了推脱的借口,而所有希望都存在于他本身之中。”这段话来自让-保罗·萨特。道路代表着自由,同时也意味着责任。对于杜向阳来说,关于烟草,关于烟草地,关于烟草生活,“所有的希望都存在于他本身之中”,所有的希望都存在于杜向阳对烟农身份的坚守之中,所有的希望也都存在于杜向阳对诗人身份的寄托之中。烟农身份是杜向阳的本分与命运,而诗人身份则是他的自由与责任,他没有推脱,他为我们带来了一组烟草诗——一座他创作的天堂。
夏尔·波德莱尔在《人造天堂》写:“出色地做梦并不是每个人的天赋,即便他有这种天赋,也很有可能由于日益增长的现代的分心和物质进步的喧闹而一步步减弱。做梦的能力是一种神圣和神秘的能力:因为通过梦人才能和包围着他的黑暗世界进行交流。但是这种能力需要孤独,才能自由地发展。人越是全神贯注,就越能广泛地、深刻地做梦。”波德莱尔写的是鸦片,而杜向阳写的是烟草。杜向阳让我们看到了他开在烟草花里的梦。无论是烟农身份还是诗人身份,烟草是他的疼痛,是他的病症,也是他的自我治疗。
如何治疗命运带来的顽疾和隐痛?杜向阳返回到了烟草生活的最低处,找到了烟草生活中最为痛苦、最为磨人的记忆:劳役。
作家夏榆在《黑暗中的阅读与默诵》中写到“工具”:“无法战胜工具,就无法战胜劳役,无法战胜劳役,就无法战胜命运。”作为烟农的杜向阳,希望借烟草(工具)改变贫困,改变处境,和与生俱来的命运抗争。烟草是劳役。作为诗人,烟草也是工具,杜向阳借烟草来关照自己的内心,剖析自己、看清自己。烟草是治愈。
虽然是“向阳”,但这却是一组让人随之沉浮、肃然生悲的诗作。对故乡的若即若离,对父亲的似曾相识,对烟草(自己)的如爱似恨,杜向阳形而下返回烟草生活的原生态中,去体验原汁原味的烟农心情。于坚在《三个词》中提到:“一个词,如果我们不能在形而下中感知它,那么只意味着这个词的死亡。”烟草是植物、作物、药物、商品,在诗歌中,它是一个词,来自生活,来自劳动现场。烟草作为意象,自然可以从形而下的生活中找到具有实体的物象,而烟草本身所具备的特质,是“烟草”成为“形而上”的意象的前提。解读“烟草”的内涵,需要追本溯源,回到诗人发现、挖掘和提炼“烟草”这一意象的生活现场,回到诗人的琐碎、疼痛的形而下的生活中去。一株烟草翠绿到金黄,鲜活变干枯,诗人要经历烟草的一生,这一生或许也隐喻了我们的一生,但在金黄的丰收之后,在高照的艳阳之下,在沉默的生活之中,总有我们看不到的生活细节和真实苦痛。“阳光只抵达河流表面”,烟草的一季,为我们展示出以“烟草”为生的农人卑微琐碎的日常。
“七月的风中/你在恋爱/但是烟草,它生长在孤独里”“别人吟诵秋风时,我们/在碎石地上作业,打埂,喷洒农药/在山腰”
“假如我没有在此工作过/成为这土地的孩子,不认识烟草/不知道机器的形状,不熟悉煤炭的等级/在冬夜时候,就没有记忆”
“白天,太阳烧烂我们的皮肤/睡前,一碗酒,我们用酒/麻木这贫穷的火灼烧命运的痛感”“烟油染黑了手,难以洗掉/我们走到田尽头的水沟边,蹲在那里/搓手上的烟油”
“在这血红的地平线/但即便我们势必改造这悲哀的土坵/悬起我们汗水滴灌出的/烟草的幼苗”“雾袋里的烟草地/肥厚的烟叶/摘尽它们!摘完它们!”
“关闭火门,我们闷息烤炉中的碳火”
山腰、碎石地、土坵;烟油、碳火、烈日;孤独、悲哀、辛劳,这只是烟草地上的苦役生活呈现出的一小部分状态,还有许多细节成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对于杜向阳来说没有烟草地,就没有记忆;没有劳动,就没有存在。伴随烟草而来的是“无尽的劳动”带出了深陷苦役的烟农。烟农的生活日常、复杂心态和悲苦命运如影随形。杜向阳返回劳动现场去触摸痛处,去解剖自己,去追问人生,以精神原力去化解现实的阵痛。这是勇气,勇气来自于尊严和坚守,面对困境、疼痛、卑微和渺小,仍然保持着尊严。杜向阳用诗歌树立了烟草的尊严,树立了烟草地的尊严,同时也给与了父辈和自己尊严。这是杜向阳的自我治疗,用劳动树立起生命的尊严。劳动现场才是生活的现场,劳动而生的疼痛感才是存在感的体现,才是生命尊严和勇气的源头。
余华在《活着》韩文版的前言这样介绍自己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烟草象征着苦难与贫困,更应该象征着烟农的坚韧,烟农并没有因为苦难与贫困而让烟草地荒芜,相反,杜向阳看到的是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烟农都在土地上刨食、生活、做梦。这轮回来自生命的坚韧,如同橄榄枝象征着和平,柔弱的烟草有资格象征人性的坚韧。
杜向阳是本土80后写作者中的一个“异类”,当大部分本土80后写作者还停留在青春式写作、才子式写作时杜向阳已经开始用经历写诗。他的经历复杂凶险到让我惊讶,这组“烟草诗”还原出的生活原貌,是大部分写作者从未经历过的。对烟草的复杂情感,使这组以“烟草”为名的诗歌深沉而复杂。如果说文学是一个人的宗教,那么杜向阳对烟草的写作是对自己的解读、分析和救赎。神只救自救。杜向阳借诗歌给我们以“炼狱”的体验,而“烟草诗”却是他的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创造出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