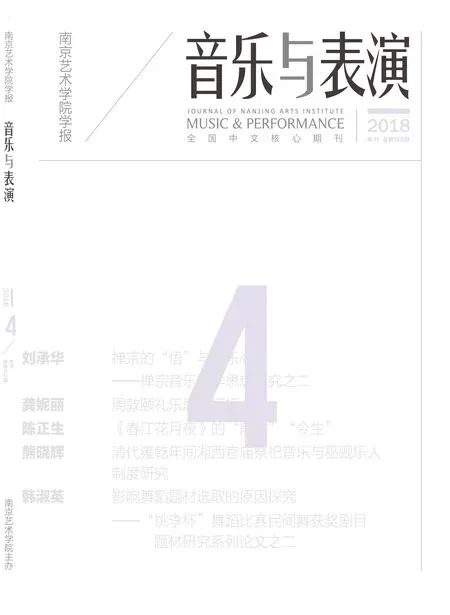弦鼗的演变与汉族琉特类弹弦乐器的发展
2018-01-24陆晓彤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100029
陆晓彤(中国艺术研究院 音乐研究所,北京 100029)
在中国古代乐器发展史中,琉特类弹弦乐器的流变过程尤其复杂,按起源可将其划分为由中原地区汉民族本土创制,以及自周边民族外来传入两类,由汉民族本土创制的琉特类弹弦乐器①为便于行文,以下简称汉族弹弦乐器。流传至今,主要有阮、三弦、月琴三类,三者在形制演进与定名的过程中脉络交融,它们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是各自独立的。系统梳理唐宋乐器文献可知,汉族弹弦乐器的分类问题早在唐宋文献中就已经厘辨不清,同名异器与异名同器问题并存导致文献记载内容缠杂,汉族弹弦乐器的本源及其演变过程仍待进一步探寻。
一、文献中“弦鼗”含义的演变
追溯汉族弹弦乐器的起源,“弦鼗说”是其根本,“弦鼗”在历代文献中的含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最初表示动作的词组发展到具体的乐器名称,考溯由晋至宋的音乐文献,可以发现,“弦鼗”的含义随着文人阶级对汉族弹弦乐器分类的深入探索而不断变化。
“弦鼗”一词始见于西晋傅玄所著《琵琶赋》的序文之中:
杜挚以为,赢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1]
文中“弦鼗”说是转引三国曹魏文学家杜挚的言论,由于年代久远、书文散失,杜挚谈论弦鼗的原文已不可考。据《琵琶赋》行文判断,“百姓弦鼗而鼓之”意为百姓张弦于鼗鼓并演奏发声,“弦鼗”一词只是作为一个动宾词组出现于文学家笔下②此观点另可参见张伯瑜《弦鼗一词的说明》,载《中国音乐》,1985年第二期。,因此“弦鼗”在三国时期并不是乐器名称,自然也不存在所谓乐器形制的问题。而傅玄之后的弦鼗史料,多被认为是南朝陈释智匠所撰《古今乐录》:
琵琶出于弦鞉。杜挚以为赢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歌之。[2]
《古今乐录》在吸纳傅玄《琵琶赋》内容之外,又增有“琵琶出于弦鼗”一句作为新资料出现在研究者视野之中。然经笔者考证其史源,该句转引自早期东晋咸和初年南郡太守王諐期所著《降幕祠议》③任明等校点本《太平御览》作“《绛幕祠仪》”,(宋)李昉撰,任明等校点,《太平御览•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95页。《补晋书艺文志》作“《降幕祠仪》”,丁国钧撰,《补晋书艺文志》,商务印书馆出版,1939年版,第53页。:
琵琶出于弦鼗,笙簧基于丝竹。[3]
文中两句以六字工整对仗,显然是魏晋骈文迤逦,句中“琵琶”与“笙簧”作为乐器名相对应,而“丝竹”不是乐器名,与之对应的“弦鼗”显然也不作为乐器名使用。王諐期创作的《降幕祠议》已经散佚,及至宋代,仅《太平御览》[4]与《事物纪原》①[宋]高承撰《事物纪原》卷二《乐舞声歌部十一》云:“王諐期《终幕祠仪》曰:出于弦鼗。”[5]99两部著作留存了其中的少量佚文,王諐期本人也没有其它音乐言论存世,故而该文献的原始出处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
唐代以前的文献中,“弦鼗”仅出现于上述三处,皆非乐器名称。及至唐代,“弦鼗”开始大量出现于文献之中,其含义也开始转变。初唐虞世南《琵琶赋》载:
寻斯乐之惟始,乃弦鼗之遗事,慰远嫁之羁情,宽绝域之归志。[6]
值得注意的是,虞世南将汉族弹弦乐器的两种起源说“弦鼗”与“乌孙公主远嫁”结合起来,“弦鼗之遗事”的说法被后世文献频繁转引,《通典·乐典》[7]1933《新唐书·乐志》[8]313中都出现了类似记载,此时的“弦鼗”没有出现具体形制或演奏方式、使用场合的记载,直至南宋类书《事物纪原》“嵇琴”条按文中,出现了对“弦鼗”形制的描述:
按,鼗如鼓而小,有柄,长尺余。然则系弦于鼓首,而属之于柄末,与琵琶极不仿佛,其状则今嵇琴也,是嵇琴为弦鼗遗象明矣。[5]100
此时的弦鼗已经成为一类乐器的名称,而不同于前,它所指代的是我国汉族弹弦乐器的初期形态。“弦鼗”含义的转变是学术史的需要,秦末至两晋时期,这件“弦鼗而鼓之”的乐器雏形由于形制简陋等原因未经定名,又或者它的称谓只流传于“弦鼗而歌”的劳苦大众阶层,而没能被文人记录并保存在文献之中。而唐宋时期音乐专著、类书、政书等文献大量涌现,其分类编纂的思想促使唐宋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梳理此前并不完善的中国传统乐器定名体系,正是这种文化的需要,弦鼗逐渐被具象为一类乐器的名称,代指由体鸣乐器“鼗鼓”发展为弦鸣乐器“秦汉子”的中间过程。汉族弹弦乐器的定型与定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以“弦鼗”来命名汉族琉特类弹弦乐器之雏形,并以此串联汉族弹弦乐器的发展史是合理且必要的。
二、两种起源说与汉族弹弦乐器发展的混沌期
汉族弹弦乐器的起源分为“本土说”与“外来说”两种,外来说即以林谦三、田边尚雄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对该类乐器起源于弦鼗的“本土说”提出异议。郑祖襄在《弦鼗研究的争议与讨论》[9]中,研究古代鼗的形制、唐代文献记载与音乐图像三方面,详尽论证了汉族弹弦乐器的本土性,并驳斥了“传播学派”的“西乐东渐”说,汉族弹弦乐器起源于“弦鼗”已成共识。
继弦鼗以后,南北朝至唐初汉族琉特类弹弦乐器的发展历程并没有记载于文献之中,这一时期该乐器的发展进入了混沌期。一方面,外来乐器的大量传入,冲击了中原地区原有的名为“琵琶”的乐器,另一方面,部分本土乐器因音量小、转调不便等原因逐渐衰落以至失传,胡、华异器同名以及汉族弹弦乐器自身传承无序等问题,影响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现在仍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承接于弦鼗之后的汉族弹弦乐器,是今之三弦还是阮咸?
(一)鼗与阮咸
目前学界多一位汉族弹弦乐器的发展,经历了由鼗到弦鼗再到阮咸琵琶的路径。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傅玄《琵琶赋》序文记录了汉族琵琶的两种起源说,其一是上文述及的“弦鼗说”,其二是“乌孙公主说”:
闻知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今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之象也。盘圆柄直,阴阳之序也。柱有十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俗语之,故云琵琶也,取其易传于外国也。[10]
文中记载的琵琶具有盘圆柄直、十二品柱、四弦等特征,对应的乐器应是今之阮咸。傅玄在文后对这两种起源说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傅玄认为汉族琵琶是由乌孙公主时的工匠所创制,《宋书·乐志》《初学记》《通典·乐典》《太平御览》等文献都沿用了上述内容一记载汉族弹弦乐器的起源。然而,从乐器学角度分析,琴、筝、筑等齐特尔类矩形音箱乐器,如何能直接演变成形制差距极大的琉特类竖抱梨形或圆形音响乐器呢?这种转变并不符合乐器发展的基本规律。
(二)鼗与三弦
若由“弦鼗说”引申而来,那么依据乐器形制演变的基本规律,鼗鼓本身的形制必然影响汉族弹弦乐器的基本形制特征。鼗鼓由来已久,《诗经·商颂·那》中已有“猗与那与,置我鼗鼓”[11]的记载,《周礼》的雅乐典礼中同样沿用鼗鼓,汉画像石刻中描绘了汉代鼗鼓广泛应用于百戏及鼓吹、丝竹乐队。
尽管鼗鼓在长时间的历史流变过程中,出现了鼓柄长短、柄端鼓腔数量等方面的变化,但鼗鼓仍持续的保持着直柄圆匡、匡体两面蒙皮的基本特征。由击乐器鼗鼓转化为拨乐器弦鼗,是由膜鸣转化为弦鸣,改变了该乐器基本的发声方式,而保留鼗鼓两面蒙皮的特性,则可以降低弦振动的难度。从二者的形制共性与乐器发声角度分析,无论弦鼗之后的汉族弹弦乐器,在定型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形制发展阶段,匡体蒙皮都是最直接的传承形式。承接弦鼗的乐器,应是具有与鼗鼓最为接近的特性——盘圆柄直、圆体修颈、柄上无品相、匡体两面蒙皮。若我们省略汉族弹弦乐器发展过程中混沌的中间环节,直接将现已经定型的汉族弹弦乐器与鼗鼓比对,最为接近的乐器类型,不是阮咸,而是今之三弦。
一直以来,学者在讨论由鼗鼓演化而来的弹弦乐器时,只是以“圆形共鸣箱,音箱上有长柄,柄上张弦、竖式弹弦”为标准,将弦鼗与阮咸相连,从而忽略了鼗鼓两面蒙皮的形制特征对弦鼗初始形态的影响。而阮咸短柄、有品、框体木质、音响圆大等特征,极有可能是汉族弹弦乐器继弦鼗与形似三弦的乐器之后的在发展。
但是,在文献和文物方面,目前有关三弦存在年代的确切实证——北京房山云居寺辽塔砖石上出现三弦伎乐石雕像[12],只能将三弦在中原地区使用的时间断代于辽。辽代以前的唐宋文献中曾出现有关“三弦”的记载,但通常被学者认为是行文中的讹误,并不作为三弦的史料支撑。如,中唐崔令钦撰《教坊记》载:
平人女以容色选入内者,教习琵琶、三弦、箜篌、筝等者,谓“搊弹家”。[13]
中华书局本将此处“三弦”考订为“五弦”的讹误。
另,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
诸乐中如琴者,长四尺,九弦,近头尺余方广,中有两道横,以变声,又如一酒榼,三弦,长三尺,腹面上广下狭,背丰隆。[14]
此处“三弦”仅指形制类似古琴的乐器其张弦数目。
但《新唐书·南蛮列传》载明了两种张有三根弦的琉特类乐器:
(骠国)有龙首琵琶一,如龟兹制,而项长二尺六寸馀,腹广六寸,二龙相向为首;有轸柱各三,弦随其数,两轸在项,一在颈,其覆形如师子。有云头琵琶一,形如前,面饰虺皮,四面有牙钉,以云为首,轸上有花象品字,三弦,覆手皆饰虺皮,刻捍拨为舞昆仑状而彩饰之。[8]4785
文中的龙首琵琶与云头琵琶是骠国进贡中原的乐器,可见,至少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在唐代已经盛行三根弦的竖抱弹弦类乐。
至五代时期,《旧五代史·后晋·少帝纪二》载有“三弦胡琴”:
帝自期年之后,于宫中,间举细声女乐;及亲征以来,曰于左右,召浅蕃军校,奏三弦胡琴,和以羌笛,击节鸣鼓,更舞迭歌,以为娱乐。[15]
胡琴在当时是外来弦乐器的统称,三弦胡琴的具体形制是否属琉特类弹拨乐器难以考定。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以确定的是,张有三弦竖抱弹弦乐器在辽代之前已经应用于中原地区的音乐生活之中,而以双面蒙皮、直柄竖抱、张有三弦为特征的汉族弹弦乐器,其出现不会晚于唐代。
笔者认为,傅玄文中记载的两种汉族琵琶起源说,并不是互斥关系。汉族弹弦乐器的根本起源是“弦鼗”,“乌孙公主说”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另一趋势。即汉族弹弦乐器圆体修颈的外形承接自流行于民间的弦鼗,而品相等与音律有关的乐器构造,如文献所载出自当时已经成熟的琴、筝、筑等齐特尔类乐器,为便于长途运输保存,音箱也由蒙皮发展为更不易破损的木制。所谓的两种起源说,其实表明汉族弹弦乐器至晚在东晋时期已经开始分流,形成了以蒙皮音箱无品、木质音箱有品为主要区别的两种发展方向。至于三弦缺载于文献可能有两方面原因:第一,相较于与文人典故紧密相关的阮咸,三弦的流传可能仅限于中原地区的民众之间,而阮咸则频繁出现在与魏晋文人相关的书文之中;第二,下文所述“秦汉子”的具体形制与三弦接近,那么唐代以前的秦汉子是否就是三弦的别称,仍待探究。
三、秦汉子、秦汉、秦琵琶、秦汉琵琶与阮咸
文献记载中的汉族弹弦乐器名目繁复、形制不一。仅《通典·乐典》“琵琶”条就记载了三类琵琶:
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傅玄云:“体圆柄直,柱有十二。”其他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7]1933
其中第二类形制上大下小、曲项、体型较大的外来琵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通典》没有记录该类琵琶的异名,可见这类是当时被普遍称为“琵琶”的乐器。
第一类被称为“秦汉子”的琵琶属乐器,作为“弦鼗之遗制”,应是汉族弹弦乐器,其形制特征是圆形音响、琴颈长、器形小,符合上文中对“鼗”与“三弦”形制共性的分析。“秦汉子”之名还出现在《新唐书·乐志》中:
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铙、钹、钟、磬、幢箫、琵琶。琵琶圆体修颈而小,号曰“秦汉子”,盖弦鼗之遗制,出于胡中,传为秦汉所作。[8]4785
隋代法曲中使用的琵琶即“秦汉子”,其形制与《通典》记载吻合。可见隋唐时期“秦汉子”的称谓是被广泛使用的。
唐宋文献中还出现了一类名为“秦琵琶”的乐器,《通典·乐典》“阮咸”条载:
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项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三柱。
《乐书》“阮咸琵琶”条载:
阮咸五弦,此秦琵琶,而颈长过之,列十二柱焉。唐武后时,蒯明于古冢得铜琵琶,晋阮咸所造也。
两部文献皆载阮咸琵琶在唐宋时期被称为“秦琵琶”。但笔者在《旧唐书·乐志》中发现一则材料:
隋平陈,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乐用钟一架,磬一架,琴一,三弦琴一,击琴一,瑟一,秦琵琶一。[16]
根据文中该琵琶使用于清乐这一特征判断,秦琵琶”更可能是“秦汉子”的异名。
而陈旸《乐书》中又出现了一类名为“秦汉琵琶”的乐器,它同样具有“圆体修颈”的特征:
(秦汉琵琶)圆体修颈,如琵琶而小,柱十有二。惟不开目为异,盖通用秦汉之法,四弦四隔,合散声四,隔声十二,总二十声。
《乐书》同时记载了秦汉琵琶与阮咸琵琶,二者都具有“十二柱”的形制特征,极有可能是同一件乐器的不同称谓,阮咸琵琶本身在因“竹林七贤”中的阮咸而得名之前,应有其本名。
根据梳理文献可以推断,文献中记载的“秦琵琶”“秦汉琵琶”“阮咸琵琶”可能是同器异名,而“秦汉子”与“秦琵琶”之间也出现了相互关联的记载,唐宋时期汉族弹弦乐器的名称及品柱、张弦数量的记载已经开始出现混乱。显然,当时的编纂者,面对外来琵琶的冲击、汉族琵琶的分流,以及我国古代本身并不严谨的乐器定名体系,已经难以梳理琵琶属乐器的名称、形制及流变过程,导致记载并不清晰。
笔者认为,《通典》所记载的三种弹弦乐器,第一种“圆体修颈而小”,可能是今之三弦;第三种琵琶“秦汉”兼似两制,应该是吸收了汉族弹弦乐器“圆体修颈”特征与外来琵琶“木质音响”特征的今之阮咸。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乐器阮咸的留存情况并不是传世的。《通典·乐典》载:
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项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时,蜀人蒯朗于古墓中得之,晋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同,因谓之阮咸。咸,晋世实以善琵琶、知音律称。(蒯朗初得铜者,时莫有识之。太常少卿元行冲曰:“此阮咸所造。”乃令匠人改以木为之,声甚清雅。)[7]1938
根据文献记载,在武后时阮咸这件乐器已不为常人所识,在西晋阮咸善弹到武后时再次现世,这三百年间,阮咸极可能处于失传的状态,而这一时段正是汉族弹拨乐器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直到蒯朗于墓葬中发现铜制陪葬乐器,才使得阮咸重新出现在唐人的音乐生活中。唐代是阮发展的高峰,可能是受当时弹弦乐器大盛之风的影响,唐阮取材名贵、曲目丰富,随阮咸的兴盛又出现了形制稍小的月琴。陈旸《乐书》“月琴”条载:“形圆项长,上按四弦十三品柱,象琴之徽,转轸应律,晋阮咸造也。”取其形似月,其声如琴之意。月琴被认为是阮咸的再发展。此后,汉族弹弦乐器开始进入文献、图像、传世实物并存,分类准确的成熟期。
结 论
汉族弹弦乐器在唐代以前的流变过程并不清晰,其乐器雏形“弦鼗”的词意,则是随着后世文献对乐器定名的深入探讨,才逐渐确定为的乐器名称。现阶段的研究无法证实古代弦鼗与形制最接近的现代三弦之间存在直接的传续关系,而“阮咸说”虽有史料支撑,但似乎并不符合乐器发展的基本规律。
分析汉族弹弦乐器的两种起源说,可以推断两晋时汉族弹弦乐器的形制,已经分化为蒙皮无品和木质有品两类,其中,木质有品弹弦乐器(即阮咸)应视为蒙皮无品弹弦乐器的再发展。但与此同时蒙皮无品弹弦乐器并没有被取代,两类弹弦乐器并存于世。两晋以后,阮咸失传,“时人莫识”。直至武后时期,阮咸再次现世并伴随唐代音乐的繁荣进入了兴盛期,此时阮咸的乐器名称已经确定,形制也与琵琶有了明显区分。唐宋文献在梳理汉族弹弦乐器的定名与形制时,业已无法准确判别秦汉、秦汉子、秦汉琵琶、阮咸琵琶之间源流、形制的异同,这也反映了此前汉族弹弦乐器本身复杂的演变过程。及至宋代,随着民间曲艺的兴盛,阮先后受到音色相近的琵琶与月琴的冲击,再一次进入衰微期,汉族弹弦乐器由此进入以三弦为主体的历史新格局。汉族弹弦乐器在唐宋两朝的发展,反映了本土传统俗乐乐器在外来乐器的冲击之下,流变、衰微与再发展的完整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