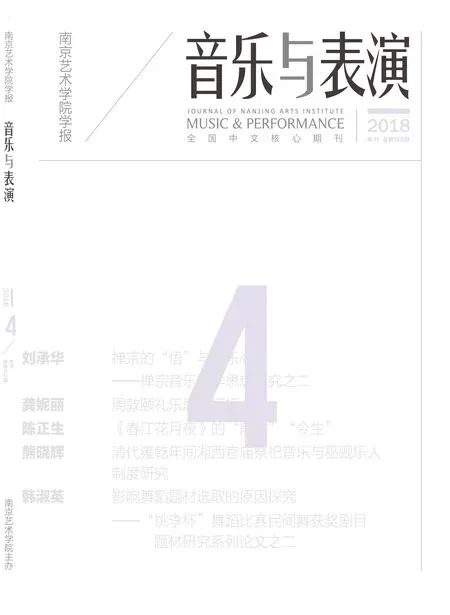民族器乐表达形式的继续大胆创新
—— 大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观后思考
2018-12-03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殷 沁(南京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自2017年7月起,中央民族乐团制作推出的大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拉开了全国巡演的序幕。此剧以玄奘西行取经的历史故事为题材,以民族器乐作为戏剧表演的核心,讲述了大唐高僧玄奘自长安西去天竺,历经磨难求得真经的故事。整个剧目展现了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乐器,以及敦煌复原乐器、印度民族乐器共七十余种,并且以多媒体、舞美技术建构历史故事场景的虚实空间,歌颂了玄奘不忘初心、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和舍身求法、普度苍生的执着信念。文化部部长雒树刚则称赞该剧是“讴歌‘一带一路’的力作,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是中华民族音乐的杰作”[1]。此剧首演至今已三十余场,受到各地观众的热烈追捧,可见这是一种契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民族器乐表演形式,它的出现为民乐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一、民族器乐表演形式的创新——民族器乐剧
《玄奘西行》表现了一个完整的戏剧故事,有清晰贯穿的戏剧主线,具有明显的剧情性和叙事性,曲目创作显示出更强的整体性,主题旋律的多次出现,起到有机的连接作用。而汉族、新疆、印度等民族乐器的争相亮相,更突出了此剧展示“民族器乐”的分量;服装、灯光、舞美、布景更加精美,堪称大制作。
作曲家姜莹首次跨界担任编剧、作曲和总导演,她对于“民族器乐剧”这一新形式的定义是“以民族器乐作为表演主体来讲述完整戏剧故事的剧种”[2]22。团长席强认为,这部民族器乐剧“打破传统民族音乐的表演形式,以玄奘西行取经路上对民族音乐的见闻为蓝本,将舞台表演和民族器乐有机融合在一起,通过演奏家‘音乐’和‘语言’的双重表述,以其高超的演奏、吟诵、台词对白、形体动作和剧情结合,融合舞美、多媒体、灯光、音响、服装等元素充分拓展艺术空间和推动剧情发展……”[3]14。指挥叶聪认为:“民族器乐具有极大的表现张力,对于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有无限潜力可以挖掘”[3]27。
器乐音乐能不能“讲”故事?通常说“讲”故事,都是用语言文字的方式,因为文字符号的意义可以更明确、更细化,我们好像不能完全脱离文字提示来讲清楚某一具象的事件。但正如指挥叶聪所言,器乐音乐有“无限潜力”,它也可以表达情节,它在“讲”故事时有它的优势。人们常说语言的尽头便是音乐的开始,观众作为接受者在聆听时,音乐的语义还在不断地延伸,它的不确定性会使人产生种种开放性的情感“解读”空间,从而延伸出更丰富的语义,表达语言“说不尽”的内容,这就是音乐叙事的优越性。观赏这部剧时,在音乐的音响作用与舞台的视觉效果下,我们的感官被同时触动引发视听联觉,在情境中产生更深入的想象和联想,加上语言台词的辅助,观众对音乐和戏剧的理解会更清晰明了,从而让人“听懂”剧情。
笔者试将“民族器乐剧”理解为以民族器乐音乐作为戏剧表演核心的新剧种,是民族器乐舞台表演的一种新形式。可看作是民族器乐与戏剧“跨界”结合产生的一种多元化的综合艺术形式,它不同于一些传统艺术形式,但博采了个中特点为己所用:与歌剧、音乐剧相比,削弱了语言的表情达意作用,更突出了民族器乐要素;与一般民族管弦乐、交响乐音乐会相较,则加入了故事情节、台词对白、肢体动作、灯光布景、多媒体等戏剧舞台因素,充分调动起观众的视听联觉,让音乐不仅“可听”,而且“可观”“可想”。
在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多元共存的时代,各种艺术形式的跨界会碰撞出新的火花,创作者们将民族器乐与戏剧结合,民族器乐剧这种跨界融合的表达形式便应运而生,从历史条件和思想政治因素等方面来看,这是历史化的必然,也是民乐发展的必然。
二、用器乐“讲”故事
那么《玄奘西行》这部民族器乐剧是如何用民族器乐“讲”故事,展示不同器乐的特色和人物间的戏剧冲突?从剧情、创作、舞台呈现、演员表演、音乐表现来看,该剧具有以下特点:
(一)剧情
这部剧的整体架构以音乐为主体搭建而成,全剧由“大乘天”“佛门”“一念”“潜关”“问路”“遇险”“极乐”“高昌”“普度”“雪山”“祭天”“菩提”“那烂陀”“如梦”“大唐”这十五个章节构成,简单来说也是由这15首乐曲组成。每一首乐曲不仅承载了剧情的发展,亦是个体完整的器乐作品。
第一幕“大乘天”是全剧的序曲,将人的目光带回1400多年前,呈现一代宗师玄奘带领众弟子吟诵《心经》的场景,象征其晚年为佛典事业做出的伟大贡献。第二幕“佛门”,青年玄奘在净土寺随师父念佛修行,八年后他坚定信念,踏上西天取经之路。第三幕“一念”,“一念心起,则有善恶二业”,胡人石磐陀最终在师父的点化下顿悟,战胜心中的邪念。第四幕“潜关”,玄奘因无通关文牒被守军抓获,面对震慑岿然不惊。校尉王祥以性命保其出关。第五幕“问路”,玄奘行至沙漠,前路漫漫。乐者以琴声指路,并劝他“凶多吉少,三思而后行”,玄奘言:“不到天竺,绝不东归半步”。第六幕“遇险”,玄奘行至沙漠深处,滴水未进,极度疲劳,逐渐失去意识,进入极乐幻境。第七幕“极乐”,净土庄严,佛光普照,天人奏乐。醒来时已在野马泉边,众佛之光助他渡过难关。第八幕“高昌”,高昌王喜迎法师、热情款待,乌孙王前来致谢,欢聚一堂,乐手奏乐助兴。第九幕“普度”,在玄奘的开导下,因思念母亲而失明的高昌公主解开心结,重见光明。第十幕“雪山”,冰封葱岭,玄奘在雪崩中遇险,记忆深处,吹着鹰笛的塔吉克族人赋予他超越自然的生命力量。第十一幕“祭天”,部落久旱,酋长欲向女神献祭活人祈雨,玄奘愿以身献祭。第十二幕“菩提”,菩提树下,引路人吹奏班苏里笛,只为等候和指引这位来自大唐的高僧,那烂陀就在前方。第十三幕“那烂陀”,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抵达佛国圣地那烂陀,在神圣虔诚的乐声中,那烂陀寺门缓缓开启。第十四幕“如梦”,玄奘在修得佛法真谛后,不忘初心,“贝叶传心语,应知如梦归”。第十五幕“大唐”,钟鼓齐鸣,普天同庆,一代宗师玄奘载誉荣归大唐。
(二)音乐创作:民族乐器的“拟人化”
为了让每件乐器在剧中充分发挥其特点又能契合人物个性,在不违背戏剧主线的前提下,主创者姜莹通过一些典型故事、典型人物的设计,表现了玄奘在西行取经途中历经的重重磨难和种种际遇。她以器乐的特点来设定人物形象、布局剧情,运用拟人、隐喻、借代等文学性的处理手法将民族乐器人格化。特邀指挥叶聪曾评价:“姜莹在这里头,用器乐来找到拟人化的办法,找到代表性的乐器来表现代表性的人物,我觉得是她的一个非常大的创举。[4]”
其中最主要的人物玄奘,一直演奏的是笛子。关于为什么设定笛子演奏家来饰演玄奘,姜莹在其“创作札记”中解释有两个原因:一、“‘笛子’是个笼统的称谓,其实还包含着小竖笛、萧、曲笛、梆笛、新笛等多种不同音色的乐器品种”,这样可以“用不同的音乐叙述方式去展现人物不同的心情特质”,“丰富的笛箫类乐器”为舞台上的各种表演调度“提供充分的可行性”。二、河南出土的贾湖骨笛距今已有约8000年历史,“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可以说笛箫是真正汉族传统文化的代表,相比拉奏二胡或吹奏唢呐,主人公在十万里西行路上吹起笛子更符合人物的气质和文化背景”[2]23。
例如,第二曲《佛门》中,笛箫的音乐对话也是师父与青年玄奘之间的角色对话。玄奘(丁晓逵饰演)最初在净土寺剃度出家、随师父(王次炤饰演)修习佛法,他曾在师父禅意的箫声中打开了精妙佛法的大门,坚定了西去天竺的初心。这段音乐描写的是玄奘在师父的教化下逐渐成长的过程,在音乐性格上突出了箫和小竖笛的音色对比,箫声深邃沉稳代表师父,竖笛声清亮代表玄奘,先是师父的独奏,而后箫与笛重奏,弦乐的和声衬于底部,之后逐渐加宽加厚使情绪层层推进,到乐曲高潮处,用G –D的近关系转调,自然地推动乐曲走向一个意蕴深长的结尾。全剧的主题曲也取自这段音乐,演出的尾声再次响起这样温情的旋律,回望西行之路,玄奘不忘初心、百折不挠的精神更加令人感动和回味。
“问路”一幕,玄奘在前路未知、顾影自怜之时,恰有一位遗世独立的仙人乐者(冯满天饰演)手拨阮咸。大阮的音色既厚重又通透,冯满天即兴色彩的演奏悠然从容,琴音似流水洗心,颇有几分仙人的气质。玄奘驻足倾听,闻琴音知心声;乐者以乐指路,琴如其人,他劝言:“倘若能找到野马泉,你便可活着出去。若是找不到,法师定要及时返回。”玄奘为求无上正法百折不回,在佛力加持下,每次路遇艰险皆能逢凶化吉。这个人物既体现“人琴合一”的境界,亦象征了佛法的慈悲示现,是一次主题精神的升华,具有多重意义。
(三)舞台艺术:抽象写意的东方笔法
戏剧舞台呈现具有高度抽象、虚拟化的特征,在中国传统的戏剧舞台中,除了必需的道具布景,戏剧空间和场景主要靠演员的唱词、念白、表演向观众交代。而现代舞台艺术形式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观众的视听审美经验已大大丰富,欣赏艺术作品的审美标准也在提高。著名舞美设计师张继文和中央美术学院数码媒体工作室的助力,为这部剧创造出立体多维的戏剧艺术空间,呈现出更丰富的视听效果。全剧十七个场景,玄奘从沙漠走到宫殿,从星空下走到雪山旁,从幻境走到现实,从长安走到天竺……布景设计运用中国传统美学结构的原则,舞台效果富有诗意禅意,美轮美奂。
多媒体动画、灯光、舞美、服装、音响的有机配合,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给剧情无限的延展可能,这是《玄奘西行》这部剧的舞台创新突破点。灯光的设计增加了舞台的灵活性和流动性,“潜关”中大功率染色的灯光渲染出“边关金汤固,风高战鼓鸣”的紧张氛围,光色光速的转换让戏剧的冲突更直观。进入佛国之后,大面积的金黄色暖光让人感受到神圣庄严的氛围。多媒体影像技术则拓展了舞台的虚实空间,扩充了舞台的叙事功能,是一大亮点。第六幕“遇险”中,多媒体制作的“风沙”投射于舞台纱幕,构建出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沙漠荒凉之景,玄奘在沙漠中艰难前行。幻影女奏起萨塔尔,苍凉的琴声穿透绵亘起伏的沙漠,十二木卡姆的歌声伴着玄奘独自远行的背影,直到远方;橘红色的明暗灯光下,人物与大漠融为一体。舞台像一幅流动的音画,诉说着西行之路的重重磨难和考验,让人如临其境。第九幕“普度”中,公主因为思念去世的母亲而失明,在玄奘的帮助下解开心结,恢复视力重见光明后,舞台上一朵朵蓝莲花在空中盛开,浪漫、意象化的多媒体动画效果烘托出人物情绪的变化,象征着公主由忧郁走向解脱,展示出传统的静态舞台无法达到的表现力。
从心理学角度看,持续的新事物的刺激充分满足了观剧者的内心期待。这样的舞台呈现,既服务于剧情的叙事功能,又不过于具象,保留了写意的舞台风格,非常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意境。将现代舞台技术和中国传统美学、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使得舞台效果更有张力,也给观众留下了艺术再创造的感受空间。从审美角度看,如此精良的制作,不仅吸引观众入戏、迷戏,也会逐渐改变观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观。
(四)“演”与“奏”:器乐表演融于剧情
演员们要将器乐表演融于剧情之中,用手中的乐器,在情境中刻画指定人物,不仅要展示高超的演奏技术,还需要台词、肢体、调度等综合的戏剧表演。执行导演金戈认为:“乐器在被设计过的情境中出现,音乐家们通过乐器与戏剧的表演来刻画人物,传达人物精神,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有着丰盈血肉的剧中人物,而不是跳出了戏外孤立存在的演奏者。用器乐演奏来表现戏剧,是舞台艺术形式的一个突破点。”[3]40
中央民族乐团一批著名演奏家:王次炤、丁晓逵、冯满天、金玥、赵聪、朱剑平、吴琳等都曾担纲主要角色,对于戏剧表演和器乐演奏之间拿捏的分寸感,饰演边关将军的打击乐演奏家朱剑平认为:“既要让观众领略器乐演奏所带来的视听满足感,又不能让演奏‘抢戏’‘出戏’‘跳戏’”,要“予演奏于无形”“予炫技于无形”[3]59。
对于将音乐融入剧情,演奏家牛建党认为音乐是抽象的,(没有剧情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和状态去想象。“但在演戏过程中则给了音乐一个情节,这时候对于旋律的处理要贴合剧情,这就加深了他对曲子的主动把控和诠释能力”,并且“演奏员要把个性藏在剧情框架中尽情表现”[3]86。
饰演青年玄奘的竹笛演奏家丁晓逵是“戏份”最重的,全剧15个章节,13幕都有他的出现,而且每一次出现人物都有不同表现,演奏上也不尽相同。而在“雪山”一幕中,玄奘孤身一人在多媒体制作的“狂风暴雪”中步履蹒跚、踉跄前行,这长达一分多钟的无实物表演,没有台词和演奏,只有肢体的动作,较好地演绎了青年玄奘对信仰矢志不渝的追寻,让人印象深刻。
多数演奏者充当了演员,精神可嘉,相比前两部民族乐剧来看,演员们在舞台上的“演”和“奏”已经驾轻就熟。但若以专业表演演员的严苛要求来看,台上演奏家们在配合的默契程度和台词对白等方面还略有欠缺,动作神态之间的互动交流还能更密切紧凑些,这样效果会更加理想。
(五)音乐呈现:整体性和多元性融合
《玄奘西行》的音乐呈现出整体化和多元化的特点,音乐之美令人如饮酣醪。作曲家姜莹的创作整体上延续了她以往的风格:抒情唯美,旋律可听性强。和声简洁,少有复杂的不协和和弦,声部线条清晰流畅,调式转换自然。同时发挥了写作西域特色音乐的功底,她曾经创作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丝绸之路》《敦煌新语》得到业内的广泛肯定。此剧中的《极乐》《祭天》《大唐》也体现了她对西域音乐风格的把握。音响结构注重通过配器的变化形成色彩对比,善用不同民族乐器的音色表现主题音调,通过增减音符、改变时值、调性处理等方法让主题旋律串联全剧。在诸多乐曲中都能听到主题音调的变形发展(部分谱例见下图):《一念》中低沉悲怆的胡琴、《极乐》中辉煌的敦煌乐器合奏、《遇险》中苍凉的萨塔尔…它作为乐曲内在的一条主线,增强了音乐曲目的整体感,达到个性与共性统一的艺术效果。
谱例1. 主题旋律

谱例2.主题变形1 《一念》二泉琴旋律片断

谱例3.主题变形2 《极乐》敦煌乐器合奏旋律片断

著名作曲家王洛宾曾说过:“丝绸之路是用音乐铺成的,在这条古道上,可以听到最美的音乐。[3]12”整个剧目展示了丝绸之路沿线的“73种不同类型的乐器”[2]27,除了汉族传统乐器外,还有新疆民族乐器、敦煌复原乐器、印度乐器等,让人应接不暇,并且请到当地的演奏家们来表演原汁原味的西域音乐,体现了音乐上的多元性。“高昌”一幕中,高昌王对玄奘景仰已久,热情款待。盛宴时恰逢乌孙国(今哈萨克族聚居地)国王前来道谢,便以乐相会。来自新疆的演奏家们分别solo展示了维吾尔族乐器弹拨尔、都塔尔、艾捷克、热瓦甫、萨塔尔、达卜以及哈萨克族乐器冬不拉和库布孜,复合的节奏、细密的音符传递浓浓的西域风情,充满一种节日的热闹气氛,与台下观众的互动也使现场情绪达到热点。“极乐”一幕中,演奏家们扮演仙人乐者,巧妙地展示了敦煌复原乐器的风采:莲花阮、五弦琵琶、龙凤笛、直嘴笙、葫芦琴……“菩提”一幕中,玄奘历经风雨险阻终于到达菩提迦耶,印度乐者在菩提树下吹奏班苏里笛,神秘空灵的笛声为他指引前行。“那烂陀”一幕中,印度僧人演奏着印度唢呐、萨朗吉、西塔尔、萨罗达、塔不拉鼓,在庄严神圣的仪式音乐中,玄奘身披红色袈裟虔诚地走向心中的目的地——那烂陀寺,印度乐器、人声、民族管弦乐队多种乐声交织在一起,玄奘向万佛朝觐的画面在此时定格,全剧达到一个精神的高点,执着追求的理想信念触动了观众的心灵深处。观众似是用听觉神游了丝绸之路绮丽斑斓的风光,领略西行朝圣之路的神秘魅力。
众所周知,玄奘西行取经的丝绸之路广袤多姿、光怪陆离,孕育了极其丰富和发达的音乐文化,也是多元民族文化交汇的平台。在整个剧目中,展示了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汉族、新疆、西域音乐、印度音乐多元碰撞,戏剧性的连接让这些音乐的呈现融合为一个整体,指挥与乐队的协作也起到整体性的融合作用。
三、民族器乐表演艺术发展的思考
今时今日,民族音乐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自信的窗口,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文化语境中呈现出以西方为主导的状态,而忽略了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民族音乐风格偏向西化、现代化,内容上常缺乏民族性,脱离了观众的审美趣味,难以引起国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共鸣。因而,新时代创作中民族音乐文化如何传承和创新?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玄奘西行》背后的文化意义
《玄奘西行》对观众来说,是一次令人目不暇接的音乐之旅,也是一次寻味厚重人文历史的文化之旅。回顾历史,汉代张骞出使西域,逐步打通了中国与欧亚各国的交通、商贸和文化交流通道,史称“丝绸之路”。公元628年,玄奘大师孤身一人踏上漫漫西行路,历经十七年,途经百余国,足迹所及贯穿西域、中亚。其行走路线主要沿丝绸之路的北道中道、南道(回程),也踏入过前人从未涉足的地域,《慈恩传》有云:“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得而载”[5],意为玄奘所到之处有张骞未曾涉足的,是司马迁、班固都没有记载过的。他和弟子辩机将西行的所闻所见著成《大唐西域记》一书,填补了印度古代历史记载的空缺,对于重建古代印度史有极高的价值,对考古学而言也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这部剧根据玄奘西行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虽然经过了艺术的提炼和加工,但从剧情中诸多细节可看出主创者对历史史实的尊重和制作的严谨。公元643年,玄奘学成回国,取回佛经657部,在人生余下的十九年岁月中潜心埋首翻译佛典,和助手们共翻译了一千三百余卷佛经。据历史记载,由金陵刻经处(今南京市内)汇集出版的玄奘译著全集就多达400册[6]。开场一幕“大乘天”中玄奘领众僧诵《心经》的场景,即是寓意晚年玄奘为译经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意义深远,许多译本至今仍是最权威的版本。剧中“潜关”一幕,边关士兵队阵的设计来源于唐太宗所绘的《破阵乐舞图》,配合雄壮威严的鼓声,加之灯光的明暗交错,营造出金鼓齐鸣、戒备森严的氛围。面对这样的震慑,玄奘却气定神闲、稳坐阵前,对比刻画其追求信仰的坚定态度。“极乐”中舞台设计则是还原了敦煌壁画《观无量寿经变》中的极乐世界景象,奇丽微妙、清净庄严,玄奘在沙漠遇险昏迷时入此幻境,众佛之光赋予他力量再次渡过难关。以上种种皆能体现作为“民族器乐剧”的匠心所在,在这样快节奏、娱乐化的传媒时代,中央民族乐团用两年的时间精雕细琢,尊重历史,不过度改编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二)民族管弦乐发展:寻找中国音色
自1919年郑觐文创立“大同乐会”以来,中国民族管弦乐至今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这百年也是不断探索传统及学习西方的漫长过程。西方管弦乐队讲究群组音色的融合,而民族乐器本身具有很强的个性,制作工艺、材料也难以统一,乐队的声音难以融合。音乐家们逐步对民族乐器的音域、音量、音色、音律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改良,民族乐队的整体性能得到明显的提高改善。在一代代作曲家、音乐家的努力下,民族乐队的曲目也渐渐充实丰富,积累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西方音乐一直在寻找自我价值,也在这种寄望和探索中不断发展,中国民乐要如何寻找中国音色?如何构筑民族化、个性化的音响?
1.乐队编制、乐器改良
在民族管弦乐发展之初,在乐队配置方面参照了西方的器乐特性,有人认为几乎是西洋管弦乐乐队配置的简单转换。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都在向西方学习先进经验,音乐界也出现了“欧洲音乐中心论”“全盘西化”的倾向,造成忽视自身民族音乐文化的特点,生搬硬套甚至削足适履的现象。但民族乐器本身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因为乐器结构、材质和演奏技术等多方面的因素,民族管弦乐团很难有像西洋交响乐队那样融合统一的音色,音响上不平衡、张力不足。
在民族管弦乐队中,低音乐器的缺乏一直是个大问题,民乐团体在乐器改良上做出了一些举措:1. 20世纪50年代,香港中乐团研制环保胡琴,使用革胡和低音革胡,逐渐被各民族乐团广泛采用。2.2013年,中央民族乐团委托乐器制作大师胡雪平研制了低音“胡”琴,是第五代形式的低音乐器品种。3.中央民族乐团研制的低音管和低音加键唢呐,弥补唢呐低音声部的不足。同时在乐队的配置上重新调整,增加低声部的乐器数量,增强中低音声部编制的比例。比如中央民族乐团在弹拨乐声部加大中阮、大阮的比例,管乐声部增加中音、低音加键唢呐和中音、低音键笙的使用[7],改善声部间的音响平衡,使音色协和、音量增大、音质统一。
通过改良乐器、调整乐队编制后,民族管弦乐队在保留音色特点的基础上,乐器性能得到提高,整体音色更融合、群体音响更立体饱满,更适应表现新时代的管弦乐作品,增强了艺术魅力,取得了良好的收效。
2.配器
中西方音乐生长的土壤和背景不同,民族传统音乐在结构布局、旋律发展、音色运用、律动形态等方面都有它独特的审美思维。当然不能一味西化,实践证明了西方作曲技术并不能替我们完美解决五声性的问题,和声也不是中国传统的音乐典型构建方法,配器理论也是从西洋管弦乐队长期的实践中发展而来。我们可以借鉴西方,但如果全盘照搬就会“水土不服”。
民族管弦乐还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有待探索和解决,比如音响上,西方管弦乐队讲究群组音色的融合,乐队的高中低声部均衡有力。而民族乐器的音色本身具有很强的个性,制作工艺、材料也难以统一,乐队的声音难以融合。音域上高音乐器品类少,高音区整体音响音色衰减,所以到乐曲高潮处常依靠打击乐、吹管乐的强烈音效“撑起半边天”,造成高音区的表现张力不足,音响浑浊失衡。以西方音色的融合观来看,这是“先天不足”的地方,但民族打击乐、管乐具有极为个性的音色,在表现中国民族音乐韵味上有它不可替代的色彩作用,如果一味地改造它,会抹杀民族乐器的个性。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借鉴西洋古典浪漫派作曲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管弦乐,可以试着摆脱西方交响乐团的模式来审视中国民族乐队的音色构建,思维上不局限于西方的和谐观念。因为追求音色的多样性和个性是民族音乐的传统,它符合民族乐器的特性,也适合中国听众的审美需求。运用作曲配器技术凸显民族音乐特有的音色,让民乐器之间产生更深度的关系对话,从而形成音乐色彩上的丰富变化,而不是舍弃或回避一部分的音色效果来追求一般性的融合。配器产生的乐器音色组合的实际效果,是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这考验的不仅是作曲家的技术,还有对民族乐器特性的把握和音乐审美意识的取向。
关于民族管弦乐发展的探索仍然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在亦步亦趋地模仿和学习后,现代作曲家们逐渐将交响化的思维结合民族器乐的个性特质,不断“实验”出新的“化学反应”,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音乐语言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8],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结 语
《玄奘西行》集结了国内顶尖的制作团队和庞大的演员团体,表现出其一流的专业水准,它大胆创新的表演形式、拟人化的音乐创作、抽象写意的舞台艺术、丰富多彩的音乐呈现,都让人获得美的享受。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可改进之处,笔者认为,台词是传达剧情的桥梁之一,但在音乐与多媒体舞美等多重艺术的共同刺激作用下,有些对话和解说可以省略,也许用音乐“诉说”加上整体舞台环境的视觉辅助,用间接地暗示戏剧的发展方式,会更加耐看。期待由音乐启发出的心灵沟通与互动更多一些,适当地运用却不于依赖视觉和语言。此剧整体的定位考虑了大众的审美取向和市场效益,具有通俗化和娱乐化的趋向,对于有些专业音乐人来说,这样的演出不像音乐会形式那样“严肃”,稍显“热闹”一些。当然,它宏大的场面、现代化的视听方式带来艺术的感染力,家喻户晓的故事人物、中国民族文化和熟悉的地域音乐使它更具有亲和力,这是它受到观众喜爱的原因。
不可否认,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再一次拓展了民族器乐的表现空间和表现力,是民族器乐舞台表演形式的一次新的探索和实践。笔者认为对民乐表演形式的探索是源于对民乐发展道路和大众艺术审美模式的反思和探索,随着时间推移新的形式还在不断地产生,对民族器乐的艺术定位和创作路线问题仍然众说纷纭。一部新作品要想保持旺盛长久的艺术生命力,需要经过观众市场的检验,通过音乐界学者专家的评价探讨,通过不断磨合,不断完善,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才能使之具备成为高标作品、经典作品的客观条件。期待中央民族乐团继续保持创新的势头,推出更多更好的民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