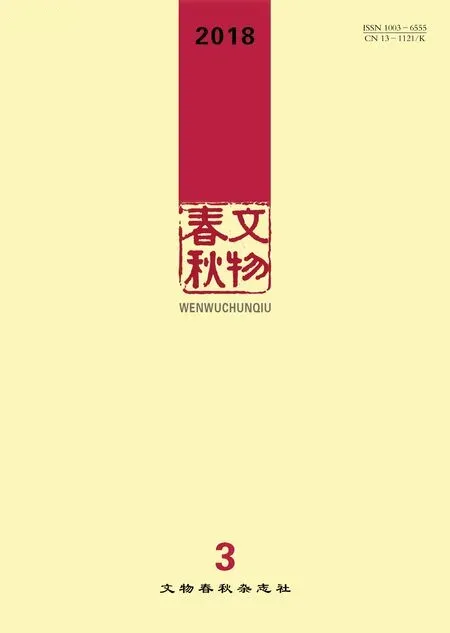吴简“折咸米”“备米”补论
2018-01-24赵义鑫
赵义鑫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出现的“折咸米”一词,在传世文献中并无记载。王子今先生最先对“折咸米”进行解读,认为“折咸米”即是“折减米”,其出现的原因在于仓储损耗[1]75—80。王文主要目的在于解读“折咸米”的含义。侯旭东先生进一步指出仓米的损耗是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出现的,并认为“备……米”的简牍与其具有同样的性质,是对吏职务过失的责任追究[2]176—191。熊曲先生则通过对比,认为“渍米”和“没溺米”也具有“赔偿”性,进而赞同“备……米”是责任追究的体现[3]211—225。总体来看,前人主要是从“折咸米”的性质入手进行探究,而对于简文中其它信息的解读尚不透彻。本文则主要从“折咸米”簿书格式复原入手,对“折咸米”的征收过程进行探讨,并且通过对“备米”简含义的重新解读来讨论责任追究的观点。
一、“折咸米”入米格式复原与研究
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叁)》中出现了以乡为单位征收“折咸米”的现象:
5.右平乡入船师张盖折咸米十四斛二斗(叁·3689)【注】“右”上原有墨笔点记[4]804
6.入平乡船师张盖折咸米十四斛二斗|||*嘉禾元年九月五日尽丘番池付仓吏谷汉受 中(叁·3710)[4]804
7.右诸乡入船师□□张盖折咸米一百一十三斛九斗九升四合(叁·3759)[4]806
根据侯旭东先生对三州仓“入米簿”的复原[5]1—13,在以上这几枚简中,简 1、2、3、6 和 8均以“入某乡”开头,应是个人分次缴纳“折咸米”的记录;而“同一乡之同类米的收据依交纳的时间先后由右向左编排在一起,每天做一统计,附一简注明‘右某乡入某种米多少’”[5]8,可知简4、5、7分别是东乡、平乡和临湘侯国(县)的“折咸米”总计简。侯先生指出,“仓吏将诸乡所入某种米的记录逐日汇制成诸乡的入米簿后,还要按照‘米’的性质分类汇总成
诸乡入某种米’”[5]6。
根据这些简,可将“折咸米”簿书的格式复原为:
A.入某乡(或某乡入)+船师○○(姓名)+折咸米○○(数量)|||*缴纳时间+○丘+具体缴纳人+仓吏○○(姓名)受 中
B.右某乡入船师○○(姓名)+折咸米○○(数量)
C.右诸乡入船师○○(姓名)+折咸米○○(数量)
这应为单独征收“折咸米”的簿书所记载的内容,其与其它米的征收记录不同之处在于,其它米由于入米数量多,应是以日账的形式记录,而“折咸米”属于非正常的征收项目,且数量有限,因此不用逐日统计,只需要进行一次总计。
另外,“折咸米”的记录还会出现在每年田赋征收的总计中,以分账的形式出现:
10.其六十七斛九斗五升船师张盖建安廿六年折咸米(叁·4399)[4]820
11.其六十七斛九斗三升船师张盖建安廿六年折咸米(叁·4701)[4]826
12.其六十八斛九斗六升船师张盖建安廿六年折咸米(叁·4704)[4]826
以上以“其”为起始的结计简与其它的入米总计简应为一册簿书,这只是其中的一项,因此并不属于“折咸米”入米簿书中的内容。
从复原的“折咸米”入米簿书格式来看,“折咸米”应当是以乡为单位征收的,而这些征收来的米都是以“船师张盖”的名义入账,也就是用来弥补张盖在运输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失。由此可知,在征收“折咸米”的问题上,并非仅仅由造成损失的船师个人负责,而是由各个乡分别承担一部分责任,至于主要缴纳者,当然是以各个乡的吏民为主:
14.入吏番观所备船师何春建安廿七年折咸米四斛(壹·2277)[6]941
15.其一百五十斛九斗故吏番观所备船帅张盖建安廿六年折咸米(柒·2078)[7]778
16.其五斛八斗故吏潘虑备船师张盖建安廿六年折咸米(捌·2950)[8]722
【注】“其”上原有墨笔点记
18.入吏周唐备船师张盖建安廿六年折咸米四斛(捌·4532)[8]761
熊曲先生在分析简14时认为,“吏潘观不是偿还船师何春应交的折咸米,而是他在其工作职责内造成了何春交的折咸米的损失或产生了误差,于是需补齐那部分”[3]223。对简14单独做这样的解读或许可以,但是如果结合其它简来看,这种观点就值得商榷了。简17中明确指出备“折咸米”的是“吏民”,也就是说“吏”和“民”都承担了这项米的缴纳;由于简17为结计简,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之前的分计简中应该有“吏”和“民”分别缴纳“折咸米”的记录,因此普通的民众也缴纳了“折咸米”。而根据王子今先生的研究,“在米粮储运过程中会发生‘折咸’现象”[1]80,不管是储存还是运输粮食,这一过程都与普通的民众没有直接联系,所以从逻辑上来说“民”没有缴纳“折咸米”的责任。但是,在现实中民众也缴纳了“折咸米”,这就说明“折咸米”的征收并不一定与造成损失的个人有关。
其次,从简16来看,仓吏潘虑也交了“折咸米”。而从潘虑被称为“故吏”来看,其所缴纳的“折咸米”的入账时间应在其卸任之后。经过排查六册走马楼吴简中的“入米簿”竹简我们发现,潘虑作为仓吏出现的时间均在嘉禾二年(233)十月之后,那么,其成为“故吏”的时间应更晚于此时。因此,从时间上来说,“故吏潘虑”与建安廿六年(221)的账目无关。
由以上分析来看,笔者认为,在简14中出现的“潘观备折咸米”,并不是潘观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而缴纳的米,而应当是潘观在一段时期内担任了征收“折咸米”的工作。
19.其一百一十五斛负者诡课贫穷无有钱入已列言依癸卯(贰·180)[9]720
20.其六十八斛九斗七升负者见诡课贫穷无有钱入已列言依(贰·186)[9]720
这两枚简中的“诡课”即“督课”之意,魏斌先生认为,这种对于逋欠的催征“仍然要由经办吏根据法令去执行,并最终以文书的形式呈现出来”[10]194。虽然“折咸米”与“逋欠”有很大的区别,但同样由“吏”来征收应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吏”对于米粮的征收负有“督课”的责任。因此,在这一时期内潘观所征收的“折咸米”都是以他的名义入账,而之后标明“船师何春”则表明这是为了弥补何春的过失。这一点在简15、16中也可以看出。简15为结计简,记在潘观名下的米有一百五十余斛之多,这显然不是潘观个人所能承担的,应是以潘观为名义的总计。在简16中,此前已述潘虑与建安廿六年的账目无任何关系,这里仍然将这笔入账记在他的名下,应是因为这些米是潘虑征收来的,所以即使其已卸任,成为“故吏”,这些米仍然以他的名义入账。
当然,征收“折咸米”的吏的姓名在吴简之中并不属于必备内容:
【注】“其”上原有墨笔点记
从这几枚简来看,“折咸米”的征收只是在意于最终的结果,只要在数量上足够就可以了,至于由谁来征收则并不重要。但是,在这类简中,有些内容是必须存在的,那就是船师的姓名。我们由此也可以判断船师应是“折咸米”缴纳的直接责任人。
综上所述,“折咸米”的征收过程大体如下:首先,在粮食储存和运输过程中产生了损耗,在确定了损失的具体数目后,由临湘侯国(县)指派吏在各乡进行征收,而各乡吏民要承担“折咸米”。在征收“折咸米”的过程中,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其在计入总计时并非必备因素,因此有时在简文中可以省略。
二、“备”米与赋税
除了“折咸米”之外,在吴简中还有很多被学界认定为具有“赔偿”性质而征收的项目:
26.其卅七斛吏谢韶备黄龙元年吏帅客限米(柒·13)[7]731
29.其五十一斛州吏张晶备黄武六年适客限米(捌·3062)[8]724
这类简的共同特点在于其中都有一个备”字,我们暂且将这类简称为“备米”简(在折咸米”类简中也常出现“备……折咸米”备……没溺米”或“备……渍米”等,但其可明确属于赔偿性质的米,因此不属于本文“备米”简的范围。本文所论“备米”是与征收赋税拖欠相关的记录)。
侯旭东先生指出,“‘备’作‘偿还’解,……作为动词的‘备’亦包含补足数额的意思,确切地说是指因未达到应有的数额而偿还补足”[2]187,因而也将这些入米记录归入“折减”的范围内,并认为:“各种‘吏’均为官府承担一定的工作,‘备’则是对他们职务行为过失的补偿。”[2]189笔者认同侯先生对于“备”字具有“补足数额”的含义的解释,但将“备”解释为“赔偿”,进而作为“职务过失的补偿”却有不妥之处。
蒋非非先生认为:“‘备’常用义为‘备具’,指达到或完成某项额定标准……秦汉至孙吴追究官吏财务过失的行政行为称‘负偿’,即责任人赔偿官物,略写为‘负’。”[11]119—120也就是说“备”字和“职务过失补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蒋先生最后认为“‘吏某所备’应是吏某向其管辖的吏民纳税人征收、收纳某项税收及专项费用,仓吏记账时亦标明该项进账额具体用途”[11]119,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蒋先生所选用的只是和“师佐”简有关的材料,并不能概括这一类简的一般性质,但其关于“备”与“负”的辨析是可取的。如果要对吏进行“责任追究”,那么其入米项应列为“负”,而非“备”。而吴简中出现的“备米”类简,所对应的应该是另一种情况,笔者认为这是对拖欠赋税的征收。这在吴简之中有所反映:
这枚简出现在采集简第24盆中,同盆的简共854枚,为叁·1313—2166号[12]。这800余枚简绝大多数为出入米的账簿,在内容上关联性较强,为同一簿书的可能性较大。这部分简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正常的赋税出入米以及“折咸米”“没溺米”“备米”和“还贷”米。其中“没溺米”和“还贷”米的简如下:
31.其三斛民还黄龙元年吏帅客旱限米(叁·1359)[4]747
32.右西乡入民所贷食米一斛五斗(叁·1402)【注】“右”上原有墨笔点记[4]748
33.入船师张睦备没溺三州仓嘉禾元年叛吏限米卅斛(叁·1849)[4]759
以上各类米与简30的“逋租”相关联者,应该就是“备米”记录。因为其中的“没溺米”与“折咸米”属于同一性质的米[3]211—225,而“还贷”米从字面意义看,似与“逋租”有一定的关联,广义上来说都有“债务”的含义,但两者在史书中的用法却是不同的。《汉书》中汉武帝“元朔三年(前 126)诏书”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诸逋贷及辞讼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皆勿听治。”颜师古注曰:“逋,亡也。久负官物亡匿不还者,皆谓之逋。”[13]169而“民田租逋赋贷,已除”[14]191,颜注作“逋赋,未出赋者也。逋贷,官以物贷之,而未还也”[14]192,将“逋”当作修饰“赋贷”词来解释。但笔者认为,这里的“逋”和“贷”应该是两个并列的词语,“逋”用于修饰“赋”,而“贷”则单独使用,表明这里除的是“民田租”“逋赋”和“贷”三项内容。这种表述在《汉书》中十分常见,如建始三年(前30) 三月,“诸逋租赋所振贷勿收”[13]306,“逋租赋”与“贷”是并列关系。前引汉武帝诏书称“诸逋贷”,说明其免除征收的内容不只一项,应是所有“逋租宿债”全部免除,这样才能与“赦天下,与民更始”相对应,如果按颜注将其理解为一个词语,那么“逋贷”之中是不包含“逋赋”的,那与前文的“诸”和“与民更始”就无法对照了。因此,笔者认为,“逋”和“贷”属于两种不同的“债务”形式。“逋”是纳税人无力缴纳当年的赋税而形成的拖欠,“贷”则是从粮仓中调配物资借给有困难的百姓。
“逋”和“贷”的这种区别在东汉三国时期也依然存在,建武二十二年(46)诏书记:“其口赋逋税而庐宅尤破坏者,勿收责。”李贤注:“逋税谓欠田租也。”[14]74由此可知,“逋税”确有“债务”的含义,但与“贷”是截然不同的。从安帝永元四年(92)诏“除三年逋租、过更、口算”[14]214也可看出此点。孙吴赤乌十三年(250)“诏原逋责,给贷种粮”[15]1148则将“逋”和“贷”对举出现。
所以,在吴简中,“还贷”米和“备米”应该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记录。而与简30中“逋租”相对应的当是“备米”:
36.入军吏谢□嘉禾□年备□钱米九十二斛(叁·1870)[4]760
38.入吏邓佃番端备夷民嘉禾元年粢栗准入米三斛九斗□升(叁·1926)[4]761
40.入吏免昂嘉禾四年备嘉禾元年品布贾米四斛(叁·2004)[4]762
41.入船师张睦备所运……元年私学限米……(叁·2013)[4]763
而在《三国志》当中也可以看到孙吴的“赋税拖欠”现象。嘉禾三年(234),孙权下诏:“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逋,勿复督课。”[15]1140即在嘉禾三年之时,免除了当时吏民所拖欠的赋税。
由此来看,孙吴当时确实存在有赋税拖欠的现象,即孙权诏书中的“诸逋”和吴简中的“逋租钱”。而吴简中所记录的“备”税米、租米和限米的情况,应该就是事后对拖欠赋税的征收。其完整的格式应该如简25所示的那样,为:
入某乡+吏○○(姓名)备+最初的拖欠时间+拖欠的项目+数量 缴纳时间+缴纳人+邸阁○○付三州仓吏○○受 中
这里的吏应该也只扮演了征收者的角色,即孙权诏书中的“督课”者,而缴纳这些米的还是拖欠者本人。当然,这种格式应是其完整的形式,在实际执行当中,有些内容或可省略[10]188。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类“备米”简是对拖欠赋税的征收记录,并非对于“折减”的赔偿。其所入的物品都是国家的正税项目,包括米、钱、皮等等。而其由产生到征收的过程大体如下:在缴纳国家赋税时,由于种种原因,缴纳者不能按时上交足额的物品,因而被当时的仓吏(或库吏)按时间和米(或其它)的类型记录下其拖欠的数额,这样就形成了史书中的“逋租”;当缴纳者有能力补交时,则将其交给负责此项“逋租”征收的吏,然后由吏按实际缴纳的时间记录其补交的赋税种类和数额。如此,就完成了拖欠赋税的征收工作。
在上述这一过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吏在征收“逋租”的过程中,实际扮演了“督课”者的角色。由此可知,史书中频繁出现的“督课”任务的实际承担者应当是“吏”。再者,对于赋税拖欠者来说,其所欠的“逋租”属于国家正税,除非有免除逋租的“诏”或“书”下达,否则即使无米无钱缴纳,其账目也要保留。从简25来看,其中的五年应是指黄武五年(226),而其实际征收时间在嘉禾二年(233),也就是说这笔赋税一直拖欠了七年之久才得以还清。孙吴赋税账目记载之详细,可见一斑。
三、余 论
“折咸米”作为一项具有赔偿性质的米,其自然是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但是,对于这项损失的赔偿却并非由“事故责任人”独自承担,而是由临湘所辖诸乡分担。这在制度上应该也是合理的。船师运输时的损耗,直接造成了州中仓(郡仓)的损失。而对于州中仓来说,他们并不在乎这一部分损失具体是由哪个人所造成的,而是将这笔账都算在三州仓(县仓)头上。而三州仓作为县属机构,当然可以在辖下诸乡进行责任分配。然后,以乡为单位征收“折咸米”。由于材料所限,对此问题本文只能探讨至此。
从“折咸米”的具体缴纳数量来看,对于个人的负担其实并不是很重。按简7,诸乡共交米一百一十三斛九斗九升四合。根据蒋福亚先生的估算,“临湘的平均亩产在2~2.7斛米之间”[17],这是原粮经过加工的结果。要缴纳上述的米,大约需要耕种42~57亩土地。因此其分担到各个乡之后,诸乡的负担应不是很重。当然,这毕竟不属于正常的赋税收入,因此吴简对其入米记录十分有限,有时候格式也不甚严格。
除“折咸米”之外,其它记有“备”的入米等项目,应是对吏民所拖欠的正常赋税的“督课”,并非是对“折减”情况的赔偿。因此,其与折咸米”的性质大不相同。后者说到底应该是正常的赋税征收,只是缴纳的时间滞后了而已。而“折咸米”则是正常赋税之外的负担。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折咸米”简和“备米”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古代,无论太平盛世还是战乱分裂,在各个政权中几乎都会存在粮储损耗和赋税拖欠现象。而后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突出,因而史书之中经常会出现“逋租宿债”这样的词语。而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得知对于“逋租宿债”的处理方式和征收过程,只能看到皇帝一次次下诏免除这些债务。但是吴简“备米”简的出现,则弥补了这一史学空白。“折咸米”简的出现,也让我们得以知晓在处理粮食损耗时,官府如何将损失转嫁到吏民身上。当然,从这些项目的征收过程来看,吏在古代生活中具有十分突出的作用,是下层工作的实际承担者。
[1]王子今.走马楼简“折咸米”释义[M]//何双全.国际简牍学会学刊:第三号.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
[2]侯旭东.吴简所见“折咸米”补释:兼论仓米的转运与吏的职务行为过失补偿[M]//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吴简研讨班.吴简研究:第二辑.武汉:崇文书局,2006.
[3]熊曲.吴简折咸米、渍米、没溺米及相关问题[M]//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吴简研讨班.吴简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
[4]长沙简牍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5]侯旭东.长沙三国吴简三州仓吏“入米簿”复原的初步研究[M]//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吴简研讨班.吴简研究:第二辑.武汉:崇文书局,2006.
[6]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7]长沙简牍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柒[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8]长沙简牍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9]长沙简牍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0]魏斌.“原除”简与“捐出名簿”[M]//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吴简研讨班.吴简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
[11]蒋非非.走马楼吴简师佐及家属籍注记“见”考[M]//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吴简研讨班.吴简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
[12]宋少华.长沙三国吴简的现场揭取与室内揭剥:兼谈吴简的盆号和揭剥图[M]//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吴简研讨班.吴简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1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5]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6]蒋福亚.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