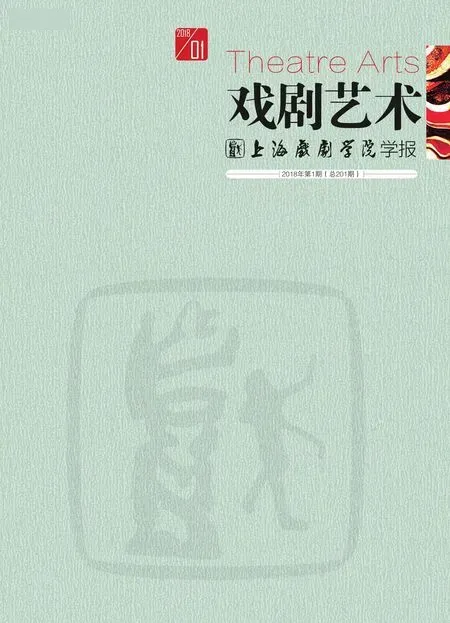话剧在清华:以《清华周刊》(1916-1937)为中心
2018-01-24
学术史的简要回顾
清华大学①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学界关于清华大学话剧活动的研究及成果大体在三个维度上展开。
其一,清华校史。此类研究多将话剧作为清华校园文化之一部分,苏云峰、黄延复可为代表。苏云峰对话剧在清华的情况作了分析,列举了“游艺社”“高二级戏剧班”等文艺社团的情况(苏云峰273-274)。黄延复所著《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专设“清华戏剧”一节,对以清华戏剧社为中心的话剧活动脉络作了较清晰的梳理和分析,把清华戏剧分为典籍和酝酿时期、复兴与繁荣时期、极盛时期等三个阶段,并指出各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为洪深与闻一多、李健吾、曹禺(黄延复469)。
其二,话剧史。有多部话剧通史提到清华的话剧活动,如葛一虹先生主编之《中国话剧通史》即认为,“清华学校的业余演剧也很有成果”(葛一虹 38)。田本相先生主编之《中国话剧艺术史》则对王文显、洪深等清华话剧人的活动作了论述(田本相 333-336)。最重要成果则为龚元的《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清华传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把话剧的“清华传统”描述为话剧史论上的现代建构、话剧内涵上的人性探求、话剧资源上的欧美取向、话剧教育上的专业本位(龚元27-39)。
其三,人物和作品。清华为中国话剧贡献了一大批话剧人和作品,其中不乏名家名作。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最丰富的。洪深、曹禺、李健吾等自不必说。王文显、顾毓琇以及闻一多等人的话剧活动也受到一些学者关注,田本相、阿鹰编著的《曹禺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张健的《中国最早的大型英文剧及其作者王文显》(《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马明的《王文显与中国话剧》(《艺术百家》1997年第3期),陈国和的《闻一多与中国现代戏剧》(《闻一多殉难6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等于此颇有建树。此外,在史料整理方面,张玲霞的《1911-1949清华戏剧寻踪》(《戏剧》2001年第3期)和《论清华大学早期的文艺社团及其刊物》(《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等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上述研究成果无疑为了解清华话剧活动概貌提供了便利,但现有研究多以中国话剧史叙述脉络为参照,从清华史料中为话剧史论断找证据,故往往聚焦于话剧史上已有定论的人物与事件,实际上,若充分阅读史料,转以清华话剧发展自身脉络为线索,即将视角从“话剧史上的清华”转到“话剧在清华”,又可发现一些值得重视的史事,对20世纪前期我国的话剧活动也可获得一些新的认识。《清华周刊》是清华校史上学生主办的最重要的刊物,创刊于1914年3月,至1937年5月共出版676期。抗战全面爆发后停刊。1947年2月复刊后,出17期再次停刊。作为清华历史最久、影响很大的出版物,《清华周刊》保存了许多宝贵史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清华话剧活动的情况。有鉴于此,本文以《清华周刊》及其赠刊为基本史料,对抗战前清华话剧活动作出全景式描述,以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话剧的发展、流变及特色,亦或有裨益于当代校园戏剧之发展。
并非仅有几朵“黄金灿烂的花”
目前可见比较全面地总结清华话剧活动的最早文章,应是1936年发表于《清华周刊》的《戏剧在清华》,作者写道:“戏剧在清华,不但有悠久的历史,还开过黄金灿烂的花。”文中提到了洪深、李健吾和曹禺,对“前辈们”表达了敬意,同时也指出清华的话剧具有“竞赛式”特点,是纪念日或欢送会上的“点缀”,“临时拉夫”“每级来一个”,缺乏专业精神。“戏剧在清华,一直是漫无秩序的发展的。历史上虽留下了几粒闪耀的金星,但始终是被沉闷的黑夜侵漫着。”(贝珍61-62)
揆诸史实,这一评判或过于苛求,话剧在清华,不仅有几朵“黄金灿烂”的花,而且是颇成气候的文化风潮。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
其一,剧目丰富,颇有声势。1922年4月,清华出版过一本专记学生生活的书《清华生活》,书中把清华学生生活分为12个“派别”,爱好话剧者被归入“文艺的生活”之中。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易卜生、萧伯纳的戏剧看得不少了,就决计自己要尝试一番。起了一次稿,一年后却又毁了重新作起,这样才看得见一个剧本。也有看人家作得热闹而仿行的。趁着一股热气,在三四天以内也许就赶了一篇出来。隔了几个月再修改,所费的时间恐怕不在三四天以下。剧本可以发表了,编剧的人觉得很可庆贺的。有时候编剧的要把自己的创作排演起来,虽然选择角色、练习对话,煞费苦心,然而不惮精力地作去,希望秩序单上编剧人同排演人底下可以省得多印一个另外的文字。”(黄延复189-190)中国话剧诞生于1907年,六年后,清华就有了话剧活动。从1913年起,以年级为单位,清华学生在圣诞节、除夕、新年等节庆期间经常举行丰富多彩的话剧演出。据统计,仅1913-1920年,清华有记载的演剧达到77次。演出最多的1914年,从年初演到6月,年底又大演一番,全年共演了19场(张玲霞 43)。因史料不全,准确统计清华话剧演出场次无法做到,但仅就现存的《清华周刊》中可查证者言,曾在清华校内演出过的话剧剧目在五十种以上。而且“清华之戏剧素称发达,屡次在校内外排演各戏,成绩昭著”(“戏剧社”17),颇受社会关注,时常有名流来校“捧场”。1916年,洪深的《贫民惨剧》在校内礼堂演出,北方另一话剧重镇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亲率70余名学生前来欣赏(“演剧志盛”14-15)。1916年12月30日晚,清华举行戏剧比赛,高中两科各演一剧,历时三个小时,观众六百人,天津南开学校张仲述(张彭春)、盐务署张柳池、交通部赵简廷担任“裁判员”(“戏剧比赛”18-19)。1917年4月13日晚,清华学生在北京青年会演出《都在我》,时任外交部参事刁作谦任主席,中西士女来观者600余人(“游艺社在京演剧”25)。次日,由王正廷任主席,观客达八百余人(“在北京青年会排演”26)。北京青年会召开新剧音乐会,也邀请清华学生演剧助兴(“演剧志盛”12)。这也反映了清华话剧活动在当时的社会影响。
其二,参与者众,覆盖全校。今天谈及清华话剧活动,人们多想到洪深、曹禺、李健吾等话剧名家,实际上,在当年的清华园,话剧并非“小众”爱好,而是参与面极广的校园文化活动。以洪深的《贫民惨剧》为例,1916年2月26日、3月4日在京演出时,演职人员表上除洪深外,还有闻一多、张光圻、陈达、刘崇鋐、汤用彤等多人(“贫民惨剧说明书”15)。在其他演剧活动中,还可以看到施济元、吴宓、吴文藻、苏宗固等的名字。1919年,游艺社改组为“新剧社”,编演部总经理为闻一多、编剧主任叚茂澜、演剧主任张祖荫、总务主任吴泽霖、化妆主任王世圻、布景主任程绍逈(“清华新剧社纪要”18)。这些人中,吴宓、闻一多日后成为文学家,吴文藻、陈达是社会学家,吴泽霖为民族学家,刘崇鋐是历史学家,汤用彤是哲学家,苏宗固为政治学家,张光圻、张祖荫为建筑学家,施济元为经济学家,程绍逈为兽医学家,王世圻则长于机械工程学……可以说,离开清华之后,他们的人生与话剧再无太多瓜葛,但在清华求学时却都是话剧的拥趸。除学生外,清华校领导、老师包括校工也浸润于话剧文化之中并推动其发展。清华副校长赵国材亲自指导学生话剧社团 (“游艺社纪事”22),不但为学生撰写剧本,而且邀请学生到家中辅导其排演(“排演新剧”20)。国学院导师赵元任担任导演,排演丁西林的《一只马蜂》(“戏剧社”820)。王文显指导高等科三年级排演英语剧《李代桃僵》(“高三演剧”19)。更有意思的是,一位名叫“赵云田”的工友“常写戏剧,除夕曾公演其‘处女作’《媒婆》于大礼堂,深为一般人所赞叹云”(“清华文风日昌”57)。而且,《媒婆》的编剧、导演均为赵云田,且演员全系工友(“庆祝新年游艺大会志略”60)。
其三,自成体制,井然有序。清华的话剧活动并非个体自发的举动,而是依托于一套秩序井然的组织体系,“年级”和“社团”是两大组织主体。演剧的“由头”则可分节庆与募捐两类,其实这也是社会上早期话剧演出的“由头”(朱双云 48-55)。每逢新年、国庆、校庆、圣诞节等各种庆典集会,清华一般都会组织演剧活动。1918年除夕,游艺社在体育馆演新剧两出。“一曰鸳鸯仇,剧情悲恻,演作诸君尤能体贴入微,备极妙肖。一曰黑狗洞,则诙谐百出,令人捧腹不置矣。”(“演剧志盛”3)1920年国庆典礼,学生会排演了《希望》(“国庆预志”34)。1921年,清华建校十周年纪念,分别排演了中、西文话剧(“十周年纪念纪事”26)。1921年圣诞节,排演了《Van Dyke》(“演剧汇志”23-24)。1923年4月28日,校庆纪念,戏剧社演出了《父之归》(菊池宽)和《喜相逢》。法文班则演出法文剧《虚荣毒》(La poudre Aux Yeux),这也是法文剧头一次出现在学校,“全剧共二幕,每幕约有十景。此剧即为现法文班所用之教材。”(“周年纪念预祝”25-26)1928年校庆纪念,又演出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戏剧社”820)。演剧活动的另一动因是募捐。1916年,为解决贫民小学创办经费,“特定校外募捐办法。于二月二十六及三月四号两晚。假座北京青年会演剧。入场券每张一元。青年会及本校均有出售。”(“演剧筹款”18)演出剧目为洪深的《贫民惨剧》。2月26日晚八点开演,演前先由张光圻致辞,“述演剧之用意”,然后由洪深“述贫民惨剧之梗概”。正式演出前,先演了“趣剧”《卖梨人》。休息十分钟后,开始演《贫民惨剧》。“剧分六幕。幕各分引正二段。描写贫民状况。形容尽致。又及家亡人散之惨。观者甚众。咸为动容。若亲历其苦境然。拍掌赞赏不已。概实有关世道人心之剧也。”(“贫民惨剧说明书”15)3月4日,第二次演时,张光圻致辞,陈达叙演剧之宗旨。然后洪深介绍剧情。这一次是先演《贫民惨剧》,后演《卖梨人》。“是晚虽狂风怒号。而来观者络绎不绝。可称盛会。”(“演剧再志”12)1916年,为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募捐,清华游艺社排演了《都在我》(“演剧助费”16)。1922年,为胶济铁路赎金等事,戏剧社以清华学校名义利用寒假期间在京演剧募捐,排演剧本《瓖珴璘与蔷薇》《父之归》《战之罪》《棠棣之花》《喜相逢》等(“戏剧社”13-14),可惜的是这次演出因故未能举行(“戏剧社”30-31)。清华的这些公益演剧颇受当时社会欢迎,前述《贫民惨剧》演出后,曹汝霖当场为贫民小学捐出一百元(“演剧纪事”14),北京通俗讲演所所长林墨卿也捐了五块大洋(“演剧再志”12)。1919年,新剧社为筹办社会服务捐款,在北京第一舞台排演新剧,“为北京一班慈善家所欢迎。捐款甚踊跃。”(“志新剧社”5)新剧社的演剧营利均用于各项慈善事业(“新剧社近闻”6)。
学生演剧“实亦一种优良之实验教育也”
演话剧的文化风潮在清华形成,首先得益于清华校方对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实现完全的人格教育之重视。在这样的办学方针下,学校鼓励学生养成各种技能,提高综合素质,而且特别重视学生演讲、社交等方面的才能。同时,清华早期为留美预备学校,当时的学生大部分都将赴美留学,要为融入美国社会作准备。1917年,《清华周刊》刊登的一则“留美通信”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文艺才能对留美学生十分必要。一是苦读之余可以“自遣”,二来可以借此联络友谊,还可调和精神、舒展肢体(王文培11)。原产于西方的话剧对此自然有帮助。
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清华学生对文艺的兴趣,以及对演剧对人格培养方面意义之自觉。在他们看来,“文艺乃是向上生命的泉源;它赐给我们和平、勇敢,与希望;它好比一条光明的彩练,把现在与理想的将来紧紧系住。它应当和人生相始终,我们学生也不能宣告例外。”(“《文艺增刊》发刊旨趣”12)1917年,《清华周刊》上出现了第一篇专论话剧的文章。作者说,“学生演剧如其情节果风雅动人,有关世道,其习练纯熟精密,布景周到完美,多大纯而少小疵,则不特演者得增进阅历,引起刻苦勤劳之精神,悟分工合作之要即观者亦受无穷之感化矣。”“夫学生之所短者,在经验之浅薄,而演剧能补助之。学生之所以见轻于社会者,乃少刻苦勤劳之精神,而演剧能贯注之。学生之所以大抵落魄无聊者,乃傲慢自大,无服从之自觉,与协同之精神,而演剧亦能挽回而矫正之。”因此,学生参加话剧活动,“实亦一种优良之实验教育也”(时 1-2)。次年,又有一篇文章借评论话剧《可以风》提出,“夫学校生活至严肃者也。然过严肃则易流于拘迂或且束缚个性之发展,阻碍心灵之活泼而转为教育之障。故西人学校务使生徒之居业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设若种种课外之作业及社交的活动一方训练其治事之才而与以阅历。一方则学校之生活自有其正当之娱乐。故人自悦学而无寂寥枯索之感。此其法良意美无可疑。学生演剧其一事耳”(“可以风”1)。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清华话剧社团蓬勃发展。目前可见较早的记载是1916年清华学生就有“组团”行动。“现闻有同学数人。发起一戏剧团。以便校中俱乐演剧。时有所专司。所有团中一切组织。已拟就草章。呈请校长核准。”(“戏剧组团”20)早期清华话剧活动最重要的组织团体是“游艺社”,它不仅组织排演剧目,而且添置演剧所需物件,“托人到上海购买各种新剧化装品。以备应用。”(“游艺社纪”29)“凡本校同学欲演剧者。均可租用价值面议。”(“游艺社纪事”24)1919年,游艺社改组为新剧社,分庶务编演二部(“志新剧社”9)。1922年,又有高等科同学20余人,集合志同道合者,组织戏剧社(“戏剧社”19)。很快,就招募到社友七十余人。1922年,星期日晚八时,举行成立大会,“为清华新剧史上开一新纪元。”(“志新剧社”17)“该社分编剧、演剧、庶务、会计四大部,各部有部长一人,各部长另成一种执行委员会,主持一切。”其中编剧部长为时昭沄,演剧部长为翟恒。5月中旬第一次演剧,“编剧部长时君以演剧在迩,剧本非常重要,特于日前宴诸部员以资鼓励云。”(“戏剧社”24)后来,清华又成立了“戏剧社”,其宗旨为“研究艺术及高尚娱乐”(“一年来校中会社一览表”26)。戏剧社聘请蒲伯英、陈大悲为名誉顾问,杨志卿、余上沅、徐国祥为顾问(“戏剧社”13)。每年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仅1923年就招募到新社员20余人(“戏剧社”18)。
李健吾、曹禺等都曾担任戏剧社的负责人。值得一提的是,戏剧社还有一些重要人物尚缺乏研究。比如,1925年当选戏剧社社长的何鸿烈。“何君绰号莎士比亚,即文艺界闻名之一公君,本刊文艺栏新主任也,公对于戏剧极有研究,且办事非常热心。”(“戏剧社”28)何鸿烈“对于戏剧有那种兴趣,那种狂热”,他执掌的戏剧社“阁员”名单为:排演部长沈惟泰,剧本部长贺麟,化装部长王国桢,布景部长王慎名,庶务部长苏宗固,会计部长沈熙瑞,文牍部长罗正晫。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是小戏院(Little Theatre Movement)的试验,打算每月在旧礼堂演一次戏,并打算请丁西林、陈西滢做顾问。(“戏剧社”27)在何鸿烈主持下,戏剧社不但修订章程扩大招收新会员,而且争取到张彭春、宋春舫等话剧名家的支持和指导(“戏剧社”31)。不幸的是,何鸿烈的宏图尚未展开,就在“三一八”惨案中受伤,不久去世。
“戏剧是一种科学”
中国话剧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这也是早期清华话剧人的自觉认同。1921年,杨夏怀仁在《清华周刊》撰文提出,“戏剧感人至深,具有左右社会之能力。故一剧之成,苟欲其盛行无阻,必需以改良风化,利导人民为宗旨。”据此,他对当时社会上所演新剧提出了批评,“社会上所演之新剧,如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系改良之歌剧。南开所演之一念差华娥传等剧堪称较完之新剧。若清华十周年所演之良心一出,则立意太深,所谓言语动作,乃不能将剧中之真精神曲曲达出,使观者了然”,进而提出话剧“立意不必太高,但务洽社会之心理,而改良风俗之宗旨。”“布景服饰须采取社会所常见者为模范”。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他对中国话剧起源的看法:“新剧胚胎于民国未成立之前,其时约在一千九百零五六年之间。发起之人,系在日本一班之留学生,目睹国政腐败,思奋起而改革之,因招集同志,假东京剧场,演习新剧,以为鼓吹革命之利器。其剧本皆取诸法国革命时代所编演者。当时国人感于清政府专制之下,观之莫不惊心动魄,泣下沾襟。故其效验彰著,为国人所共识。此新剧发生之原始也。迨后革命告成,始稍稍演行于内地。而学界尤以之为集款助账之惟一良法。于是一班市侩,见新剧组织之易而获利厚也,遂群起效颦,新剧遂得盛行于社会。”(杨夏怀仁10-11)曾在清华任教的余上沅认为话剧艺术是国家建设之手段。他提出,“国家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我以为是:把人类的一部分归纳于一个完善的组织之中,使他成为一个有机的单位;若干同性质的组织彼此互相辅助着,使人类得以享受最完美的生活。”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将物质和精神互相调剂,这就“不能不在美术上去努力,尤不能不在美术之汇总的戏剧艺术上去努力”(“余上沅先生来函”39)!而学生戏剧社团也明确表示要“研究戏剧的性质、派别,挐来应用到中国戏剧界,求社会的改良”(“本学期会务一瞥”40)。
正因为如此,清华校园内的话剧活动与校园外的社会思潮、时局变换及其中反映的时代主题密切相关,排演的剧目取材于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表现出深切的社会关怀。洪深的《贫民惨剧》的说明书如是说:“贫贱小民幼时无适当之教育,长成无一定之职业,不能自活,强横者或竟为社会蟊贼,愚懦者亦冻馁而死,哀惨莫甚。王一声者,故家子也。父在以珍爱废学业,父没不能治生产,家遂日落,其后贫甚。王不能谋饔飱,告诸亲友,亲友莫应。或劝之卖妻,不得已从其计。获得数十金,博负又尽忘。妻至豪家,不屈自刎死。噫惨矣。”(“演剧纪事”14)顾一樵的《张约翰》批评了留学生喜新厌旧,管效先的四幕剧《惨杀》深刻反映留学生婚姻问题,而且取材于当时的社会新闻。汪梧封的Frist Impression、各它的《姑母的侄女》回应了社会上关于娜拉的探讨。梅玄改写的《我俩》赞扬了“留守”的女士。“九一八”事变之后,还出现了《纪念日》《活埋》等抗日题材的作品(张玲霞 84-85)。
不过,更值得注意和思考的是,清华话剧人在张扬话剧社会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对话剧艺术性的追求。张彭春在戏剧社演讲时,一方面提出话剧不能只为少数学者欣赏,而要与民众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则强调,“演剧最要紧的是人——人的深的广的感情,和活的语言工具”,这就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演作的训练”,“演作比剧本的价值高得多……即使剧本很好,若是不能表演,终于是没有生命的。”二是 “新剧本必由多方的深切的新生活经验得来”,“必须以感情去运用语言,换言之,要能够抒发情感的语言才是活的语言。”三是“新的观察”。新剧应“博得未受教育的观众的赞赏”,“活的戏剧,必须雅俗共赏”(贺麟 12-14)。洪深翻译了《编剧者须知》,提出15条操作性极强的编剧法则,即:1.凡盗贼欺骗杀人等事不可入之戏剧。2.爱情之剧须高尚清洁,不可令妇人见之蹙额男子见之狂笑。3.新鲜为第一要义,虽从未经人道过,不妨自我作古,勿取新闻为题目。4.不知之事不如勿写。5.戏中人物须自然,喜怒哀乐,言语举动,应如常人。6.文字须典雅,语气须连贯。7.饰恶人以髭鬚,饰英雄为美少年,此套已太俗。8.勿言说,观剧者为观剧而来,欲听言说,早向教堂去亦。9.勿忘观剧者极富幻想。10.勿忘观剧者极富感情。11.一人独说适宜于半唱半戏之剧寻常不可用。12.一剧不宜包含太广。13.勿以第一幕为一八六六年之隆冬,第二幕为一九〇九年之季夏,此四十三年中,有无数好戏在焉。14.勿以第一幕为非洲,第二幕为芝加哥。15.编完一剧应细读数过,自寻弱点(洪深18-19)。华因在《戏剧与“美的剧场”》中提出,戏剧是供人观览的,不仅是诵读的;其重要点在动人的视听。“戏剧是一种科学,要美术家来研究的。除去扮演的动作外,剧场的建筑,和光线布景化装等,均是重大问题,要精深地研究的。”(华因 20-21)
正因为对艺术的自觉追求,使清华的话剧具有较高专业水准,演员舞台表现和艺术技巧都值得称道。1916年5月12日,高等科三年级演英语话剧《李代桃僵》,“是剧饶有趣味。而演剧人神情自然。然曲尽其妙。观者皆赞赏不致。”(“高三演剧”19)同年12月的戏剧比赛中,高等科的《劫里姻缘》“表情高尚,曲折尽致”;中等科的《紫荆魂》则以“布景之精巧,谈谐之奇诡”受到称赞(“游艺社在京演剧”18-19)。1923年演出的独幕趣剧《喜相逢》“情节离奇本已可笑,而演剧员善于表现,尤觉滑稽”(“剧社排演”27)。1924年,戏剧社上演《平民的恩人》。王国桢扮演的哑子尤其“神情逼肖”,受到称赞。王国桢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于未演之先,费尽心力,始得遇一真正哑子及一半哑者接谈至数时之久,遂尽得其秘诀”(“练哑苦心”17)。除了表演,服装、道具也力求精致。高二级排演德国名剧《织工们》,专门从新民大戏院借“非常美满”的布景,并赶制“式样均采德国古式”的演员服装(“赴京演剧”54)。日本名剧《父之归》“用日本装束,饰胤姑者化装尤佳,表情至深刻处,观众多有流泪者,亦可见动人之一斑”(“庆祝十二周年纪念志盛”27)。洪深组织编演英国名剧《侠盗罗宾汉》时,为使舞台环境更真切,特意把戏搬到校园中树林的空地间演出(陈美英 195)。值得格外一提的是,1917年4月14日,清华学生演出《都在我》至第三幕时突发意外。“点灯遽坏。全堂黑暗。而剧员在台上者。并不停演。急燃烛以代电灯。约经三分钟。电灯复亮。而其间烛之去取。均由剧中之店仆为之。故观者尤以为妙。盖合于剧中情节也。又每次闭幕布景时。皆有赵曹二女士。互奏洋琴。以破岑寂而增兴趣云。”(“演剧志盛”25)对突发事件的沉稳处理也反映出清华话剧人的“老练”。
希望将来“可以不用外国的注脚”
清华是一座充满洋气的学堂,对西洋事物的介绍是其优势所在。清华话剧人在话剧实践外,对西方话剧剧本、剧作家和理论等也作了不少介绍。
在话剧理论史论方面,早在1917年,洪深就翻译过《编剧者须知》(洪深 18-19)。1920年代,《清华周刊》刊登了数篇西方戏剧发展史的书评,介绍了Isaac Goldberg Kidd所著The Drama of Transition,此书是对西班牙、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南美洲、犹太作家及美国的戏剧发展趋势的研究(“The Drama of Transition”34)。还介绍了K.Mac Gowan&R.E.Jones Harcourt所著Continental Stagecarff,此书“专叙新舞台技术之大要。由书中之记载及插画,即可详细了解近十年来世界上戏剧场中的新运动。而于中欧最近的最进步的最有意味的舞台改革诸事尤详”(“Continental Stagecarff” 34)。 此外,对国外的喜剧(Herbert Read 39)和悲剧(Aldous Huxley 1157)研究,美国剧院之反法西斯运动(朋蒲27),以及剧场(“莫斯科的五觉剧院”81)和舞台研究(Glayton Hamilton 105)的成果均有介绍。
在作家作品方面,德国戏剧家哈蒲曼(今译豪普特曼)被重点介绍(张锐 33),不但在《清华周刊》上刊登了其代表作《织工们》(1892年)的概略(郝则德 31),还请谭唐写了评介,称《织工们》为“自然主义运动的最高点”(谭唐 32)。在《清华周刊》上被介绍的国外剧作家还有萧伯纳(“A Dialogur On Things in General” 44)、格雷戈里夫人(“Three Wonderpalys” 34),西班牙戏曲大家 Sierra(Walter Starkie 39),英国的狄更斯(“Mr.Dickens goes to the Play” 35)、哥斯华绥,巴蕾(“萧伯纳,哥斯华绥,巴蕾”67),德国的阿尔培·巴瑟曼(今译巴塞尔曼)(石坚 63)等。西方学界关于莎士比亚(本得75)、易卜生的研究成果(“The Real Dolls House”39)也在《清华周刊》上得到介绍。剧本方面,《清华周刊》刊登或介绍过的有Ludwig Fulda著、梅玄改译的剧本《我俩》(梅玄 53),萧伯纳的《苹果车》《荒岛愚人》《百万富女郎》《柯顿的六个人》等(“萧伯纳的三个剧本”65)。此外,《清华周刊》也关注东洋的戏剧,介绍了日本戏剧家、新思潮派代表人物菊池宽的作品《唐太宗的心理》,并指出“此篇系用新式话剧体裁以表演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马嵬坡死别这一段遗事,……此种历史剧中国新剧界上不多观也”(菊池宽 17)。《清华周刊》还关注到了苏联戏剧的新动向(苏菲亚110),以及苏联戏剧节的情况(“苏联的戏剧节”28)。
清华话剧人放眼世界,目的是推动本土戏剧发展。1936年,《清华周刊》的一篇文章明确提出“编译戏剧辞典”的倡议。文中说,中文方面理化、哲学、教育等学科有专门的辞典,“而戏剧就始终没有”,“Cyclorama,Proscrnium等字至今尚没有妥当的译法”,“第四堵墙”的详细解释,也付之阙如。“我们所需要的戏剧辞典,当然不是一种Dictionary,而是一部Encyclopedia,应包括作品与作家,舞台技术,作剧用语,史源……等之东西。”“希望几年之后写中国文章时,可以不用外国的注脚。”(“编译戏剧辞典”29)这显示出很切实际的话剧艺术本土化自觉和努力。在“化西”的同时,清华话剧人对“化中”,也就是改造中国传统戏剧也有所探索,曾借一则书讯表示,“欧美人观中国戏剧往往具西方之眼光,故未能得其优美之处。至其批评中国戏剧之弱点,则在乐器之振耳,声调之不和,以及服饰之不当耳。然观者如能抛弃其西方文化的主观并稔知中国几千年之历史及各地风土人情,则中国戏剧之善于描摹,实不亚于欧美各国之戏剧。”(志骞19)从中也可看出,在当时多少有些偏激的戏曲改良舆论氛围下,《清华周刊》保持了可贵的客观和理性。
共同的艺术追求
如前所述,清华话剧活动的参与者不仅有学生,还有老师,不仅以年级为单位,而且有专门的学生社团,形成人脉与艺脉的交织传承。其中的源头性人物应属王文显。王文显,字力山,生于1886年,自幼求学英伦,1915年获伦敦大学文学士。同年到清华任教。后曾任清华教务主任、代理校长。1925年9月,清华增办大学部后,任西洋文学系主任。王文显在话剧方面成就不凡。他曾于1927年至美国耶鲁大学研习,从戏剧大师贝克教授学编剧。他编的英文剧《北京政变》《委曲求全》在当时十分有名。但王文显对中国话剧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话剧教育。在他主持制定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程大纲及学科说明”中,列入了《戏剧概论》《莎士比亚》两门课程,《现代西洋文学》课程中也专设戏剧部分,这些课程都由他亲自主讲。《戏剧概要》“讲授西洋戏剧发达之略史。自上古希腊以至现今,选读名剧约五十篇以资阐明,并论究戏剧之技术。关于编剧、演剧、排剧之各种问题亦讨论及之”。《莎士比亚》这门课的“目的有二:(一)为学生讲解莎士比亚之文学价值;(二)使学生自知如何欣赏莎士比亚文学,莎士比亚之生平及其著作之精妙所在,统于两学期内教授之。读莎氏重要著作10余篇”(黄延复 142-146)。1933年,又加开《近代戏剧》,专门讲授易卜生以后之戏剧。做过王文显助教的张骏祥说,王文显的讲稿“扎扎实实,对于初接触西方戏剧的人来说,是个入门基础。……选了文显先生这两门课,至少就得把莎士比亚主要剧作和欧美戏剧史的名著通读一遍”(张骏祥226)。除了上课,王文显也指导学生话剧社团的活动。1928年,清华戏剧社成立,王文显被聘为顾问。1930年11月14日,王文显应邀讲演,题目为How Plays Hre Produced in American,内容为美国大学戏剧社及职业团体剧社之舞台布置等,并举了Peking Polities和She Stoops Compromise两剧,“听众极表满意”(“剧社消息”59)。王文显对清华话剧的另一大贡献,是为学校积攒了大批专业书籍。张骏祥说,“那时学校每年有一大笔钱买书,文显先生自己研究戏剧,每年也要买不少戏剧书籍,从西洋戏剧理论到剧场艺术,到古代和现代名剧的剧本都应有尽有。所以我们这些对戏剧有兴趣的同学,就有机会看到不少书。”[90]受益于王文显购买的这些戏剧书的还有曹禺。他说,“应当感谢他的是,他为西洋文学系为清华图书馆买了不少外国戏剧的书,当然是外文的。我就是看他买的戏剧书,钻研戏剧的。”(田本相、阿鹰 72-73)
洪深、李健吾、曹禺、张骏祥等著名话剧人均受其影响。1926年李健吾毕业留校担任王文显的助教,将《委曲求全》译成中文。1932年8月,李健吾赴法深造,又推荐张骏祥继任助教。从清华园走出来的话剧人才大多出自西洋文学系,绝非偶然。学生们对王文显这位清华话剧“教父”般的老师也充满敬仰之情。1935年,青年剧社公演《委曲求全》,李健吾担任导演,并在剧中饰演张董事;张骏祥担任剧务;林徽因担任舞美设计,轰动一时。《委曲求全》演出期间,还举行了座谈会,曹禺等人参会,对剧作进行了评论(田本相、阿鹰 106)。后来,得知王生活困难,李健吾又翻译了《北京政变》,改名为《梦里京华》,并组织演出,收取上演费接济王文显(韩石山 53)。王文显对于学生们的戏剧成就也一直十分关注。曹禺的《雷雨》问世时,王文显已在上海,但特意给曹禺写信进行交流(田本相、阿鹰 73)。
师生之间的纵向承传和学生之间的横向联络,似一组交织的经纬线,使话剧精神传续不绝。学生之中,演剧资格最老的应属洪深,在清华读书时,凡是学校里演戏,只要能参加的差不多每次他都有份。他又长于编剧。“在清华四年,校中所演的戏,十有八九,出于我手。”(洪深 474)曹禺尚未进入清华便已领略了洪深翻译的《少奶奶的扇子》的魅力。“我入南开新剧团,正赶上排这部戏,我天天看天天背,把剧本都翻烂了。”(田本相、阿鹰 43)曹禺自认洪深的“私淑弟子”,在四川江安,洪深被请到剧专任教,曹禺以师礼待之,他说,“我觉得那是我很幸福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从他那里不只是学习戏剧、学知识,还学习了如何从事戏剧教育。”(陈美英18-19)
需要给予关注的还有闻一多,虽然不以话剧闻名,但他在清华的文艺活动是从话剧起步的。1913年,闻一多就参与了班级戏剧编演活动,这一年,他还参加了话剧《革命党人》的排演。1916年,他又参加了《贫民惨剧》的演出。1919年,清华成立新剧社,担任编演部总经理的也是闻一多。闻一多扮演的角色多种多样,在《蓬莱会》中甚至扮演了主角——驴子。早在1917年,年仅19岁的闻一多就对戏剧的价值,以及话剧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夫戏剧者,襄善惩恶,鉴古资今,入人深而为用广,此其所以亘百世而不绝也。”“晚近欧风东渐,则又有所谓新剧者焉。其在于肖实而近情,不杂管弦,不以歌咏,其事简而感人速,故功恒倍蓰于旧剧。欧西是以为通俗教育之一。今吾校提倡学生演戏者,意亦在斯乎。”提出“戏剧者,亦教育之一途尔”(黄延复 447)。学生时代结束后,闻一多依然没有放弃对清华话剧人的关注。据李济五回忆,“曹禺和闻一多先生真是一见如故,……在共同的艺术追求中,他们合作得很好。”(田本相、阿鹰 229)1939年7月,正为现实而深感苦闷的闻一多致函曹禺,提出“现在该是演《原野》的时候了”。他又与吴铁翼等联名电请曹禺到昆明指导演出。7月13日,曹禺抵达昆明,亲自导演《原野》,当时已久不出书房的闻一多担任了舞台设计和服装设计。8月16日,《原野》在新滇大戏院公演,连演九场,虽逢大雨,仍场场满座。闻一多为演出写了说明书,其中说“蕴蓄着莽苍深厚的诗情,原始人爱欲仇恨与生命中有一种单纯真挚的如泰山如洪流所撼不动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当今萎靡的中国人恐怕是最需要的吧”(洪深 579)!
除了艺术方面的共同追求,清华话剧人还共同推动话剧教育事业发展。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健吾考虑到上海话剧界人才济济,各演出团体又缺乏演员,想创办戏剧学校,就得到了时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昔日的清华话剧活动积极分子顾毓琇(顾一樵)的支持(韩石山271)。
结 论
通过清华大学最重要的学生刊物《清华周刊》可以发现,1913年以后,演话剧在清华园中蔚然成风,不同专业的学生及教师均参与其中,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清华早期话剧人不仅重视话剧的社会功能,而且强调其艺术特性,为此,他们译介西方话剧理论和作品,锤炼话剧艺术,传续艺术精神,技道并重、会通中西,为中国的话剧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注释【Notes】
①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本文叙述范围(1915-1936)内涉及清华学校、清华大学两个校名,为行文方便,除史料原文一仍其旧外,一律称清华大学。
Huxley Aldous.悲剧与全部的真实.可宋译.清华周刊,1933(562-563).
[Huxley,Aldous.“Tragedy and Reality.” Trans.Ke Song.Tsing Hua Weekly 562-563(1933).]
贝珍.戏剧在清华.清华周刊·向导专号,1936.
[Bei,Zhen.“Theatre In Tsing Hua Campus.” Tsing Hua Weekly-Special Guidance,1936.]
本得.希太劣治下的莎士比亚.清华周刊,1936(619).
[Ben De.“Shakespeare Rules By Hitler.” Tsing Hua Weekly 619(1936).]
本学期会务一瞥.清华周刊,1920(185).
[“The Affairs In This Semester.” Tsing Hua Weekly 185(1920).]
编译戏剧辞典.清华周刊,1936(619).
[“Editing and Translating Theatre Dictionary.” Tsing Hua Weekly 619(1936).]
陈美英.拓荒者之路.本书编委会.回忆洪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Chen Meiying.“The Pioneer’s Road.” To Memorizing Hong Shen.Ed.The Editorial Committee.Beijing:China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2015.]
Continental Stagecarff.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4(10).
[“The Drama of Transition.” Tsing Hua Weekly-The Introduction of Books and Newspapers Supplement 10(1924).]
A Dialogur On Things in General,Between george Bernard Shaw and Archibald Hender on Harper’s Magazine May number,1924.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4(12).
[“A Dialogur On Things in General,Between george Bernard Shaw and Archibald Hender on Harper’s Magazine May number,1924.” Tsing Hua Weekly-The Introduction of Books and Newspapers Supplement 12(1924).]
The Drama of Transition.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4(10).
[“Continental Stagecarff.” Tsing Hua Weekly-The Introduction of Books and Newspapers Supplement 10(1924).]
赴京演剧.清华周刊,1924(303).
[“Coming To Beijing To Perform.” Tsing Hua Weekly 303(1924).]
高三演剧.清华周刊,1916(77).
[“The Play Performed By The Senior Students of Grade Three.” Tsing Hua Weekly 77(1916).]
葛一虹.中国话剧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Ge,Yihong.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Drama.Wuhan:Wuhan University Press,2015.]
Glayton Hamilton.近代舞台的图画性.仰山译.清华周刊,1935(608-609).
[Hamilton,Glayton.“The Picturesque Features of Modern Stage.” Trans.Yang Shan.Tsing Hua Weekly 608-609(1935).]
龚元.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清华传统”.戏剧艺术,2012(3).
[Gong,Yuan.“ ‘Tsing Hua Trad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Drama.” Theatre Arts 3(2012):27-39.]
国庆预志.清华周刊,1920(193).
[“The Preparation For National Day.” Tsing Hua Weekly 193(1920).]
郝则德.“织工们”概略.郑骏全译.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3(7).
[He,Zede.“The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Weavers.” Trans.Zheng Junquan.Tsing Hua Weekly-The Introduction of Books and Newspapers Supplement 7(1923).]
韩石山.李健吾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Han,Shishan.The Biography of Li Jianwu.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17.]
Herbert Read,The Kefinition of Comedy.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4(11).
[Read,Herbert.“The Kefinition of Comedy.” Tsing Hua Weekly-The Introduction of Books and Newspapers Supplement 11(1924).]
洪深.编剧者须知.清华周刊,1917(111).
[Hong,Shen.“Notice For Playwrights.” Tsing Hua Weekly 111(1917).]
---戏剧的人生.洪深.洪深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Hong,Shen.“Theatrical Life.” Collected Works By Hong Shen(vol.1).Beijing:China Theatre Press,1959.]
华因.戏剧与“美的剧场”.清华周刊,1921(224).
[Hua,Yin.“Drama and ‘Amateur Theatre’.” Tsing Hua Weekly 224(1921).]
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Huang,Yanfu.Tsing Hua Campus Culture In 1920th and 1930th.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0.]
菊池宽.唐玄宗的心理.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3(2).
[Kikuchi,Ken.“The Psychology of Emperor Xuanzong of Tang.” Tsing Hua Weekly-The Introduction of Books and Newspapers Supplement 2(1923).]
剧社排演.清华周刊,1923(280).
[“The Drama Club.” Tsing Hua Weekly 280(1923).]
剧社消息.清华周刊,1930(497).
[“The Information of The Drama Club.” Tsing Hua Weekly 497(1930).]
可以风.清华周刊,1918(127).
[“The Tendency of Allowance.” Tsing Hua Weekly 127(1918).]
练哑苦心.清华周刊,1924(301).
[“To Practice Hard As A Mute.” Tsing Hua Weekly 301(1924).]
梅玄改译.Fulda Ludwig.我俩.清华周刊,1931(506).
[Fulda,Ludwig.“Two of Us.” Trans.Mei Xuan.Tsing Hua Weekly 506(1931).]
莫斯科的五觉剧院.清华周刊,1936(623).
[“Moscow Five-Sense Theatre.” Tsing Hua Weekly 623(1936).]
“Mr.Dickens goes to the Play” by Alex.Woodllcott Putnam.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4(10).
[“ ‘Mr.Dickens goes to the Play’ by Alex Woodllcott Putnam.” Tsing Hua Weekly-The Introduction of Books and Newspapers Supplement 10(1924).]
排演新剧.清华周刊,1916(89).
[“Rehearsing New Drama.” Tsing Hua Weekly 89(1916).]
朋蒲.美国剧院之反法西斯运动.清华周刊,1936(619).
[Peng,Pu.“Anti-fascist Movement In American Theatre Houses.” Tsing Hua Weekly 619(1936).]
贫民惨剧说明书.清华周刊,1916(66).
[“The Introduction of Poor People’s Tragedy.” Tsing Hua Weekly 66(1916).]
清华新剧社纪要.清华周刊·第五次临时增,1919年.
[“The Notes of Tsing Hua New Drama Club.” Tsing Hua Weekly-The Fifth Temporary Supplement,1919.]
清华文风日昌.清华周刊,1929(450).
[“The Growing Atmosphere of Liberal Arts In Tsing Hua Campus.” Tsing Hua Weekly 450(1929).]
庆祝十二周年纪念志盛.清华周刊,1923(280).
[“The Record of The Grand Occasion of The 12th Anniversary.” Tsing Hua Weekly 280(1923).]
庆祝新年游艺大会志略.清华周刊,1929(450).
[“The Briefing of The Festival Celebration For New Year.” Tsing Hua Weekly 450(1929).]
“The Real Dolls House” by Xians in Living Age,Mar.1,1924.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4(11).
[“ ‘The Real Dolls House’ by Xians In Living Age,Mar 1,1924.” Tsing Hua Weekly-The Introduction of Books and Newspapers Supplement 11(1924).]
十周年纪念纪事.清华周刊,1921(219).
[“The Record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Tsing Hua Weekly 219(1921).]
时.学生演剧平议.清华周刊,1917(107).
[Shi.“The Review of Student’s Drama.” Tsing Hua Weekly 107(1917).]
石坚.德国的亡命戏剧家.清华周刊,1936(618).
[Shi,Jian.“German Exiled Playwrights.” Tsing Hua Weekly 618(1936).]
苏菲亚.苏联文艺底新动向.清华周刊,1933(566-567).
[Sophie.“The New Trend of Soviet Literature and Art.” Tsing Hua Weekly 566-567(1933).]
苏联的戏剧节.清华周刊,1936(617).
[“Soviet Theatre Festival.” Tsing Hua Weekly 617(1936).]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Su,Yunfeng.From Tsing Hua College To Tsing Hua University.Beijing:SDX Joint Bookstore,2001.]
谭唐(讲演).哈蒲曼的“织工们”在德国文学上和历史上的地位.贺麟笔记并译.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3(7).
[Tan Tang(Speech). “The Importance of Hauptmann’s The Weavers In Germ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rans.He Lin.Tsing Hua Weekly-The Introduction of Books and Newspapers Supplement 7(1923).]
田本相、阿鹰.曹禺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Tian,Benxiang,and Aying.The Chronicle of Cao Yu.Shanghai: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2016.]
田本相.中国话语艺术史(第二卷).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
[Tian,Benxiang.The History of Chinese Drama Arts(vol.2).Nanjing:Jiangsu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6.]
“Three Wonderpalys” by Lady Gregory Putnam.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4(10).
[“‘Three Wonderplays’ by Lady Gregory Putnam.” Tsing Hua Weekly-The Introduction of Books and Newspapers Supplement 10(1924).]
Walter Starkie,Gregorio Martinez Sierra and the Modern Spanish Drama by Walter Starkie,in contemporary Review,Feb.1924.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4(11).
[Starkie,Walter. “Gregorio Martinez Sierra and the Modern Spanish Drama by Walter Starkie,in contemporary Review,Feb.1924.” Tsing Hua Weekly-The Introduction of Books and Newspapers Supplement 11(1924).]
王文培.敬告清华同学之将来美者.清华周刊,1917(110).
[Wang,Wenpei.“To Notice Those Tsing Hua Students Who Will Come To The USA.” Tsing Hua Weekly 110(1917).]
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Wen,Liming,and Hou,Jukun.The Chronicle of Wen Yiduo.Wuhan:Hubei People’s Press,1994.]
《文艺增刊》发刊旨趣.清华周刊,1924(319).
[“The Purpose of Literature and Art Supplement.” Tsing Hua Weekly 319(1924).]
戏剧比赛.清华周刊,1917(94).
[“Drama Competition.” Tsing Hua Weekly 94(1917).]
戏剧社.清华周刊,1922(237).
[“The Drama Club.” Tsing Hua Weekly 237(1922).]
戏剧社.清华周刊,1922(238).
[“The Drama Club.” Tsing Hua Weekly 238(1922).]
戏剧社.清华周刊,1922(240).
[“The Drama Club.” Tsing Hua Weekly 240(1922).]
戏剧社.清华周刊,1922(260).
[“The Drama Club.” Tsing Hua Weekly 260(1922).]
戏剧社.清华周刊,1923(280).
[“The Drama Club.” Tsing Hua Weekly 280(1923).]
戏剧社.清华周刊,1923(293).
[“The Rehearse.” Tsing Hua Weekly 293(1923).]
戏剧社.清华周刊,1925(340).
[“The Drama Club.” Tsing Hua Weekly 340(1925).]
戏剧社.清华周刊,1925(342).
[“The Drama Club.” Tsing Hua Weekly 342(1925).]
戏剧社.清华周刊,1925(344).
[“The Drama Club.” Tsing Hua Weekly 344(1925).]
戏剧社.清华周刊,1928(438).
[“The Drama Club.” Tsing Hua Weekly 438(1928).]
戏剧组团.清华周刊,1916(81).
[“Establishing Drama Club.” Tsing Hua Weekly 81(1916).]
萧伯纳的三个剧本.清华周刊,1936(618).
[“Bernard Shaw and His Three Plays.” Tsing Hua Weekly 618(1936).]
萧伯纳、哥斯华绥、巴蕾——不列颠三岛三个娇儿.清华周刊,1936(618).
[Shawn,Bernard,and Galsworthy.“Barley:Three Innocent Children In Britain Islands.” Tsing Hua Weekly 618(1936).]
新剧社近闻.清华周刊,1919(179).
[“Recent Information on New Drama Club.” Tsing Hua Weekly 179(1919).]演剧筹款.清华周刊,1916(65).
[“Raising Money For The Performance.” Tsing Hua Weekly 65(1916).]
演剧汇志.清华周刊,1921(226).
[“The Summary of Performing Dramas.” Tsing Hua Weekly 226(1921).]
演剧纪事.清华周刊,1916(66).
[“The Notes of The Performance.” Tsing Hua Weekly 66(1916).]
演剧志盛.清华周刊,1916(69).
[“Performing Is Flourishing.” Tsing Hua Weekly 69(1916).]
演剧志盛.清华周刊,1916(72).
[“Performing Is Flourishing.” Tsing Hua Weekly 72(1916).]
演剧志盛.清华周刊,1919(157).
[“Performing Is Flourishing.” Tsing Hua Weekly 157(1919).]
演剧再志.清华周刊,1916(67).
[“Recording The Performance Once Again.” Tsing Hua Weekly 67(1916).]
演剧助费.清华周刊,1916(78).
[“The Sponsorship For The Performance.” Tsing Hua Weekly 78(1916).]
杨夏怀仁.我之新剧观.清华周刊,1921(231).
[Yangxiahuairen.“My Opinions On New Drama.” Tsing Hua Weekly 231(1921).]
一年来校中会社一览表.清华周刊·第十次增刊,1924.
[“The List of Clubs In This Year.” Tsing Hua Weekly-The Tenth Supplement,1924.]
游艺社纪事.清华周刊,1916(87).
[“The Record of Youyi Theatre.” Tsing Hua Weekly 87(1916).]
游艺社纪事.清华周刊,1916(88).
[“The Record of Youyi Theatre.” Tsing Hua Weekly 88(1916).]
游艺社纪事.清华周刊,1916(93).
[“The Record of Youyi Theatre.” Tsing Hua Weekly 93(1916).]
游艺社在京演剧.清华周刊,1917(105).
[“Youyi Theatre Is Performing In Beijing.” Tsing Hua Weekly 105(1917).]
余上沅先生来函(戏剧艺术).清华周刊,1924(304).
[“The Letter From Mr.Yu Shangruan(Theatre Arts).” Tsing Hua Weekly 304(1924).]
在北京青年会排演(都在我).清华周刊,1917(105).
[“Rehearsing All In Me In Beijing Youth Club.” Tsing Hua Weekly 105(1917).]
张骏祥.王文显剧作选序.新文学史料,1983(4).
[Zhang,Junxiang.“Prefaces of Selected Plays By Wang Wenxian.” New Documents of Literature 4(1983).]
张玲霞.1911-1949清华戏剧寻踪.戏剧,2001(3).
[Zhang,Lingxia.“Studies On Tsing Hua Theatre From 1911 To 1949.” Drama 3(2001):43-50.]
---论清华大学早期(1925-1937)的文艺社团及其刊物.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5).
[Zhang,Lingxia. “On The Early Art Clubs and Journals In Tsing Hua University(1925-1937).” Journal of Tsing Hua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5(2000):80-85.]
张锐.自然派的哈蒲提曼.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3(7).
[Zhang,Rui.“Hauptmann of Naturalism.” Tsing Hua Weekly-The Introduction of Books and Newspapers Supplement 7(1923).]
张仲述讲、贺麟笔记.新剧在中国的前途.清华周刊·文艺增刊,1925.
[Zhang,Zhong,and He Lin.“The Future of New Drama In China.” Tsing Hua Weekly-Literature and Art Supplement,1925.]
志骞.中国戏剧.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3(4).
[Zhi, Qian.“Chinese Theatre.” Tsing Hua Weekly-The Introduction of Books and Newspapers Supplement 4(1923).]
志新剧社.清华周刊,1919(159).
[“Zhixin Drama Club.” Tsing Hua Weekly 159(1919).]
志新剧社.清华周刊,1919(166).
[“Zhixin Drama Club.” Tsing Hua Weekly 166(1919).]
志新剧社.清华周刊,1922(239).
[“Zhixin Drama Club.” Tsing Hua Weekly 239(1922).]
周年纪念预祝.清华周刊,1923(279).
[“To Congratulate The Anniversary Beforehand.” Tsing Hua Weekly 279(1923).]
朱双云.新剧史.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
[Zhu, Shuangyun.The History of New Drama.Shanghai:Wenhui Publishing House,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