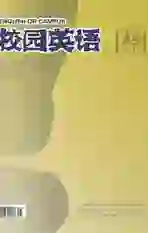CET—4汉译英背后的英汉差异分析
2018-01-23何金
【摘要】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中的汉译英部分是很多学生的弱项。汉译英的一个主要难点就是需要译者跨越汉语的语言模式,解构源语,将其整合重构成符合英语语言习惯的译文。学界在英汉语对比研究中,总结出英汉两种语言有诸多差异,而究其根源,在于英汉两个民族不同的思维模式导致的英语的时间性特质和汉语的空间性特质。分析两种语言的差异及其隐藏在背后的根源,旨在为大学英语的翻译教学提供思路。
【关键词】汉译英;语言模式;思维模式
【Abstract】It is a drawback for many students of the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part in College English Test 4 (CET-4). The main obstacle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is that the translator has to go beyond the mod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deconstruct the source language, so that the translation can be reconstructed to meet the mode of English language. The previous contrastive studies have revealed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but their origins lie in the temporality of English and spatiality of Chinese, which are caused by the distinctive modes of thinking of the two peoples.
【Key words】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Mode of Language; Mode of Thinking
【作者簡介】何金(1978-),女,重庆人,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英汉对比与翻译。
一、引言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改革之后便引入了汉译英的题型,这一部分重点在于考察学生对英语词汇、语法和句法的熟悉和综合运用,难点在于要跨越汉语模式化的语言习惯,使译文通顺完整,表达流畅,从而符合英语的思维习惯。和阅读理解等题型相比,学生在翻译中的表现往往差强人意,汉语固有的语言模式和思维模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对原文的解构和对译文的重新建构。所以在汉译英的过程当中,译者应该努力摆脱汉语的用词表意习惯,不能墨守汉语的条条框框,而是要顺应英语的表意特点。
二、从CET-4的汉译英谈起
学生在汉译英时,思维容易受到源语的影响,忽略目的语的特点,翻译时在主谓语、时态的选择和句子的衔接上容易出现问题。例如①:
[1]通车后从浙江宁波到上海的陆路距离缩短了120千米左右,大大缓解已经拥挤不堪的沪杭和杭甬高速公路的压力。(CET-4,2011-12)
[1]a The bridge reduces the previous trip from Ningbo to Shanghai by 120km and greatly alleviates the congested Huhang Highway and Hangyong Highway.
[1]b(大桥)通车后从浙江宁波到上海的陆路距离(被)缩短了120千米左右,(大桥)大大缓解已经拥挤不堪的沪杭和杭甬高速公路的压力。
[1]a为译文,选择用bridge作为主语,统辖两个子句,避免了主语的变化导致主动被动切换,使译文更加流畅,连词and的使用,使译文呈现出一个线性的整体。
[1]b在汉语的基础上补充了被省略的部分。由于汉语表达中主语经常缺失,导致学生在译文中对主语的选择也表现出很强的随意性,同时汉语的特点是形散,句子成分之间缺少连接词,导致学生在翻译时也会忽略连接词的使用。这些问题会导致译文缺乏结构上的紧密性和表意上的流畅性,甚至出现语法和句法错误。
[1]c *After the bridge is built, the distance between Ningbo of Zhejiang Province to Shanghai reduces 120km, it also reduces the pressure of Huhang Highway and Hangyong Highway.
[1]c是一个典型的错误例子,学生在汉语的基础之上生硬照搬,翻译成英文。主语it指代不清,第一个子句中reduces的使用在于没有厘清语义上主语和谓语之间的主被动关系,对于汉语的中动句只是单纯套用原文的表达,且两个子句之间缺少连接词。而之所以译文问题多多,是因为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多方面的差异,其中以形合与意合为最主要的差异。在任何语言中,形合与意合都是并行的。只不过汉语义合重于形合,注重语义上的连贯,而英语恰恰相反,形合重于意合,注重形式上的接应;从语法特征来看,汉语的语法是隐性的、柔性的,而英语语法则是显性的、刚性的(邵志洪,2005:196)。汉语的特点是结构松散,注重功能、意义,从表达上看比较简洁,而英语句子要求主语谓语(主述结构)完整,注重结构、形式,因而比较严谨。相对于英语注重结构层次表达,汉语体现出平面性倾向,这给形式表达带来的是模糊性,表现在逻辑上就是缺乏严密性(彭维宣,2000:43)。因此,在汉译英时,需要先分析原文的功能和意义,才能确定译文的结构和形式(连淑能,1993:58)。正是由于学生对英汉语的差异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因此在CET-4的汉译英中错误频出。出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A.主语的选择。
[2]在刺绣的过程中应用了中国的绘画艺术。(CET-4,2012-6)
The art of Chinese painting has been applied to embroidery.
[3]丽江到处都是美丽的自然风光。(CET-4,2015-12)
There is natural scenery everywhere in Lijiang.
前文例[1]a由译者根据上下文内容补出[1]缺失的主语bridge,[2]的译文则采用被动语态解决[2]中名词性主语缺失的问题,[3]属于汉语的静态存在句(黄伯荣,廖序东,2003:129),“丽江”是主语,在译成英语时,“丽江”成为了地点状语,在没有主语的情况下,采用形式主语there,使句子更加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和语法要求,英语中类似的形式主语还有it is reported(据报道)等形式。
B.谓语动词的有与无。
[4]设计时速为100千米,设计使用寿命100年以上。总投资118亿。(CET-4,2011-12)
The designed speed is 100 kilometers per hour, and the designed longevity is more than 100 years. The total investment on the bridge was RMB 11.8 billion.
[5]南起宁波慈溪,北至嘉兴海盐。(CET-4,2011-12)
It connects Haiyan in Jiaxing city and Cixi of Ningbo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例[4]和[5]都是选自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介绍,原文积词组而成句,语言精练,信息量大,很好体现了大桥的特点和优势。而译文则将短语缺失的谓语动词全部添加完整,满足英语语法的强制性要求。
C.动词形态变与不变。
[6]木版年画是一种传统民间艺术,是自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至近代印刷术出现之前最富特色的图画传播形式,至今仍在民间流传。(CET-4,2013-6)
Wood engraving picture is a traditional form of folk art in China. It was the most expressive form of pictures rich i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invention of the block printing in China to the appearance of modern printing, and is still popular among the people.
[7]中国有不少这样的特殊购物日。(CET-4,2015-6)
There are many such special shopping days in China.
汉语动词不会随时态(如[4]、[6])以及人称单复数(如[3]、[7])发生形态上的变化,但是英语的语法对动词却有这样的要求,并且是强制性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表达。这也体现出英语作为形态型语言的特点。
D.衔接手段使用与否。
[8]他们强调,人们应当读好书,尤其是经典著作。(CET-4,2014-6)
They emphasized that people should read good books, especially the classics.
[9]中秋节一般都是在晚上庆祝,人们聚在一起点灯笼,吃月饼,赏明月。现如今,很多人在中秋这天去欣赏音乐会,……(CET-4,2012-12)
The celebration usually takes place in the evening when families get together to light lanterns, eat moon cakes and enjoy the round moon. Today, many people celebrate the Mid-Autumn Festival by going to a concert, …
[10]它來源于中国古代的门神,其题材极其广泛。(CET-4,2013-6)
Wood engraving picture originated from the Door Gods in ancient China,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汉语具有流散性,讲究行文上的连贯,而英语则注重形式上的衔接。英语有大量的关系词(如when, whose等)、连接词(如and, so…that等)、介词(如in, onto, according to等),加上各种形态变化等手段来完成衔接的使命,使英语句子结构紧密,逻辑严密,可读性强。因此,汉语的流水句和分句,在译成英语时,需要化简为繁,组合成复句或长句。而事实就是学生在汉译英时,往往会受到源语框架的影响而忽略连接词的使用。
由此可以看到,学生的译文之所以质量不高,是因为汉英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少有学生真正意识到个中差别,导致翻译过程中依葫芦画瓢,译文不符合英语的语法要求和表达习惯。
三、英汉语言差异
连淑能(1993)曾提出过英汉语言的十大差异,比如形合与意合,静态与动态,客体与主体等。其中最大的差异,或者说最值得探讨的差异,就是形合与意合。此处就汉语和英语两种不同的语言类型从以下两方面做简要分析:分析语与综合语、意合与形合。
1.分析语与综合语。汉语属于分析型语言,即汉语中的语法关系主要不是通过词本身的形态来表达的,而是通过虚词、语序等方式来实现。汉语常常以词汇手段来表示语法意义,比如表征名词的数的数量词,比如“两件”、“五辆”、“九只”,表征动词的时态、语态、语气的“着,了,过”,“把、被”,“啊,吗,吧”,等。而英语则是从综合型向分析型发展的语言,偏综合型,也就是说英语主要通过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来表达语法意义。英语的词汇形态变化相对丰富,且集中体现在动词的形态变化上,形成以动词形态变化为主的句法结构模式,语义与句法形态紧密结合。(邵志洪,2005:7-8)
形态学包括词汇形态学和屈折形态学两种。前者针对构词,着重研究词缀的变化,汉语在利用词缀构词方面不管从数量还是从种类上看都远不及英语。所以在汉英翻译时,往往需要转换词类,以求更加自然通顺的表达源语的意思。比如,同样是汉语“评估”,译成英语时,可能是assess, 也可能是assessment。后者针对语法,着重研究词的屈折变化。而汉英两种语言在词的屈折变化上有着明显不同的倾向。英语最典型的屈折变化体现在名词的数和动词的语态及时态上。汉译英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汉语用词汇表意,英语却是用形态表意。英语中名词的数的变化,例如:
[11]我有两本字典。/ 这本字典对你很有帮助。
I have two dictionaries. / This dictionary is helpful to you.
动词的屈折变化,例如:
[12]人的思维活动很奇怪,有时会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毫不相干的事上去。我看电影《火烧圆明园》,忽然想起一些幼小时的事,从记忆深处走出一个久已淡忘的人来……(徐三下老师 刘厚明)
Peoples minds work in very capricious ways, sometimes jumping from one seemingly unconnected idea to another. While I was watching the movie, The Burning of Yuan Ming Yuan, the memory of my childhood and a man whom I thought I had long forgotten came to me from the depths of my past.(陈家宁 Elizabeth West 译)
例[12]中汉语的动词不会随时态变化而发生形态上的改变,其时态主要是靠读者意会,但是译文中,丰富的时态变化则通过动词的形态变化清楚的体现出来。原文第一句的内容并无特定的时间状语,只是泛泛而谈,所以译文谓语work采用一般现在时,后半句是对前面内容的补充说明,采用非谓语的形式jumping。第二句虽然也没有明确的时间状语,但是“我看电影《火烧圆明园》,忽然”,暗示“走出”是一个过去发生的行为,译者采用了过去时came,而时间状语采用过去进行时was watching,正好衬托出came这一行为的“忽然”发生。“从记忆深处”和“久已”暗示“淡忘”这个行为发生更早,所以使用过去完成时had forgotten更为恰当。
又如前例[6],该句是对木板年画的介绍,所以基调定为一般现在时。其中第二小句中的“自……以后至……之前”,表明陈述的事情发生在过去某一特定时间段,所以在翻译时此处应使用过去时was,而最后一个小句中“至今仍”又把时态带回到现在时。
由此可见,汉语主要不是通过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来表意,相反,英语则明显偏重于通过词的形态变化来表意。汉英翻译的过程,就是英语运用形态手段表达汉语的语法意义,从而构建起英语的语义结构。
2.意合与形合。意合指词句间的连接主要凭借语义或者逻辑关系来实现,而形合则是指词句间的连接主要依靠连接词或者语言的形态手段来实现。汉语不重形式,句法结构不必完备,重在意合,动词的语法作用没有英语那么突出;英语表达则高度形式化、逻辑化,以动词为核心,句法结构严谨。意合与形合是汉英对比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汉语文字结构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灵活,其特点是离散性,靠逻辑关系来实现词语之间的连接,对话人需要自己解读,通过意会来理解语义。而英语语言的特点是勾连性,靠词汇的形态变化和各种关系词、连接词、介词来实现词句之间的衔接。例如:
[13]出名要趁早。
Its better to be famous before its too late.
[14]酒不醉人人自醉。
It is not the wine that intoxicates but the drinker who gets himself drunk.
[15]我细细量过九十九次标高,实属“终生残废”系列。(终生遗憾 木木)
After making perennial efforts to measure my exact height, I reached the inescapable conclusion that I was permanently handicapped.(孙艺风 译)
[16]他没动,也没敢看,只盼快点到站。(钱包 祝承玉)
The thief stood motionless, eyes lowered, searching only for the next stop.(何志范 譯)
以上几个例子,汉语里面都没有表示明显的连接手段,其语法意义和逻辑联系往往都是隐藏在字里行间,而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译者都对原文的语义进行了重新构建,通过词汇的形态变化(例[16])和各种衔接词(例[13]-[15])将语义揉捏组合,使译文的语法意义和逻辑联系得以清晰地呈现出来。
汉语形散神聚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马致远的《天净沙 秋思》:
[17]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Crows hovering over rugged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 - the day is about done.
Yonder is a tiny bridge over a sparkling stream, and on the far bank, a pretty little village.
But the traveler has to go on down this ancient road, the west wind moaning, his bony horse groaning,
trudging towards the sinking Sun,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home.(翁显良 译)
整首散曲仅仅28个字,完美地表现了漂泊天涯的旅人的愁思,描绘出一幅悲凄的画面。本诗开篇一系列名词,把十种平淡无奇的客观景物巧妙地连缀起来,由近及远、动静皆宜,也体现出汉语综合性思维之下注重对整体的把握,其语法意义和逻辑联系都是隐性的。全文不用任何连接词,全凭意合,即整体意思的连接贯通不是借助于形式手段,而是靠内在的逻辑关系来构建空间性。但是一旦译成英文,必须添加谓语动词,并借助连词、介词、分词等形式来实现形合。如果说原文如同一盘珍珠,那么译文就好比一串珍珠,英语的主谓结构犹如一根线,在它的统辖之下,其他成分在分词和各种连接词语的帮助下,紧紧围绕这根线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可以看出,汉语的语法是柔性的,而英语的语法是刚性的,尽管翁显良先生采用了散文体的译法,尽量再现原诗的内涵,且译文意思更加完整易懂,然而有了语境却失了意境。汉语诗歌的不可以译性正好诠释了英汉在形合与意合上的差异。
因此,汉译英的过程,就是对形散的源文进行逻辑分析,使语义条理化,再按照目的语的形式要求使其各就各位,语义转换得到最大可能实现的同时,又完全符合目的语强制性的语法和句法要求。再如:
[18] 我想画的最高境界不是可以读得懂的,一说到读便牵涉到文章词句,便要透过思想的程序,而画的美妙处在于透过视觉而直诉诸人的心灵。(读画 梁实秋)
To my mind, the best of painting is not to be read so as to be understood. Reading entails words and texts. It is possible onl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while what is beautiful and unique about a painting appeals, by way of visualization, direct to the heart.(朱纯深 译)
译文通过各种介词、连词等衔接手段把原文架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其中“读得懂”译为to be read so as to be understood,so as表示结果,强调“读”这一行为导致“懂”这一结果,和后面的“透过视觉”的方式形成对比,使语义的内在逻辑关系更加清晰明确。
四、英汉时空观差异
前文所述英汉语言的差异,都只是表象,正如王文斌(2013a、b)所提出的,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不同语言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时空观。语言是思维模式的体现,折射出使用这一语言的民族对世界的经验方式和思维方式。任何一种语言都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但人类的时空意识必然含有人类的主观成分,因此难免会导致与客观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差异,由此导致不同的语言在时空性上各有偏向。英汉语言的本质差异,在于英语的时间性特质和汉语的空间性特质。
事物的行为、动作、变化是时间的主要表现。英语注重从事物的行为、动作、变化中去把握时间,就是注重事物的时间性。其最有力的佐证就是英语借用动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不同的时态,借以指明事物、行为、状态的时间关系,这一点是汉语所不具有的。如例[12]的译文,借助动词的形态变化体现丰富的时态转变,而原文的时态标记远不如译文明显。虽然英语表达偏爱名词,这样可以在谓语动词的引导下,串连起丰富的内容,使表达简洁凝练,行文自然,便于表述复杂的内容,但是我们却很容易发现英语中大量名词派生于动词,语法上为名词,语义上仍然保留着动性(王文斌,2013a),比如:decision,gradation,等。
对标英语,汉民族的思维则重于事物,表达事物的名词特别受到重视,所以英语重动词,汉语重名词(郭绍虞,1979:117),汉语的语篇往往由大量的词组构成,而其中以名词性词组为最。如例[17],整首散曲几乎全是名词的排列,可见汉语擅长借用体现空间的名物来表达具有时间性的行为或动作。关注事物就是关注空间,由此形成一个特殊的语法范畴,那就是量词。量词的作用就是提供名词所指事物的形状、数量或其他的感知性限制特性,对事物进行形状和离散性的描述。即便是认知抽象事物,汉民族也倾向于采用形状来描述,比如“一陣悲愤”、“一线生机”、“一片繁华”(孟瑞玲 王文斌,2017)。名词的视觉空间属性反映了汉语对空间的偏爱,事物的形状和离散性正是事物空间性的典型表征。汉语表达少用连接词,体现出汉语的空间聚集性(王文斌,2013b)。
[19]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荷塘月色 朱自清)
从例[19]可见,汉语是一种空间性语言,少用连接词和形态手段,完全依靠空间的聚合,以语义引领结构,体现出一种非线性的空间特质。在翻译成英文时,则需要运用各种衔接手段,来体现时间观的连接性和延续性,使句子结构呈现线性延伸。其结构可表现如下:(alongside)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even in the daytime) 白天(there is)也少人走,(and now at night)夜晚(it)更加寂寞。(all around)荷塘四面(there are)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on the side where)路的一旁,(there are)是些杨柳,(interlaced with)和一些不知道(whose)名字的树。
再如下例:
[20]河身多的是曲折,(in)上游是有名的拜伦潭,(where)当年拜伦常在那里玩;(there is)有一个老村子叫格兰骞斯德,(and)有一个果子园,(where)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树荫下(sipping)吃茶,(as)花(or)果会掉入你的茶杯,(and)小雀子会到你桌上来啄食,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我所知道的康桥 徐志摩)
由此可见,英汉语言一系列的差异,比如汉语多量词,英语多介词,汉语重连贯,英语重衔接,等,都是表象,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两个民族时空观的不同。这也直接导致我们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中国学生在进行汉译英时,先入为主套用汉语的思维模式,违背了英语的语言特性和规律,生硬的把英语词汇堆砌成句,使得译文不仅语法错误频出,且句子生硬而没有可读性,最后得分不理想。其实写作也是一样,不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即使英语词汇量很大,语法也没有问题,但是写出来的文章读起来就是有违和感。
五、结论
英汉两种语言有着各自的特点,对此学界进行过诸多对比研究。然而语言仅仅是表现,思维才是内在。英民族认知世界时偏重时间,汉民族则偏重于空间,因此形成了英语更具时间性特质而汉语更具空间性特质。这才是英汉两种语言外在差异的根本原由。弄清楚这一点对于教师如何指导学生汉译英、学生如何打破思维的条条框框进而反思改进译文,都大有裨益。
注释①:文中CET-4汉译英的原文和译文均出自2016年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谢忠明编著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历年真题精解》。
参考文献:
[1]邵志洪.汉英对比翻译导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2]彭维宣.英汉语篇综合對比[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3]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4]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王文斌.论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13a,45(2).
[6]王文斌.论英汉表象性差异背后的时空特性-从Humboldt的“内蕴语言形式”观谈起[J].中国外语,2013b,10(3).
[7]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孟瑞玲,王文斌.论汉英名量搭配差异背后的时空特质-以“piece”的汉译与“群”的英译为例[J].山东外语教学,2017,38(1).
[9]杨平.名作精译——《中国翻译》汉译英选粹[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