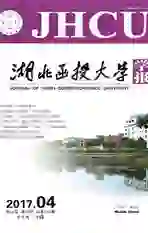王阳明心学的个体化和普遍化倾向
2018-01-23董飞
董飞
[摘要]心学中的心既是个体道德的依据也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它是道德良心的依据和个体良知的呈现,具有鲜明的个体化的倾向。同时它也遍及宇宙万物之中,是万物本体。道德不能仅仅只存在于个体的良知之中,还需具有公共性,因此心不能仅局限于个体之内还应具有普遍化的趋势。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张力导致心学后学中产生了各种分歧,影响远及日本韩国的。这种张力的存在实际上是王阳明试图解决道德良知的私人化与公共性的矛盾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个体化;普遍化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7)04-0093-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7.04.046 [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心学中的心既是良知也是万物本体。《传习录》中本体有时指“心”本来存在状态,有时也指事物存在的依据。既然良知是宇宙本体遍及万物,那么草木瓦石也应有良知。王阳明曾直言“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传习录》下,第274条)。这是由王阳明的基本命题“心即理”所推导出来的。吴震的《<传习录>精读》中细论述了如何从“心即理”推导出良知为宇宙本体的过程。
首先,朱熹认为心和理是二,唯有通过功夫最后打并为一。而阳明则认为心理不是两件,本身就是一。万事万物中都有理的体现,理都在心中具足了,很自然得到了“心外无理”的结论。功夫的重点也从外在的事物转到个人的“心”上。
其次,从心的感知功能上看,阳明通过“心意知物”论述了心与物不分离的关系。《传习录》卷上,第78条中说:“问:‘身之主为心,心之灵明是知。知之发动是意。意之所着为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这里指出“意之所着为物”,说明“物”不是脱离了“意”独立存在的东西。意也不能脱离物而孤零零存在,不能“悬空”。如《传习录》下,第201条:“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挌之,去其人欲而归于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的功夫。”由此处“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可知,心物二者处于一个整体的结构中,即“物”并不能独立于意识之外。在《传习录》南镇观花一节更明确了“物”唯有在意识活动中被感知才具有意义。意识之外的物对于主体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存在。
这样万物的存在都不能离开主体意识参与,宇宙万物因主体而显现出来。阳明讨论心物关系的目的在于主体的道德实践,他将郑玄对《大学》中“格物”的解释——“物犹事也”,改为“物即事也”,将格物的含义从纯粹的认知的意义转为侧重道德实践的意义。当阳明提出“致良知”的学说时,良知作为心体,再同前面心物关系的论述贯通起来,自然就得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的结论。
王阳明从主体的心出发,不断向外扩充直至囊括整个宇宙万物,实现理论上以心统摄一切的彻底一元论倾向。杨儒宾在《“性命”怎么和“天道”相贯通的——理学家对孟子核心概念的改造》一文中提到,“理学家从《孟子》处借得诠释的正当性时,事实上已作了语义的转换工作。孟子的“性善”与“良知”两个核心概念原本只是纯粹的心性论语汇,理学家将它们扩充到形而上学去,天道性命因此相贯通”。也就是说孟子讨论良知良能等有关问题并无讨论事物本体的意图。但是孟子提的这些概念后,经历了李翱、张载等人打磨后,心性问题从道德界开始转向存在界。作者提到:“如果比较理学家和孟子的人性论及良知理论,会发现两者在施用的范围上有明显的不同。孟子论人性,论仁义内在,论良知,他的这些概念都是在道德心的范围,亦即都隶属于一道德主体。而理学家的这些概念所施用的范围都不仅止于道德界,而且也遍布到存在界。枯槁有性,仁为宇宙之生意,良知是乾坤万有基,这些语言都出现了。”有了这样的一个传统,阳明提出“心即理”,将主体的道德,同宇宙万物的存在打通,共一个本体,也就不显得特别突兀了。
从“心即理”推出“良知是宇宙本体”,良知完成了从个体到宇宙的一个跨越。其内在逻辑是:作为个体的道德良知是私人的,即所谓的良知自知,良知独知。如果良知仅仅局限在个体中则丧失了普遍性,无从指导社会道德实践。因此良知必须具备普遍性。假如良知本体也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则良知遍在一切处,自然也就可以成为道德实践的社会公共标准,避免了个体局限。阳明的“心即理”把原来朱熹的外在天理这一普遍性原则纳入到主体的“心”之中就具有将个体和普遍结合的意图。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虽然阳明指出良知是具有普遍性的,可是这种普遍性也是很模糊的。首先良知具有独知的特点,人可以直接体悟到自己的良知,却无法直接把握他人的良知。独知和自知毕竟隔绝了个体间良知相互比较的可能,丧失了作为道德标准的作用。其次良知无知无不知的特点说明良知并不是具体的道德准则和见闻之知,因此良知总是一种无分别的直觉。这种“无知”可以透过“信得及”的保证达到“无不知”来保证。(《传习录》卷上,第115条有:“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功夫,诸公需要信得及。”)。但是在凡人身上,良知未曾完全显现出圣人的完满状态,“信得及”也有可能成为一种独断,并成为放纵自我的口实。阳明弟子中就有“简略事为,言行无顾,甚者荡灭礼教”(《王阳明全集》下《大学问》跋)的现象。
阳明哲学中个体与普遍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虽然陽明意识到这个问题,也试图通过理的普遍性来避免价值判断私人化标准的倾向,却一直未能避免向这两种倾向分化的趋势。阳明在世时,弟子钱德洪和王畿曾就阳明的“四句教”产生争论相约找王阳明决断。这一争论可以算作是后来心学分裂的征兆。王畿重视心体,认为“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如说意是有善有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传习录》卷下,第315条)。而钱德洪重视功夫,他认为:“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贝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传习录》卷下,第315条)重视心体,则有个体化倾向;重视功夫,则容易同朱熹学说混同,有普遍化倾向。之后心学分裂为数个派别,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记载阳明后学分成了七个学派,日本的冈田武彦则根据王畿的《抚州拟岘台会语》记载的六个派别,自己在此基础上总结为现成派(王学左派),归寂派(王学右派),修正派(王学正统派)。
这两种倾向在韩国和日本的心学中也有所体现。比如韩国和日本的心学代表人物郑齐斗和中江藤树。根据《东亚阳明学》的说法,郑齐斗以体用来理解良知是为了克服阳明学说中“即良知的浑然一体性、完全性、主观性及过分强调主体能力等体用问题”,为了“防止出现良知盲目强调和独断行为的可能性”。他的具体做法是“靠近朱子学的理气性情体用论来达到”(《东亚阳明学》第三章阳明学在韩国的展开,第66-67页)。朱熹的理是外在于心且具有普遍意义的。郑齐斗向朱熹靠拢,目的就是为了平衡阳明学说中个体化倾向。而在日本的中江藤树则将良知改造成了人格神——上帝,使得良知具有了绝对的主宰性,目的是克服良知现成论中“任情纵欲”的倾向。《东亚杨明学》的第五章《霞谷学与中江藤树的比较理解》中提到,中江藤树确立的“皇上帝”(见于《藤树集》卷三,“天太虚主宰指所谓皇上帝”)是人格神,并非是无声无臭,内在抽象的观念之理,皇上帝能命令天地万物一一观察敬与怠、勤与逸,用福善祸淫进行审判。中江藤树虽然接受了致良知的命题,但是却没有提到阳明的“心即理”。很明显“心即理”的个体化的倾向更深,不提“心即理”与其设定外在的人格的上帝是一脉相通的。中江藤树的这种做法则是更靠向普遍化的一端,已经大不同于阳明心学了。
由此可见阳明心学内个体化和普遍化的张力,从其理论内部以及学派分裂的事实中都能得到印证,甚至在传播到韩国和日本后也未能幸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