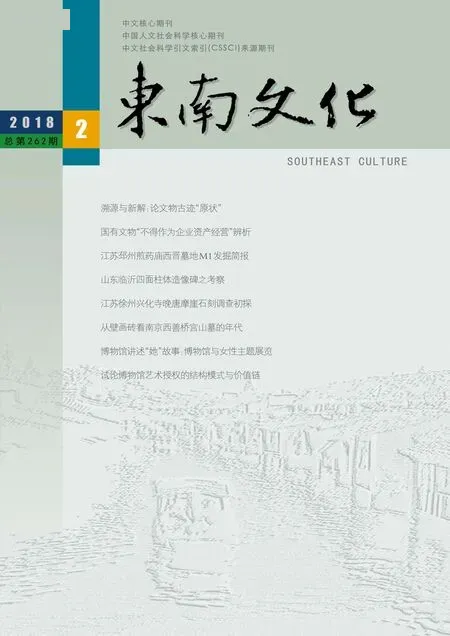溯源与新解:论文物古迹“原状”
2018-01-23王璐
王 璐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陕西省古迹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西安 710055)
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有一条充满了“批判”的路线,那就是人们总是在与过往的不断对话中找到处置历史的方式,形成保护运动的伦理观,从而找到自我的定位与认同。因此,文化遗产作为拥有诸多价值的实体,总是要被评判和选择,不可避免地带有评判者的主观烙印,且立足于评判者所处的时代。
“不改变原状”作为我国文物古迹保护的核心原则,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其他相关法规条例,映射出我们面对过往的态度和历史观,也传达出何以确定一种被保护对象的理念。然而,它从被提出至今,不乏各种争论和相异的理解,对于“原状”的阐释也总是在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目的的主观评判中产生不同的解读。究竟是“原物”、是“初建时的原状”、是“某一时期的状态”、是“各个时期叠加的状态”、是“原真状态”、还是“体现价值的状态”,人们争论不休。在我们对西方经典保护理论逐渐反思、后现代思潮涌动的当下,我们更应该客观地追溯它思想的起源,理解它理念的闪光之处,思考它带来的问题,提出我们在今天对它的理解,并眺望它的未来。
一、过往我们如何理解“原状”
(一)西方:对于“原状”的认知变迁
“原状”概念来源于西方经典保护理论,其萌芽于文艺复兴,诞生于启蒙运动,激辩于反修复运动,成熟于二战以后,反思于后现代社会。
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萌芽,意识到今天与过往的距离感,对历史产生兴趣的同时又热衷于摆脱历史束缚,古迹成为可以被翻新、重建、再生的对象,此时尚未形成对“原状”的清晰认知。
事实上,“原状”概念的真正产生可以追溯至18世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激发的“历史性觉悟”主导了古迹保护思想的诞生。线性发展的历史观引发人们以“独一无二”的观点来看待艺术品和古迹。德国学者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最早提出Original和Genu⁃ine、区分了“原物和后加物”,尊重原创者的劳动及其美学价值,极力主张对艺术品“原作”进行保护。与此同时,新古典主义和“如画”运动的兴起,使得“废墟美学”于18世纪末建立起来,这成为“原状”的美学起源。
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的剧烈转型导致了人们对工业时代的不自信和对过去文明的仰慕,此时古迹风格上的一致和纯粹成为修复的目的。至19世纪上半叶,伴随着“折衷主义”和“实证主义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建筑风格上完整状态的追求和修复战胜了对原物及原作者的尊重。而随着“反修复运动”引发的激烈批判,人们开始强调保存现实中“真实而纯正的状态”、保留“不同时期的改变和岁月的痕迹”,最终形成了对“现代保护运动”的强大推力。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现代保护思想逐渐理论化的这一时期,终于确立了将各个时代的叠加物视作价值平等的保护对象,新的保护观念登上历史舞台。
国际会议和国际宪章的推动使得相关古迹保护思想在全世界范围扩散。1931年《雅典宪章》强调对纪念物的各个时期的不同风格予以尊重和保护;1964年《威尼斯宪章》再次重申“各个时代为一古迹之建筑物所做的正当贡献”都必须得到尊重,并将这种时间岁月沉淀的真实状态扩大到更大的“环境”范围,成为国际上主流的保护理念。
20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后现代哲学基础上,人们逐渐对“过度理性”的经典保护理论进行反思。虽然“文化意义”已经在《威尼斯宪章》中提及,但真正将其作为保护对象的标志性文件是1979年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澳大利亚国家委员会(Australia ICOMOS)完成并实施的《巴拉宪章》。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重新评估了保护的文化语境,“真实性”逐渐开始接受文化多样性、延续文化传统的大背景。2014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的ICOMOS第18届大会以“遗产范式的转换”(Heritage Paradigm Shift)为题,强调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它不仅具有一定的物质意义,还有更广泛的文化意义,即从对“原物真实”的保护走向了“价值意义”的传承。
(二)中国:从“原状”的提出到多元释义
1935年《山西省各县历代先贤遗物及名胜古迹古物保存办法》中出现“改变其原状”“恢复原状”的表述[1],当是这一概念第一次在中国政府文件中被界定。自此,“改变”“恢复”“原状”这些词语与中国文物古迹相关联并被官方延续下来。在此之前,民国文物保护法规中接近“原状”的表述有1913年《河南保存古物暂行规程》中“不失其原有之价值”[2]及1928年内政部《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的“本来面目”[3]等用语,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释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物法规文件起初对“原状”前的动词有多样的提法,如“恢复”“保护”“保持”原状,对其变动时亦有“改变”“变更”原状的说法。直到1961年国务院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不改变原状的原则”“恢复原状或者保存现状的原则”被正式明确;至1982年“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被写入《文物保护法》,随后又被写入《准则》,并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我国文物古迹保护的第一要义。而追溯“原状”在中国保护理论中的源流,从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引入日本学者关野贞1929年在世界工程学会发表的《日本古建筑物之保护》一文中所提出的“以不失原状为第一要义”至今,国内对于“原状”的阐释与讨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阶段一:“初建时的原状”
在1932年刘敦桢翻译的关野贞讲义里,“修葺的原则”这一部分中,可以看到“初建时的原状”概念涵盖了“原来的构造与式样”“建筑物的地址”“原来款式”“建筑物内外着颜色”的内容,其中第三条特别提出:“建筑物的现状,因为增改的原故,也许与原状不同。但若增改之处,无碍大体,则修葺时应仿照现在模样。设使原来构造款式,已确凿证实,则照原来款式重修。”[4]这句话体现出:首先,此时的认识“现状”是不同于“原状”的;其次,“原来款式”是优先于“现状”的,除非现状的增改之处无碍大体;再次,“设使原来构造款式,已确凿证实,则照原来款式重修”,这句话道出了恢复原状的意思,所谓的“原来款式”,此处则可理解为建筑物原初建造时的法式与式样。
反观日本,在1929年制定的《国宝保存法》中即强调了“当初式样复原”,即不改变文物的样状原则。荣山庆二解释道:“在明治维新时,日本也曾崇洋求新,忘了自己的古老传统。但冈仓天心提倡复古、找回自己的文化,关野先生则尽力于文物建筑研究,遵立了依据原始式样复原的原则。”[5]
正是由于国外学术思想的传入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影响,伴随着中国营造传统与新史观的碰撞,“保存或恢复原状”的思想逐渐在中国传播。梁思成在1935年《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中说:“所以我以为不修六和塔则已,若修则必须恢复塔初建时的原状,方对得住这钱塘江上的名迹。”[6]在《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中的看法是:“我们须对于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而同时在外表上,我们要极力地维持或恢复现存各殿宇建筑初时的形制。”[7]他在1941年写给孔祥熙的信中建议将重庆文庙修葺工程分为暂时计划及永久计划,暂时计划“以足蔽风雨保持现状不再浸漏”,永久计划则“以恢复孔庙古建筑原状为原则,在外表上须尽力求其恢复原状……”[8]。由于对原初建造时法式与形制的强烈追求,以及西方“风格式修复”在文化心理上的相似,这与同时期国际上广为传播的《雅典宪章》在价值理性上有一定程度的背离,也埋下了我国在随后半个多世纪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反复争论的种子。
2.阶段二:“整旧如旧”
“整旧如旧”无疑是我国文物古迹保护与建筑整修在一段时间里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梁思成所倡导的“整旧如旧”首次正式见于1963年他发表的《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一文,他在文中针对“焕然一新”而正式提出“整旧如旧”[9]。事实上,早在1934年,他就在《修理故宫京山万寿亭计划》中说:“修理古物之原则,在美术上,以保存原有外观为第一要义,故未修理各部之彩画,均宜仍旧,不事更新。……所绘彩画花纹色彩,俱应仿古,使其与旧有者一致。”[10]从文中看出,梁思成谈及的第二个“旧”字与焕然一新中的“新”字相对,是指“外观”所呈现的“苍老面貌”。而梁思成并不赞同拉斯金(John Ruskin)将衰朽视为历史的馈赠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11]。梁思成所看重的是正统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也映射出我们民族在经历战争的破坏之后弘扬民族精神的时代愿望。对于科学性,则是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恢复原初形制和“尽量采用力学上之新智识及新材料,以匡救我国古式结构法上之弱点而求其永固”[12]。
3.阶段三:对于“原状”的多元释义
然而,《威尼斯宪章》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传入中国,其强调“各个时代为一古迹之建筑物所做的正当贡献必须予以尊重,因为修复的目的不是追求风格的统一”,这给当时国内思想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人们也开始了解到原来“修复”不等于“复原”。
此阶段,学界对于什么是“原状”,表现出极其多元的解读。1986年文化部发布的《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等修缮工程管理办法》中“不改变原状”的原则“系指始建或历代重修、重建的原状”。1985年,祁英涛在《古建筑维修的原则、程序及技术》一文中指出,“不改变文物原状,就包括了恢复原状和保存现状的含义在内”[13];1986年他提出“‘恢复原状’这是作为维修古建筑的最高原则而提出来的”[14]。1990年,罗哲文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将“原状”总结为:(1)初建时的面貌;(2)鼎盛时期为主的原状;(3)各个时代的原状;(4)原来建造时的原状(以现存实物的鉴定年代为准的原状)[15]。但是,这些对于“原状”的解释均指代不明,甚至可以说见仁见智。罗哲文认为,保存现状指“在原状已无可考或是一时还难以考证出原状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原则,又是一种由于恢复原状需要较大的投资和较大的技术力量,目前还不能进行时所采取的措施”[16],这一点承袭了梁思成的观点,但增加了“保持现状不是一丝一毫也不能动,我们所要保持的现状是有价值的部分”[17],这道出了“原状”与“价值”的关系。1990年吴晓、黄滋在《中国文物建筑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中指出:“需求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包含在物质性的含义之中,所以,今天想要把它恢复到某一个固定的时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18]1992年建设部发布的《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中指出“原状系指古建筑个体或群体中一切有历史意义的遗存现状”,则更接近《威尼斯宪章》。20世纪90年代末,阮仪三的“整旧如故、以存其真”观点引起了不小反响,搭建起“原状”与“真实性”之间的桥梁。乔迅翔的观点是:“‘原’作‘原真’解,‘原状’即‘原真状态’之意,强调本质上的‘真’。不改变‘原状’即不改变其‘真’。”[19]
《威尼斯宪章》指出保护古迹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现存状态”,正体现了古迹作为历史见证的价值,在其影响下形成了《准则》中“不改变原状”的文物保护原则[20]。2002版《准则》第21条指出“保护现存实物原状与历史信息”,阐释中进一步明确了“原状”的主要的四种状态[21]。“原状”正式与国际接轨,指向了《威尼斯宪章》所谈的各个时代叠加物所形成的现状;同时,这条阐释在内容上衔接了中国式“保存现状、恢复原状”,也吸纳了西方的“修复”理论。但随后,这种合璧又引发了激烈争论。2005年的《曲阜宣言》就是对《准则》进行针锋相对地叫板:“‘原状’应是文物建筑健康的状况,而不是被破坏、被歪曲和破旧衰败的状况。衰败破旧不是原状,是现状。现状不等于原状。不改变原状不等于不改变现状。对于改变了原状的文物建筑,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要尽早恢复原状。”[22]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从思想和制度上已基本与国际同步,《准则》的推出和对《巴拉宪章》思想的吸收也促进了我国保护思想逐步形成共识。
4.阶段四:“体现价值的状态”
2002版《准则》对“文物古迹”的界定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或人类活动遗留的具有价值的不可移动的实物遗存”,并澄清了保护是以“真实、全面地保护并延续其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为目的。2015版《准则》中对“原状”进行了新的定义:“不改变原状:是文物古迹保护的要义。它意味着真实、完整地保护文物古迹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及其体现这种价值的状态。”[23]这道出了“时间叠加的现状”正是“价值”的源泉。在更加倡导文化多样性、强调人类情感、注重社会参与、关注可持续发展与多层次保护管理的今天,认识“原状”中蕴含的“价值”和“意义”正成为保护工作的基础和通往未来传承之路的桥梁。
二、当下应如何理解“原状”
随着时间推移,对保护理论的吸收和对现实的批判使得学界对“原状”的解释不断演进。“原状”思想揭示了现代保护的目的是确定被保护和存续的“实物”对象——从第一历史原作到认识到绵延的“时间”之于“实物”的价值,形成了对“真实而客观”的“现状”给予的尊重、敬畏以及美感——这些正是一切保护行为的前提。然而,它在当代却引发了反思,比尼亚斯(Salvador Muñoz Viñas)指出,现代保护理论“本质上是基于它的物质属性和组成成分”且走向了“物质至上主义”[24]。
事实上,保护的观念总是立足于评判者所处的“当下”,标准即是打着时代烙印的“价值”。那么,当代该如何理解“原状”这一“体现价值的状态”?价值是否只蕴含在“实物遗存”当中?什么样的原状构成揭示了其对于人们的重要意义?这成为保护工作的首要问题,也就是说只有认识清楚什么构成了“原状”,“价值”才能为我们所“看见”。
下文从原物、原信息、原地点、原场所精神、原用途五个主要层面,揭示“原状”蕴含的重要意义及表现形式。
(一)原物
“原物”指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承载价值的实物遗存。在保护历史上,基于历史和美学两个维度的经典保护理论,主要针对保持对象证据的、物质的真实存在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而展开,随着科学特别是考古学、历史学等的发展,对“原物”的保护成为遗产保护的绝对主流。长期以来,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中,修缮、修复甚至是重建面对的都是实物对象,因此往往将“原状”与“原物”相等同,2002版《准则》第21条就将“原状”直接指代为“现存实物原状”。
正如前文所述,在西方,认识到实物遗存中所包含的“岁月价值”经历了两个世纪。虽然1931年《雅典宪章》将“岁月价值”涵盖进去,但是在我国,那时还没有走出“重式轻物”[25]的时代。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威尼斯宪章》被介绍到中国,我们才开始逐渐认识到要保存各时期的证据。时至今日,视历史上每个时代的叠加物都是“原状”的组成部分已形成共识,绵延的往昔都值得尊重,已成为普遍的认识。原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亦是包含遗产价值的重要部分,保护行动应当有助于而不是妨碍人们对它的理解。
(二)原信息
“原信息”指现状中隐含的、或从中揭示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信息。从《奈良真实性文件》开始,一系列文件反映出当代保护工作注重建构在“信息来源”上的真实性与广泛性。2015版《准则》指出,“保护的目的是通过技术和管理措施真实、完整地保存其历史信息及其价值”,这事实上映射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阐释学为基础的后现代历史观,其认为历史在于解释历史现象,我们对其进行干预的本质是保护对象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而“原物”正是“原信息”的物质载体。我们通常是通过保护“原物”而达到保护“原信息”的目的。因此,在对古迹进行保护操作时,应首先要求不能对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造成扰乱、篡改和破坏,这是后续工作的根本前提。这个“原信息”包含了历史上各个时期对遗产所作的贡献,揭示某一时代的信息时不能以破坏其他时代信息为代价。
原信息可以从原物中直接读取,亦可以通过考古等手段进行揭示、延伸。比如通过对一段城墙遗迹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整个城防格局,在保护时就不只局限在城墙遗迹的物质实体,所揭示的格局信息、位置都可能成为阐释的对象。所以,“原物”中所隐含信息的保存及准确读取成为确保真实性的关键。而对于相关法式、形制、风格、工艺、技术的探究,如果不是建立在对现状中客观信息的直接读取或揭示的基础上,则当视作研究。
(三)原地点
“原地点”指古迹所在地方、环境要素及其关联意义。遗址,英文为Site,原意“地点”“位置”,这一解释道出了遗址所在地点的重要性。保护理论形成初期,古迹“地点”的景观风貌和历史价值被看重,这反映在《雅典宪章》《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等一系列文件中。然而,遗产“地点”所包含的“文化意义”自《巴拉宪章》开始强调:“地点的地理位置是其文化意义的一部分。”[26]《西安宣言》亦重申古迹遗址在其环境中的存在意义,并充分拓展了“环境”概念。
存在主义现象学(Existentialist Phenomeno⁃lo⁃gy)大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人与地点以及通过地点与空间的关系根植于定居。”[27]从建筑产生之日起,“定居”就成为最原始的目的,而“定居”使得一块地域从周遭中分离出来,使得该地点产生“意义”。在界定遗产价值时,不可以丢弃地点的重要性和与这个地点相关联的自然因素。比如我国,无论是古代城址、墓葬,抑或是建筑,其选址与自然山水环境相融合,与天地产生了有意义的联系,这正是我国先民的营建智慧。回顾世界文化遗产的分类,“文化景观”遗产才开始强调其是“自然与人的共同作品”,反映了人类社会和定居地的历史沿革。而事实上,有哪个古迹不是“自然与人的共同作品”呢?要完整、真实地理解古迹,我们的视野就不能仅局限在物质实体及其信息上,还应看到定居地点所承载的意义和自然赋予它的价值。换言之,迁建、易地保护需要相当谨慎,只有当其成为唯一有效的保护手段时才能被允许。
(四)原场所精神(人、记忆、情感、特征、联系、定向、认同、现象、精神、意义)
“场所精神”(the Spirit of the Place)一词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登场,并逐渐成为保护界、建筑界共同探讨的话题。2008年ICOMOS第16届大会通过了《魁北克宣言》,提出“保护有形和无形遗产,以保存场所精神的建议,因为这是确保全球永续与社会发展既富创意又有实效的方法”[28],其宗旨在于“捍卫并促进场所精神,亦即场所的生活、社会与精神本质”。“场所精神”被界定为“有形(建筑物、场址、景观、路径、物件)和无形成分(记忆、口述、书面文件、仪式、庆典、传统知识、价值、气味),即实体与精神成分,能赋予场所意义、价值、情感与神秘”。“原场所精神”强调“场所”与真实“生活世界”的紧密联系,即人们从古迹现状中获得的真实的知觉、感受与经历。它与群体记忆、生命力、持续性和精神的捍卫有密切关联,由各个社会角色共同建构而成。
“场所”是人类记忆的一种物体化和空间化,每个场所都是唯一的,呈现出周遭环境的特征,这种特征由具有材质、形状、肌理和色彩的实体物质和难以言说的、一种由以往人们的体验所产生的文化联想共同组成[29]。1979年,《巴拉宪章》中就提出“场所”(Place)概念,同是1979年,挪威城市建筑学家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基础上提出了“场所精神”的建筑现象学理论。他将“场所精神”解释为“对一个地方的安全感和归属感”[30],认为定居包含着两种环境心理和认识活动:一个是“定向”,一个是“认同”。为了获得在自然环境中的立足点,人们必须有能力为自己定向,建立与环境的关系并获得安全感;认同则与记忆和文化有关,人们通过认识和把握自己在场所中生存的意义而获得归属感。这一理念强调遗产特征所表现的更为普遍、综合和整体的气氛,这也意味着“原状”中的精神价值被提到了与实物价值并驾齐驱的高度。
(五)原用途
“使用”是对遗产身份认定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的定居总是有目的的,或是居住、或是祭祀、或是防御、或是丧葬……“原用途”包含了遗产深刻的文化意义,揭示了遗产的本质属性。《巴拉宪章》第7条指出:“一个地点应当保留的文化意义就是该地点之用途所在。”[31]现代保护运动“过度理性”的历史观也导致“社会”维度的长期隐没,“原用途”或“原功能”中包含的价值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最后几十年,保护才转向接受文化的多样性意义,并认为这是延续传统的重要手段。
原用途中的价值主要存在于三种状况。第一,仍然存活的原初用途。对于遗产而言,原初营建时的用途如果还是“活态”的,那便是最大的意义所在,弥足珍贵。比如香火绵延的寺庙,仍然有原住民居住的历史街区、古村落,活态的祭祀圣地,局部仍然通航的运河等。第二,仍然存活的、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业已形成的与遗产相契合的用途、社会生活,其反映了岁月价值及遗产变迁。比如古迹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新功能或成为新用途的场所。例如遗址在废弃后逐步变迁为农田与村落,其与遗址或环境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三,前两种用途都已消亡。比如不再使用的古建筑、大部分的遗址。
“原用途”与遗产的“合理利用”或“延续性”相关。2015版《准则》第40条指出:“合理利用是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要内容。应根据文物古迹的价值、特征、保存状况、环境条件,综合考虑研究、展示、延续原有功能和赋予文物古迹适宜的当代功能的各种利用方式。”[32]《巴拉宪章》提出,“延续、修改或者恢复一种有重要意义的用途是恰当的,是要优先选择的保护形式”[33]。需要强调的是,“原用途”是遗产真实性、完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意义的重要表现,其保护的原则重在不应造成仍然存活、拥有价值的原用途消失,也就是尽可能地保护遗产的“活态”特征;当原用途消亡需要被赋予当代新功能时,则优先考虑“活化”或者最大限度地“唤醒”“阐释”原文化意义的功能。笔者认为,“活化”原用途并不等于“恢复原状”或者“重建”,更多的是指适度延续或发展与原初用途相容的功能和文化传统。当赋予遗产新功能时,一些国家提出了“适应性利用”[34],我国2017年出台的《文物建筑开放导则(试行)》中就规范了新功能的适应性要求。“原功能”与“传承”息息相关,新功能在符合保护要求的同时应能够最大限度地传承遗产价值与文化意义。以不相适应的用途替换原用途,或将活的遗产标本化、博物馆化,一定程度上都会使得原用途中蕴含的意义受到损失。
三、结语
原物、原信息、原地点、原场所精神、原用途构成了“原状”的重要内容。“原物”“原信息”以历史见证与科学为基础,以物质实体及信息为主要保护对象,自启蒙运动开启现代性始,引领文物保护运动一路走来;“原地点”“原场所精神”“原用途”以后现代新史观和哲学、社会学的发展为基础,是我们对过度理性的现代保护运动反思后的新认识,更加关注人类情感、遗产与社会的共生关系,并伴随着后现代性开枝散叶,成为认识遗产价值状态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1]李晓东:《民国文物法规史评》,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01—103页。
[2]同[1],第17—18页。
[3]同[1],第85—87页。
[4]〔日〕关野贞著,刘敦桢、吴鲁强译:《日本古建筑物之保护》,《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3卷第2期。
[5]〔日〕荣山庆二:《日本文物建筑保护及维修方法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6]梁思成:《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梁思成全集》(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355—370页。
[7]梁思成:《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梁思成全集》(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125页。
[8]胡懿:《湮没不闻的梁思成重庆文庙修复计划》,《世纪》2016年第6期。
[9]梁思成:《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文物》1963年第7期。
[10]梁思成:《修理故宫京山万寿亭计划》,同[6],第213—223页。
[11]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梁思成全集》(五),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79—184页。
[12]同[7]。
[13]祁英涛:《古建筑维修的原则、程序及技术》,中国文物研究所编《祁英涛古建论文集》,华夏出版社1992年,第169—236页。
[14]祁英涛:《当前古建筑维修中的几个问题》,同[13],第307—311页。
[15]罗哲文:《中国古代建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5—48页。
[16]同[15],第47页。
[17]同[15],第48页。
[18]吴晓、黄滋:《中国文物建筑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保护理论与技术的研究》,《东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19]乔迅翔:《何谓“原状”?——对于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原则的探讨》,《建筑师》2004年第6期。
[20]吕舟:《〈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修订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中国文化遗产》2015年第2期。
[21]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关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若干重要问题的阐述》,《中国长城博物馆》2013年第2期。
[22]《关于中国特色的文物古建筑保护维修理论与实践的共识——曲阜宣言(二〇〇五年十月三十日·曲阜)》,《古建园林技术》2006年第2期。
[23]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2015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国家文物局网站[EB/OL][2015-05- 28]http://www.sach.gov.cn/art/2015/5/28/art_1823_121246.html.
[24]〔西〕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著,张鹏、张怡欣等译:《当代保护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2页。
[25]常青:《关于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的反思》,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编《建筑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论文集》,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26]郭立新、孙慧译:《巴拉宪章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澳大利亚委员会关于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点的宪章》,贺云翱主编《长江文化论丛(第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226页。
[27]M.Heidegger.Building,Dwelling,Thinking.Poetry,Lanuage Thought.NY:Harper and Row,1971:157.
[28]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化资产总管理处:《魁北克宣言——场所精神的保存》,《文化资产保存学刊》2008年第5期。
[29]〔美〕罗杰·特兰西克著、朱子瑜等译:《寻找失落空间——城市设计的理论》,中国建筑出版社2008年。
[30]〔挪威〕诺伯舒兹著、施植明译:《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
[31]同[26]。
[32]同[23]。
[33]同[26]。
[34]〔美〕威廉.J.穆尔塔夫著、谢靖译:《时光永驻——美国遗产保护的历史和原理》,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