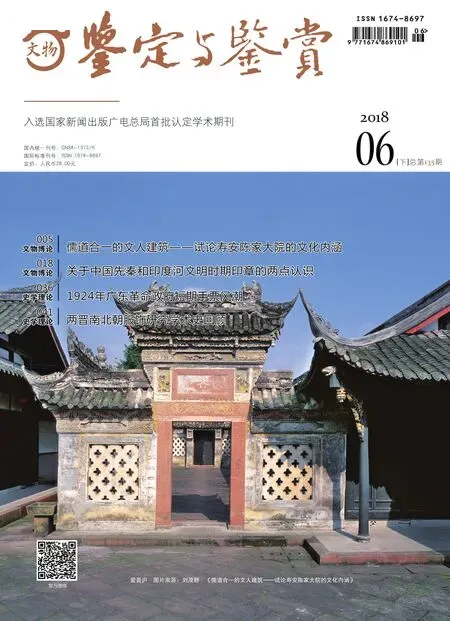徐家汇圣母院女工工场始末研究
2018-01-23冯志浩
冯志浩
(上海市徐汇区土山湾博物馆,上海 200231)
徐家汇的土山湾孤儿院一直被业界认为是“中国西洋画之摇篮”,土山湾的工场在工艺美术的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也被认为是中国早期职业教育的代表之一。
其实在徐家汇地区,同一时期还有另一座教育机构——徐家汇圣母院。早在19世纪中叶,这座圣母院内的女工工场就率先开风气之先,在长大的孤女中开展系统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让那些失去父母的女孩们获得一技之长,能够立足于社会。
和土山湾的孤儿工艺院一样,徐家汇圣母院内的女工工场也同样闻名海内外。但相比土山湾孤儿工艺院,之前论述徐家汇圣母院女工工场的文献较少,1949年后仅一本译作以及一些零散记录。因此,本文试通过回溯历史,从各类历史的记录中还原出圣母院工场的真实情况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1 徐家汇圣母院孤女院的缘起与女工工场的诞生
徐家汇圣母院的女工工场起源于徐家汇圣母院的孤女院。由于连绵战争以及天灾人祸,造成了大量的孤儿。1849年之前,教会对于孤儿和弃儿的处理方式都是在教友家庭寄养。然而1849年底,江南地区的洪水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出现大量的孤儿和弃儿。刚来华不久的法国教会便在青浦的小东圩(今属青浦赵巷)建造了第一座孤儿院。当年就收留了400个孩子,其中包括150个女孩。几经辗转之后,孤儿院搬到蔡家湾(今属青浦徐泾),尚有66个孤儿,其中包括23个女孩[1]。
1.1 徐家汇圣母院孤女院的缘起
土山湾孤儿院院长柏立德(Gabriel Palatre)曾在他写的《通讯》中提到:在当时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条件下,一旦遇到灾荒,这些无法成长成“壮劳力”的女婴,往往更容易被父母遗弃,甚至典卖。在当时简陋的医疗条件下,大部分孩子都夭折了,侥幸活下来的女孩们便留在了孤儿院里。
1851年,蔡家湾孤儿院中的女孩先是被接到唐墓桥(今属于浦东唐镇),交给当地的本地贞女管理。1855年3月,薛孔昭神父正式在横塘创办了圣母院,9月,圣母院移交给中国本地的贞女(后发展成本地的献堂会修女)管理后,贞女们就把孤女们接来横塘圣母院集中养育。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横塘圣母院又集体迁往张家楼避难。1864年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再次迁到徐家汇附近的王家堂(今徐汇区南丹东路天钥桥路附近)[2]。1856年,王家堂的孤女院交由中国的献堂会修女打理,并由其中有点文化的中国修女和守贞姑娘教授文化课程。
1867年,在当时总部设在上海徐家汇的耶稣会士们的邀请下,两个法国拯亡会的修女怀揣着对神秘中国的向往来到上海,也顺理成章地从中国修女这边接管了王家堂的育婴堂以及教授孤女们文化的任务。
拯亡会修女们来华不久,“江南代牧区”代牧郎怀仁交给这些女同胞们三项任务:一是培养中国修女;二是开办女校;三是开办育婴堂[3]。
1869年,徐家汇圣母院建筑落成。同年,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建立,之前王家堂的育婴堂、孤儿院等慈善机构全部集中于此。和育婴堂一样,圣母院内的女工工场也是“附属机构”之一[4]。
1.2 女工工场的诞生与培训
1869年,圣母院建筑落成之后不久便在这里建立刺绣车间,车间里的工人是已婚的孤女们。不久之后,花边车间也随之建立。建立这两个车间的初衷有两个:
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前收留的一些孤女逐渐长大。和传统的中国女性不同,这些女性从小学习全新的西方文化,会读书认字,已经很难再适应中国传统的依附于男性的生活。
二是随着中国教会的发展,对于绣品的需求逐渐增大,为了传教需要,教会内部需要一批既有圣教特色又有中国风的装饰品,用于教堂建筑以及仪式上的饰品、堂旗等。
在妇女教育还未达成社会共识的19世纪中叶,圣母院内还有一个由拯亡会修女们开办的寄宿女校,其中的学生依然大多是被父母抛弃的孤女,除了学习读经、教理之外,她们同样也会学习刺绣、做花边等技艺,以便将来离开圣母院之后得以安身立命。
一开始,圣母院的女工工场仅接受教会内部订单,专做教会用品,工人也大多是已婚的孤女。但是19世纪末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圣母院的女工工场便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5]。
一方面,妇女教育逐渐为社会所认同,教会女校的招生对象逐渐转变为富家女,培养的目标也旋即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19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县城和浦东地区的织布厂、丝织场、棉纺厂层出不穷,不少孤女都被这些新兴工厂招去做工,这本是对教会公育的充分肯定。然而不久之后教会发现,将这些女孩们置身于“外教人”之中无疑对于她们的信仰是危险的。因此,1893年开始,拯亡会便将之前的刺绣间和花边间扩大,正式成立了属于教会的女工工场。
从成立女工工场开始,圣母院的女工工场便对外接受订单,甚至还在工场内树立了布拉格耶稣圣婴像以求得更多订单。
1.3 女工工场的诞生与培训
按照当时的规定,孤儿全部进入圣母院内的育婴堂,一起经过“小毛头间”和“大毛头间”。在6岁左右时,男孩送临近的土山湾孤儿院,而女孩则进入圣母院孤女院的“小班”读书。和土山湾一样,圣母院孤女们的食宿费用全部由法国的圣婴善会承担。
“小班”通常为40~60个女孩,她们开始读一些书。除了教理课之外,还有国文课,由献堂会修女教她们读书认字,使她们能写书信和叙述一篇讲道的摘要,同时也按照她们的年龄做些工作。将近13岁的时候,她们会进“大班”,即同样位于圣母院内的女工工场。修女们会根据她们的天分将她们安排到不同的车间。在车间里孤女们会学习一些技艺,如纺纱、织布、裁剪、洗衣、做饭、种花、除草等,有的也学刺绣、做花边等。之后她们可以去外面工作,也可以留在圣母院的工场做工[6]。
圣母院的学习安排如下[7]:
①刺绣间:学制为三年。第一年学习是免费的,工作也是无偿的。学习的科目除了中国传统的“大带小”之外,管理修女们也会根据当时国内外流行的款式开发一些新的产品教授给女工们。第二年没有正式的工资,但是有一些奖金和补贴。第三年有正式的工资。
②花边间:学制仅两周。最初的两周内没有任何报酬,之后至两个月是没有正式工资,之后为正常工资。一些老的女工会做带教老师,这些带教老师也会得到两个月的带教经费。花边间的女工大多为13~18岁的年轻女孩。
③对于被分配进其他车间的女工,从一开始就有报酬。
2 土山湾与圣母院的“别样姻缘”
2.1 圣母院孤女出嫁
中国有句古话“门当户对”,现代流行的话便是夫妻必须“三观一致”。因此,在圣母院的孤女们和土山湾的孤儿们两个类似命运的群体之间,便有了别样的姻缘。
中国古代的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这两个群体来说,传统的婚姻从形式上不可行,从文化上不愿意。因此,他们的婚姻采用的是全新的形式。
作为孤女的“娘家人”,圣母院的姆姆把了第一道关。在收到来自土山湾孤儿院神父的请求之后,便首先由代表“娘家人”的姆姆去见男方,查看男方的情况、要求、人品等情况。回去之后,她便根据男方的情况在圣母院的女孩中找一个条件相当的孤女,再安排男女双方见面。见面之后姆姆代表“娘家”询问女方意见,孤儿院神父则代表“夫家”询问男方意见。若男女双方都觉得中意,便着手安排婚事[8]。
中国传统的婚姻礼仪十分复杂,有六礼之说,即问名、订盟、纳彩(纳聘)、纳币(纳徵)、请期、亲迎。后来并为四体,即问名、订盟(送定)、定聘(纳彩、纳币)、亲迎(并请期)四个主要流程。在教会的新式礼仪中,肯定不可能进行如此繁复的礼节,但是夫妻双方都是中国人,又在中国的土地上,完全照搬西方的那一套也不可能。因此,这个特殊的婚姻就采用中西合璧的形式。
首先由土山湾孤儿院的神父写信给管理教友村的神父为小夫妻申请婚后的廉租住房,教友村位于圣衣院西南角的“三角地”、东北角的“底田里”(今上海体育场附近)。专门低价出租给土山湾出身的孤儿工人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居住。
在圣母院这边,姆姆们则按照中国的习俗,为即将出嫁的孤女置办子孙桶、被褥等陪嫁用品,并购买土山湾孤儿工艺院五金车间的戒指作为礼物。婚礼当天,在徐家汇的教堂中举行完宗教仪式之后,并在教友村的叙伦堂中举行中式结婚仪式。之后夫妻双方便会到教友村居住,从此这对有着相同命运的夫妻成立了新的家庭,彼此都成了对方在世间唯一的亲人。
对于这样的婚姻,教会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从教会角度,不希望这些他们一手带大的孤儿进入非教友的家庭,在他们看来,这对他们的信仰是一种威胁。因此,对于孤儿和孤女的婚配,教会乐助其成。
从社会角度而言,较他们的同龄人,孤儿和孤女们率先掌握了婚姻的自主权。教会从来没有也不可能逼迫孤儿孤女接受这样的婚姻形式。从女性角度而言,由于这样的婚姻,孤女们婚后不需为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去斗争:一方面,光靠土山湾孤儿院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养活一家人,这也就意味着孤女们婚后肯定需要出去工作;另一方面,因为圣母院的姆姆们始终扮演着“娘家人”的角色,在婚后的生活中时刻关注着孤女们的需要。
2.2 “特殊家庭”的婚后生活
圣母院的工作从上午8点到11点45分,下午1点30分到5:30分(夏天稍有延迟)。中午为午休时间,从不存在晚上加班和夜班。在各个宗教节日,由于宗教生活需要,工场的工作时间会延迟。每天工作期间,会有一个修女或一个女工讲授教理。每天女工们都会唱经。
在刺绣间和花边间,为鼓励女工们更加积极地完成工作,工资的支付方式为计件制,一件作品完成之后付钱。如有需要,也可以提前支取。其他车间为按日计酬。对于那些在刺绣间和花边间中作品出众的女工,会以“红点”和“黄点”的方式表示鼓励:一个“红点”加上5个铜板,一个“黄点”值24个铜板,一年两次将这些“红点”和“黄点”兑换一些实物或者补贴。每个女工都有一个小本子记账,如有病假和事假,一天扣3个铜板的奖金,不影响工资[9]。
每年会有3个月时间,这些女工还会接到上海县城工厂的订单,主要是编织孩子的围巾、帽子等。这些订单的报酬通常比圣母院的工作报酬高,故很多女工都愿意以每天3个铜板的损失去接这些订单,修女们也十分清楚这点。
1906年,一个圣母院好的女工每月可以拿到5~6个银元,年末还有一次性给予的年终奖。1912年,女工们的收入提高到一年包括工资和奖金100~150个银元(300~400法郎)[10]。通常家中的丈夫会在土山湾做工,夫妻两份收入,加上低房租的“教友村”房子,以及徐家汇相比市区来说低廉的物价,这样的小家庭即使不算大富大贵,但也能大致温饱无虞[11]。
值得一提的是圣母院女工工场的“福利”。由于许多女工已经做了妈妈,作为孤女,不可能有老人帮忙带孩子。为了切实解决孩子没人带的问题,在女工工场中设有托儿所。这个托儿所由一些老妇人(通常是获得众人尊敬的法国老姆姆)管理,孩子一出生就能放入这个托儿所。那些会走路的孩子可以去托儿所隔壁的学校开始接受最基础的教育。这些女工每天有两次机会离开工作岗位去哺乳。在圣母院的女工工场里,除了对出勤率高的女工有奖励之外,对于病假或产假的女工也有每天50个铜板的额外补助(病假补助标准为一个月,产假补助标准为两周),一切的规定都学习当时国外的经验[12]。
3 “海派绒绣”的发祥地与徐家汇源地区的形成
3.1 屡获殊荣的圣母院女工工场
随着女工工场的发展,女工们的作品也逐渐丰富起来。除了最初的宗教用品之外,刺绣工场逐渐拥有了各种中式和西式的刺绣品,如刺绣的手帕、假花、扇子,甚至裙子上的刺绣装饰等都可以生产。绒绣、包花绣等新式绣品相继引进了圣母院。圣母院女工的作品获得了上海县城那些太太们的青睐,在沪的英国妇女也同样喜欢圣母院女工的作品,经常给工场下各种来样定做的订单,觉得比商场中买来的更有价值。
女工工场的产品不仅行销中国,还出口越南、菲律宾等国,甚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来样定做她们的堂旗。
管理花边间的修女们也始终不断地创新产品,看似简单的花边,修女们相继引进了针点花边、爱尔兰凸花花边、威尼斯点状花边等不同的类型,以供客户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绒绣”,由于其既有西方绒绣作品粗犷浑厚的庄重质感,又吸收了中国传统刺绣的优点,在表现细节部分时有着中国传统刺绣的精致细腻。因此,早在刺绣车间时期,就迅速从徐家汇辐射到各个堂口,又从教会扩大到民间的工场,成为中西合璧的成功典范,有着无可替代的工艺价值和收藏价值。
3.2 圣母院工场的落幕
新中国成立之后,圣母院业务迅速萎缩,女工逐渐进入其他相关的刺绣、花边工场和合作社。1952年,圣母院的育婴堂停办。按照当时政策,圣母院工场同时停办,员工全部归口相关单位安置。
20世纪90年代末,在徐家汇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圣母院女工工场的房子被拆除,这座曾经承载“海派绒绣”摇篮的工场完成了历史使命,至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