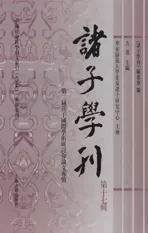陳繼儒生命情境中的《莊子》解讀
2018-01-23臺灣謝明陽
(臺灣) 謝明陽
内容提要 萬曆十四年,二十九歲的陳繼儒焚棄儒者衣冠,決心與塵世隔離,之後陸續隱居在小崑山、東佘山中,成爲晚明隱逸人物的代表。本文討論在其隱居生涯中,陳繼儒如何從生命情境的角度來解讀《莊子》。統整陳繼儒與《莊子》相關的材料有三: 一是單篇文章,如《郭注莊子叙》《南華發覆叙》,均是爲友人著作所題的序文;二是注本《莊子雋》,所注鎖定於内七篇,代表陳繼儒對於《莊子》的詮解理路;三是詩作中述及《莊子》者,這些作品更以真實的樣貌,融入了陳繼儒的生活之中。下文即取此三種類型的篇章加以探討,藉此以窺陳繼儒在閲讀《莊子》時所流露出的情感狀態,以及所呈現出的心靈樣貌。
[關鍵詞] 莊子 陳繼儒 《莊子雋》 《晚香堂小品》 《陳眉公先生全集》
前 言
明代文學家陳繼儒(1558—1639),字仲醇,號眉公,松江華亭人。萬曆十四年(1586),兩次鄉試失利的陳繼儒年方二十九,即取儒者衣冠焚棄之,決定此生不再參加科舉。隔年,他在小崑山上買乞花場,祭祀陸機、陸雲兄弟,表明隱居之意,確實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生活重心。萬曆二十八年(1600),陳繼儒四十三歲,顧憲成(1550—1612)及諸名賢招往東林書院講學,但他辭謝不往,已然將之視爲世俗雜務。至萬曆三十五年(1607),五十歲的陳繼儒得新壤於東佘山,於此構築高齋,廣植松杉,杜門著述而終老(1)以上對陳繼儒一生的概述,參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間華亭陳氏家刊本,第5—6、10、13頁;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九十八,《隱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631頁。。然而,陳繼儒爲何三十不到便決定過起近乎隱者的生活?此一志向又如何堅守五十餘年?試觀陳繼儒《文娱録叙》云:“往丁卯前,璫網告密,余謂董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願爲文昌,但願爲天聾地啞,庶幾免于今之世矣。’”(2)《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二,第35頁。董思翁,即董其昌(1555—1636)。丁卯前,即天啓七年(丁卯,1627)以前,這段時期,陳繼儒放棄讀書功名,只願“天聾地啞”,目的是爲了在政治上保全自己,故而不問複雜世事,盼望可以藉由其他渠道,追尋個人的自由(3)關於陳繼儒的隱居心態,論者頗衆。較早的討論可參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論李卓吾與陳眉公》,(臺灣)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113頁。。
隱居後,陳繼儒曾將個人内在的情志,投射在古人的形象上。例如其《晚香堂小品》最後一卷名曰“志林”,其中有《顔子身諷》一則,文云:
顔子,王佐才也,簞瓢陋巷中,卻深藏一個王佐。當是時,不特仲由、子貢諸儕輩拉他不去,即其師孔子棲棲皇皇,何等急于救世,而顔子只是端居不動,而且有以身諷孔子之意。其後孔子倦于轍環,亦覺得陋巷的無此勞攘;厄于絶糧,亦覺得簞瓢的無此困頓。又其後,居夷浮海,畢竟無聊,原歸宿到蔬水曲肱地位,而後知顔子之早年道眼清澈耳,所以有感而三歎其賢也。(4)陳繼儒《晚香堂小品》,《中國古代小品精選》第9册,卷二十四,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5年版,第456—457頁。
此中提到,正當孔子棲遑於救世之事時,顔回卻端居不動,以己身勸諷孔子,而這樣的苦心,必須等到孔子過着曲肱而枕之的生活時,才能真切體會顔回早已道眼清澈,看透一切。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文人心態》一書曾根據此段話語加以解釋:“顔子的形象中映現着陳眉公本人的影子。……二十九歲便棄卻儒者衣冠的陳繼儒豈非與顔子如出一轍,其全身遠害的追求豈非與顔子同一旨趣,則其端居不出的行爲是否也有以身諷世的深意呢?”(5)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文人心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59頁。這樣的説法,清楚地掌握了陳繼儒提出此論的實際用心。陳繼儒心中的顔回形象出於自身的改造,但此一改造卻也得力於《莊子》。《讓王》云:“孔子謂顔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顔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内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陳繼儒筆下的顔回,豈不與《莊子》書中“不願仕”的顔回如此貼近(6)章太炎云:“莊子載孔子和顔回的談論卻很多。可見顔氏的學問,儒家没曾傳,反傳於道家了。莊子有極讚孔子處,也有極誹謗孔子處,對於顔回,只有讚無議,可見莊子對於顔回是極佩服的。”見章太炎演講,曹聚仁整理《國學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頁。?是以,先秦諸子中真正隱逸不仕的典範,應該是逍遥的莊子。《秋水》中有莊子不願意爲廟堂神龜,寧願曳尾於塗中的記載;《列禦寇》也有莊子拒絶聘任,以免淪爲大廟犧牛之事。這兩則寓言未必是事實,卻深刻地反映出莊子的行事風格,而此種風格與陳繼儒歸隱山中的選擇是相同的。那麽,陳繼儒究竟是以何種眼光來看待莊子呢?他看待莊子的方式與其生命又有着怎樣的聯結?本文即針對此一議題加以討論。
一、 陳繼儒解讀《莊子》的材料
陳繼儒解讀《莊子》的材料可以分成三類: 一是單篇文章,如《郭注莊子叙》《南華發覆叙》,均是爲他人著作所題的序文,從中可見陳繼儒自身的想法;二是注本《莊子雋》,所注鎖定於内七篇,此書代表着陳繼儒對於《莊子》的詮解理路;三是詩作中述及《莊子》者,這些作品的詩意與内容,更融入了陳繼儒的生活之中。本節先考察此三種著作的寫作背景。
《郭注莊子叙》《南華發覆叙》二文同時收入《晚香堂小品》及《陳眉公先生全集》中(7)《晚香堂小品》卷九題作《郭注莊子叙》《南華發覆叙》,《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二題作《郭象注莊序》《南華發覆序》。今從《晚香堂小品》。。《晚香堂小品》是陳繼儒的女婿湯大節所刻,湯大節在書中《乞言小引》提到:“念節生二十六日而孤,先慈斷指殉烈,蒙先生贅而撫之,德真昊天矣。追隨峰泖,越二十年,耳提之暇,先生凡有著述,覽輒記,記輒筆,再補再謄,靡間夙夜,盈几盈篋,頗費護持。”(8)《晚香堂小品》,湯大節《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例言》,第7册,第17頁。湯大節入贅於陳家,與陳繼儒關係親近,此書即是追隨陳繼儒的貼身記録,經日夜謄補而編成。不過,陳繼儒長子陳夢蓮(1582—?)卻在《陳眉公先生全集總目》中説:“先有《晚香堂小品》《十種藏書》,皆係坊中贋本,掇拾補湊,如前人詩句、俚語、僞詞,頗多篡入,不無蘭薪之誚。”(9)《陳眉公先生全集》,陳夢蓮《陳眉公先生全集總目》,第6頁。文中《晚香堂小品》當即湯大節刻本(10)《晚香堂小品》僅見湯大節刻本。另有陳繼儒《晚香堂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6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但此書名曰《晚香堂集》,而非《晚香堂小品》。,但批之爲“坊中贋本,掇拾補湊”,指斥未免太過。今以兩種版本的《郭注莊子叙》《南華發覆叙》相互比對,《陳眉公先生全集》之文經過修飾簡化,實不如《晚香堂小品》之文來得完整,且真能與《莊子郭注》《南華發覆》原書序文相合,故下文均以《晚香堂小品》爲據。
陳繼儒《郭注莊子叙》云:
近世《老莊翼》最稱駢辨,而吾友鄒孟陽則謂餘注皆可盡廢,獨以郭子玄孤行足矣。(11)《晚香堂小品》卷九,第8册,第28頁。
《莊子郭注》爲陳繼儒友人鄒孟陽所印,其書獨傳郭象注,郭注之外,未再添加任何注語。鄒孟陽即鄒之嶧(1574—1643),同時也是錢謙益的好友,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中屢屢提及,並有《鄒孟陽墓誌銘》記其生平(12)錢謙益《牧齋初學集》,《錢牧齋全集》本,卷六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0—1451頁。。陳繼儒此序並未標記寫作時間,但鄒之嶧《莊子郭注》在陳繼儒序文之前有馮夢禎(1548—1605)《莊子郭注序》,注明“乙巳九月朔”;後有吴之鯨《莊子郭注題辭》,也注明“乙巳七夕”(13)分見鄒之嶧《莊子郭注》,《無求備齋老列莊三子集成補編》第26—28册,(臺灣)成文出版社1982年版;馮夢禎《莊子郭注序》,第26册,第6頁;吴之鯨《莊子郭注題辭》,第26册,第25頁。。可知此書刻於萬曆三十三年(乙巳,1605),陳繼儒《郭注莊子叙》也應作於此年,此時陳繼儒四十八歲。《南華發覆叙》是爲釋性《南華發覆》所題,其開端云:“《南華發覆》,清涼山孔雀菴藴暉老人所撰也。老人繩戒精緊,狀貌清孤,望之類須菩提,衣表瘦骨,可捫而數也。”(14)《晚香堂小品》卷九,第8册,第23頁。釋性的生卒年不詳,但根據此文,可推測約與陳繼儒同時。又據釋性《南華發覆》所録,陳繼儒的序文曾注明寫作時間,題云:
丙寅清和月五日書於苕帚菴中。(15)釋性《南華發覆》,陳繼儒《南華發覆叙》,《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9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頁。此語在陳繼儒文集中未見。
知此序作於“丙寅”年四月。觀方勇《莊子學史》云:“陳繼儒的這篇序文撰於天啓六年丙寅(1626)……釋性的《南華發覆》八卷當著成於此年。”(16)方勇《莊子學史》,第六編《明代莊子學》,第3册,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2頁。是矣。當天啓六年時,陳繼儒已六十九歲。
陳繼儒另有注《莊》之作,書名曰《莊子雋》,僅注内七篇。此書有《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本,標明“藝文印書館據明蕭鳴盛刊五子雋本影印”(17)陳繼儒《莊子雋》,《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第30册,(臺灣)藝文印書館1974年版,頁首。。蕭鳴盛,字戒甫,號儆韋,生於萬曆三年(1575),卒於崇禎十七年(1644),爲福建建陽的書商(18)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頁。。其所刻《五子雋》,包含《老子雋》《莊子雋》《管子雋》《韓子雋》《屈子雋》,此叢書今藏淮安市懷陰中學圖書館(19)見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90頁。。“雋”者,意味深長之意,既然先秦五子皆可臻及雋永之境,則此“雋”字並非專屬於莊子。而《莊子雋》於何時刊印?觀《莊子雋》開端明列“書林少渠蕭世熙繡梓”(20)《莊子雋》,第3頁。。蕭世熙,字佛友,號少渠,一作少衢,生於隆慶四年(1570),卒於天啓元年(1621),亦福建建陽人(21)《福建古代刻書》,第321—322頁。。《五子雋》爲蕭鳴盛所刊,但《莊子雋》卻是蕭世熙繡梓,前後似乎不一。事實上,蕭鳴盛的年紀雖小於蕭世熙,但卻是蕭世熙的族叔(22)下文述及蕭氏刻書之事,均詳《福建古代刻書》,第320—325頁。,推想當是由蕭鳴盛負責經銷全套《五子雋》,而由蕭世熙負責刻印其中的《莊子雋》,叔侄各司其職之故。再以蕭世熙卒於天啓元年觀之,可知《莊子雋》的出版當在此年以前。
以《莊子雋》的發行時間來看,此書的刊刻陳繼儒必然知曉,其著作權亦可歸屬於陳繼儒。試看錢謙益《列朝詩集》論陳繼儒:
仲醇又能延招吴越間窮儒老宿隱約饑寒者,使之尋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瑣言僻事,薈蕞成書,流傳遠邇。款啓寡聞者,争購爲枕中之祕。(23)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第十六,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5931頁。
陳繼儒組織著書團隊,集合衆人之力,尋章摘句,匯聚成書,甚至引發了衆人争購的風潮。而前述的建陽蕭氏刻書,曾將刊印中心移往金陵,出版的著作中即多陳繼儒評選者,除了《五子雋》之外,尚有《秦漢文雋》,以及戲曲《西廂記》《幽閨記》《琵琶記》《玉簪記》《紅拂記》等十餘種,很有可能蕭氏刻書即是陳繼儒出版事業的合作廠商。同樣地,《莊子雋》的成書也可以放在同樣的脈絡之下來作理解。
再看陳繼儒與《莊子》有關的詩作。《晚香堂小品》前七卷爲詩歌,其中援引《莊子》典故並具有討論意義者,可得五言古詩《田園十六首》其十六、七言古詩《贈人作》、五言律詩《求仲過訪山中賦贈》《同辰玉過澹圃四首》其四、七言律詩《壽吴蘇臺》《月明睡起閒步庭中》,共計六首。首數雖然不多,但值得讀者用心體會。再檢《陳眉公先生全集》,前述六首詩中,僅得四首,且四首詩的題目、内容與《晚香堂小品》略有差異(24)《陳眉公先生全集》中的四首詩,分别是《田園詩》其十三、《同辰玉過澹圃》其四、《依韻答韓求仲》《月明睡起閑步庭中》,分見卷二十七,第14頁;卷三十,第5頁;卷三十,第9頁;卷三十一,第17—18頁。這四首詩,也就是《晚香堂小品》中的《田園十六首》其十六、《同辰玉過澹圃四首》其四、《求仲過訪山中賦贈》《月明睡起閒步庭中》。,故後文將以《晚香堂小品》爲主,《陳眉公先生全集》所録若差别較大者,列於腳注供作對照。至於這些詩歌的寫作時間則難以查考,文中將以代表陳繼儒一生視之。
二、 莊子與屈原、老子之别
陳繼儒《郭注莊子叙》作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南華發覆叙》作於天啓六年(1626),寫作時間相差超過二十年,但二文分别提到莊子與屈原,以及老子與莊子的性格差異,論述均强調了莊子的特殊性,前後説法仍相貫通。因此,我們閲讀《郭注莊子叙》《南華發覆叙》,應該超出鄒之嶧、釋性二書的原意,探究陳繼儒文中如何型塑莊子的形象。
先看《郭注莊子叙》開篇云: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于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毗于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語言無端,乃注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大抵注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25)《晚香堂小品》卷九,第8册,第27頁。李北海,即唐代書法家李邕(678—747)。
據陳繼儒之説,莊周與屈原之間有異有同,其異者在於屈子哀,莊子樂;其同者在於二者的哀樂皆語言無端,文章無首尾。就異者而論,屈原的悲哀融貫於作品之中,如《離騷》云:“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長太息以淹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26)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卷一,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1、13—14、25、30頁。辭句之中,哀傷連連,反覆訴説着屈子對於生命的孤沉絶望。然而,莊子是否快樂,卻值得再作探討。觀宋儒葉適《莊子》云:“莊周者,不得志於當世而放意於狂言,湛濁一世而思以寄之,是以至此。其怨憤之切,所以異於屈原者鮮矣。”(27)葉適《葉適集》,《水心别集》卷六,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712頁。時代稍後於陳繼儒的譚貞默(1590—?)在《夢楚雜詩》其一中也説:“屈子故言愁,莊生詎言樂?”(28)譚貞默《埽庵集》,《叢書集成三編》第53册,(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21頁。二人皆認爲莊子並未言樂,反而與屈子的怨愁相當。細思之,“現實生活”中的莊子確實有其愁苦,但對於“思想超脱”的莊子來説,卻不能不以樂字許之。《逍遥遊》云:“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此逍遥無爲的生活,即是從無可奈何中轉化而得,是一種從悲中提煉而得的快樂。正如莊子妻死,他卻可以摒棄傷感,箕踞鼓盆而歌;當莊子和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更由一己而擴充至天地萬物,深刻體知魚之樂(29)“莊子妻死”,見《至樂》;“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見《秋水》。。此樂,是一種“天樂”、“至樂”,並非一般世俗之樂。如《天道》云:“以虚静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至樂》更説道:“至樂無樂,至譽無譽。……至樂活身,唯無爲幾乎!”陳繼儒説莊子的精神可達至奔放飄飛之境,又豈虚言哉!那麽,又何以説莊子、屈子的文章皆無首尾?此中深意當指,莊子、屈子之作在於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情感,在哀樂激盪中毋需刻意安排文章的開頭與結尾,如詹尹卜卦,僅取其龜策之意而不取其象;行人出使,亦僅受君王命令而不受其辭。正因爲莊、屈哀樂不一,卻不以文辭工巧作爲寫作目的,故謂之“無首尾”。
在《郭注莊子叙》中,同時也提到了老、莊之間的不同。陳繼儒文云:“唐玄宗遂號爲‘南華真人’,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生徒習老、莊、文、列者,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而《莊子》之稱《南華經》自此始。其後宋徽宗又追封‘微妙玄通真君’,儼若帝聃而相莊者。夫莊生生不受楚威王相,而後乃受宋、唐封號,甘爲老氏素臣乎?”(30)《晚香堂小品》卷九,第8册,第28—29頁。唐玄宗時,莊子得到“南華真人”之號,但卻是列在老子“道德真人”之後;宋徽宗時,莊子又被封爲“微妙玄通真君”,但仍居於老子“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之下。如此一來,老子成爲“素王”,然而莊子願意成爲“素臣”嗎?陳繼儒話語中已表示莊子屈就,但詳細的理由尚未陳述,這部分則有待《南華發覆序》。
二十餘年後,陳繼儒再作《南華發覆序》,序云:
世謂老、莊一家,余獨確然判而爲二。老子生于周平王末,實有作《易》者憂患之意,其言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七尺之軀,厭而離之不得,計莫若以曲自全,以昏自晦,以柔弱自抱,以勇于不敢自活,若谿谷,若嬰孩,若冬涉川,若畏四鄰。自古之善恐怖者,莫老子若也。南華生搰搰然笑之,烏用是頑且鄙哉?于是以逍遥、齊物之説,出而救之,蓋破我然後能破執,破執然後能破生死,破壽夭,破禍福,破譽誹,破理事,破聖凡,而老氏崎嶇世途之恐怖,悉粉爲虚空矣。老子爲憂畏粘縛者也,莊子爲老氏解粘釋縛者也。(31)同上,第23—24頁。“搰搰然”,原作“愲愲然”,今逕改。
所謂“世謂老、莊一家,余獨確然判而爲二”,話語中極爲自負地表明自己的眼光獨出衆家之上。而老、莊分判爲二的原因何在?陳繼儒舉出《老子》十三章來作説明:“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章的解説歷來不一,可以王弼之注爲準。王弼在“及吾無身”下注:“歸之自然也。”(32)王弼《老子王弼注》,收入《老子四種》上篇,(臺灣)大安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頁。可知“無身”即回歸自然之意也,意謂吾人若能重返大道,又有何患?則此語的重點原本應該落在“無身”的修養工夫,但陳繼儒卻過度强調“吾有何患”的效果上,故藉“曲則全”(二十二章),“我獨昏昏”(二十章),“柔弱勝剛强”(三十六章),“勇於不敢則活”(七十三章),“曠兮其若谷”(十五章),“如嬰兒之未孩”(二十章),“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十五章)諸語,反覆説明老子有意離棄令人厭惡的大患,可謂“古之善恐怖者”、“爲憂畏粘縛者”。搰搰然笑之的莊子則不然,其逍遥、齊物之論,用意在於破我執,破生死禍福的觀念,將老子的恐怖之感粉碎虚空,乃是“爲老氏解粘釋縛者也”。在這裏,陳繼儒的《老子》解讀值得商榷,但更引人注目的反而是他對於莊子情有獨鍾,一心嚮往。
《南華發覆序》的後半篇,陳繼儒引用王世貞(1526—1590)《讀莊子三》的話語,倘若孟子與莊子發生學術論戰:“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33)《晚香堂小品》卷九,第8册,第25頁。原語見王世貞《弇州山人讀書後》卷一,(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間長洲許恭刊本,第7頁。陳繼儒不贊成其説,笑曰:
孟子之怒,必加於老而不加於莊。學老子之恐怖,未免流而爲鄉愿;學莊子之豪宕奔放,不失爲狂。此老、莊二氏門庭之辨也。(34)同上,第25頁。
依陳繼儒的見解,孟子只可能攻擊老子,不可能攻擊莊子,這是因爲我們若學老子,不免流爲鄉愿;我們若學莊子,卻可以成爲狂者。陳繼儒區分兩家門庭,明顯給予莊子遠高於老子的評價。
對照《郭注莊子叙》與《南華發覆序》,可以發現二文分别以“奔放飄飛”和“豪宕奔放”來形容莊子,在“奔放”的莊子身上,陳繼儒寄托了情感的認同。必須追問的是: 此一情感認同在其生命情境中又占有多少的分量?
三、 《莊子雋》的解莊路向
《郭注莊子叙》云:“善教兵者,殺其士卒之半;善注書者,亦去其書之半。此郭之所以獨標法外,玅得《莊》解也。”(35)同上,第28頁。郭象注《莊子》,篇幅約略《莊子》之半,得到了陳繼儒的肯定。而陳繼儒作《莊子雋》,分量又遠少於郭象注,全書除了以扼要注語揭示《莊子》之“雋”以外,甚至還删去了外、雜篇,僅注内七篇,可謂精簡中的精簡。以下就《莊子雋》内七篇舉例説明。
先看《莊子雋·逍遥遊》注“北冥有魚,其名爲鯤”一段云:
此段又自“二蟲何知”上生下“小知大知”,又自“小知大知”上生下“小年大年”。二句意亦相承,教人把胸襟識見擴充一步,不得以所知所歷者而自足也。
又注“故夫知效一官”一段云:
此明小大之辨。宋榮子未得爲大,列子大而不大,唯至人、神人、聖人之能無,然後爲大。(36)分見《莊子雋》,第6、8頁。
據第一注,“小知不及大知”係從“之二蟲又何知”推得,意思是蜩、鷽鳩皆自我滿足於所知所經歷者,僅屬“小知”;然大鵬鳥高飛九萬里,然後圖南,則屬“大知”。再據第二注,至人、神人、聖人爲“大”,宋榮子、列子則爲“小”,二者如同大鵬鳥與斥鴳的對比,可謂“小大之辯也”。若以今日眼光來看,陳繼儒的詮解可謂平穩,但如果上溯至晚明,此注實具創意。這是因爲大鵬鳥與小鳥究竟誰逍遥?誰不逍遥?歷來説法不一。郭象《莊子注》云:“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遥一也。”(37)郭象注、成玄英疏《南華真經注疏》卷一,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4頁。意謂二者皆逍遥。支遁《逍遥論》云:“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内。”(38)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説新語箋疏·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頁。此爲劉孝標注語。意謂二者皆不逍遥。郭象和支遁之論,影響深遠,唐、宋諸注均沿之,直到晚明才出現新説。如釋德清(1546—1623)《莊子内篇注》明確提出:“唯大而化之之聖人,忘我、忘功、忘名,超脱生死而遊大道之鄉,故得廣大逍遥自在,快樂無窮,此豈世之拘拘小知可能知哉?正若蜩、鳩、斥鴳之笑鯤鵬也。主意只是説聖人境界不同,非小知能知,故撰出鯤鵬變化之事,驚駭世人之耳目,其實皆寓言以驚俗耳。”(39)釋德清《莊子内篇注》卷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頁。“鯤鵬”原作“鵾鵬”,今逕改。此一論點認爲大鵬鳥逍遥,蜩、鳩、斥鷃則非,大大擴展了《莊子》寓言的解釋向度。而陳繼儒僅小釋德清十餘歲,注解意旨則與釋德清相同,二人的逍遥界説幾可謂同時並出。
再看《莊子雋·齊物論》,“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一段眉批云:
物論所以不齊者,見得世間有死有生,有可有不可。殊不知可不可本一貫,死生本一條,本無不齊也。通篇只此意。
同樣是“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一段,解“吾喪我”云:
“今者吾喪我”,子綦自謂也。蓋喪我則忘物忘我,無是無非,大意總括於此。(40)均見《莊子雋》,第15頁。
《齊物論》原是《莊子》内篇中意涵相對複雜的篇章,陳繼儒卻直探本原,認爲萬物原本自齊,可不可、死生,皆可一以貫之,通篇不過此意。這樣的説法十分扼要,然讀者未必皆能體會,於是陳繼儒繼續解釋“吾喪我”一語,説明真我若能忘物忘我,也就是忘卻形骸之我;又能無是無非,也就是忘卻認知之我,則精神之我便可提升至萬物與我爲一的齊物之境。
又《莊子雋·養生主》篇末總論,陳繼儒曰:
莊生《養生主》一篇,不上數千言,而扼要在神靈凝注之處。開口便道“緣督爲經”一句,此“緣督”即有生來所謂督脈也,凝神在此,自能把握死生大關頭,哀樂俱不足以入其心。(41)均見《莊子雋》,第45頁。
此説指出《養生主》的關鍵在於“緣督以爲經”一句。歷來均訓“督”字爲“中”意,至宋人趙以夫才明確指出:“奇經八脈,中脈爲督。”褚伯秀《莊子義海纂微》續作發揮,云:“蓋人身皆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復有壬脈爲之配,乃命本所係。非精於養生,罕能究此。”(42)趙以夫、褚伯秀之説,分見褚伯秀《莊子義海纂微》卷五,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6—87頁。依循此論,陳繼儒也認爲養生必須凝神於督脈,順中虚之道而行,方能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又《莊子雋·人間世》注“虚者,心齋也”云:
只一虚字,便是普物無心,千古學脈在此。
本研究利用学生在小测验前抱有一定的紧张和焦虑心理,让学生更加专注到PBL课后的学习中。根据老师上课的一些反映,提前得知PBL课程结束后有小测验的试验组学生,上课时发言更加踊跃,在上课时能提出更多观点,覆盖更全面的细节,这可能和学生在得知PBL课程会有小测验,在课后花了较多时间查询相关资料,整理了更多笔记,做了比较充足的准备。
又注篇末“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云:
兩言正是《人間世》一篇大結。(43)分見《莊子雋》,第53、66頁。
此注自有所承,但陳繼儒體會了“虚”字以及“無用之用”之意,已能掌握《人間世》的要旨。篇中,孔子告訴顔回:“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齋也。”耳朵止於感官聽覺,心志止於認知符應,唯有處於心齋狀態,方能以虚静之氣來體證大道;這是不得已的入世之事。至篇末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爲《人間世》的結語,在無所可用時方能呈顯其用;這則是出世之事。
又《莊子雋·德充符》在“才全而德不形者也”之後注云:
“豚子”至“全德之人乎”,見所愛惡不在形骸之美,蓋德充於内,無假於飾;德餒,即外飾無益也。“德不形”,無可見之迹也。(44)同上,第77頁。
《德充符》此段文句,先是論“全德之人”,後又論“德不形者”,二者均屬正面意涵,但乍讀之下,彼此似未盡合。陳繼儒的解釋是,“全德之人”受人喜愛的原因並不在形骸之美,而是德充於内,自然符應於外。但哀駘它是全德之人,卻又是“德不形者”,此又何説?陳繼儒續言,德不形意指“無可見之迹”,也就是德性不刻意顯露,雖無可見之迹卻能自我飽滿。故知“全德之人”、“德不形者”,皆“德充符”也。
在《莊子雋·大宗師》總論中,陳繼儒曰:
大宗師者,道是也。莊子嘗曰:“吾師乎!吾師乎!”故道謂之大宗師。得道者真人也。真人之爲得道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死生無變於己而無容心,爲真知也。(45)分見《莊子雋》,第103頁。
儵者,喻昏黑無象也。忽者,喻荒忽無形也。渾沌者,無孔竅,清濁未分也。儵忽之間,渾沌已破,言保之甚難,而散之甚易也。三者稱帝,謂帝王之道以純樸未散自然之爲貴也。(46)《莊子雋》,第112—113頁。
此注與歷來詮解不盡相同。陳繼儒是將“昏黑無象”的儵者、“荒忽無形”的忽者、“無孔竅,清濁未分”的渾沌,均視爲純樸未散的帝王。觀《應帝王》云:“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故陳繼儒續云“儵忽之間,渾沌已破”,意思是説,原本無象無形的儵、忽,爲了報答渾沌的禮遇之恩,竟然突發奇想地鑿死渾沌,可見帝王之道不僅“保之甚難”,而且“散之甚易”。此則寓言通常采用梁簡文帝的解法:“儵、忽取神速爲名,渾沌以合和爲貌。神速譬有爲,合和譬無爲。”(47)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三下,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310頁。陳繼儒則認爲,儵爲“南海之帝”,忽爲“北海之帝”,渾沌爲“中央之帝”,既然同爲帝王,三者原應無所差别,而儵、忽所以鑿破渾沌,當是瞬間形成的妄念。亦即梁簡文帝以儵、忽譬“有爲”,陳繼儒則以儵、忽譬“先無爲而後有爲”,二者可謂大同而小異。
《莊子雋》對於莊子的詮譯有一定的見解,但話語往往過於簡賅,點到爲止。若問: 陳繼儒爲何不細論《莊子》全書?爲何不在書中寄托更爲深刻的懷抱?答曰: 《莊子雋》僅是《五子雋》之一,陳繼儒編寫此書的目的仍在於出版,盈利維生。此一寫作傾向,正如陳平原《文人的生計與幽韻——陳繼儒的爲人與爲文》所云:“把神聖的文學,降低爲一種謀生的手段。把中國人源遠流長的‘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變成一種獲取生活資料的勞動。……山人的獨立人格,很大程度依賴於出版業。”(48)陳平原《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42—43頁。因爲出版書籍必須求得暢銷,書中的義理自然以人人能懂爲上策,過度繁複而有創意的看法,可以不必提出,《莊子雋》正可以作如是觀。《莊子·外物》有“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的故事,顯然,陳繼儒不願意如此貧苦,他是一位隱者,固然注解《莊子》,但絶非生死與之,而是悠閒生活的一種追求。
《莊子雋》另有特殊之處,即對於袁宏道(1568—1610)《廣莊》(49)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95—815頁。的引用。陳繼儒雖長袁宏道十歲,但《莊子雋》的成書時間卻較遲,各篇的結尾中,共有《逍遥遊》《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應帝王》六篇引用《廣莊》之説(50)分見《莊子雋》,第14、39—40、45—46、66—67、81—82、114頁。六篇之中,《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均作“袁石浦曰”,“石浦”,袁宗道(1560—1600)之號也,然其文實出自袁宏道《廣莊》,當作“袁石公曰”爲是。,徵引的話語均長。事實上,《廣莊》並非正式注解《莊子》之作,甚至没有提及《莊子》的寓言與術語,用袁宏道的話來説,乃是“廣者推廣其意,自爲一《莊》”(51)《答李元善》語。《袁宏道集箋校》卷二十二,第763頁。。那麽,《莊子雋》又爲何廣泛徵引《廣莊》?推求陳繼儒的用意,應當有二: 其一,表示對於袁宏道文章的尊重與嚮往;其二,藉着袁宏道的名聲來增進書籍的銷售。根據這兩項寫作用意,我們回顧陳繼儒《南華發覆序》云:“學莊子之豪宕奔放,不失爲狂。”袁宏道在萬曆二十六年(1598)寫作《廣莊》,時年三十一歲,其書自爲一《莊》,真可謂豪宕奔放的狂者;但以陳繼儒《莊子雋》來看,其書之注均依傍着《莊子》原書而展開,語言簡要,顯然失去了如袁宏道著書般的雄心壯志。故《莊子雋》固然追慕狂者,但卻是狷者的作品,此一心境,正如陳繼儒《與方公旦心》所揭示:
此梅幹在冰雪中,俗眼未及見花香時候耳。當今中行救世不得,狂亦救世不得,唯狷者是向上第一路人。然狷之有所不爲,尚置之賢知過中,則聖賢豪傑喜静而不喜動,喜冷而不喜熱,可知矣。(52)陳繼儒《白石樵真稿》,《尺牘》卷二,《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6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51頁。
政治局勢一如冬季冰雪,可惜俗眼未及見梅花芬芳。正因爲時節非春非夏,故爲中行,爲狂者,均無法救世;不如爲狷者,其賢智反可超過中行。喜静、喜冷的狷者,是陳繼儒此時的生命依歸(53)參張德建《明代山人文學研究·山人尺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1—352頁。,也反映在《莊子雋》的書寫上。
四、 詩歌作品中的莊子身影
陳繼儒在隱居期間與顯貴者、窮約者密切往來,甚至爲了生活所需,屢屢編書販售,故其隱居實非真隱。如錢謙益《列朝詩集》所述:
仲醇通明俊邁,短章小詞皆有風致,智如炙輠,用之不窮。交遊顯貴,接引窮約,茹吐軒輊,具有條理。以仲醇之才器,早自摧息,時命折除,聲華浮動,享高名,食清福,古稱“通隱”,庶幾近之。(54)《列朝詩集》,《丁集》第十六,第5931頁。智如“炙輠”,原作“炙髁”,今逕改。
論中以“通隱”稱呼陳繼儒,通隱者,通達隱士之謂也。參看《梁書·處士傳》云:“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55)姚思廉《梁書》卷五十一,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732頁。此“通隱”,也算是隱逸的一種模式。但到了晚明,陳繼儒不僅和文人們頻繁過從,同時也編寫書籍,大力出版,這樣一位成功的流行文學作家,已臻及“享高名,食清福”的境地,其“通隱”已然具有明代的獨特性。而在這樣的生命情境中,通隱陳繼儒又如何以詩歌來抒寫對於《莊子》的感受呢?
先看陳繼儒五古《田園十六首》最後一首云:
入林何必密?入山何必深?受屋三兩廛,四顧垂清陰。藨蔉既已便,采汲亦足任。墳塚因坡陁,籬落緣丘岑。中有荷蓧叟,傴僂髮未黔。野逸無威儀,蹇拙能謳吟。沉者不羨飛,飛者不願沉。萬類各有適,齊物皆童心。儀秦自水火,遺恨到于今。(56)《晚香堂小品》卷一,第7册,第175—176頁。
詩言入山林不求深密,能有小屋兩三間,於此耘田除草、采收汲水,即可感受到田園生活的樂趣。詩中“中有荷蓧叟,傴僂髮未黔”,用《論語·微子》“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的典故,此荷蓧丈人近於道家,與合縱連横的蘇秦、張儀迥不相同,故云“儀秦自水火,遺恨到于今”。再觀“沉者不羨飛,飛者不願沉。萬類各有適,齊物皆童心”,“齊物”一詞出自《齊物論》,詩中意指荷蓧丈人臻及“吾喪我”的境地,不僅形如槁木,心亦如死灰;“童心”則出自李贄(1527—1602)《童心説》,云:“夫童心者,絶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57)李贄《焚書》卷三,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98頁。合觀之,可明白達致齊物,則形軀之我、認知之我已然忘卻,此時只有最初一念的本心,故云“齊物皆童心”。若就荷蓧叟已然體得齊物而言,可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若就萬物自身而言,卻無妨或沉或飛,各得其適,這也正是陳繼儒對於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種期許。
再看陳繼儒七古《贈人作》云:
人間十九倚塵堵,五濁紛紛不堪數。隙中駒馬鬬是非,誰向清宵夢長古?羨君策足踏烟雲,嶺頭笙鶴遥相聞。醉鄉遨遊日復日,醒來落花滿雙膝。世事齷齪不足言,且須一夜傾千石。碧天秋月君爲心,洞庭夢澤吐且吞。浣盡斗餘俗子腸,松前箕踞彈瑶琴。墨池雨晴蕉葉緑,咫尺市頭如空谷。簷阿棋韵響丁丁,散入東窗一林竹。有樂如此亦足矣,此心莫向江頭洗。吾心亦自空無塵,同摘芙蓉看秋水。(58)《晚香堂小品》卷二,第7册,第190頁。
此詩多處暗用了《莊子》的話語,先是“隙中駒馬鬬是非,誰向清宵夢長古”,用《知北遊》典故——“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陳繼儒意謂,人生如駒馬過隙,倏忽之間徒生是非,又有誰能真正的夢見長古?再又“浣盡斗餘俗子腸,松前箕踞彈瑶琴”,用《至樂》篇典故——“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陳繼儒此詩的贈與對象與莊子遭遇並不相同,但箕踞彈琴的逍遥心態則一。詩末“吾心亦自空無塵,同摘芙蓉看秋水”,二句皆與《莊子》有關。前句化自陶淵明詩《歸園田居五首》其一:“户庭無塵雜,虚室有餘閒。”(59)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卷二,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76頁。更往上溯,則出於《莊子·人間世》:“瞻彼闋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後句則化自唐人皇甫冉《秋日東郊作》:“閒看秋水心無事,卧對寒林手自栽。”(60)皇甫冉《唐皇甫冉詩集》,《四部叢刊三編》第60册,上海書店1985年版,第44—45頁。再向前推,則出於《莊子·秋水》,此篇以“秋水時至”開端,鋪叙河伯與北海若之間的七問七答,問答的基本要旨在於“以道觀之,物無貴賤”。陳繼儒此詩的結尾靈活運用《莊子》典故,莊子的形象遂成爲隱逸者的最佳代表。
再有陳繼儒五律《同辰玉過澹圃四首》其四云:
轉徑入花溪,風光似瀼西。桐花垂覆局,禾浪罷耕犂。老鶴解迎客,殘蕉不礙題。居然漢陰丈,高卧水邊畦。(61)《晚香堂小品》卷三,第7册,第241頁。
此詩寫自己的隱居之樂。轉徑入花溪之後,風光猶如瀼水西岸,此蓋以杜甫自比,杜甫《瀼西寒望》云“瞿唐春欲至,定卜瀼西居”(62)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十八,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562頁。。後又云,桐花垂落,彷彿重布棋局;禾浪摇擺,此時已罷耕犁;老鶴可以迎客,殘蕉無礙題詩,陳繼儒正如漢陰丈人,高卧在水邊畦地。結尾二句用《天地》篇漢陰丈人抱甕灌畦的典故。寓言中曾藉孔子評論漢陰丈人,云:“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這段話的解釋歷來不一,郭象《莊子注》釋“假脩”之“假”爲不真,所謂“以其背今向古,羞爲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63)《南華真經注疏》卷五,第249頁。。係從反面解之。但明代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釋“假脩”之“假”爲假藉,所謂:“假脩,謂假人事以脩渾沌氏之術。……識其一不知其二者,守其純一而不雜也。治其内而不治其外者,得乎己心而自忘乎物也。”(64)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卷三,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82頁。則是從正面解之。以陳繼儒詩作來看,應從正面解釋,抱甕出灌的漢陰丈人是一位能得渾沌氏之術者。
以上所舉三例,陳繼儒均對《莊子》精神抱持肯定的態度,此一接受的重點不在於深究《莊子》,而在生命情志的一種寄托。然而,陳繼儒對於《莊子》,另有意欲超越而上的自在讀法,如《求仲過訪山中賦贈》云:
我亦無如我,卿應自愛卿。雲霞滋木食,風雨感花刑。獨坐歌《山鬼》,訛言付墨兵。近來胡蝶嬾,未肯化莊生。(65)《晚香堂小品》卷三,第7册,第236—237頁。此詩《陳眉公先生全集》亦録,題《依韻答韓求仲》,詩云:“我亦無如我,卿應自愛卿。老餘肝胆在,閒覺世途輕。獨坐脩花史,訛言付墨兵。方知蝴蝶懶,未肯化 莊生。”
此詩尾聯用《齊物論》最後一則“莊周夢蝶”的典故,但卻是反用其意。莊子原本是説“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描述的是萬物化而爲一的境界;但陳繼儒卻説“近來胡蝶嬾,未肯化莊生”,反而嚮往胡蝶的悠遊而拒化爲人。此一拒絶,正可與首句“我亦無如我”相互呼應,但這樣一來反而與莊子原意産生了偏離。這是陳繼儒閲讀《莊子》的獨特處,此一獨特處尚有發揮,再看《月明睡起閒步庭中》云:
窈窕簾櫳曲彔牀,空山寂寂漏偏長。秋生幽徑蘭芽長,雨過柴門稻葉香。小睡片時遊混沌,閒行幾步納清涼。凭闌卻笑南華叟,胡蝶飜飛徹夜忙。(66)《晚香堂小品》卷四,第7册,第348頁。
詩作前四句,描寫居於空山的幽静場景,至五、六句“小睡片時遊混沌”、“閒行幾步納清涼”,分别對應於題目的“月明睡起”與“閒步庭中”。此時,遊於渾沌而清醒的陳繼儒,内心感到無比清涼,無比透徹,反而説“凭闌卻笑南華叟,胡蝶飜飛徹夜忙”。莊周夢蝶仍然醒來,未醒的是他無法釐清自己究竟是莊周夢蝶,還是蝶夢莊周。此所以爲清醒的陳繼儒所笑。再和前詩“近來胡蝶嬾,未肯化莊生”相對照,胡蝶忽而懶,忽而徹夜忙,真是隨興所致,完全交由陳繼儒當時的心境來決定。
更特别的接受方式是陳繼儒《壽吴蘇臺》一詩所云:
芰荷衣冷葛巾斜,人説當時季子家。片片青山落君手,年年白髮賣烟霞。杖頭錢挂十千酒,籬下菊留重九花。來去扁舟有秋水,逍遥不復讀《南華》。(67)《晚香堂小品》卷四,第7册,第311頁。
詩題“壽吴蘇臺”,友人姓吴,號蘇臺,恰與吴地、姑蘇臺相應。開端説,隱者的荷衣漸冷,其居處人謂爲當時季札家,正如《史記》記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68)司馬遷《史記》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450頁。。因爲如季札歸隱,故片片青山落於其手,煙霞山水也任其炫耀。再看“杖頭錢挂十千酒”,十千即萬,言其多也,源自曹植《名都篇》“我歸宴平樂,美酒斗十千”(69)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卷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頁。;下句“籬下菊留重九花”,則用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其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70)《陶淵明集箋注》卷三,第247頁。語,意謂隱居的吴蘇臺正似陶淵明一般開朗豁達。尾聯提到來去扁舟有秋水承載,此“秋水”與《莊子·秋水》正合,雖未指篇名,卻已隱隱呼應;後句更直接點出,吴蘇臺的生命達到了逍遥的境界,超越了書本,已然不復閲讀《莊子》。當然,“逍遥不復讀《南華》”,這是陳繼儒的詩句,也是他個人的獨特經驗。
從以上諸詩來看,陳繼儒的《莊子》接受具有兩面性: 一是未述及《莊子》之書,但卻從正面來徵引《莊子》的典故;二是述及《莊子》之書,但卻不願意停留在莊子身上,每欲超拔而上。如此説來,陳繼儒詩中的莊子僅能説具有“身影”,而未必是内在的精神血肉。陳繼儒不是漆園吏莊子,在他的詩作中,在他的生命中,終究有屬於個人的追求。
結 論
方勇《莊子學史》描述明代莊子學的發展過程云:“進入明代中葉之後,由於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變化逐漸加劇,整個社會出現了近代化的人文啓蒙思潮,莊子學也就隨之啓動起來。……到了嘉靖末,直到萬曆、天啓、崇禎時期,明代莊子學呈現出了全面持久的繁榮景象。”(71)《莊子學史》,第六編《明代莊子學》,第3册,第10頁。陳繼儒的《莊子雋》以及詩文中與莊子相關的篇章,正是此一繁榮時期的著作。另觀《明史·隱逸傳》介紹明代隱者十二位,陳繼儒是唯一的晚明士人,晚明的隱逸者注解《莊子》,歌詠《莊子》,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雖然,陳繼儒的《莊子雋》過於平穩而較少創意,以致於當代討論者不多,但如果我們能改换視角,不着眼於《莊子》的闡釋是否新穎,轉爲探測陳繼儒如何藉由莊子來表現其山人的性格與生活,則陳繼儒的《莊子》解讀,在歷史上仍然具有特别的意義。最後,以陳繼儒的詞作《山居雜咏七首》其六作結:
黄冠白麈太清閒,家在沙青水碧間。竹籬門、蕉葉參差見。槿爲墻、草閣茅簷。 酒腸鬆,詩債畢。彈一曲《高山》調,讀一行《秋水》篇。笑呵呵,如醉如顛。(72)《晚香堂小品》卷八,第七册,第519頁。此闋詞未標明詞牌。
戴着道士黄冠,握着白色拂塵,悠閒地生活在青山緑水之間的陳繼儒,此時也翻讀《莊子》,卻僅讀《秋水》篇一行,這樣的瀟灑舉止,又如何貼近於《莊子》的本意?事實上,陳繼儒並不在意是否契合《莊子》,重點在於笑呵呵,如醉如顛,因爲這一方面迴避了當時政局的艱難,一方面尋找到了通隱的生命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