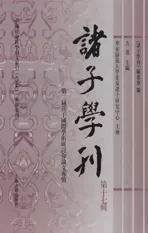莊子論技藝與身體
2018-01-23臺灣鄭燦山
(臺灣) 鄭燦山
内容提要 本文以莊子的技藝與身體爲主題。類似題目,學界多舉《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故事,以舖衍“道”與“技”的辯證關係。筆者並不認爲庖丁所好的“道”,就是老莊所艷稱的“道”,二者毋寧是同名而異實。因爲庖丁,或是其他身懷神技的捕蟬聖手、游泳高手,實不足以成爲證道、體道的例證。跳脱通常的思考角度,我們並不認爲,莊子書中所述及的身體技術是體道的一種類型;身體技術之描述,毋寧只是莊子的一種隱喻。《莊子》書中的技藝故事,或許可以當作是技藝的道家思想化來看待吧!因此,我們直接討論技藝(技術)與身體,盡量不預設與老莊的“道”有關。我們希望透過《莊子》,分析中國古代的技藝觀念,嘗試整理出一些技藝的概念或理論雛形。
[關鍵詞] 莊子 技藝 身體 知識 工具
前 言
本文以莊子的技藝與身體爲主題。類似題目,學界已有許多著作出版。因爲前輩學人所作,多關注在身體技術與“道”的關聯,特别是徐復觀先生討論中國藝術精神課題時,認爲莊子所説的學道工夫,與一個藝術家在創作中所用的工夫相同;學道的内容與一個藝術家所達到的精神狀態全無二致。他並舉《莊子·大宗師》“女偊論道”與《莊子·達生》“梓慶削木”爲例作比較,以證成己説(1)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臺灣)學生書局1974年版,第54—56、120—131頁。。徐氏的觀點對於後學特别具有影響力(2)研究《莊子》的學者,普遍將技藝與“道”關聯起來闡述,或者也據以發揮《莊子》的藝術精神,如顔崑陽《莊子藝術精神析論》[(臺灣)華正書局1985年版]。。不過,本文希望跳脱這個思考角度。因爲我們並不認爲,《莊子》書中所述及的身體技術是體道的一種類型;身體技術之描述,毋寧只是莊子的一種隱喻——與修道、體道未必有直接關係。《莊子》書中的技藝故事,也没有明顯地引導或討論藝術性的問題。《莊子》所述,或許可以當作是技藝的道家思想化來看待吧!所以,我們打算直接討論技藝(技術)與身體,盡量不預設與老莊的“道”有關。我們希望透過《莊子》,分析中國古代的技藝觀念,即便《莊子》作者或許不是有意爲之,也未必關注此課題,但無礙於我們可據以嘗試整理出一些技藝的概念或理論雛形。
關於《莊子》的研究,晚近學者逐漸關注身體技術的課題,而且每每與《莊子》的心性論與修道觀綰合起來討論。學者幾乎無一例外地舉《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故事所及名言“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爲證,以舖衍“道”與“技”的辯證關係。這似乎是《莊子》一書的特色與叙述專長,因爲《道德經》不討論技或是術,或者是技藝之事。因爲老子對於技術之事,視爲巧詐有餘,爲道不足。
筆者並不認爲庖丁所好的“道”,就是老莊所艷稱的“道”,二者毋寧是同名而異實。因爲一位庖丁,實不足以成爲證道、體道的例證,何況《莊子·養生主》結語也只是稱説“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庖丁的故事,只是爲莊子本人所持的養生觀作見證,一如《莊子·養生主》篇首即開宗明義地説“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可謂通篇三句不離“養生”宗旨,卻與莊子的至人神人真人聖人等等之典範人格無關。可見“養生”不等於“得道”,莊子也未提出“養生”可以“得道”的説法。所以,筆者倒是傾向如此解讀,庖丁所好的“道”,就是“依乎天理”的高超技術,或者説是“神乎其技”。依照天理(天道)所展現出來的“神技”,與一般習見的技術,自然不可等量齊觀。“神技”與“技”,不同層次,更是異質,所以説“進乎技矣”。
因此,就讓我們如是觀,讓道回到道,讓技藝回歸技藝,各歸其位。本文論述的主題聚焦於技藝,或者會或者不會觸及“道”。
一、 道家對於技藝的態度
學者討論莊子時,作出如下定義,所謂“技藝”,是指運動領域的技術與美學領域的藝術(3)楊儒賓《技藝與道》,收入楊儒賓《儒門内的莊子》,(臺灣)聯經出版社2016年版,第312頁。。考察《莊子》原文,大致如是。而《道德經》並不特别在乎技藝之事,但是《道德經》對於技藝采取批判的態度。《道德經》五十七章:“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 我無爲,而民自化。”人民追求奇技巧藝,便能製造許多神奇器物。這種“巧”的成果,就是奇物製品。而利器奇物,是爲了滿足人們的功利需求,這是《道德經》所反對的。所以《道德經》十九章要强調“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巧利奇物,誘惑人們生起争奪之心,自然是禍端。《道德經》也並非一味反對巧利,只要巧利歸根於素樸,那就可以接受,所以《道德經》四十五章説“大巧若拙”。而徐復觀就認爲,巧利奇技與世俗工匠之巧,都非老莊所讚同的,但是老莊卻都能認可具有創造性而與造化同工的大巧(4)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第57、60頁。。徐先生的觀察,深刻而有意義。
談到莊子對於技藝的態度,學界必引這段故事。《莊子·天地》如下叙述: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5)參考王叔岷《莊子校詮》,“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年版,上册,第444—450頁。另參郭慶藩《莊子集釋》,漢京文化公司1983年版,第433—438頁。以下援引《莊子》之原文仿此,不另注出。
此寓言説子貢帶着他的弟子南遊楚而反於晉,子貢顯然已能獨當一面了,而這未必没有史實的根據。此可能影射子貢出使吴國説吴王夫差以伐齊而後與晉争霸,遂使數國大亂以保魯的歷史。此事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司馬遷盛讚之曰:“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吴、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大概子貢往説吴越之君,而後途經楚國以反晉,再去説晉君。那麽子貢正是大建功勳,卻也是機心用盡之時。子貢固然大有功於孔子祖國魯國,但是其外交詭計卻害慘了其餘四國。《莊子》作者未嘗不知此史事,故設寓言以譏之,文中有言“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聖人之道”,似乎隱隱然指向子貢憑藉利口巧辭而機關算盡的外交大業,而這卻正是孔子對子貢的諄諄教誨。《莊子》借用機械機心的比喻,嘲諷儒家的機關肆出的世俗事功。機械的使用與機關的設計,都是充滿功利的機心在背後指導。在此,機械明顯是技藝的完成品。這樣子的工藝品藴藏着機心,不見容於《莊子》作者,而慘遭漢陰丈人批判,因爲機心破壞了“渾沌”,勾起利害而興風作浪,這非常符合道家的思維。《道德經》也同樣排斥背離素樸的巧詐取利之事。可以想見漢陰丈人當是一位道家的隱士,既有師承又能深刻思考,一般的農夫顯然不會如此反應。
機械之發明,最初大概也會引來一陣驚嘆,見證了技藝的“神乎其技”。其實技藝本是中性的,但卻有兩評。學者認爲,莊子對於技藝的評價,有兩歧的現象。如果技藝出之於認知性的主體(機心),而所運用之機械是爲人爲的秩序服務,莊子便反對。而如果技藝是與人格緊密相扣,表徵一種人之身心功能的一體化,那麽莊子即持正面意見(6)楊儒賓《技藝與道》,第312—313頁、346—347頁。。
在《莊子》中,與負面的“機心”相對的,則是正面的“天機”。《莊子·大宗師》深刻地説:“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道家對於人類的慾望非常防備,前文《道德經》便要棄絶巧利,主張少私寡欲,回歸素樸之道。“天機”之義,與素樸之道相應,無私無我無爲也。《莊子·秋水》設寓言以抒“天機”之義,説:
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蚿與蛇的行動方式,都是天生自然的,無容私意於其間,這就是“天機”,這是天地之間隱微的機理,卻平平實實、自自然然,不可以有爲改變之。《道德經》講自然無爲,顯得抽象難懂,《莊子》就具象許多,似乎天地之間處處可見“天機”,只在人們能察覺否。《莊子·至樂》觀察到萬物之變化現象,帶出“機”的概念,而言:“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天機”,是宇宙運行之法則原理,幽隱細微,不易辨認。“天機”,無心無爲無意而任運,成就了宇宙之生生不息、變化萬端。
内藴“機心”的事物或因之生出的産品,都與道家思想相違逆。此外的技藝之事,似乎比較得到正面肯定。以下我們進一步作申論。
二、 對於《莊子》技藝的分析
技藝的類型,依據《莊子》書中的例子,我們可以區分爲有成品與無成品兩大類型,這兩大類都有賴於身體技術的支持。吴光明關於《莊子》的“身體”的思考觀點很有深意,他説“身體的思維”,是以身體爲手段行使思維;“身體思維”,則是身體本身在思維(7)吴光明著、蔡麗玲譯《莊子的身體思維》,收入楊儒賓主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臺灣)巨流圖書公司2009年版,第395頁。。我們藉此轉語,則“身體的技術”,是以身體爲手段施展技術;“身體技術”,則是身體本身就是技術。前者,身體與技術爲二,身體透過學習,而習得技術。後者,身體即技術,技術内化於身體,合而爲一。本文討論的,正是《莊子》書中的“身體技術”。
其次,有成品的技藝,又可分爲工藝與藝術兩類。而技藝原則上是手工的,而非透過工具機器或其他輔助器具的商品製造類型之技藝。至於無成品的技藝,則純粹是一種身體技術的展演。
技藝在時空架構下展現出來,而形成技藝事件,這個事件構成的元素,可能包括從事技藝者的心理質素、身體條件、技藝知識以及技藝者所需要的工具、材料、場所等等現象。法國社會學大家毛斯(M. Mauss)認爲,身體是人首要的與最自然的工具。或者,更準確地説,不用説工具,人首要的與最自然的技術對象與技術手段就是他的身體(8)馬塞爾·毛斯(Marcel Mauss)《社會學與人類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頁。。所以我們對於《莊子》技藝的分析,自然會涉及“身體技術”範疇,因此相對而言,“身體”可以算是技藝中的直接工具,而身體所憑藉的身外工具,則屬於間接工具。
此外,身體條件的差異性,或是技藝施展的場所(外在環境),其意義與重要性,似乎比較被《莊子》所忽略。當然技藝事件也很需要在場的見證者。如果没有見證者,則技藝現象便只如山中花開花落,卻也並無礙於技藝現象的自足自存。所以見證者,只是技藝事件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
關於《莊子》書中的技藝事例,本文不擬直接當作修道體道之典範看待,而傾向抱持那是技藝的道家思想化現象之觀點,也就是在技藝的實踐過程,某種程度地體現道家的思想精神。因爲我們實在很難將游泳高手、捕蟬聖手乃至於庖丁,歸類爲至人、神人、聖人。《論語·子路》不是説過:“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巫醫只是孔子印證恒心重要性之舉例而已,巫醫可不是儒家的人格典範。《莊子》書中的技藝範例,也可如是觀。所以,我們打算針對技藝事件的現象進行分析,盡量不與“道”、“修道”關聯討論。
以下我們依照前述技藝的類型,分類做討論:
(一) 有成品的技藝
《莊子·達生》記載一則故事: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静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禄;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梓慶應當是位木工,他的技藝展現在製作鐻上,鐻成而讓人驚歎鬼斧神工。這則故事叙述梓慶在製作成器之前的準備工作,注意到幾個關節。一是技藝者的心理質素。二是成品所需之材料。梓慶必須先齋戒静心,以免耗散神氣。這是對於技藝者精神主體之要求。楊儒賓一向强調道家的形氣主體(9)楊儒賓《技藝與道》,第3頁。,不是無因。《莊子·人間世》標揭“心齋”,暢論虚氣之道。“心齋”工夫可以達到“徇耳目内通而外於心知”,也就是開發耳目等感官之内在隱微之潛能,以致得以摒除心知算計之干擾,而臻“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境界。這也同於上文《莊子·天地》漢陰丈人所説“純白皆備”(此爲作者之轉語)之義。《莊子·達生》另一則故事也如此闡述這個道理: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關尹論列至人、聖人之道,也要守氣以摒除心知巧利,才得以保全其天性、神氣,而不爲外物外事所干擾。
梓慶藉由齋戒静心,三五七日,逐漸戒除外在功名利禄、利害關係之心,甚至忘掉形體感官功能,人的形氣主體算是達到類似於《莊子·大宗師》“坐忘”境界了。瑞士著名漢學家、哲學家畢來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研究《莊子》,特别關注在身體技術活動中,由一個機制向另一個機制過渡變化的過程,他説那是一種主體性的基礎物理學(10)畢來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莊子四講》,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1頁。。賴錫三分析了畢來德之説,認爲畢氏堅持身體思維,拒絶以氣論解釋之,以便避開傳統以所謂形上學思維解釋道家的窠臼。不過賴氏卻不贊成畢來德的論點(11)賴錫三《道家型知識分子論: 〈莊子〉的權力批判與文化更新》,(臺灣)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93—198頁。。如果畢來德將《莊子》的“身體”局限於物質性、經驗性,那麽在解讀《莊子》許多文本段落時,恐怕會出現扞格現象。況且《莊子》作者,似乎也不是一位人體生理學專家,所以,這位作者顯然不會强調生物學意義的身體議題,如畢來德所關心的那樣。我們從上列《莊子》引文,可以看出“氣”概念對於身體技術的關鍵意義,筆者類同於賴錫三之看法。
心理素質達標,梓慶不再因爲從事公事以至患得患失而淆亂其心,此時心靈專精内巧。條件具足了,所以梓慶便入山林選材。器物的原始材質,是製作器物之成敗的關鍵環節之一。我們看到梓慶自述,他選材必須入山林,因爲可以廣泛取材,而且依照樹木之天生材理,所謂“天性”,作爲選材之標準。這自然預設着梓慶深諳樹木材理之知識(12)同樣,“庖丁解牛”的知名故事,也觸及了技藝的知識問題。而技藝所需具備的知識,向來容易被忽略,楊儒賓則認爲應當嚴肅面對與思考這個問題。楊氏的觀察相對敏鋭而有意義。參楊儒賓《技藝與道》,第336頁。另參楊儒賓《無知之知與體知》,收入楊儒賓《儒門内的莊子》,聯經出版社2016年版,第384頁。,但他不能摻雜私意慾望,而是憑藉鍛鍊多時的專精内巧之心理素質,判斷合乎製鐻的木材,最後才加工成鐻。末尾一句“以天合天”,更是結穴所在。清代王先謙注解道:“以吾之天遇木之天。”(13)王叔岷《莊子校詮》,中册,“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年版,第709頁。非常精到,一語道破。以吾人之天性,遇合於樹木材質之天性,那便決定了製鐻的成敗。梓慶在此倒是不特意强調木工的身體技術問題,在製作木鐻的流程中,心理素質與木鐻之素材,似乎更具有關鍵地位。材料關係着製鐻之成功與否,而心理素質則決定了是否可尋着最佳材料。
由這則故事,可以看到,梓慶從齋戒静心以保全其天性,以至入山覓尋“天性”之木材,都浸潤着道家思想的精神。明顯的,技藝已經被道家思想化了,這應當是《莊子》刻意鋪排這類技藝寓言的用心所在吧!當然,即便如此,我們也大概不會將梓慶當作是《莊子》所謂的至人、神人、聖人吧!
另一則鑄鐘的故事,出現在《莊子·山木》,如是説着:
北宫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樸。’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
藉着北宫奢口中道出,製鐘並無特别方法或技術,只要謹守樸拙純一之心思,爲鑄鐘做準備。我們看到技藝之心理素質問題再次被凸顯出來,也一樣被道家思想化了。
工藝品之製作如上例,而藝術品,如繪畫,例子見於《莊子·田子方》: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礡,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依照常理,作畫之前理當有一些準備工作,所以宫廷中的諸多擅長畫藝的文書官,聽得國君征召,一個個摩拳擦掌地舔筆研墨想要有所表現,以博取美名與國君青睞。廳堂之内馬上蟻聚了一大批文書官,甚至滿溢,有一大半人只能堂外候命。則彼輩趨利之心與汲汲營求之態,昭然如戲。《莊子》非常生動的描述,卻又語帶嘲諷,正是爲了鋪排“真畫者”的出場。最後到場的那位文書官,姗姗來遲,卻又大摇大擺地,向前承受命令之後,也不佇立恭候,反而直趨官舍,大氣地脱掉上衣,赤裸上身,準備作畫,活脱脱如“坦腹東床”的王羲之。
衣服對於身體是種束縛,相對於裸體,也是文明的象徵,自然對於心靈也是一種框限。解衣,算是解除對於身心産生束縛的一切外在條件,而進入一種坦然舒適的身心狀態與氣勢,曰磅礴。總之,這位文書官是非利害權勢等俗事全不關心,作爲畫家擁有這般的心理素質,便被宋元君讚嘆爲“真畫者”。這可算是“無畫之畫”的境界了,正如我們後文會引用的另一則關於列禦寇射箭的故事,其中所述“不射之射”之理一般。而《莊子》這則故事,對中國後代之書畫理論或創作産生深刻影響。北宋大畫家郭熙《林泉高致集》論“畫意”一段時説:“世人只知吾落筆作畫,都不知畫非易事。《莊子》説畫史解衣礴,此真得畫家之法。人須養得胸中寛快,意思悦適。……則人之笑啼情狀,物之尖斜偃側,自然布列於心中,不覺見之於筆下。”正是在闡明心理素質的涵養也是作畫的法則之一。不過紙筆墨硯等作畫技藝所需之材料或間接工具,卻都未論列。
(二) 無成品的技藝
以下展現各種技藝的例子,都没有製作完成品,都算是身體技術。《莊子·達生》開篇便討論通達於養生之正理,這一篇中收録了許多則身體技術的寓言,在《莊子》書中顯得突出。或許《莊子·達生》是受到《莊子·養生主》中也有“庖丁解牛”身體技術寓言的影響吧!
《莊子·達生》一則故事强調“神”對於身體技術之重要,如此叙述: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承蜩的痀僂丈人自謂“有道”,這個“道”,是方法之義,並非老莊所盛論的形上的“道”。這則寓言,重點在强調“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的道理。究其實,也並非老莊的修道體道。
痀僂丈人能够以竿子抓蟬,運用純熟,巧妙如手,讓孔子大嘆靈巧神妙。痀僂丈人的技術是藉由長期專一心志的訓練而來。我們可以這麽説,身軀與手臂是直接工具,間接工具則是承蜩的竿子。他練習在竿子上堆疊丸形物而不墜落,等到積累五丸而不墜,則用竿如用手,竿手合一矣!這種心手相應而能展現神乎其技的身體技術,當非這位丈人一己的創發。我們參考法國社會學家毛斯(Marcel Mauss)爲“身體技術”給出定義式的説明,乃指人們在不同的社會中,根據傳統瞭解使用他們身體的各種方式(14)馬塞爾·毛斯(Marcel Mauss)《社會學與人類學》,第301頁。,便可以推知潛在於身體技術背後的族群性、文化性與社會性。
《莊子》書中所述及的身體技術各種寓言,其中人物都是中下階層的勞動者,其實背後的族群性、文化性與社會性問題,不應該被輕易忽略,或有意地引導而轉移他題。譬如,説《莊子》是爲了强化論述社會階級性的議題,如社會主義中國哲學史家所刻意强調那般;或者説《莊子》也具有符合左派精神的勞動意識(15)參楊儒賓《技藝與道》,第351頁。另參楊儒賓《無知之知與體知》,第380—381頁。。其實,問題没有這麽複雜曲折。《孟子·滕文公》不是説“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麽?即便無一官半職而遊學於各諸侯國的儒生孟子,都自居於勞心的統治階層,則身懷技藝的勞力者勞動者,本來就遍布於社會底層。我們無法想象,齊桓公會精通或做着輪扁所從事的勞動工作。所以,《莊子》只不過是忠實地反映社會實況,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事實,因此對於《莊子》的主觀解釋,恐怕是無謂而多餘的,也背離歷史事實。
所以,這則寓言的内容,未必是憑空捏造的。承蜩的痀僂丈人,可能就是以承蜩爲業的老人家,疊丸不墜的訓練方法與承蜩如掇的身體技術,當是他的本業職能,而非别行别業所能專擅者。我們大概可以預想當時有這種職業類别,而這個職業社群,可能流行着這種師徒相承襲的訓練培養承蜩技術,從而形成了其職業之文化性,而痀僂丈人則是其職業圈中的佼佼者。
我們分析,痀僂丈人展現他的身體技術,神乎其技地運用了間接工具竿子,但是在整則寓言之叙述中,並未特意强調間接工具(竿子)的關鍵性,並未對於竿子之材質、形狀、長短或是輕重,乃至顔色有所着墨。關鍵處反而是直接工具身軀與手臂的訓練。手臂必須持竿累丸而不墜,才能大功告成,可以承蜩矣!而且手臂還需訓練到彷彿槁木樹枝一般,紋風不動,達到最高的穩定性。甚至另一直接工具身軀,也要訓練到像樹幹盤根一樣,立定不動。而《莊子》書中,屢屢談及形如槁木而心若死灰之語,實有深意。槁木是死物,了無生機,形如槁木,隱喻完全没有意欲、意向性(16)郭象注《莊》説:“死灰槁木,取其寂寞無情耳!”又説:“槁木死灰,無情之至。”參考郭慶藩《莊子集釋》,(臺灣)漢京文化公司1983年版,第44、791頁。而《莊子》原文,一則説因爲“吾喪我”,所以才槁木死灰;另一則説嬰兒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所以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參考郭慶藩《莊子集釋》,第43—45、790頁。此顯示出,槁木死灰不是具象的寫實,而是隱喻,是無情無欲、無意向性的隱喻。或者將槁木死灰,當作是《莊子》工夫論的進境之一,也算是具有啓發性的一種詮釋角度。參考蔡璧名《當莊子遇見Tal Ben-Shahar: 莊子的快樂學程——兼論情境、情緒與身體感的關係》,收入余舜德編《身體感的轉向》,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229、236—244頁。。人的意識實際上是貫串整個軀體的,身體的動静,展現了人的意欲、意向性。如若槁木之死物,則無意欲、意向性,自然没有捕蟬之意了,與物無傷,蟬就不會警覺而走避,最後自然蟬就手到擒來了。
以上工夫與工具諸多條件一切具足,又須專心致志,貫注於蜩的翅膀上,這樣才能如掇般地施展承蜩技術。不過,對於身軀與手臂這種身體條件,高矮胖瘦曲直,倒是不計較不討論,顯然不重要。孔子聽完丈人自述後,總結一個“神”字。“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的心理素質的磨鍊,是承蜩這種身體技術的根源性基礎(17)“凝神”的工夫,不僅只是技藝展現之基礎,學者也認爲中國傳統藝術之創作,主體心靈操持的“凝神”的工夫,居於成敗之關鍵地位。而“凝神”的工夫,多得自《莊子》的啓示。參考顔崑陽《莊子藝術精神析論》,第256頁。,而承蜩所需的直接或間接工具,則居於輔助地位。
“庖丁解牛”故事是家喻户曉的,見於《莊子·養生主》: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庖丁肢解牛隻的技術,更在良庖之上,依照寓言中的叙述,解牛過程充滿韻律感與音樂感,真真神乎其技了!文惠君觀後,歡喜讚嘆,引出庖丁的由衷之言:“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其中所説的“道”,基本上不能當作是老莊長篇大論所指涉的“道”,而毋寧是指超越於解牛之“技”(良庖所能)的解牛之“道”(主角庖丁所臻之境)。庖丁所好的“道”,就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神妙技術。依照天理所展現出來的“神技”,與一般習見的技術,自然不可等量齊觀。“神技”與“技”,不同層次,更是異質,所以説“進乎技矣”。而從天理、固然二詞,可以看出這個天理不是什麽形上學概念,而是指牛的天生本來的生理機理結構之理則。庖丁解牛之前,當然必須充分掌握關於牛的知識。這可以從其自我訓練過程看出端倪。
爲了達至解牛之“道”,庖丁説出他的自我訓練。一開始學解牛,則專一心志於牛,三年之後,進而對於牛隻之身體結構之瞭解,細密入微。這兩個階段,都可算屬於“用志不分”層次,相對地所運用的身體工具,則是感官。庖丁又自述十九年後的今天,則官知止而神欲行,並能依乎天理以解牛,於是臻於“乃凝於神”境界,展現出“神乎其技”的化境,讓文惠君大開眼界,歡喜讚嘆,而欲臻這般化境所運用的則是心神。
這個過程,庖丁身心狀態的轉變,特别引人注意。所見無非牛者,是對象化;未嘗見全牛,則是去對象化。此時牛之“天理”,即關於牛的知識,已經完全被庖丁意識化了,技藝施展所需的知識也被超越了(18)不僅如此,庖丁解牛故事所引生的“養生”課題,也需要養生的知識與技術,而這個知識、技術最後也會被超越,才能達到真正的養生之旨。參考[日本] 池田知久著,王啓發、曹峰譯《道家思想的新研究: 以〈莊子〉爲中心》,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431頁。池田氏援引了《莊子》以至兩漢的文獻,從中可見知識與技術,仍有其必要性,但最終也被超越了。。最後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則更是超越了意識與感官。“神”是牛之“天理”與庖丁身心完全融合爲一的一種最佳狀態。楊儒賓説得很好,完美技藝的創造不是意識,而是身體。只有意識退位,它的作用散布到全身,全身精神化之後,才能技也進乎道(19)楊儒賓《技藝與道》,第329頁。。而此時便已超越了技藝的熟練狀態,即技藝的技巧狀態,而進入高階技藝的無技巧狀態了,那便是“道”(20)[德] G·沃爾法特著、那薇譯《無技巧的藝術》,收入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二輯(“道家與現代生活專號”),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285頁。。
其次“神欲行”,“欲”字點出“神”之勃發沛然之勢,此時解牛,那就真是勢如破竹、出神入化了。“神”字是本文之“眼”,也是道家思想的關鍵概念。其他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是直接工具,間接工具則是刀子,則都不論矣!
《莊子·達生》有兩則在水中施展的身體技術之故事,第一則曰:
顔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憚,以黄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
這位津人之所以能操舟若神,因爲他忘了水的存在,在水中活動,就好比在陸地上一般那麽自在,所以游泳與操舟,都能得心應手。或許如此,這位津人大概也不知有什麽學習的方法可以告訴顔淵。津人無視於水的存在,不會將水中活動視爲畏途,所以不會犯外重内拙的毛病。
《莊子·達生》第二則故事爲: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文中所謂“有道”、“無道”,這個“道”,也是方法之義,也非老莊所盛論的“道”。“從水之道”,這位吕梁丈夫只是順着水流等之水性之理而不違逆而已,這即是水之道,也算是在水而忘水。其意旨相當於庖丁解牛故事中所説的“依乎天理”。實際上與老莊的修道體道議題,並無直接關聯。而這位吕梁丈夫的游水技術,似乎算得上是“天生”使然。“天生”,所以没有學習與訓練的方法可循,故曰“無道”。即便無跡可尋,但還是頗爲符合道家思想的精神,因爲不論是“從水之道”或是“依乎天理”,都是容不入一己私意之有爲,所以就是“無爲”了。吕梁丈夫所展現的是真正的身體技術,無須任何間接工具。
《莊子·達生》有二則故事涉及身體技術的工具問題,值得一論: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钩百而反。顔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馬是展現駕馭之術的工具,馬力竭盡,可見東野稷這位駕駛者,不瞭解駕馭所需工具的重要性,而且對於工具的性質,也無法真切瞭解掌握,以至工具至折摧的地步猶不自知。所以,駕馭這種身體技術,對於工具品質的要求很高。否則,即便如東野稷有相當高超的駕馭技術,工具條件不具足,最終也會敗事。
另一則故事雖然也談工具,但是卻强調工具是可以被身體技術所超越的,最終也無需工具了。《莊子·達生》説: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内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倕,帝堯時的巧工(21)王叔岷《莊子校詮》,中册,“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年版,第711頁。。他之所以名垂千古,因爲他的巧技(22)《莊子·胠篋》便説:“毁絶钩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工倕手指之巧,可與钩繩規矩相比擬,所以天下人便顯得相形見絀了。。他可以僅憑藉自己的手指畫出圓與直角,畫迹可以與規矩所畫重疊。也就是可以超越規矩,無需運用規矩。身體技術之心理條件,具有關鍵地位,甚至有時可以超越工具所提供的實用性與便利性,乃至取而代之。正所謂心中有規矩,無處不規矩。以自己的身體作爲工具,超越且取代外在的間接工具,如“工倕旋而蓋規矩”者是。
《莊子·徐無鬼》這一則觸及身體技術展現的場所或者外在環境的問題,非常獨特: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身體技術展演的場域非常重要,外在環境的條件之配合,可以提升身體技術之施展之效能。匠石如果没有郢人這麽好的合作對象配合演出,就是有通天本領,也無處表現。郢人立不失容,死生無懼,所以也不會犯外重内拙的毛病,而可以讓匠石肆無忌憚地盡情發揮他的運斤成風的神技。
結 語
我們透過上文的分析與討論,《莊子》書中的技藝例子,不管是有成品或無成品之類型,都涉及身體技術。而構成技藝事件的元素,可能包括的心理素質、身體條件以及工具、材料、場所等,也在《莊子》中被述及。相對區分,心理素質、身體條件屬於主體面,而工具、材料、場所等,則算是客體面。但是無論主體面或是客體面,都呈現出技藝的道家思想化的情況,所以本文並未將技藝當作修道體道的範例。我們在《莊子》中看到了如老聃、南郭子綦、女偊、壺子等至人聖人一一登場,搬演着道家體道的故事,不過本文所討論的這些出神入化的技藝的持有者,是無法與他們等量齊觀的。所以,學者認爲,至人聖人與藝術家(或者技藝家)只有偏與全之别,而無本質之别,都是“體道”的例子(23)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第131頁。。這種觀點我們有保留看法。《莊子·田子方》記載列子的故事: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黄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這也是極有代表性的故事。列子的射箭技術非常高超,也可謂神乎其技了!但是列子還是犯了外重内拙的毛病,因爲列子有怵然之心、恂目之志,死生之念入懷,當然就純白不備了,而與神閒氣定的伯昏無人比較起來,天壤之别也。如果伯昏無人所説的“不射之射”歸類爲“體道”之例,那麽列子的“射之射”,即便也算已臻令人驚嘆的射藝化境,但還是被比了下去。因爲列子射藝還是包含着形式機巧,而伯昏無人則超越而調適上遂,已是“道境”。所以,列子與伯昏無人,就不是偏與全之别而已,而是有本質上的差異,就無法以王陽明所説的聖人純金的“成色分兩”説譬喻之。
我們在列子故事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到矛盾情況的存在,是以本文采取的解釋立場,便是技藝的道家思想化,而不是將技藝當作體道的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