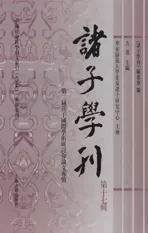“以儒解莊”的詮釋策略
——宋代莊子學研究回顧與展望(1981—2016)
2018-01-23臺灣劉芷瑋
(臺灣) 劉芷瑋
内容提要 本文先以總論整理宋代莊子學合論的代表作,再透過蘇軾學派、王安石學派、朱子學派、艾軒學派四個學派的莊子詮釋,探討宋代莊子學在“以儒解莊”詮釋策略上的效用,反思此種詮釋策略的可見與不可見。本文主張並不是因爲宋代是理學的時代,所以解莊以儒,無可厚非,而是因爲從莊子詮釋史的角度來看,可以得見這樣的儒學内容應具有三教的特質,宋代莊子學實是晚明莊子學的前哨站。而從詮釋策略的觀點來説,儒學作爲莊子學吸收三教發生裂變的平臺,這樣的莊子學不是被局限在儒學的框架中。最後,以儒解莊不過是一種策略的運用,儒學自身也隨時在變化之中,也解構了詮解自身的既定限制。三教融合並非走向同一,而是透過建構與解構,與時俱進。
[關鍵詞] 蘇軾 王安石 林希逸 以儒解莊 日本朱子學 中國陽明學
前 言
“以儒解莊”是當代莊子研究中普遍常見的詮釋策略之一,若追溯其源,此説建立肇端於宋代,是宋代莊子學現有研究中最主要的特徵。宋代是理學的時代,“以儒解莊”的詮釋策略似乎與理學的發展息息相關,但宋代解莊之儒者並非全爲理學家,如北宋的王雱、吕惠卿、蘇軾等並不屬於理學學派,僅能概括爲廣義的儒學學者。即使同屬理學派别,看待莊子的態度、見解也有不同之處。宋室南渡以後,在福建的艾軒學派和朱子學派均可追溯至共同始祖伊川,兩個學派雖具有共同的始祖,然而學派風格卻根本不同。在現有理學研究中,對於艾軒學派的着墨極少,僅可確定的是,此派並不在當代濂、洛、關、閩的理學系譜之中。相較於朱子學派僅有部分評論、音義校對《莊子》,艾軒學派爲首度對《莊子》進行全面注疏的南宋理學學派。這樣的差異,當視爲理學發展中的某種歧出,或是有助於還原南宋理學學派風格的呈現方式。從以上儒學差異化的風格呈現可知,即便宋代屬於理學的時代,也當正視理學學派發展上的多元特徵。由此推論,以儒解莊之“儒”並不能概括爲後世道統意識中的朱子學,從莊子詮釋史的發展來看宋代思想史,實有探究宋代思想以何爲“儒”與何以爲“儒”的必要。
有鑒於此,筆者提出以下的問題,作爲回顧自1980年代以來,宋代莊子學研究成果的觀看視角。其一,宋代各派解莊,各自具備怎樣的學派特色;其二,關於歷代莊子學史的比較,一般常將晚明莊子學比擬於魏晉莊子學,而宋代莊子學的討論則較少述及,筆者將指出宋代莊子學和晚明莊子學有何相似處。本文將先行以總論整理對宋代莊子學進行全面地、整體地理解的代表作,再透過蘇軾學派、王安石學派、朱子學派、艾軒學派這四個學派的莊子詮釋,以探討宋代莊子學在“以儒解莊”詮釋策略上的效用及其邊界,反思此種詮釋策略的可見與不可見,最後對林希逸《莊子口義》十七世紀中葉在中國和日本的傳播與影響進行立論。
一、 總論:“以儒解莊”的宋代莊學概況
華語學界對宋代莊子學的研究在1988年以前是一片空白(1)參閲黄錦鋐《近三十年來之莊子學——論文部分(1951—1981)》,《漢學研究通訊》第1卷第4期(1982),第147—149頁。另簡光明《大陸莊學研究概況》一文考察1949—1988年間大陸地區莊學研究,於宋代莊學也是付之闕如。,臺灣以簡光明的博士論文《宋代莊學研究》(2)簡光明《宋代莊學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1997年。作爲開始。本論著主要結構分爲四個部分,分别爲宋代莊學著述解題、北宋莊子學、南宋莊子學、宋代莊學孚説,其中的北宋、南宋莊子學以注疏家的時代先後爲依序排列,包括: 北宋吕惠卿、王雱、程俱、王旦、劉概、吴儔、賈善翔、蘇軾、陳景元,南宋洪邁、林希逸、劉辰翁、范應元、褚伯秀。本論著居於宋代莊子學研究發展的前端,爬梳其注解與評論之特色,自有其開創意義。然而,面對莊子學於宋代思想中所居的角色與地位,或其注疏與佛教、道教、儒學之交涉,當有繼續深入探索的空間。
近年來,另一部探討整體宋代莊學的專書爲蕭海燕《宋代莊學思想研究》。本書爲博士論文改編,共分爲五章: 第一章講述宋代的學術背景,包括懷疑、創新、經世、包容精神,統治者與文人學者對莊子的重視和關注;第二章爲宋代莊學文獻的目録、提要、詮釋特點;第三章爲宋代莊學中的道論,包括道與理的虚實關係、以理釋道等部分;第四章講述宋代莊學中的心性論,包括儒家性命道德學説解莊,道教内丹心性論,以及佛教心性論對莊學的滲透;第五章講述宋代莊學的治世思想,包括認爲莊子是救世之書,推無爲以寄有爲,及借莊子發揮仁義禮法的思想。作者認爲:“宋代學者在解《莊》論《莊》時表現出很强的儒學化傾向,他們或將莊子歸入孔門弟子之列,莊孟並稱,努力消解莊子與孔孟之間的矛盾;或援引儒家經典以釋《莊子》,分析儒、道兩家在思想理論上的一致性。”(3)蕭海燕《宋代莊學思想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頁。此説頗能把握宋代莊子學的儒學化傾向,但《莊子》三十三篇本身即已具有孔子及其弟子言論凡四十餘段,且不乏重要言談,如心齋、坐忘等均由孔顔論述中引出,莊子與孔子之間,未必有强烈的矛盾,在分析儒、道兩家是否應具有思想的一致性之前,仍需面對宋代注疏的背景與先秦在時代區隔以及受佛道思想刺激之不同處。
宋代莊儒關係在近期研究中頗有發揮,除了以上專書以外,單篇論文亦所在多有。如《宋代“援莊入儒”綜論》(4)簡光明《宋代“援莊入儒”綜論》,《嘉大中文學報》,2009年第2期,第121—150頁。一文,先介紹“援莊入儒”等術語的使用差異和重疊處,再述宋代“援莊入儒”的幾個論點,包括: 蘇軾“陽擠陰助”説、王安石“存聖人之道”説、朱熹“見得道體”説、林希逸推尊孔子説、褚伯秀尊孔子説。其後,介紹宋代“援莊入儒”的論述,包括: 王雩以《易》解莊、吕惠卿以《孟子》解莊、林希逸以《論語》解莊、褚伯秀以《中庸》解莊。在檢討宋代“援莊入儒”一節中認爲,宋代學術氛圍以儒學最盛,儒者熟讀儒書,並以儒學解莊是一件相當自然的事。一般而言,中國思想史分期主要可分爲六期,但這六期的分類只是用以突顯該時代有其較爲明顯的主流思想崛起,因此而有别於前代。儘管宋、明以理學見稱,但宋、明思想不僅限於理學,因爲魏晉以後,儒、釋、道三家在每一時代均同時存在。如以宋代學術以儒學最盛來解釋“以儒解莊”在該時代出現的必然性因素的話,則歷代《莊子》注疏之發展,應該僅宋代莊子學有“援莊入儒”的傾向。儘管筆者同意以儒解莊是肇端於宋代的一種莊學詮釋策略,但“以儒解莊”的策略取向並不限於宋代。在莊子尊孔論的系譜上,我們可以肯定此説有其顯著之發展,明清注疏自亦不乏相近的策略運用。問題的關鍵在於,不同時代或同時代而不同學派的儒學在共通詮釋策略的運用下,有何殊異的特色?因爲,若只是説明解莊以儒是一件自然不過之事,那麽就將忽略掉宋代儒學在性命之學上與莊子同道的新時代的特徵。
另《宋人以論語詮解莊子之探討》(5)簡光明《宋人以論語詮解莊子之探討》,收録於《經學與文化全國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中興大學中文系2013年,第241—252頁。一文,認爲以儒解莊的發展是莊子學史的重要課題,宋代的學術氛圍以儒家爲最盛,注家以《論語》解釋《莊子》,藉以説明孔子與莊子的思想有其會通之處。其文分爲幾個部分: 其一,蘇軾的莊子“助”孔之説和“楚公子微服出亡”之寓。但筆者考察助孔説是翻史遷舊案,《論語》並無楚公子一事的記載,所以蘇軾之論並非屬於以《論語》解莊。其二,林希逸以“樂”詮釋逍遥。但其後提到《應帝王》篇一段,林希逸以《論語·子罕》“四毋”釋之,又與此小節標題之論樂和逍遥無關。僅有其三之王雩“予欲無言”釋莊子立言之旨,及其四之王旦以君子三變釋《應帝王》季咸相人二段,與其題旨相關。
以上所舉的研究著述均以綜合討論的方式,總論宋代莊學的特色,四項著作有一個共同表述,便是强調宋代以儒學最爲興盛,表達宋代學者以儒解莊是自然不過的一個詮釋現象。然而細觀諸論,其在論述上難免單薄,普遍忽略了宋代在儒學以外仍有釋、道家等思想活躍的存在,以及在長期的思想史變遷中,三教間的互動與發展。這些變動性的因素,在判讀文獻時,也都必須納入考量的範圍。
二、 北宋莊子學: 蘇軾與王安石學派的《莊子》詮釋
蘇軾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莊子的啓發已是衆人所知之事。相關論著中,最爲詳細的早期著作,爲韓籍學者姜聲調的《蘇軾的莊子學》(6)姜聲調《蘇軾的莊子學》,(臺灣)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本書是作者的博士論文所改編,全書可見四個主要部分: 其一,以《莊子祠堂記》爲探討蘇軾評論《莊子》之中心;其二,以《廣成子解》爲探討蘇軾注解《莊子》之中心;其三,探討蘇軾文藝中的莊子學;其四,蘇軾的莊子學淵源及其影響。本書結論認爲,蘇軾在中國莊子學史上的地位建立於三個部分,其一建立“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的理論基礎,此論爲後世廣爲徵引,其二判《讓王》《説劍》《漁父》《盜跖》爲僞作,後世辨僞者亦頗徵引其説,其三是將《莊子》融入文藝的文學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余中樑《論蘇軾及其門人的莊子學思想》(7)余中樑《論蘇軾及其門人的莊子學思想》,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爲近年首次針對蘇軾及其門人的莊子學進行分章研究的碩士論文,本文認爲蘇軾在文學作品中闡發莊子思想,對後世産生重要影響,並指出黄庭堅等蘇門學者也有多篇闡發莊子思想的著作,作者認爲他們的著作行爲具有獨立意識、文化官僚的人格特徵,並强調貶謫的遭遇使他們以莊子思想爲依托,以面對人生的挫折與困頓。本論文第二、三章爲主體,第二章主論蘇軾的莊子學思想,第三章主要討論黄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五人的莊子學思想。
中國大陸、臺灣近年相關論文數量頗多,絶大多數研究側重於兩面,其一在於影響(8)這樣的立論很常見,例如張瑞君《論莊子思想對蘇軾人生境界的影響》,《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周洋《試析〈莊子〉對蘇軾散文的影響》,《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08年第8期。。他們普遍同意蘇軾創作受到莊子思想的影響,這樣的影響反應在字裏行間的表露,恰好説明了在貶謫遭遇的困頓裏是莊子思想給予蘇軾慰藉,使他超越苦難,追求心靈的自由與提升人生的境界。其二在於引用(9)例如: 陶慧《夢里栩然蝴蝶一身輕——試析蘇軾詞中的〈莊子〉典故及意象》,《文教資料》2012年9月。宋德樵《蘇軾詞化用〈莊子〉文典淺探》,《有鳳初鳴年刊》第3期(2007年10月),第59—78頁。戴伶娟《蘇軾詩莊子用典之接受研究》,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5年。。蘇軾詩詞不乏引用莊子典故,這樣的説明從蘇軾作品進行整理與比對,其結論或有認爲蘇詞因爲引用了莊子典故,而有神仙出世之姿,或仍又歸結莊子思想是身處逆境者的精神解脱之道。以上兩個側重面實爲一體,所述爲同一事實的兩種表達,都是認爲莊子思想是蘇軾貶謫人生的安慰,蘇軾作品的高超絶妙與莊子思想的空靈不可言不僅同理可證,並且殊途同歸,這樣的立論根源是因爲學界長期以來將莊子思想定位在消極、避世、隱逸、出世,只存有而不活動的境界型態。文學史的詮釋與思想史的定位彼此間互爲因果,由此可推見其端倪。
蘇軾的莊子學説在後世影響很大(10)徐聖心:“下至明代,東坡之説已蔚成一大風勢。”見氏著《莊子尊孔論——莊學史上的另類理解與閲讀》,《臺大中文學報》,2002年第17期,第18頁。,儘管經常被歸類於文學家,但並不表示他没有作爲一位思想家的可能。無論是從尊孔論系譜中,或是從莊儒關係的古老問題中,抑或在以儒解莊的詮釋策略中,蘇軾莊子學都具備着在發展史中一個重要的座標位置。蘇軾及其學派缺乏全文注疏,但是蘇軾學説於後世的渲染力卻可能是王安石、林希逸等注疏家所難以企及的。
近年王安石學派莊子學的研究著作較多,楊文娟《宋代福建莊學研究》(11)楊文娟《宋代福建莊學研究》,三晉出版社2012年版。書中的北宋注莊代表爲王安石學派。本書也是作者的博士論文改編,全書分爲五章,共四個部分,分别爲: 宋代福建的文化背景與莊學繁榮、北宋新學思潮下的以儒解莊、朱熹對莊子及其相關問題的論説、《莊子口義》的三教融合思想。該書在北宋學者的部分選擇了吕惠卿、陳祥道、林自三人的注疏加以探討,並表示:“此三者雖爲北宋中後期的閩地學者,但他們受王安石思想的影響遠遠大於當時福建學術文化的浸潤。”(12)同上,第40、41頁。這即是説,三人的注疏與福建文化的關係較小,而受到王安石影響更大。儘管本書書名爲福建莊學研究,有從地方性探究其思想脈絡之本意,但由於福建學術文化並未深刻地浸潤於三人的著作思想中,於是這樣的地方性彰顯得不太得宜,充其量只能説三人恰巧都是福建人,又逢朱熹與林希逸同在福建,是以形成此題。福建文化自有其特色,地方性的特色如何與其時代的莊子學接軌在此則難以説明。不過本書仍可提供讀者一些訊息,如據作者對方志的查證,艾軒學派的幾代傳人皆曾有注莊之作(13)楊文娟:“《道光福建通志·經籍志》、《光緒莆田縣志·藝文志》著録有林光朝《莊子解》,不知卷數。《康熙福建通志·人物志》、《乾隆福建續志·道學志》著録有林亦之《莊子解》,不知卷數。何喬遠《閩書》卷一二六謂陳藻有《莊子解》,《乾隆福清縣志·藝文志》、《道光福建通志·經籍志》著録有陳藻《莊子解》五卷。這幾位艾軒學者素有只重口述不重著書的習慣,以上著述當是後來整理成文的。可惜他們的注本皆佚,只能從林希逸《莊子口義》的間或引用中窺見一鱗半爪。”見氏著《宋代福建莊學研究》,第131頁。,可惜注本皆佚,只能從《口義》的引用中窺見一二。
黄紅兵論吕惠卿的莊子學,認爲王安石學派主要特徵雖在調合儒道,但在調合方式上,吕惠卿更重視以心來調和,故判定爲以心注莊,對明代崇尚心靈自由的莊學派别的出現及心學的發展或許有所啓迪。其文區分了王雱(14)王雱專論可參閲簡光明《王雱“南華真經新傳”析論》,《中國文化月刊》第228期(1999年3月),第25—50頁。沈明謙《王雱〈南華真經新傳〉思想體系詮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7年。陳柏洋《王雱〈南華真經新傳〉研究》,東華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4年。和吕惠卿注莊的不同:
王雱是以理學思想(後面説到)注莊,吕氏是以心注莊;王雱把孔子改造成亦儒亦道之人,而孔子在吕氏眼中更似道家之徒;王雱以理學及辯證思想注莊,其莊學理論顯得縝密而稍繁瑣,吕氏以心注莊,其莊學理論顯得有點粗糙而稍簡潔。像王安石學派中陳祥道和林疑獨,陳氏亦未區分仁義與仁義之迹,對仁義否定較多,其莊學似接近于吕惠卿,不過其莊學基本上没有像吕氏那樣以心注莊。林疑獨以理學注莊,其莊學思想貼近雱些。(15)黄紅兵《吕惠卿的莊學思想及其注莊特色》,《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第107頁。
在以上的比較討論中,作者還加入了王安石學派的另兩位成員陳祥道和林疑獨作爲比較對象,在作者的比較中,林疑獨與王雱較相近,陳祥道與吕惠卿有異有同,吕惠卿與其他三位成員在注莊上有較大的差異,便是吕氏以心注莊,這不免令人聯想到與後來心學的關係,作者文中也表達了吕惠卿以心注莊對晚明心學的影響。但作者又表示:“……吕氏以心注《莊》,不能理解爲以心學注《莊》。因爲心學還是屬於理學範疇。”(16)同上,第108頁。筆者同意陸王之心學與程朱之理學同屬理學範疇,但以心注莊與以心學注莊的具體差異和判斷方式在這篇論文中没有説明,僅能從作者論述中推敲一二,如:“……而吕氏的‘心造’之説就是十足的唯心主義了。這或許對王守仁亦有啓發。明代王守仁的‘心外無物’與孟子的萬物皆備于我及吕氏的‘心造’之説,可以説是一脈相承。這都是對人心的張揚。”(17)同上。吕氏之説是否對王陽明有所啓發,恐怕還當看王陽明有無透露其學曾涉獵吕惠卿之學,作更全盤地考量,至於“心外無物”、“萬物皆備于我”和吕氏的“心造”的關聯,可能需要更詳密的論證。本文在此層面着墨不多,甚爲可惜。不過作者此文至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路,即明代心學的莊子學或許有上溯至宋代莊子學的可能。
另一篇關於吕惠卿莊子學的研究從哲學性的詮解展開,在林明照《無我而無物非我: 吕惠卿〈莊子義〉中的無我論》一文中可見其關注的層面:
吕氏關注從莊學中領略一種既能“反乎本宗而入乎神天”、“變化而不測”(《進莊子義表》)的天道、性情之源;同時又能依此本源“方其建立而未嘗無物也,雖事法形名,猶皆存之”創制軌則與興化立業的恒常之道。凡此,乃是吕氏詮《莊》時較具創造性的詮釋觀點,也是其對於時代課題及個人政治實踐的哲學性詮解。(18)林明照《無我而無物非我: 吕惠卿〈莊子義〉中的無我論》,《中國學術年刊》第35期(2013年9月),第29頁。
如上文所言,吕氏莊學的最終關懷在於變化不測的天道、性情之源,具有本源性的創化之道,同時也是吕惠卿個人政治實踐的哲學詮釋。宋元豐七年,吕惠卿進陳宋神宗的奏章《進莊子義表》所述“非若世儒之玩其文而已”(19)吕惠卿撰、湯君集校《莊子義集校》,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頁。一段已透露其所欲參透的天道關懷。對吕惠卿而言,《莊子》並非僅是案牘勞形之後的消遣賞玩之文,而具有對於時代與個人政治實踐的現實意義。
在北宋莊子學的發展中,已出現辨僞、翻案之説,王安石學派的莊子學呈現了政治思想如何與莊學結合與運用,以及調合儒道的思維之出現,是莊子儒學化運用在政治層面的初步成形。在對晚明及當代研究者的影響中,蘇軾看待莊子與儒家關係的論點,儘管被視爲文人筆墨,不能太過當真,但在後世,無論是晚明,或是當代研究中,普遍能接受蘇軾的觀點,並視其辨僞是一種宋人學術的精神。反觀王安石學派在後世的影響不彰,或許是在變法失敗以後,自北宋末年以來,其學受到其執政失利的牽累,難以獲得肯定,加上理學家普遍對王安石缺乏好感,我們不能期待在理學壟斷學術發言權的情況下,可以還原他們治學的本來面貌。但若撇開這個因素,單純地就此派在莊學發展上的貢獻來看,他們可能是最早視《莊子》爲天道性命之學的儒者,也是最早對《莊子》進行全面注疏的一個儒學學派,也是最早將莊子應帝王的政治哲學進陳於帝王的儒者。但他們的注疏較少受到關注,在後世的迴響相當有限(20)儘管明代孫應鰲《南華真經新傳孫序》一文頗能支持王雱,但宋代湯漢《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早已出現批評,稱:“……況雱、惠卿流,毒蟄滿懷,而可與於帝之懸解乎!”,從諸家紛紛自尋出路,以探索一條具有時代意義與個人切身相關的莊子學詮釋而言,或許這是“以儒解莊”詮釋策略中一次意外的失敗;但是從莊子學在近代以後不斷與各種儒學進行對話的可詮釋邊界而言,宋人對莊子的嘗試發言,展現了力求改變的企圖。
三、 南宋莊子學: 朱子學派與艾軒學派(一) 朱子學派: 以邵雍、朱熹和吴澄爲代表
朱子學派可上溯至北宋的周、張、二程、邵雍等,本段所要介紹的是朱子學派中對莊子的重要論述,在此以邵雍、朱熹、吴澄(21)吴澄爲宋末元初朱子學者,目前的吴澄研究未見與其相關之莊子學專論。吴澄著有《莊子内篇訂正》,另有《老莊二子叙録》《逍遥遊説》《莊子正義叙》三篇文章收録於《吴文正公集》。其他金、元兩代莊子文獻詳見於李瑞振《金元莊學文獻考》,《圖書館學刊》,2011年第1期,第117—119頁。爲代表。許志信認爲邵雍的觀物思想自莊子發揮出來,而與儒學思想融會:
莊子夢蝶,必須兩忘,才能知宇宙之真相。莊子之知物迥異於人之常識,認爲“忘”才能觀物知物。邵雍可以説將莊子的這種思想發揮到了極致,又配合着儒家的思想融會成一種新的觀物思想。(22)許志信《邵雍的觀物思想》,《東吴中文學報》,2009年第17期,第111頁。
以上引文認爲邵雍觀物思想是取資於莊子的物我兩忘,因忘而能觀物、知物,對於莊子物論的闡發也是莊子思想史發展上的前端。本段揭示了邵雍在物論上與莊子的接軌,此已不僅是對莊子有好感的雅好層面,實是通過莊子,更好地闡發儒學新的一面。許志信認爲邵雍思想中的莊子元素應做這樣的理解:
邵雍的思想突顯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也就是他的思想有很多的莊子思想烙印,這個思想烙印,説明了理學家一直存在的莊子因素,這在後來林希逸註解莊子突顯的極爲明顯。(23)同上,第131頁。
從以上的評斷中透露出重要的訊息,邵雍思想中具有很多莊子思想的烙印並不會被視爲是思想的歧出。實則如崔大華所指出的張載宇宙圖景中表述的“氣”所涵蓋的“太虚”“太和”,實際上也是最早出現在《莊子》中(24)崔大華《莊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0頁。。儘管不能否認理學家確實有對莊子的批評,但“理學的理論矛頭一直都不是主要指向莊子或道家,而是指向釋氏和當世的功利之學。”(25)同上,第474頁。崔大華的論述頗能反映維護莊學與理學關係的立場與既存的事實。許志信所稱理學家的莊子學,此命題的得以成立與否,這段評斷的最末一句,似乎將希望寄托在後來有著作注解《莊子》的林希逸身上。
一般以爲朱熹判教意識較强,對於莊子的接受度不高,在王志楣《朱熹理學與莊學》(26)王志楣《朱熹理學與莊學》,《輔仁國文學報》,2010年第31期,第79—94頁。一文的爬梳整理與論述中,已打破了這個慣性印象。本文肯定朱熹對莊子較老子爲友善,在《朱子文集》中對莊子較多批評,但在《朱子語録》則對莊子肯定較多,而對老子則批評依舊。另理學之“理”得名自莊子,主要探討朱熹理學與莊學交涉的關係及比較,重點放在“理”和“理一分殊”兩項。不僅在外緣背景上,朱熹與道家淵源頗深,其理學内容亦可與莊子之天理等一一對照,作者證明了其學不脱離莊學框架地嫁接儒學,分析二者異同,最後綜合討論朱熹借用莊子的優缺點。全文主要引用孔令宏《宋代理學與道家道教》和馮達文《程朱理學與老學》的觀點作爲論述的參考。
耿紀平《略論宋代莊學的“儒學化”傾向》一文除了就王安石、蘇軾兩個北宋文人集團和周、張、二程、邵雍乃至朱子對莊子的評論内容作出一些簡要的介紹之外,對朱子心態的描摹較具特色:
他經常思考如何對《莊子》作出獨特的、有利於充實和提高儒學教義的理解和運用。因此他在回答弟子所問能否閲讀《莊》《老》等書時,就給以“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的肯定性答復;但同時他又堅守理學立場,提醒學生警惕“恐爲所漂蕩而無以自立”的後果。表面看來,似乎朱熹在究竟如何對待《莊子》上也有些進退失據,實際上他對儒學與莊學、正統與異端的分合之界是掌握得極有分寸的。看他在失意以後曾以注釋《楚辭》寄托憂憤,卻根本不打算真正兑現他以自負口吻許諾過的《莊子》的解注一事,就已經很能説明問題。(27)耿紀平《略論宋代莊學的“儒學化”傾向》,《中州學刊》,2000年第6期(總第120期),第48頁。
耿氏一文恰如其分地描摹了朱子面對莊子的矛盾與曖昧心態,卻又在正統與異端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的關鍵處拿捏得當。朱熹回答其弟子是否可讀老、莊之書一段的問答可以在《朱子語録》中找到完整的對話,可謂信而有徵。但這段文字能説明出的問題實則仍然有限,筆者依循此文脈絡,所要繼續追問的問題是,既然理學與莊子學實在關係甚深,儒學與莊子學的近世發展,與伴隨着三教合一思潮的開展,已經從宋代開始,中國朱子學並不欠缺容納多元思維文化的雅量,但是在中國朱子學的發展上,在朱熹及其後學的論述中,爲何幾乎不見對《莊子》的注疏和研究,中國朱子學爲何始終没有發展出有如日本朱子學般的《莊子》注疏研究。
(二) 艾軒學派的《莊子》注疏: 以林希逸爲代表
前文已述及艾軒學派的《莊子》注疏留存至今的僅有林希逸的《莊子口義》,最早對此注的研究爲簡光明《林希逸莊子口義研究》(28)簡光明《林希逸莊子口義研究》,逢甲大學中文碩士論文,1991年。,本文歸納出四個《口義》的特色: 其一,注解淺顯暢達,明白易懂;其二,論《莊子》的文字血脈;其三,以禪宗解莊,尤其是大慧禪學;其四,以《四書》解莊。爲林希逸的莊子學樣貌勾勒出一個大致的輪廓。
近年學界對林希逸的關注日漸增多,在此列舉幾個較具特色的著作進行論述。如邱敏捷《林希逸〈莊子口義〉“以禪解莊”析論》(29)邱敏捷《林希逸〈莊子口義〉“以禪解莊”析論》,《玄奘佛學研究》,2006年第4期,第1—34頁。一文,以林希逸“以禪解莊”的進路爲唐代以來“莊禪合流”趨勢下的一種詮釋,莊禪有相近的義理結構,因此“以禪解莊”實爲這種思想文化演進的一種展現,並認爲《莊子口義》也體現着中國傳統文人取資老莊玄學以觀察禪宗思想的現象。
不過筆者以爲,林希逸所處的南宋,已經距離玄學發展的中古時代太遠,唐代的禪宗與宋代的禪宗如有不同風貌之開展應屬常理,林希逸所接觸到的禪宗,應該是與其同時代的大慧禪(30)荒木見悟和池田知久的研究均指出,大慧宗杲的禪宗是林希逸追求不已的理想。分别見於荒木見悟《林希逸の立場》,《中國哲學論集》1981年第7期,第54頁。池田知久著,王啓發、曹峰譯《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莊子〉爲中心(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07、708頁。,何以見得必是屬於中古時期的禪宗呢?除非作者有至少一個很有力的證據徵引,以證明林希逸接觸到的禪宗來自中古時期,否則在立論上很難説服。
另有楊黛《〈莊子口義〉的理學觀》一文肯定林希逸注莊的理學觀與程朱以醇儒自居的不同:
程朱理學者堅持“道統論”,以醇儒自詡,因而他們在思想交鋒中竭力鼓吹、抬高自家的學説,不但不承認吸收過佛學的營養,還以辟佛爲標榜,排斥貶低異己理論。……林希逸發揚光大艾軒學派的學説,痛快淋漓地承認融儒、道、佛爲一體,就某種角度來講,是遠比程朱羞羞答答、否認引禪入儒的事實來得高明的。(31)楊黛《〈莊子口義〉的理學觀》,《浙江學刊》,1989年第3期(總第56期),第79頁。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理學實則吸收了佛教與道家思想,相較於艾軒學派光明正大地吸收《莊子》、注解《莊子》,且安然地表示“佛書最好證吾(儒)書”,朱子學派則對於融三教爲一體的學説,一直是暗中使用而不予明言。不過本文也認爲林希逸曲解了《莊子》,也違背了理學(32)同上,第81頁。。相似的論述實則在整理宋代莊子學研究成果中相當常見,一方面研究者居於肯定其研究對象的立場,發掘其人其學於時代的特色或對後世的影響,畢竟宋代是一個理學的時代,我們也不需要否認儒學對莊子學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滲透,不過宋代儒學也不是先秦儒學的複製,許多的儒家經典已歷經多元詮釋的嘗試,且在漫長的思想史發展過程中,不同家派的思想整合或互相豐富,本屬常態。與其就横的向度探究其人其學的特色,不如就縱的向度看待其自身的發展,如作者點出《口義》對明清注疏家的影響,如“明孫應鰲《莊子要删》、釋德清《莊子内篇注》、清胡文蔚《莊子吹影補注》、宣穎《南華經解》都推崇林希逸,並有所繼承發揚”(33)同上,第78頁。。孫應鰲爲陽明後學,是王陽明在黔中時的學生,他也曾爲王雱之注作序,其人其學至今極少受到關注,憨山德清爲晚明高僧,胡文蔚與宣穎爲清初《莊子》注疏者。相較於王雩,林希逸受到明清注疏家較多的接受。
關於明清注本受到口義本影響的發言還有李見勇、王勇的《三教合一 歸終理學——論林希逸〈莊子口義〉的思想傾向》一文,此文也表示:
在《口義》一書中,身爲理學家的林希逸,受三教合一思潮的影響,用佛、道、儒三家來解釋《莊子》,但其最終歸依仍然是理學,這種思想傾向對於明清《莊子》研究也有着較大的影響。(34)李見勇、王勇《三教合一 歸終理學——論林希逸〈莊子口義〉的思想傾向》,《内江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第78頁。
如上文所述,一般認爲林希逸的理學、莊子學及三教合一思潮呈現正相關性,這種發展傾向是三教歸於理學,且對明清莊子研究有較大的影響。但本文没有説明這較大的影響應該從哪些具體的層面談起,如要論就具體的影響層面,仍待日後更深入地研究和探索。
關於林希逸莊子學的研究,更多來自日本莊子學研究的訊息,連清吉、王迪、池田知久、荒木見悟均就不同層面進行各自細部的考察。連清吉所著的《日本江户後期以來的莊子研究》(35)連清吉《日本江户後期以來的莊子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版。是中文著作中最早提及林希逸口義本在日本流傳情況的。本書以江户後期(1716—1886)的日本莊子研究爲討論對象,作者以中井履軒《莊子雕題》、龜井昭陽《莊子瑣説》、帆足萬里《莊子解》、岡松甕谷《莊子考》爲主要探討對象。書中述及林希逸口義本在江户前期(約17世紀中葉)相當盛行,但主要探討的四家《莊子》注疏屬於江户後期(約18世紀中葉)的著作。本書簡短地説明了由於幕府時代以朱子學爲官學,隨着宋學大行的趨勢,《莊子》以宋代林希逸的《莊子鬳齋口義》爲依據,在荻生徂徠的古文辭學興起後,其門下在反對朱子學的旗號下,主張捨棄林希逸的《口義》,改以郭象注來理解《莊子》(36)同上,第219、220頁。。在日本,口義本的盛行與否和朱子學的地位息息相關,二者具有高度的連帶關係,根據目前已知的文獻,這樣的情況在中國從未發生。簡言之,中國朱子學的發展與莊子學在近代的開展之間幾乎没有正向發展關係。
據連清吉的蒐羅整理和楊文娟其書的簡介,可知日本朱子學派成員自其始祖林羅山開始,即不乏《莊子》注疏,其中以小野壹的《莊子鬳齋口義棧航》最能代表此派的注莊風格。王迪《日本老莊學之研究》(37)王迪《日本老莊學之研究》,《龍陽學術研究集刊》,2007年第1期,第7—31頁。一文對此注有諸多介紹,據其所述,有以下幾個相關重要訊息: 其一,卜幽軒(38)王迪著作中作“卜幽軒”,池田知久作“人見壹”,連清吉其書與嚴靈峰收録之延寶八年刊本作“小野壹”。的《莊子鬳齋口義棧航》刻印版本原有多部,但現存於各圖書館與文庫的僅有延寶九年(1681)的版本。其二,卜幽軒編著的《莊子鬳齋口義棧航》,可説是完成了其師林羅山之未完的口義鼇頭本。而林羅山曾經師事五山禪僧英甫雄習《莊子鬳齋口義》,所以亦可認爲卜幽軒的老莊研究是繼承了室町時代五山禪僧之系統。其三,雖然老莊思想是由中國傳入,但從中世開始,就與中國有不同的研究狀況。這種現象與其説是受“三教一致論”之影響,不如説是禪僧們爲了習禪,將禪普及於中世社會,除了學習儒書以外,也必須有《老》、《莊》、《列》三書之素養。
王迪於另一篇論文中,表示:“《宋元學案》林希逸傳裏完全未提及口義本。又《四庫全書》僅收《莊子口義》,而《老子口義》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都未予著録,由此可證口義本在中國未曾被重視過。”(39)王迪《從書誌考察日本的老莊研究狀況——以鎌倉、室町時代爲主》,《漢學研究》,2000年第1期,第 14頁。王迪斷言口義本在中國並没有像在日本一樣受到廣大的歡迎,但以上所述《四庫全書》的收録狀況,應是指清代官方對口義本不太重視,據筆者所見的晚明諸家注疏内容,實則中國的情況較爲複雜,不是受不受重視一語所能概括。日本江户前期(約17世紀中葉),林希逸口義本取代了郭象注本,而在江户後期(約18世紀中葉),徂徠學興起,再度由郭象取代林希逸,在日本,郭象與林希逸不曾並存而同時流行,是一家取代一家的情況,較爲單純。相較於日本,中國晚明的接受狀況則複雜許多,如焦竑版本,既引用郭象注,又收録口義本,像焦竑這樣通用的情況實屬常見,筆者目前雖不能斷言晚明的實際狀況爲何,因爲這需要做進一步地釐清和考察,但口義本對於中國晚明以至清初諸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是肯定的事實。因此,筆者並不那麽悲觀地認爲口義本在中國不受重視,只能説口義本在中國晚明未曾出現過獨尊的情況,不過口義本在宋明莊子注疏史上足以作爲郭象注的反對派。王迪徵引《宋元學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表達口義本不受重視的一段叙述,可以確定的是: 帶有道統意識的立場與四庫館臣對宋明理學的成見,在此雙重的夾殺中,勢必無法給予林希逸在中國明清思想史中一個應有的歷史地位。
但至少王迪對照了口義本在中、日兩國的不同際遇,並推論了口義本在日本最早期的流傳狀況:
口義本在中國不曾被重視過,而在日本的中世不但被禪林所援用,就連當時的博士家清原宣賢的講義《莊子抄》、《老子經抄》裏也多處引用口義注,這足可證明口義本早在日本的中世就已受日人的歡迎了。兩口義本傳入日本的正確年代現在無從考證。但由上述可推斷《莊子口義》在南北朝期間,也就是至遲在西元1392年就已爲日人所知。(40)王迪《從書誌考察日本的老莊研究狀況——以鎌倉、室町時代爲主》,第21頁。
1392年爲明代洪武二十五年,一個中國莊子學十分沉寂的時代,明代《莊子》注疏在嘉靖年間才開始興盛,屬於明代的莊子學這才開始發展起來,開始回顧和整理前朝注本。然而,早在日本中世,口義本已經受到重視和歡迎。
關於此點,池田知久自問了一個問題,即是江户時代以後,爲何人們重視口義?他也自答了兩個原因,其一爲林羅山的推重,其二爲林希逸後裔即非如一在1658年留居日本,並攜帶了家傳本《老子口義》赴日並爲校定刊行。但池田知久又認爲:“……上述兩個理由不免流於表面和偶然……這是個很難解答的問題,日本似乎還没有研究這個問題的人。”(41)池田知久《林希逸莊子鬳齋口義在日本》,第525頁。筆者也同意現有的各種對口義本在日本流行的原因,在解釋上大多流於表面與偶然,儘管這些原因可以構成一些蛛絲馬迹般的線索,但在理論的部分,仍欠缺有力的論證,所以根本的原因我們仍是未知。回過頭來,從日本思考中國,池田知久在另一本書中依據林同所撰寫的《莊子鬳齋口義序》認爲:“林希逸的思想立場,也還是儒教,屬於廣義的理學。根據荒木見悟教授所説,在這個學問系統中,没有程伊川和朱子的‘理’的理論所具有的拘束性和嚴肅主義。”(42)池田知久著,王啓發、曹峰譯《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莊子〉爲中心(下)》,第702頁。林希逸莊子學並不是理學的歧出,而是儒學的擴大,是有别於程朱學派,且有其學脈上的依據,可謂理學的自成一格,相近的論述在荒木見悟的論文中有詳細的論證(43)荒木見悟《林希逸の立場》,《中國哲學論集》,1981年第7期,第48—61頁。。可惜的是,林希逸口義本在明清中國的具體影響,我們仍是一知半解,更遑論還原其應有的理學地位,是謂現今道統意識之儒學籠罩下的不可見。
在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見朱子對待莊子的曖昧心態與朱子學派暗用莊子卻不能明言的情況,我們可以肯定朱子學派對待莊子並無歹意,如邵雍獲益於莊子良多,而理學之理、太極、太虚等宇宙圖景均與莊子高度相關,但在“以儒解莊”策略運作的實際支持上,其實欠缺誠意。據方志記載,艾軒學派可説全數撰寫了《莊子》注疏,但遺憾的是僅林希逸口義留存,於是在以儒解莊的隊伍中,存在着殘缺。17世紀中葉日本朱子學的興盛,使得口義本一度取代郭象注本,這一現象可以説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意外收獲。
結 語
本文透過宋代莊子學總論的介紹和以學派爲分論的各家解莊,以淺顯易懂的方式,歸納出宋代以儒解莊的發展脈絡。整體而言,宋人對《莊子》多有新説,且已有意識地希望脱離郭象注的魏晉傳統,也對於史遷的定論進行翻案,在此層面體現了宋代學術中的批判懷疑精神,最重要的是宋人解莊新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晚明莊子學的發展。從口義本的三教内容呈現來看,宋代實際上是晚明的雛型,對晚明注家而言,林希逸更是一個具有開創意義的先知,林希逸口義本對17世紀中葉的中國莊子學和日本莊子學的影響,及與日本朱子學、中國陽明學之間的關係,實是有待研究的課題。
宋代莊子學的研究相較於魏晉或晚明更晚,至今研究成果在數量上也較少,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落差,一個可能的因素爲文獻保存不易,許多著作亡佚,實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另一個可能的因素是學界對宋代思想的研究,太過傾向於儒學,尤其是道統化的理學,這種追求一致性的學術傾向勢必扼殺了多元詮釋的機會與可能,形成了偏於此見而忽視彼見的不可見。
朱子學的三教特色與《莊子口義》的結合,並没有在中國開花結果一事,從中國自身的角度來看,可以追究於中國朱子學背負着道統意識,且有醇儒的自我要求,或許更能從兩國朱子學的開山始祖朱熹與林羅山兩人思想的一致性與差異性(44)可參閲龔穎《“似而非”的日本朱子學: 林羅山思想研究》,學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215頁。中窺見終將殊途而不同歸的結果。但從朱熹歷任祠官的經歷(45)關於朱熹歷任祠官的宗教經驗可見於孟淑慧《朱熹及其門人的教化理念與實踐》,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3年版。,與對佛老的理解、對莊子的吸收,及近年學界對張載、邵雍理學與莊子的關係來看,完全否定中國朱子學的三教色彩似乎不是誠實的話。而事實上,儒學的三教特色與《莊子口義》的結合,在中國反倒是發生在與陽明學淵源甚深的陽明後學身上,至少是較爲傾向及認同陽明學的士人身上。結果,中國陽明學反倒與日本朱子學在三教的立場與口義本的接受上更爲相近。
綜上所述,筆者從對宋代莊子學的研究回顧,反思以儒解莊在效用上的實質邊界,並不是因爲宋代是理學的時代,所以解莊以儒無可厚非,而是因爲從莊子詮釋史的角度來看,可以得見這樣的儒學内容並不單純,其中亦應具有三教的特質,因此説宋代莊子學其實是晚明莊子學的前哨站,思想史的複雜氛圍早已肇端於此。從以儒解莊作爲一種詮釋策略的觀點來説,儒學足堪作爲莊子學吸收三教而發生裂變的平台,這樣的莊子學不是被局限在儒學的框架中,它時常超出這個既有的框架,並不排斥與佛、道保持平行發展,相互援引的關係。最後以儒解莊充其量不過是一種策略的運用,因爲儒學自身也隨時在變化之中,三教融合並非走向同一,透過建構其自身内涵,與時代俱進,也解構了詮解自身的既定限制,並且繼續在下一個時代參與所將開創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