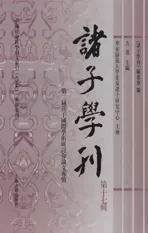宋元時期莊子齊物思想批判析論
2018-01-23劉濤
劉 濤
内容提要 宋元時期,理學家以孟子“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之語爲準批判莊子的齊物思想。但他們對莊子齊物思想實存在極大誤解,認爲莊子乃强齊萬物,並以理學理一分殊思想對其加以解析。實際莊子齊物思想與孟子物情不齊思想本質相通,莊子欲以不齊齊之,任萬物之不齊,只是表述與孟子恰好相反,遂致誤解。齊物思想表現了儒道二家寬容萬物之廣闊胸懷。另外,劉因從胡蝶夢寓言聚焦於夢的虚幻性,證明莊子齊物之推論過程不成立。但這並未抓住物化的真精神,即對生死的齊同。從人的本性看,莊子齊生死對人提出了過高要求。
[關鍵詞] 莊子 齊物論 孟子 思想批判 理學 夢
一、 齊物與齊論
對於《齊物論》題意的理解,大致可以兩宋爲界,宋以前多以“齊物”連讀,爲齊萬物之意,入宋以後,漸有以“物論”連讀者,認爲莊子所欲齊同者端在“物論”。章太炎説“物論”連讀始於王安石、吕惠卿(1)章太炎《齊物論釋》云:“‘齊物’屬讀,舊訓皆同。王安石、吕惠卿始以‘物論’屬讀。”,但不知其依據爲何。見聞所及,較早將“物論”連讀的是張耒,其《劉壯輿是是堂歌并序》有云:“昔楚人有莊周者,多言而善辯,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托之於天籟。其言曰: 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2)張耒《劉壯輿是是堂歌并序》,《柯山集》卷三,《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30頁。南宋林希逸不僅將物論連讀,解釋爲關於人物之衆論,而且聯繫莊子生存的時代背景,將物論坐實爲戰國時期諸子之間的互相争鳴,可謂卓見,其言曰:“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衆論也。齊者一也,欲合衆論而爲一也。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非,故莊子以爲不若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此其立名之意也。”(3)林希逸《莊子鬳齋口義》卷一,方勇編纂《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20册,影印南宋刻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版,第534—535頁。而劉辰翁則針鋒相對,他也將“物論”連讀,卻認爲物論泛指普遍的是非,而非專指諸子間的不同觀點:“或謂莊子欲齊物論,非也。欲齊則愈不齊矣,不是齊他物論,是自看得他物論原自齊,看得齊則心平,心平則無物論矣。物論謂指戰國時學問,亦非也。天地間自有人我即有是非,從堯舜事業、六經議論、戰争、興廢、出處、成敗、死生,皆是非也。”(4)劉辰翁《莊子南華真經點校》,方勇編纂《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28册,第42頁。
王應麟在《困學紀聞》討論諸子時則明確以“齊物”連讀爲非,以“物論”連讀爲是,他説: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毁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詩謂“齊物到頭争”,恐誤。(5)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翁元圻等注,欒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 1241頁。
邵雍詩將“齊物”連讀,這恰好給王應麟提供了反面例證。清人錢大昕則從歷史的角度追溯這種錯誤理解的源頭,他在《十駕齋養新録》中云:
按左思《魏都賦》“萬物可齊於一朝”,劉淵林注云:“《莊子》有《齊物》之論。”劉琨《答盧諶書》云:“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文心雕龍·論説》篇云:“莊周《齊物》,以論爲名。”是六朝人已誤以“齊物”兩字連讀。唐人多取“齊物”兩字爲名,其誤不始康節也。(6)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卷十九,楊勇軍整理,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381—382頁。
錢大昕通過歷史考察,指出“齊物”連讀始自六朝,盛於李唐,此誠不刊之論。不過,他上溯至左思《魏都賦》,卻非最早,至少嵇康在《琴賦》和《卜疑》二文中已經將“齊物”連讀了(7)嵇康《琴賦》云:“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卜疑》云:“寧如老聃之清净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夏侯湛《莊周贊》亦將“齊物”連讀:“邁邁莊周,騰世獨遊。遁時放言,齊物絶尤。”(8)夏侯湛《莊周贊》,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六十九,中華書局1958年影印版,第1857頁。其年代應與左思《魏都賦》相當。其後直到兩宋,涉及《齊物論》的詩文絶大部分都是如此連讀(9)方勇《莊子纂要》第七册《附録: 莊子詩文序跋匯輯(上)》,學苑出版社2011年版。,對莊子齊物論思想的理解相應地就是齊萬物。
二、 形 與 理
魏晉南北朝玄風大暢,竹林時期以後,玄學即以《莊子》爲中心了;唐代雖則推行三教並行政策,然而皇室奉老子爲祖,尊道家道教優先於儒佛,莊子因之被追尊爲南華真人,《莊子》其書也被奉爲《南華真經》,所以從魏晉到唐代,《莊子》一書地位都比較高,人們對於齊萬物的思想多持欣羡仰慕態度,基本未見有批評的,即使疾呼廢莊的王坦之,在《廢莊論》篇末仍然認同莊子的齊物思想(10)《廢莊論》云:“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時至兩宋,道學革新。宋朝士人面對時弊,頗具大膽的懷疑精神和强烈的變革願望,他們融通三教,卻以注重功利實效的儒學爲主,同時爲了强調儒學的純粹和正統,又激烈地排斥佛道,視之爲異端,不遺餘力地進行攻擊。對於莊子的齊物思想,自然也出現了很多批評的聲音。
邵雍《擊壤集》卷三《放言》詩云:“既得希夷樂,曾無寵辱驚。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争。”(11)邵雍《伊川擊壤集》卷三,《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成化乙未(1475)畢亨刊本。意謂進入與道合一的境界之後,變得寵辱不驚,既無對事物的汲汲追求,也無對是非的呶呶争辯,此時去看佛家孜孜追求於空,覺得終是拘泥也不免執著,而莊子倡言齊物,也仍然擺脱不了争論。在其《皇極經世書》中,上述詩理化的表達則轉化爲更具體直白的批評:“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争,争則不平,不平則不和。”對此,明代黄畿注云:“《齊物論》齊物之不齊,彼此較量,未免物與物争,殊失平坦和渾之致。孟子謂:‘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矯情求齊,孟大莊小。”(12)邵雍《皇極經世緒言》卷八下,黄畿注釋,清光緒三十二(1906)年二仙菴刻本。他們認爲莊子齊物的本質是争,争則有失平和,境界較低。
先秦時期,齊物思想並非莊子首創,亦非莊子獨有,在他之前,儒家的孟子,道家的慎到、彭蒙、田駢,墨家的墨子,名家的惠施等,均對齊物思想有所探討,但只有莊子集其大成,超拔衆家,擺落衆家的私心,克服諸子的缺點,成爲齊物思想的代表(13)葉蓓卿《先秦諸子“齊物論”思想比較》,《諸子學刊》第十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中晚唐以來,《孟子》愈加受到儒者的重視,地位不斷提高,其齊物思想也得到關注,甚至作爲標準。此處邵雍並未明言其以孟子爲凖,但黄畿之注卻將之揭示出來,渾然不覺有欠妥處,可見邵雍確據孟子爲言。單就字面看來,孟子云物之不齊乃物之實情,這是人們觸目即可驗證的真理,莊子之齊物,卻似乎包含了强不齊以爲齊的意味,這不正是黄畿所説的“矯情”嗎?首先,萬物自在生長於天地之間,各隨其本性擁有自己獨特的面貌,人必須在萬物之間進行一番比較、較量才能發現萬物之不齊,或大或小,或長或短,這就體現出人心之中具有一種争勝念頭,此念一起,心中本來的平静熙和之氣就被破壞了。邵雍所言僅止於此,其實,强制齊物真正的害處更在於用統一的標準衡量裁割萬物,是對萬物本性的漠視,更是對萬物生命的殘酷宰制。相比之下,孟子所言反倒更像是道家的順其自然,任其不齊了。這種看法明顯違背對儒道的一般認識,但在宋代卻並不罕見。
二程也認爲莊子的齊物是不合天理的:
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虧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强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14)《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程顥、程頤《二程集》,王孝魚點校,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2—33頁。
這裏二程不僅明引孟子關於齊物之言,還爲孟子的觀點找到了堅實的根據,創造孕育萬物的天地陰陽二氣就是不齊而變化無常的,根源不齊,作爲末和流的萬物自然也就具有不齊的特徵了,這是從根本上就無法改變的。因而莊子强要齊物,也終究是白費功夫。
二程還從物形與物理兩方面分析了莊子齊物的謬誤: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别去甚處下腳手?不過得推一個理一也。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15)《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九,程顥、程頤《二程集》,第264頁。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16)《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上,程顥、程頤《二程集》,第289頁。
崔大華曾指出,二程係以理學“理一分殊”的觀念批判莊子的齊物思想(17)崔大華《莊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3頁。。從物形方面看,正如孟子所説,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無法可齊;從物理方面看,萬物皆是一理,本來就是齊一,不須去齊。無論從物形還是物理哪個層面,齊物都是没有道理的,也無法進行,而莊子卻要齊物,在二程看來,這説明莊子對大道的領悟及對萬物的認識還很淺薄。
二程對莊子意欲齊物不以爲然,對莊子的齊物方法更是嗤之以鼻。《齊物論》開頭便描寫了南郭子綦達到了齊物我的境界,“隱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喪其耦”(18)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2004年第2版,第48頁。本文所引《莊子》均出自此本,以下僅標明篇目,不再出注。,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對此,二程評論道:
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19)《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程顥、程頤《二程集》,第26頁。
二程修養極高,言語柔和,這裏卻近乎斥責。二程以爲,天理流行,活潑潑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20)《河南程氏遺書》卷五,程顥、程頤《二程集》,第76頁。。莊子的槁木死灰,是忘形骸,黜聰明,防止形體與内心的妄動,這正與二程的主張完全相反,因而遭到二程的嚴厲指責。我們還可以從動静這對理學的重要範疇來理解二程對莊子的批評。與動相比,莊子更注重静,《天道》篇云:“聖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虚静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虚静是天地的準則和道德的極致,也是人的本真狀態,只有在虚静的狀態下,人才能如鏡子一樣照鑒天地萬物,使天地萬物自動呈現其本來面目,散發其獨特的個性光輝,而没有人的主觀視角的摻雜;同時,面對紛擾,人能如鏡子一般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内心就不會受到擾動。虚静也是養生、長生所需保持的狀態:“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無勞女形,無摇女精,乃可以長生。”(《在宥》)相較而言,二程則更注重動:“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焉!”(21)《周易程氏傳·復卦》,程顥、程頤《二程集》,第819頁。陳來解釋説:“這裏的天地之心指主宰天地的根本原則,照這個思想來看,動静二者之中,不是静,而是動才是更爲根本的,才體現了宇宙生生不已的根本規律。”(22)陳來《宋明理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108頁。因此,在二程看來,以槁木死灰式的虚静爲最高境界的莊子是没有把握動静的正確關係。
南宋理學家張栻也以孟子物不齊之論來談齊物,並且分爲物與理兩個層面,但與二程的思路又有不同。他在注釋《孟子》時云:
有天地則有萬物,其巨細、多寡、高下、美惡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加損於其間哉。若强欲齊之,私意横生,徒爲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强欲以理齊之,猶爲賊夫道。(23)張栻《癸巳孟子説》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9册,(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394頁。
張栻將孟子物不齊思想做了具體的闡述,其中除了巨細、多寡等物形之不齊,還包括高下、美惡等物之品質、價值方面的不齊,但他强調這種種不齊都是符合天地之理的。張栻並未强調理之一,反而謂莊子强欲以理齊物,不僅違反天理,而且是賊害天理。二程將物分爲物形、物理,以爲它們都是“齊物論”要齊同的對象,這實際是二程自己的劃分和理解,而在莊子那裏並没有物形、物理的劃分。相比之下,張栻雖然也分物和理兩層來談,但他認爲莊子只是齊物,並不要齊理,理並非莊子要齊同的對象,因爲理並非物理,而是天地之理,是物不齊這一現象和規律背後的總根據和總原則,大概和莊子的道相當。張栻的這一理解在結構上與莊子的思想更爲接近。張栻以爲,莊子以此天地之理爲齊物的手段或方法,就是强求,也是對天地之理和物之情的關係没有充分理解。而如果正確把握天地之理和物之情的關係,就會“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加損於其間”。實際上,莊子的齊物思想最終所要表達的正是如此。胡文英總結《齊物論》主旨云:“《齊物論》是言物之不能齊,不可齊,不當齊,不必齊。”(24)胡文英《莊子獨見》,方勇編纂《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107册,第106頁。齊物主要是價值上的齊同,不加人爲地分别、評價,也就没有高低貴賤,没有是非之争,讓萬物包括人類都回到各自的自然本然狀態,按照自己的本性要求生長於天地之間,逍遥於宇宙時空。這與張栻任物不齊的要求差相仿佛。而莊子確實也是以道爲用,來達到齊物的目的,但這裏的道並不是本體論意義上的萬物的根源,而是一種境界和眼光,和張栻所説的理有所不同。
除了兩宋的理學家,稍晚於二程的文學家,蘇門四學士中的黄庭堅、晁補之二人,也都引了孟子的話評論莊子的齊物思想。
黄庭堅在其《莊子内篇論》中云: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外之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爲齊物之書,涽涽以至今,悲夫。(25)黄庭堅《山谷全書·正集》卷二十,《宋集珍本叢刊》影印乾隆宋調元緝香堂本,線裝書局2004年版,第472—473頁。
此文可與其《幾復讀莊子戲贈》詩互爲參照,詩中有云:
物情本不齊,顯者桀與堯。烈風號萬竅,雜然吹籟簫。聲隨器形異,安可一律調?何嘗用吾私,總領使同條。惜哉向郭誤,斯文晚未昭。(26)黄庭堅《山谷全書·外集》卷十三,《宋集珍本叢刊》影印乾隆宋調元緝香堂本,第777頁。
黄庭堅認同孟子物不齊之論,但他認爲莊子的意思與孟子一致。他從文學的角度解讀《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一段,認爲莊子以衆竅形狀不同,所形成的風聲也不同,比喻萬物之不齊,亦不可齊,齊物只是俗人之一己私意。這個視角頗爲獨特,爲後人理解《齊物論》提供了一條可貴思路。他又將齊物的罪過推到向秀、郭象身上,認爲是向郭二人的注釋誤導了後人,以致千年以來莊子的思想無人能够正確領會。這如果不是誤解,就是黄庭堅對莊子的有意回護。
如果按照二程物形、物理的劃分,黄庭堅顯然只關注到了物形這一方面,而晁補之則與二程一致,將物理、物形分開討論。其《齊物論》云:
此篇論齊物,然物之理齊而情故。……物之情不齊而其理齊,聖人窮理,衆人役情,聖人欲反情之異,合理之同,所以圖滑疑之耀,使無疑無滑而泯乎冥冥者,莫要於此矣。……然非夫以道泛觀而備萬物之應,則以不齊齊,其齊也不齊;乃若莊周,則以齊不齊,其不齊也齊矣。(27)晁補之《雞肋集》卷二十七,《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詩瘦閣仿宋刊本。
與二程不同的是,晁補之利用物理、物形之分將莊子與孟子的齊物思想進行了調和,他認爲莊子所欲齊者也是物理,並非不齊的物情。他的理解是莊子能够“以道泛觀而備萬物之應”,這與莊子在《齊物論》中傳達的精神若合符節,可見晁補之的理解遠勝以上諸人。晁補之所批判的則是與莊子相反的“以不齊齊,其齊也不齊”之人:“故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皆爲者敗之也,皆非所明而明之也,故雖竭其智而理終不可窮,謂之堅白同異、名實之辯,若此其察矣。然要於不察而以昧終,其爲滑疑也,不甚矣乎!”(28)同上。晁補之借郭象“爲者敗之”語批評《齊物論》篇提到的師曠、惠子諸人,認爲其均欲以自己之理齊同萬物之理,而不是順從萬物遵循各自之理,因此遭到了失敗,誤入了歧途。
邵雍、二程、張栻、黄庭堅、晁補之等都以孟子的齊物思想作爲參照,來評論莊子的齊物思想,是莊子學史上的新發展,呈現了一些新特點,比如以理學的“理一分殊”思想從物理、物形兩方面看待齊物。但這種理解與評判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究竟是有助於對莊子齊物思想的理解還是會造成誤導,需要仔細檢討。
宋末褚伯秀在纂集了諸家之説後,就對此做出了評價: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子名篇以“齊物論”,或疑其與儒家悖,重增不齊之情。殊不思孟子特爲許子言之耳。況孟之所言者情,莊之所言者理,理一分殊,則情之不齊也宜矣。故南華原本究極,主一理以齊天下之物論。(29)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道藏》第1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第219頁。
褚伯秀做出解釋的動機就是調和儒道兩家,因爲字面上孟子主張物不齊,莊子主張齊物,看似相反,容易引起争論,若不解釋清楚,反增二家之不齊。因此,褚伯秀分兩點辨析: 第一,他將孟子原意發掘出來,指出孟子主張物不齊係針對許行,而非莊子,從而撇清了孟子、莊子之間的緊張關係。這一點可謂擊中了理學家們的要害,他們往往抓住經典中的片言隻語就在理論上大肆發揮,有時竟脱離原文意脈也在所不顧。褚伯秀則重新返回經典的文本去討論,比較實事求是。第二,與晁補之類似,褚伯秀從理學家認同的理一分殊的思想出發,將孟子、莊子分離開來,拆解其矛盾。褚伯秀説孟子所謂的不齊是物之情,而莊子所言的齊則是物之理,這樣,孟子、莊子所論分屬不同層次,並不構成矛盾,而莊子的齊物也符合理學家的理一的思想。只是褚伯秀所理解的“齊物論”已非早期理學家的“齊物”論而是齊“物論”了。
實際上,以今日的眼光來看孟子之語與莊子的齊物思想,二者確實不矛盾,甚至可以説還很契合(30)當然,細究起來,孟子、莊子還是有很大不同的,孟子認爲物雖不齊,但其中存在高低貴賤的次序,莊子則認爲只有自然的差别而没有高低貴賤之分。此條承劉思禾師兄惠示,在此表示感謝。。晁補之、褚伯秀也觀察到了這一點,試圖調和二者,但他們所利用的理論也同時造成了一定的限制,因爲理學上所講的理一分殊並不切合莊子思想,以此量彼,本身就已是不齊。孟子所説的物之不齊,雖然是針對許行的絶對平均主義,但也是一個普遍真實的道理,而這一道理正是莊子所承認和欲加保衛的,且也是莊子齊物思想的基礎與依據之一。孟子認爲萬物千差萬别,“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引申一步,則可以説這是由於萬物自身具有的特性、本性,因而是不可抹殺而需要予以尊重的。孟子正是要根據萬物不同的特點,交相利用,互爲輔助,才能人盡其力,通其有無,最終達到治國的功利目的。莊子雖然並無功利目的,卻看到了抹殺萬物不同特性的危害,因此,他所謂的齊物,並非如許行那樣追求絶對平均,用一種强制手段將萬事萬物統一成一種模樣,整齊劃一,而是尊重其特性,承認其價值,“因物付物,所以爲齊”(31)章太炎《齊物論釋定本》,《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頁。。《胠篋》篇云:“擢亂六律,鑠絶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絶鈎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 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瞽曠確爲天下耳力最爲聰敏之人,他可以校準樂器的六律,但以他爲最高標準,天下其他人就只能違背自己的本性和特點,去適應這一標準,這是“適人之適”、“役人之役”,只有打破這一規定,天下之人才能各自按照自己的聽力、品味去欣賞音樂。這裏强調的是“自己的”(“其”聰,“其”明,“其”巧),自己的無疑比他人的外來的更加符合自己的本性。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耳力去聽聲辨律,不與他人争高下,這就是耳力的齊了。莊子的齊正是以不齊齊之,聽其不齊,與標題的字面含義正好相反,可能這也是引起衆多誤解與批判的原因之一。而莊子齊物的最高境界就是“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這兩句常常被誤解爲莊子抹殺萬物的差異和特性,其實並不是,因爲萬物的差異和特性是客觀存在的,不容抹殺,這裏莊子只是就境界上講,即人能認識到在道的層面萬物都是相通的,以道觀之,物無貴賤,萬物平等,如此就不會有紛争與壓迫,這就是齊物。二程等批判莊子,似乎並未把握到莊子思想的真髓。
面對這吹萬不同的世界,莊子主張兼懷萬物,展現了一種博大的包容精神,這與儒家的忠恕絜矩之道有相通之處。朱敦毅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所以齊不齊以致其齊者,在因物付物,是以有絜矩之道焉。絜矩之道即忠恕之道,推己及物,其施不窮,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32)朱敦毅《莊子南華真經心印》,方勇編纂《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111册,第370頁。對於不同的個體,本來是“自彼而不見”的,莊子站在道的高度,認爲彼此相通,是非無定,因而放棄争辯,兩行兩存;而儒家則主張推己及人,也是根據彼此相通之處去爲他人考慮。只是莊子更重存異,其異其同爲兩個層次,而非在同一層次的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在異的層次中的所有個體地位平等,價值相同,皆須尊重,因而劉咸炘《莊子釋滯》云:“佛家主空,一切俱不要,道家主大,一切俱要。”(33)劉咸炘《莊子釋滯》,黄曙輝編校《劉咸炘學術論集·子學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頁。儒家對於差異,存而不論,更重求同,認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人可以以自己的心理揣度他人之心,在實踐上,消極方面就要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積極方面則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派仁者氣象。總之,道家與儒家,一爲博大,一爲仁愛,同爲包容,卻體現了兩種不同風貌。
三、 夢 與 覺
與前代讀《莊》者有所不同,元代理學家劉因則獨闢蹊徑,從另一角度展開了對莊子齊物思想的批判。《齊物論》篇以莊子的蝴蝶夢結束,在這個寓言中,夢覺不分,蝶周通化,因而可知物我齊同。劉因抓住夢字,展開分析,其在《莊周夢蝶圖序》中説:
周寓言夢爲胡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説者以爲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爲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横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己以渺焉之身,横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内,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詫夫家人時俗而爲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爲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吾之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爲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於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爲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説而趨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説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34)劉因《静修先生文集》卷十九,《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元宗文堂刊本。
夢的最大特點就是虚幻,劉因將批判的焦點聚集於此,認爲莊子將一切都視作一夢,虚幻不實,在虚幻的夢境中,自然所有事物都同爲虚幻,因而可以齊同萬物彼我。劉因認可莊子的思路,卻在根底上將它撅起: 莊子憑什麽認定這個活生生的世界是虚幻的夢境呢?他分析了莊子的現實遭遇,認爲莊子由於懷才不遇,失志於當時,内外交困,所以將此世一切視爲虚幻,自己便可在這虚幻世界中放肆妄行。可見,這個虚幻世界還有一定的因果和邏輯在,它並非真的虚幻。這確有一定見地,真正的夢恢恑憰怪,哪有什麽邏輯可言?此意范縝曾經論及:“子謂神遊蝴蝶,是真作飛蟲耶?若然者,或夢爲牛,則負人轅輈;或夢爲馬,則入人胯下。明旦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也?”(35)范縝《答曹録事難神滅論》,釋僧祐撰、李小榮校箋《弘明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88頁。只是范縝從反面説,夢無邏輯而爲虚幻,劉因從正面説,現實有邏輯而爲真實。莊子不分虚實,顛倒夢真,又怎能真正齊物?再者,世界若爲虚幻,其中就不會有真實的道存在,没有道作爲主宰,萬物就不能齊同。劉因更接近二程,也以天地萬物皆是一理的思想解釋齊物,這就要求理是確實存在的,而非虚幻。從這裏就可以看出莊子這一世界萬物皆是虚幻夢境的思想與齊物之間的矛盾。而且,即使理真實不虚,也要做工夫,循序漸進,待到窮理,方能齊物;莊子卻“一舉而納事物於幻”,認爲如此物便可齊,不須任何工夫修養,這在劉因看來,過於輕易,無異自欺欺人。也正是這一點,吸引了後世一些魯莽厭煩者,趨易避難,如蟻慕羊肉,争歸趣之。同時,以一切爲虚幻夢境,也能給失意之人以精神慰藉,因而莊子此説也受到困折之人的追捧,劉因一併將之斥爲不知義命。總之,劉因對無適而不可的齊物思想是讚同的,但他認爲莊子以夢作爲齊物的基礎卻是失敗的。
實際上,蝴蝶夢寓言的重點並不在夢的虚幻上,而在於無法分辨夢覺,則夢覺中的兩個主體可以互相轉化,因而它們是平等的,相通的,莊子着重從物化角度表現物之齊。相比之下,郭象將夢覺解釋爲生死,更爲接近莊子的本意。郭象云:
方其夢爲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爲此則不知彼,夢爲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爲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36)郭慶藩《莊子集釋》,第119—120頁。
郭象的解釋來自《齊物論》另一段關於夢的闡述:“予惡乎知説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夢中有夢,夢外還是夢,這才是劉因强調的虚幻,但莊子的重點仍不在此。莊子以爲,死生夜旦,存亡一體,世間的生命都是陰陽造化創造的,從個體生命的角度看固然是有生有死,但從陰陽造化的角度看,不過是將生命從一種形態重新鍛造成另外一種形態罷了。莊子通過妻子的去世反思了生命過程的實質,他説:“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至樂》)因此,從一個形態到另一個形態的流轉,就好像夢覺、晝夜的轉换,只不過人過於執著自我,係戀此生,又且智慧短淺,囿於此生,不知玄同生死,遂有在生憂死、貪生怕死之態。郭象則從人之樂生推斷出,人死後進入另一生命形態,也會樂於那一生命形態,“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37)同上,第111頁。。只是對於前一形態的生命即人來説,那都是死後之事,他已無從得知了。由此看來,兩種生命形態可以齊同爲一,這對此世的人來説,就是生死齊同。
然而,雖然彼我可同,人物可齊,甚至可以承認此世是夢,可是人在夢中,並不覺其爲夢,而是蘧蘧然周也,是真實的存在。郭象説:“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38)同上。悲歡離合、得失禍福仍然是必須面對的困境,並不會因洞達萬物齊同之理就會完全化去,劉因揭示的莊子齊物以及後人認同齊物的現實原因就是明證。王羲之生長在玄學大盛的東晉,且以天師道爲終生的信仰,可當他面對山河破碎滿目瘡痍時,也不得不發出强烈的感慨,堅決否定莊子生死一齊的觀點:“固知一死生爲虚誕,齊彭殤爲妄作。”
郭象解釋“逍遥遊”時云:“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遥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39)郭慶藩《莊子集釋》,第1頁。這是借鑒了當時的才性論思想,郭象認爲,萬物並生,而内在的才性不同,它外在所應獲得的分位與所能實現的功業與其才性相稱,所以不能要求萬物達到某種統一的要求,萬物只要找到符合自己本性才能的分位、事業,便可稱作逍遥了。適性是否就是莊子説的逍遥,可以討論,但郭象説的萬物須按其本性生存,卻是符合莊子之意的。南宋劉震孫在《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中發揮此意云:
戰國諸侯,蠻觸併鬥,以糜爛其生民,其禍實起於不知分。莊子於是時,思有以覺其迷而砭其疾,故於《逍遥遊》篇首寓微言。其曰鳩鴳之不敢自擬於大鵬,物之知分者也;其曰許由不敢受堯之天下,人之知分者也。夫使天下而皆知分,則賤不慕貴,小不圖大,强不淩弱,衆不暴寡。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舉一世莫不各安其天分之當然,而無僭踰争奪夭閼之患,則夫物之不齊者,非必物物而齊之,而無不齊矣。(40)劉震孫《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道藏》第15册,第174頁。
内在的性與外在的分確有相應相通之處,但儒家顯然只重外在的名分,莊子更重内在本性。郭象的性分思想意在調和二者,而劉震孫則又偏向了外在名分。而這並非本文重點,姑置勿論,這裏所要强調的是内在的本性對人與物是具有規定限制作用的。
不過歷史上對性分的討論都局限於人這一品類之中,觀察人性之不齊,將此理論推論開去,芸芸衆生,萬品殊類,其性其分,也無不如此。實則在《莊子》中,已將人作爲一個品類置於更大的生物界比較來看,從而也更能認清人這一品類的本性。按照莊子所説,萬類均須按其本性生存,猿猴棲木,泥鰍濕寢。即使如劉因所説,莊子將現實當作夢幻,在這個夢境破碎之前,它就是真實無比的,萬物也仍須按照其本性規定生存,“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没於淵”(《大宗師》)。同樣地,人作爲萬類之一品,也有自己的本性規定,這一方面是需要遵守本性規定,一方面是按照其本性規定便可。這即是説,人按照人的眼光觀察、認識世界便可,又何必以道觀之呢?又何以可能以道觀之?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包,道是大全,人則爲萬物之一,僅占一偏,要求人具有道的眼光是否超越了他的本性呢?他又怎能超越一偏達到大全的境界呢?在其一生之中,以褊狹的眼光看待世界、他人及個人的得失、生死,産生自以爲是、樂生惡死的想法難道不是符合其本性規定的正常現象嗎?如果對人可以有這樣的要求,那麽對其他物種是否也可以有同樣要求呢?莊子的齊萬物就是要讓萬物按照自己的本性自自然然地存在,萬物並作,和諧平等,互相之間不干擾,無紛争,更没有一個蠻横有力的外物不顧萬物本性之不齊,强求齊同。莊子説這就像那朝三暮四的猴子,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但是莊子自己卻在批判别人强求齊同時,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萬物尤其是人的本性的規定與限制,對人性與道相合提出了過高的要求。
由上述分析可見,歷代對於莊子齊物思想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宋元時期,批判者基本都是儒家學者,他們站在儒家思想的藩籬内,以孟子物情不齊思想爲準繩,以理學理一分殊思想爲解牛之刃,對莊子齊物思想進行剖析和批判。但由於過分局限於門户之見,不能真正深入瞭解莊子思想的真髓,僅以標題的表面含義爲討論對象,因而産生了極大誤解。實際上他們的意圖並不在批判莊子的齊物理論,而是通過對莊子齊物思想的批判,一方面宣揚自己的思想,一方面達到排斥異端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