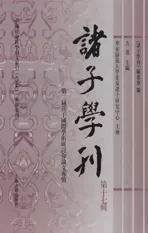“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内涵的轉變與意義*
2018-01-23臺灣江毓奇
(臺灣) 江毓奇
内容提要 就整個《莊子》詮釋傳統而論,歷來之論者在評議各家《莊子》注疏之作時,郭象(252—312)的《莊子注》往往具有承上啓下的輻輳性指標,而這種指標或者被逕行視爲評價時的正向標準,也或者衍生爲評價時的負向反思,皆顯見郭象《莊子注》在《莊子》學史中實具有正反相成的範型意義。同時,從郭象《莊子注》所衍生出來的相關理解問題,也就是如何詮釋與實踐《莊子》義理的問題,更是屢屢在《莊子》學史中造成諸多的議辯,而此中最爲重要的議題之一,即爲“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對此,當代的研究者或將此議辯類比於宋代陸九淵(1139—1192)所謂“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的關係,而指向不同的詮釋取向與目的問題。但回到《莊子》學史發展的脈絡觀之,此議辯之内涵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盡然都是詮釋取向與目的的問題,其意義在個别的詮釋情境之中,有所承繼,也有所轉變。因此,有鑒於學界目前仍尚未有完整的考察與討論,筆者將根據已掌握到的傳世文獻,從“議辯之前: 一個禪思性問題的肇端”、“議辯之始:‘《莊子》注郭象’之批判中的可能性内涵”、“議辯之中: 作爲正向範型的顯化及其内涵的差異”、“議辯之中: 作爲負向範型的反思及其内涵的差異”到“結語: 議辯之後?正向顯化與負向反思的承變與調適”的討論架構,説明不同論者在不同脈絡下,提出此議辯之内涵的差異與價值意義。
[關鍵詞] 郭象注《莊子》 《莊子》注郭象 範型性詮釋 話頭禪 正向範型 負向範型
一、 問題的討論與提出
對於魏晉時期向秀(?—275)與郭象(252—312)承傳衍構之《莊子注》的理解(1)《莊子注》之作者問題,始自《世説新語·文學》所謂:“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參見劉義慶編撰、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説新語箋疏》(上册),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26—227頁。歷來的《莊子》研究者對此説多有討論,但此問題並不影響本文的觀點與論述,兹不重新討論,以下采《莊子》詮釋傳統與歷代史志目録的説法,仍以郭象爲《莊子注》的代表作者。,在直接解讀元典之前,當代的研究者們往往可先從著名的哲學(史)或思想史的相關著作中找到觀察的角度:
一如: 湯用彤(1893—1964)在《魏晉玄學聽課筆記》中,從政治實踐及其理論創構的角度評價向、郭《莊子注》,指出:“郭象注《莊子》是講政治學説,至於其講形上學(Metaphysics)乃欲完成其政治學説也。他們對莊子學説並不甚滿意,乃因政治學説如此之故。”(2)湯用彤《魏晉玄學聽課筆記》,收録於《魏晉玄學論稿》(增訂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0頁。
二如: 馮友蘭(1895—1990)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從哲學建構之詮釋目的的角度認爲郭象注《莊子》“並不是爲注而注,而是借《莊子》這部書發揮他自己的哲學見解,建立他自己的哲學體系”(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四册),收録於《三松堂全集》(第九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436頁。。
三如: 方東美(1899—1977)於《原始儒家道家哲學》中的“莊子部分”,從“後設哲學”(meta-philosophical)的觀點,批評郭象以“物任其性,各當其分”注解“逍遥”之義,僅爲“近代小市民的心聲,是每個人都有的微末觀點”(4)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臺灣)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04—307頁。。
四如: 牟宗三(1909—1995)在《才性與玄理》一書中,從義理相應與否的角度評價“向、郭之注《莊》”,褒貶分明地指出“向、郭注《逍遥遊》,大體皆恰當無誤,而注《齊物論》,則只能把握大旨,於原文各段之義理,則多不能相應,亦不能隨其發展恰當地予以解析”(5)牟宗三《才性與玄理》,(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版,第196頁。。
五如: 勞思光(1927—2012)《新編中國哲學史》一方面從注解《莊子》的立場指出,郭《注》對於“《逍遥遊》之旨大體能有適當解説”,但對“内篇破除‘形軀’、‘認知’等執著之理論,在郭注中則完全不明本義”。另一方面則又從自身理論建構的立場指出: 郭注雖提出“萬物各全其性”之主張,但是“根本未解釋‘本性’如何制定,又‘本性’間之衝突如何處理;遂不能建立一足以自立的觀念系統”(6)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二),(臺灣)三民書局2002年版,第184—185頁。等。
這些知名的著作雖然寫作的立場、目的與方法皆不盡相同,但對於後起研究者來説,皆爲理解郭象《莊子注》提供了燈塔般的引導作用,以及許多哲學建(重)構時的反思性提問。其中包含了“郭象《莊子注》與《莊子》義理之間的相應問題”、“郭象《莊子注》的理論架構問題”以及“郭象《莊子注》的詮釋方法問題”等,這些問題視域都是以郭象《莊子注》爲主要的研究焦點或對象,而學界目前亦累積了相當豐碩的成果,不待筆者贅言。
然而,若我們調整觀察的視域與焦距,從郭象《莊子注》之詮釋内容的本身,轉向整個《莊子》詮釋傳統的脈絡來討論,則歷來的注疏者、評價者在評議各家《莊子》注疏之作時,郭象的《莊子注》往往具有承上啓下的輻輳性指標,而這種指標或者被逕行視爲評價時的正向標準。例如: 唐代陸德明(550—630)《經典釋文·序録》在評價漢魏以來的《莊子》注疏時認爲:“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故爲世所貴。”(7)陸德明著、吴承仕疏證《經典釋文序録疏證·注解傳述人》,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41頁。宋代陳景元(1024—1094)在《南華真經章句音義》中也從詮釋内容的角度認爲:“郭象之注,論其大體,真可謂得莊生之旨矣。”(8)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明·正統道藏本),見方勇主編《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13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版,第605頁。清代紀昀(1724—1805)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批評宋代林希逸(1193—1271)《莊子口義》時指出:“今案郭象之註,標意旨於町畦之外,希逸乃以章句求之,所見頗陋。”(9)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六道家類《莊子口義》,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246頁。諸如此等,皆顯現出郭象《莊子注》作爲評價之用的正向價值。
與之相反,亦有衍爲評價時的負向反思。例如: 宋代晁公武(1105—1180)《郡齋讀書志》在解釋唐代文如海《莊子疏》之作的動機時指出:“以郭象注放乎自然而絶學習,失莊生之旨,因再爲之解。”(10)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卷第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82頁。清代阮元(1764—1849)在《揅經室外集》所撰寫成玄英(活動於631年前後)《南華真經注疏三十五卷》提要指出:“疏之所本爲郭象《注》,象《注》掃除舊解,標新立異,大半空言,無所徵實,不免負王弼注《易》之累。”(11)阮元《揅經室外集》卷一,(臺灣)藝文印書館1967年版,第29頁。清末黄侃(1886—1935)替阮毓崧(1870—1951)作《莊子集注·序》時提出:“欲通《莊子》之書,必不可捨其言而求其意。自郭象《注》孤行,世以得意忘言貴之。然未獲魚兔,而先棄荃蹄,亦未爲善學郭氏者也。”(12)阮毓崧《重訂莊子集註》(1936年排印本),見《子藏·道家·莊子卷》(第137册),第1頁。諸如此等,亦顯現出郭象《莊子注》作爲評價之用的負向意義。以上例證,都不難使我們瞭解到郭象《莊子注》在《莊子》學史中實具有正反相成的範型意義。
不僅如此,從郭象《莊子注》所衍生出來的相關理解問題,也就是如何詮釋與實踐《莊子》義理的問題,更是屢屢在《莊子》學史中造成諸多的議辯,其中最爲重要的議題之一,即是“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對此,當代的研究者,或如湯一介(1927—2014)從郭象注《莊子》之目的的角度(13)湯一介《郭象與魏晉玄學》(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63頁。,也或者如劉笑敢從中國哲學方法論之定向問題的角度(14)劉笑敢《詮釋與定向——中國哲學研究方法之探究》,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60—96頁。,將此議辯類比於宋代陸九淵(1139—1192)所謂“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15)陸九淵著、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卷三十六《年譜》,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522頁。的關係。但總括來説,此議辯之内涵在《莊子》學史中的轉變與意義,學界目前仍尚未有完整的考察與討論,是以,筆者將根據已掌握到的傳世文獻,從“議辯之前: 一個禪思性問題的肇端”、“議辯之始:‘《莊子》注郭象’之批判中的可能性内涵”、“議辯之中: 作爲正向範型的顯化及其内涵的差異”、“議辯之中: 作爲負向範型的反思及其内涵的差異”到“結語: 議辯之後?正向顯化與負向反思的承變與調適”的討論架構,説明不同論者在不同脈絡下,提出此議辯之内涵的差異與價值意義。
二、 議辯之前: 一個禪思性問題的肇端
從傳世文獻的角度而言,根據筆者的考察,許多《莊子》注疏者提及“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此一議辯時,多僅以“昔人之説”的類似稱法交代論者身份,因此我們想要瞭解歷來的《莊子》注疏者對此議辯的基源性理解並不容易。然而,當代學者之相關論述涉及此議辯時,往往會提及或推測此議辯或許肇始於宋代無著妙總禪師(1095—1170)之語。雖然,就現存文獻的數量而言,不見得能够完全證實此議辯的起始源頭,但筆者認爲此語出現的應答語境依舊是一條重要的線索。因爲,就筆者目前所掌握到的傳世文獻而言,妙總禪師之語相對早於其他相關傳世文獻,並且在對話中充滿濃厚的經典詮釋觀及其實踐藴涵。兹論如下: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臨濟宗六南嶽下十六世”下,“徑山杲禪師法嗣: 資壽尼妙總禪師”題下記載: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脱去緣飾,咨參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檝隨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麽也不得囌嚧娑婆訶,不恁麽也不得唏哩娑婆訶。恁麽不恁麽,總不得囌嚧唏哩娑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卻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别宫商。雲山海月都抛卻,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16)釋普濟《五燈會元》,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348頁。
這段關於大慧宗杲禪師(1089—1163)與無著妙總禪師的傳法機緣(在場的還有馮檝居士),涉及了許多禪宗公案的典故,而《五燈會元》的編撰僅有概述,讀者閲讀不易,因此筆者擬重新梳理分析,以明妙總禪師兩次運用自身對於《莊子》學的體知,慧解宗杲禪師問題之因由,重構如下:
(一) 在此段中,宗杲禪師與妙總禪師的傳法機緣共有二次: 第一次是宗杲禪師舉“藥山(唯儼禪師)初參石頭(希遷禪師),後見馬祖(道一禪師)”公案開示衆人,在馮檝居士提出了自己的慧解後,宗杲禪師也請妙總禪師提出了自己的應答。第二次的傳法中,宗杲禪師爲了進一步瞭解妙總禪師的悟性如何,又舉“巖頭(全奯禪師)與婆子對話”公案再次開示妙總禪師,使其禪悟。
(二) 在妙總禪師第一次的應答語境中,上引馮檝居士的應答顯然是根據當年石頭希遷禪師對於藥山禪師的提問:“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子怎麽生?”與馬祖道一禪師“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麽生”的再次開悟而來(17)釋普濟《五燈會元》,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57頁。,但妙總禪師選擇不同於馮檝居士的直接類比與思考轉用,而是别開生面地以“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間辯證思考,應答宗杲禪師。
(三) 正因妙總禪師選擇應答的思考有所不同,所以在第二次的應答語境中,妙總禪師又直接針對宗杲禪師所舉“巖頭(全奯禪師)與婆子對話”的内容(故事節要: 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抛向水中(18)同上,第376頁。)作偈文應答:“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别宫商。雲山海月都抛卻,贏得莊周蝶夢長。”此解雖不同於先前的應答模式,在結尾處卻也使用了“莊周夢蝶”的典故,而使《莊子》義理契入於她的慧解之中。
在上述的人物中,宗杲禪師爲臨濟宗的大師,而臨濟宗在傳授禪法時最大的特色之一,即爲“話頭禪”或稱“看話禪”,此法的修行與過往禪宗公案密切相關,禪宗公案大體上與歷代禪師開悟的故事相關,此後亦成爲修行禪法時的經驗題材。“話頭禪”的禪法修行,即爲禪師舉用過往的禪宗公案開示弟子,並請弟子應答,弟子在應答時也不是用過往的經驗、觀念與知識,進行邏輯的推理與分析去尋求答案,而是在放鬆且安定身心的情況下,以不斷迫切詢問而非思考的方式,重複公案中最感興趣的某些句子或片段,最終使得“念話頭”、“問話頭”之問題與自我感徹底瓦解,以達禪悟之境界(19)關於“話頭禪”或“看話禪”的修行要旨,請見聖嚴法師著、單德興譯《虚空粉碎——聖嚴法師話頭禪指要》(SHATTERING THE GREAT DOUBT: The Chan Practice of Huatou),(臺灣)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1—37頁。亦可參見荒木見悟著、廖肇亨譯《大慧宗杲論禪語》,《“中研院”文哲所通訊》第15卷4期(2005年12月),第151—176頁。。
依此,妙總禪師在第一次的應答語境中所謂“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卻是莊子註郭象”之説,並未重複“藥山初見石頭,後見馬祖”公案中的句子或片段,提出的問題也不在公案的故事内容之中,顯然不是典型的“念話頭”與“問話頭”,甚至在過程中有妄生《莊子》學相關觀念與知識以參禪的危險。但筆者認爲,細忖妙總之禪思,反倒開啓了另一種跳脱禪宗公案之範圍限制的參禪法門,也就是説: 雖有妄生《莊子》學觀念之疑義,但將“問話頭”的内容從宗杲禪師藉由禪宗公案的給予,置换成妙總禪師自行生起的大疑——究竟是郭象注《莊子》?還是《莊子》注郭象?——並且排除其他所有的念頭,一樣可視爲“參話頭”的修行法門。畢竟,“話頭”中的問題僅是方便法門。因此,不應有任何必然如此的選擇限制,否則,也可説是另一種妄念我執。
然而,妙總禪師在第二次的應答語境中,以偈文“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别宫商。雲山海月都抛卻,贏得莊周蝶夢長”作答,從禪思的内容而言,“泛渺茫”、“别宫商”、“都抛卻”的意象,隱喻了修行者對於人文社會與自然世界所生起之總總妄念與我執的虚空粉碎,而入於“莊周夢蝶”之彼我消融、物我合一的境界;就禪法的修行而論,妙總禪師應答之偈文,不僅引用了前人詩詞的典故,更借用了其他公案中的偈文典故。例如“一葉扁舟泛渺茫”之語,可見於宋代司馬光(1019—1086)《漁父》“楚岸菊花香,扁舟泛渺茫”句;“呈橈舞棹别宫商”之語則分别出於宋代圓悟佛果禪師(1063—1135)開示時的法語“東海鯉魚振鬣揚鱗,南國波斯呈橈舞棹”(20)《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八,CBETA, T47, no.1997, p.748a20。句,與“掣電光中分皂白,海潮音裏别宫商”(21)同上,卷第十九,CBETA, T47, no.1997, p.804c06。句;而“雲山海月”之語,亦出自於“雲山海月渾閑事,一語歸宗萬國朝”(22)同上,卷第十九,CBETA, T47, no.1997, p.801b04。句。顯見,妙總禪師也不是一味地求新求變,而忽視禪宗公案與偈文之方便法門的傳統與作用。
因此,從禪學修行的角度而言,無論是“郭象注《莊子》”還是“《莊子》注郭象”之問題所生起的疑情,都可視爲“參話頭”過程中的大疑,也可説是參禪的方便法門,所以提出此問題對於妙總來説,並不在於透過知識與邏輯進行分析或討論,而是一種基於修行實踐的工夫論意義。再者,“莊周夢蝶”之義理的提出與引用,若僅從知識證立的視角觀之,論者或許認爲妙總禪師的應答中,令人有以“莊”解“禪”之感,但事實上,回到禪學修行的情境觀之,不僅是《莊子》義理,包括過往的禪宗公案、禪詩偈文都是方便法門的一種。所以,與其説妙總禪師是以《莊》“解”禪,不如説她是以《莊》“參”禪,而同於以“公案”參“禪”、以“偈文”參“禪”之工夫。
不過,若以《莊子》注疏史的角度觀之,原本“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的問題,雖然僅爲妙總禪師在參禪過程中之“看話頭”的方便法門,但在脱離此禪修的情境與脈絡之後,在《莊子》注疏史之再脈絡化過程中,此問題就容易變成“看話尾”的心智活動,意即思考此問題的具體答案而進入實質議辯的層面,使得後起之論者們在各自的論述情境中,進一步思考、分析與討論此問題所藴涵的不同内容與議辯核心。
三、 議辯之始:“《莊子》注郭象”之批判中的可能性内涵
在妙總禪師之後,宋代又有魏了翁(1178—1237)引用朱熹(1130—1200)對於解經體式之“經”、“注”分立的範型性觀點,並延伸至王弼(226—249)《周易注》的相關問題,再以“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作結。《鶴山集》卷一百八曰:
晦翁謂釋解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事,唯看注而忘經。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語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而其易明處更不説,此最得體。後來輔嗣注《易》,不但爲玄虚語,又間出己意,一段《易》反晦而難明。故世謂郭象注《莊子》,反似《莊子》注郭象。(23)魏了翁《鶴山集》,收録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3册),(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583頁。
魏氏删引了朱熹的觀點(24)魏了翁的引文省略了朱子之説,原文是説:“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腳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需各作一番理會,添卻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需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則知其非經外之文,卻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詳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收録於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4册)卷74《記解經》,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1頁。,主要是想確保以經典爲尊的主體性,不被後來經典注解者的詮釋反客爲主或者合流爲一,所以也認同朱子以漢儒毛亨對於《詩經》、孔安國對於《尚書》以字詞名物之難解處作基本訓解的範型。因此,以義理詮釋之發揮見長的王弼《周易注》就容易受到魏氏的批判。此中所謂“不但爲玄虚語”,主要是指王弼盡掃漢魏象數之注中使用具體物象的比附解釋(25)王弼對象數之學的批評請見《周易略例》,收録於樓宇烈《王弼集校釋》,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609頁。,進而提出“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26)同上。等詮釋方法,再借用《老》《莊》之“有”、“無”等抽象觀念進行詮釋。而所謂“間出己意”,則是指王弼對於《周易》經、傳合體的重構(27)例如,楊時喬(1531—1609)言:“古《易》二《經》、四《傳》、十《翼》各自爲篇,取《彖》、《象》傳作注解經,文附經下,自費直始,而定於劉向,成於鄭康成。取《文言》《乾》、《坤》二卦,附於《彖傳》後,始於王弼。”轉引自林慶彰、蔣秋華、楊晉龍、馮曉庭主編《經義考新校》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頁。與承變《易傳》以來的詮釋傳統(28)關於王弼對《易傳》解《周易》的承繼與創變,可參見戴連璋《玄智、玄理與文化發展》,(臺灣)“中研院”文哲所2010年版,第31—57頁。,而發展出自己的思想。顯然,不僅是朱子所謂“注腳成文”而會有經、注不分的問題,對魏氏而言,王弼對於《周易》詮釋傳統的承變,本身亦有“晦而難明”的問題。雖然明與不明也不一定都是注解者與注解本身的問題,有時也跟讀者的才學背景以及理解態度有關,但站在魏氏的角度,提出“世謂郭象注《莊子》,反似《莊子》注郭象”的議辯,顯然是一種連類比況的作用。如此,魏氏對此議辯雖稱“世謂”,但此議辯在此顯然還是要放在這個批評脈絡中加以理解。同時,也如同魏氏對於《周易注》的理解,本置於王弼對《周易》詮釋傳統的承變中去批評,則此議辯中的郭象《莊子注》問題,自然也須從郭象對於《莊子》詮釋傳統的承變去理解其中的問題,方得此議辯作爲批判時之較爲完整的可能性内涵。依此,在《莊子》詮釋傳統的參照下,則可有多面向而連續性的解讀,兹分析如下:
1. 就版本文獻而言,在漢代以來,《莊子》版本内容流行紛雜的情況下(29)陸德明對於漢以來的《莊子》版本問題,曾有以下觀點:“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説,若閼弈、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詳見氏著、吴承仕疏證《經典釋文序録疏證·注解傳述人》,第141頁。,從文獻内容的選定到内、外、雜篇性質的分判,皆出自郭象之思考與選擇下所構成的“理想文本”,即“《莊子》郭象本”,而非郭象對於過去某個統一或固定的《莊子》版本進行注解的工作。反之,批評者則可能據以批評郭象依己意重構文本,而喪失原本《莊子》可能有的豐富材料與思想上的多元面向。
2. 就詮釋目的而言,不僅注解的對象是出自於自己思考與選擇下的版本内容,郭象對其“理想文本”的詮釋,也往往着眼於“自然”與“名教”之義理思想的調和與現實需求而生。因此,既爲“調和”,則其詮釋的目的自不可能完全緊扣於《莊子》文獻進行詮釋,而需要創造出彼此之間的詮釋空間。反之,批評者則可能據以批評郭象不重視《莊子》文本在詮釋過程中的優先性與基準性。
3. 就詮釋方法而言,爲了創造新的詮釋空間,又因《莊子》本多以寓言的思考與表達對於天地萬物的詮釋與思想,即郭象所説的“寄言”(30)郭象注、成玄英疏《南華真經注疏》,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2、15、41、161、392、393、399等頁。,那麽郭象同樣地以“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31)同上,第1頁。、“宜忘言而循其所況”(32)同上,第10頁。、“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33)同上,第155頁。等方式去詮釋《莊子》。這一方面跳脱了漢代以來的章句訓詁之學的詮釋方法,另一方面也呼應了《莊子》之表達方法而加以轉出。反之,批評者亦可能據以批評郭象不先瞭解《莊子》之所言,又何以能够超越《莊子》之言。
4. 就義理核心而言,郭象在創造出新的詮釋空間之後,所提出之“自生説”的宇宙觀與“玄冥論”的工夫論,皆是藉由《莊子》之文本的詮釋而不盡同於漢魏以來的相關論述而有所轉出(34)關於郭象注《莊子》時的創發,可參見戴連璋《玄智、玄理與文化發展》,第246—291頁。,進以創建了自己的思想體系以及詮釋實踐的方式。反之,批評者亦有據以批評郭象的詮釋是實踐自己的思想,而非實踐《莊子》之義理的空間。
如此,在《莊子》詮釋傳統的參照下,魏氏如何將“郭象注《莊子》”理解爲甚至批評爲“《莊子》注郭象”,實可從版本文獻、詮釋目的、詮釋方法與義理核心等不同卻又彼此相關的角度去探討。不過,在後續的討論中,我們也會發現歷來提出此議辯者,多半僅從其中一、二種面向切入,以論述他們對於郭象《莊子注》或者正向、或者負向的評價,甚至是他們對於《莊子》應如何詮釋的觀點。
四、 議辯之中: 作爲正向範型的顯化及其内涵的差異
在第一節中,筆者已指出在整個《莊子》學發展的過程中,郭象的《莊子注》經常被當作評價的標準,而在不同的評價者與不同的面向中,亦或有正、負向範型的差異。回到郭象《莊子注》的本身,“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也往往涉及郭象《莊子注》的評價而有不同的内涵。以下,筆者將從此議辯作爲郭象《莊子注》之正向範型的顯化論起。對此,宋元之際的劉壎(1240—1319)在《隱居通義·莊子注》中曰:
郭象注《莊子》,議論高簡,殊有義味,凡莊生千百言不能了者,象以一語了之。余嘗愛其注“混沌鑿七竅”一段,唯以一語斷之曰:“爲者敗之。”只用四字,辭簡意足,一段章旨,無復遺論,蓋其妙若此。是謂《莊子》注郭象,亦是一説。(35)劉壎撰《隱居通議》卷十九,收録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6册),第166頁。
此處所謂“議論高簡”,主要是指郭象在詮釋《莊子》時,義理詮釋之高明博發、注解體式之精煉簡要。此中,體式簡要的評論基準很容易理解,一方面如與劉氏同時的褚柏秀在《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中,對於郭象注解“南海之帝爲儵”到“七日而渾沌死”一段即評論道“右章七十四字,郭氏引《道德經》一言以蔽之,簡要切當,莫越於此”(36)褚柏秀編撰、張京華點校《南華真經義海纂微》,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65頁。,另一方面也仍是從郭象自道“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説”(37)郭象注、成玄英疏《南華真經注疏》,第1頁。的詮釋觀點,與《莊子注》實際上非以章句訓詁的方式貫串全篇的解釋而斷定。但劉氏對於詮釋高明的評論基準,或者由於是筆記辨條的關係,特舉郭象對於《應帝王》“混沌鑿七竅”一段的注解爲例,既非《世説新語》所論魏晉時期即被關注的《莊子》“逍遥義”(38)《世説新語·文學》曾曰:“《莊子·逍遥》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遥》。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外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參見劉義慶編撰、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説新語箋疏》(上册),第 242頁。,亦非後之論者經常討論的郭象“自然義”、“性分論”、“聖人觀”與“名教觀”等,因此劉氏此處的論據就顯得較爲薄弱與和寡。不過,以“同情之理解”來看劉氏的論述,則“凡莊生千百言不能了者,象以一語了之”,以及“只用四字,辭簡意足,一段章旨,無復遺論”等説,其評斷的標準顯然是落在“詮釋的表達”而非“詮釋的内容”,則劉氏評斷的基準並不是以《莊子》作爲郭象詮釋的評斷依據,而是將郭象與《莊子》放在同一個天平,比較各自對於天地萬物或自然人文之理解的詮釋。如此,原先對於一般讀者而言,郭象的注解在於詮釋《莊子》之寓言,僅有幫助理解《莊子》所藴涵之義理的工具性價值;但對於劉氏而言,《莊子》之寓言反不如郭象之注解,而成了郭象創構與表達思想時的文獻基礎,而這也是“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在此脈絡中的主要意義。
其後,元明之際的陶宗儀(1329—1410)在《説郛·翼莊》中也説:
晉郭象注《莊子》,人言《莊子》注郭象,妙處果然。傳稱本向秀所爲,秀本不行,象竊取之耳。秀耶?象耶?吾不知也。然其言真足羽翼莊氏,而獨行天地間。爲八十一章,名曰“翼莊”。(39)陶宗儀編撰《説郛》卷三,收録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6册),第167頁。
《翼莊》一篇,主要是陶氏對於郭象《莊子注》之部分注解内容的再詮釋,而上引之論述,大致等同於“提要”的作用。只是陶氏把這個提要的焦點集中在郭象《莊子注》的價值,以便逕行嫁接其再詮釋之因由。此中所謂“妙處果然”的評論,顯然也是將“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用作正向價值的評論,則其内涵自須從“然其言真足羽翼莊氏,而獨行天地間”一句獲得理解。對此,不同於劉壎的反客爲主將郭象《莊子注》的地位隱約地凌駕於《莊子》所代表的經典地位之上,陶氏則仍以《莊子》爲尊,郭象《莊子注》爲輔,只是“獨行於天地之間”的評價,將郭象《莊子注》在《莊子》學史中的地位推尊爲“具有典範性意義”的地位,猶如《周易》之有“十翼”(《易傳》)一樣。
時至明代中期,對於此議辯之郭象《莊子注》的評價,亦有折衷於劉壎與陶宗儀之間者,如楊慎(1488—1559)在《郭象注莊子》一文中指出: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録《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余愛郭《注》之奇,亦復録於此。(40)楊慎著、焦竑編、桂有根校《莊子解》(明刊升菴外集影印本),收録於嚴靈峰編《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第3册),(臺灣)藝文印書館1974年版,第4頁。
對此,楊氏的説法直接從學養之襟懷、筆力之表達的角度,肯定了“《莊子》注郭象”等同於“郭象注《莊子》”的正面意義。但與劉壎、陶宗儀兩人不同的是: 劉氏以郭象《莊子注》爲勝,陶氏以《莊子》經典爲尊的立場,是以義理思想應如何表達,或《莊子》義理應如何詮釋的角度進行思考;楊氏思考的面向則在於《莊子》義理應如何契入實存的生命情境,以做出存在的詮釋與實踐。如此,“郭象注《莊子》”之筆力表達的詮釋活動,自然也是“《莊子》注郭象”之學養襟懷的存在實踐。因此,對楊氏來説,在經學史上同樣作爲“範型性詮釋”(41)所謂“範型性詮釋”,主要指在《莊子》詮釋史中,某些先行詮釋者之目的、方法與體式,在後起集釋者之“承繼/通變”與“反思/批判”的理解關係中,逐漸形成集釋《莊子》之核心基礎,而有其基準性之價值意義與實踐性之功能效用的詮釋著作。此觀點見於江毓奇《集釋型〈莊子〉學研究》,第167頁。的《禮記》鄭玄注,與《莊子》郭象注的典範意義之“同”而有“異”的意義,即在於楊氏認爲郭象的《莊子注》除了學術建構的傳承性層面之外,還有存在境遇的實踐性層面。
其後,稍晚於楊慎的何良俊(1506—1573)在《四友齋叢説》中,又不同於上述諸家在各自的論述中,賦予“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在不同脈絡下的不同意義。何氏先否定了他所認知到的“世謂觀點”,再轉出郭象《莊子注》的正面意義。對此,他説:
《莊子註》莫過於郭象,世謂非郭象註《莊子》,乃《莊子》註郭象,此不知言之甚也。蓋以其不能剖析言句耳。然郭象妙處正在於此。夫莊子之言,謬悠奔放,莫識端倪,非俗學之所能窺。而郭象之注,直以玄談發其旨趣。蓋晉人之談,略去文詞,直究宗本,非若後人之章句,但句解字釋,得其支節而已。苟以是求之,則郭象之言可逆刃而解。淺見者不知,遂爲此過談,可笑可笑。如吕惠卿、王雱、陳祥道,陳碧虚、趙虚齋、劉槩、林疑獨、吴儔諸人之注,與成法師疏,范無隱講語,林鬳齋口義,皆是章句之流。若王文正公(旦)又有《莊子》發題,李士表十論,恐亦不足以發南華老仙之趣。唯山谷内篇論,能見一斑。(42)何良俊《四友齋叢説》卷十九,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68—169頁。
依此,從“不知言之甚也”的批評,與“蓋以其不能剖析言句耳”的推因看來,何氏所認知下的“世謂觀點”,合理的推論應是指:“郭象注《莊子》”時,不僅不就原有的文獻語脈逐一解釋,反藉由對於《莊子》的詮釋,創發自己的思想,故有“《莊子》注郭象”之説。對此,何氏之所以不能認同的原因是: 歷來許多的詮釋者不能對《莊子》之“謬悠奔放,莫識端倪”的語言特性做出深切的瞭解,以致期望以章句之“句解字釋”做出詮釋,而郭象之所以可以“逆刃而解”,即是對於《莊子》之“寄言”有所反思、有所領悟,並能提出“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等詮釋方法,如此而可“直究宗本”。顯然,何氏認爲在《莊子》義理之究竟的體證中,玄思談理之辨證更勝文脈字句之訓詁。
此外,此議辯的内涵在何氏之前的論述中,常與經學注解的相關案例對顯而出,如前文所引之魏了翁、後文將論及之熊朋來、陳天祥等人皆是如此。何氏則是少數就《莊子》學史中的注解,率先加以提出例證而比較者。只是,這些幾乎都與郭象《莊子注》一起收録於宋代褚伯秀(1270年前後有活動)《南華真經義海纂微》(43)何氏所舉的例子中,除了成玄英《莊子疏》,其他皆在褚書中有所收録,詳見褚柏秀編撰、張京華點校《南華真經義海纂微》,第5、6頁。的注解,是不是皆如何氏所論之“章句之流”,恐怕有很大的商榷空間。總之,何氏雖以此議辯具有負向之義涵,但因其之根本立場仍在於推尊郭象《莊子注》,故筆者仍將其列於此處討論,以作爲變例之比較。
明代在何良俊之後,比較能够回到《莊子》學史的脈絡中討論此議辯的還有馮夢禎(1548—1605)。他在《莊子郭注序》中指出:
注《莊子》者,郭子玄而下凡數十家,而精奥淵深,其高處有發《莊》義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蓋《莊》文日也,子玄之注月也,諸家繁星也,甚則爝火、螢光也。子玄之注在前,而諸家不熄,譬之毛嬙、西施在御,而粉白黛緑者,猶然累累争憐未已也。近世金陵焦弱侯並行《老》《莊翼》,蓋收郭注而旁及諸家,趙女、吴娃俱充下也,余則盡去諸家而單宗郭氏,回頭一顧,六宫無色。今先列正文,低一字即録郭注,俱爲大字,無所隆殺,進之也。昔人曰:“非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知言哉!余故進之,進之與《莊子》等也。(44)馮夢禎撰《莊子郭注序》,見沈如紳《南華經集評》(明萬曆三十三年凌以凍刊五色套印本),收録於嚴靈峰編《無求備齋老列莊三子集成補編》(第29册),(臺灣)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頁。
不同於前文所引之論,多半以筆記雜説的方式,附帶或專門提出此議辯對於各自議題的脈絡意義,馮氏站在重新校勘與批注《莊子》的立場撰作此序。在此序中,“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的内涵,則與前人之論有所同,也有所不同。例如,馮氏與劉壎一樣,皆認爲郭象《莊子注》對於《莊子》義理不及之處有所創發,但劉壎認爲郭象《莊子注》更勝《莊子》,馮氏則認爲兩者是同等的價值與地位。又如,馮氏與陶宗儀、何良俊一樣,肯定郭象《莊子注》在《莊子》學史中具有典範意義,但陶、何二氏没有實際注解《莊子》的經驗,而馮氏則有重新校勘與批注的經驗。因此之故,馮氏又舉明代同期學者焦竑(1540—1620)的《莊子翼》爲例,認爲焦氏之書雖能廣澤各家,兼采衆解,但所集之注的價值,均無法與郭象《莊子注》等量齊觀。因此,馮氏在他的書中,獨尊郭象之注,甚至在版刻的呈顯上,也使郭象之注文與《莊子》之經文的字體大小皆同,顯然從詮釋的内容到版刻的呈顯,都有獨尊郭象之注的傾向。不過,較之於焦竑在詮釋内容上偶有批評郭象之説(45)焦竑《莊子翼》(明萬曆十六年王元貞校刊《老莊翼》本),見《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45册),第214頁。,在詮釋方法上承繼“要其會歸”但通變“遺其所寄”的詮釋觀(46)詳見江毓奇《集釋型〈莊子〉學研究》,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年1月,第150、151頁。,則馮、焦二氏之間,亦有明顯的不同。
其後,林堯俞(1589年進士)雖然没有自己對於《莊子》義理的注解之作,但在替郭良翰(1616年尚在世)《南華經薈解》作序時也提出:
《南華》注者百餘家,而郭象爲著。或曰象注本於向秀,迨後人尊之,至謂非郭注《莊》,而《莊》注郭,則何以稱焉?蓋注書之家,名爲訓詁,字比句櫛,期於曉暢而止耳。乃象之於《莊》也,洞其寓言之意,而神明之,而宏擴之。《莊》或有不可解之語,而象無不極馳騁之路,讀者第見其邃於理、燁於詞,以爲若《左氏》之可以孤行者,是著書之體,非注書之體也。(47)序載於郭良翰《南華經薈解》(明天啓六年刊本),見《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79册),第1、2頁。
林氏主要是從詮釋方法的層面,對此議辯的内涵進行“注書之體”與“著書之體”之差異的“正向”思考。依林氏的觀點,“注書之體”雖然重視《莊子》字詞之訓詁、章句之解釋等“言内之意”的解讀,但其效用頂多使得經典的閲讀獲得文從字順的理解;而“著書之體”則重視《莊子》寓言之根本精神,並試圖擴大“言外之意”的空間與可能,進而創造出更大的理解效益與詮釋效果。因此,林氏也才會認爲郭象《莊子注》爲“著書之體”,而同於此議辯之“《莊子》注郭象”的“正向”解讀。同時,由於《南華經薈解》的作者郭良翰對此議辯的解讀理路與林氏不盡相同,所以筆者將在下一節再予以介紹及討論。
此外,還有一種從彙集諸家評點之角度對此議辯提出觀點者,例如沈汝紳(生卒年不詳)的《南華經小序》曰:
余始有事於《南華》,而彙集諸家評點……既而細閲諸解,唯晉郭子玄首出,升庵先生嘗有“非郭注《莊》,寔《莊》注郭”之語,則子玄已久膾炙人口矣。兹不可不載者,第千百世之下恒以臆見懸揣千百世之上,恐讀《莊子》不易,而讀子玄書亦不易耳。唯得郭解劉評,而《莊》之微既闡矣。(48)沈如紳《南華經集評》(明萬曆三十三年凌以凍刊五色套印本),收録於嚴靈峰編《無求備齋老列莊三子集成補編》(第29册),第11、12頁。
不同於大多數的論者多半以“昔人”、“世謂”交代“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的由來,再賦予自己對此議辯的觀點内涵。沈氏對此議辯的理解,雖清楚地交代是由楊慎之説而來,但他們對此議辯的肯定仍是就不同層面説的。如上文之所分析,楊氏的思考在於《莊子》義理應如何契入實存的生命情境,以做出存在的詮釋與實踐,所以對楊氏來説“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可視爲一辯證的連續性實踐。但沈氏對此議辯着眼的是“子玄已久膾炙人口矣,兹不可不載者”的角度,則是根據郭象《莊子注》作爲“範型性詮釋”甚至文學性的意義(49)此處可輔以方勇的考察進行交互的理解,他説:“王世貞曾著《南華經評點》,後由沈汝紳録入此套色印本而得以流傳至今,此爲沈氏此書最有價值者。今依本書顔色所示,可清楚看到王世貞在評點《莊子》全書時,亦評點郭象注。其評點可分爲兩層面,即一是屬於一般斷句意義上之圈點,另一是屬於文學欣賞等意義上之評點。”詳見氏著《子藏·莊子書目提要》,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頁。,作出文獻的整合,評點《莊子》的同時,也評點郭象之《莊子注》。
到了明末,具有實際注解《莊子》經驗的方以智(1611—1671)則苦心孤詣地創構《向子期與郭子玄》一文,藉由向秀替郭象辯誣的情節與理由,展示其對詮釋《莊子》的特殊觀點。此中,方以智不僅嘗試藉由虚擬向秀的角度切入,也不時藉由“平叟雜拈”的第三方立場,對此文做出評議。例如,虚擬的“向秀”在此文開宗明義點出“世皆以君竊僕書,補《秋水》、《至樂》,易《馬蹄》行世。或譽君,或詬君。君將謂有功于莊子乎哉?爲此言者,將謂有功於于僕乎哉?請爲君釋冤,以釋吾之冤”(50)方以智著,張永義、邢益海點校《藥地炮莊》,華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頁。之問題時,方氏又别以“平叟雜拈”詮釋曰:
《莊子》注郭象,然哉!莊子使才放憨,郭則正語,此真向秀筆也。劉孝標云: 秀與嵇康、吕安爲友,康傲世,安邁俗,而秀雅好讀書。李禿翁言向秀,七賢中最可鄙。沈幼宰曰: 秀佐康鍛柳下,注意依附。叔夜許之,正如幼安不絶子魚耳,愚正喜子期平心,不作放曠詭態也。其容迹也,張衡之對,謝瀹之飲也。此處不識,何用看《莊》?
郭之竊向,亦是山谷换骨法耳。老子不竊管子之《内業》篇耶?黄帝、周公,集天下之智者,上也。《吕覽》、《淮南》亦巧矣,奈何以法聖齊丘爲例耶?正言若反,莊是賊魁。既非其才,套更可厭。向、郭皆以正語三昧出之,更覺中和相忘不争,亦以此故。(51)同上。
此中,方氏開宗明義就同意過去或有“郭象《注》莊子”的説法,但其内涵與前人之説不同,並從向秀對於《莊子》的詮釋實踐與郭象對於向秀的承繼,分兩階段立論。
在第一階段中,方氏認爲向秀對《莊子》義理的闡發,既不同於《莊子》或有的“使才放憨”式的義理精神與修養工夫,也不同於嵇康與吕安等放曠詭態式的生命實踐,而是根據自己的才學修養與生命情調,體會並隱解出《莊子》尚未被世人闡發出的義理精神。如此,則向秀的詮釋與實踐自不在於“考證”《莊子》的言内之意,而是“體證”《莊子》即於實存生命的言外之意。此後,向秀之筆以郭象正語傳之,故世稱“《莊子》注郭象”。
在第二階段中,方氏又以黄庭堅(1045—1105)之“换骨法”的文學創作觀喻之,雖然恰不恰當、精不精準仍有討論的空間,但從較爲寬泛的使用角度而言,方氏認爲: 不僅是郭象,從古聖賢人如黄帝、周公,與經典書籍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往往匯聚天下之智與巧而出,所以對郭象《莊子注》的評論,不應僅從拾人牙慧的角度觀之。此外,關於詮釋的問題,方氏亦認爲: 由於莊子思想本身常常貫通天下之“正言”,進行“若反”之思考的辯證與表達,但向秀、郭象均無莊子之才,因此只能從己出之“正語”作爲體證的方便法門,去理解與詮釋《莊子》,而非蠅營狗苟於《莊子》之字字句句,亦不啻爲“中和相忘不争”的具體實踐。
由此可知,方氏對於“《莊子》注郭象”之正向思考在於: 一方面有鑒於向秀、郭象本非以《莊子》文獻爲絶對基準,以詮釋《莊子》義理之事實;另一方面則是標舉: 向秀、郭象對於《莊子》義理的理解,乃是依其才性隱解《莊子》義理即其生活世界的存在意義。
方以智之後,一樣具有實際注解《莊子》經驗的金兆清(1635年尚在世),則與焦竑《莊子翼》對於郭象《莊子注》的集釋態度較爲相同,其《莊子榷·條例》曰:
注《莊子》者,郭子玄而下,凡數十家,而精奥淵深,其高處有發《莊》義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昔人云:“莊文日也,子玄之注月也。”雖升庵有“非郭注《莊》,實《莊》注郭”之語,然《莊》文之有郭注,闢猶佛法之先驅耶?今以郭注爲主,而旁及諸家,第其間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有不必解、不得不解者,吾安知可解者之非不可解,而不得不解者之非不必解也,在善讀者之會其意則可耳。(52)金兆清《莊子榷》(明崇禎八年刊本),見《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74册),第267頁。
眼尖的讀者可能會發現: 金氏對於郭象《莊子注》開宗明義的幾句評論,與馮夢禎在《莊子郭注序》中的開頭評論極爲相似,其後又略引馮氏“莊文(日)—子玄(月)”之喻,顯然有暗取略引的問題,但不管當時是否也有像當代一樣的著作權的歸屬問題,金氏顯然也贊同馮氏評論郭象《莊子注》時,所謂“其高處有發《莊》義所未及者”之論點。但兩氏最大的不同在於: 馮氏是無條件地獨尊郭象《莊子注》而將《注》與《莊子》之地位同等,金氏則僅以郭象《莊子注》爲集釋《莊子》時的“範型性詮釋”,所以金氏也不完全認同楊慎將“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視爲詮釋實踐時的辯證連續性,而是回歸詮釋《莊子》的立場,仍將郭象《莊子注》與其他的注解皆視爲理解法門之一。同時,所謂“在善讀者之會其意則可耳”,當然也是承自郭象“要其會歸”的觀點而來,只是在《莊子榷》中,亦多有集引“形”、“音”、“義”之解釋成果的情況下,金氏與焦竑的觀點一樣,仍是“要其會歸”但“‘不’遺其所寄”的(53)金兆清對於《莊子》的詮釋觀,可另參江毓奇《集釋型〈莊子〉學研究》,第151、152頁。。
討論至此,就劉壎、陶宗儀、楊慎、何良俊、馮夢禎、林堯俞、沈如紳、方以智、金兆清以來的論述譜系而言,雖然皆肯定了此議辯或郭象《莊子注》的“正向”意義,但其細節内涵的差異,仍須回到各自被提出的脈絡之中加以討論,以明其動態之承變關係。
五、 議辯之中: 作爲負向範型的反思及其内涵的差異
就傳世文獻而言,除了在“議辯之始”一節中,筆者已舉宋代魏了翁之例,並分析其對此議辯作爲批判王弼《周易注》之類比的可能性義涵之外,宋元之際,又有將此議辯的其中一部分,應用於經學史之相關詮釋之批判者。例如,陳天祥(1230—1316)《四書辨疑》曰:
觀聖人天地所不能盡之一句,且論聖人不能盡,若以亦有所不知、亦有所不能之,經文爲解,猶有可説,然已幾於《莊子》註郭象矣。(54)陳天祥《四書辨疑》卷十五,收録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2册),經部八,四書類,第521頁。
此處所謂“《莊子》註郭象”之説,主要在於批判朱子對於《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的解釋(55)此處《中庸》之原文如下:“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參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22頁。。根據“經文爲解,猶有可説”的線索,可知陳氏認爲: 就原本經文之脈絡而言,所謂“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與“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56)同上。應爲理解的關鍵核心,當就君子之道對於聖人的體證層次與實踐義涵作解。但朱子在《中庸章句》的解釋中,對於聖人之部分卻解作“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内,可謂費矣”(57)同上。,而將此段的理解導向“道”之“費而隱”乃超越聖人與天地之大而無外的特質。因此,姑且不論朱子與陳天祥彼此之間到底有没有或到底是誰“誤讀”《中庸》的詮釋問題,“《莊子》註郭象”之諷喻的内涵,在陳氏的觀點中應是站在經典詮釋當貼合於文獻語脈的標準上,對於跳脱語脈之詮釋者的批判。
這種經學史上之詮釋問題的相關見解,稍後的熊朋來(1246—1323)也在《經説·漢儒以漢法解經》一文中指出:
漢儒以漢法解經,如《周禮》中,五齊、二酒皆以東漢時地名、酒名言之,更代易世,但見經文易通而注語難曉,使人有《莊子》注郭象之歎。(58)熊朋來《經説》卷四,收録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4册),第307頁。
此中,“五齊”當指《周禮·天官·冢宰下》所謂:“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59)鄭玄注、賈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禮注疏》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頁。“二酒”或爲“三酒”傳鈔之誤,即“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60)同上,第163頁。。依此,熊氏所謂“漢人以漢法解經”,“以東漢時地名、酒名言之”,主要是指漢代鄭玄在解釋《周禮》“五齊”、“三酒”之義時,往往以漢代的地名、酒名相比附。如鄭玄對“五齊”中“泛齊”,以“如今宜成醪矣”比況;對於“醴齊”,以“如今恬酒矣”比況;對於“盎齊”,以“如今酇白矣”比況;對於“緹齊”,以“如今下酒矣”比況;對於“沈齊”,以“如今造清矣”比況(61)同上,第162頁。。又如對於“三酒”中“事酒”,以“其酒則今之醳酒”解説;對於“昔酒”,以“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解説;對於“清酒”,以“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解説等(62)同上,第163頁。。據此,尚且不論《周禮》中的名物或制度與東漢時究竟相差多少,以及是否適合用比況的方式進行解釋等詮釋問題,熊氏所謂“經文易通而注語難曉”之意,則是指詮釋者不僅要理解《周易》的名物制度,因爲注解的關係,反必須理解東漢時期的名物制度,而徒增困擾。如此,“《莊子》注郭象”在此處之所以被用以類比,也是指郭象常運用魏晉時期玄思辨理的方式詮釋《莊子》,對於後世可能産生的理解問題。當然,《莊子》與《周禮》之義理内容與型態相去甚遠,熊氏的類比是否完全精當則又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了。
此後,到了明代,陳治安(1550年進士)在《南華真經本義·附録》中,又將此議辯帶回到《莊子》本身的詮釋問題中進行評論。他説:
昔人言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用此褒美,亦似譏彈。注不了經,何取於注?今録注數則,以挹其玄奥逸麗之風,不必爲解《莊》之藉也。(63)陳治安《南華真經本義》(明·崇禎五年刊本),見《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81册),第391頁。
從“用此褒美,亦似譏彈”的評論,即可發現陳氏所針對與批評的是,上一節中將“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視爲正向價值之意義者。並且站在“人共一心,理無二趣”(64)陳治安《南華真經本義》(明·崇禎五年刊本),見《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81册),第7頁。以及“解《莊》而不得本意,雖欲藉爲通曉,祇增結塞耳”(65)同上,第18頁。等經典義理詮釋觀,而以《莊子》經典爲尊。因此,陳氏自然會認爲: 在郭象多有跳脱《莊子》文獻進行解讀的情況下,則《莊子注》中的創造性詮釋也是值得商榷的。所以,陳氏在他的《莊子本義》中,並不采行郭象《莊子注》的説法,僅作“附録”以供讀者對於魏晉玄風之解《莊》的參考。
不同於陳治安的《莊子》學觀點,明代的郭良翰在《南華經薈解·説》一文中,另外提出了自己對於《莊子》詮釋的反思:
蓋自《南華》之尊爲經也,解者無慮數十家,愈解愈不可解也。則不解之解,解而不解。微乎微乎,蓋難言之。於是世始盡詘諸子,孤行郭子玄之説。昔之人至謂非郭注《莊》,乃《莊》注郭。迨乎今,玄風大暢,辯囿競馳,朝假筏於丹基,夕乞靈於靈鷲,談之燁然,按之窅然。於是乎,昔之注《莊》易,《莊》注難也者;而今也,《莊》注易,注《莊》難矣。非誠注之難易也,師心於一己易,肖神於作者難也。(66)郭良翰《南華經薈解》,見《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79册),第18、19頁。
在郭氏的認知中,“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的内涵,原先是用來讚美郭象對於《莊子》詮釋之開創性與範型性意義的評論,但隨着《莊子》學史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詮釋者或許受到“《莊子》注郭象”的啓發,也或者基於自己的詮釋情境與需求,而加入了許多經典之外的知識或者信念,如丹基、靈鷲等元素的涉入,使得理解《莊子》的詮釋活動逐漸有主、客反轉的現象。所以郭氏提出“昔之注《莊》易,《莊》注難也者”與“而今也,《莊》注易,注《莊》難矣”的對比來説明這個現象。其實也是要説,在郭象注《莊子》以前,能够以“《莊子》注郭象”的方式,藉由注解進行義理創建的工作並不容易,亦甚有價值;但在郭象注《莊子》以後,許多類似“《莊子》注郭象”類型的詮釋卻變得到處浮泛,缺乏基準(67)郭良翰在《南華經薈解·凡例》中指出:“《莊》注自子玄而後,玄風大暢,家挾赤水之珠。郭子注《莊》,《莊子》注郭,互有闡明,發所未發。一云郭本於向,此專言郭者,總其成也。”即爲明顯的例證。詳氏著《南華經薈解》,見《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79册),第25頁。。所以,“難”與“易”的標準,僅限於詮釋者之詮釋意向與目的,而不在於詮釋的内容及層次。也正因此,對郭氏而言,如果“《莊子》注郭象”説的是郭象的注解本身,那麽是具有“正向”意義的,但如果是成爲一種評議其他《莊子》詮釋的標準,那麽“《莊子》注郭象”就可能帶有一種負向反思與批評的義涵。
明清之際,周拱辰(活動於1637年前後)在《南華真經影史·自序》中,從實際理解《莊子》義理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反思:
吾髫即喜讀《南華》一書,而於《逍遥》《秋水》,尤深諷詠,顧省其義,茫然無畔。歸而求之諸家,而諸家之注勿善是也,庶幾求之向、郭,而茫然者彌甚。或曰: 注《莊》有五難: 目豆一也,腹儉二也,刻舟三也,落草四也,行濁而言清五也。非郭注《莊》,乃《莊》注郭,以爲服誠之言乎哉!猶乎烈影伏地,土不能飲其誠而暴其形,土則何辭?(68)周拱辰《南華真經影史·自序》(清嘉慶八年聖雨齋重刊本),見《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89册),第14、15頁。
周氏的反思遍及他以前的各家注解,他認爲在他理解《莊子》的過程中,並没有任何一家注解能給他多少燈塔般的指引,而《莊子》學史上最負盛名的郭象《莊子注》更是造成他“茫然”甚鉅的元凶。因此,不同於宋代林希逸(1193—1271)從儒學之立場所提出的“五難”(69)林希逸著、周啓成校注《莊子鬳齋口義校注·發題》,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2頁。,周氏則是站在批判的立場由隱漸顯地提出“五難”,以針砭郭象《莊子注》的相關問題。此中,“目豆”指目光如豆,見識短淺;“腹儉”指胸中貧乏,學問短淺;“刻舟”指刻舟求劍,不知變通;“落草”指落草爲寇,强奪其理;“行濁而言清”指品行卑劣,但言語清高。顯然,周氏對於郭象在注解的過程中,從知識學養到人格實踐,都有很大的意見。雖然,除了人格實踐的問題,《世説新語》中本有“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70)參見劉義慶編撰、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説新語箋疏》(上册),第226、227頁。的説法之外,知識學養的問題是否也如周氏所論,恐怕在不同的觀點與標準下,仍有見仁見智的空間。但總括來説,周氏如同上引陳治安的觀點,都是對“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所受到的“正向”肯定提出批判的角度。
其後,與周拱辰年代較爲接近的胡文蔚(1656年尚在世),則是從《莊子》學史的角度提出反思,其《莊子合注吹影·自序》曰:
凡言道者,皆吹影也。注《莊》云乎?疏《老》也。注《老》云乎?疏“道”也。皆謂之吹影之人也。古今注《莊》者多矣,晉之吹影者,稱郭象,或以爲攘自向秀,宋儒以爲郭注如夢,明陸方壺深然之。阿之者,復詫爲《莊子》注郭,是真夢中説影者。平情論之,夢固夢矣,至於删繁定訛,分别内外諸篇,殊有定識,經始之功,不可誣也。(71)胡文蔚《南華真經合注吹影》(清康熙間刊本),見《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93册),第150、151頁。
依此,胡氏對於歷來詮釋者的評論主要立基於他的“言—道”觀,在他的“言—道”觀中,從“語言”之活動與層面對“道”之究竟進行理解與詮釋的工作,無異於吹散影子般的不可能與徒勞無功。因此,不論是注解《莊子》,還是注解《老子》,都只能説是“吹影之人”。也因此,無論郭象在《莊子》學史上代表了什麽樣的意義,都像陸西星在《南華真經副墨》中説的“昔晉人郭象首註此經,影響支離,多涉夢語”(72)陸西星撰、蔣門馬點校《南華真經副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頁。。若再結合胡氏的“言—道”觀,則所謂“《莊子》注郭象”之意,就不是“正向”地肯定郭象對於《莊子》的創造性詮釋,而是批判郭象之詮釋猶如在自己的夢境中吹影——注解的過程是如此的真實,但實際上卻是如此的虚幻,也是如此的徒勞。同時,與前引之論者比較不同的是: 胡氏即便批判了郭象《莊子注》的詮釋型態,但還是從文獻整理與篇章分判的角度給予了肯定。
清代前期,吴承漸(1699年尚在世)從儒學之道的根本立場,對於郭象《莊子注》的影響力提出反思,其《莊子旁注·序》曰:
予少喜讀其内外諸篇,而病其離合於道也。尤病注《莊》者之甚害於道而實以害於《莊》也。史稱凡注《莊》者數十家,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之外爲之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絀,道家之言遂盛焉。夫自戰國以迄漢魏,人莫不知有《莊子》也。自向、郭索隱繪空,競清談而標玄旨,士習波蕩,海宇風頹,時謂非郭注《莊》,乃《莊》注郭耳。信斯言也,與桓温、孫武子所歎何以異!當時有識之士,追禍本而泝亂源,每不能爲向、郭諸人貸也。(73)吴承漸《莊子旁注》(清康熙三十八年璫水春波漁舍刻本),見《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97册),第303—306頁。
對於吴氏而言,在其儒學的基準下,《莊子》義理或有“離合於道”的問題,但真正令吴氏感到不滿的是,歷來注解《莊子》的詮釋者亦或有將《莊子》的義理詮釋得更加偏離者,此中之甚者即爲郭象《莊子注》。而吴氏推斷的原因,一來是承自《世説新語·文學》篇中的説法(74)參見劉義慶編撰、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説新語箋疏》(上册),第226、227頁。,認爲向秀與郭象帶起了競以玄思理解《莊子》的風潮;二來是在此風潮之後,論者或以“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爲“正向”的肯定。所以,在吴氏的觀點下,《莊子》已有離、合於儒學之道的情況,郭象又離、合於《莊子》之道,那麽他自然無法將此議辯當成對於郭象之創造性詮釋的讚揚,相反必須對其提出批判。
其後,清代末期的馬先登(1807—1876)則是從注解的妙思創意層面提出批判,其《南華瀝摘萃重刻序》曰:
降及魏晉六朝,其風大競,崇尚清談者,皆祖其説,故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特列書目,其流傳反在《孟子》七篇之上,其爲之注者,無慮數十家,而以郭象之妙析奇致、大暢元風爲最上。然考《世説》載:“向秀初注《南華》,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有郭象者,爲人薄行而有雋才,乃竊爲己有,自注《秋水》《至樂》,又易《馬蹄》一篇,餘則點定文句。”而世遂侈爲美談,曰: 郭象注《莊》,《莊》注郭象。此以見作者之妙於前,愈不可無注者之妙於後。(75)馬魯摘評《南華瀝摘萃》(清同治九年敦倫堂刊本),見《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108册),第181、 182頁。
此説也是對於將“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視爲“正向”意義的批判。馬氏認爲: 從《莊子》學史的角度來看,根據陸德明《經典釋文》的説法,郭象《莊子注》之所以被視爲詮釋《莊子》的“範型性詮釋”,與魏晉之清談玄風的詮釋基準不無關係(76)陸德明原是説:“然莊生弘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説,若閼弈、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故爲世所貴。”陸氏是否僅從玄風評價郭象之注,則有待商榷。詳見陸德明著、吴承仕疏證《經典釋文序録疏證·注解傳述人》,第141頁。。但回到郭象注《莊子》的注解過程,根據劉義慶《世説新語》的講法,則郭象不過增加《秋水》《至樂》的注解,改動《馬蹄》的篇序,並點定全書文句,要説郭象藉由詮釋《莊子》以進行創造性的詮釋,未免太過不符合創構的比例。所以,馬氏認爲“見作者之妙於前,愈不可無注者之妙於後”,即意指對於經典詮釋而言,假如先行詮釋者之妙解創意已擺在眼前,則後起詮釋者更要以此爲準,再行妙解創構於後。當然,這個觀點所提出的用意,其實也是爲了推尊其先輩馬魯的《南華瀝摘萃》才是真正善解於後者。
討論至此,就陳天祥、熊朋來、陳治安、郭良翰、周拱辰、胡文蔚、吴承漸、馬先登以來的論述譜系而言,雖然皆否定了此議辯或郭象《莊子注》的“正向”意義,但其細節内涵的差異,與“正向”的情況相同,仍須回到各自被提出的脈絡之中加以討論,以明其動態之承變關係。
六、 結語: 議辯之後?正向顯化與負向反思的承變與調適
根據筆者對於傳世文獻的掌握,“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的相關文獻,較早或可溯自宋代無著妙總禪師所謂:“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 卻是莊子註郭象”之語。不過,此語出現的語境卻是在大慧宗杲禪師與妙總禪師的參禪應答,而此應答之語,根據筆者在前文中的分析,應視爲“話頭禪”之“話頭”,即疑情生起之“大疑”,也就是“問話頭”或“看話頭”之禪修功夫。妙總禪師此語的用意,並不在於用過往的觀念與知識進行邏輯的推理與分析去尋求答案,所以筆者認爲妙總之語的出現只能説是議辯之“前”。
其後,妙總禪師此語一出,若不在“問話頭”之禪學修行的脈絡中,則“看話頭”的工夫體證,自然容易變成“看話尾”的智思活動,而去思考甚至解答此議辯所藴涵的各種問題。然而,當此語成了真正的議辯之“始”的智思活動之後,較早被關切的焦點反而不在郭象《莊子注》身上,也不在《莊子》學史的脈絡之中,而是被應用於經學史之相關案例的評價之中。例如,稍後於妙總禪師的魏了翁對於王弼《周易注》的批評,宋元之際,陳天祥對於朱熹《中庸章句》的辨疑,熊朋來對於鄭玄注《周禮》的批評等,都是以“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的“負向”解讀進行比觀與評價的工作。顯然,在其他經典研究的歷史情境中,此議辯作爲一種延伸應用,作爲“負向”範型的反思問題,勝於作爲“正向”範型的顯化意義。
真正回到郭象《莊子注》與《莊子》學史的議辯之“中”進行討論的例子,則是“正向”範型的顯化與“負向”範型的反思同時兼具的發展。但也如同筆者一再提醒的: 不論是“正”、是“負”,它們被顯化與反思的内涵與意義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以下權且省略前文之討論過程,歸結各家要點如下,以明其承變:
(一) 就正向範型的顯化而言
1. 劉壎對此議辯之正向顯化在於: 將郭象《莊子注》與《莊子》放在同一個比較基準,則《莊子》之寓言反不如郭象之注解,而成了郭象表達與創構思想時的文獻基礎。
2. 陶宗儀對此議辯之正向顯化是仍以《莊子》爲尊,郭象《莊子注》爲輔,但將郭象《莊子注》在《莊子》學史中的地位推尊爲“範型性詮釋”的地位,猶如《周易》之有“十翼”(《易傳》)一樣。
3. 楊慎對此議辯之正向顯化在於:“郭象注《莊子》”之筆力表達的詮釋活動,自然也是“《莊子》注郭象”之學養襟懷的存在實踐。所以郭象的《莊子注》除了學術建構的傳承性層面之外,還有存在境遇的實踐性層面。
4. 何良俊對此議辯之正向顯化在於: 在《莊子》義理之究竟的體證中,玄思談理之辨證更勝文脈字句之訓詁。
5. 馮夢禎對此議辯之正向顯化在於: 認爲郭象《莊子注》對於《莊子》義理不及之處有所創發,但兩者仍是同等的價值與地位。
6. 林堯俞對此議辯之正向顯化在於: 突顯郭象《莊子注》作爲“著書之體”,以明其重視《莊子》寓言之根本精神,並試圖擴大“言外之意”的空間與可能,進而創造出更大的理解效益與詮釋效果。
7. 沈汝紳對此議辯之正向顯化的用意在於: 根據郭象《莊子注》作爲“範型性詮釋”甚至文學性的意義,以作出文獻的整合,評點《莊子》的同時,也評點郭象之《莊子注》。
8. 方以智對此議辯之正向顯化的作用在於: 一方面有鑒於向秀、郭象本非以《莊子》文獻爲絶對基準之事實;另一方面則是標舉: 向秀、郭象乃是依其才性隱解《莊子》義理即其生活世界的存在意義。
9. 金兆清對此議辨之正向顯化的用意在於: 僅以郭象《莊子注》爲集釋《莊子》時的“範型性詮釋”,在回歸詮釋《莊子》的立場中,仍將郭象《莊子注》與其他的注解皆視爲理解法門之一。
(二) 就負向範型的反思而言
1. 陳治安對此議辯的負向反思在於: 在以《莊子》經典爲尊的前提下,郭象多有跳脱《莊子》文獻進行解讀的情況,則《莊子注》中的創造性詮釋也是值得商榷的。
2. 郭良翰對此議辯的負向反思在於: 在郭象注《莊子》以前,“《莊子》注郭象”般的思想創建並不容易,亦甚有價值;但在郭象注《莊子》以後,許多類似“《莊子》注郭象”類型的詮釋,卻變得到處浮泛,缺乏基準。
3. 周拱辰對此議辯的負向反思在於: 在郭象注解《莊子》的過程中,從知識學養到人格實踐都有許多值得商榷的空間。
4. 胡文蔚對此議辨的負向反思在於: 批判了郭象《莊子注》的詮釋型態,但還是從文獻整理與篇章分判的角度給予了肯定。
5. 吴承漸對此議辨的負向反思在於: 站在自身的儒學基準之上,《莊子》已有離合於儒學之道的情況,郭象又離合於《莊子》之道,那麽他自然須對郭象之創造性的詮釋提出批判。
6. 馬先登對此議辨的負向反思在於: 就注解的妙思創意層面而言,根據《世説新語》的記載,要説郭象藉由詮釋《莊子》以進行創造性的詮釋,未免太過不符合創構的比例。
綜上所述,在《莊子》詮釋傳統中能够像郭象《莊子注》一樣,受到歷來衆多《莊子》詮釋者之反思與批判、承繼與通變而具有“範型性詮釋”之意義者,可謂極爲少見。不僅如此,郭象《莊子注》所衍生的相關詮釋問題,例如“郭象注《莊子》”與“《莊子》注郭象”之議辯,更常在《莊子》學史與其他經典的詮釋問題中,作爲正向的顯化與負向的反思之範型,顯見郭象《莊子注》在傳統學術史上的影響力。雖然,在過往的《莊子》詮釋傳統中,郭象《莊子注》的開顯性與遮蔽性早已或隱或顯地擺在那裏,但對於當代的《莊子》詮釋者而言,如何適當地承變與調適郭象《莊子注》的詮釋遺産,或開發其他不同意義的詮釋型態,並且即於當代社會的存在意義,應是當代《莊子》研究者可共同開拓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