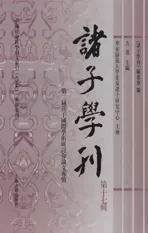從《聲無哀樂論》之“和聲”義看嵇康對莊子思想的傳承與轉化
2018-01-23臺灣李美燕
(臺灣) 李美燕
内容提要 先秦兩漢以來,儒家視雅樂爲道德教化之用,唯雅樂才能對人心、社會與國家産生正面的教化作用;反之,凡是讓人們放縱情欲的音樂(如鄭衛之音)都應該被禁止。然而,在魏晉時期,嵇康提出《聲無哀樂論》重新解構儒家以樂教教化人心的理論,他提出“和聲”作爲音樂本質,“和聲”對人只能産生躁静的反應,而與人之哀樂情感無涉,其目的乃在强調樂教之所以能“移風易俗”的關鍵乃是在於“人心”,而不在於音樂。但嵇康所謂的“和聲”究竟是甚麽意義呢?“和聲”如何可能對人心産生影響呢?本論文試圖溯其本源,從嵇康所引述《莊子》的話語(以“天籟”與“至人”爲主)對“和聲”的意義提出解讀。
[關鍵詞] 嵇康 《聲無哀樂論》 和聲 莊子 道家
前 言
從先秦早期的文獻史料的記載來看,由於中國在周朝(前1046—前256)是以血緣親情形成的宗族社會爲主要結構的,因此,從家庭、社會到國家向來都是以和諧爲貴,作爲維繫倫理與安定社會的理想。周公制禮作樂以維繫周王朝的統治,直到周朝末年禮壞樂崩之後,諸子百家才紛紛提出救世之道(1)李美燕《中國古代樂教思想(先秦兩漢篇)》,(臺灣)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其中尤以儒、道二家最具有代表性,儒家肯定周朝禮樂文化的價值,認爲禮樂制度的敗壞,其問題是在於人心,而不是在於制度本身,人們應該要回歸周禮的精神;道家則否定周朝的禮樂制度,認爲周禮只是徒具形式的存在,已經没有實質上的意義。
所以,儒家正面地肯定禮樂與道德教化的實用性,提出以“和”爲美的價值觀;然而,道家則從負面的立場否定禮樂與道德的功用性,認爲禮樂的形式會使人心流於虚僞、造作與不自然,因而提出以“真”爲美的價值觀,認爲人的精神生命應該從現實的束縛中解脱,以追求逍遥大自在的理想歸宿。儘管儒、道二家對禮樂文化的觀點有其根本的差異,但兩者皆以主體生命之修養境界爲人生之大美,在以“和”作爲物我關懷的實踐理想方面卻殊途同歸。
同時,在儒、道兩家文獻中也保留着對禮樂傳統的省思,有關於音樂以“和”爲本質的記載(2)李美燕《先秦儒道樂論中“以和爲美”之異同析辨》,《儒道學術國際研討會·先秦: 論文集》,臺灣師範大學2002年版,第75—92頁。。爾後,魏晉時期的嵇康在儒、道兩家思想的影響下,也提出對音樂的本質“和聲”的省思,重新解構儒家以禮樂教化人心的理論,融入道家自然的思想,而開創出“和聲”在音樂美學上的新意義。本論文即試圖溯其本源,從嵇康所引述《莊子》的話語對《聲無哀樂論》中的“和聲”提出省思與解讀。
一、 嵇康對音樂之本質“和聲”的省思
先秦兩漢的儒家在道德教化的前提下,重視樂教的教化意義,但魏晉時期的嵇康在《聲無哀樂論》一文中卻提出新的省思,他質疑儒家欲透過樂教以教化人心的可能性。《聲無哀樂論》一文前後八次進行反覆辯難,其層層論證的重點在於嵇康認爲音聲只能引起人們“躁”、“静”的反應,音聲本身並没有哀、樂的情感可言,當人們聽音樂時會産生哀、樂的情感,那是因爲人本身既有的哀、樂情感隨着音樂的導引,才宣洩而出。然而,何以音聲能引發人本身既有的哀、樂情感流露呢?嵇康提出那是因爲音聲有其自體存在的本質——“和”。嵇康對儒家樂教的可能性提出了顛覆性的説法,但令人困惑的是,嵇康《聲無哀樂論》一文中“聲”、“音”、“樂”、“聲音”、“音聲”與“音樂”經常混用,並没有嚴格的區分,這些字眼多半都可以指廣義的音樂而言,唯有提出“和聲”作爲音樂的本質是個例外。然而,他對於“和聲”也没有給予清楚的界義,只有交代“音聲”的起源:
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3)嵇康《嵇中散集》第五卷,《四部備要》,(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頁。
嵇康首先提出音聲是自然存於天地之間,在陰陽五行的變化下所産生,有如氣味在天地之間一樣,且“其體自若”。如此的觀點一開始就決定了音聲的本質不是人爲的,而是自然的,所以,這個定義也決定了音聲必然没有哀樂之情在其中。其次,在嵇康《聲無哀樂論》一文中亦可見“和”是音樂本質,而有所謂“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4)嵇康《嵇中散集》第五卷,《四部備要》,(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8頁。、“隨曲之情,盡乎和域”(5)同上。之説,點示出“和”作爲各種不同樂曲的本質,此即“聲音以平和爲體”(6)同上,第9頁。,人的心志是早有所定,只是隨着平和之音聲的感應,而使内心的感受流露而出,這也就是嵇康提出的“聲”、“心”(“情”)異軌觀念。
同時,嵇康在反對聲音具有哀樂的情感色彩的前提下,提出“和聲”其實是無象的存在,亦即“自然之和”,所謂“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7)同上,第5頁。,“自然之和”即是音聲的自然之理,嵇康藉此以點明“和聲”之體性自若,而且“和聲無象”(8)同上,第2頁。,“和聲”之體性無具體之形象可擬,純屬客觀之存有,卻具有感發人之情感流露的作用。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嵇康並未證成“和”作爲音聲的本質如何可能。而且依照嵇康的觀點來看,音聲既然是客觀存有,“和聲”是抽象之自體,如何可能對人心産生感發的作用呢?同時,也不免會引發我們思考的是,各式各樣的音樂都能被看作是一種“和”的本質的表現嗎?相對於“和”而言,是否也有本質上不平和的音樂呢?
就嵇康的文脈來看,音聲有自然之和爲其自然之理,所謂“和”應該是就着音聲的共性而言,也就是説不論音聲有何等不同之殊性,其之所以爲音聲的自然之理,皆是以“和”爲體性,因此,才有所謂“大同於和”(9)同上,第8頁。、“盡於和域”(10)同上,第8頁。之説。問題是,“和”如果是就聲音之體性所産生的理念,如何能對人之心情有所感發呢?而且音聲如果加上人爲的創作,就有創作者之情感與理念表現在其中,又如何能説“和聲無象”呢?由此可見,嵇康對於“和”作爲音聲的本質在立論上實有無法圓説的不足之處。
由於嵇康對“和”作爲音聲本質的定義並不是很明確,只强調“和”是非感知,也非存在的形上本質,而且是跳脱出人爲的價值判斷,不具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因此,他只能用描術性的語言來呈現“和聲”的本質意義(“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體自若而不變”),如此一來,自然也會引生另一個問題,就是“和”與人之情的關係究竟要如何建立呢?
根據筆者的省思,嵇康的重點應該不是在建立音樂的形上理論,否則其以“和”作爲音聲的本質,在理論本身就有無法圓説的問題。其所關注者應該是在一開始秦客與東野主人展開對話的問題上,嵇康欲藉此以引發人們重新審視儒家樂教的教化理想如何可能?而在第八組問答中,嵇康即明白地點示出,雅樂與鄭聲不是決定移風易俗的關鍵,因爲不論是雅樂或鄭聲都具有“和”的本質,何以雅樂能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而鄭聲卻會使人心陷溺沉迷呢?换言之,嵇康發現世俗人心以爲音樂能教化人心其實是有盲點,事實上,人之主體生命的自我修養才是樂教教化的可能根據,所謂移風易俗的關鍵應該是在於“人心”,而不是在於音樂本身(11)李美燕《從〈聲無哀樂論〉探析嵇康的“和聲”義》,《鵝湖》第309期,2001年版,第40—50頁。。
所以,當人心返歸於道之自然,“和心足於内”(12)嵇康《嵇中散集》卷五,第11頁。,内藴而外發,而“和氣見於外”(13)同上。,然後透過“歌以叙志”(14)同上。(樂),“舞以宣情”(15)同上。(舞),“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16)同上。(詩),“播之以八音”(17)同上。的教化薰習,可使人的精神與體氣獲得導養,性情平和,自然能“感之以太和”(18)同上。,使“心與理相順,氣與聲相應”(19)同上。,以成就天人和諧之美。最後,嵇康提出如下之説:
故曰: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悦,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本不在此也。(20)同上。
嵇康透過層層轉進的論辯,主要的用心在説明,樂教移風易俗的根據乃在於“人心”,而不在於音樂,人如果没有平和之心,内藴而外發地生平和之氣,就無法與平和之樂産生感應,而這也就是嵇康何以提出“聲無哀樂”的目地所在。
二、 嵇康“和聲”説與莊子的“天籟”義
從上述所論可以得知,《聲無哀樂論》一文是由秦客(代表儒家樂教立場)與東野主人(代表嵇康)的層層對話來展開,嵇康之所以透過論辯的方式提出“聲”、“心”(“情”)異軌的觀點,其用心並不在於作純概念性的思辨,而在對儒家樂教提出省思。他指出“和聲”作爲音樂的本質只能引發人既有深藏於内心的情感宣洩,“和聲”本身並無所謂的哀樂可言,更遑論有“移風易俗”的功能。嵇康試圖藉此以扭轉人們對有聲之樂的執著,將樂教移風易俗之實踐根據,返歸於人心之自我修養。
因此,嵇康有謂“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21)嵇康《嵇中散集》卷五,第11頁。,實承《老子》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22)李耳《老子》,《四部備要》,(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0頁。的觀點而來,由此來强調“簡易之教”(23)嵇康《嵇中散集》卷五,第11頁。與“無爲之治”(24)同上。,反映出嵇康承襲道家的理念,認爲“移風易俗”的理想,乃在使人心“默然從道”(25)同上。,“而不覺其所以然”(26)同上。,不同於儒家之名教以外鑠之禮樂教化來改變人心。嵇康的説法雖然對扭轉儒家傳統樂教的價值觀有其不可抹殺的貢獻,但對於“和聲”的定義與作用卻留下尚未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證實“和聲”可以作爲音樂的本質,“和聲”作爲音樂的本質與人之主體交感的理據何在,嵇康《聲無哀樂論》一文顯然並未對這些問題提出省思。
此外,嵇康所謂的“和聲無象”,以“無象”來呈現“和聲”的意義,這種表述的方式顯然是融入了來自道家思想的啓發。我們在《聲無哀樂論》一文中可見嵇康兩次引用《莊子·齊物論》的“天籟”(“吹萬不同”、“使其自己”)之説:
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哉!(27)同上,第2頁。
且聲音雖有猛静,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慼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28)同上,第9頁。
有關《莊子·齊物論》的“天籟”之説,自古迄今,歷代的解讀相當多,筆者的重點不在於如何還原莊子的“天籟”本意,而在於辨析嵇康如何運用莊子的“天籟”之説以建立其觀點,及他引用莊子“天籟”之説的意義究竟在哪裏。這裏,筆者先從“三籟”之説的内在理路來看。首先,人吹簫管産生的聲音是“人籟”,“人籟”是有待於人吹簫管而成聲;其音源是來自一個方向,此種聲音在一定的距離之内才能爲人們所感知。“地籟”有待於風吹大地之孔竅而成聲,風吹大地孔竅所産生大自然空間的回響是來自四面八方,“地籟”的音源没有固定的方向,也没有一定的距離。此處“人籟”與“地籟”都是在人的身體感知範圍之内。至於“天籟”則是“自己”、“自取”,無所依待,意味着“天籟”是無任何外在之因素使然,换言之,所謂的“天籟”不是透過人的感官認知而得。
事實上,“天籟”其實是一種隱喻,不是就着現實存在的聲音而言,其背後的意義乃在比喻人之生命修養的精神境界——“自然”、“無待”。由此推知,嵇康引用莊子“天籟”之説,有可能即是欲藉諸“天籟”的超越義以説明聲音之本質“和聲”能體現於衆聲之中,但卻與人的主觀情感無涉(29)林朝成《嵇康〈聲無哀樂論〉初探》,收於《文學與美學》第三集,(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頁。林氏亦提出“《聲論》借用莊子《齊物論》‘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的句子,以説明聽音樂後出現的情感是聽者自己從内心發出而不是音樂所引起、所賦予”。。然而,前人談及嵇康《聲無哀樂論》引用《莊子》“天籟”的意涵者卻不多見,目前有林修德在《從〈聲無哀樂論〉引用〈莊子〉“三籟”典故探其“聲情關係”中所藴含的工夫向度》一文中提出具體的論述:
《聲無哀樂論》旨在引用“三籟”典故以揭示聆樂者得以透過聆樂活動而展現某種“體道之情”,亦即是一種同樣出自於“人心”,但其卻得以受到“和聲”引導轉化的自然和諧之“情”,因而此“情”將有别於僅是基於“哀心有主”主導下所引發的“成心之情”。在此對應關係中,正顯現出《聲無哀樂論》對於《莊子》“三籟”思想的繼承與轉化。具體而言,此種“體道之情”即是一種聆樂者在受到“和聲”引導之“躁静和應”下而仍然能够引發出的“哀樂情應”,且此種聆樂的情感反應亦即是一種得以升華轉化進而趨向平和的哀樂情應。如此一來,《聲無哀樂論》的“聲情關係”中即藴含了某種工夫向度,亦即是指聆樂者得以透過聆樂活動進而修練轉化自我的内心情性,以促使自身的内在心境趨近平和的體道境界。(30)林修德《從〈聲無哀樂論〉引用〈莊子〉“三籟”典故探其“聲情關係”中所藴含的工夫向度》,《“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54期2013年版,第95頁。
林氏的説法顯然與其導師吴冠宏的説法一脈相承,吴氏説:
若就嵇康而言,其意當在反撥傳統的聲情關係,使主客體相離於哀樂之“情”,卻於躁静之“氣”處相即,進而會通於“和域”,並賦予主體的修證作爲聆樂體道之理境的助緣……彰顯嵇康滌“情”以顯“氣”乃至會通以“氣”交融於“和”的音樂進路。(31)吴冠宏《魏晉玄義與聲論新探》,(臺灣)里仁書局2006年版,第207頁。
上述二人之説皆指出嵇康藉“和聲”以體道,然而,遺憾的是,未能指出嵇康在《聲無哀樂論》中所提出的“和聲”何以能有發滯導情的作用,嵇康藉“和聲”以體道如何可能。凡此皆是尚未解決的問題。而筆者對於嵇康引用《莊子·齊物論》的“天籟”之説的觀點是,嵇康藉由“和聲”因乎自然——“其體自若”,以建立“聲無哀樂”的論點,其實與《莊子·齊物論》中藉“天籟”以比擬人之生命修養的境界——自己、自取,亦即無所待的進路並不完全相同。
審言之,筆者也試圖爲嵇康《聲無哀樂論》一文所提出的“和聲”義在《莊子》一書中尋找相關的線索,而查考《莊子》一書中有關“和”的説法,則可見《莊子》思想中的“和”,乃在藉“遊心乎德之和”以達到“和以天倪(天鈞)”的境界,尤其是在内篇《齊物論》《德充符》中,莊子點示出透過生命修養以達到人與萬化合一的境界;在外、雜篇中則明白地點示出人如何通過修養工夫的實踐,以遊心於和,而達到“道通爲一”的境界(32)李美燕《〈莊子〉思想中“遊心於和”的美學意涵》,《諸子學刊》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160頁。。换言之,《莊子》書中“和”字的精義是一種生命修養的境界型態,此與嵇康對音聲之起源於天地之間五行以成,音聲之本質“和聲”——“其體自若”的説法並不相同。
而事實上,嵇康並未説明何以人之内心在“無所先發”的“平和”狀態下,就可以感受到“和聲”對“人情”的和諧轉化作用。且值得思考的是,嵇康《聲無哀樂論》中所謂的“和聲”能對每一個人都産生同樣的效應嗎?是否會因人而産生個别差異呢?又“和聲”使人心産生和諧的反應究竟是如何可能呢?换句話説,“和聲”既然能對人心産生影響,就必然與人心之間會形成主客體之間的關係,其與《莊子·齊物論》的“天籟”乃是自己、自取,亦即“無待”的進路並不相同。所以,林氏謂“聆樂者得以透過聆樂活動進而修練轉化自我的内心情性,以促使自身的内在心境趨近平和的體道境界”,究竟如何可能呢?顯然,仍有待再做深入的探討。而在林氏一文中尚可見其提及“關於‘和聲’、‘和氣’與‘和心’互動影響作用下的工夫思想”:
此段論述所隱含的工夫思維是從創作者的“和心”出發,而當此創作者的内心處於“平和哀樂正等”進而“無所先發”的狀態,則其外顯之作爲便自然是“躁静和氣”的顯現,所以此論述即明確地指出“和心足於内,和氣見於外”,進而其所創作之音樂也皆成爲得以“感之以太和”的具體“和聲”。(33)林修德《從〈聲無哀樂論〉引用〈莊子〉“三籟”典故探其“聲情關係”中所藴含的工夫向度》,第124頁。
事實上,筆者以爲即使一個作曲家專注而投入地創作,創作當下的内心或許可處於“平和哀樂正等”而“無所先發”的狀態,但並不等於“其所創作之音樂也皆成爲得以‘感之以太和’的具體‘和聲’”,更何況甚麽樣的音樂才是具體的“和聲”呢?有甚麽曲目可以證明嗎?當嵇康在《聲無哀樂論》中一開始就指出“音聲”是來自天地之自然,五行所成時,就已經説明了“和聲”的意涵並不完全是直承莊子“天籟”説而來,嵇康引《莊子·齊物論》中“天籟”之説,有謂“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哉”(34)嵇康《嵇中散集》卷五﹐第2頁。,“斯非吹萬不同邪?”(35)同上﹐第9頁。顯然,其用心乃在藉“吹萬不同”、“自己”(“自取”)之本性的意涵來説明“和聲”乃因乎自然,其體自若,换言之,嵇康是爲了説明聲音各有其自體之本性,才在其文脈下順理成章地引用《莊子·齊物論》中“天籟”説的“自己”、“自取”之義。所以,嵇康是否有欲藉“和聲”以體道之意,可能還有待商榷。
三、 嵇康“和聲”説與莊子的“至人”義
其次,嵇康在《聲無哀樂論》中曾將鐘鼓(金石)、管弦之樂分説,强調“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弦也”(36)同上,第5頁。,“至和之聲,無所不感”(37)同上,第8頁。,可見嵇康對樂器本身的特質各有其體會,才有“克諧之音”與“至和之聲”不同的説法。很顯然,管弦之樂更受嵇康的青睞,可能與他本身也是一位古琴演奏者有關,因此嵇康以“至和”之聲來表述他對管弦之樂的體認。相關的論點還可見於嵇康在該文中提出筝、笛、琵琶本身在樂器的音色上,具有高亢而明亮的特質,自然會使人的身體産生躁越的反應;反之,琴瑟的聲音較低沉而緩慢,自然聽起來讓人的身心平静(38)同上,第8頁。。换句話説,嵇康强調音聲是客觀的存在物,同時,人之所以會受音樂的影響,也是受限於樂器的材質、結構與音色,再加上彈奏者的手法技巧與演奏功力,因而會讓人産生不同的反應。
而在《聲無哀樂論》一文中也可見“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盤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御之”(39)同上,第11頁。,“至人”一詞的出現,可見嵇康以此上契莊子的生命理想作爲祈嚮,説明人心修養才是樂教“移風易俗”的關鍵,關鍵並不在於“雅、鄭之辨”。换言之,嵇康在《聲無哀樂論》一文中提出“聲”、“心”(“情”)異軌的觀點,以“和聲”作爲音樂的本質,使人對音聲能直接影響人的情感與情緒的認知産生新的省思。
此外,我們在嵇康的《琴賦》一文中也可以發現兩處提及莊子思想中的理想人物——“至人”,一者是“至人攄思,製爲雅琴”(40)嵇康《嵇中散集》卷二,第2頁。;另者是“能盡雅琴,唯至人兮”(41)同上,第5頁。,不論是從斵琴技藝或撫琴操縵的立場來説,嵇康都援引莊子的修養論中的“至人”,來説明由技入乎道的境界,並將此理想的境界作爲“琴德”的内涵,審諸如下之文:
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紛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42)嵇康《嵇中散集》卷二,第4—5頁。
所謂“琴德”其實與人的身心修養有密切的關係,撫琴者在體氣清浄無煩擾,心靈遠離世俗塵囂的情境下,才能體現“雅琴”的意義。事實上,所謂的“雅琴”在漢代《風俗通義·聲音·琴》中即有“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43)應劭《風俗通義》,《四部備要》,(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4頁。之説,所謂“雅”琴原本是與儒家“雅”樂的教化意義有關。然而,嵇康卻是引進《莊子》的“至人”之説——“能盡雅琴,唯至人兮”,説明“琴德”與人的身心修養有密切的關係。
事實上,嵇康在《琴賦》一文中提出人在撫琴操縵時,琴樂對人有“導養神氣”與“宣和情志”的功能,能使人的心志情感獲得提升與轉化,同時以莊子思想中的“至人”來點示撫琴操縵可以展現一條自我修行的道路。審言之,當琴人在世俗塵囂中不斷地沉澱自我,使一己之情淡泊無求,在這種心境下撫琴操縵,可以讓人之體氣與琴聲相激相盪,心志與情氣融合爲一,使生命境界逐漸轉化與提昇,以達到“哀樂正等”的平和心境,進而“感之以太和”——契接天地宇宙大自然之氣(44)李美燕《嵇康〈琴賦〉中“和”的美學意涵析論》,《藝術評論》2009年第19期,第189—207頁。筆者在該文中曾對嵇康的“和聲”、“和氣”與“和心”的交感融通做過詳盡的探討,此處不再贅述。。
這裏,“氣”的重要性在嵇康的樂論中突顯而出,前人如林朝成即曾提出嵇康的“氣聲相應説突顯了‘氣’爲審美感受的獨立範疇”,“‘氣’與‘情’乃不同範疇概念”(45)林朝成《嵇康〈聲無哀樂論〉初探》,第204頁。。爾後,吴冠宏也以“躁静”作爲切入點,提出類似的説法:
躁静是聲音造成的作用,與人之喜怒哀樂不同,喜怒哀樂是人的情感表現,而躁静卻是受聲刺激下所呈現的氣動氣應,此背後實涉及一重要的觀念即是“氣”,“氣”是嵇康論“人”與論“聲”的共同本源。(46)吴冠宏《魏晉玄義與聲論新探》,第205頁。
又説:
(嵇康)其意當在反撥傳統的聲情關係,使主客相離於哀樂之“情”,卻於躁静之“氣”處相即,進而會通於“和域”,並賦予主體的修證作爲聆樂體道之理境的助緣,是以“躁静説”若能由此契入,或可避免“躁静情緒説”所帶來的糾葛與混淆,而更能彰顯嵇康滌“情”以顯“氣”乃至會通以“氣”交融於“和”的音樂進路。(47)吴冠宏《魏晉玄義與聲論新探》,第207頁。
基本上,彼二人皆主張嵇康《聲無哀樂論》中的“氣”與“情”是不同的兩個範疇,而吴氏更明白地點示出嵇康以滌“情”顯“氣”的方式作爲人與“和”樂交融的進路,其中的關鍵就在於“躁静”,乃是“受聲刺激下所呈現的氣動氣應”。事實上,筆者以爲一般人很容易將嵇康《聲無哀樂論》中的“躁静”視爲音樂帶給人們躁静“情”應的表現,亦即視躁静爲一種心理和生理的反應,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吴氏卻指出“躁静”是“受聲刺激下所呈現的氣動氣應”,並通過“氣”將人心與和聲之間建立起會通之道,無疑是替嵇康的“聲無哀樂”説圓場,闢出另外一條合理化的理解思路。但問題是,“躁静”的氣動氣應畢竟還是要由“聲”來産生,所謂的氣動氣應依然是就人的身體對“聲”所産生的反應而言,但人之身體受聲的刺激所呈現的氣動氣應,並不必然保證就能與和聲交感爲一,更遑論由此就能作爲聆樂體道之理境的助緣。
而在吴氏的説法中,似乎也並未釐清所謂的“主體”究何所指——是創作者,還是演奏者?抑或是聽衆?事實上,人之身體受聲的刺激所呈現的氣動氣應,在不同的主體所産生的效果不可能一致,又如何能保證人受聲的刺激所産生的氣動氣應就能與“和”的音樂進路交融,甚而由此論斷嵇康由滌“情”以顯“氣”,進而聆樂以體道呢?
换言之,人欲由聲的刺激所産生“躁静”的氣動氣應,以達到與“和聲”交融爲一,其中還需要透過修養工夫的漸進歷程而體現,並非一蹴可就,也絶不是單憑“聲”的刺激所産生“躁静”的氣動氣應即能達成,因此嵇康在《琴賦》中才會以“至人”的修養境界來比擬撫琴操縵的最高境界。嵇康所謂撫琴操縵的理想境界,其關鍵還是在於主體生命的修養,透過修養工夫産生自我生命内在氣息的運行,結合高明的指下功力,才能讓“和心”、“和氣”與“和聲”交感爲一,而不是由外鑠的“躁静”所産生的氣動氣應就能達到如此的理想境界。换言之,今日如欲解讀嵇康在《聲無哀樂論》中由“和聲”以感染人心,使“和心足於内”,内藴而外發,而“和氣見於外”的深層意涵,必然還要正視嵇康當年撫琴操縵的實踐體認,才能給予客觀而相應的説明(48)有關嵇康的琴學中“氣”在古琴音樂與人心之間的交融感應,筆者已另有專文及相關作品探討,參閲如下: 李美燕《嵇康〈琴賦〉中“和”的美學意涵析論》,第189—207頁。李美燕《嵇康古琴美學中的養生觀與自然》,收入《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六輯,(臺灣)里仁書局2010年版,第499—520頁。李美燕《古琴美學中的“氣”與莊子“心齋”説》,《經學研究集刊》第19期,2015年版,第29—42頁。。
結 論
先秦兩漢以來,儒家透過禮樂來達到教化人心與移風易俗的目地,因此,自孔子以來,崇雅樂、貶鄭聲的理念長期爲儒家樂教所奉行。然而,在魏晉以後,嵇康提出《聲無哀樂論》重新解構儒家以禮樂教化人心的理論,他認爲音樂其實有其獨立的意義,而與人之哀樂情感無關,更遑論有移風易俗之功能。同時,他提出“和聲”作爲音樂的本質,“和聲”對人只能産生躁静的反應,不會産生哀樂的情感。
然而,“和聲”究竟是甚麽意義呢?嵇康並未給予直接而正面的定義。他引述莊子的話語如“天籟”以呈現其意涵,由“天籟”之自己、自取説明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繫於人情,且“和聲”遍在於各種音樂之中。其次,他藉諸“至人”之修養工夫來提升撫琴操縵之境界。嵇康從撫琴操縵的親身體驗,將古琴推崇爲體道的載體,且在《聲無哀樂論》及《琴賦》一文中都援引莊子的“至人”境界,來説明人心修養的重要性。
相對地,在《莊子》一書中雖有論及音樂者,但音樂並未被莊子視爲達道的載體(49)郭平《魏晉風度與音樂》,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頁。“莊子懂音樂並能鼓琴,但他似乎並未把音樂作爲通往‘道’的載體。”,更無將至人與音樂繫聯者。因此,嵇康只是藉《莊子》一書中的至人形象結合撫琴操縵的修養境界,以提升琴德的價值,其所要强調的是,由“和聲”以感染人心,使“和心足於内”,内藴而外發,而“和氣見於外”,關鍵還是在於自我修養的境界高下,同理,樂教之所以能“移風易俗”的關鍵乃是在於“人心”,而不是在於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