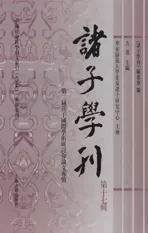論《淮南子》對《莊子》在禮學思想方面的闡發
2018-01-23臺灣賴升宏
(臺灣) 賴升宏
内容提要 《淮南子》乃淮南王劉安集門下賓客合著而成(1)“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高誘序》,(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班固《漢書·藝文志》歸之“雜家”(2)班固《漢書·藝文志》,(臺灣)鼎文書局1997年版,第1742頁。,高誘以其思想近老子(3)高誘:“(《淮南子》)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虚守静,出入經道。”《淮南子注釋·序》,(臺灣)華聯出版社1968年版,第1頁。,近代學者或以爲道家(4)熊鐵基以爲“新道家”,見熊氏《秦漢之際新道家略論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119頁。陳德和則名爲“淮南道家”,並説它最合乎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中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之要件者。見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臺灣)南華管理學院1999年刊,第195頁。,直至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出土,今日學者乃以《淮南子》爲漢初黄老思想集大成者(5)陳麗桂:“其實,除了黄老帛書、《管子》四篇和申、慎、韓諸人的著作之外……下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黄老道家思想理論益臻完備,終於在前漢七十年的政治上實際操作成功,其具體的理論結晶便是兼具集黄老思想與西漢學術思想大成雙重身份的《淮南子》二十一篇。”《戰國時期的黄老思想》,(臺灣)聯經出版社1991年版,第4頁。。可知《淮南子》與《莊子》思想上的密切關係。《莊子》重“道”輕“禮”,禮學思想非所重。《淮南子》重“道”兼重“禮”,對《莊子》禮學思想上多所闡發。本文由氣化思想,論禮樂之生,批判儒家之禮,因性而制禮等四大面向,探討《淮南子》對《莊子》在禮學思想上所做的闡發及其意義。
[關鍵詞] 《淮南子》 《莊子》 禮學 道家 黄老
一、 《淮南子》氣化思想對莊學的闡發
老莊思想主旨並非在“禮”,多藉批判儒家之“禮”,以凸顯“道”與“自然”(6)“太史公曰: 老子所貴道,虚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史記三家注·老莊申韓列傳》,(臺灣)七略出版社2003年版,第863頁。的重要。《淮南子》義理多夾雜老、莊思想(7)高誘:“(《淮南子》)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虚守静,出入經道。”《淮南子注釋·序》,第1頁。,但書中論禮學主張者甚具特色。本文就禮學思想角度,探討《淮南子》對莊子禮學思想的闡發及其意義,氣化思想乃其理論基礎。
(一) 精氣與煩氣
《莊子·至樂》云:“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8)郭慶藩《莊子集釋·至樂》,(臺灣)莊嚴出版社1984年版,第614—615頁。此段表現莊子後學對喪禮的看法。莊妻死,惠子弔唁,莊子不哀反鼓盆而歌,以此態度面對妻喪,惠子斥之。莊子後學由氣化思想論之,天地之始本無生無形,繼而氣化有形有生,今則由生復死,故氣化聚散生死如四時週而復始,明白氣化之道,則能消解人情之悲,感大道之全而歌。莊子《知北遊》亦云:“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9)郭慶藩《莊子集釋·知北遊》,第733頁。亦由氣化思想解釋生死情狀,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大道無損,氣化有别,故莊子後學以氣化思想來安頓人情。
《淮南子》氣化思想深受莊子後學與《管子》精氣説影響,主張天地一氣,由氣化論人、物之生,但人、物氣化内涵有别。“古未有天地之時,唯象無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别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蟲,精氣爲人。”(10)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精神訓》,(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頁。此説有二點意義: 一、 人與萬物皆爲氣化而生,不管煩氣或精氣本質皆爲氣,此乃延續莊子後學氣聚則生,氣散爲死,死生一氣之説。二、 人與物雖爲氣化所生,“精氣”與“煩氣”畢竟不同,故人禽之氣化内涵有别,而以人爲貴,此乃受齊“稷下道家”精氣説影響,而對莊學氣化思想的闡發。陳鼓應先生云:“《淮南子》還吸收了稷下道家的精氣説,認爲生物由氣産生,氣又有精粗之分……這顯然是脱胎自《管子·内業》‘天出其精,地出其形’的説法,至於‘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則是對人死亡後歸返天地的説明,實質上與莊子以死生爲一氣之聚散的理論相同。”(11)陳鼓應《從〈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論道家在秦漢哲學史上的地位》,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52期,第81頁。説明《淮南子》氣化思想承於莊子後學與《管子》思想之背景,但“精氣”與“煩氣”氣化内涵差異有在。
(二) 守形、氣、神而不失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蠕動蚑作,皆知其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别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12)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原道訓》,第39—40頁。《淮南子·原道訓》論人、物之内涵差異,可解讀爲“精氣”與“煩氣”之異。“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蠕動蚑作,皆知其喜憎利害者”以其徒有形氣之性,而無“神”在其中,故“煩氣爲蟲”内涵乃徒具形、氣而已。人之内涵則有三: 形、氣、神皆具。“形”者生之舍,是爲軀殼;“氣”者生之充,乃充於軀殼之内者,是爲血氣;“神”者生之宰,則爲形氣之主宰,凡人之感官、美醜的審美、同異的認知、是非的道德判斷等,皆以“神”爲之主。故“精氣爲人”的内涵乃形、氣、神,而人者神有所繫,故爲貴。
近代學者徐復觀以爲:“《淮南子》中的道家們的特色,是把人的生命分成爲形、神、氣三部分,認爲有相互的影響,實際是承認了形與心有平等的價值;這可能是受了《吕氏春秋》重生貴生的影響,而加以折衷的。他們所説的形,指的五官百體;所謂神,即是精神,即是心的作用,也即是心;所謂氣,他們有時稱爲‘志氣’、‘血氣’,而以‘血氣’最爲恰當。”(13)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版,第239頁。《原道訓》論人、物之生以氣化角度論之,元氣之精者造化爲人,元氣之煩者化爲蟲魚鳥獸,人之精氣内涵爲形、氣、神兼具,故能感知判斷,蟲魚鳥獸之煩氣内涵則徒具形、氣,只能感知利害,不能判斷是非,故人之貴在守其形、氣、神而不失。人當慎守其形、氣、神而不失,所謂“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俯仰”(14)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原道訓》,第42頁。爲《原道訓》追求的天人理想。
“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於外,萬物恬漠以愉静,攙搶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遊,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於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遊,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15)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俶真訓》,第48—49頁。《俶真訓》謂上古人民“神氣不蕩於外”,乃能交感於天地之和德,故上位者治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不施刑罰,仁義禮樂不必行,天下自然賓服,萬物自然繁茂,是謂大治。《老子》云:“不尚賢,使民不争;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虚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16)高明《帛書老子校注》,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235頁。老子主張在心靈境界的修養上,要人不争、不欲,回復無知無欲以至無爲之純樸。《俶真訓》亦是推崇這樣的理想,但不僅只是心靈修養之境,更有其具體内涵,不勞其形,以和其氣,以養其神,故能與道一體。
《淮南子》吸收莊子後學與《管子》氣化之説,主張天地萬物一氣而有别,人得“精氣”而生,禽獸草木得“煩氣”而生,萬物本一氣同源,此點在《莊子》中多有申論,但萬物既生之後其内涵爲何則無詳論。《淮南子》論人之内涵爲形、氣、神兼具,禽獸草木則唯形、氣而已,人能守其形氣神而不失,便能不失性而德全,此乃上古之人能仁義不行、賞罰不施之因,此可謂《淮南子》對《莊子》氣化成形思想的内涵闡發,亦是其禮學思想的理論基礎。
二、 衰世而禮生,今世則失禮義之本
《莊子·馬蹄》論禮樂之生,云:“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白玉不毁,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17)郭慶藩《莊子集釋·至樂》,第336頁。言上古至德,民樸自性,禮樂不用;聖人制禮樂仁義之道,民遂争於名利不止,是乃聖人之過。莊子後學對禮樂之生采否定批判態度,以爲禮樂之起乃屈折人身,扭曲人性,使民争利欺詐。《淮南子》對禮樂之生的看法則不盡相同。
(一) 衰世而禮生
“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遊。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毁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於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争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諝,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群居雜處而無别,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争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18)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本經訓》,第250—251頁。《本經訓》論上古同氣於天地,禮義不設,逮至衰世,人心機巧,禮樂乃起而救敗,此説重點: (1) “同氣於天地”乃氣化思想天地一氣的主張,上古人本形、氣、神兼具,人與天地同德同樸,渾然同化,無須慶賞刑罰,禮義不設。(2) 衰世人衆財寡,無以爲養,故忿争乃生,民懷機巧,乃有仁義之生;男女雜處,民相淫樂,乃有禮樂之防。仁義禮樂的産生,乃爲救治衰世人心而起。(3) 《本經訓》肯定仁義禮樂在衰世的作用,雖然仁義禮樂比不上太古人心之樸,但卻是衰世不得已的救敗之方。
《本經訓》對仁義禮樂之起的看法,不同於《莊子·馬蹄》以制仁義禮樂乃聖人之過的强烈否定説法,人心不古的禍首乃是衰世之生,是因時代演進,衍生人口增加而生産不足的問題。《本經訓》認爲衰世之生才是人心不古的禍源,仁義禮樂乃因應衰世人心而生,不得不有。其論仁義禮樂之産生與莊子後學已有顯著不同。
“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19)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謬稱訓》,第319頁。《謬稱訓》由上世、中世、末世論道、德、仁、義之内涵:“道”爲最高主體,上世之人體道;“德”乃人性之内涵,中世之人守德;“仁”爲人心之積恩,施恩之所積;“義”乃群、己之所適行。上古之民體道純樸,中世之民守德不失,末世之民乃以仁義與嗜欲之别區分君子、小人。
《老子》通行本三十八章:“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20)高明《帛書老子校注》,第4頁。學者陳鼓應先生以爲:“三十八章有二層重要的意義,一是在於描繪道家行仁爲義要合乎人性之自然,如‘鳥行而無彰’,不必大事喧嘩,如‘擊鼓而求亡子’;其次是作爲世界本原的‘道’藴含着一切生機,‘仁’、‘義’、‘禮’皆共同地根源於孕育它們的母體‘道’之中,意即道德與仁義禮之間具有一種連鎖的關係,一旦根源的母體發生失離的情況,就會産生環環相扣的連鎖反應,此即所謂‘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21)陳鼓應《先秦道家之禮觀》,《漢學研究》第18卷第1期,2000年6月,第5頁。《謬稱訓》對道、德、仁、義的詮釋也有類似看法,“道”對“體”而言,“德”對“性”而言,“仁”對“積恩之行”而言,“義”對“人心、事理”而言,故道、德、仁、義非層層下落的關係,道、德、仁、義實是同質異層的關係。上世之人與道同化,中世之人守德施仁爲貴,末世之人則堅守仁義而不敢失,故道、德、仁、義實是因時代演進所造成的偏向所致,道、德、仁、義的本質没變,是人心隨時代而有所偏狹,道、德、仁、義實是由於時代人心的變異,不得已的自守與因應。
《本經訓》與《謬稱訓》對仁義禮樂的看法相近,即仁義禮樂的産生不是敗壞人心的禍源,人類文明的日益演進,才是造成人心衰敗的原因,仁義禮樂乃應衰世之人心而設,乃是救敗之方,爲通達大道之治不得已的途徑,這樣看待仁義禮樂的角度,與戰國晚期莊子後學實有很大的差異。
(二) 今世則失禮義之本
“夫禮者,所以别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搆而多責。……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毁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緌,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楗,抽箕踰備之姦;有詭文繁繡,弱緆羅紈,必有菅屩跐踦,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22)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齊俗訓》,第343頁。《齊俗訓》分古之民,禮義之生,今世之禮三階段: 古之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民樸而美;後世禮義之生,雖有曾參、孝己之孝,亦有盜跖、莊蹻之邪;今世之禮更失禮義之本,以至“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齊俗訓》雖亦有上古爲貴的主張,但亦肯定“禮者,所以别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等禮義對社會人倫的規範作用,此與《本經訓》《謬稱訓》對禮義之生的看法基本一致。
《齊俗訓》論“禮”上古無所用、中古以規範人倫,與《本經訓》《謬稱訓》主張相同。唯《齊俗訓》特别點出“今世之禮”的問題,上古乃至德之世,中世、衰世不得已而用禮義,今世更甚,君臣相非,骨肉相怨,連禮義之本都守不住。《齊俗訓》主張今世當先回復禮義之本,先恢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禮,再進一步回歸上古之樸,對禮義的看法較《本經訓》《謬稱訓》對禮義的肯定表現更積極。
比較《淮南子》與《莊子》對禮樂之生的看法,莊子後學對禮樂采批判否定的態度,禮樂之生,聖人之起,是造成人心争利、欺詐横行的禍源,主張要回復上古之樸。但《淮南子》對禮樂之生看法不同,雖然《淮南子》也認同上古是至德之世,無所用禮,但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争生”,遂有禮樂之起,以規範君臣、父子、夫婦之序,此或《淮南子》因應時代的需要而有的務實態度。
三、 對儒家之禮的批判(一) 禮因時地而制
孔子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2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9頁。孔子主張夏商周三代之禮有其損益,但又言繼周者百世可知,損益者自有其特殊性,但對百世而言,孔子更强調三代禮樂文化的一貫性與永恒性,故孔子乃有“從周”之意(24)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第65頁。。儒家面對春秋禮崩樂壞的局勢,主張要回復周禮的本質與永恒性,回復周禮以重建人倫秩序。
對於莊子及其後學,天道才是永恒,禮樂之道乃人心之亂源,不可以爲常道。《莊子·秋水》云:“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湯、武争而王,白公争而滅。由此觀之,争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 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25)郭慶藩《莊子集釋·秋水》,第580頁。《莊子·秋水》言天地萬物殊技、殊器,以何爲正?政治上堯、舜、湯、武,或争或讓,乃順其時之所爲,非可以視爲天下之常道。帝王非皆以禪讓爲正,三代亦莫有傳承之意,唯有“當其時,順其俗”而已,莊子後學對儒家倡禪讓政治與三代之禮持批判態度。《天運》篇云:“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26)郭慶藩《莊子集釋·天運》,第514頁。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皆異,皆可使天下大治,故禮義法度本順時而爲、應時而變之價值觀。
《淮南子》之禮學主張亦有此意:“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用槨,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於闇,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27)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泛論訓》,第423—426頁。《泛論訓》藉夏商周三代殯禮、葬禮、祭禮及用樂的不同,呈現三代禮樂的差異性,主張“禮無定制,因時而變”,禮樂没有永恒性,只有因時而制宜的特殊性,此亦從時代變遷來呈現禮樂的變動性。《齊俗訓》云:“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遷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28)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齊俗訓》,第359—361頁。《齊俗訓》主“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泛論訓》主“因時變而制禮樂”,皆與莊子後學《秋水》《天運》主張禮制應時而變的看法一致。
“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勾踐劗髪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髪,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内。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29)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齊俗訓》,第355—356頁。《齊俗訓》主張禮樂因時而生,也因地而異,以魯國行孔子之道卻日衰;越王勾踐無儒服,無禮容,卻霸天下;胡貉匈奴蠻夷之國,國亦不亡;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天下;晉文君大布之衣,威立海内諸例,證鄒魯之禮非唯一之禮,此乃要打破儒家以鄒魯之禮爲宗的主張。《莊子》中未見以鄒魯之禮爲批判對象(30)《莊子》中論鄒魯之士,唯見於《天下》篇,其云:“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郭慶藩《莊子集釋·天下》,第1067頁)可知對鄒魯之士並無批判之意。,其批評多針對儒家禮樂拘泥形式與違背天性而發。《泛論訓》主張“禮,因時而制”,强調五帝異道、三王殊事,禮當因時而制,不可拘泥於傳統,可謂承莊子後學所論。《齊俗訓》“禮,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反對禮的地域局限性,主張禮不僅要因時而制,更當因地而設,不必拘守以鄒魯之禮爲正,可謂針對儒家之禮的進一步批判。
(二) 三年之喪,以僞輔情
莊子後學對儒家之禮的批判,多針對儒家之禮的虚僞而發。如《漁父》篇所云:“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31)郭慶藩《莊子集釋·漁父》,第1032頁。莊子後學强調“貴真”,“法天貴真”乃其重要的價值觀,“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發乎真情乃能動人。而儒家之禮已淪爲世俗之强制規範,婚禮當具六禮之備,喪禮更有居喪之禁,守三年之喪,最爲莊子後學所詬病,所謂强哭不哀,强怒不威,强親不和,以其不真也,非發乎性情之真也。陳鼓應先生指出:“莊子後學對禮文發出不少强烈的批判,這反映了戰國晚期禮崩樂壞的情況日愈嚴重,而部分儒者推行‘世俗之禮’,外化而至異化的情況越來越突出,即連荀子也對儒家陣容中的‘俗儒’、‘賤儒’發出强烈的指責,可見莊子後學的激烈言辭,並非無的放矢。”(32)陳鼓應《先秦道家之禮觀》,《漢學研究》第18卷第1期,第12頁。此正説明彼之時代背景。
《淮南子·齊俗訓》云:“夫三年之喪,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絶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强人之所不能爲,不絶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33)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齊俗訓》,第356頁。强制性規定“三年之喪”不考慮個别性,是强人之所難,乃“以僞輔情”,遂主張悲哀當發於真情,葬親當稱於個人之財力。儒家主厚葬久喪,墨家主薄葬,皆違背人情之實,乃矯情虚僞之行。
《齊俗訓》並非反對“禮”或“三年之喪”,它批判的是“僞”,主張的是“情”與“稱”。“情”對人性言,“稱”對個人財力言,故《齊俗訓》主張的是禮當發乎真情,儀節器物上要量力而爲,相稱個人的情況而爲,批判的是矯俗干名,繁文縟節,奢華鋪張的虚榮與虚僞。
《淮南子》諸篇對儒家之禮的批判,多承襲莊子後學而來,反對禮的永恒性,主張禮爲一時之制,當因時而異,也主張當尊重各地的特殊性,不當以鄒魯之禮爲正,最重要者是,禮當本乎真心,發乎天性,不要强人之所難,違背人性而虚僞。對儒家之禮的批判,《淮南子》諸篇與莊子後學是一致的。
四、 因性制禮,化民返性
(一) 禮樂必有其質,乃爲之文
《莊子·大宗師》論子桑户的喪禮云:“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屍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34)郭慶藩《莊子集釋·大宗師》,第264—267頁。此段與《莊子·至樂》莊妻死,莊子鼓盆而歌稍不同(35)“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郭慶藩《莊子集釋》,第614—615頁。,莊妻一段直接論氣化思想來消解喪妻之哀情,此段則加上“禮”之角度論生死之義。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爲友,子桑户死,另二人卻相和而歌,此與莊子鼓盆而歌同,皆是就天道氣化義而言,莊子言氣聚爲生,氣散爲死,生死如四時,乃自然之行,故不悲而歌;此言“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桑户雖死,實則返歸造化之真,子貢以禮責之,二人卻斥子貢“惡知禮意”,故孟子反、子琴張主張當知造化之情,順生命之自然生死,不强爲世俗之禮,才是真知禮意者,乃以“順”與“真”作爲禮之内涵。
學者劉豐以爲:“莊子這裏所説的‘禮意’,雖然看似超越了人的日常之情,是‘無情’,但莊子的本意是與儒家的‘世俗之禮’對比,因此放在莊子的思想中來看,這實際上是一種擺脱了各種外在的束縛,是人的真實情感流露的自然之禮。”(36)劉豐《先秦禮學思想與社會的整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頁。《淮南子·本經訓》云:“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静。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干戚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37)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本經訓》,第265—266頁。此從人之本性切入,人喜則歌舞,憂戚則悲,氣激則怒,動其心性自然手舞足蹈,禮樂遂因應而生,所謂“必有其質,乃爲之文”,禮樂乃爲表現人性中的喜、怒、哀、樂而産生,故禮樂本於人性。“質”指人性之喜怒哀怒,“文”指鐘鼓管簫之儀節。故禮樂的表現不徒然只是形式,或虚應故事,禮樂的表現必有來自人性之真性情爲基礎。《本經訓》反對的是無其質而徒具其文的禮樂形式。
“夫三年之喪,非强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絶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欲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胷,思心盡亡,被衰戴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38)同上,第266—267頁。“三年之喪”乃孝子爲父母守三年之喪,《本經訓》强調“三年之喪”非强而致之的虚文禮制,此禮制的背後乃本之於人性“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絶也”的真情流露,此乃人性之自然。反對的是末世風俗敗壞,披麻帶孝,卻戲笑其中的虚應禮俗。儒家三年之喪的禮制,本建立在孝親之心的道德基礎上,亦非虚應故事而設。《本經訓》論喪親而哀乃本人性,喪親之哀必然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此乃人性之自然,故禮的本質來自於人性。
《主術訓》同申此意:“故古之爲金石管弦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絰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此皆有充於内而成像於外。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唇沸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胄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39)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主術訓》,第305—307頁。《主術訓》主樂、怒、效善、諭哀本爲人性之質,遂有金石、兵革、觴酌、酬酢、哭泣之節,實因“充於内而成像於外”,即人性之自然舒發於外的表現。至於亂世之主,取民無度,求民無厭,遂使民不得其生,君臣相疾;更進一步人君追逐感官享樂,民苦不堪言,禮而無禮,樂而不樂,遂使本發於人性内在喜樂之情的“禮樂”流於感官逸樂,乃失禮樂之本。陳鼓應先生以爲:“莊子後學對禮的態度約可分爲三類: 一是抒發個人的真情實感,《大宗師》‘返真’的人生觀發展至外、雜篇任情放性的‘貴真’説,《駢拇》及《漁父》等篇可爲其代表;二是安於所行、釋然忘懷,由《大宗師》‘坐忘’的心境到《天運》談至仁、孝親之行止臻於忘境,及《山木》描述‘建國之德’,人們舉手投足自然適然地合於禮儀,這是道德行爲最高境界的寫照;三是落實到現實人間,肯定人倫道德社會作用的走向,而《天運》提出‘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的主張爲其代表。”(40)陳鼓應《先秦道家之禮觀》,《漢學研究》第18卷第1期,第14頁。
莊子後學論莊周妻死鼓盆而歌,論子桑户死,二友臨屍而歌,可看出莊子後學乃據氣化天道之理,以超越知解,消解人情之哀。但《淮南子》論禮樂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則落實在人性之喜怒哀樂自然而發處論,三年之喪思慕之心自不能絶,自然聽樂不樂,食旨不甘,喜、怒、效善、諭哀之情本自於人性,此皆心之所感而發乎性情,是爲禮樂之質。可見《淮南子》論禮樂本質之説較近於《大宗師》《駢拇》及《漁父》一系,乃以真情實感“貴真”爲主,批判晚世風俗衰敗,禮義廢弛,思慕之心盡亡,披麻而戲笑其間,失禮樂之本。
(二) 禮者,因民之所好而節之
《莊子·天運》云:“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41)郭慶藩《莊子集釋·天運》,第514頁。肯定禮義法度應時而變,對人倫社會的作用,但莊子及後學未論及本於真情實感的禮意究竟要如何建立禮樂的具體問題。《淮南子·泰族訓》云:“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斫,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窬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自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42)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泰族訓》,第670頁。《泰族訓》論“禮樂”之起,首論當順金、木之性以冶、斫乃可行;再論當順馬、牛、雞、狗之性,乃可服駕馭、司晨、看守之功;最後論民之性有好色之性、飲食之性、喜樂之性、悲哀之性,故先王順應人性以制禮樂之法,因好色而制婚姻之禮,因飲食而制宴饗之禮,因喜樂而制鐘鼓之樂,因悲哀而制喪祭之儀,皆本於人性,而由聖人所匠成。
《荀子·禮論》云:“禮起於何也?曰: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争;争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43)王先謙《荀子集解·禮論》,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46頁。荀子言禮樂本於人欲之求而節制之,唯荀子之性乃食色之性,荀子之禮乃針對食色之性的節制而設。
但《泰族訓》“性”的内涵卻不盡相同:“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44)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泰族訓》,第671頁。此論“禮”本於人性之自然,人性之自然内涵有仁義之資,又有好色之性、飲食之性、喜樂之性、悲哀之性,可謂雜糅各家人性之説,既有儒家之道德性,也有道家之性情説,實則爲人性之實然面。特别的是《泰族訓》主張道家的人性自然説,卻也認可人性有仁義内涵,也接納儒家教育思想,强調須待學、待教化乃得成其禮樂之行,其人性主張甚具特色。
《泰族訓》論禮的建立乃順應民性之所好而有所節制的表現,言“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順男女好色之情乃制婚姻之禮,使男女不淫而有别;順好音之性而制《雅》、《頌》之聲,使風俗不亂;順人寧家室、好交友之性,乃制父子之親、長幼之禮,使人倫有序而不亂。
孔、孟論禮之來源於仁心,人性之善端,其弊端則流爲矯情虚僞;荀子論禮之源於人欲之節制,故重外在人倫之規範以節制(45)王先謙《荀子集解·禮論》,第346頁。,其弊端則流於强制。《泰族訓》論禮源於人之情性,故其貴真,但順應情性,卻也主張要合理節制與安排,以防止放蕩爲亂之弊,此乃《泰族訓》論禮之特色。學者徐復觀以爲:“因民之性以制禮作樂的思想,大概在戰國中期以後才發展出來的。此一思想的重要性,在於把禮起源於適應封建政治要求的歷史根據完全淘汰,而認定適應人性的傾向、要求,才是禮的起源,才是禮的意義,這便使禮從原來的封建統治的束縛中完全突破了出來,使其成爲集體社會中所共同需要的行爲規範。”(46)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271頁。徐氏由封建政治的禮樂文化發展,論《淮南子》由“因”以論“禮”起源的歷史意義。筆者以爲從道家禮樂思想的發展而言,此説亦有其意義,即道家對“禮”的議題,不再只是站在批判的立場反對儒家之禮,而是提出有道家思想内涵的禮樂主張,非固守三代之禮,非拘泥鄒魯之禮,乃本於人性之自然之禮,禮要因民之性,要依據人性而設,才能避免强人所難、矯情虚僞之弊病。但順應民性不代表任性放縱,同樣需要透過學習與教育而知有所節制,亦有其規範當遵守,此乃《淮南子》所認同的禮樂義。故《淮南子》不再如莊子後學只是批判禮文之縟節與虚僞,它要重建一代新的禮樂文化,此乃《淮南子》論禮“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的重要意義。
(三) 參五以制禮,化民返性
“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别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47)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泰族訓》,第671—672頁。此合天、地、人以論治世之綱紀,“參者”天、地、人,“五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泰族訓》治國之道的内容與其宇宙氣化觀的主張一致,天地由一氣生生爲陰陽五行,順四時以生人與萬物,煩氣爲蟲,精氣爲人。下落於人世,乃由人以上達天地之道,聖人治國亦當考其天時陰陽之變,察其地利水澤之宜。值得注意者,人德的部分乃爲民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利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禮樂仁義之道乃因民之性而節之制,使民能除暴亂以移風易俗,以達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效。
老子論“無爲而治”云:“聖人之治,虚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48)高明《帛書老子校注》,第237頁。老子强調個人修身寡欲使民無知無欲的無爲理念。《本經訓》云:“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静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憺然無爲而民自樸,無禨祥而民不夭,不忿争而養足,兼包海内,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49)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本經訓》,第252頁。合心與神,形與性的協調;静而體會天地之道,動而順應事物之理,回歸自然之性情,進而能無爲而使民自樸自化,此可謂承老子“無爲而治”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泰族訓》用“參”、“五”以蒞政施教,以天、地、人爲懷,以君臣、夫婦、父子、長幼、朋友之倫的建立作爲施政綱領,以移風易俗,化民遷善,使民復天性之自然,以爲治世之方。《泰族訓》豐富老子無爲而治的内涵,除延續老子聖人的修養功夫,更强調聖人在天人關係上的一體性,此外也主張合天地人之道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由五行之性以立父子之親,由五音之别以立君臣之義,由四時之序以立長幼之禮,故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乃合天人之道以發乎人德而成者,此爲道家義的禮樂思想,爲化民成俗,落實無爲而治的理想,增進實踐上的可行性。
“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遊心於虚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攓性,内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蟯振繾物之豪芒,摇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爲也。”(50)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俶真訓》,第67頁。《俶真訓》論“學”有三種類型: 聖人之學,達人之學,俗世之學。聖人之學返性於太古,逍遥於虚心。達人之學通達於本性,無所羈絆。俗世之學勞苦耳目感官,逐物逞名於世,是以羞而不爲。《俶真訓》論學之目的在“返性”、“通性”,勿追逐名物以愁勞感官五臟,當回歸本性之初心。
老子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51)高明《帛書老子校注》,第314頁。,“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52)同上,第370頁。。反對人爲聖智之弊,主張回歸素樸之心。此回復“素樸之心”,正是《俶真訓》主張“返性”的人性本質,此乃道家思想重要修養論理據。莊子云:“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人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53)郭慶藩《莊子集釋·刻意》,第546頁。莊子提出“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的修養功夫,進一步説明人之返性需“貴精守神”,保養精與神而不失,正是回歸人性素樸的修養内涵。
《淮南子》合“參”以制“五”的禮學思想,主張制訂一套合於天地人之道的禮樂制度,此禮樂制度立基於人性之所好,卻也要有所節制與安排。所謂:“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54)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泰族訓》,第671頁。故《淮南子》主張要“學”與“教”(55)“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同上,第671—672頁。,但學習的不是詩書禮樂之經,學的目標是“返性於初”,是回歸初心之樸,即是順應情性與節制性情的禮樂之道。此可説是《淮南子》對老莊“無爲而治”思想的重大進展。
結 論
《淮南子》氣化思想深受莊子後學《至樂》《知北遊》諸篇與《管子》“精氣説”影響,主張天地一氣,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死生如四時之自然,又主“煩氣爲蟲,精氣爲人”,人禽氣化同源而又有别,故人之貴在保神、氣、形而不蕩於外,乃可體道而德全。《淮南子》吸收氣化思想以詮釋道家“復歸於樸”(56)“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溪。爲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高明《帛書老子校注》,第369頁。的主張,乃以保全形、氣、神不失詮釋“樸”的内涵。“樸”由先秦道家的心靈境界轉爲保全形、氣與神的修養功夫,顯得更具體可行。
天地一氣的氣化思想乃《淮南子》禮學思想的根據。上古之世體道而德全,至於衰世人心敗壞,禮樂乃生,故禮樂之生乃返性於初而設,透過禮樂的制定與節制,希冀回復上古人心之樸。陳鼓應先生以爲禮、法“同出”於道,視禮、法爲道的衍生物,從而倡導法治與禮義教化相互爲用。這裏展現出黄老經世的雄心,爲要掌握時代的脈動而推動社會改革(即所謂“時變”),遂在以道爲依歸的前提下,把作爲權衡準則的道通過禮法而落實到現實社會的層面(57)陳鼓應《先秦道家之禮觀》,《漢學研究》第18卷第1期,第18頁。。此正説明《淮南子》禮學主張的時代意義。
《淮南子》對《莊子》論禮思想上的闡發,有幾點特色:
(1) 《淮南子》對《莊子·馬蹄》所論上古至德,無所用禮,無欲素樸,至於後世,聖人制禮,天下始分,故毁道德以爲禮義,乃聖人之過的主張不盡認同。《淮南子》認爲人心不古,並非禮義之過,而是衰世人衆財寡,風俗衰敗所致,禮樂仁義之道乃爲維繫衰世人倫秩序不得已的手段。《謬稱訓》分上世、中世、末世三期。上古人心純樸,無所用禮。中世、衰世人心日詐,遂有“禮”之産生。今世之禮其況尤下,君臣相非,父子相怨,大失禮本。《淮南子》認同上古之世無所用禮,但在衰世、今世卻不否定禮的價值,甚至認爲要先回復禮樂之本,乃得返性於初,這點與莊子後學對禮樂之生的看法有很大不同。
(2) 老子、莊子及其後學皆對儒家禮樂儀節的虚僞矯情采批判態度,對儒家禮文的虚矯,《淮南子》是延續莊子後學之態度的,認爲禮樂制度乃因時而制,因地而設,不當拘守三代之禮,不當拘執鄒魯之禮,三年之喪當發乎真情,當稱人之力而爲,不當强人所不及,這是一致的。
(3) 《淮南子》較莊子及其後學在禮樂思想的進展上較具特色的一點是,莊子及其後學批判儒家禮樂之僞,雖然也省思禮的本質,所謂“禮意”的問題,但並没有再進一步提出屬於莊學的禮樂主張。《淮南子》在這一點上提出因性制禮、化民返性的主張,實深具意義。《淮南子》批判儒家禮文之僞,主張禮樂當發乎真情,當出自人性,道家肯定人性的自然面,《淮南子》亦主人性的自然面,並以人性的自然面來會通禮樂之道,主張要順應民之所性而制禮樂。人性的内涵有喜怒哀樂,有好色之性、有飲食之性、有喜樂之性、有悲哀之性,亦有仁義之性,故《淮南子》主張禮樂之制當順應民性,而又有所節制,順好色之性而制婚禮,順飲食之性而制大饗之儀,順喜樂之性而制鐘鼓之樂,有悲哀之性而制哭踊之節,所謂“因民之所好而節之”(58)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泰族訓》,第670頁。。故人君當體察天地人之道,以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禮,分職以治,分財以衣食,立學校以教,使民順性而知節以好禮,以化民成俗,返性於初,所謂“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59)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本經訓》,第252頁。。《淮南子》制禮樂乃是要使衰世之民能返性於初,以回歸於“樸”。故《淮南子》仍是延續先秦道家返樸理想,《淮南子》收攝禮樂思想實則是化民返性的一種途徑。回歸天地一氣的天道人德,仍是《淮南子》的最高理想。此乃《淮南子》禮樂思想特色。
由《淮南子》諸篇對《莊子》在禮學思想方面的闡發觀察,可以看出戰國以來至於漢初道家思想發展的幾個趨向: (一) 吸收氣化思想以落實道體的掌握,原始道家無形抽象的天道本體,漢初轉向於形、氣、神的存養不失而越見落實。學者陳德和以爲:“相較於原始道家的立場,稷下黄老道家由於受自古以來論氣的傳統和同爲稷下一系的陰陽家思想的影響,氣概念被引入形上道體的思維中,於是精氣成爲道的同義詞,道之客觀實有義於焉確然不可移,而《淮南子》的道概念又是承繼稷下黄老道家精氣説的思考,當然它的道概念必是屬於客觀實有的認知,也必然會有‘道即是氣’的主張。道概念在原始道家如老子《道德經》中本來是以‘無’立宗的,到了稷下黄老和淮南由於氣概念的介入,乃變成以‘有’爲核心,‘無’只成了對‘絶對大有’之無形色、無古今、無方所、無意志的一種總持的形容而已,這種改造無乃是原始道家的變型與轉化。”(60)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第102頁。此正説明《淮南子》道氣思想對原始道家的轉化意義。(二) 對禮樂之道的産生,由否定批判轉向認同,進而吸收其説,以説明其乃衰世不得已的過渡階段,轉向務實態度。(三) 對儒家禮樂思想的看法主要爲虚僞矯情,强人所難,但不反對發自人性的規範,並進一步思考禮樂的本質,提出人性的本質,才是禮樂真正的内涵。(四) 《淮南子》提出因性制禮、參五之道以制禮,乃道家思想在禮樂主張上的重要進展,道家思想發展至漢初,在禮樂的議題上,不再只是反對者的立場,《淮南子》所提的禮學主張正有别於儒家禮樂主張,而代表道家思想的禮樂主張,有其重大學術意義。惜乎,隨着淮南謀反一案及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歷史發展,此種主張後遂湮没於歷史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