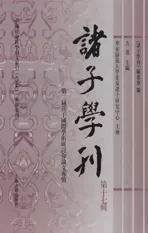《莊子》外雜篇中的黄老理論
2018-01-23臺灣陳麗桂
(臺灣) 陳麗桂
内容提要 黄老以其强大的滲透力與輻射能量,使莊子後學的思想也無可避免地受其影響,依於老、莊的觀點,去談政道、論生化、理形神,也交融他家思想。他們以虚静無爲爲帝道、聖道的最高原則與境界,卻崇功尚用、重時變,姑捨萬物平等的“齊物”觀,去定上下、别君臣、分主從、列尊卑、講刑名,也求用,並有限度地容許仁義,也談氣,兼論形神的一致健全,搭上了黄老的時代列車。唯在論這些理論的同時,更多的是對虚静、無爲、寂寞、恬淡的一再推崇與叮囑。在正向界定仁義的性質與功能的同時,更大程度提醒,過度强調仁義將殘性裂德。它以“氣”爲萬物生化的基元,也瞭解“神”賴“形”之運作而健全、靈妙的道理,卻始終大量正面地强調“心”、“神”爲主的觀念,審慎、保守地涉及對身形的關切。
[關鍵詞] 莊子外雜篇 黄老 天 道 德 仁義 氣化 時變 形神
有關《莊子》外雜篇中所呈現的後期道家理論,歷來學者推斷内中多黄老思想,尤其是《天地》《天道》《天運》《在宥》《刻意》《知北遊》各篇中的氣化觀、外王論與養生論。與此同時,學者卻也認爲,在這些與内七篇思維不完全一致的外雜篇黄老訊息中,其實也仍和其餘各篇的理論思想,維持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1)參見蕭裕民《〈莊子〉内外雜篇新論——從思想的一致性來觀察》,《興大人文學報》第三十六期,第159—186頁,2006年3月版,第159—184頁。。换言之,整部《莊子》,雖非一時一人之作,然既被匯集在一起,思想上仍有相當的一致性,其間的異同依違情況如何,有待細部釐清。
外雜各篇部分内容之所以被推定爲黄老思想理論,主要是它們談到外王問題、氣化萬物與養生問題,這些問題都是《莊子》内七篇所不重視的,卻爲戰國以下黄老思想的幾大核心問題。
一、 黄老思想的核心議題
要釐清《莊子》外雜篇中的黄老訊息,必須先瞭解黄老思想的核心課題。根據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對黄老思想議題的提挈,參看馬王堆出土黄老帛書,以及戰國秦漢之間各黄老相關典籍文獻中的理論内容,可以清楚提挈出黄老思想的基本特質(2)這些黄老文獻與典籍包括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經法》等多篇黄老帛書、《管子》四篇、《韓非子·解老》《喻老》與《荀子·解蔽》,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中的黄老理論,乃至於董仲舒《春秋繁露·基義》《玄元神》《離合根》《循天之道》中的黄老理論,個人已於《戰國時期的黄老思想》《秦漢時期的黄老思想》乃至於《黄老思想通論》中細部討論過,兹不贅述。:
(一) 外王的目的與功能。
(二) 兼融各家: 陰陽、儒、墨、名、法皆所參采。儒、法、陰陽都被吸納進黄老道家虚静無爲的君術中。
(三) 因天道以論治身、治國之道。
(四) “氣”化、“術”化《老子》的道,去論證治身、治事、治國之理。其“氣”多轉指“精氣”,其“術”主要指“静因”與“刑名”。
(五) 爲了實際操作的效用與功能,它們也重“時”變。
就(一)而言,黄老思想緣起於田齊政權的造祖運動與政權漂白,先天上其有崇功尚用的外王目的與功能。就(二)而言,那是黄老發源地——稷下學術的普遍特質。就(三)而言,它雖以《老子》學説爲核心素材,推崇“虚静無爲”,治身與治國並論,卻都一本于《老子》的基本教義,以“道”爲治身、治國的依據,由自然之道去推衍治身養生之理與治國統御之道,視自然天道、人事政道、養生之道爲一理相通,可以仿效取法。儒、法各家都被吸收進道家虚静無爲的君術中。就(四)而言,在治國的政道上,他們以虚無的“静因”之理與具體的“刑名”方案,去“術”化《老子》的“道”,成爲可以操作且重“時變”的“君綱”。它的統御之“道”因此不是玄虚不可捉摸的形上思維,而是可以依循操作、切實把握的要領與原則。在治身養生方面,它以“氣”去詮釋替代《老子》的“道”,圍繞着《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生萬物”的命題,開展出戰國以下的氣化宇宙論,從而突破老莊貴神賤形、養神遺形的傳統,推衍形神並重兼養的精氣養生説。它的道生萬物因此是氣化萬物。人的形神和萬物一樣,都是天地一氣之化生,特其生“氣”之品質優於它類,或稱“精氣”或“精”。養人之形、神,因此須由“精”或“精氣”着手,形、神兼養。相較於《莊子》内七篇的輕“形”觀點,外雜篇中多了“氣”的生成説與“形”的關注。而不論是“術”化的“道”或“氣”化的“道”,都明顯下降入天地之間,“天地”大於“道”。
總之,静因、刑名的君術與氣化生成、精氣養生之説,加上儒、道、法兼糅的理論内容,都是黄老典型而明顯的標記。檢索《莊子》外雜篇的黄老成色與訊息,可以從這些地方去查索。
二、 外雜篇中的黄老論述
今檢閲上述各載有黄老相關理論的篇章内容,可以清楚看到(3)本文所引《莊子》各篇内容悉依郭慶藩《莊子集釋》,(臺灣)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版,下文所引但標頁碼。:
《在宥》基本上以“堯舜治天下”爲苦情鉗性之事,以仁義爲攖擾人心,認爲“絶聖棄智”,天下大治,傾向“無君”、反治觀點。唯亦接受若“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只有“無爲”,而後才能“安其性命之情”。换言之,對於外王,《在宥》作者認爲,只有“貴身”,愛身的人,才可以寄托天下,因爲只有貴身、愛身的人,才懂得以“安性命之情”去治天下。全篇大致遵循道家清浄、無爲、重生、貴身、全性的觀點去論“治”。但與此同時,卻有兩小節論及情緒調養的形神問題;一節論及“道”及“天道”、“人道”一體的問題,卻以“天道”爲“無爲而尊”,“人道”爲“有爲而累”,並以“天道”擬“主”,“人道”擬“臣”,這三小節已是“黄老”的道法論。
《天地》全篇基本上以“道”爲恍惚玄冥之類的存在,反機心,反炫名聲,嚮往一種無君、無政、象惘、混蒙、聽物自爲、自然從化的理想狀態。它所推崇的“德人”是去思慮、泯是非、率任自然;“神人”則是渾沌未開的混冥淡實、任真樸素。它藉諄芒對苑風的論述,所提出的理想管理,亦即所謂的“聖治”,是各業各人自行其是,自然而化。其中除了“聖治”,基本上都存留了相當高程度的老莊風教。
《天道》在各篇當中保留黄老理論較多,它開宗明義便串天道、帝道、聖道爲一理相通,標榜一種虚静、無爲、寂寞、恬淡的管理模式,稱爲“天德”、“天樂”,説“帝道”當仿“天道”。又清楚定位君臣、上下、本末、先後之尊卑順序,顯示了人倫與政倫的次序,推崇“古之明大道者”的“聖治”,畫定了天地、道法、仁義、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賞罰的先後位秩,以虚静無爲爲“上畜下”之道,形名、禮法、度數爲“下事上”之理,又退仁義,責禮樂,以賞罰爲末。
《天運》以“六極”、“五常”爲“天”之内容,帝治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對於仁義有相當的批駁。推崇一種“默默蕩蕩”、“乃不自得”,寂寥而超於視聽的自然之理,稱爲“至樂”、“至聲”;以“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達情遂命的境界爲“天樂”,既有黄老因天道以推政道的基本風格,卻又不脱去虚、沖漠的莊子情調。末了卻提出應時而變的法家與黄老新精神。本篇和《天道》一樣,是道、法融合材料最多、程度最深的一篇。
《刻意》以寂寞、恬淡、虚静、無爲爲天地之道與聖人之德的内容,卻有專節討論形神與情緒的調理問題。
《知北遊》推闡“道”無所不在之理,也涉及萬物之生死榮枯不過一“氣”之轉化,應爲中國氣化宇宙論之先驅。
從上述《天道》等各篇的内容看來,黄老的相關論述,主要集中於《天道》《天地》《天運》《繕形》各篇,《刻意》和《知北遊》則有專論氣化與形神的調理議題。但各篇一致通貫且反覆强調的,仍是恬和養性、虚静無爲、寂寞恬淡的天道與聖德,相當程度地保留了莊子式的淡遠氣質與風格。但從各篇中一定分量的黄老理論與素材中,仍可以看出,戰國時期由稷下學宫所引發的黄老學術輻射所及,在《莊子》外雜篇中所呈現的某些狀況:
(一) 它列序了“大道”内容的先後之次,依次是: 天→道德→仁義→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賞罰。並謂: 能循此事以治物、修身,則平治。這就是其所謂的“聖治”。
(二) 在這個列序中,“道德”仍應該是道家的“道德”,非儒家的“道德”,故儒家之“仁義”居次。“原省”應是推原省察之意。在這一系列中,“天”與“道德”是道家治事依據,“仁義”屬儒家教義,從“分守”到“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至“賞罰”,屬法家治政要項。依次由道而儒、而法,《天道》比列了其治事理政的高下層次與步驟,顯示了黄老以道爲上,兼儒、墨、名、法的基本模式。
(三) 在這個序列中,“天”是高於“道德”的,仁義也被納入了治道的要項中,列序尚在各法家要項之前。
以後到了《淮南子》列序更明白了,《主術》説政道的高下依次是:“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最下賞賢而罰暴。”所謂“神化”,就是精誠動化,指主政者透過心靈的精誠,去動化全天下,達到良好的治政效果。《莊子·漁父》曾載孔子問“何謂真”,客答以“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真在内者,神動於外”(4)郭慶藩《莊子集釋》,第1031—1032頁。。應是《淮南子·主術》之所本,是道家所嚮往的管理。“使不得爲非”應是儒墨正向的道德仁義教化。“賞賢而罰暴”則是法家以賞罰爲主的政道。《主術》對道、儒、法政治的先後列序與《莊子》中《漁父》《天地》篇相同。
(一) 天道治理一理相通
劉笑敢曾把《莊子》外雜篇的内容依質性不同,區分爲述莊派、黄老派與無君派三類。屬於“黄老派”的内容分見於《在宥》《天地》《天道》《天運》《刻意》《繕性》《天下》各篇,並謂其與内篇之關係是“同異參半”,其思想成分多了“融合儒法”(5)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61—78頁。。基本上都説中了《莊子》外雜篇的黄老質性,其實還包括了《知北遊》的氣化論和《庚桑楚》的形神觀。它們常常是站在内篇的基點上,去融合儒、法,益以戰國時期流行的氣化論與形、神觀,轉向了外王、入世的功能表述。然内篇“述莊”、“無君”的思想仍不時自性强烈地貫穿、牽繫於其中。《天地》和《天道》兩篇開宗明義就揭示了天道、治道一理相通,因天道以挹政道的思維,它們説: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天地》)(6)郭慶藩《莊子集釋》,第403頁。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静者矣。……夫虚静、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天道》)(7)同上,第457頁。
《天道》又假老聃之口論“天下”如何“無失其牧”,説: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8)同上。
上文揭示了幾個要點: (一) 治道與天道一理相通,治道源自天道。所謂“天道”之“常”,就是日月星辰的運行,樹木禽獸的生長活動。(二) 天道以成萬物,治道以“歸”天下、“服”海内。治道、帝道既源於天道,循天道以論治道,天道自然而必然,帝道、治道因此也就自然而必然,愜理以厭心。透過“天道”,肯定、保證了政道之必然,這就是《韓非子·大體》所説的“因道全法”。這和《莊子》内篇乃至外雜篇“無君”的觀點是很不同的。(三) 這天道、政道相通的一理就是“静”,就是“無爲”。這樣的觀點也是黄老的基本思維,馬王堆黄老帛書和《管子》四篇等黄老文獻中充滿了這類思維。
馬王堆黄老帛書《經法·道法》説:
天地有恒常,萬民有恒事,貴賤有恒立(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9)《帛書老子·黄帝四經》,(臺灣)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版,第194頁。
一切政道、人事之道的矩度,事實上正如天地之道一樣,都是有分寸可據,有軌則可循,也必須持守和依循。只不過《天地》《天道》篇所述天道、政道一理,只是一個總括性的説法。黄老帛書則較爲具體而明確地説出它的詳細内容,《經法·君正》説:
天有死生之時,國有死生之正(政)。(10)《帛書老子·黄帝四經》,第196頁。
《論》説:
天執一,明〔三,定〕二,建八正,行七法,然後〔施於四極,而四極〕之中無不〔聽命〕矣。歧(蚑)行喙息,扇蜚(飛)需(蠕)動,無〔不寧其心,而安其性,故而〕不失其常者,天之一也;天執一以明三,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月信生信〕死,進退有常,數之稽也;列星有數,而不失其行,信之稽也;天明三以定二,則壹晦壹明,〔壹陰壹陽,壹短壹長〕;天定二以建八正,則四時有度,動静有立(位),而外内有處。(11)同上,第202—203頁。
《論約》也説:
四時有度,天地之李(理)也;日月星晨(辰)有數,天地之紀也。三時成功,一時刑殺,天地之道也;四時而定,不爽不代(忒),常有法式,〔天地之理〕;一立一廢,一生一殺,四時代正,冬(終)而復始,〔人〕事之理也。逆順是守,功洫(溢)於天,故有死刑。功不及天,退而無名;功合於天,名乃大成。人事之理也。順則生,理則成,逆則死。(12)同上,第206頁。
這和前述《莊子·天道》所説: 天地有常,日月有明,星辰有列,禽獸有群,樹木有位的“天道”,要執政的“天子”當“仿德而行,循道而趨”,意思是一樣的,只是説得更豐富詳瞻。總之,人事上的禍福、存亡、興廢之理,和天地自然的生殺循環,是一理相應、緊密連結、息息相關的。依循天地自然的生殺循環去處理人事政務,便能稱心順手,這就是《莊子·天地》《天道》所謂“虚静”而“無爲”的“帝道”、“聖道”、“天道”、“天德”的詳細内容。《天地》因此藉諄芒之口,述“聖治”説:
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13)郭慶藩《莊子集釋》,第440頁。
换言之,一種主客合宜,用人得當,行事適切,施政輕鬆容易,順遂、平穩的人事與政事管理,叫做“聖治”,這是黄老所推崇的“虚静”而“無爲”的政治範式。
(二) 静而無爲,以用天下
《天道》説: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14)郭慶藩《莊子集釋》,第465頁。
這裏的“道德”當然是道家的“道德”,而非儒家的仁義、忠信。理想的帝王之治是循天地之道,無爲而治。這雖不合乎《莊子》的“無君”一系思想,至少不離《老子》以静勝躁、自然無爲的“聖人之治”。
值得注意的是: 不論“天道”、“帝道”還是“聖道”,雖然都以“静”而“無爲”爲核心之理,這“静”而“無爲”卻不是一無作爲,它是“運而無所積”,永不止滯,生生不息,《老子》所謂“週行而不殆”,是一種理想有效、自然恒久卻不勉强的運作。對於黄老這一式的“静”而“無爲”,作爲漢代集黄老理論大成的《淮南子》,在《脩務》中有很正面而直捷的詮釋,它説: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爲不然。……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15)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卷十九《脩務》,(臺灣)文史哲出版社翻印1985年9月再版,第33頁。
這就是黄老所推崇的“無爲”。“無爲”不是什麽事都不做,而是要求費力少而效果好,精簡有效的操作。表面上它“虚静”,似無作爲;事實上,它恒定運作,永不止息,只是依循自然之理,尊重事物客觀規律,以求四兩撥千斤,精簡有效的成果,不妄造作。
老、莊都不求用,至少不正面求用;《天道》卻説,“無爲”是要“用天下”、“爲天下用”,這是黄老崇功尚用的基本特質。
(三) 君本臣末,上下異道
緊接着“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之後,《天道》話鋒一轉,説:
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説也;能雖窮海内,不自爲也。天不産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 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 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16)郭慶藩《莊子集釋》,第465頁。
這就轉入了法家君上臣下、君臣異道、君静臣動、君逸臣勞、君無爲臣有爲的基本教義,與虚静因任的治事之則,這就是道、法結合,以求精簡有功的黄老“無爲”。整篇《天道》就在這種道、法糅合交論的表述中,開展其黄老之論。《天道》説: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17)同上,第467頁。
這幾乎就是法家君尊臣卑、君逸臣勞的同調表述。《天道》又説:
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18)同上,第471頁。
這裏顯示了三點:
(一) 偉大的政道極則是從自然的“天”中去逐次透過“道德”、“仁義”、“分次”、“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賞罰”等種種過程與手法去逐漸運作提煉起來的。
(二) 儘管君上臣下、君主臣從所采的是法家的政治架構,在儒、道、法三家思想價值的列序上,黄老的列序依然是先道,次儒,最後才是法。
(三) 只要透過道、儒、法的處理過程與手法,相信政治上,不論名位的安排還是才幹的識别,都能適切合宜,不多傷神費心,這叫“太平”,叫“至治”,這就是申不害、韓非所説的“因任而授官”。
(四) “天”、“德”、“道”的特殊列序——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天道》《天地》把天地之道與聖人之治、聖人之德畫上等號,顯示其所論之道,指的是在天地之間的現實世界裏操作的政道。黄老之“道”是求用的經世之道,當然必須落實在現實世界裏操作。因此,儘管因爲黄老思想源自老子,其“道”也源自老子,老子之“道”超越天地,生天生地,是“天地根”;黄老之“道”質性功能雖與之相同,位階卻常是落在天地間、時空中,這在戰國的黄老文獻中便已如此。《管子·心術上》説:
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道在天地之間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19)安井衡《管子纂詁》卷十三,《心術上》第三十六,(臺灣)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版,第4頁。
《内業》説:
道滿天下,普在民所……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20)安井衡《管子纂詁》卷十六,《内業》第四十九,第5頁。
説來説去,這個“其大無外”的“道”,終究只是“在天地間”、“滿天下”的天地之物。至於馬王堆黄老帛書裏所論的,不管是有律、有度、有則的“天道”,還是循天道而爲的刑名政道,基本上也都是由“天地既成”(《十大經》)以後開始講的,所有虚静因任的刑名之理、刑名之治,也都是爲了“執道者之觀於天下”(《經法·論約》《名理》)。因此,在黄老的經世之論中,“道”是“天地”間“道”,《莊子·天地》《天道》中的“道”,位階也經常如此呈現。《天道》説: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21)郭慶藩《莊子集釋》,第404頁。
《天道》序列“古之明大道者”的順序,以“天”爲第一序位,“道德”次之,“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道德爲主”也就可以理解了。《天下》同樣説“聖人”要:
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22)同上,第1066頁。
“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就是《天道》所謂“仿德而行,循道而趨”。聖人的治道要以“天”爲根源,以“德”爲基礎,以“道”爲關鍵,同時還要能掌握“變化”之機兆。這是黄老的思維,而非老、莊本旨。依照《老子》的序列,原是道——德——天(地);《老子》説“失道而後德”,《天道》卻以“天”爲“宗”,“德”爲“本”,“道”是事物變化的關鍵。這樣的“道”,顯然不是宇宙本源的自然之道,而是人事變化、運作、處理之治道,這就是黄老道和老莊道的重點歧分。
此外,在“聖人”、“聖治”的“天”、“德”、“道”之間,這幾篇黄老相關文獻中,總是相當一致地先“天”,次“德”,後“道”,“道”不只在“天”中、“天”後,更在“德”之後,這是《莊子》外雜篇各黄老篇章中一致的特殊列序,爲其他先秦黄老文獻之所未見。其他黄老文獻頂多是“道在天地間”,“道”在“天”之下,未聞在“德”後者。以“道”、“德”爲在“天地”之間,不論是“道”、“德”分稱,還是合稱,基本上都是黄老的思維;以“德”更在“道”先,則無論如何是《莊子》外雜篇的黄老論述所獨有。
更值得注意的是: 聖人之治除了宗“天”、本“德”、循“道”之外,還要兆見“變化”之機,知所應變,非只“虚静”而已。因爲《天道》説過,不論“天道”、“常道”、“聖道”都是“運而無所積”的,當然是“變動”不已的,自然能兆見“變化”之機。《天下》的説法和《天道》是一致的。
(五) 仁義的義涵與功能
在較早版本的郭店《老子》中,原本是看不到對仁、義的批駁與反對的,今本《老子》中都還有“動善時,與善仁”的論述。但到了《莊子》外雜篇,卻有大量剽剥儒墨仁義的論述,即使在上述充滿黄老理論的各篇章中亦然。郭店簡本《老子》的研究者多因此認爲,剽剥仁義是莊子外雜篇之事,非《老子》本旨。
1. 剽剥仁義
今檢視外雜篇這些被認定多黄老理論的篇章,大致也如此,推闡虚静無爲與否定仁義幾乎是各篇必然一提的公論。
《在宥》説“昔者黄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愁其五藏以爲仁義……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而儒墨畢起”,弄得“天下衰矣……而性命爛漫矣。……而百姓求竭矣……賢者伏處……萬乘之君憂慄”,簡直天下大亂。
《天地》述“至德之世”是“不尚賢,不使能……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並説“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天地》述老聃譏孔子之揭仁義爲“擊鼓而求亡子……亂人之性”,又假老子之口,以“形德仁義”爲“神之末”,要人“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才能使“至人之心有所定”。
《天運》載商大宰蕩問仁,莊子以“仁”爲“虎狼”,並謂“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又借老聃對孔子之言,以“仁義”爲“憯然憤心,亂莫大焉”之事。
《知北遊》假黄帝之口謂“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以闡述《老子》“失道而後德”一章之旨,卻肯定道、德,否定仁、義。
上述這些篇章,都程度不一地誹詆仁義之裂性殘德,禍亂天下。在“芴漠無形,變化無常……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於萬物”的莊子學派眼中,仁義道德真是鉗性累德的致亂根由。
2. 假道於仁,托宿於義
儘管如此,上述各篇在剽剥仁義的同時,卻仍參差可見對仁、義、禮等儒家道德的挹取與參采。《天地》以“義”的位階置於“德”與“事”之間,在“天”、“道”、“德”之下,至少不全然加以詆斥。《天道》旨意相同,次“仁義”於“天”與“道德”之後,“分次”、“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賞罰”之先,與其前後之各元素參用並濟,以臻“治之至”境。到了《天運》,接納的程度更深,它説: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遊逍遥之虚,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23)郭慶藩《莊子集釋》,第519頁。
這叫“采真之遊”。成玄英疏説,這是一種“逍遥任適,隨化遨遊”。《莊子》所推崇的“逍遥任適,隨化遨遊”理想至境,竟然是要透過仁、義,藉由仁、義去過渡,才能臻至,這對“仁”、“義”的功能價值已大大肯定了。《繕性》説:
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遍行,則天下亂矣。(24)同上,第548頁。
《繕性》所嚮往稱揚的,原本是一種“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陰陽和静,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莫之爲而常自然”的古人、古境;也就是一種不治的,無治道的狀態。但與此同時,它也退而求其次地尋求一種較爲不失其性的“治道”。它説“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而不是養“性”。郭象注“以恬養知”説:“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成疏曰:“以恬静之德養真實之知,使不外蕩。”此處已不再堅持循性無知,而是略爲放寬,求一種恬静安和,知與不知、爲與不爲合一無别的自然之“知”,這叫“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一切是那麽自然地寧静、和順。這種自然的平静和順叫做“德”,叫做“道”。“德”的外在體現,就是“仁”;“道”的軌則條理,就叫“義”。軌則條理既明,外物自來親附,謂之“忠”;内在純實,合乎本情,便是“樂”;真能體現内在真純的本質,而合乎一定的節文,便是“禮”。這是《繕性》上節引文的義涵。很明顯地,它已將仁、義、禮、樂納入了道德的内涵中;然而,它卻仍然不忘提醒回歸老莊本旨,以禮樂的過度張揚爲致亂的根源。
《天下》列序人的修爲層次,有“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之不同。“不離於宗”的“天人”,“不離於精”的“神人”,與“不離於真”的“至人”,都是老莊領域中的高修爲典範。第四級的“聖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是黄老典範人物;到第五級的“君子”,“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是儒家的標桿人物。第六級“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百官以此相齒”,就不折不扣是法家政道中事了。至第七級(末級)“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以衣、食、農、畜爲常務,安養老、弱、孤、寡以度日,這便是“(庶)民之理”。在這七級的區分中,從管理者到被管理者,從治人者到治於人者,依序是老莊、黄老、儒、法、民層遞而下,黄老天、道、德的“聖人”被列於第三級,儒家仁、義、禮、樂的“君子”次之,列於第五級。黄老雖然重政道而采擷法家,法家列序卻始終不高,總在老莊、黄老、儒家之後,這在《莊子》中《天道》《天地》幾篇黄老相關的篇章裏,表現相當一致。黄老的統御叫做“聖人”之治、“聖治”、“帝德”,儒家則以“仁義”、“君子”爲標記。儒家雖屢遭剽剥,卻也得到一些肯定,列序總在老莊、黄老之後,法家之前,各篇這種列序相當一致。
尤其是,雖然對仁義尚不滿意,卻仍能對其加以接受的觀點,是上承《老子》而下入黄老的顯例。《老子》三十八章確實是以仁→義→禮的出現爲道德的依次衰跌,認爲“禮”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但法令則更後——“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天地》《天道》乃至《繕性》《天下》篇的意思大致都保留了這樣的思維。戰國時代黄老學大本營——稷下學宫集體著作的《管子》中也同樣有對義、禮下義界的論述,《心術上》説:
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25)安井衡《管子纂詁》卷十三,《心術上》第三十六,第2頁。
雖然一樣爲義、禮、法下義界,卻更清楚地説明了,義、禮、法之所以不能不采從,只因爲要處理“人間”之事,人事需要“節文”,也需有適切合宜的分度、理路,義、禮的功能因此被肯定。而在不得已的特殊情況下,“法”也成了一時權宜的手段。這一切總體地説,都是爲了切“道”、合“道”,這就是義、禮、法不能避免要被采從的因由,它們有無法全然抹煞的功能。
《管子》之外,在《韓非子·解老》中也有類似的觀點與載述。集法家理論大成的《韓非子》在《説難》《六反》《八説》中,基本上都是反對“仁”、“義”的,視之爲對賞罰威信之嚴重侵犯與挑釁。但在專門解《老》的黄老篇章《解老》中,卻循其老師荀子之論,説: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内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26)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卷六,《解老》第二十,(臺灣)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影印再版,第329—330頁。
對仁、義、禮的義界與性質功能,都給予清楚的表述與相當的肯定。在《難一》中,對於“仁義”甚至賦予了合乎其法家君國政治義涵的詮釋,説:
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27)同上,第809頁。
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28)同上。
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内,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29)同上,第721頁。
换言之,仁義之價值,不光在其爲内在的道德自覺或者人間倫理;更重要的是,它合乎外王的政治規範。這是《韓非子》的仁、義觀。
以後,到了《吕氏春秋》《淮南子》裏,仁義的論述更豐富了。編寫成書於秦始皇以法一統思想,經營六國之前的《吕氏春秋》,歷來學者多有歸其爲雜而偏儒者,説它以“儒”統合各家,主要就是因其内容中仁義説充斥全書。《淮南子》全書在“考驗乎老莊之術”(《要略》)的核心宗旨下,同樣多采仁、義之説,去“接”論“人間之事”。它先也是因承《老子》三十八章之旨,在《俶真》《本經》《齊俗》裏,視“仁”、“義”爲“道德”之衰跌與散溢,唱出“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道毁然後有仁義”的高調;但與此同時,它又在相同或不同的篇章裏,對仁、義的功能給予了一定程度肯定,它説:
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繆稱》)(30)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繆稱》,第36頁。
仁者,所以救争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本經》)(31)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本經》,第80頁。
禮者,所以别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齊俗》)(32)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齊俗》,第53頁。
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人間》)(33)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人間》,第14頁。
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主術》)(34)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主術》,第34頁。
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齊俗》)(35)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齊俗》,第62頁。
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恲以見容,禮不過實,仁不溢恩。(《齊俗》)(36)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齊俗》,第62頁。
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泰族》)(37)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泰族》,第70頁。
《繆稱》界定了仁義之義涵。《本經》《齊俗》《人間》《主術》論述了仁、義的價值功能與實踐之分寸節度。《泰族》更標舉“仁義”爲人事行爲的正向歸趨。從對“仁義”的否定到相當程度的肯定,清楚顯示了從老子到黄老轉化的軌迹。《管子》《韓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如此,《莊子》外雜篇的“仁”、“義”論述亦復如此。這一轉化,在莊子後學或許有過相當的猶豫與遲疑,《庚桑楚》曾假南榮趎之口,顯示了這樣的猶豫與遲疑;南榮趎曾困惑地問老子:
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軀。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38)郭慶藩《莊子集釋》,第781—782頁。
南榮趎的猶豫與兩難可以代表莊子後學對於仁、義取捨之間的困惑與猶豫。但畢竟,當主要的“道”、“德”,或“天道”成爲只能推崇、標舉,而難能具體實踐、操作的理想時,仁、義在濁亂紛雜的現實社會中,猶不失可以維繫一定人心與規矩制度的準則。這就是南榮趎的猶豫與兩難抉擇之因由,也是黄老與《莊子》外雜篇在標崇老莊虚静無爲的“帝道”、“帝德”之同時,偶或不能不退而求其次的原因。
(六) 應 時 以 變
《莊子》外雜篇之所以猶豫遲疑於仁、義之間,主要在於“迹”與“所以迹”的問題。《天運》説: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没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39)郭慶藩《莊子集釋》,第513頁。
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狀況,要有不同的處理,刻舟求劍,膠柱鼓瑟,終必徒勞無功,甚或惹禍招殃。《天運》又説: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40)同上,第514頁。
至於如何順應狀況,做有效的調配與斟酌損益,考驗着調制運用者的智慧。這種智慧是絶對心靈、柔性的。站在《莊子》内篇齊物的觀點,天下没有絶對不可用的東西,也不會有永遠通行無礙的東西,只看使用者如何因物應時而變化操作,對於遠古聖王的“禮義法度”正當作如是觀。能不以古之“迹”看待,而能適時靈活運用,便能永遠焕發新生命,端在“用”者知不知因時變用。《天運》因此説:
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41)同上,第515頁。
儒家的仁義禮樂若能站在這樣的觀點看,就能看出一定的價值。因爲它們原來就是因對象、因人、事而設定調整的非定則,當然不應永恒不變,也不可能一體通用。不得已而用時,則需把握根源,因時、因事、因狀況而調整,仍是合宜可行;否則,一定窘態百出,滯礙難通。换言之,一旦涉及現實人生問題,黄老“用”的功能就必須列置首位,“不矜於同而矜於治”。這就在道家唯“道”爲絶對真理之外,開出了黄老道及法家與時應變的新方向。司馬談説黄老“道家”“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就是這個意思。《天運》要人掌握“所以迹”的根源,與時俱進,彈性調整,不窒不拘。
(七) “氣”的生化與調養
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裏談到黄老道家除了兼容各家,以虚静無爲、刑名考核及因循時變爲操作原則與考核機制的“君綱”外,同時也考量到治身是治國的先決條件,因此也重視“形”、“神”的安養問題,説“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黄老道家在提煉治國君綱的同時,因此也重形神兼養問題,且他們談形、神的安養,是從其原本的生成元素——“氣”的生化開始談起。
原本在《老子》,論“道”都重在論其本體性質、律則、境界,不太談生成,只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四十二章)一則,是唯一涉及生成的命題,隱約帶出了“氣”化的概念。此後,道家後期文獻與學者論道的生成,大致依據且圍繞此一命題作推衍,用“氣”去詮釋“道”的内容,開啓戰國以下的氣化宇宙論。氣化宇宙論是黄老學術思潮對中國哲學的重大貢獻,由是向下甚而衍生出“氣”或“精氣”的養生論。《管子·内業》開宗明義便説:
氣,物之精(42)安井衡《管子纂詁》卷十六,《内業》第四十九,第1頁。唯此處首句本作“凡物之精”,兹依張舜徽校改,説見《先秦道論發微》,(臺灣)木鐸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頁。,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
天地間一切有形無形的存在,包括自然現象、動植物,乃至人形身的健康與精神的靈明問題都是這一“氣”之變化生成與充盈。人體内的“氣”或“精氣”充盈飽滿,精神智慧便靈明,身體便康健。《内業》説:
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内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43)安井衡《管子纂詁》卷十六,《内業》第四十九,第6頁。
因此,要保持身心的靈明健全,須從充養其氣着手。《内業》説:
摶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摶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44)安井衡《管子纂詁》卷十六,《内業》第四十九,第7頁。
《韓非子》也一樣,《解老》説“道”:
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
萬物的生死,智慧的運作與開展,萬事的成敗,《解老》説,都是一“氣”之作用,又説:
知治人者其思慮静,知事天者其孔竅虚。思慮静,故德不去;孔竅虚,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45)陳奇猷《韓非子集釋》,第351頁。
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46)同上,第384頁。
一切形上的精神活動,《老子》所謂“德”、“不德”的問題,在《解老》看來,全部都是精氣的盈虚問題。精氣貯積充滿,精神便靈明,行事穩當,叫“有德”;反之,精氣消散虚餒,精神行爲都會出狀況,叫“不德”。“德”與“不德”成了物質精氣所造成的生理反應與作用,《解老》以此詮釋《老子》三十八章“上德不德”之旨。老莊養神遺形之修養綱領到了黄老,有了相當大的轉化。因了氣化論、精氣説的推衍,形的調養思維比重增加了,這就是司馬談所呼籲的“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二者應該交修兼養。這類理論自管、韓而下,經過《吕氏春秋》,到集黄老思想大成的《淮南子》,終於完成了中國傳統氣化宇宙論的建構模式,及形、氣、神三位一體、交養兼修的黄老養生理論。我們循着這一氣化生成與精氣養生説的發展軌式,檢索《莊子》外雜篇中黄老相關篇章的論述,仍然可見這樣的發展軌迹。
《知北遊》説: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47)郭慶藩《莊子集釋》,第733頁。
人的生死與萬物的榮枯一樣,都是一“氣”之變化,這應該是很典型的氣化宇宙觀念。但儘管承認人的生死是一氣之化生,在論及“治身”的相關問題時,外雜篇基本上仍不離老莊養神遺形、貴神賤形的基本教義,只是不再如内七篇之强調齋忘、超越而已。《刻意》説“養神之道”當如水之性,不雜則清,因此能體純素、純粹不雜、静一不變、淡而無爲,才能四達並流。《達生》説: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48)郭慶藩《莊子集釋》,第630頁。
教人“棄世”、“無累”,才能使“形全而不虧”,又説“醉者險車,雖疾不死”是因“神全”之故。《桑庚楚》也以“抱一勿失”、守真不二爲“衛生之經”,基本上都不離老莊養生唯“神”是崇之原旨,認爲“養形不足以有生”。但生命畢竟離不開形體,形體的安養離不開“物”,不是只有“齋”、“忘”問題而已。
《達生》同時卻也承認,單豹清心寡慾,充養内在精神,卻遇虎而傷形;張毅交遊高門,結友世貴,無外害,卻“病攻其内”,最後皆不免一死。此似乎隱喻着: 理想的全生、攝生之道,應當是形神交攝、内外兼養的。與《老子》以“身”爲“大患”,以及《莊子》内篇强調精神超越,“坐忘”、墮黜身形的思維相較,《達生》對形骸的關照多了起來。《知北遊》也説: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49)同上,第741頁。
有形有象可查之物雖然是來自不可知、不可見的存在,但萬物之所以能够生生不已地繁衍不息,主要仍是形骸的燼傳。這似乎意味着,没有健全可依托的“形”身,一切的生命現象恐怕就要終止了。這兩則雖不明言重“形”,“形”的不可忽略意味已逐漸明朗。《達生》載齊桓公畋獵而自以爲見鬼,有誒詒之病,齊士皇子告敖卻分析其“病”因是:
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50)同上,第650頁。
成玄英疏此云:
夫邪氣上而不下,則上攻於頭,令人心中怖懼,鬱而好怒;下而不上,陽伏陰散,精神恍惚,故好忘也。夫心者,五臟之主,神靈之宅,故氣當身心則爲病。(51)郭慶藩《莊子集釋》,第650頁。
説穿了,就只是“氣”的鬱積不暢所致。一切生理方面的形、神毛病,全肇因於“氣”,“氣”不平、不和、不順、不暢、“忿滀”,便要生病。身心是交互影響的,情緒不好,肯定傷害形身。因此,要精神能虚静、寂寞、恬淡,首先就必須調理情緒,讓它平和穩定。《刻意》説:
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52)同上,第542頁。
必須使“心不憂樂”,才能全其德;“無所於忤”,才能至於“虚”、“粹”;“不與物交”,才能“淡”。最後,歸結出:“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終於注意到了形身健全的重要性,没有了健康充沛的身形與精力,精神無論如何是“逍遥”不起來的。《刻意》終於得出了和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與《淮南子》一樣的結論——“形”也須兼顧。而在《庚桑楚》中,庚桑子最後給予南榮趎的“治身之經”是:“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精神虚寧當然是重要的,但全身形骸與耳目官能的完整健康、正常運作,正是精神寧明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
結 語
不論就治身或治國言,黄老都是崇功尚用,積極入世的。這樣的思想和“外天下”、一死生,以求卓然超乎物外的《莊子》内篇思想,基本上是不兼容的。然而,作爲一代學術思潮的黄老,以其强大的滲透力與輻射能量,終究使莊子後學的思想也無可避免地受其影響,也談帝道,推聖道,論氣化,關涉形身的處理;依於老、莊的觀點,去談政道,論生化,理形神,也交融他家思想。他們以虚静無爲爲帝道、聖道的最高原則與境界,卻崇功尚用,重時變,姑捨萬物平等的“齊物”觀,去定上下,别君臣,分主從,列尊卑,講刑名,並有限度地容許仁義,也談氣,兼論形神的一致健全,搭上了黄老的時代列車。唯在論這些理論的同時,更多的是對虚静、無爲、寂寞、恬淡的一再推崇與叮囑。在正向界定仁義的性質與功能的同時,更大程度提醒,過度强調仁義將殘性裂德。它以“氣”爲萬物生化的基元,也瞭解“神”賴“形”之運作而健全、靈妙的道理,卻始終大量正面地强調“心”、“神”爲主的觀念,審慎、保守地涉及對身形的關切。
一般黄老推崇“虚静”、“無爲”爲“帝道”、“聖道”之核心要則,卻始終只及政道、天道一理相通;也定上下、講刑名,一定程度地采法家,卻非特從未正面强調參驗、察奸之術。即使對因循任下的一般黄老常則也言之審慎,不輕深入。
從《莊子》外雜篇《天道》《天地》等諸篇中所顯現的黄老論述看來,其所呈現的,應視爲戰國時期黄老學術思潮在莊派後學族群中所輻射狀況之一斑。其理論之分量、比重較之所謂“述莊派”、“無君派”,仍然遠有不及。儘管如此,亦可見戰國時期黄老思想輻射能量之廣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