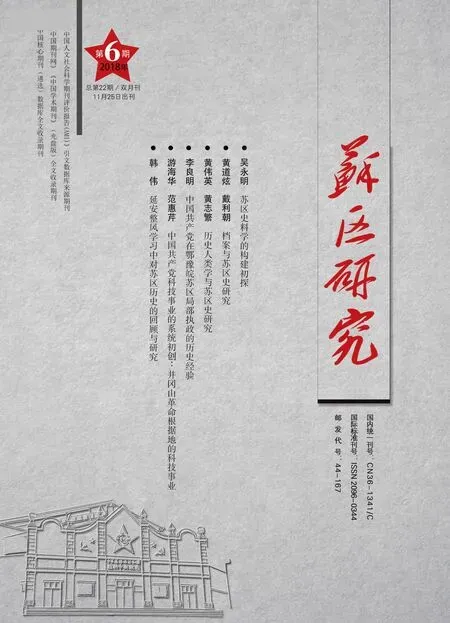档案与苏区史研究
2018-01-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越来越得到认同,档案收集、整理和出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杨奎松、王奇生等学者之所以能取得重大的学术突破,突出的原因正是依赖于档案史料的开发、运用。鉴于前人的经验和苏区史研究的实际需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央苏区民间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特设一个子课题,着力于基层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十分必要。
一、苏区档案及其特点
苏区档案,是指其内容与1920-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苏维埃运动紧密相关的文献或实物。除了一般档案具有的原始性、系统性、丰富性等特点外,苏区档案还有以下特点:第一,稀缺性。原始档案越多,历史书写就越有可靠保障。如梁启超所说:“历代官署档案,汗牛充栋,其有关史迹者,千百中仅一二,而此一二或竟为他处所绝不能得。档案性质,本极可厌,在平时固已束诸高阁,听其蠹朽,每经丧乱,辄荡无复存。旧史纪、志两门,取材什九出档案,档案被采入者,则附其书以传,其被摈汰者,则永久消灭。”[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同理,由于多年战争的影响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保留至今的苏区原始档案特别稀少。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但从瑞金到达陕北后中央和中革军委等有关部门保存的文书档案资料较少,才50余斤,数千件。[注]刘英、丁家栋、杨洁:《长征史料的挖掘、保存》,《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1期,第146-153页。虽然除了中共自己保留的档案,还有国民党方缴获及海外保留下来的档案,但原始的苏区档案总数稀少。第二,非专属性。本来,从档案的来源来看,档案的生产者是特定的组织、单位或个人,一经入馆收藏,档案是按照全宗、卷宗来分类归属的,此全宗、卷宗就是该档案的名号。但是,从实际归属看,苏区档案不仅仅藏在档案馆,同时也收藏在革命博物馆、革命纪念馆、党史办等相关单位。甚至在有的地方,苏区档案没有保存在档案馆,反而是在上述其他单位。如新近学者在福建省新泉革命纪念馆发现的105件乡苏维埃政权公文底稿,较为罕见,有助于重新认识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具体实践。[注]参见张侃、李小平:《1929-1930年闽西乡村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实践——以“芷溪苏维埃政府公文底稿”为中心的分析》,《东南学术》2017年第1期,第67-78页。因此,从“稀缺性”特点出发,我们要加强苏区档案史料的搜集工作;从“非专属性”特点出发,我们在实地搜集中不仅要关注档案馆,还要关注其他收藏单位。
二、苏区史研究中常用的档案
从苏区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与相关成果来看,当前苏区史研究中常用的档案主要如下:
一是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为代表的“中央”档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起初是“内部本”,增补后于1989-1992年出版成为“公开本”,是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大型档案文件汇编,共计18册,按年度分册,其中第3-11册为1927-1938年的史料。《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则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并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大型文献选编,其中首次公开发表的300多篇文献即来自中央档案馆,共计26册,3600多篇,约1350万字。其中4-14册为1927-1938年的史料。这类档案有三个特点:一是编者权威,即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等是档案资料整理和编辑的主体;二是内容权威,即大多数档案资料来自中央有关部门的保存或收藏,且内容都经过编者的考证;三是内容专门而系统,基本上都是中央文件及长时段的资料汇编,有助于考察苏区的兴衰流变及来龙去脉。除了系统的文件档案汇集之外,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年谱、文集、传记等著作中也公开了相关的中央档案。
二是以各地革命史档案为代表的地方档案。由于苏区革命的在地性与底层性,各个苏区所在市县的党史部门、档案馆等也组织或联合编辑了地方革命档案。这类档案分为两块,一块是长时段的革命史档案。这批档案有300多种,称“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或“革命历史档案资料汇编”,大多数在1980-1990年代已经完成编辑,但印数很少,且属于内部发行,极少数公开出版(如《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1986年版)。这类档案的价值独特,“最大特点在于其地方性和事务性。毫无疑问,这些历史文献是研究中共与地方关系,尤其是地方党,包括各省和各个早期根据地内部发生的种种历史问题与历史事件,和研究中共地方史,特别是深入探讨中共基层组织历史状况的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从整体研究中共党的历史而言,它们对已经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也具有极为重要的补充参考作用”[注]参见杨奎松:《6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谈往阅今——中共党史访谈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98页。这里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可能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这批革命史档案,从内容来看,除了“地方性”“事务性”特点外,还有长时段、系统性的特点,涵盖了地方革命活动的酝酿、党团组织的发展、革命兴衰与社会状况等内容。这对系统地揭示苏区的发生背景、发展源流、变迁走向等问题都极有助益。另一块是专门性的苏区档案。这无疑是苏区史研究中最基础的史料。以中央苏区为例,从1980年代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革命历史资料丛书”之一,上中下3册)到2011年以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赣州、龙岩党史部门共同编辑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已出13册),都是最受学术界重视的文献汇编,档案是其大宗,如党的中央领导系统文件、中央政权系统文件、军事系统文件、中央群众团体文件、中央革命根据地所辖各省文件等。此外,苏区的若干专题,如工商税收、司法、妇女运动等,也出版了档案汇编。
三是以“民国档案”尤其是蒋介石、陈诚等个人档案为代表的国民党档案。苏区时期,国民党是共产党革命的对手方。近年来苏区史研究的一个明显进步,是补充或加强了对国民党一方的研究[注]如陈红民依据“蒋介石日记”这一档案史料,对国共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参见氏著:《从〈蒋介石日记〉看其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苏区研究》2016年第6期,第10-19页,《新华文摘》2017年第7期转载。,使得相关结论更为客观和全面。之所以有这个进步,是因为对国民党一方史料尤其是档案的利用。国民党的档案收藏极为丰富,主要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省的档案馆及海外尤其是大学的特藏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以收藏民国时期档案史料为主的国家级档案馆。所藏的五大类档案中,“南京国民政府档案”共1010个全宗,数量最多。[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官方网站(https://www.shac.net.cn/dagis/gcmgda/)。又由于苏区时期国共之间以军事冲突——“围剿”与反“围剿”为主旋律,苏区史料主要集中于该全宗的“军事机构”档。至于台湾,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台湾省“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等的收藏为最。国民党档案史料中的个人档案,在苏区研究中利用较多、价值突出的有蒋介石档案和陈诚石叟档案,主要收藏在台湾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近代中国档案特藏室,后者收藏了蒋介石、宋子文、陈诚等国民党政要的私人档案资料和其他相关档案,总计600多种,逾300万份。[注]参见严昌洪编著:《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国民党方的档案,还有一大块是基层县市的“民国档案”或“旧政权档案”。它产生于民国时期,1949年后移交或接转到原苏区市县的档案馆。有的地方,这批档案数量巨大,还未全面整理,也未引起学者的充分重视。如学者在四川发现,基层的民国档案,无论数量还是保存的质量,都远甚于清代档案。万源市档案馆和战史馆珍藏了数量丰富的1932-1935年间万源县政府档案,渠县档案馆收藏了6000多卷民国档案,其中很多是红四方面军独立师师长任伟章在渠县任知县时的档案。[注]编者:《前言》,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这些对于全面、深入地研究川陕苏区的历史很有帮助。
四是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为代表的海外档案。这是指保留在海外的外文或中文形式的中共革命档案。在中西交通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中共的革命并不是纯粹一国之内的事件,而始终处于国际关系网络当中。研究中共早期革命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联共(布)之间的互动关系。多年来,受语言等因素的限制,大陆学界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建立在国内史料基础上,而缺乏域外尤其是苏俄方面的史料支撑。这种情形的基本改观,始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这套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于1997-2012年间出版的大型档案文献,主要由两块组成,首要一块是《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1920-1949)》的中译,这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原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丛书共计21卷,其中第7-15卷是有关苏区时期的档案,如第7-10卷的内容涉及1927-1931年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制定、实行苏维埃方针初期对华政策的各个方面,为既有研究中史实、内容、观点的修改或补充提供了关键性的档案支撑,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史的研究。[注]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如凌步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经费与物资援助》,《苏区研究》2015年第1期,第42-56页,《中国现代史》2015年第10期全文复印;余伯流:《共产国际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苏区研究》2016年第4期,第22-35页,《中国现代史》2017年第2期全文复印等。此外,日本、欧洲等地收藏的档案也有不少系中文原件或复制件。据介绍,日本外务省档案在美国占领期间曾经复制为胶卷,以后公开出售,共计2116卷,200万页。其中有相当数量与中国有关,如民国历史(1917-1942)、内战历史(1913-1936)等类,部分内容就采自中国。1962年有单位曾把其中收集的中文原件——党和革命政权的传单266件汇编为两册,名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史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史资料》。绝大部分日文材料还没翻译。[注]参见张注洪:《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页。整体而言,海外苏区史档案的搜集整理工作,方兴未艾。
三、苏区史研究中档案利用的几点思考
诚如上述,当前苏区史研究越来越重视档案,不过,相比之下,对基层档案的认识和运用还有待加强。面对丰富多元的基层档案,研究者该如何利用?以下结合课题组一年多来的实践,提出三点初步的思考,希望有助于推动本领域的研究。
一是档案的“在地化”利用。从场域来看,苏区的建设空间主要在乡村社会。乡村与城市或国家的场域性质不同,这一属性决定了苏区史研究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城市史等领域的研究更加需要紧紧扎根于基层大地,此所谓“在地化”。在这方面,华南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值得借鉴。从方法论来看,研究者到田野中不仅是为了发掘、搜集史料,更重要的是将档案(史料)带到田野中阅读。田野即历史现场,研究者须从在地的角度,基于档案的社会属性,努力将档案和与其关联的地方社会情境、社会结构、基层组织、民众日常生活等予以整体思考,在“历史现场”解读档案,在档案中理解历史现场。地方基层革命史档案通常具有名目繁多、来源不一、版本多样等特点,需要细加考证、鉴别之后方可使用。例如,学者考证后发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所编的《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中选刊了14份有关宁都起义的档案资料,其中有些并不符合史实。[注]曾庆圭:《“宁都起义”几个史实问题的考辩》,原刊《江西党史通讯》1985年第12期,后收入宁都起义纪念馆编:《宁都起义》,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50页。这种“在地化”的考证对于进一步提高档案利用的准确性及澄清史实都有裨益。
二是着力探析档案的历史源流。档案是历史的产物。利用档案之前,要了解档案的来历和生产过程。以兴国县的苏区档案资料为例,主要由《兴国革命斗争史参考资料》《江西革命斗争史文选》和“系列档案”三块组成。“系列档案”,具体分为如下八种:1类(自传、经历、简历、信件、照片、题词及将军老干部名册等)/共8号盒;2类(历史文件)/共11号盒;3类(回忆资料)/共8号盒;4类(文件资料摘抄)/共6号盒;5类(专题资料、书稿、文稿)/共11号盒;6类(党史刊物、报刊、信件等)/未统计盒数;7类(参考资料——民国及国外资料)/未统计盒数;8类(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资料)/未统计盒数等。结合上述名称,就可以探寻这些档案史料的生产机制,如1类主要来自党史办的搜集和当事人及其家人的捐赠,8类来自各地档案馆资料的复制等。
三是努力遵循档案的内在系统。每个苏区的革命档案都是一个整体,涵盖了从文件到文稿、报刊、证件等丰富多元的史料类型,有助于全面揭示本地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历程及其各个方面。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档案尤其是地方苏区史档案本身的多元化构成。从地方档案馆的收藏来看,通常分为两种:革命史全宗及散在的革命史档案,而不会直接命名为“苏区”档案。如福建龙岩、上杭市县的档案馆,收藏的中央苏区革命史料主要是如下五种类型:(1)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著档案。常见的是马列经典作家的著作,苏联、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相关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档案资料等。(2)外地创办而传入的、本地创办的革命报刊。(3)苏区党政军各级组织的公文。(4)苏区经济、社会史料:以票证、统计清单或名单、个人史料等三类价值较高。(5)苏区教育、宣传史料:学校或教育、社会团体、宣传、纪念活动等有关的史料。[注]董兴艳、李莉:《地方档案中的中央苏区革命史料》,《福建史志》2017年第3期,第16-18页。这些多元化的档案,提供了将档案和影像、报刊、革命回忆录、歌谣、故事等史料综合运用的可能性,如果做得好,可以大大推进苏区历史的研究,进一步逼进苏维埃革命的历史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