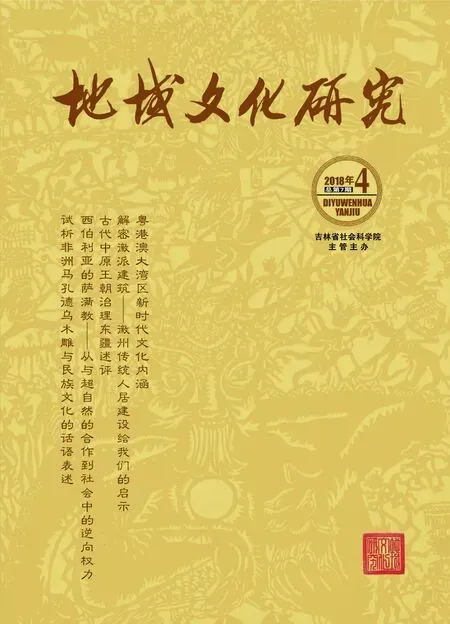西伯利亚的萨满教
——从与超自然①的合作到社会中的逆向权力
2018-01-23罗伯特哈玛雍著于洋译
[法]罗伯特·哈玛雍著于 洋译
一、问题的提出
当我们考察萨满教与权力的关系时,几乎所有专家都会认可以下三个事实:
第一,只有在那些古老的、小规模的、非集权社会中,萨满教才表现为包容性的观念系统。因此萨满教普遍被视为是基本的、原始的象征系统或宗教形式。第二,在集权社会中也可发现萨满教现象,这表明了它的适应性特征。不过,尽管萨满教是古老社会中的主要内容,但在集权社会中,它不仅是碎片化的、变形的,而且是边缘化的,甚至与中央权力相对立,这表明了萨满教的结构性脆弱。与萨满教适应性、脆弱性相伴随的是这一体系在各种社会类型中具有潜在的有效性,此有效性在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此时萨满教实践很容易复苏或重现。第三,无论在部落还是集权社会中,都没有萨满教的神职人员、教义、教理、教堂等。因此,萨满教通常被描述为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有局限和不充分的宗教形式。换言之,尽管在国家社会中仍可发现萨满教现象,甚至在国家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它在国家宗教中却没有位置。
以上这些事实仅是历史偶然,还是反映了萨满教的内在结构性特征。这是否说明萨满教的内在属性决定它不能演化为教会形式?若不将萨满教实践者及其活动推向边缘,萨满式社会就不能演化成国家?我们该如何分析和阐释萨满式社会由部落向国家演变的历史案例?该如何理解与这一过程相关的宗教生活变迁?
本文的目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概括,也无意重新分析历史上的案例,而是基于萨满教的基本结构做一些讨论,诸如在古老社会(如西伯利亚)中的萨满教,①我使用“萨满教”术语表示它作为核心象征系统的表征。是否同时满足两个标准:第一,萨满教制度是社会组织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二,萨满教制度负责定期的丰产(life—giving)仪式(目的在于保证社会和自然资源的再生产)。②需要强调,在严格意义上的萨满式社会中,萨满所实践的这类仪式是常规性的。从政治学的观点看,这一现象表明政治与宗教关系的高度相关,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形容词“萨满教式”③萨满教式(Shamanistic)指从业者和实践者即仪式的表演者和仪式的受众。用来指如下表现,例如,第一,神灵观念即神灵与动物、植物、自然地点、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类似人的灵魂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可直接接触④从本质上说,与神灵直接接触的观念和人们认为神灵与灵魂相似有关,而且神灵、灵魂与神明(gods)不同。。第二,治疗、占卜、预言等活动,这类活动由特殊环境或秩序混乱带来的,不管它们在政治和仪式生活中的位置和价值如何,通过这类表现和实践活动,我们可以判断萨满教是否处于核心位置。
本文是基于西伯利亚萨满教资料的系统分析,尝试理解此区域萨满教的基本原则。通过与西伯利亚社会的比较,我们对萨满教进行分析性的划分,例如,第一种类型旨在概括出那些在古老社会中发现的萨满教体系,居住在西伯利亚森林的人民主要以狩猎为生,这类萨满教可称为“狩猎的萨满教”或“猎人的萨满教”。第二种类型“畜牧的萨满教”或“游牧者的萨满教”,是指那些居住在森林边缘或者草原地区人群的萨满教,这些人群偶尔也会狩猎。在这两种类型萨满教中,关于超自然以及人类与超自然的关系的观念,保持着各自的特征。我将特定社会的萨满教归类为这一类型而不是另一种类型,主要是这一类型的萨满教在其中更为流行。这两个类型完全符合前文的萨满教定义。第三种类型萨满教已经是非常边缘化的现象。具体的社会情况没有必要严格对应任何一种类型的萨满教。每一类型的萨满教从逻辑上说都源于其前一类萨满教。⑤这并不是说,第一种类型萨满教自动地为接下来的类型提供基础,并只会进化成后面类型的萨满教。这里所探讨的问题能够表现出一种进化,帮助我们从政治事件理解萨满教进化的基本原则。
二、狩猎的萨满教:与动物神灵的交换
在西伯利亚森林狩猎社会的信仰观念中,人类生存依赖的野生动物物种(哺乳动物、鸟类、鱼类)是神灵养育的。人们的渔猎活动有必要与神灵达成协议,即人们若想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就必须对超自然施以行动。萨满的主要功能是达成协议,他的特长在于与神灵保持关联。萨满的任务被理解为为他的社区成员从神灵那里获取好运或运气,也就是让神灵允诺在即将到来的季节中赐予猎物。萨满对神灵的行动是猎人狩猎活动的前提,人类与神灵的关系被想象成类似社会内部的关系,因此,人类的行动(获得“好运”并杀死猎物),一定要发生在交换关系框架中,并通过补偿保持关系的平衡。
人类和动物的交换关系将萨满置于超自然的女婿的角色:为确保他的任务获得必要的合法性地位,萨满必须仪式性地娶赐予猎物神灵的女儿或妹妹①赐予猎物神灵的形象用主要的猎物来表示,在西伯利亚地区是麋鹿或驯鹿。,这样萨满就能够以合法性丈夫而不是掠夺者的身份在超自然世界行动。这一交换预期也带来了流行于所有西伯利亚林区的观念:人类在食用猎物肉的同时,动物神灵也食用人类的血与肉。人们将社区中的疾病(失去生命力)与死亡理解为成功狩猎的偿付。人们对神灵的矛盾态度亦源于此:神灵赐予生命,但迟早要将生命收回。萨满的情况也是如此,他的任务是执行这一交换过程。后一种观念决定了萨满的行为与实践特征。萨满的行为要与“女婿”的角色保持一致,其装束与主要猎物形象相似。②萨满的帽子用鹿角装饰,与萨满所“娶”动物妻子的形象对应。萨满模仿动物的行为,首先是“丈夫”的行为举止(跳跃、腾跃、喊叫以及喷鼻),接着萨满表现出被杀死动物的样子(跌倒,仿佛死去)。萨满的实践是非常务实的、个性化的。萨满的行为模式并非程式化,而是一门实践的艺术,其中包含引诱、协商、甚至戏弄的味道。
简而言之,人与自然、超自然世界间存在交换法则,他们保持伙伴关系的同时,彼此间也是对方的“猎物”。神灵在本质上与灵魂一致,与人类是联姻和交换的关系,并非是超越性的。人们恐惧神灵,但不崇拜神灵。只有在交换过程和制度性框架中,神灵才得到尊敬。③萨满的仪式性婚姻使联姻关系具体化。
这种二元原则也体现在地理学意义上的自然观念中:以人类为基点,在水平和纵深的角度看,自然与其他一系列的地点构成对照是一个有营养的环境。更确切地说,森林是一个整体环境,哺乳类动物和鸟类可代表整体环境。一棵树是一个整体,树根到树梢各部分与整棵树具有同样的意义。河流从源头到河口的每一部分与河流整体同样重要。人们与各个部分保持二元关系。萨满娶赐予鱼之神灵之女儿,同时也意味着娶了这位神灵。二元原则在社会组织也起作用:社会被划分为半偶族,联姻关系在半偶族或半偶族内部的氏族分支间遵循交换规则,而且,狩猎活动依据不同姻亲间合作的社会规则进行。
虽然从结构的观点看这些关系是二元的,但在功能上说则不然:虽然交换者同时是对方的索取者和给予者,但在意识形态中,它们或是索取者,或是给予者,而不是同兼两种角色。在联姻或交换的过程中,参与主体所处的位置不是互惠的,而是按照特定的方向进行。给予和索取不具有同等的价值。从猎人的观点看,在意识形态上索取是优先的,需要英雄主义;而给予则意味着有东西付出,虽可提高声望,但也遭到嘲讽,因为给予者将会失去财富、女儿、生命等。西伯利亚各民族将自身认同为索取者,将给予者置于伙伴的位置上。而且,无论是时间的拖延还是仪式性分离,索取和给予中间有时间间隔。这一时间间隔可通过引入调节者,商量给予的时间、方式及数量。这一观念上的区分将互惠的交换转变成不同参与者具有等级性的三阶段过程。换言之,从形式上看,交换者间的关系是互惠的,但每一阶段的具体交换却是等级性的。因此,这一模式为等级化提供了可能,同时也限制了它的范围,防止等级化特征的固定化。这意味着交换者社会地位轮流变化,每一个半偶族中的人之于另一个半偶族来说,有时是给予妻子者,有时则是获得妻子者。
这一模式向我们提出了萨满的社会地位问题。他代表社区与作为整体环境的动物神灵交换。作为萨满,他要尽快尽多地为社区带来丰产,最少最迟地偿还人的生命力。萨满调节所带来的时间延迟使社区获益,萨满在社区中的权力也来源于此。这样的权力可否演变为政治意义上的集权化?答案是否定的。萨满对权力运用受到社区成员的控制。萨满的权力完全取决于其作用,萨满的权威不是因为他是一名萨满,而是通过行为证明他是有用的。在狩猎社会中,虽然二元原则运行时,为调节行动留下了空间,但由于此原则阻碍调节行动的制度化,所以从根本上说,这类萨满教与集权化的意识形态及国家的形成是不匹配的。
三、畜牧的萨满教:来自人格化神灵的遗产
上文所探讨萨满教的古老模式伴随生计方式的变迁而改变,饲养家畜导致了对自身世界内部传递的偏好,而不是与他者世界进行交换:畜群与牧场是继承下来的(可以是实际的财产,或者是用益权)。①几乎西伯利亚所有地方都实行父系继承制。不过,虽然狩猎社会彼此之间十分相似,但畜牧社会则不然。这部分所概括的萨满教模式主要基于居住在贝加尔湖西部一个畜牧群体(Exirit-Bulagat)的情况。这伴随着社会组织的重要变迁。我们观察到直接交换向间接交换规则的转变、从妻居到从夫居以及半偶族到氏族的转变。在社会结构和生活中,相对姻亲关系而言,父系关系变得更重要。②虽然两种关系都会呈现出来,但从结构和功能的观点上看,父系关系要比姻亲关系重要。人们对自然和超自然的观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自然不再是一个直接提供食物的环境,而是成为可能进行系列食物生产的地点。自然不再被想象成一个单一的横向水平结构,而是沿着垂直轴线形成的几个等级结构。因此,树木被划分为根部、树干和树梢,分指涉不同领域。与之类似,河流分为河源,河道和河口。
山川自下而上被视为特定世系群体(氏族的分支)的牧地,③牧地是这些群体领地的地理标志,也是他们祖先居住的地方。对这些世系群而言,山川构成了其合法性的象征,使他们有权力占领这片土地,提供与祖先接触的准确地点,向祖先要求对放牧有利的东西,尤其是雨水,同时希望能防止敌对人群的入侵。尽管祖先是人,但他经常被吸纳到山川之中,被视为属于山川的神灵。就像狩猎社会中赐予猎物的神灵,这位拥有动物形象的神灵代表森林本身。与山川一起,祖先成为一类赐予生命的超自然实体。但祖先赐予的不是生活资料本身,而是生产这些东西的条件。祖先喜欢后代尽可能多地参与山川旁举行的集体仪式,他们会惩罚违反父系规则和伦理的成员,给这些人送来疾病,尤其是皮肤病。④这类疾病是可见的,对患病的人来说是一种公开的羞辱。
献祭祖先的仪式富于大量的创新,祭品包括奶制品和饲养的动物。所有的这些祖先崇拜都标志着向祖先乞求“恩惠”的一种补偿。在向人类实体(祖先)祈祷时,人们使用自身的语言;⑤在向动物神灵祈祷时,猎人要模仿动物的叫声,要求获得野生动物。向更高实体祈祷时,人们是崇拜者的态度。与猎物不同,饲养者与所饲养的动物之间保持连续性,所以饲养动物可以作为饲养者替代品。因此,作为赐予生命超自然类别的人类实体的出现,与祭司和动物牺牲的发展相伴随,同时也伴随着空间的垂直化和关系的等级化。作为一项规则,萨满不能主持祭祀祖先的仪式,萨满的特殊作用在于关注祭肉。①每位仪式参与者都会得到一部分肉。创新和献祭活动通常由人群中的长老或与接近祭司的专家主持,而非萨满。在这一领域,虽然萨满式的制度仍然具有功能,但也让步给氏族法。②贝加尔湖西部布里亚特人(Exirit-Bulgat)和畜牧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是混合在一起的,氏族作为独立单位的作用只是出于族外婚的目的;没有一块共同的领地。相反,本地的氏族单位至少由两个氏族分支组成,彼此之间可以通婚。因此,由于祭祀居住在山川上祖先的仪式是为了本地氏族举行的,不是严格地局限在氏族事物上;大多数时候,仪式的参与者包括两个或更多的氏族成员。
部落的建立者作为另一类超自然实体在赐予生命的过程中也起到作用。建立者在本质上是动物,但他诞生了氏族祖先③这方面的例子如公牛王,它是贝加尔湖西部布里亚特人部落的建立者,其形象是一只公牛,与赐予猎物的神灵例如麋鹿或驯鹿形象一样,都有角或者带鹿角的反刍动物,同样,通古斯人中的超自然实体“布噶”最初是赐予猎物的神灵,一直是麋鹿形象(在通古斯人和蒙古人中,麋鹿或驯鹿与“布噶”的含义一致),即便在畜牧人群中它被称为祖父、老人(或者祖母,老妪)。人的属性化为这一超越开拓了道路。,发挥了人类的作用。他源于超自然世界的动物部分,又在人类的祖先之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赐予生命的实体,其活动凭借动物来源。④作为动物,他应该在丰产仪式中体现丰产能力。萨满被赋予代表神灵的特殊权利,将丰产传递给社区,这是畜牧社会唯一的周期性萨满仪式,其中萨满模仿与丰产有关动物的行为是非常明显的标志。而且,作为部落建立者的形象只在神话中表达与丰产的获得没有任何关联。
这类神灵角色的出现,对于萨满教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十分关键。这一角色的动物来源是在人类和赐予生命的超自然实体间延续合作关系的基础。这种合作关系意味着二元世界观的持续,反过来也表明了对社会中权力的限度。不过,这种萨满教模式是混合型的,因为赐予生命的超自然实体被划分成两类,这两类实体说明了两种关系类型,一方面,畜牧萨满教保留了狩猎萨满教的基本特征即与动物实体之间的关系,但这一实体赐予生命的角色缩减为提供丰产的原则;另一方面,畜牧萨满教中的原则要通过人类实体祖先才能起作用。因此,与超自然动物之间的互惠关系,从属于基于父系的、依赖人类实体的非互惠关系。在社会制度方面,这反映了萨满教制度从属于氏族制度。萨满与超自然动物演变为从属性的目标和结果,其实是对人类世系关系的逃离。
我们这里提及的“联姻的附属化”过程,是姻亲关系向父系关系的一种整合。例如,虽然萨满仍然有超自然妻子(动物来源),但更强调他作为祖先后代的身份。其中的原因是,人们认为超自然妻子喜欢男人,会出于同样的原因选择萨满,萨满以此代代相传。这反过来改变了关于萨满的合法性观念。尽管固定的等级化关系是允许发展的,但这种关系是被阻止进化成集权化形态的。只要丰产仍然被认为需要依赖动物起源的实体,其中的关键原则就是不同性质实体之间的联姻关系,而不是相同性质实体间的父系关系,联姻原则在此范围内发生作用。
尽管出现了动物形象,但西伯利亚畜牧社会世界观的二元论方面与狩猎社会仍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两部分之间的角色和位置不再可互换,而是固定的。采用畜牧生计方式和从父居,与长幼对立的主张有社会相关性。只要缺乏与社会地位相匹配的道德价值,此类二元论就能得到维系。在西部布里亚特人中,虽然长者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年轻人却有更高的价值。年轻人虽缺乏声望,且具有社会依赖性,但年轻人与英雄主义、男子气概以及效率相关。缺乏理解和有缺陷的行动则被归因于年长者。这样的二元论能否进化成与集权和国家形成相协调的形式?
在一些西伯利亚畜牧社会中等级化超自然实体的出现让这个问题十分明显。例如,居住在贝加尔湖西部的布里亚特人将属于宇宙的、非人类非动物的超自然实体,作为部落建立者的公牛王,也就是“腾格里”(复数的天)。神话中公牛王是天的儿子,这些天被分为两大彼此间无休止战争阵营,一边天代表年长者,另一边天代表年幼者。因此,二元论依然在上界起作用。一个类似的事实是,在帝俄统治时期,这个部落包括一些敌对的氏族,没有出现任何集权化的趋势。
四、二元论的限度抑或萨满教的界限
在关系垂直化的过程中,能否在达到国家形成集权化特征的同时,也维系着萨满教?这里以居住在贝加尔湖西部和东部布里亚特人部落的不同命运为例。罗琳·汉弗莱(CarolineHumphrey)在《谱系学的运用》中提到:为什么基于父系世系关系的集权化等级秩序可以在贝加尔湖东部的游牧部落中产生并维系,而贝加尔湖西部的部落则没有?更令人惊讶的是,居住在贝加尔湖两侧的布里亚特人曾被鼓励围绕替俄国管理部门服务的首领团结起来,但此等级化培育只在东部的布里亚特人中成功了。①[英]卡罗琳·汉弗莱:《谱系学的运用:游牧与定居布里亚特人的历史研究》,载《畜牧生产与社会》,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
两个部落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萨满教在西部布里亚特人中更有影响力,而东部布里亚特人的萨满教被喇嘛教②这里的喇嘛教发展出一座寺庙和一位僧侣。取代。在西部,萨满仍旧是男性,他们很愿意通过“出马仪式”获得担任萨满的资格,并承担主持赐予生命仪式的周期性任务,仪式的目的在于再生产世界秩序。因此,在西部布里亚特人中,萨满教仍然是氏族制度的一部分。在东部布里亚特人中,萨满大多数是女性,而男人认为当喇嘛是更有利的(声望、财富与社会地位)。人们获得萨满式的功能一般在晚年,没有制度化的仪式。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萨满承担的是占卜、治疗以及其他此类特殊情境中的仪式,目的在于修复失序,萨满不参加周期性的仪式。在东部布里亚特人中,萨满教不再是社会再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制度,而成了一种被鄙视的职业。东部布里亚特人社会的萨满实践者和受众是边缘化的,其活动被认为与权力相冲突。从整体上看,东部萨满的活动都是为私人事务服务,萨满仪式所反映的关系是人们与那些非正常(“非自然的”或夭折)死亡者或犯罪而亡者的关系,这些灵魂游荡在人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麻烦。就此而言,萨满教关注的是社会内部的关系,而不是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因此,东部布里亚特人的萨满教被整体赋予了颠覆和越轨的意义。
一些相关的差异也表现在神灵观念中,尤其是关于赐予生命神灵形象的观念。贝加尔湖两侧最显著的赐予生命者是不同的。在西部布里亚特人中,赐予生命者是公牛王的形象,而东部布里亚特人中则不是动物形象,而是白须老者,是掌管土地和水的神灵,其形象具体表现为骑着一头鹿,或者有一头鹿在其脚下。他是一个混合型的角色,在喇嘛教祭祀山上神圣石堆“敖包”的仪式中,也有这位神灵。在其他的超自然形象中,“腾格里”(复数的天skies)在综合性的仪式及表现中也是重要的一类。值得注意的是,在贝加尔湖东部,这些天神与西部布里亚特的人情况不同,不再是两个对立的阵营(尽管也没有整合在一起)。①正如蒙古史诗格斯尔中的33位腾格里,或多或少借自因陀罗中的33个天,或者在蒙格腾格里(永恒天)的个案中,是一种与蒙古人中成吉思汗帝国出现的意识形态观念。(参见BeffaandHamayon,1990)(《蒙古秘史》中“天”的概念,纪念《蒙古秘史》750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乌拉巴托)。腾格里主义(tengerism)这个术语用来表示如下事实,内亚突厥—蒙古社会国家形成用“天”(上帝)观念作为特权性的意识形态支持,这一观念借自汉人是明显的。而且,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吸收到或者混融到佛教神祇“布尔汗”之中,在很多混合性的仪式文本中,用“布尔汗腾格里”来表示这类神灵。与之类似,东部布里亚特人中也发展出居于下界的恶魔与妖怪类别。上界或下界的存在,不像超自然的人类或动物那样,与人类之间保持着婚姻或世系关系。②在喇嘛教压迫所产生的宗教变迁下,下界的掌管者“额尔勒格汗”头上有角,这重现了森林狩猎社会中有角或鹿角的赐予猎物神灵,或者半畜牧社会中赐予丰产的神灵形象。这些上界和下界的存在不再是神灵,而是在本质上与灵魂不同的上帝和魔鬼。进而,狩猎萨满教的两可性原则让步给两极化原则,垂直轴的顶端被认为是完全正面的,低端则被认为是完全负面的,位置和价值随之被结合到一起。
结 论
虽然利用帝俄历史背景下的西伯利亚萨满教资料,不可能对萨满教是否可能与国家形成相结合做出判断,尽管它有可能向等级化的方向进化,但可以肯定萨满教内在的二元原则是达到这一状态的结构性障碍,在集权化的国家中,不可能存在包容性的萨满教式社会,其中的萨满教往往会沦为由边缘化专家主持的一些碎片化的实践。二元主义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集权化社会顶部权力的二元化形式。这需要对权力二元化形式可能出现的萨满教特征进行深入研究。例如,在一个神圣的王国中,国王可以在两种相反的功能间转换,或者委派一名弄臣,来承担与国王有关的影响性角色。其二是人类与超自然世界间的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否是二元论都意味着互惠性。
萨满教社会中国家形成的第二个障碍是萨满行动模式的实用性特征,这表现在二元原则的组织与超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在二元原则所涉及的关系类型中,实用主义表现为伙伴之间的联姻或交换关系。这使萨满教实践成为一门可操作的艺术,而非一种礼拜仪式。因此,实用主义不是一种缺陷,它并非缺乏规则与规范,相反是对教条主义的蓄意拒斥。萨满式社会以及非萨满式社会中的萨满,都拒绝用书写的方式来规范萨满事物,这也使得萨满教没有教堂和神职人员。总之,萨满教似乎拒绝将自身法典化。因为萨满教不会事前将任何与人类生活有关的事物排除在视野之外。只要它能将想象的实体转换成合作者并与之交易和协商,这个阻碍与超自然总是可取得联系的,
第三个障碍源自萨满活动中所宣称的“运气”和“好运”的性质,无论其关注点是猎物、雨水、丰产、精神健康、爱情、贸易成功、日常事务、出行或任何其他事情,其中普遍的要素都依赖个人的才干及对集权化组织日常规则的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