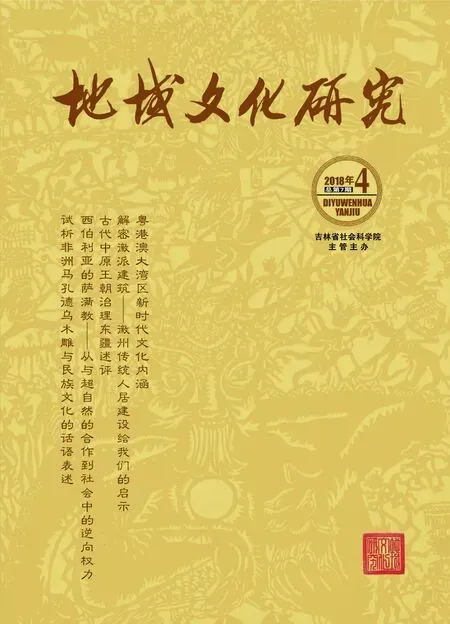改革开放以来的清代东北人参问题研究述评
2018-01-23滕德永
滕德永
人参具有极高的药效价值,很早即为国人所熟知、利用。清代,东北人参的地位崇高,为皇帝所垄断,是宫中贡品,在皇室成员饮食、医疗等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如此,东北人参还有极高的经济价值,是宫中重要的经济来源,对皇帝和内务府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清代统治者非常注意参务的管理。同时,东北人参问题还反映了清政府东北地区的管理制度以及人参资源枯竭等问题。因此,改革开放40年来人参问题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有关史料文献的整理、出版
较之前朝,清代东北人参的采集大有不同,它被纳入到官方的管理体系之中。这就直接产生了大量的文书档案。这些档案既集中又分散。集中是指主要存放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等档案管理机构;分散是指除这些档案馆之外,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等机构亦保存有相当数量的此类档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档案封存在库房之中,未能面世。
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得到改善。随着学术研究的开展,管理者加强了对档案的整理和出版,这其中关系清代东北人参者众多。改革开放之初,东北人参问题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其档案则是作为其他档案组成部分,为编辑者整理并出版。1978年,故宫明清档案部编的《清代档案史料》第一辑中即有人参摊派交进银的内容,这是为了显示当时清朝财政支绌状况。
20世纪90年代,人参问题的专档开始出现。1991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吕小鲜选编了部分乾隆朝的参务档案,以《乾隆朝参务史料》为名,刊发于该馆的《历史档案》上,这是国内第一次系统的、公开出版的人参管理档案。几乎与此同时,吉林文史出版社亦出版了《清代东北参务》一书。该书主要从《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清会典》及《吉林通志》等文献中搜集了东北参务——主要是吉林参务的档案。
进入21世纪,人参档案的整理与出版有了更为喜人的成果。200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哈恩忠选编了《乾隆五十九年吉林参务案》。2002年,王道瑞又对嘉庆朝的参务档案进行了选编,分两期刊载。2003年,辽宁省档案馆自馆藏的《黑图档》《盛京内务府档案》《兴京县公署》等档案中,编译出版了《盛京参务档案史料》。更为重要的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加强了档案的数字化建设工作,其所藏的《内务府奏案》和《内务府奏销档》已于2007年全部上线,并由故宫出版社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出版,极大地便利了研究人员的利用。2017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完成了30余万件《内务府堂呈稿》的数字化工程,并对外开放利用。201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50余万件《内务府来文》也将完成数字化,并对外开放。这些档案涉及东北贡参的采集、宫内管理、销售等情况,有助于我们更为详细地了解清代参务情况,这必将推动人参问题研究的深入。
在人参档案集中问世的同时,仍有大量的相关史料分散于其他档案之中。199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出版,该书中有相当多的史料揭示了雍正皇帝打破前朝成规,终结官方垄断,开放民间采参的史料。还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档案出版社出版的《清代上谕档》,其中亦有相当分量的谕旨与人参相关。2016年,辽宁省档案馆整理出版了《黑图档》。该档是盛京总管内务府同北京总管内务府、盛京将军、奉天府府尹、盛京五部等衙门来往公文的抄存稿簿,其内容庞杂,多有关系人参问题者。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等也有部分档案涉及人参问题。这样的资料为数不少,需要研究者耐心爬梳,方能有所收获。
诸多官修史书也涉及人参问题,《大清会典》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它对人参的采集、牲丁的管理、人参的赏赐都有明确的规定,并且还涉及相关制度的沿革,是研究东北人参问题的基础史料。清朝皇帝的《起居注》记录了历朝的政务活动、财政经济、政治制度、国典朝章、官吏任免、军事活动、重大事件、民族关系等内容,其中亦有大量涉及参务管理方面的篇幅。清朝皇帝的《实录》也有人参方面的内容,亦可互相参照。此外,东北三省及各州县等修撰的地方志也有人参方面的内容。清朝时编修的《柳边纪略》《盛京通志》《吉林通志》《吉林外纪》《黑龙江外纪》等,民国时期编撰的《义县志》《奉天县志》《临江县志》《黑龙江志稿》等,现在多已数字化和再版,十分便于研究利用。此外,在一些清人笔记中对人参问题也有涉及,如《啸亭杂录》《檐曝杂记》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二、有关研究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在东北人参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但在国外,人参问题已经引起部分学者注意,主要是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日本学者今村鞆1939年出版了《人参史》,该书共7册,分为“人参思想篇”“人参政治篇”“人参经济篇”“人参栽培篇”“人参医药篇”“人参杂记篇”等。此外稻叶君山也多次提到明末清初东北边境人参问题的重要性。铃木中正与川久保悌郎则探讨清代的人参采集制度。美国学者VanJaySimons和PrestonM.Torbert都关注到人参的经济意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的人参研究成果日渐增多,并且出现了较为喜人的成果。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端:
(一)人参的采集
自努尔哈赤时期开始,满族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东北人参的巨大经济利益,注重对人参采集的管理。清军入关之后,顺治、康熙等皇帝延续了这一政策,并逐步实现了对东北人参的垄断。
王佩环较早地开展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在充分利用《黑图档》《盛京通志》《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等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王佩环详细考察了东北地区采参业的勃兴、发展及衰落的过程。该文认为清入关之初,基本延续了入关前的采参制度,实行八旗分山采参,但因为资源枯竭、旗办采参制混乱及流民偷采等因素的影响,至康熙时期,八旗贵族采参制度废止,并最终为皇室垄断。此后,清政府又实行了招商承包采参的办法,一直延续至乾隆朝方被终止,以后改为官办。但随着开采日久,参源枯竭以及承办官员的贪腐,清代东北的采参业日趋衰落,至咸丰初年,已基本停止,虽每年也发放少量参票,“不过是专供皇室需用而已,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的经济意义”①王佩环:《清代东北采参业的兴衰》,《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第192页。。
廖晓晴对人参采集问题也有探讨。廖晓晴认为在八旗分山采参与招商承包采参之间尚存在盛京上三旗包衣采参。康熙初年,清政府规定“正黄、镶黄和正白上三旗包衣所采人参,经由盛京户部送交朝廷户部”。这表明“朝廷不但加强了对八旗贵族采参的监管,而且还将正黄、镶黄和正白上三旗包衣刨采之参直接收归皇室所有”,并由此“便形成了八旗分山制和盛京上三旗包衣采参制并行的局面”。同时,该文亦认为乌苏里等处大参场的开发具有重大意义,“为加强皇权和逐步削弱八旗贵族的势力提供了难得的契机”②廖晓晴:《清朝参务管理制度的嬗变》,《理论学刊》2013年第11期,第102-108页。。
丛佩远则对东北人参采集者的身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顺治、康熙时期,获得公开、合法采参地位的有打牲乌拉壮丁、满洲八旗士兵、王公大臣派遣的壮丁,“民间采挖处于非法的、私密的地位”。至雍正时,准许民人采挖人参,后改为商人雇人刨采。乾隆年间,又改为国家招募、组织刨夫采挖人参。与此同时,又有烧锅商人获得领票雇觅人夫采挖人参的资格。但无论东北人参的采集形式如何变化,“政府从来没有从人参的生产领域中撤退,始终是人参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和生产物的主要占有者。”③丛佩远:《东北三宝经济简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64-104页。
随着参务档案的整理与出版,东北人参采集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佟永功针对盛京参务的情况,将其以乾隆九年(1744)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且由于“经办参务的衙署形制及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其经办的方法亦不同,各有其特点”④佟永功:《清代盛京参务活动述略》,《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42页。。赵郁楠详细考察了清代东北采参机构,认为在顺康年间东北采参存在两条主线:其一是由京师总管内务府和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共同经办的盛京采参;其二是由京师总管内务府和吉林打牲系统管理吉林、宁古塔、三姓采参。同时认为在实行将军衙门参局制时,在领票采参管理方面,盛京和吉林两地均实行过烧锅领票采参制度,并“对于官放接济银采参之不足进行补充,为清朝采参管理注入活力。但由于盛京和吉林地理位置和自身特点的不同,又存在差异,主要体现于盛京船规银津贴参票法和吉林私放民票,虽然前者最后得到清廷承认,后者自生自灭,但均是地方政府为转嫁采参困难而实行的新尝试。”①赵郁楠:《清代东北参务管理考述》,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1-2页。
(二)人参的销售
国内学者中,丛佩远较早的关注到这一问题。在其专著《东北三宝经济简史》中开设有专章,讲述清代的人参贸易。但与其后的学人不同,丛佩远主要关注的是清代初期的人参贸易情况,认为早期的清统治者“把人参的采挖、贸易视作八旗贵族的独占经济权益”,故“只有八旗贵族享有从事人参贸易的特权”。八旗持户部所发票证出关购参,输入关内,赴各省销售,后被禁止,只许在京售卖。而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流民、商人甚至官兵和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也秘密贩卖人参。在此情况之下,清政府对人参销售政策进行了变通,实行参厂统售。即先挑取官参,解交内务府,剩余之参,再交由盛京、吉林、宁古塔三个参厂出售。此外刨夫剩余之参,有的就地售卖于苏州、山西等商人,有的则是刨夫等自赴苏州等地售卖。此外,丛佩远还对有清一代的人参价格进行了考证。由于人参销路的扩大,产量的锐减,其销售价格暴涨②丛佩远:《东北三宝经济简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105-123页。。《东北三宝经济简史》一书关于人参销售的论述虽然简略,但在档案尚未公开的当时,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料,大体勾画出参源地的人参销售情况,其意义重大。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今天,对于参源地的人参销售情况的研究也未能超越该书。
叶志如则主要关注宫廷人参的销售情况。叶志如追溯了清宫人参售卖的历史,并依据清宫所藏档案梳理了清宫人参销售的情况。叶志如认为清宫的人参自售卖发端于康熙时期,且初期主要在京销售,后曾尝试发交江宁、苏州和杭州制造销售,但其效果并不理想。康熙以后诸帝延续了宫中人参变价政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宫廷特供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和保障”③叶志如:《从人参专采专卖看清宫廷的特供保障》,《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1期,第67-80页。。《从人参专采专卖看清宫廷的特供保障》一文影响极大,为许多论著引证。可惜的是,该文对雍正、乾隆年间的人参销售情况论述过于简单,且将嘉庆、道光年间的参斤加价银与道光、咸丰年间的参斤摊派交进银混为一谈。对此,滕德永曾经撰文探讨这一问题,详细考证了参斤加价银与摊派交进银的异同,认为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④滕德永:《嘉道时期内务府人参加价银问题辨析》,《东北史地》2013年第4期。。但是也应该看到叶志如此文的重要意义,它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宫中人参变价的情况,揭示了清宫人参的功能——尤其是对宫中的经济意义。
前人的研究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几经艰辛,为后学者的研究创造了条件。蒋竹山的研究则是最为主要的成果之一。蒋文极大地突破了以往的研究,使得人参销售研究不再简单地局限于“内务府库储人参的变卖,或者是产地多余官参的买卖”,而是考察了人参流通与消费的关联,探讨内务府与人参买卖的关系,商参的流通。蒋著认为清初的人参顺着大运河由淮安到扬州,甚至跨过长江,到较南的苏、杭、芜湖等地销售,最远发送至福建的延平府,每年贩售的银两上交户部。乾隆及其以后,内务府主要通过三处织造、盐政和税关,将官参销往江南地区。并且,蒋著还以个案的方式考察了购买官参的参商资质的获取以及清代商人是如何买参、贩参,官府如何掌控这些参商的。蒋著认为宫中太监在人参买卖中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蒋著还对非官方渠道进入市场的人参进行了考证,认为当时民间所用的辽参是来自私参的流通。①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0-212页。
当然,清代的人参销售的情况远较我们想象的复杂,诸多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不同的侧面,依然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在前辈学人研究的基础上,滕德永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奏案》《内务府奏销档》等档案文献,对有清一代,尤其是乾隆、嘉庆、道光等朝的内务府人参销售情况进行了考察,对其销售政策、销售数量、成败原因都进行了翔实的考证,认为嘉庆末年内务府的人参销售已经遭遇困境,道光朝恶化,至咸丰朝终止,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经济的衰退——具体而言是盐政与粤海关收入的锐减所致,而并非人参供应的不足②滕德永:《乾隆朝内务府对库存参斤的管理——以内务府的参斤变价为考察对象》,《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4期;《道光朝人参变价的困境》,《满族研究》2012年第4期;《嘉庆朝内务府人参变价制度的新变化》,《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对于清宫内务府的人参变价问题,祁美琴与台湾学者赖慧敏都将其作为内务府经济来源的重要方面之一,亦有所论述,但着墨不多。其中,赖慧敏主要依据清宫内务府广储司月折档,对乾隆朝人参收入有更为确切的考证,认为自乾隆十五年(1750)至六十年(1795)所卖人参共得银11,220,806两③赖慧敏:《清乾隆朝的税关与皇室财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年12月,第87页。,平均每年得银24.39万余两,而当时宫中每年的收入在50万两至250万两之间,其重要性由此可见。这是对清宫人参变价研究的一大贡献。
(三)人参与政治
清代人参为皇室垄断,从而使得人参的采集、管理、应用及销售等不再仅仅属于生产于经济问题,而是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东北人参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这为管理参务的官员提供了贪腐之机。对于参务官员贪腐问题,诸多研究者都有所揭露,但并未作为专题论证,而只是将其作为清代人参事业衰败的重要因素加以讨论。其实,在诸多案件中,贪腐并非案件的主因。廖晓晴考察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参务案,认为“清初诸帝在开发人参资源问题上明显表露出急功近利和与民争利的思想,在对待地方官员的问题上颐指气使,难以沟通,关系十分紧张”,而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参务案,“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冤狱”④廖晓晴:《乾隆五十九年参务案》,《满族研究》2013年第4期。。孟繁勇则考察了嘉庆朝吉林将军秀林参务案,认为“秀林参务案既反映出官场腐败现象的严重,同时对秀林的处置也反映出仁宗整顿吏治较严的一面”⑤孟繁勇:《清仁宗与吉林将军秀林参务案》,《学理论》2015年第21期。。
清代帝王还将人参作为笼络朝臣的重要工具。清初时,康熙、雍正诸帝即将人参作为赏赐臣工的重要物品。至乾隆朝,则将大量人参售卖于文武大臣。入嘉庆朝后,在借鉴乾隆朝内务府参斤售卖的基础上,嘉庆朝内务府形成了贡参赏买制度,并进而演变成御赏贡参制度。滕德永认为,御赏贡参制度的形成不仅提高了内务府的参斤收益,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于嘉庆皇帝吏治整理的大背景下,它是嘉庆皇帝控制京师官员的一种手段,这项简单的经济活动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色彩①滕德永:《嘉庆朝御赏贡参制度》,《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
而在人参变价过程中,皇权政治色彩更浓。乾隆朝时,若内务府人参销售官员不能如期完成销售任务,并将所得银两如期解交内务府广储司,将要受到惩罚。至道光时期,内务府的人参变价遭遇困境,虽然道光皇帝几经调整变价政策,但收效甚微,最后将“吏部条例引入到人参变价的惩罚机制中,实则是将国家权力引入到内务府的管理体系之中”②滕德永:《道光朝内务府人参变价的困境》,《满族研究》2012年第4期。。即使如此,内务府的人参销售状况亦未得到改善,并最终走向终结。
(四)人参的药用功能
人参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故为人所重视。对于人参的药用功能,古人早有著述。至改革开放以来,学人又有诸多成果问世。1984年吉林省图书馆编写出版了《人参文献专题目录(1714-1980)》,该书收录了1714年至1980年间有关人参基础理论、栽培、育种、采集加工、药理、临床应用、制剂等题录,其中包括中文、日文、英文、俄文和朝文条目,共计2,728条③吉林省图书馆编:《人参文献专题目录(1714-1980)》,长春:吉林省图书馆,1984年。。这次条目的系统整理,为东北人参医疗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继之,1985年王本祥编写的《人参的研究》则以现代科学的方式探讨人参的疗效。更为重要的则是王铁生的《中国人参》④王铁生编:《中国人参》,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一书。该书对人参的资源分布、栽培、人参加工记述、人参的药理及临床应用、贸易及文化史都有论述。2006年,宋承吉教授搜集古今含有人参的中药方剂3,521例,整理并注释成《中国人参方集》。
综合而言,这些有关人参的著作都是宏观的研究,并非探讨历史上东北人参药用价值的研究成果。蒋竹山探讨了清代人参药用与江南文化盛行的关联性。该文认为“清代自乾隆年间以来,医书中出现了相当多讨论人参的医论,这些和人参有关的医论的出现与江南社会上好用补药的文化息息相关。”社会上形成的非参不治、服必万全的观念,影响所及上至富贵人家,下至贫苦百姓。它的形成则推动了内务府人参的销售,但是这种风气却并不有利于疾病的治疗⑤蒋竹山:《非参不治,服必万全——清代江南的人参药用与补药文化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2007年,第114-127页。。邓玉娜则通过清宫档案探讨东北人参的应用,认为清宫广泛的使用人参进补,每年都有大量人参用于制药,有的制成汤药、药丸等药剂,有的以人参配伍当代茶饮,有的被制成药膳等等。同时,对于滥用人参的副作用,该文亦以实例予以证明。
(五)人参文化
人参的神奇医效以及采集的不易,被人们赋予了神秘的色彩,产生了独特的人参文化。东北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产参地,亦有其独特的人参文化。1989年,王德富撰写《初论人参文化》一文,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反响。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吉林省民俗学会召开了人参文化学术研讨会,会后相关论文结集出版。论文主要从采参习俗、采参人的形象、长白山地域性特色对人参文化的关系以及人参故事、人参谚语等角度探讨了丰富多彩的人参文化。此后,吉林省有关机构又先后编辑出版多种人参文化书籍,并拍摄宣传人参文化的电视专题片、电视剧多集。
人参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扩大人参的影响,但这些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对文化外在表现形式的描述上,否则人参文化的研究将会维持在低水平,非常不利于人参品质和内涵的提升,不利于人参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影响的扩大。对此,人参问题研究者应积极探索人参文化的深层内涵。宋丽瑄等考察了人参传说的艺术性问题,认为盛产人参的长白山是人参传说的优质土壤,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切身感受创作的口头文学,经过艺术的加工,在“艺术上构成了一种富于生活感、地方色彩和泥土气息的朴素之美”①宋丽瑄等:《长白山人参传说的艺术性初探》,《人参研究》1996年第4期,第43页。。王博凡则探讨了长白山人参传说的人民性问题②王博凡:《论长白山人参传说的人民性》,《人参研究》2008年第2期。,张雯虹考察了长白山人参故事与人参习俗中的道家生态观念③张雯虹:《长白山人参故事与采参习俗中所体现的道家生态观》,《人参研究》2013年第1期。,孙大志等探讨了长白山人参故事的民俗因素④孙大志等:《长白山人参故事的民俗因素研究》,《人参研究》2017年第4期。等等。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探究人参故事形成、流传的因素,有助于推动人参文化研究的深入。
当然,人参文化不仅局限于此,它还深入到人们的具体生活之中。蒋竹山认为:由于清代东北人参价格高昂,购买人参成为一种相当奢侈的消费行为,“所以成为皇帝赏赐给臣子的最佳礼物;而朋友之间的馈赠,也以人参当作是最昂贵的礼物,这种礼物文化尤其以乾隆、嘉庆年间最为普遍”⑤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4页。。通过对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的考察,赖慧敏亦有类似认知,认为“市面上参价更居高不下,成为官场贿赂上司的高贵礼品”⑥赖慧敏:《清乾隆朝的税关与皇室财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年12月,第89页。。
(六)人参与生态环境
人类对自然的索取要维持一个限度,否则就会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清代,时人已经有朦胧的生态平衡意识,并将之付诸实践。
丛佩远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认为随着人参产量的锐减以及需求的剧增,清初曾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措施。最初是扩大参场,雍正、乾隆时期实行了歇山轮采——即“把全部人参产区划分成几个大的区域,一个区域开采一定时间,另一个区域并相应封禁一定时间,以求保护人参的正常生长,延缓资源破坏的过程”⑦丛佩远:《中国栽培人参之出现与兴起》,《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第264-265页。。但是,歇山制度在实际中并未得到有效贯彻。更为严重的是,为了扩大和维持人参的产量,清政府还竭泽而渔,不断扩大采参队伍。最终,参源枯竭更甚。此后,诸多学者都关注到歇山轮采制度,但对于其研究则未能更进一步。
面对日益枯竭的参源以及社会上不断增长的人参需求,东北地方实行了人参栽培。但这些栽培的人参并不能得到皇帝和内务府的认可,并最终引发了嘉庆朝的秧参案。秧参案的主要官员受到了处罚,但参源不足的问题并未解决。栽培人参继续存在并逐步发展起来。道光时期,秧参种植“已经由查禁到弛禁再到合法化了”,光绪年间,还被纳入到国家税课系统⑧刘贤:《长白山人参栽培史小考》,《东北史地》2004年第7期,第58页。。
人参栽培的发展是野生参源严重不足的结果,它的出现虽不能完全改善生态环境的现状,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参源的不足,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三、研究的特点与展望
40年来,有关清代东北人参的研究,不乏力作。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大量利用地方和中央档案以及地方志等文献,研究较为扎实。其二,研究问题较为集中,主要研究人参政策及人参变价,但对人参流通过程与方式等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其三,研究视角的拓展,突破了历史视角,从商品角度、医疗角度深化了东北人参的研究。①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8-260页。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增多以及档案的利用日趋便利,研究视角的扩大,东北人参的研究也应该有新的趋势。对此,蒋竹山有过深入的思考,认为人参研究应置于全球视野之下,从全球医疗史、药物流通史、疾病、环境与医疗的全球视角深化。其实,就目前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人参研究。
首先,应加强东北人参与宫廷的研究。清宫是东北人参最为重要的消费场所,无论是药用,还是膳食需用,为数甚多。更为重要的是,咸丰以前,皇帝及后妃中高寿者众多,乾隆皇帝更是寿高89岁。此外,康熙、嘉庆、道光都寿过花甲。还有孝庄文皇后、孝恭仁皇后、孝圣宪皇后等亦臻高寿等等。这其中与宫中人参使用之间不无关系。随着清宫档案的逐步开放,其研究亦应随之跟进。还需注意的是,宫中女眷利用人参美容养颜,这是人参的又一重要用途。对此问题的研究,更能促进我们今天对人参的了解和使用。
其次,应加强东北人参销售史的研究。目前学界对人参贸易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务府人参的变卖方面,对其运作的具体过程并不清楚,对于这些人参如何为销售地的人们所接受等方面研究较为薄弱。蒋竹山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始,应该有更为深入的研究。
最后,应加强人参管理与东北地区发展关系的研究。清代东北人参的采集、贸易并非完全属于官方的行为,它需要更多群体、力量的介入。但毫无疑问的是,官方机构在其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而流民、商人的加入则对官方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吉林将军、盛京将军等的参务管理早已超出了人参的范畴,还要将流民的管理、商人的管理纳入到日常的管理体系之中,这都是清代东北地方管理的重要内容。此外,参商、采参流民等人的活动亦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亦是今后研究应该注意的地方。
此外,东北人参在清代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中国,朝鲜、安南等都有所知,甚至安南国王还设法购求。这反映了怎样的历史,亦需我们不断追问、探讨。总之,东北人参的研究仍大有空间、大有可为,而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后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加强理论修养,不断开阔视野,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不断深化东北人参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