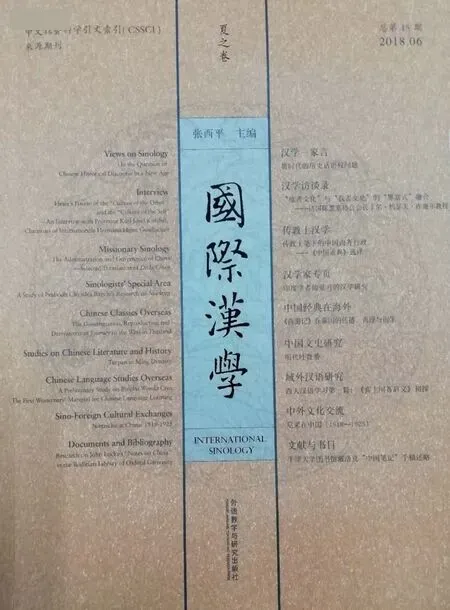印度学者师觉月的汉学研究*
2018-01-23
印度国际大学中文教授那济世(Arttatrana Nayak)在为《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撰写有关印度学者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1898—1956)的条目时指出:“印度中印学家。为20世纪中印古典学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做出了具有原创性的贡献。”①中印联合编审委员会编:《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详编上”,那济世撰,张忞煜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583页。应该说,这种评价基本上合适,因为它大体上概括了师觉月涉及汉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方面。如对其著述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师觉月的身份的确远非汉学家(或中国学家)这一标签所能囊括。本文在介绍师觉月的汉学研究成就前,先对现代印度汉学萌芽的时代背景做一简介。
一、现代印度汉学萌芽及其时代背景
放眼当今学术界,印度汉学无法像德国、法国、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的汉学或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汉学那样,成为一门显学,但印度文明的悠久历史与中印文化的千年关系又使人难以释怀:印度应该也有自己悠久的汉学研究传统。非常遗憾的是,印度没有类似法国汉学、德国汉学、美国汉学的前现代传统。例如,印度学者戴辛格(Giri Deshingkar,1932—2000)指出:“在印度的中国学研究迎来自己的时代以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印度从来没有自己的汉学传统……印度中国研究最大的弱点是,印度学者的语言能力很差。”②Tan Chung, ed., Indian Horizons.Vol.43.New Delhi: 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 1994, pp.500-501.从印度学者的内部视角肯定了印度汉学缺乏近代基础的尴尬事实。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看似反常、实则合理的学术现象呢?
历史上的中印交流要早于中国与欧美各国的交流。由历史记载看,近代以前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大特点是,印度对中国的影响一直处于“贸易出超”的状态。因此,欲了解中国的印度记载或汉译佛经概况并非困难,但如考察印度的中国记载却又非常不易。某些学者将此归结为印度来华僧人的文化优越感或宗教使命感所致,也并非空穴来风。③这方面的分析,参阅周宁:《 “我们的遥远的近邻”——印度的中国形象》,《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在中国长达千年的弘法传教史上,有名或无名的天竺高僧不计其数,当其回到印度后,并未留下多少关于中国历史、文学、哲学、宗教的心得体会。印度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尔(Romila Thapar)说:“众所周知,与中国或地中海世界的古代历史相比较,印度早期的历史记载是模糊的。印度的文献资料只能确认归属于某一段时期而非某个准确的年代。”①Romila Thapar,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arly India 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 “Chronology”, New Delhi: Penguin Books,2003.我们自然可用印度人自古不好历史记载等表面因素进行解释,但或许可以这样说,印度古人具有文化优越感或宗教优越意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精髓的译介。印度学者D.M.达塔(Dhirendra Mohan Dutta)指出:“文化傲慢(cultural vanity)不是一种真正文化的标志,自负会导致停滞不前。到了我们该发自肺腑地扪心自问的时候了:千余年之间,当中国与日本以自己的语言翻译了我们如此之多的作品、西方学者翻译了许许多多此类经典而丰富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时,我们又以自己的印度语翻译了哪怕一种中国、日本的巨著吗?然而,谁能否认孔子、墨子、杨朱、孟子、老子、卓越的禅宗大师和其他人智慧学说的全部内在价值?这些智者矗立在人类文明的真正高峰上。”②Kshitis Roy, ed., Sino-Indian Studies.Vol.5, Parts 3 & 4, Santiniketan: Visva Bharati, 1957, p.39.没有译介,自然没有研究。虽然有些学者勉力搜寻古代印度接受、传播中国文化的例子且略有收获,但整体看来,并不足以完全推翻这样一种基本判断:以弘法高僧为代表的印度古人对于向天竺国传播中国文化兴趣不大,否则,车载斗量的印度梵文古籍一定会留下足够令人惊喜的蛛丝马迹。关于这一点,师觉月指出:“古代中国文献揭示了悠久的中印关系。奇怪的是,印度方面的文献对两国的交流记载甚微。不过,考底利耶的《政事论》提到了中国丝和中国布,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提到了中国。我们不能确定这些作品的成型时间。”③Prabodh Chandra Bagchi, India, India and China: Interactions through Buddhism and Diplomacy: A Collections of Essays by Professor Prabodh Chandra Bagchi.Compiled by Bangwei Wang and Tansen Sen.London, New York, Delhi: Anthem Press,2011, p.205.
随着近代印度、中国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印知识分子直面交流的机会几乎断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亡国灭种的民族忧患,加上西方文化的特殊魅力,中印两国知识精英对对方的研究自然受到极大的限制。
由此可见,无论是古代来华后返回印度的高僧,还是近代文化交流几乎隔绝条件下的印度知识精英,他们限于各种主观、客观的因素,缺乏足够的汉学研究动力和兴趣,自然也就难以留下多少有价值的汉学研究著述(当然不能排除由于历史资料匮乏而被淹没在世人视线外的极少数例外)。因此,戴辛格所谓“印度从来没有自己的汉学传统”,确属正见。
国内外学界几成共识的是,现代意义或曰欧美意义上的印度汉学萌芽、草创于20世纪初,它与新时期的中印文化互动、西方东方学家列维(Sylvain Levi,1863—1935)等造访印度和印度智者远涉重洋学习包括汉学在内的东方学以探究印度古代文明的世界地位及其“含金量”等因素密切相关。
印度学者指出:“1918年,加尔各答大学为印度历史文化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了一门‘中国语言文学’课程,为将东亚研究提升到学术高度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④哈拉普拉萨德·雷易著,蔡晶译:《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概览》,载蔡枫、黄蓉主编:《跬步集:深圳大学印度学研究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1页。中国学者认为:“1918年加尔各答大学开设了中国语言和文学课,这是近代印度大学里研究中国学的第一个步骤。”⑤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两位学者在论及印度的中国研究或中文教学时,均不约而同地提到1918年这个关键词。尽管加尔各答大学的中文课影响不大,但它毕竟是印度汉学萌芽期第一声清脆的独立鸣叫,因此将其称为印度现代汉学的萌芽似不为过。与师觉月师承的法国汉学相比,印度汉学的萌芽可谓姗姗来迟。1688年,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奉命来华,开启了法国汉学的序幕,由传教士转为汉学家的包括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和李明(L.D.Le Comte,1655—1728)等多人。1814年12月11日,雷慕沙的汉语讲座被视为西方汉学的开始。⑥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4—165页。由此可见,印度汉学比之法国汉学的开端,至少晚了二百多年。对于人文学科而言,两百年的距离不是一个小数。这也是当今印度汉学始终难与法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汉学相提并论的重要前提之一。
印度作为中国文明的伟大邻居,其汉学研究之所以出现这种“怪相”,某些关键因素亦如前述。19世纪中后期至1920年左右,中印之间的交流非常少。20世纪初,虽然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译介印度文学作品,中印文化界人士仍旧缺乏正常的面对面交往。自1924年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访华后,中印两国文化交流方才得以逐渐恢复和开展。
20世纪初,中国人对印度历史、文学、哲学、佛学等知识领域所进行的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已经开始。印度方面,在1921年国际大学创办之前,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这说明了印度汉学缺乏前现代积累的真实一面。鉴于此,国际大学鼓励和支持西方学者来印度教学和研究,鼓励师觉月等印度学者远涉重洋求取东方学的“真经”。“国际大学的创办,在促进印度的中国研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学在该校课程中占特殊重要的地位。”①《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第229页。这便是师觉月开启汉学与印度学研究之路的时代背景。
二、师觉月的学术生涯
对一般中国人而言,师觉月可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甚至对许多研究南亚现实问题的专家而言,都显得有些陌生,但对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学者而言,他的名字不可谓不响亮。
1898年11月18日,本名Prabodh Chandra Bagchi的师觉月出生于当时属印度、现属孟加拉国的杰索尔(Jessore)。②关于师觉月生平的介绍,参考以下几书相关内容:Haraprasad Ray, ed., Contribution of P.C.Bagchi on Sino-Indo Tibetology.Kolkata: The Asiatic Society, 2002, pp.111-115;师觉月著,姜景奎等译:《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4—206页;金克木:《金克木集》(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524—525页;郁龙余等著:《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1—490页。师觉月的印度原名之姓Bagchi属当地望族婆罗门阶层。他自幼天资聪颖,成绩优异。他在加尔各答大学学习古代史,于1920年获得硕士学位。校长A.穆克吉(Asutosh Mukherjee,1864—1924)聘其为加尔各答大学研究生系讲师。
1922年,师觉月被A.穆克吉派往圣蒂克坦(Santiketan)即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所在地,跟随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列维学习汉语、藏语和法语等东西方语言。列维当时受泰戈尔之邀,来国际大学做客座教授。和列维建立师生关系,成为师觉月学术研究的重要起点。
1923年7月,师觉月受印度政府奖学金资助,赴法国进行为期三年的高级研究,随列维和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éro,1883—1945)等学习东方学。1926年秋,师觉月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在法国留学四年,对师觉月的印度学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研究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③关于师觉月接受法国东方学传统影响的具体分析,参见王琼林:《师觉月的汉学研究》,第三章《法国东方学对师觉月的影响》,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48—60页。向达先生评价伯希和等师觉月的导师时说过:“法国的汉学家因能运用比较语言学的工具,加上对于中亚、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中国的渊博的历史、地理知识,所以在汉学研究上能有光辉灿烂的成就。他们所用的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及对于一个问题的新的看法,新的解释,这都不是我们的乾嘉学者所能办得到的。”④向达:《悼冯承钧先生》,载冯承钧著,邬国义编校:《冯承钧学术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80—681页。师觉月的印度学研究便带有明显的列维式或伯希和式风格。他所继承的法国汉学传统使其受益匪浅。
1927年,师觉月关于中国汉译佛经的两卷本法语博士论文《中国佛教藏经:译者与译文》(“Le Canon Bouddhique en Chine les traducteurs et les traductions)出版(共742页),这可视为现代印度中国学(汉学)研究的正式开端。根据相关记载,师觉月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以下简称《印中》)的初稿首次发表于《大印度学会》(Greater India Society)杂志1927年(第2期),而非一般学者所记载的1944年。因此,将1927年视为印度汉学研究或“中印学”正式诞生或正式开端之年似更合理。①有学者指出:“可以说,《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于1944年的出版正式确立了‘中印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这一论断似乎值得商榷。参见《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第198页。
1926年至1945年,师觉月供职于加尔各答大学。近二十年里,他积极参与印度语言学会的工作,被任命为孟加拉亚洲学会研究员和印度文学院(Sahitya Academi of India)的成员。师觉月还分别于1929年、1937年在巴黎和加尔各答先后出版了法语版的两卷本《两部梵汉词典:利言〈梵语杂名〉与义净〈梵语千字文〉》(Deux Lexiques Sanskrit Chinois: Fan Yu Tsa Ming de Li Yen et Fan Yu Ts’ien Tseu Weu de Yi-Tsing),该书共计 559 页。
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国际大学设立中国文化研究项目,师觉月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国际大学,出任项目主任。“泰戈尔是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灵魂和源泉,紧随其后的便是谭云山和师觉月。如果说谭云山建构了物理形态上的中国学院,那么师觉月则以其持之以恒的学术研究充实了中国学院。”②《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第485页。在师觉月的主持下,《国际大学年刊》(Visva Bharati Annals)第一卷即创刊号如期出版,该卷刊载了几篇佛经和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其中包括《撰集百缘经》(Avadanasataka)和《义足经》(Arthapadasutra)选译,《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朝贡典录》《殊域周咨录》和《明史》选译。该期还刊载了论文《浅议〈撰集百缘经〉及其汉译》(“A Note on the Avadanasataka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和《帕坦时期的孟加拉与中国政治联系》(“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Bengal and China in the Pathan Period”)。它还介绍了两部佛藏中的药书及其选译。该卷作者、译者包括白乐天(Prahlad Pradhan,1910—1982)、巴宙、师觉月、泰无量(Amitendranath Tagore)和沈兰真(Satiranjan Sen)等。③Prabodh Chandra Bagchi, ed., Visva Bharati Annals. Vol.1, Santiketan: The Visva Bharati, 1945.
1945年,师觉月创办了以中印文化关系史和佛教研究为主要探索对象的期刊《中印研究》(Sino-Indian Studies)。根据季羡林于1947年撰写的《期刊简介:〈中印研究〉》一文可以发现,它主要登载佛教研究与中印文化关系研究相关的论文或译文。季先生指出,中国学者很少注意欧洲和日本学者关注的中印文化关系领域,印度更无人关注。这是一大遗憾,师觉月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他(师觉月)在1945年创办了《中印研究》,是季刊,每年一、四、七、十,四个月出版。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关于印度历史和文化的材料,翻译印度已经佚失而在中国译文里还保存着的典籍,此外当然也涉及中印关系的各方面。根据我上面所谈的,这刊物本身已经有很大的意义,尤其是当中印两方面都正在努力恢复以前的文化关系的时候,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④季羡林:《季羡林全集》(第13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2页。
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在北京大学设立印度讲席,师觉月获聘,成为在北京大学担任讲席教授的第一位现代印度学者。1948年,师觉月回国,继续任教于国际大学。1952年,师觉月随印度独立后的首个访华代表团访问中国。1954年4月,他出任国际大学校长。1956年1月19日逝世。1959年,其遗稿英译本《释迦方志》由国际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概述
谭中认为,师觉月在法国追随乃师著名东方学家列维,于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印度,成为现代印度的第一位汉学家。⑤谭中:《现代印度的中国研究》,《南亚研究季刊》2011年第1期,第89页。之所以称其为“第一位汉学家”或现代印度汉学鼻祖,是因为以《印中》为代表的师觉月著作可以视为现代印度中国研究的开山之作、拓荒之作或划时代标志。
《印中》这本两百来页的小书,主体部分自1927年首次在刊物发表以来,先后于1944年(印度)、1950年(印度)、1951年(美国)、1971年(美国)、1975年(美国)、1981年(印度)和2008年(印度)出版七次。印度学者评价该书说:“这是一部开创性的作品,它首次向通晓英语的学者展现了许多甄选自原始中文文献以及法德专家著述的重要资料。”①《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引言”,第1页。日本学者中村元(Ten Nakamura)认为,该书“不愧是博学的师觉月博士的著作,虽是小册子,但内容详实有趣。遗憾的是,书中的引证均未注明出处。书的主要内容是叙述两国历史上的交往”②转引自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方广锠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6页。。因此,该书的几位汉译者不得不大量地以“译者注”的方式代为疏解。这可视为该书的一个瑕疵。
《印中》主要涉及以佛教为沟通媒介的中印古代文化交流史,具体涉及中印古代物质交流、人员往来、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概况、印度接受中国文化影响与中印文明的共同点和差异处等重要方面。师觉月利用丰富的中文和梵文资料,围绕佛教这条文化“红线”,对中印古代文化交流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仔细梳理。师觉月的这本书使印度的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站在一个理想的起点上,有的洞见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③参阅尹锡南:《印度的中国形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6—180页。
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介绍古代中印交通路线和历史接触。作者具体叙述了三条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还重点介绍了龟兹、敦煌、室利佛逝等地的简况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具体贡献。第二章介绍古代印度来华传教高僧。第三章介绍古代赴印取经的中国高僧,主要介绍法显、玄奘和义净等三位著名高僧的事迹和中国官员王玄策四次出使印度的史实。他对玄奘的评价是:“不仅在唐朝,而且在所有时代的中印文化关系史上,都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人是玄奘。”④Prabodh Chandra Bagchi, 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1951, p.68.第四章介绍佛教在中国的历史传播亦即佛教中国化历程。第五章介绍卷帙浩繁的中国佛教典籍。师觉月认为:“不求助中国如此热心保存给后代的文献,不仅是佛教历史,就连印度文明史的各个方面都无法得以合理地研究。”⑤Ibid., p.145第六章介绍印度艺术和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师觉月注意到佛教艺术在华传播中的变异现象,即印度元素、西域元素和中国本土文化的融会。
就师觉月的中印文明融合说而言,第七章《两大文明的融合》和第八章《中国和印度》非常重要。在第七章的开头,师觉月提出了中印文明融合说:“中印两个民族住在不同的地域,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设若这样的两个民族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平台(common platform)上对话,并为创造一个共同文明(common civilization)而齐心协力,它们这么做,或许有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还要深刻得多的缘由。两个民族的文化和社会观念存在许多共同之处……同样信仰某种神圣的秩序,依赖相同的传统力量和奉行相似的社会观念,这是中印两大文明的历史特征。”⑥Ibid., p.174.这里所谓“共同的文明”,其实便是中印文明融合说的代名词。关于“共同文明”的概念,师觉月继而举出一些例子加以说明。如中国的“天”和印度的“伐楼那”(Varuna)都与神圣秩序有关。他指出,佛教对于缔造中印“共同文明”益处甚大。
在印度汉学界,师觉月有一个开创性的理论建树即中印文化双向交流说。他指出:“印度与中国的文化联系似乎是纯粹的单行线(oneway traffic),因此没有谁认真尝试寻觅中国对印度生活与思想的影响……不过,即使稍微留意一下,也能发现中国对印度生活与思想的影响。”⑦Ibid., p.197.为此,他在第八章着力探讨中国对印度文化的影响。他说:“印度极大地帮助了中国文明的发展。”⑧Prabodh Chandra Bagchi, Indological Stud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Santiniketan:Visva Bharati, 1982, p.95.他还发展了这一视角。他同意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的观点,即梨和桃来源于中国。他还补充说,朱砂(硫化汞)、瓷器、各种蚕丝(Cinamsuka)以及茶和荔枝的种植都应该来源于中国。他还探索了中国哲学家老子的《道德经》对印度宗教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尽管这些结论甚或探索本身也许还存在学术观点的分歧,但它的确已为师觉月的中印文明融合说亦即“共同文明”说成功奠基。
吹毛求疵地看,师觉月的《印中》在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的引证注解方面相当粗疏,这给研究者、翻译者带来了理解和查证的极大困难。此外,师觉月的某些译文与中文原著如《法显传》存在明显差异,他在理解原著方面或许还存在不足,解读古代汉语的功力稍欠火候。作为国外汉学家,这种现象并非个案,因此并非不可理解。
四、佛教探索与中印交流研究
国内学者一般将师觉月称为汉学家或佛学家,但少数中国学者和部分印度学者并非如此。例如,金克木说过:“本世纪(20世纪)初期,印度有三位‘汉学’博士,都不是到中国学习汉文得学位的,而且学习目的也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印度本国,学汉文为的是利用汉译的佛教资料……他们不是‘汉学’博士而是印度学博士。”①金克木:《金克木集》(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524页。印度学者认为:“师觉月的著作为印度学家的研究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②《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概览》,第231页。两位学者的身份界定,对师觉月而言是基本合适的。因此,另一位印度学者的评述较为契合师觉月的学术身份:“迄今为止,在印度,师觉月在印度学领域所展示的特殊才能是非凡的,这便是关于印中关系的研究。在现代印度学者中,师觉月的学术成就近似于联结印度学(Indology)和汉学(Sinology)的一座桥梁。”③Prabodh Chandra Bagchi, Indological Stud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Memoriam”, Santiniketan: Visva Bharati Research Publications, 1982, p.IX.事实上,师觉月用力最多的两个研究领域确属印度学与佛学(主要包括印度佛教经典与中国汉译、藏译佛经),而其汉学研究大体上是围绕这两个领域而衍生的结晶。从研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看,他跨越了中国、中亚国家和印度等南亚国家,有时甚至超越了上述范围,这显示了他的学术视野之广。这与他师承以列维为代表的法国汉学传统不无关联。
师觉月的佛学研究涉及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就印度佛教研究而言,师觉月既探索佛教的源头,也考察佛教衰落之因(应属印度佛教史范畴),还研究佛教的微观细部,并英译部分巴利语和梵语佛经。例如,他在写于1946年的《原始佛教经典和语言》(“On the Original Buddhism, Its Canon and Language”)一文中,先结合佛经的汉译和藏译,对大众部、根本说一切有部、上座部等部派佛教的发展演变进行介绍,再对佛教原典采用何种语言传播、梵语和巴利语关系如何、佛教原典的外延和内涵、原始佛教的内涵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探索。他大量引用德国学者盖格(Wilhelm Geiger,1856—1943)、奥登伯格(Hermann Oldenberg,1854—1920)、吕德斯(Heinrich Luders,1869—1943)、英国学者里斯·戴维斯(T.W.Rhys Davids,1843—1922)和法国学者列维等西方的东方学家的观点,再融合自己的思考,形成最后的结论。他认为:“因此,毋庸置疑的是,佛教的原始语言就是摩揭陀语(Magadhi)。巴利语能否代表摩揭陀语?斯里兰卡的传统说法使我们以为巴利语确属摩揭陀方言,不过,因为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巴利语不能视为摩揭陀语。”④Ibid., p.8.他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佛教代表了印度文明的国际化……因此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一种印度的文化重建,可以忽视佛教文明的研究。”⑤Ibid., p.23.
在汉译、藏译佛经研究方面,师觉月也有不凡造诣。如将这一领域归入印度学研究或印度佛教研究范畴,似无不可,因为它们的源头正是印度梵语、巴利语佛典。这或许是金克木先生称师觉月等三人为“印度学博士”的原因之一。师觉月的法语版博士论文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师觉月涉及藏译佛经的论文有《彰所知论》(“Chang So Che Lu, Jneya Prakasa Sastra”),涉及汉译佛经的论文包括《佛说八大灵塔名号经》(“The Eight Great Caityas and Their Cult”)、《无畏三藏禅要》(“Bodhisatttva-sila of Subhakarasimha”)、《汉译〈迦叶仙人说医女人经〉残卷》(“A Fragment of the Kasyapa Samhita in Chinese”)、《佛说十二游经》(“Twelve Years of the Wandering Life of Buddha”)等。师觉月充分发挥自己擅长母语即梵语和巴利语的天然优势,结合自己熟悉的汉语、藏语、日语、法语等外来语言的优势,对上述印度佛经的中国译本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探索。
在佛教与中国关系的研究方面,师觉月的成果值得关注,除了前述的标志性著作《印中》外,相关论文包括《安息早期在华佛教弘法僧 》(“Some Early Buddhist Missionaries of Persia in China”)、《印度对中国思想的影响》(“Indian Influence on Chinese Thought”)和《佛教在中国的发端》(“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m in China”)等。他认为:“印度佛教对中国人生活与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印度对中国思想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主动适应中国人的思维方式。”①Ibid., p.78.在中印古代交流领域,师觉月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论文,如《帕坦时期孟加拉与中国的政治联系》(“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Bengal and China in the Pathan Period”)、《坦焦尔的中国钱币》(“Chinese Coins from Tanjore”)等。
作为一位倾心佛教研究的学者,师觉月对汉译佛经的利用达到了出奇、出新的效果。例如,在《罽宾与迦湿弥罗》(“Ki-Pin and Kashmir”)一文里,师觉月利用汉译佛经和中文史料如《前汉书》与《后汉书》等,对克什米尔在中国史书中的各种称呼进行考证,最后确认罽宾与迦湿弥罗等是同一个地名。②Ibid., p.406.在发表于1946年的论文《禁蜜舍与德米特流士》(“Krmisa and Demetrius”)中,师觉月还利用《大方广菩萨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和《天譬喻经》等汉译佛经,对禁蜜舍和德米特流士这两位东西方历史人物所负载的印西古代交流进行文化考古。
顺便提一下,师觉月与同时代以及后来的许多印度学者一样,在参考和利用伯希和、斯坦因等西方的东方学家的研究成果时,并未深究这些西方人如何不择手段,在敦煌等地骗取、掠夺中国古代文化宝藏的卑劣行径。例如,斯坦因对自己在敦煌藏经室如何诱骗王道士而取得中国经卷的自叙是:“到了半夜,忠实的蒋师爷自己抱着一大捆卷子来到我的帐篷之内,那都是第一天所选出来的,我真高兴极了。他已经同道士约定,我未离中国国土以前,这些‘发现品’的来历,除我们三人之外,不能更让别人知道。于是此后单由蒋师爷一人运送,又搬了七夜,所得的东西越来越重,后来不能不用车辆运载了……因此我们立约,用施给庙宇作为修缮之需的形式,捐一笔款给道士作为酬劳。到最后他得到很多的马蹄银,在他忠厚的良心以及所爱的寺院的利益上,都觉得十分满足,这也足以见出我们之公平交易了。”③斯坦因著,向达译:《西域考古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04—205页。或许是师觉月当时并未读到或知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自叙,或许是他选择性遗忘,他在著述中从未提及此类让中国人痛彻心扉的故事。这一点在后来接续师觉月学术血脉和理路的印度著名学者、印度文化国际学院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主任、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 ICCR)副主席洛克希·钱德拉(Lokesh Chandra)的著述中依然如故。他们还在著述中不约而同地将西藏视为独立的“国家”,且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仍然如此。例如,巴帕特(Purushottam Vishvanath Bapat,1894—1991)主编的佛教通史的目录第一、二页均将中国西藏放在Northern Countries(北方国家)的标签下,与中国、韩国、日本、尼泊尔等主权国家相提并论。④P.V.Bapat, ed., 2500 Years of Buddhism.New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Government of India, 1971.这是主编巴帕特和执笔者郭克雷(Vasudev Vishvanath Gokhale,1901—1991)等人对中国西藏地区归属问题的模糊认知与错误判断。无独有偶,师觉月的文中也有类似表述,他将Tibet(西藏)归入all these countries(所有国家)之列。①Prabodh Chandra Bagchi, Indological Stud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Santiniketan: Visva Bharati Research Publications, 1982, p.8.当代中印关系曲折坎坷,以上几位现代著名学者的历史地理书写,从一个人们很少注意的角度,形象而有力地说明了许多问题,也迫使中国学者思考未来在这一方面如何与印度学者对话沟通。由此可见,通过对对象国研究而升华为文化认同、情感共鸣,对于师觉月、巴帕特、郭克雷和洛克希·钱德拉等许多印度学者而言,是一个永远在路上且无法抵达终点的过程。令人欣喜的是,这一现象在当代印度学者如玛妲玉(Madhavi Thampi)和狄伯杰(B.R.Deepak)等人那儿,已经有所改观。
综上所述,师觉月担得起“汉学家”这一美誉。尽管金克木断言其为“印度学博士”,印度学者首先将其视为印度学家而非汉学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纳入汉学家的视野进行考察和研究。从印度学、佛学到汉学,师觉月不仅搭建了一座成功的跨越喜马拉雅的文化桥梁,也成功地自我摆渡为印度现代学术史上的第一位汉学家。王邦维先生指出:“师觉月研究的范围很广,如果要对他的研究做一个全面的评价,可以看到,他不仅仅是一位‘汉学家’,也不仅仅是‘印度学家’,他也不仅仅研究佛教,而是跨越多个方面,只有一个词,‘印中文化研究’,大概可以概括他研究的领域。他在这方面研究的特点,其实值得我们仿效和学习。”②Prabodh Chandra Bagchi, India and China: Interactions through Buddhism and Diplomacy, “Introduction”.采用王邦维先生自译。总之,师觉月的创见和研究特色,在缺乏前现代深厚汉学基础的20世纪印度汉学界显得尤为突出,并在某种程度上映照出20世纪中后期印度学界研究中国的某些不足或空白。
《汉学先驱巴耶尔》一书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张西平教授主编的“著名汉学家研究丛书”之一。该书基于西方著名汉学家巴耶尔(Gottlieb Siegfried Bayer,1694—1738)的著作、手稿和信件,以专著形式描述巴耶尔开始汉语语言、文献研究工作,并在各种驱动下为这项事业献出毕生精力的学术历程。本书由现代丹麦学者龙伯格(Knud Lundbaek)教授用英文撰写,由北京语言大学王丽虹教授翻译为中文。译稿成书之时,北京外国语大学柳若梅教授、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叶向阳博士、张明明博士均为此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