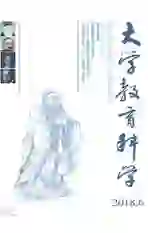师范院校百年发展中的“师范”坚守与时代流变
2018-01-22刘丽群刘景超
刘丽群 刘景超
摘要: 在师范院校百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从培养模式来看,早期师范教育以封闭式培养为主,交织着综合模式,当前形成了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校共同参与的开放性教师教育体系;从课程设置来看,师范教育早期课程带有鲜明的师范特色,但师范性与学术性的争论却不断,当前甚至出现了教育类课程弱化、师范院校“去师范化”的不良发展势头;从师范院校层次来看,师范院校整体升级,但教师培养的质量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性提升。师范院校能否及如何坚守“师范”属性,是一个需要引起足够关注与重视的时代命题。
关键词:师范院校;师范坚守;师范性;学术性;院校升格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8)06-0105-06
收稿日期:2018-06-23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评审委项目“湖南省高校师范生顶岗实习现状调查研究”(XSP18YBZO42)。
作者简介:刘丽群(1976-),女,湖南华容人,教育学博士、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教育政策研究,长沙,410205;刘景超,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湘潭,411201。
教育是立国之本,师范是教育之母。我国历来有“首重师范”的光荣传统,梁启超就曾发出过“故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的感叹[1]。新中国成立后,师范教育一直被摆在重要位置,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时,我们也不无忧虑地看到,近年来,一些综合性大学相继撤销教育学院,一些师范院校纷纷“脱帽”。在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政策驱动下,在教师教育综合化的宏观背景下,师范院校是继续坚守师范教育还是走向综合,这一具有方向性、战略性也是决定性的问题越来越严峻地摆上日程。基于此,本文试图以师范教育百年发展史为纵坐标,以师范院校的培养体系、课程设置、教育质量等三个核心命题为横坐标,绘就一幅师范院校百年发展动态图,以透过历史,反观当下,照见未来。
一、独立建制抑或开放培养——师范院校独特地位的百年之争
“立国以教育为根本,教育以师范为根本。”[2]师范教育对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陶行知先生甚至把发展师范教育与拯救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3]应该说,在整个教育长河中,对师范教育的重视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但教师究竟是由独立建制的师范院校封闭式培养,还是其他非师范院校都可参与的开放式培养?这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摇摆不定的论题。
(一)历史的轨迹:封闭培养为主线,交织着综合模式
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师范学院,这是我国师范教育的起步,然而官方独立师范教育出现的标志则是1904年1月清政府正式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它将师范教育分为初级和优级师范学堂两级,并在教师任用标准、教师的奖励及约束外籍教员等方面作了相关规定。此后,《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1907)、《检定小学教员章程》(1909)、《师范教育令》(1912)、《高等师范学校规程》(1913)以及《师范学校规程》(1916)、《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1919)等文件相继颁布,对师范教育的目的、学额、学科及修业年限、入学退学及学費、服务等进行了规范。这一时期,教师基本是由相对封闭的师范院校独立培养。但1922年民国政府先后颁布《学制系统改革令》和《学校系统改革令》,要求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与普通大学合并,或改为普通大学,师范教育的封闭体系开始打破。1925年,湖南教育会颁布《改革学校系统案》,指出“教授中等学校之技术,易于初等远矣, 本无须专门养成”“更无独设一校之必要”[4]。1932年的《改革我国教育之倾向及其办法》中更是明确要求“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应立即停办”[5]。从1923年到1938年长达15年间,我国基本没有独立的师范院校,师范教育走向开放化。直到1938年7月27日,“教育部”的《师范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单独设立师范学院,或者将师范学院设置于大学中,这标志着我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综合化模式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始终强调和重视师范教育。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必须大力发展和加强从幼儿师范到高等师范的各级师范教育;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将师范教育视为培养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母机,指出“各级政府要努力增加投入,大力办好师范教育。”在《优先办好师范教育,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打好基础》一文中,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着力强调:“师范院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和造就精于从事素质教育的师资。”[6]这一时期,我国主要以苏联为模板,建立并不断完善独立封闭式师范教育体系,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95年。
(二)现实的困惑:师范院校是独守师范教育还是走向综合化?
1.教师教育大学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师范院校封闭、独立培养教师的局面被打破。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明确规定:“中国公民凡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具备本法所规定的学历或经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具有教育教学能力,经认定合格后,可以取得教师资格”。1995年国务院颁布《教师资格条例》,详尽规定了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的具体要求。两项法规的相继颁布,意味着非师范院校毕业生只要符合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也可按程序依法申请取得相应的教师资格。至此,封闭型师范教育体系已失去其独立存在的法律基础。随后在1998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综合大学可以培养教师”的规定得到确认;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布,明确提出“鼓励综合高等学校和非师范类的高等学校参与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工作,探索在有条件的综合大学试办师范学院”。以上规定为封闭型师范教育向开放型教师教育转型奠定了政策基础。2001年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开放型教师教育体系的确立与完善。至此,教师培养打破了由高等师范院校独立、定向培养的模式,由“定向型”向“非定向型”转变。
2.教师教育大学化与师范院校综合化
随着封闭型教师培养模式的打破,高等院校同时涌现了两股潮流:一是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二是师范院校走向综合化。综合性大学举办教师教育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模式:(1)整合全校原有的教育资源组建形成新的教育学院(或教育科学学院、教育研究院、师范学院等),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等;(2)设立相对独立的师范学院(延边大学等);(3)设立“二加二、三加一”培养模式的教师学院(四川大学等);(4)将教师教育各专业分散到文、理、外等专业学院的混合模式(北华大学等)[7]。与此同时,一些师范院校开始走向综合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为首的部属师范大学陆续开设了大量非师范专业,迈出了向综合性大学转型的步伐[8]。
3.综合性大学教育学院的撤销与师范院校独特地位的重申
随着“双一流”建设政策的驱动,综合性大学又开始掀起一股撤销教育学院的新浪潮。从2015年4月起,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等综合性大学,相继不同程度地调整或裁撤其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学院等机构。如,兰州大学校方在2016年7月15日正式颁文宣布,裁撤其教育学院及内设机构[9]。针对“师范性”弱化这一现实问题,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界则开始重申和强调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和独特性。2017年1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现有的181所师范院校一律不更名、不脱帽,聚焦教师培养主业。”[10]我国著名学者顾明远先生也提出应“重建师范教育体系”,他指出,“我们有1200万名中小学教师,如果没有专门培养教师的学校不行,还是要把师范院校办好。”[11]在此大形势下,兰州大学在学校官网发文称“根据我校教育学科发展的特色,结合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于2018年6月重建高等教育研究院[12]。
二、专业课程抑或教育课程:师范院校课程设置的定位之惑
课程是学校培养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载体,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培养模式,都需要通过课程来达成其目标。“师范性”是师范院校的核心定位,如何凸显其师范性关键在于课程设置。我国师范院校的课程设置在一段时间内有鲜明的师范特色,但师范性与学术性孰重孰轻,争议不断,当前甚至出现了教育类课程弱化、师范院校师范性淡化的不良势头[13]。
(一)教育类课程是师范院校凸显师范性之根本
教育类课程的开设是师范院校区别于一般大学的主要标志,强调教师要懂教授之法、管理之术。关于这一点,蔡元培先生早就有过经典论述:“知识富矣,而不谙教授之术,则犹之匣剑帷灯,不能展其长也。”[14]1938年,陈立夫在第一次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会稿中指出:“师范教育制度之特点,在肯定教育事业之专门性,教育事业惟受有专业训练者,使能担任,此乃师范教育之前提。”[15]廖世承也认为,“师院与(大学)文理学院之设系虽同,而主旨不一,例如大学有西洋文学系,师院则有英语系,英语系不应以西洋文学为研究对象,应以英语的基本训练为首要。”[16]国际上也有类似观点:“凡要当教师的都应首先学好教育专业课,这就正如医生和律师的专业课一样”,由此他们也非常强调教育理论课程及教育实习实践课程,以充分凸显“师范性”[17]。可以说,教育类课程开设的必要性是由师范院校自身性质及其培养目标决定的,它是师范院校“师范性”的体现,是师范院校区别于其他高校的特色所在。
(二) 师范院校的课程设置:突出师范性还是强调学术性?
我国师范院校课程设置的“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由来已久。持“师范性”观点者认为“学者未必是良师”,教师是专门人才,主张师范院校应增加教育类课程的开设比例;持“学术性”观点者则认为“良师必然为学者”,主张师范院校应加强文理科和学科专业知识的课程。这一争论贯穿于我国师范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中。
早期有关师范教育的相关政策十分强调教育类课程的设置以凸显师范院校的师范性。1904年《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初级师范学堂着重在教育学,故特增此科,其钟点除经学外为最多”;1912年“教育部”制订的《师范学校规程》也特别指出:“教育要旨在授以教育上之普遍知识,尤当详于高等小学校及国民学校教育之旨趣方法,习其技能,并修养教育家之精神[18](P440)。1913年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文件,加大了教育学科在总课程中的比例;1916年的《修正师范学校规程》还专门提及板书技能,“习楷书行书及草书并练习记录与黑板写法,兼课教授法。”[18](P467)但自1922年到1949年,關于师范教育“师范性”还是“学术性”的争论异常激烈。1922年《壬戌学制》中规定师范院校无需单独设立,师范大学课程内容与普通大学同。尽管1925年10月的《新学制师范科课程标准纲要》中规定后期师范学校与高中师范科的教育类科目占总学分的26.09%[19],但是《纲要》并未能在全国普遍实施。可以说,1922~1931年,师范院校的“师范性”跌入了谷底。1932年12月和1933年3月,《师范学校法》和《师范学校规程》先后颁布,规定单独设立师范教育,师范学校开设教育类课程。1934年9月《师范学校课程标准》颁布,又适当增加了教育类课程的课程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课时数已占总课时数的26.33%[20],“师范性”得到空前彰显,这一特色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以苏联为蓝本独立设置师范院校,“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主要表现为师范院校内部课程结构的分歧。“文革”前基本倾向是重点师范大学强调“学术性”,普通师范院校突出“师范性”。在课程政策上,1952年,教育部颁发《师范学校教育计划(草案)》,教育专业课程所占总学时只有17.16%[21]。此计划经1953年、1956年两次修订,加强了教育专业课程与教育实习的比重(占教学总时数的30%),使课程的“师范性”特色愈加突出[22]。在1960年召开的师范教育改革座谈会上,有人指责师范院校过于强调“面向中学”从而导致“学术性”低,提出师范院校要“向综合大学看齐”,精简教育类课程,取消教育实习。故中师和高师教育理论课程学时数锐减至仅占总学时的8%和6.5%左右[23](P23-26)。师范院校“师范性”地位骤降。此后,教育部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于1961年10月颁发《关于中等师范学校教育计划调整方案》,对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教育类课程(包括教育实习)所占比例提升至约13%,“师范性”再次回升。
1980年6月的全国师范教育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师范院校因过于强调“师范性”而导致“学术性”低下,主张打通、融合重点师范大学与综合大学。这种强调“学术性”的观点,客观上弱化了“师范性”,师范性课程减少。这一时期中师和高师教育学科课程学时数约占总学时的14.58%和5.18%左右[23](P23-26)。1989年《三年制中等师范学校教学方案(试行)》颁布,其中教育理论课时占13.7%,教育实践的时间为十周[24]。1995年教育部制定《大学专科程度小学教师培养课程方案》,建议开设教育学、心理学、中外教育简史、小学生心理指导、小学教育科研方法、小学语文教材教法、小学数学教材教法、班主任工作概论等科目。此方案虽未对教育类课程的学时比例加以明确,但相对前一时期中等师范教育类课程设置内容更丰富、“师范性”目标也更高。
(三)教育类课程的整体式微与师范院校的“去师范性”
师范教育自创立之日起就一直在探索与寻找“学术性”和“师范性”之间的平衡点,然而“重学术轻师范”的现象却始终存在。教育类课程在总课程中究竟应该占有多少比重,一直没有明确一致的规定。1904年颁布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及《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中,教育类课程的比例分别为26.11%和14.81%[25];1912年的《师范学校规程》中教育学科课程(不含各科教学法及教育实践课程)所占比重为13.77%[18](P460);1934年9月颁发的《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规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课时比例为26.33%;1938年的《师范学院规程》中教育专业课程占总学分的27%;1950年《北京师范大学暂行规程》中对教育类课程的比例规定为30%;1954年《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规定教育类课程占比为22%~25%;而到了1963年以后,教育类课程遭到冷遇,其比例大幅下降,教育学、心理学、中学各科教材教法共占总课时比例的5%~9%[26];1981年,《高等师范院校四年制本科文科三个专业教学计划试行草案》颁布,规定教育类课程应占教学总时数的5%[27]。改革开放后,我国师范院校教育类课程只包括教育学、心理学、分科教学法和教学实习等四门课程,并且这些课程通常作为师范生的公共必修课而非“专业课”开设。它们“与公共外语、体育、计算机、哲学等课程一起,同处于一个层次”[28]。教育类课程在师范院校的式微,使得师范院校“去师范化”趋向日益明显。
三、学历提升与能力欠佳:师范院校升级背后的素质之忧
中等师范教育(中师)在我国存在有百年之久。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各省份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中等师范学校,专门培养小学教师。学生们接受师范“全科教育”,文理兼修,体艺兼备,专业功底扎实,综合素质较高,他们为我国的基础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随着师范院校升级之潮的驱动,中师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师范院校在转型升级,师范生的学历在不断提升,但师范生的素质是否也随之提升?答案不一定是绝对肯定的。
(一)师范院校升级之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师范教育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建立起由中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师范学院和师范大学构成的三级师范教育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中师层次的教师培养开始逐渐取消,并加大教育硕士层次教师培养的比例。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由教育部颁发,其中提出实施“跨世纪园丁工程”,要求到“2010年前后,具备条件的地区力争使小学和初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分别提升到专科和本科层次”,我国中师教育的升格与转制运动由此开始。此后,教育部于1999年3月颁行《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提出“到2010年左右,新补充的小学、初中教师分别基本达到专科和本科学历”。这一系列的政策目标,一方面导致众多中师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据统计,我国的中等师范学校数量自1998年起直线下降,由1998年的875所下降到1999年的815所,到2010年时只有141所[29]。而另一方面,全国掀起了师范院校的升级之潮。以2011年与2002年的数据进行对比:高师本科院校数由96所增至108所;师范专科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则大幅减少,师专由140所减少至36所,中师由815所减少至132所;师范毕业生学历层次明显提高,本专科毕业师范生和中师毕业生之比从2002年52.5∶47.5提升到2011年的90.1∶9.9[30]。师范教育办学层次实现了从中师、大专和本科的“旧三级”向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新三級”的转变。
(二)师范生教学能力缺失之忧
师范院校纷纷升级的目的是提升教师学历并以此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此举顺应了时代潮流。然随之而来的现实却是,近年来师范院校培养的学生质量欠佳,甚至有用人单位作出师范生质量下降的判断[31]。一些用人单位表示,高师毕业生普遍缺乏敬业精神、教学技能欠佳,他们大多难以胜任岗位。而以前的中师毕业生,多是“教学能手”,他们师德好、技能好,有上进心,还非常稳定[32]。为什么教师学历提升了,但教学能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这一定程度上与师范院校“师范性”的式微相关。中师教育尽管学历层次很低,但其“师范性”特色彰显:比如非常重视教学基本功训练,普通话、三笔字、吹拉弹唱、简笔画是学生每日必修功课;重视与小学的交流,每所中师学校都有一所或多所附属小学作为学生固定的教学实践基地;琴房、舞蹈室常常人满为患……由此培养的中师生综合素质强,教学基本功扎实,爱岗敬业。而当前的师范生培养“师范性”式微,由此导致师范生经验缺乏、教学实践能力弱,难以胜任基础教育实践工作。在专业技能方面,传统中师十分重视的教学基本功训练在当前师范生培养中日渐淡化,传统的“三笔一话”未能很好地传承,师范生的教学基本功弱。一位长期负责教师招聘的中学校长如是说:“在一场微型课招聘试讲中,60%多的学生在黑板上一个字都没写。而个别写的也存在字体差、板书设计混乱的状况,甚至还有不少写错别字的。”[33]虽为个案,但也侧面反映出当前教师培养中的一些问题。另外,师范教育对教学实习实践关注不够,也容易导致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有学者针对初入职的师范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6.45%的毕业生认为自己“所学专业知识未能很好契合实际教学需要”;71.33%的毕业生认为自己“不能较好地把握课堂教学的重点、难点及课堂节奏”,78.12%的毕业生认为自己“缺乏处理课堂突发事件的经验和能力”[34]。
(三)“中师现象”之思
随着中师退出历史舞台,本科层次的师范教育开始成为主角。但是,这些高学历的师范生,并不一定因为学历的提升而必然得到社会更高的评价与认可。有基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招的老师,还都是师范类毕业的,但是,学生质量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师范院校在转型升级,师范生的学历在提升,但教师的素质并没有随之得到根本性的提升,“有不少农村的学生、家长、学校领导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反映,昔日的中等师范毕业生甚至比如今的大专毕业生和本科毕业生还管用。”[35]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也坦言:“我们的师范教育改革走了弯路。比如说为了提高学历,就取消中等师范学校,而且把整个中师取消了。”[11]当然,时代在发展,我们的师范教育不必重新回到中师,但中师重全科教育、重教学实践、重教学基本功等方面的做法与经验,仍值得我们今天学习与借鉴。
当前,师范院校在与综合性大学的竞争中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师范院校的传统优势学科及特色学科不断受到综合性大学的挑战,其优势已日渐式微;另一方面,师范院校学科体系覆盖面窄、延展性差的特点,使得师范院校在当今以知识和技术创新为特色的知识经济社会背景下,不具备与综合性高校竞争社会资源的优势,甚至处于劣势。面对此种情形,师范院校是坚守师范属性、继续深耕、做优做强师范教育,还是寻求突围、转型升级成为综合性大学?这始终是我国教育领域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也是攸关师范院校办学方向的现实难题。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论师范[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C].北京:中华书局,1989:34.
[2]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332.
[3]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八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139.
[4]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三辑上册)[M].上海:華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63.
[5] 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60.
[6] 李岚清.优先办好师范教育,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打好基础[J].中国高等教育,1996(11):5.
[7] 赵炳辉.综合大学教师教育的优势、问题与对策分析[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4-5.
[8] 于兴国.转型期中国教师教育政策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94.
[9] 沙璐.兰州大学撤销教育学院引争议[N].新京报,2016-08-27(A13).
[10] 赵婀娜.师范院校当聚焦教师培养主业[N].人民日报,2017-01-17(05).
[11] 李新玲.顾明远历数师范教育改革犯下的错——呼吁重建师范教育体系[N].中国青年报,2015-06-29(09).
[12]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诚聘海内外英才[EB/OL].http://ldrsc.lzu.edu.cn/lzupage/2018/08/06/N20180806090332.html.2018-08-06.
[13] 马洪正.在“学”与“术”之间——我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的艰难选择[J].教师教育研究,2016(3):102-107.
[14] 黄军昌.蔡元培的师范教育思想[J].师范教育,1986(3):31.
[15] 陈立夫.对于高级师范教育之希望[J].教育通讯,1938(11):2.
[16] 廖世承.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师范教育[J].中华教育界,1947(1):16-34.
[17] 朱宁波.现代国外高师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4(1):73-75.
[18]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19] 崔运武.师范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56-57.
[20] 郑登云.中国近代中师课程的沿革[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6(3):45.
[21] 季银泉.百年回眸:初等教育师资职前教育课程的设置与改革[J].南通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12):81.
[22] 李友芝.中国近现代师范教育史资料:内部交流资料[C].北京:北京师范学院,1983:1326.
[23] 高谦民.试论中国师范教育的经验和教训[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3).
[24] 严启英.中等师范教育课程文化的百年进程及其启示[J].贺州学院学报,2014(09):115.
[25]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04):403-431.
[26]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557-559.
[27] 杜静.我国教师教育课程存在的问题与改革路向[J].教育研究.2007(9):78.
[28] 杨朝霞.论师范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的改革[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5):40.
[29] 刘秀峰.辉煌与消逝:中等师范教育发展的回溯与反思[J].教育发展研究,2017(10):60.
[30] 许涛.转型中谱写新篇——教师教育改革发展十年巡礼[J].人民教育,2012(17):6.
[31] 朱旭东,李琼.论我国教师教育的二次转型[J].教育学报,2014(5):98.
[32] 李益众.高师毕业生为何站不稳三尺讲台[N].中国教育报,2001-05-21(02).
[33] 李柯.师范生教师教育技能的反思与重构[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4(1):118.
[34] 李飞鸿.师范院校学生的职业适应性水平及其提升策略——基于湖南省K师范院校学生的问卷调查[J].当代教育论坛,2017(4):89-90.
[35] 向宇循.昔日中师教育留给我们的启示[N].中国教育报,2010-03-03(08).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over 100-year development, the normal institutions have changed greatly. First,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has evolved from a closed one or a comprehensive one at the early stage to an open education system in which the normal institutions play a dominating role while other universities also play a part. Second, the curriculum in the past had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eacher-training, but the debates on its normal and academic nature have never been ended. At present, there is even a trend of weakening educational courses and the normal nature. Third, the normal institutions have been upgraded, but the quality of teacher training has not been radically enhanced. Therefore, whether the normal institutions can adhere to the normal nature is still an issue that needs to be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in this era.
Key words: normal institutions; adherence to the normal nature; teacher-training character; academic nature
(責任编辑 陈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