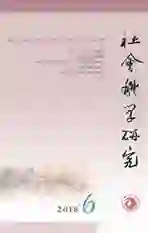孟子“从兄”说义理发微
2018-01-22田探
〔摘要〕 孟子为何要以“从兄”为“义之实”?在两千多年的孟子研究中,只有朱熹的弟子向朱熹提出过此问题,却并未获得满意回答。孟子的“从兄”说,在形态上源于宗法礼制的“兄道”,却又具有新的义理内涵:他以“从兄”来确立人伦中所应有的“敬”的原则,并展开而为“贵贵”与“尊贤”的统一。这种统一既肯定了道德理性的正当性,也肯定了贤臣代表民意参与政治的政治正义理想。道德理性与政治正义的统一,就体现在作为“制度之骨干”的君臣关系之中。孟子所理想的君臣关系是“贤王与贤士忘势相交”的兄弟朋友式关系,表达了他对民本君主理想政体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是他严厉批评各种“以顺事君”“尊君卑臣”之思想观念的基础。周代礼制文化虽为孟子提供了若干思想资源,却并不合乎其君臣人格平等的理想。因此,孟子只好将其立论的前提置于三代之前的尧舜时代,将“尧舜之道”解释为“孝弟而已”的伦理原则。这就是孟子必然要以“事亲”“从兄”为“仁”“义”之“实”,以展开其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是他“言必称尧舜”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从兄立敬;君臣互敬;道德理性;政治正义;理想政体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6-0129-08
〔基金项目〕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儒学视域下的空间正义研究”(106112015SDJSK47XK31)
〔作者简介〕田探,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哲学中心讲师,博士,重庆 401331。
一、问题的提出
孟子曾指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汉代赵岐《注》曰:“事皆有实,事亲从兄,仁义之实也。”〔1〕题为宋代孙奭的《疏》曰:
此章言仁义之本在孝悌。盖有诸中而形于外也。……孟子言仁道之本,实在事亲是也;义之本,实在从兄是也。……由此言之,则事亲之孝为仁之实,凡移之于事君者,则为仁之华也。从兄之悌为义之实,则知凡移于从长者,是为义之华也。……盖当时有夷子不知一本,告子以义为外,故孟子以是言之,而救当时之弊者也。〔2〕
孙氏以“仁义之本在孝悌”来解释仁义之“实”,可谓一种本源论解释。这固然也符合孟子的有关论述,然而,“义之实”就是“义之本”吗?对此,朱熹做了专门解释。他说:
此数句,某煞曾入思虑来。尝与伯恭说:“实字有对名而言者,谓名实之实;有对理而言者,谓事实之实;有对华而言者,谓华实之实。今这实字不是名实、事实之实,正是华实之实。仁之实,本只是事亲,推广之,爱人利物,无非是仁。义之实,本只是从兄,推广之,忠君弟长无非是义。事亲从兄,便是仁义之实;推广出去者,乃是仁义的华采。”〔3〕
朱熹只认此“实”字为“华实之实”,并进一步将其解为“根实”,他说:“事亲从兄是仁义之根实处,最初发得来分晓。”〔4〕根实论仍是本源论,从本源论出发,朱熹解释此二句说:
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事亲。义主于敬,而敬莫先于从兄。故仁义之道,其用至广,而其实不越于事亲从兄之间。〔5〕
从本源论的角度说,朱熹的解释固然也可以自圆其说。然而,孟子此说的本意就真的没有本质论的意义吗?如果真如朱熹所说,孟子此句中的“实”字,“不是名实、事实之实”,而只有本源论意义上的“根实”之意,那么,孟子何以不直说“仁之本,事亲是也。义之本,从兄是也”?何况,以“根”解“实”,于古无训。《说文》:“实,富也。从宀贯,贯为货物。”段玉裁《注》曰:“以货物充于屋下是为实”,“引申之为草木之实”。〔6〕《尔雅·释草》谓:“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7〕可见,“实”的本义是实物、财物,引申之而为果实,进一步就衍生出坚实、充满、事实、实际、实质、实在等义。朱熹以“根”释“实”,不惜在训诂上否认“实”字的本义,并不能得到学界的认同。清代的焦循就另做解释说:
仁义之名至美,慕其名者,高谈深论,非其实也。孟子指其为事亲从兄,然则于此二者有未尽,虽日驰骛于仁义之名,皆虚妄矣。〔8〕
显然,焦循正是从“名实”角度将“事亲从兄”释为仁义的实质性内容。焦氏立论的角度,可谓实质论。但焦循所谓“实”,乃指“事亲从兄”(孝悌)要能“尽”其“量”;如果“于此二者有未尽”,就仍不能算是“义之实”。何谓“尽”其“量”?他引全祖望《经史问答》之语曰:
孝弟之量,原未易造其极,故古今以来,所称孝弟,不过至知而弗去一层,其于礼乐二层皆未到;便到得知而弗去一层,已是大难。〔9〕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孝悌只是伦理义务,而礼乐是政教;若不能尽“孝悌之量”(这已是“大难”)推至于礼乐政教,就仍是“虚妄”,算不得“义之实”。而尽“孝悌之量”以至于礼乐政教的关键,乃是个有位无位的问题。焦循所引《经史问答》已有解释:
蔡文成以为舞蹈只是手足轻健之意,则是不过布衣野人之孝弟耳,孟子意中却不然。虽有其德,苟无其位,则一身一家之中,手足舞蹈之乐亦自在,而究未可以言礼乐之全量也。〔10〕
焦循最后表达自己的观点说:
仁义智礼乐必本孝弟乃实,孝弟必依仁义智礼乐,乃至本末兼该,内外一贯。说仁义而不本孝弟,说孝弟而不极于礼乐,皆失之也。〔11〕
这其实是在批评本源论未能做到“本末兼该”。焦氏将“义之实”释为“义的实质内容”是对的,但他从尽“孝弟之量”的角度来指出本源论之失,却未必有多少道理。实际上,本源论之失,并不在于忽视了对“量”的扩充,而在于掩盖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大问题:自从孔子以来,就以“事君”为“人之大伦”,例如,《论语·微子》篇载子路从孔子游于列国,遇隐者讥其奔走求仕而不知避世,子路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潔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钱穆说:“大伦即指君臣。”〔12〕那么,“君臣之义”就是“大义”。孟子同样将君臣父子视为人之大伦,他说:“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孟子·尽心上》)类似的表述在《孟子》中并不鲜见,例如:“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孟子·尽心下》),又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既然如此重视君臣之大伦,孟子何不以“君臣大义”为“义之实”,而必以“从兄”为“义之实”呢?焦循虽然批评本源论之失,主张“本末兼该”,但并未真正触及问题所在。倒是朱熹的弟子反复质疑朱熹本源论解释的正当性,如问:
“父子兄弟皆是恩合,今以从兄为义何也?”“事之当为者皆义也,如何专以从兄言之?”
尤其是有一位弟子问:
“五典之常,义主君臣。今曰‘从兄,又曰‘尊贤,岂以随事立言不同,其实则一否?”(朱熹)曰:“然”。〔13〕
依照这位弟子提问的逻辑,既然“五典之常,义主君臣”,那么,孟子为何不以“君臣之义”为“义之实”,却反而以“从兄”为“义之实”?但这一问题却似箭在弦上而未曾发出,写进《语类》中却突然转换为另一问题,乃使朱熹可以轻松地回答曰:“然”。是否这一问题确实难以回答而故作如此处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本质论的角度说,研究孟子者却不能不回答这一问题。
二、“贵贵”与“尊贤”——“从兄”说义理发微
①“礼”为“义之实”,则“义”为“礼”之内在义理。《荀子》:“义者,理也。”
我们首先需要阐明孟子“从兄”概念的内涵。《礼记·礼运》云:“礼也者,义之实也。”孟子以“从兄”为“义之实”,从外在形式看,似与宗法礼制有某种关联。清代的程瑶田曾指出宗法礼制的特点说:“宗之道,兄道也。大夫士之家,以兄统弟而以弟事兄之道也。”〔14〕仅从一种义务论的外在形态上看,孟子所讲的“从兄”正是源于这种“以兄统弟而以弟事兄”的“兄道”。但是,孟子却在“从兄”中注入了新的义理内涵。宗法礼制的根本精神是“亲亲”“尊尊”。王国维说:“周人以尊尊之义经亲亲之义而立嫡庶之制,又以亲亲之义经尊尊之义而立庙制,此其所以为文也。”〔15〕这种“亲亲”“尊尊”精神也被理解为“仁”和“义”,但此种意义上的“仁”“义” 是以宗族为本位的。《礼记·大传》曰:“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名曰重。一轻一重,其义然也。”郑玄注曰:“用恩则父母重而祖轻,用义则祖重而父母轻。”〔16〕这即是说,“亲亲”“尊尊”是以宗族为本位的。孟子也讲“事亲”“从兄”,却是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八口之家”的小家庭为本位的:“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
在孟子这里,“爱其亲” 就是“仁”,“敬其兄”就是“义”;概言之,“爱”即“仁”,“敬”即“义”,故朱熹说“仁主于爱,义主于敬”。值得强调的是,从“事亲”“从兄”到“仁”“义”之间,暗含着一个逻辑,就是要以“事亲”“从兄”来为其“仁”“义”思想提供“爱”与“敬”的新解释。孔子说过:“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礼记·祭义》)这证明孟子提出“事亲”“从兄”,就是为了“立爱”“立敬”,并以“爱”“敬”为“仁”与“义”的伦理新内涵。“爱”与“敬”不同于“亲亲”“尊尊”。“亲亲”“尊尊”具有为宗法礼制所限定的血缘亲情的狭隘性;而孟子所讲的“爱”与“敬”则可以行诸更为广泛的人伦关系,从而具有超越宗法礼制精神的普遍性伦理价值。孟子指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只要不是“妄人”,“爱”与“敬”施之于人,就一定可以得到回报,这就为“仁”“义”何以可能提供了根据。不仅如此,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四心”说进一步为“爱”与“敬”的可能性提供了人性论基础,从而为“仁”“义”何以可能提供了心性论根据。由此,我们说“恻隐之心”发而为“事亲”之“爱”就是“仁”;“羞恶之心”发而为“从兄”之“敬”就是“义”。在宗法礼制及其内在观念已经式微的战国时代,孟子以“事亲”“立爱”,以“从兄”“立敬”,使其“仁”与“义”均具有了超越宗族性的普遍性伦理价值,这既是对“仁”“义”理论的一种重建,也为宗法制解体后的社会秩序重建提供了新的价值和本体根据。限于主题,我们只就孟子的“从兄”说对其“义”的思想体系建构而展开论述。
“事亲”所立之“爱”与“从兄”所立之“敬”的哲学内涵是不同的。“爱”的情感趋向于人、我一体,而人、我一体意味着万物一体的哲学视域,这也就是儒家“仁”学的哲学内涵,故程明道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17〕 “敬”的情感却趋向于人、我之別。因为,“敬”就是“自卑而尊人”的情感。《礼记·曲礼》开篇就说:“曲礼曰:毋不敬。……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自卑而尊人”即把自我放在他人之下,这就体现着人与我的差别。人与我的差别则代表或者象征着宇宙间万事万物普遍的差别性,这种普遍存在的差别曾被荀子称为“分”。荀子从宇宙间事物差别的普遍性出发,来论证“明王”治国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社会有“分”。他说:
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
由此可见,“明王”是根据“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的原理来“制礼义以分之”的,因而礼义所具有的“分”功能,正是宇宙事物普遍差别性的体现。换言之,“义”作为制度之“礼”的内在义理①,本身就具有普遍差别性的哲学内涵。正因为“义”具有差别性的哲学内涵,它才能成为“仁”的调节者,使“一体之仁”在实践中成为“差别之爱”。当回到“义主于敬”的话题上时,我们可以判定:具有差别性哲学内涵的“敬”,就是“义”之所以为“义”的伦理内涵,这正如具有统一性哲学内涵的“爱”就是“仁”之为“仁”的伦理内涵。
①这样的“道德理性”,既有“规范”意义,又有“美德”意义。
从哲学上说,差别性的本质是矛盾性,故差别最终必然显现为矛盾。黑格尔说:
差别自在地就是本质的差别,即肯定与否定两方面的差别。……每一方面之所以各有其自为的存在,只是由于它不是它的对方,同时每一方面都映现在它的对方内,只由于对方存在,它自己才存在。因此本质的差别即是“对立”。〔18〕
作为具有差别性哲学内涵的“敬”,同样在本质上必然表现为“我敬人”与“人敬我”的矛盾对立。孟子以“从兄”的伦理概念所确立的“敬”的价值,作为“义之实”,也就必然使“义”表现出自身的对立性的内涵。孟子与万章谈到君臣相交的关系时说:“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下》)在儒家思想中,“长长”“贵贵”“尊尊”都可谓“用下敬上”,但长者未必都有位,故“长长”的伦理色彩较重;贵者、尊者必有位,故“贵贵”“尊尊”的政治色彩较重。《礼记·丧服四制》中说:“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孔颖达《疏》曰:“贵贵谓大夫之臣事大夫为君者也。……尊尊谓天子诸侯之臣事天子诸侯为君者也。”〔19〕可见,“贵贵”与“尊尊”虽有不同,但均可谓以臣事君。故赵岐《注》曰:“下敬上,臣恭于君也。上敬下,君礼于臣也。皆礼所尚,故云其义一也。”〔20〕依赵岐的解释,作为上下互敬的“贵贵”与“尊贤”,就是指君臣互敬,这二者虽是对立之两极,但皆是“从兄”所确立之“敬”。由此我们就找到了“从兄”的切实义涵,它应当包含“贵贵”与“尊贤”这样相互对立而统一的两极。
既然“贵贵”可解释为“敬君”,那么,“贵贵”也就意味着对以君权为表征的整个伦理政治秩序的敬重和服从。而对此秩序的服从,其实就是对礼义的服从。《孟子·尽心上》云:“无礼义,则上下乱。” 礼义即人道:“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可见,孟子思想中作为“人道”的礼义秩序,确有君臣父子之别的一面,但是,其重点是对对等性的伦理义务的强调而不是对政治等级的强调。如他说:“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人子、人弟、人臣各以仁义事其父、兄、君,这就是人的当然之则。而人人盡其该尽的义务,遵循其应该遵循的社会伦理规范,就是孟子所说的作为“人之正路”的“义”。这种对人伦秩序的敬重之“义”,既然是“行吾敬”,“非由外铄我也”,是“心之所同然”之“理”,那么,它正是今人所谓的“道德理性”。①
也正由于“人之正路”主要是对伦理义务的强调而不是对基于权力的政治等级的强调,所以,孟子之“义”的等级色彩较淡,具有较为鲜明的平等色彩,这突出地体现在他的“敬君”态度中。孟子批评杨、墨“无父”“无君”,证明孟子是主张“敬君”的。但孟子之“敬君”,乃是舜那样“怀仁义以事其君”的“事君”态度:
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上》)
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
如果其君不能“志于仁”,那就要“格君心之非”。因此,孟子的“敬君”之义,颇不同于孔子。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确立了儒家“君臣之义”的基本内涵。孟子则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上》)这可谓对子思“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21〕之思想的延伸。正因为如此,当时就有人认为孟子不敬其君。《孟子·公孙丑下》载景子对孟子说:“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孟子回答说:“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可见,孟子的“敬君”不是顺从君上之意志,而是要求其君行仁政,顺民心,这就是所谓“以舜之所以事尧者事君”。换言之,要求其君能够像尧那样真正代表社会整体利益,这就是孟子“责难于君”的“敬君”之义。孟子的“敬君”虽不同于他人的敬君,但仍属于“事君”之义务,故孟子的“君臣之义”仍属于孟子的道德理性。
“尊贤”之义亦有三重:其最直接的涵义就是孟子所谓的“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其次,是对贤者所代表的价值体系——“道”的尊崇与实践。自孔子讲“士志于道”以来,“以道自任”就是贤士的基本使命和本质规定。孟子曰:“礼义自贤者出。”(《孟子·梁惠王下》)荀子亦云:“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荀子·王制》)这都表明“尊贤”其实就是对贤者所代表的仁义礼智之价值系统的尊崇。最后,从根本上说,“尊贤”是对民心民意的敬重。因为,儒家之“道”最终的价值指向,是普通民众的生存利益。从《尚书》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观点,到孔子对圣人的本质规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再到孟子讲的“失天下”在“失民心”,“得天下”在“得民心”,乃至荀子讲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无不是以“民”为其“道”的终极目标。而作为“道”之承担者的贤士,就正是民心民意的代表者。《孟子·梁惠王下》载: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在这里,孟子首先肯定了贤者有乐,然后阐释了贤者之乐的内涵,乃是“与民同乐”,并要求王者亦能做到。正因为贤者是“与民同乐”,故能成为荀子所说的“民之父母”。余英时曾对中国古代士阶层的精神特质做了高度概括,他说:
知识分子以道自任的精神在儒家表现得最为强烈。……所以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22〕
也正由于贤士对自身利益的超越和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深厚关怀,乃能使贤士真正成为民心民意的代表者。从而,“任贤使能”“俊杰在位”的要求,就不仅是贤者对自己个人政治前途的追求,更是贤者代表民心民意参与政治的民本主义政治要求,这可谓儒家政治正义的核心内涵。也只有在此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中庸》所谓“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的深刻意蕴。
“贵贵”与“尊贤”虽是对立的两极,然而,“其义一也”,内在地要求着二者的统一,其统一性就体现在人君与贤士所构成的君臣关系之中。儒家所论的君臣关系,乃是在“道”的基础上既相统一又相矛盾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君作为社会秩序的代表者,必须要获得“道”的支持,即荀子所谓“故人主,天下之利势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荀子·王霸》)因此,人君不能没有贤士的支持。另一方面,士人入仕為臣以行“道”,“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是其天职。因此,君臣相合乃“道”之所需。但是,君与士在现实上又都是社会个体,不免都将其个体的私利欲求掺与其中,于是,君臣相合必然出现非常复杂的情况,这里不能详谈。孟子的“从兄”说所展开的“用下敬上”和“用上敬下”的统一,显然是从理想的君臣关系一面说的。而其所理想的君臣关系,乃是君与臣之间建立在“道”的基础上的平等友好关系。他指出:“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这里所强调的重心,乃是贤君与贤臣之间的“忘势相交”:人君不以自己的权势而骄臣(这就是“尊贤”),人臣亦不以人君有势而媚君(这就是“敬君”);君臣之间互尊互敬,真诚合作,这可谓建立在“道”的基础上的朋友兄弟式关系,有似于郑玄《六艺论》所谓古之时“君臣之接如朋友。”〔23〕孟子之所以追求这种关系,就因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实现“贵贵”与“尊贤”两大价值系统的统一;而这两大价值系统的统一,又正是孟子“从兄”说的逻辑归宿。
综上所论,孟子以“从兄”说“立敬”,展开而为“贵贵”之“义”与“尊贤”之“义”的统一。这种统一既肯定了道德理性的正当性(个体对君权所表征的社会秩序的敬重);也肯定了贤臣代表民意参与政治的政治正义理想。道德理性与政治正义的统一,不能不说就是儒家之“义”的核心内容和实质内涵。本源说就因不能达到对“从兄”的这层理解,故否定“义之实”为实质之“实”。“贵贵”与“尊贤”相统一的具体形式,正是“作为制度之骨干的君臣的关系”〔24〕,这种兄弟朋友式的君臣关系,实质上表达了孟子所追求的理想政体,即以君权为主导,以贤臣代表民意参与政治的君主民本政治体制。
三、以“从兄”为“义之实”的原因
阐明了孟子“从兄”说的义理体系,就可明白孟子之“义”虽然浸润了周礼的若干观念,但却明显超越了周礼精神。其一,在周礼中,“尊贤”只是“亲亲”“尊尊”的必要补充,如王国维说“周人之制度”:
皆由尊尊、亲亲二义出。然尊尊、亲亲、贤贤,此三者治天下之通义也。周人以尊尊、亲亲二义,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而以贤贤之义治官。故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盖天子诸侯者,有土之君也。有土之君,不传子不立嫡,则无以弭天下之争。卿大夫士者,图事之臣也,不任贤,无以治天下之事。〔25〕
《礼记·丧服小记》讲:“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根本没有提到“尊贤”。但孟子却将“尊贤”与“贵贵”设为两种平衡的价值,并追求二者的统一,这显然不同于宗法礼制精神。其二,“尊君或尊王,必然是内在于宗法体系的隐秘指向”〔26〕,故有人君“绝宗”之说。《礼记·郊特牲》说:“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礼记·大传》中又说:“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郑玄注曰:“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亲自戚于君。位谓齿列也,所以尊君别嫌也。”〔27〕这即是说,即使是君之亲戚兄弟也不能与其君称兄道弟。然而,孟子却理想“贤王与贤士忘势相交”,人格平等如朋友兄弟。孟子对周代礼制精神的超越,只能从其时代精神中寻求原因。
孟子的时代,君权独尊的思潮正在形成中,如商鞅就已提出君权独制说。《商君书·修权》谓:“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权制独断于君则威。”〔28〕但在另一方面,激烈的兼并战争,也早把“尊贤”意识推上了历史舞台,《墨子·尚贤上》说:“尚贤者,政之本也。”〔29〕魏文侯礼贤下士,更是闻名诸侯。《史记·魏世家》载:
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30〕
可以说,“尊君”与“尊贤”几成战国时代精神旋律中的“双调”。《淮南子·修务训》云:
段干木辞禄而处家,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其仆曰:“君何为轼?”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轼。”其仆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轼其闾,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趋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干木虽以己易寡人不为。吾日悠悠惭于影,子何以轻之哉!”〔31〕
“势不若德尊”之语,本是“道高于势”的另一种表达,出自魏文侯之口,可信度如何,姑且不论;但田子方也讲过“贫贱者骄人”“富贵者不能骄人”的话〔32〕,证明“德尊于势”的思想在士人中是存在的。至少,魏文侯将“光于德”与“光于势”相提并论,可证“尊君”与“尊贤”在当时均为社会所重。有学者指出:
君主专制政体是个历史形态,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战国时代的君主专制政体刚刚形成,其专制的程度还不像后世那样绝对化,各国之间又有不同表现。……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中,君权并非绝对不可侵犯,……确实还有那么一点‘民主遗风。〔33〕
孟子主张“敬君”与“尊贤”的平衡,正是对这种精神的发扬。
然而,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尊君”意识便很快压倒了“尊贤”意识,并发展为“尊君崇势”观念。与孟子同时的慎到就提出“贤不若势”的观点。《慎子·威德》云:
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34〕
在尊君崇势思潮的推动下,君主专制政体迅速发展,君权至高无上,远非昔日的尊君意识可比,君臣关系乃至转变为君臣-主仆关系。有学者指出:
君权高于一切,人人都要服从,已成为时代的共识,战国诸子百家在任何问题上都各抒己见,而谓君权高于一切则不约而同。〔35〕
于是,一种主张人臣单方面效忠君主的“以顺事君”的思潮兴起,反而批评称誉尧舜的儒家一派的君臣观是“反君臣之义”。《韩非子·忠孝》篇谓:“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孟子对当时“以顺事君”的思潮予以激烈地批评说:
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鄕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鄕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孟子·告子下》)
“为君辟土地,充府库”者,无疑是指法家。法家之事君,韩非子有过集中地概括:
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韩非子·有度》)
“为君约与国,战必克”,则明显是指纵横家。对于纵横家,孟子针对景春称其为“大丈夫”,而斥之曰:“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这并不只是对纵横家个人人格的批评,而是对纵横家及法家脱离道德前提的事君之道的批评,认为这是“长君之恶”和“逢君之恶”,(《孟子·告子下》)是“非义之义”。(《孟子·离娄下》)孟子对“以顺事君”的批评,实质上就是对当时各种尊君崇势思潮的批评和对已经显现的尊君卑臣之历史趋势的拒斥,从而使他的事君态度表现出以贤抗势的性质。上文中提到的景子,因为孟子讬疾以辞王命,不合于“君命召,不俟驾”之礼,就说孟子对齐王不敬。孟子回答说:
岂谓是欤?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公孙丑下》)
“不可召”体现了“德尊于势”的观念。在此种观念支配下,孟子甚至说: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
孟子的这种事君态度,代表了当时士人阶层在日益威严的君权面前不愿丢失自己人格尊严的普遍心态;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则是对儒家基本价值的捍卫。尊君崇势的思想发展到法家,尤其是韩非子,乃至于贬道德、反仁义。《韩非子·五蠹》篇中说:“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八说》篇则谓:“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故存国者,非仁义也。”更为偏颇的是,韩非在“人性自利”的人性观发酵下,把君臣关系完全说成“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相互交换、相互谋算的可怕关系。《韩非子·难一》篇曰:“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备内》中说:“人生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甚至,后妃、夫人及太子,都有希望其君早死,以保自己的既得地位者,人君还能相信谁呢?人君只能以高深的权术驾驭群臣,严密地防范他们,包括妻、子在内的身边每一个人,以防篡夺自己的权位。在《八说》中,韩非为人君献上了驾驭大臣之三法:“曰质,曰镇,曰固。亲戚妻子,质也。爵禄厚而必,镇也。参伍责怒,固也。……名实当则径之。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不然,而与其仇。此谓除阴奸也。”儒家基本价值被完全否定。
孟子“以贤抗势”的立场,使他很难再以“君臣之义”为“义之实”。孟子对 “以顺事君”的批评和对“尊君卑臣”的拒斥表明,他所要坚持的乃是以道德为政治之前提而又君臣人格平等的“君臣之义”。正因如此,即使传统的“礼制”文化为他提供了若干思想资源,却仍然必须超越。于是,孟子只好逾过三王,把他立论的前提置于三代以前的尧舜时代,将“尧舜之道”阐释为“孝弟而已”(《孟子·告子下》)的伦理原则,来安置其“仁”“义”思想的伦理学根基。这就是孟子不能不以“事亲”“从兄”为“仁”“义”之“实”的逻辑必然,也是孟子之所以“言必称尧舜”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2〕〔20〕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723,2723,2742.
〔3〕〔4〕〔13〕〔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56〔M〕//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1821,1822,1822-1823.
〔5〕〔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350.
〔6〕〔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40.
〔7〕尔雅·释草〔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2630.
〔8〕〔9〕〔10〕〔11〕〔清〕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532-533,534,534,534.
〔12〕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548.
〔14〕〔清〕程瑶田.宗法小记〔M〕//程瑶田全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137.
〔15〕〔25〕王国维.殷周制度论〔M〕//观堂集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468,472.
〔16〕〔19〕〔27〕〔唐〕孔颖达.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3).北京:中华书局,1980:1508,1695,1508.
〔17〕〔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M〕//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15.
〔18〕〔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54.
〔21〕郭店竹简·鲁穆公问子思〔M〕//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34.
〔2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4-25.
〔23〕毛诗正义·诗谱序疏〔M〕//十三经注疏(1).北京:中华书局,1980:265.
〔24〕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二卷〔M〕//儒家思想与人文世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111.
〔26〕陈赟.“继所自出”:“宗统”与“君统”之间的连接〔J〕.学术月刊,2017(9).
〔28〕商君书·修权〔M〕.诸子集成(5).北京:中华书局,1954:114.
〔29〕〔清〕孙诒让.墨子闲诂〔M〕.诸子集成(4).北京:中华书局,1954:28.
〔30〕〔32〕〔汉〕司马迁.史记·魏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82:1839,1838.
〔31〕淮南子·修务训〔M〕.诸子集成(7).北京:中华书局,1954:334-335.
〔33〕〔35〕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310-312,313.
〔34〕慎子〔M〕.诸子集成(5).北京:中华书局,1954:1.
(责任编辑:颜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