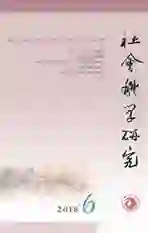无产品的劳动:后福特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
2018-01-22张一兵
〔摘要〕 后福特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方式已经被融入生产,劳动越来越转向没有终端产品的广义文化产业,在这种智力、政治与劳动的交融中,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接近非及物的表演艺术。这使得今天的诸众存在的去政治化,劳动和生活本身已经成为最大的政治,从而出现了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构序逻辑完全相反的意向。
〔关键词〕 维尔诺;《诸众的语法》;后福特资本主义; 文化工业; 无产品的劳动
〔中图分类号〕B5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6-0036-06
①维尔诺 (Paolo Virno, 1952-):意大利哲学家,左翼运動旗手。1979年因牵涉红色旅事件被捕,1982年被判刑12年,维尔诺上诉获释候审;1987他最终被无罪释放。1993任乌尔比诺大学哲学教授,1996年任蒙特利尔大学哲学和传播伦理学教授,现为罗马大学哲学教授。代表作为:《诸众的语法》(2003);《诸众:创新与否定之间》(2008)等。
②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The MIT Press, Cambridge,2004. 中文版:〔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董必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此书为维尔诺任卡拉布里亚大学传播伦理系主任时,于2001年所做的三次专题讲座整理而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MZD026)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23。
维尔诺①可能是意大利左翼理论思潮中阿甘本之外最有思辨能力的理论家之一。《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2003)②一书,是他讨论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时代的主体——诸众问题最重要的文本。在此书中,维尔诺对后福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思考,主要集中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问题上。在他看来,原先只是出现于政治行为中的语言与交流活动,现在越来越成为今天劳动者本身必备的基本技能和条件,当自动化生产成为物质生产过程的主导方面时,劳动者越来越转向没有终端产品的广义文化产业。在这种智力、政治与劳动的交融中,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接近非及物的表演艺术。这是维尔诺眼中后福特资本主义劳动活动的全新主体性特征。然而,维尔诺新劳动观的理论构序意向,却是否定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概念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我以为,他的这种构境思路是需要进一步深究的。
一、后福特时代:劳动、政治与智力的杂交
维尔诺明确说,之所以提出诸众作“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正是为了“解释后福特制生产方式(post-Ford mode of production)的一些显著特征”。这也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首先是今天后福特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当然,可以察觉,维尔诺所理解的生产方式与马克思对其的定义域边界已经有所不同,在他这里,“生产方式不仅意味着一定的经济构式(economic configuration),还是生活方式的复合统一(composite unity)”。〔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董必成译,55页。中译文有改动。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The MIT Press, Cambridge,2004.p.51.这里的configuration一词是重要的,它表征了一种复杂的构序方式,在我的构境论中,通常被表征为构式。更准确地说,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首先指证的不是经济构式,而是物质生产中的塑形和构序结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会历史性生成现代中的经济活动构式。比如在原始部族生活中,就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构式。实际上,维尔诺并非弄错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差别,他就是想指认,后福特资本主义中生活方式已经被融入生产,所以此处他重点想强调的是后福特式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复杂统一体。
维尔诺告诉我们,在传统人类存在经验的分类里,通常会有三个基本领域,即“劳动[或创制(poiesis)]、政治行动[或实践(praxis)]和智力[或精神生活(life of the mind)]”。〔1〕他说,这种分类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后来又由汉那·阿伦特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年):德籍裔美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哲学家。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人的条件》(1958)、《精神生活》(1978)等。在《人的条件》一书得到细描和展开。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用vita activa表示三种根本的人类活动:维系生命的劳动(Labor);人造事物的、世界性的(worldliness)工作(work);相应于人的复数性(plurality)的、在人们之间的行动(action)。vita activa一词直接的意思是积极生活,其构境源于希腊-中世纪的vita contemplativa(沉思生活)。〔2〕显然,阿伦特的三种活动并非能对应维尔诺这里三种生活经验的重构,特别是作为第三种活动的智力。维尔诺自己说,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也对这三大领域的界划持肯定态度。一般看来,
劳动是与自然界的有机交换:新物品的生产,一个重复的和预知的过程。纯粹的智力具有隐士般的、不显眼的特征;思想家的冥想逃避旁人的注意;理论思考减弱世界的表象。政治行为不同于劳动,政治行动介于社会关系之间而不是介于自然物质之间;它与可能性与不可预见性相关。〔3〕
如果认真一点,维尔诺这里的表述在每一个构境层中都是不精准的。一是劳动作为一种主体活动,并不直接与自然交换,更不会孤立地创造财富,它只是生产和制作过程的一个环节,劳动与自然的交换,只发生于生产和制作这样一种直接与自然交换的及物性对象化过程。在生产和制作的终点上,才会出现劳动产品。所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一般物质生活新材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出发。并且,劳动生产如果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恰恰是不可预设的,只是再生產中的惯性实践才会是重复和预知的。不过,维尔诺同时使用的poiesis(创制)一词是有趣的,它表征了一种以后可以从劳动塑形中分离出来的构序性。二是praxis(实践)作为一种感性的物质构序活动,则首先是物质生产,政治斗争也只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阶级的产生)才历史发生的。我以为,维尔诺此处表述最大的问题是缺失了历史性维度。三是隐士般的智力活动的表述过于外表化,也缺位了作为现实关系的基础。还有,维尔诺提出这三种基本存在经验现象时,竟然没有交代三者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三种存在经验并不是维尔诺要肯定的东西,维尔诺告诉我们,在今天的后福特资本主义现实中,上述这个经典的三分法已经失效了。“也就是说,纯粹的智力活动、政治行动和劳动之间的界限已经逐消失了”。 〔4〕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断言,因为之后的一些新的判断都基于这一断言。在维尔诺看来,这三种活动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杂交(hybridization)”,或者说,过去人们三种不同存在经验的边界已经开始模糊起来。
维尔诺认为,这种杂交的表现首先是创制(劳动)与实践(政治行动)的并置(Juxtaposition)。维尔诺说,“当代的劳动已将许多最初标着政治经验的特性整合进了自身。创制在许多方面已具有实践的特征”。 〔5〕这是不容易理解的奇怪说法。他自己指认说,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是阿伦特。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已经发现了“20世纪的政治已经成为一种新客体的制作(fabrication of new objects)”。在这一点上,政治在模仿劳动。阿伦特在《人的条件》第五章第31节的标题就是“制作对行动的替代”。〔6〕这里的行动是政治空间的缘起。阿伦特认为,用制作代替行动自柏拉图始,而之后的亚里士多德则是“最早提出用制作的形式来处理政治事务与占统治的政治体系的人”,在阿伦特看来,“制造替代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沦为一种实现所谓‘更高目的的手段” 〔7〕并且,是霍布斯开始“把制造和计算两个新概念引入政治哲学”。 〔8〕可是,阿伦特并没有直接讨论20世纪的政治与制作的关系,这应该是维尔诺自己的延伸发挥。然而,维尔诺很自信地说,他的观点与阿伦特正好相反,他的构序方向与阿伦特是逆向的,因为,在20世纪后福特资本主义现实中,不是政治模仿劳动,而是“劳动已获得政治行动的传统特色”。维尔诺认为,
在当代的劳动世界里,是我们发现了“出现在别人面前“,发现了与他者在场(presence of others)、与新工艺创建、与偶然性、与为可预见性和可能性本质上的精通等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后福特制的劳动、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从属性的劳动(subordinate labor)、发挥人才和专业资格的作用等,从世俗的眼光看,已更多地与政治行动相关。〔9〕
我前面已经说过,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的构序逻辑是维尔诺此处诸众的政治哲学构境的重要背景。所以这里可以看到,维尔诺这段表述中的大部分观点都在承袭阿伦特关于行动与劳动的界划,而维尔诺只是将原来阿伦特表征行动的构序质点转入劳动的描述中来了。原来在阿伦特那里,“不像劳动那样为情势所迫而强加于我们,也不像工作那样由功利所激发”,人能够行动的事实意味着:“他能预见不可预见的东西,能做几乎不可能的事”,并且,在行动中,人通过言行中表明他们是谁、积极地展现其个性,从而使自己出现在他者在场的人类世界中。〔10〕行动的这些特质,并不出现在传统的劳动和工作之中。而维尔诺认为,在今天的生产中,已经包含了许多阿伦特定义政治(行动)的东西,比如劳动必须与他人交往、劳动本身的技艺化和创造性,以及可预见性等等。维尔诺认为,今天后福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特质的这种转变,能够帮忙我们理解今天诸众存在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或者反过来讲,劳动和生活本身已经成为最大的政治。
二、劳动成为没有产品的表演
劳动成为政治,这是一个很难入境的命题。我们可以通过维尔诺对劳动特质变异的分析来逐步地体知。首先,维尔诺认为,在后福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带有政治色彩的劳动已经成为没有产品的精湛技艺(virtuosity)。这也是一个很怪的说法。前面我们刚刚说明了,主体性的劳动活动必须融入生产和制作过程,才会塑形自然物质对象进而生产出劳动产品,可为什么会出现“没有产品的劳动”呢?我们来看维尔诺自己的解释。
维尔诺说,在过去,通常只有一些艺术大师那里才会出现才艺精湛这样的生存状态,这里,他列举了钢琴家、舞蹈家、演说家、老师和牧师。可以注意到,维尔诺刻意去除了有“产品”的画家、作家、雕塑家、作曲家等艺术大师。在艺术大师那里,一是活动本身就是成就,比如一个舞蹈和一次音乐会的演出,艺术大师“没有将这种活动本身客观化成终端产品(end product),没有成为‘制成品(finished product)”。其实,表演性艺术的这一特征在今天已经被彻底改变了,因为舞蹈、音乐演出现在都被现代化的录像录音技术制作成激光视频产品和CD,甚至老师的授课也通过Mooc生成终端产品。这使得维尔诺此处的对比性分析缺少了说服力。二是这些特定的艺术活动本身是“一种需要他者在场(requires the presence of others)的行动,只有在观众面前,这种活动才存在”。 〔11〕艺术表演、演讲和布道,没有听众是无法进行的。这基本是准确的。我们在大学的课堂里上课时,一是要有学生在场,当然,这种在场并非人的肉身在,而是思在,我讲课反对学生做笔记,而是希望他们能跟着我一起思考,这种在场是双向的互动。二是上课也没有具象的产品,讲授是塑形学生的灵魂,当然这不是指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方法论的训练。在这里,维尔诺说到了我们在阿甘本讨论中已经遭遇过的那个著名的钢琴家古尔德,他甚至拒绝向观众现场表演。当然这是一个例外。其实,古尔德也是在1964年的洛杉矶音乐会之后才不再公开演出的。有趣的是,拒绝了公开演出的古尔德却制作唱片。
①丰田主义(Toyotaism):由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创造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也是后福特主义生产管理方式的典型代表。
自然,讨论这些表演性艺术大师的“有他人在场互动”和“无产品”的精湛才艺,并不是维尔诺真正要引导我们进入的思想构境,他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引出对马克思的批评。他顺势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艺术大师的表演,在马克思关于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定义中,却是被统统排除的。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这些“没有终端产品”的活动都“不产生剩余价值,于是都被打回非生产性劳动(non-productive labor)的领域”。〔12〕维尔诺反讽地说,可是,令马克思没有想到的情况出现了,在今天的后福特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性的劳动整体上具有表演艺术(virtuosic performance)的特性”。维尔诺的这个判断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因为,他并没有回答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形成的根本性问题,即这些没有产品的艺术表演如何创造价值。维尔诺认为,
在后福特制时代,劳动需要一个“公开组织的空间”,并且类似于艺术表演(没有终端产品)。这个公开组织的空间被马克思称为“合作”(“cooperation”)。可以这么说:生产性的社会力量发展到一定水平,劳动合作将语言吸收了进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政治行动的复合体。〔13〕
显然,维尔诺这里试图突显的构序原则包括:一是今天的后福特劳动(生产)从工厂车间已经扩展到整个社会,在第三产业的服务劳作中,公开的合作空间是其发生的前提条件;二是相当多的服务工作并不产生具体的产品,比如以语言交流为主体的咨询工作;三是今天的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其实,维尔诺的这一判断是不够准确的。一是服务业虽然已经成为今天现代社会极其重要的产业,但它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产业;二是在新型科技企业中,信息网络技术的创造性生产仍然会以程序和操作系统的方式生成终端产品,并且对象化到物性对象中,如数控机床、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智能设备的运用中。
可以看出,维尔诺这里构序重点是想突出语言交流和情感关怀在今天生产中的劳动特点。为此,维尔诺列举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丰田主义。①在他看来,后福特式的丰田主义是“基于语言的劳动”,甚至是“认知能力的生产性动员”的生产。〔14〕在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一书中,他们已经谈到福特主义,但只是从宏观生产层面入境的。这里维尔诺的构境意向更多的是偏重具体生产过程中对工人管理问题。我们知道,1920年代起,美国福特汽车创立的基于泰勒流水线生产之上的管理方式中,每一个工人都是流水线的劳作程序的一部分,无需太多的主体技能,每位劳动者只要把自己的工序完成就行,从上游到下游,劳动者之间互不打搅,也不需要语言或智力的交流。这种管理模式一度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模型,发达国家从此进入工业流水线大生产时代,史称“福特主义”时代。直到1970年代,日本的丰田公司及其首创的“丰田主义”管理方式打破了福特体制下的非主体性的管理关系,提出“精益生产”理念,其主要目标是减少所有不能增加产品最终价值的间接劳动形式,包括监督活动、质量控制、维护工作和清理工作等等。通过各种工作轮训将车间工人培养成能自我管理的多技能的劳动者,这种管理方式鼓励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进行全面的交流,形成圆桌会议式的语言和智力上的交流方式,发现问题立即解决,这样,极大地提高了产品质量,同时,对劳动者的主体积极性也大有增加。维尔诺关于诸众概念的思考构境中,多有丰田主义的影子。维尔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潜在的表演大师,因为我们都是讲话者,并且,语言是没有终端产品的。所以,当后福特主义生产中开始包含语言交流的功能,或者说采取了“通过传播手段的交流的生产(production of communication)”,那么,生产本身就开始具有没有终端产品的技艺性。维尔诺认为,这一点,在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的兴起中得到更加明显的表征。我觉得,在现代生产特别是后工业生产过程中,语言交流的确起到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绝不可能真正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比如在信息技术的原创性编程和设计中。维尔诺的断言显然存在夸大的成分。
在维尔诺看来,资本主义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第一次使“精湛才艺成为面向大众的劳动”。这是一个领域性的指认,倒是一个必要的特设说明。因为在他看来:
在文化产业领域中,劳动活动没有终端产品,也就是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中枢和必要的元素(a distinctive central and necessary element),交往活动(communicative activity)本身作为终端。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最重要的是文化产业中雇佣劳动结构(structure of wage labor)与政治行动结构有着重叠。〔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董必成译,69页。中译文有改动。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The MIT Press, Cambridge,2004.p.56.
应该说,维尔诺这里的文化产业可能是广义的,它泛指了一切工业生产之外的服务行业、卫生医疗、新闻文化教育工作等整个第三产业。在他看来,整个文化产业在后福特资本主义中都成為没有终端产品的精湛才艺的表演性劳动。
在这里,他专门以意大利著名作家卢西亚诺·卞塞雅迪卢西亚诺·卞塞雅迪(Luciano Bianciardi,1922-1971):意大利记者、翻译家和作家。代表作有《苦日子》(1962)、《明火》(1969)等。所写的小说《苦日子》(La vita agra)中的故事,来说明他眼中的文化产业与传统农业和工业的差别。从小说的主人公的口中,我们得知,从事文化产业的人,不同于可以定量的“从无到有”的农业生产或者“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东西”的工业生产,因为记者或“公关先生”的职业中的工作是无法定量测度的,“他们既不是生产工具,也不是输送线上的传动皮带,他们是润滑剂,最纯粹的凡士林。如何去评价一个牧师、一个记者、一个公共关系的从业人员?如何讲师信仰的数量、购买欲的数量、这些人鼓动起人心亲和度的数量?不能”。 〔意〕卢西亚诺·卞塞雅迪:《苦日子》,转引自〔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董必成译,71页。能看得出来,小说中所描述的20世纪50年代这位主人公的职业,是以改变人的心智所进行的工作,这种劳作会是以语言和智力的付出为主。依此维尔诺推断说,在后福特资本主义现实生产中,“物品的物质生产交付给了机器的自动化系统,而由活劳动(living labor)提供的服务却越来越像语言艺术(linguistic-virtuosic)的服务”。〔15〕这是说,有终端产品的物质已经由自动化生产系统承担,而劳动者则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这种以心智交流为主的没有终端产品的文化产业劳动。并且,依阿伦特的构境意向,维尔诺将其视作没有终端产品的以言说交流为核心的政治行动的维度。
维尔诺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用以概括整个后福特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物质上,可能都说得太满了。
三、文化产业:战胜福特主义
维尔诺认为,他所描述得越来越像语言艺术的文化产业会是“战胜福特制/泰勒制模式”的力量,甚至还可以“对后福特制生产范式(paradigm of post-Fordist production)做总体上的调整”。〔16〕这是在更大尺度上的宏大逻辑描绘了。在他看来,
文化产业的行动模式(mode of action)从某种角度开始,已成为典范性的和普遍性的(exemplary and pervasive)。在文化产业里,即使在本雅明和阿多诺验讫的它那古色古香的化身里,也可了解到后来进入到后福特制时代生产方式的早期迹象,成为广义性的并提升到经典(canon)之列。〔17〕
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断言。如果我推测得不错,维尔诺此处使用的文化产业就是在广义的语境中使用的,它包含了一切非物质生产领域之外的所有第三产业。他认为,文化产业的劳作方式已经成为后福特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经典范式,因而带有普遍性的特征。
还能够看到的理论倾向为,维尔诺并不赞同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批判。在他看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对传播产业(communiation industry)的批判是过头了。因为后者“粗鲁地断言‘灵魂的工厂(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等)也遵照了福特制的序列化和模块化标准(criteria of serialization and parcelization)”,好像文化产业也像泰勒制流水线上的“传送带(conveyer belt)”,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精神生产”也像金属加工一样地被机械化。〔18〕维尔诺显然不认同这种结论。如果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在批评文化艺术在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生产中出现了机械性和模式化异在现象,而在维尔诺看来,后福特资本主义生产中,则出现了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构序逻辑相反的意向,即后福特资本主义文化产业中出现了“一些可以抑制福特制组织的劳动过程完全同化的要素”,即“不循规蹈矩、非程序化的空间”:
即对不可预见的灵光敞开着的空间,对坦率的交流和创造性的即兴创作敞开着的空间:这并不是为了眷顾人类的创造力,理所当然是为了使企业的生产力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可以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来说,这只不过是没有影响力的残留物、过去留下的废物。顶要紧的是文化产业被普遍福特制化(general fordization)了。〔19〕
也由此,维尔诺才乐观地说,在今天的后福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原来只是政治社会交往中才会有的“不拘礼节的交往行为、竞争互动式的会议、让电视节目充满活力的‘意料之外”,这些让劳动者的主体性充分表现出来的特点,“在后福特制时代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生产领域的典型特征”。〔20〕他认为,这充分说明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精湛才艺的混合物,政治和劳动之间的扩展渗透已远处不在”,这不仅是文化产业中的现实,甚至也是意大利梅尔菲(Melfi)的菲亚特汽车菲亚特汽车公司(Fabbrica Italiana Automobili Torino,缩写即F.I.A.T.),意大利著名汽车制造公司,世界十大汽车公司之一,成立于1899年,总部位于意大利工业中心,皮埃蒙特大区首府都灵。菲亚特的梅尔菲工厂投产于1993年,现在8000名员工,450台机器人,到2015年生产汽车600万辆。工厂中的现实。似乎,这都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没有预见到和更深刻地批判透视的方面。
在这一点上,我会坚定地站在本雅明和后来的霍克海默、阿多诺一边。因为从本雅明“文明进步同时也是野蛮”开始的批判性构境,历经《启蒙的辩证法》对工具合理性中支配邏辑的批判,并不是在思考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中劳动者主体性的问题,而是在现代性本身的终结意义上思考整个启蒙以来的资产阶级总体性统治和工具理性支配的合法性逻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批判,文化工业的异化现象,包括文化产品的批量序列生产等问题的否定性思考,只有在这一更深的构境中才能体悟。而维尔诺对后福特资本主义的思考,也因为总是坠入生产劳动者的管理机制这一窄狭的视域,他才会津津乐道于劳动者是否能够言说和交流,是否具有终端产品一类问题。
〔参考文献〕
〔1〕〔3〕〔4〕〔5〕〔9〕〔11〕〔12〕〔13〕〔14〕〔15〕〔16〕〔17〕〔18〕〔19〕〔20〕〔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M〕.董必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58,59,60,60,61,62,65,65,65,72,72,72,73,73,73-74.
〔2〕〔6〕〔7〕〔8〕〔10〕〔德〕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214,222,294,第5章第24节.
(责任编辑:颜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