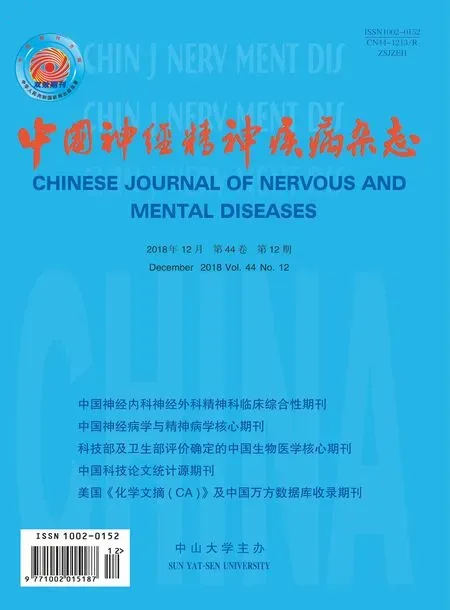帕金森病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2018-01-20张凯琳唐北沙徐倩
张凯琳 唐北沙 △※◎# 徐倩
近年来,作为遗传与环境之间纽带的表观遗传修饰与PD发病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表观遗传是指在没有DNA序列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的基因表达或功能的改变[1]。表观遗传修饰包括DNA甲基化、DNA羟甲基化、组蛋白修饰以及非编码RNA(non-coding RNA,ncRNA)介导的基因表达变化等。本文将着重从上述四个方面介绍PD相关的表观遗传研究进展。
1 DNA甲基化
1.1 DNA甲基化概述DNA甲基化是目前研究最多的表观遗传修饰。在真核细胞中,DNA甲基化是指DNA甲基化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DNMT)将 S-腺苷甲硫氨酸(S-adenosyl methionine,SAM)上的甲基转移至胞嘧啶使之变成5-甲基胞嘧啶(5-methylcytosine,5mC)的过程。DNA甲基化主要发生于胞嘧啶-鸟苷酸二核苷酸(CpG)部位,特别是CpG密集区(又称CpG岛),但是近年来也有研究发现非CpG部位的甲基化改变[2]。DNA甲基化既可以阻止转录激活因子与DNA结合来抑制基因表达,也可以招募甲基化CpG结合结构域蛋白,导致染色体构象改变和基因沉默。近年来甲基化测序技术飞速发展,测序种类繁多,总体来说按原理可分为三大类:重亚硫酸盐测序、靶向富集甲基化位点测序以及基于限制性内切酶的测序。而将这些测序技术加以改进并与二代测序平台相结合则诞生了许多高通量的甲基化测序手段,如全基因组重亚硫酸盐测序(whole genome bisulfite sequencing,WGBS)、简化代表性重亚硫酸盐测序 (reduced representation bisulfite sequencing,RRBS)、单细胞重亚硫酸盐测序(single-cell bisulfite sequencing,scBS-seq)以及甲基化DNA免疫共沉淀测序(methylated DNA immunoprecipitation sequencing,MeDIP-Seq)等 ,并且WGBS、RRBS和scBS-seq均可实现单碱基分辨率的DNA甲基化检测,大大促进了PD甲基化修饰的研究[3]。
1.2 DNA甲基化与PD众多研究表明PD致病基因SNCA的表达受到DNA甲基化调控:PD患者的大脑以及外周血中均可以观察到SNCA内含子和启动子的低甲基化并且CpG的低甲基化与SNCA基因过表达以及PD发病相关[4]。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并未在PD患者脑组织和外周血中检测到SNCA基因甲基化水平的改变。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左旋多巴的使用影响了SAM浓度进而影响了PD患者体内的甲基化水平,而大部分研究并未关注患者的用药情况,因而造成了结果的差异;再者,SNCA基因的甲基化水平在早发性PD患者中下降更明显,因此不同研究中PD患者发病年龄的不一致可能也会影响实验结果[5]。此外,我们既往的研究表明SNCA基因的多态位点rs3756063及Rep1与SNCA基因内含子的甲基化水平相关,却与SNCA基因的mRNA水平无相关性,因此除了甲基化修饰外,SNCA基因的表达可能还存在其他层次的转录调控,例如,细胞内a-突触核蛋白的异常聚集可能对SNCA基因表达存在反馈抑制等[6]。综上所述,PD患者SNCA基因的甲基化修饰尚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MAPT基因编码微管相关蛋白tau,亦与PD发病相关。研究发现PD患者和健康对照的额叶皮层和外周血白细胞中MAPT基因甲基化水平存在差异[7],且PD患者脑区病理改变越严重,甲基化水平越低,另外,男性白细胞中MAPT基因的甲基化水平比女性更低[8],这可能有助于解释男性中更高的PD发病率。
除此之外,在PD患者中还有许多基因亦存在DNA甲基 化 水 平 改 变 , 如 PARK16、GPNMB、STX1B、FANCC、TNKS2、CYP2E1、PGC-1a及NPAS2等,甚至在PD患者黑质线粒体DNA的D环区也存在甲基化水平降低[9]。
2 DNA羟甲基化
2.1 DNA羟甲基化概述DNA羟甲基化是一种近年来才被引起关注的表观遗传修饰。5mC可经10-11转位(teneleven translocation,TET)酶氧化形成5-羟甲基胞嘧啶(5-hydromethylcytosine,5hmC),而5hmC又可进一步被TET酶氧化成5-甲酰胞嘧啶(5-formylcytosine,5fC)和5-羧基胞嘧啶(5-carboxylcytosine,5caC),最后5fC 和5caC 经被动稀释或碱基切除修复成为胞嘧啶而完成DNA去甲基化过程[10]。因此,5hmC是5mC去甲基化过程的中间产物,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5hmC也参与表观遗传调控。5hmC具有组织特异性,它在哺乳动物大脑高度富集并随着年龄增长而动态变化;5hmC主要位于基因内部,并且可能参与基因转录的调节[11]。众多研究表明5hmC改变与神经系统疾病高度相关,如在亨廷顿舞蹈病、阿尔茨海默病以及帕金森病在内的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中都可以观察到5hmC改变[12]。
2.2 DNA羟甲基化与PD目前关于PD与DNA羟甲基化的研究较少,且不同研究得到的结果并不一致。ZHENG等[13]人检测了6-OHDA诱导的PD小鼠与野生型小鼠的纹状体中的5hmC水平,结果发现两组之间并无差异。然而,STOGER等[14]比较了PD患者和正常对照尸检脑组织的5hmC水平后发现PD组的中位5hmC水平几乎是对照组的两倍。这两个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6-OHDA小鼠模型是一个急性PD模型,因而并不能完全模拟PD患者脑内的表观遗传改变;此外,两个研究检测的羟甲基化脑区不一致,可能也会导致得出不一样的结果。总之,PD的羟甲基化修饰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3 组蛋白修饰
3.1 组蛋白修饰概述组蛋白是真核细胞染色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经发现了组蛋白尾部残基存在多种类型的转录后修饰,例如甲基化、乙酰化、磷酸化、泛素化、ADP核糖基化、脱氨基化、脯氨酸异构化以及赖氨酸苏素化等,随后相关蛋白质识别这些化学修饰并募集转录激活或抑制因子到特异的修饰位点以调节基因表达[15]。组蛋白修饰中最重要的是组蛋白乙酰转移酶 (histone acetyltransferase,HAT)所介导的组蛋白乙酰化,该修饰导致染色质结构松散,并能促进基因激活相关转录因子的募集,进而导致转录激活。
3.2 组蛋白修饰与PD
3.2.1组蛋白乙酰化与PD异常聚集的α-突触核蛋白可阻止整体组蛋白乙酰化、促进染色质浓缩、抑制基因表达,并最终导致细胞死亡。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HDAC)活性降低介导的神经保护作用也进一步验证了低乙酰化对神经元的毒性作用。HDAC抑制剂姜黄素能够减少DJ-1敲除大鼠模型中的细胞凋亡,并改善其运动缺陷[16]。HDAC抑制剂还能减少小胶质细胞活化以减轻炎症反应,同时保护多巴胺能神经元[17]。然而,有文献报道组蛋白高乙酰化也与PD相关。在MPTP处理的急性PD小鼠模型和PD患者的中脑组织中也可以检测到组蛋白高乙酰化[18]。组蛋白高乙酰化会上调多巴胺能神经元中氧化应激敏感蛋白激酶Cδ的表达,并增加细胞对氧化损伤的易感性[19]。有趣的是,YAKHINE-DIOP等[20]检测了特发性PD以及具有LRRK2基因G2019S或R1441G突变的遗传性PD的原代成纤维细胞中的乙酰化蛋白,结果发现特发性PD细胞乙酰化水平降低而遗传性PD细胞乙酰化水平升高。因此,多巴胺能神经元可能对组蛋白低乙酰化和高乙酰化均敏感。
3.2.2其他组蛋白修饰与PD GDNF和BDNF的启动子中存在组蛋白修饰,而这两种神经营养因子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生长、存活和突触可塑性中起关键作用,并且在帕金森病模型中具有保护作用。而多种HDAC抑制剂均能引起GDNF和BDNF基因表达上调[21]。
4 ncRNA
4.1 ncRNA概述细胞内存在许多类型的RNA,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为具有蛋白质编码功能的信使RNA(messenger RNA,mRNA),缺乏开放阅读框的其他 RNA被统称为ncRNA。 ncRNA 包括核糖体 RNA(ribosome RNA,rRNA)、转移 RNA (transfer RNA,tRNA)、 微小 RNA(microRNA,miRNA)、piwi RNA(Piwi-interacting RNA,piRNA)、转录起始 RNA(transcription initiation RNA,tiRNA)、小核仁 RNA(small nucleolar RNA,snoRNA) 以及长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等。在所有的 ncRNA 中,miRNAs研究最多,miRNA是一组21-24个核苷酸组成的ncRNA,其结合到目标RNA的3'非翻译区(3'-untranslated region,3'UTR),导致目标RNA的降解或翻译抑制。miRNA功能失调是PD神经退行性变的研究热点之一。
4.2 miRNA与 PD目前已有多项研究表明miRNA参与PD致病基因的调控。TATURA等[22]用microRNA芯片检测了PD患者和正常对照扣带回的744个miRNA,结果发现miR-144、miR-199b、miR-221、miR-488及 miR-544参与调节SNCA、parkin及LRRK2基因的表达[23]。此外,miR-21、miR-224、miR-373、miR-379、miR-26b、miR-106a 和miR-301b可通过结合至自噬相关蛋白,降低SNCA基因表达,从而减少α-突触核蛋白的降解进而导致其在细胞内异常聚集。miR-494可以结合至DJ-1基因的3'UTR进而调节其表达,上调的miR-494可以降低DJ-1蛋白水平,从而使神经元对氧化应激易感性增高,亦可增加小鼠对MPTP的敏感性[24]。LRRK2的表达受到miR-205的控制,miR-205在PD患者的额叶皮层中表达下调,证实其可能参与PD发病[25]。另外,PD患者和正常对照人脑组织的研究显示,启动子相关的lncRNA MAPT-AS1与MAPT基因表达相关,提示MAPT-AS可能是MAPT表达的潜在表观遗传调节剂[26]。
miRNA除了可能参与PD致病基因调控外,还可能参与到多巴胺能神经元分化及神经炎症等方面。miR-124参与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分化和成年神经发生,在MPTP诱导的PD小鼠模型的黑质中miR-124水平降低,这可能在PD多巴胺能神经元丢失中起作用[27]。miR-30e和miR-124均参与神经炎症调节,miR-30e通过降低nod样受体蛋白3的炎性体活性来改善MPTP模型的神经炎症,而miR-124则通过调节有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3/核转录因子信号通路抑制PD的神经炎症[28]。
5 基于表观遗传的诊断和治疗
PD是一种进展性的神经变性疾病,然而当很多患者因为典型的运动症状获得首次诊断时,约50%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丢失,因此发掘PD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对于治疗及预后具有重大意义。脑组织和外周血高度相似的甲基化修饰模式提示外周血也许能够有效代表脑组织的甲基化水平[7]。既往研究已经提出外周血白细胞中SNCA和LRRK2低甲基化可以作为PD早期诊断的潜在生物标志物[29]。此外,也有研究提出从血清、血浆和循环血细胞获得的miRNA可能作为PD生物标志物[30]。然而当前PD表观遗传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困境,首先,血液标本并不能完全代表脑组织的甲基化水平,同时不同脑区的甲基化水平可能出现差异,PD患者黑质区多巴胺能神经元存在大量丢失,这些均可能影响结果;其次,左旋多巴制剂的使用能够逆转SNCA基因内含子的低甲基化状态,因此针对已经服用左旋多巴制剂治疗的PD患者进行的甲基化研究可能会低估PD患者的本身的甲基化水平[31]。再者,当前很多关于甲基化的研究采用的重亚硫酸盐转化测序或者芯片检测,这些方法并不能有效识别5mC和5hmC,可能将5hmC状态误认为5mC。
目前也已经有数种表观遗传相关药物正在被研究,例如DNMT抑制剂和HDAC抑制剂。DNMT抑制剂5-氮杂-2'-脱氧胞苷诱导的低甲基化可以同时上调神经保护基因如TH基因以及PD致病基因如SNCA和UCHL1的转录[32],因此,DNMT抑制剂在治疗PD中的作用尚待确定。而HDAC抑制剂的情况则更加复杂,尽管多项研究均证明非特异性HDAC抑制剂能在体外及体内发挥神经保护作用,但是关于特异性HDAC在PD中的作用尚缺乏统一的结论,这也阻止了其靶向治疗策略的发展。此外,也有研究在SH-SY5Y细胞中证明HAT激活剂可能对PD有益[33]。而对于ncRNA而言,证实其治疗相关性的体内研究数据仍然缺乏,并且靶向ncRNA治疗还存在脱靶风险以及血脑屏障渗透性低的问题。但miRNA可以维持神经元干细胞分化,使miRNA成为PD的潜在治疗靶点。
6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已有许多研究从多巴胺能细胞、PD动物模型、PD患者脑组织和血液组织等各方面对PD表观遗传修饰做出了探索,但是不同的研究可能会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因此对表观遗传全景的正确理解可能需要更精确的解析,相信随着表观遗传检测技术的发展这一目标最终会得到实现。而对PD异常表观遗传修饰的全面了解将为PD的发病机制提供更好的见解,并促进PD新的生物标志物和新型治疗策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