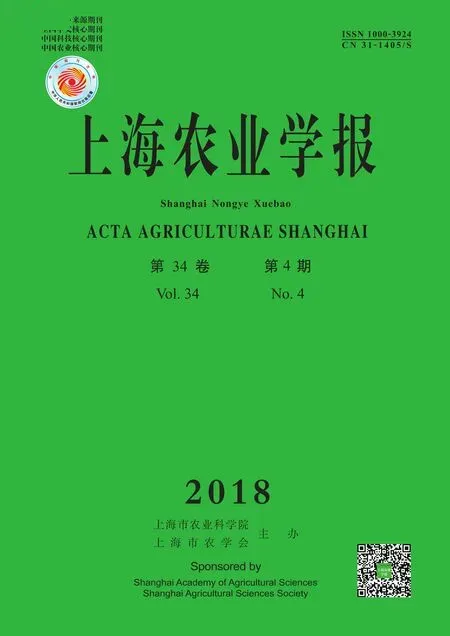杆状病毒感染昆虫围食膜的效应及其干扰因子
2018-01-17蒋杰贤季香云万年峰
郭 玲,蒋杰贤,杨 安,季香云,张 浩,万年峰∗
(1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上海201403;2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上海201306)
围食膜为一层包裹着食物的非细胞长管状的薄膜结构,由昆虫中肠上皮细胞分泌,能抵御有毒有害物质的侵害。据报道,围食膜是一种功能性的抗氧化剂,保护中肠上皮细胞免受严重的氧化性损伤[1-2]。杆状病毒是鳞翅目昆虫的重要病原微生物,通过与昆虫围食膜上的特异位点结合破坏围食膜结构,进而提高病毒对昆虫的致病力。杆状病毒作用于昆虫围食膜后,后者的结构、功能与生理特征会发生变化。鉴于此,本文对围食膜的功能、杆状病毒对围食膜的影响以及影响杆状病毒感染性的干扰因子进行简要归纳,以期为杆状病毒与昆虫围食膜的互作研究提供参考。
1 围食膜的结构与类型
1.1 围食膜组成与结构
围食膜主要由蛋白质、几丁质和多糖组成。围食膜上的蛋白质主要以糖蛋白的形式存在,能增强围食膜的半渗透性和致密性,其含量在所有组分中最高(占20%—55%)。根据蛋白质提取的难易程度,将其分为4类:1)在高或低浓度的盐溶液中易移除的蛋白[3];2)能够被温和去垢剂去除的蛋白[3];3)以非共价键结合,需要强变性剂才能将其洗脱的蛋白;4)以共价键的形式结合在围食膜上的蛋白。其中,第4类蛋白质稳定性好,在前3种蛋白质的提取条件下,不能被移除[4]。
几丁质在围食膜中的含量也比较高(占4%—20%)。经几丁质合成酶的作用,该物质由N-乙酰-D-葡糖胺(GlcNAc)借助β-(1,4)糖苷键形成[5],可分为α、β和γ 3种形式。此外,围食膜中还含有少量的多糖。多糖往往决定围食膜的致密性,其含量因昆虫种类不同而有所差异。如甜菜夜蛾(Spodoptera exigua)和华北大黑鳃金龟(Holotrichia oblita)围食膜中糖含量分别占2.05%[6]和8.91%[7]。
电镜观察视野下发现:10根(或大于10根)同向排列的几丁质微纤丝耦合成微管微纤丝束,多个微管微纤丝束又进一步耦合形成围食膜[8-9];一般情况下,几丁质微纤丝以60°或90°交叉形成网状结构,但有时也以其他形式交织成网状结构,该网状结构中塞满着蛋白质和糖类[10]。
1.2 围食膜类型
根据合成位点的差异,可将围食膜分为Ⅰ型和Ⅱ型[2]。鳞翅目和一些直翅目幼虫的围食膜大多属于Ⅰ型,该类型的结构为多层重叠管状,由中肠上皮细胞经肠腔分泌而成。Ⅱ型围食膜多存在于双翅目、革翅目、等翅目以及一些鳞翅目幼虫中,由昆虫的前肠和中肠连接处的特殊结构——贲门环状细胞分泌形成。观察发现,Ⅱ型围食膜比Ⅰ型更加规则有序[11]。
昆虫取食不同食物后,其围食膜形成与类型往往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有毒有害的液体食物(即对昆虫生长发育不利)对昆虫围食膜影响较为明显。研究发现,取食血液等无菌或者少菌液体食物的昆虫,一般不会形成围食膜,而摄取污染程度高的食物(如粪便、腐烂水果)的昆虫,则会保留围食膜[12]。此外,有些围食膜的类型与其发育阶段有关,如蚊幼虫期的围食膜为Ⅱ型,而雌性成虫却为Ⅰ型。有的昆虫围食膜类型与其发育阶段无关,如红头丽蝇(Calliphora erythrocephala)幼虫期的围食膜类型与成虫期的相同[13]。有研究表明,围食膜的厚薄程度与昆虫取食的食物种类有关,并且围食膜的厚度决定着昆虫防御病原物入侵的能力,如取食叶片的鳞翅目幼虫围食膜比取食饲料的厚,且前者具有较低的病毒感染率和死亡率[14]。
2 围食膜的功能
2.1 机械保护
虽然围食膜是外界病原菌侵入的重要位点,但同时它也具有防止微生物入侵的功能。围食膜上存在类凝胶功能的物质,具有润滑作用,该类物质能够使食物顺利通过中肠,避免昆虫因食用大颗粒物质而引起中肠涨裂[15]。研究发现,围食膜的糖位点可与病原微生物发生吸附作用,进而阻止病原物破坏中肠上皮细胞[16]。如家蚕(Bombyx mori)幼虫的围食膜对杆状病毒具有一定的抵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肠上皮细胞免受病毒破坏;当家蚕幼虫围食膜被降解后,杆状病毒对其中肠细胞破坏严重[17]。此外,围食膜机械保护作用还受其他一些化学物质影响。如刚果红可与蛋白质竞争性结合几丁质,致使围食膜功能发生暂时性紊乱。
2.2 化学保护
围食膜不仅能阻止中肠细胞对金属离子的吸收,而且能将其排出体外。如Abedi等[18]用杀虫剂DDT处理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幼虫后,发现大量的围食膜被排出体外,这可能是围食膜与有毒物质结合,产生螯合作用的结果。研究证实,昆虫围食膜的黏蛋白可以消除重金属离子的危害,但某些幼虫对重金属离子反应敏感,如冈比亚按蚊(Anopheles gambiae)围食膜受铜和镉影响强烈[19]。此外,昆虫围食膜对植物释放的有毒有害物质也具有抵御作用。
2.3 选择透性
围食膜是一种具有选择透性的薄膜,其选择透性与其孔膜结构、食物通过围食膜速度等有关。研究表明,鳞翅目和直翅目昆虫围食膜的孔径分别为21—29 nm和24—36 nm,食物通过围食膜的流量分别为32—159 ng∕h和98—2 821 ng∕h[20]。围食膜能够从中肠上皮细胞中分离大部分的单宁酸和其他异种化感物质,但却允许其他小分子(酚类物质、营养物和消化酶)进入。有研究发现,几丁质酶能够破坏围食膜结构,几丁质酶作用时间越长,围食膜损害就越大,选择透过性也越低[21]。围食膜的通透性与蛋白多糖的抗击压性能和几丁质纤维丝弹性有关,也与中肠的位置有关[22]。据报道,低温使围食膜产生孔洞和缝隙,进而使其通透性发生变化[9]。某些昆虫的围食膜组分存在性二型现象,如雄性刺舌蝇(Glossina morsitans)围食膜的通透性较雌性的高[23]。外源凝集素分子能干扰围食膜的通透性,这些物质与围食膜蛋白、几丁质或昆虫中肠上皮细胞表面的糖基化位点结合,从而使围食膜通透性降低。
2.4 区室化作用
位于昆虫中肠内部的围食膜,将肠腔分为内外两个空间——围食膜内空间和外空间。围食膜相当于一个分子筛,可使一些消化酶(如分子量较小的淀粉酶)和已被消化完全的营养物质透过,而将一些物质(如分子量较大的氨肽酶和羧肽酶)阻挡在外间隙内。经围食膜消化产生的小分子物质(如寡糖和多肽等),可与消化酶再次发生作用而进行二次消化。据报道,肠腔的区室化加快了营养物质在其内外的流动,可使营养物质容易被消化分离,从而提高中肠吸收营养的效率。在食物流向围食膜后方的过程中,食物流的方向与围食膜外侧液的流向相反,该流动方式可以提高消化酶利用率和食物消化率,有利于保存营养物质[12]。
2.5 其他功能
围食膜还具其他两个功能:一是抗氧化作用,如保护昆虫中肠上皮细胞免受氧化剂的损伤[1];二是促使茧的形成,如在结茧前,裸蛛甲(Gibbium psylloides)幼虫的围食膜是解离的,结茧后,从肛门排出丝状物[24]。
3 杆状病毒对围食膜的影响
3.1 改变物理结构
围食膜具有多孔性,允许水、盐等小分子通过,却将一些较大的入侵物(细菌、病毒颗粒体等)拒之门外。核型多角体病毒感染斜纹夜蛾(Spodoptera litura)幼虫的研究表明[25],杆状病毒能破坏昆虫围食膜结构,致使围食膜孔径增大、膜破裂。此外,杆状病毒与增效蛋白的联合作用对昆虫围食膜结构的破坏更加明显。如刘琴等[26]研究发现,甜菜夜蛾幼虫经黏虫颗粒体病毒(PuGv-Ps)和增效蛋白(Enhancin)共同处理后,围食膜由原来的表面光滑逐渐表现为粗糙凸起,以致破损降解。虫媒病毒感染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的研究表明[27-28],昆虫围食膜也能抵御病毒的侵害,可以将病毒颗粒体紧紧包裹,减少病毒与中肠接触的空间,进而降低病毒感染的几率。
3.2 影响化学成分
杆状病毒感染昆虫后,对围食膜结构蛋白影响最大,如感染杆状病毒后,黏虫(Mythimna separata)围食膜蛋白丢失,进而引起围食膜渗透性发生变化[17]。此外,病毒增效蛋白能助推杆状病毒对围食膜蛋白的破坏,降解围食膜中一种分子量较大的糖蛋白。如棉铃虫颗粒体病毒(HaGV)的增效蛋白能将棉铃虫(Helicoverpa armigera)围食膜蛋白HaIIM86降解为70 ku和90 ku两个多肽[22]。但Shi等[29]研究表明,蓓带夜蛾杆状病毒(MacoMNPV)增效蛋白对蓓带夜蛾(Mamestra configurata)围食膜蛋白McMUC4无影响。杆状病毒对昆虫围食膜蛋白的影响已受关注,但杆状病毒如何调控围食膜上的几丁质和多糖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3.3 调控蛋白基因
迄今,杆状病毒对昆虫围食膜蛋白基因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几丁质蛋白基因。如Levy等[30]研究发现,梨豆夜蛾(Anticarsia gemmatalis)感染核型多角体病毒(AgMNPV)后,抗AgMNPV品系的几丁质蛋白含量较敏感品系的高;Jakubowska等[31]报道,棉铃虫感染棉铃虫多角体病毒(HearNPV)后,中肠几丁质去乙酰基酶HaCDA5a表达量下降。蛋白基因维系着昆虫围食膜结构的稳定性,若这种稳定性被破坏,围食膜的结构与功能也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研究显示,家蚕(Bombyx mori)被核型多角体病毒(BmNPV)感染后,其丝氨酸蛋白酶基因的表达量在感染后早期显著上调[32],究其原因,该基因与丝氨酸蛋白酶2(简称“BmSP-2”,一种具有强大抗BmNPV活性的蛋白基因)具有高度相似性。多糖也是围食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成多糖的酶系基因如何响应杆状病毒的感染有待进一步研究。
4 影响杆状病毒对围食膜感染性的干扰因子
4.1 病毒增效蛋白
昆虫病毒增效蛋白是一种富含酸性氨基酸的金属蛋白酶,主要存在于病毒颗粒中。虽然增效蛋白含糖量不高,但具有较多与围食膜蛋白因子结合的糖基化位点,该位点使病毒粒子易穿过围食膜,造成围食膜降解。昆虫病毒增效蛋白能够促进病毒对昆虫的感染,其作用机理主要有:1)病毒增效蛋白破坏围食膜蛋白上的糖基化位点和蛋白之间的二硫键,以及破坏几丁质-蛋白质复合物,进而使围食膜结构发生改变;2)增效蛋白金属蛋白酶能降解围食膜的肠黏蛋白,有利于病毒粒子进入中肠,并且避免病毒被肠液消化或排出体外;3)增效蛋白金属蛋白酶有利于病毒核衣壳与细胞膜的吸附融合,加速病毒感染昆虫进程[33]。研究发现,病毒增效蛋白能明显增加病毒致病力,如TnGV与增效蛋白联合作用于粉纹夜蛾[Plusia ni(Hubner)]幼虫后,幼虫病亡率随增效蛋白剂量的增加而增加[34]。
4.2 荧光增白剂
荧光增白剂能够吸收紫外线,发射415—466 nm波长的荧光[35]。该物质能增强病毒致病力,加快昆虫病亡。健康昆虫围食膜表面光滑、有弹性、无孔洞缝隙,由蛋白质和几丁质以共价键的形式组成。当荧光增白剂作用于围食膜后,其与蛋白质发生竞争结合,破坏共价键,破解围食膜结构,进而便于病毒感染。荧光增白剂的作用时间和作用剂量影响围食膜结构[36],如甜菜夜蛾取食混有1%荧光增白剂的食物后4 h,围食膜形态无变化,而6 h后,围食膜弹性逐渐下降;当甜菜夜蛾的食物源替换为0.1%荧光增白剂时,其围食膜结构的变化较1%荧光增白剂处理的小,并且在每个处理后时间点都表现这种趋势。
4.3 几丁质酶及几丁质合成抑制剂
几丁质酶是一种催化几丁质水解生成N-乙酰葡糖胺反应的酶,由N-催化域、中部富含Ser∕Thr区和C-端富含Cys的几丁质结合域组成[37],能够提高杆状病毒对昆虫的致病力,其作用机理为:通过降解围食膜几丁质,致使围食膜结构破坏、形成孔洞缝隙,进而使病毒颗粒体更易穿过围食膜,侵入中肠上皮细胞,加速幼虫病亡。研究发现,经几丁质酶处理的围食膜,其结构出现孔洞缝隙,围食膜结构的损坏程度随处理后时间的延长而加重,并且对围食膜蛋白质和糖含量也有一定影响。如黄杉毒蛾(Orgyia pseudotsugata)幼虫的围食膜在灰色链酶菌(Streptomyces griseus)几丁质酶的作用下,结构变松散,并且出现了孔洞和缝隙[38]。几丁质合成抑制剂能提高杆状病毒对昆虫的致病力,这类物质主要包括酰基脲类和噻嗪酮类;该类物质不仅能阻止几丁质合成,还减弱了膜蛋白O-糖苷键对围食膜肠黏蛋白的保护作用[39]。通过改变几丁质、几丁质合成抑制剂与杆状病毒对昆虫围食膜的联合作用效果,有助于研发新型杀虫剂[40]。
4.4 其他因子
影响杆状病毒对围食膜感染性的干扰因子还与昆虫消化道酸碱度、食性、种类等有关。杆状病毒几丁质酶基因参与降解中肠围食膜几丁质[41],若昆虫肠道pH值过高或过低,几丁质酶活性均会受到抑制,进而降低病毒对昆虫的致病力[42-43]。与取食卷心莴苣和人工饲料的感毒烟芽夜蛾(Heliothis virescens)幼虫相比,取食棉花叶片的幼虫对核型多角体病毒(AcMNPV)的易感性较弱[44]。昆虫围食膜上的肠黏蛋白具有保护中肠上皮细胞免受外源病原物侵害的能力,其含量因昆虫种类不同而不同。有研究表明,棉铃虫肠黏蛋白含量较甜菜夜蛾的高,使得病毒对前者的致病力较后者弱[45-46]。
5 展望
综上,围食膜与杆状病毒互作研究已成为科学家们普遍关注的焦点。然而,笔者认为,该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有待深入挖掘,如探讨昆虫被杆状病毒感染后,围食膜功能基因、细胞凋亡caspase基因、抗菌肽gloverin基因表达量和围食膜结构特征的差异。此外,从应用角度出发,鉴于肠黏蛋白和几丁质结合蛋白在昆虫免疫中的功能,可以研发以围食膜蛋白等生物大分子为靶标的新型杀虫剂,开创一个通过控制昆虫中肠来解决虫害的新方法。
迄今,昆虫围食膜与杆状病毒的互作关系,主要是基于昆虫-病毒两营养级水平,若从“植物-昆虫-病毒”三营养级关系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47],将有助于拓宽该方面的研究内容。据报道,植物中的几丁质酶、植物凝集素等化学物质会干扰昆虫围食膜的结构及其生理功能[48],为此,研究该类化学物质调控昆虫围食膜对杆状病毒的响应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最近,笔者所在团队研究发现,取食不同寄主植物后,昆虫(甜菜夜蛾幼虫)围食膜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如何与杆状病毒的感染产生联系,有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