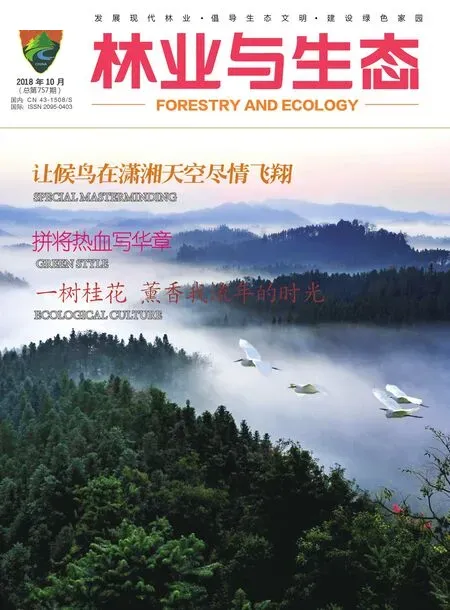致那些消逝和即将消逝的生灵
2018-01-16肖辉跃
文/肖辉跃
我老家在靳江河上游。记忆中,河堤的草地上铺满了地木耳、草菇;河岸有层出不穷的野花野草野果,以及发出奇异香味的高高的野芙蓉树,各种蜂蝶在花间飞舞。年少的我嚼着“乌泡子”(树莓),嚼着桑椹子,嚼着“冷饭坨”(土茯苓),嚼着鸡把子草(翻白草),口里汁水横流;带饭的搪瓷缸里装着我捡的地木耳,手里高举着几枝芙蓉花;我的头上戴着四季编成的花环;我的书包里还夹着我的小秘密:一只蝴蝶、一只蜻蜓,或一只蚱蜢的标本。我的嘴里哼着父亲每天清早的开嗓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靳江河的发源地在我们宁乡市麻山的白鹤山寨子冲,全长八十八公里,在长沙岳麓区的柏家洲村附近汇入湘江。它名字的由来,说来让人难堪。世人皆知屈原的爱国情怀,对那个陷害忠臣的小人——同为楚大夫的靳尚,恨之入骨。很不幸,这条河就因流经靳尚墓前得名。
河流自有河流的生命,河流的法则。清澈见底的河水中每天都有节目表演:鲤鱼打挺,泥鱼吊水,还有脚鱼(甲鱼)躺在河底圆滚滚的各色卵石中吹着成串的泡泡。“木嫩古”(子陵吻虾虎)像个小强盗,一动不动卧在石缝中,吓唬过路的“花妹子”( 鳑鲏)。河中有两种虾。一种是米虾公,很小,比米粒大不了多少,永远也长不大。用撮箕一撮,随便都可捉一箕。另一种是大虾公,喜欢舞着刀叉在河底称王称霸。齐白石画的就是这种虾,估计还是靳江河的虾。因为齐白石是湘潭人,靳江河在宁乡道林烧汤河地段进入湘潭界。
在“马家军”创造神话的那个年代,靳江河沿岸、河中心,不管白天黑夜都有打脚鱼、摸脚鱼的队伍前赴后继。脚鱼从不值一分钱的下脚货,价格一路飙升。当升到五百元一斤时,我再没在河中见过吹泡泡的脚鱼了。顺带的,那些收脚鱼壳、乌龟壳、鸡肚子皮的人也从此消逝。
还有一些无影无踪的。
据说靳江河中有个妖怪,名字叫“水猴子精”,夏天的晚上会跑到河堤上歇凉。它会拖到河中洗澡的人,特别是小孩的脚,拖了就吸人血。1993年6月的一天,我骑自行车送外婆回去。途中祖孙俩口渴难耐,我和外婆便到河边去捧水喝,水中赫然趴着一只有四只脚,浑身圆滚滚,长着两撇胡须的怪物:“水猴子精”!我们吓得半死,外婆的小腿整整抽了半天筋。多年以后,我才搞清这个妖怪的学名:“水獭”。
奶奶以往喜欢和我们讲动物的故事。她把“四不象”“麒麟”“红毛野人”和 獐子、黄脚虫(黄鼠狼)、老虎都归属到动物一类。每一个地名都对应着一个物种,她说对门那个“老虎冲”是真有老虎出没的,她还听过老虎叫咧。我还真不确定她讲的那些到底是真的动物还是传说中的怪物。但父亲所说“懒王蛇”(穿山甲)却是确有其事。他说在他小时,在我们后山的坟地里,他曾看见过“懒王蛇”。他说那个浑身长鳞的家伙极懒,想要吃东西时,便张开嘴流着涎痰“汪——汪”低叫,成群的白蚁就像听了催眠曲似的,排着队自发钻到它嘴里去。
还有一种叫“四脚蛇”的,实际并不是蛇,而是一种大蜥蜴。往往我们在田间小道上正走着,一条全身碧绿,肉滚滚的四脚蛇就冲过来了。刚开始很害怕,父亲告诉我们不用怕,四脚蛇不咬人。我有次踩住了一条四脚蛇的尾巴,它扭着屁股送了一条又粗又长的尾巴给我。我拎着那条断尾到处炫耀,直到它变成一根细绳。
说到蛇还是要起鸡皮坨的,那时的蛇可真多。走路时可能碰到“扇头风”(眼镜蛇),“白际蛇”(银环蛇),甚至还有“五步蛇”;去菜园寻菜有“拿(读ne)蛇子”(一种大拇指大,麻灰色的毒蛇,不知学名);爬树会有“竹叶青”;到河里去洗脚会有“水蛇子”;吃饭时说不定茅屋顶上还会掉下一条“火链斑”(颈槽蛇);就是睡觉也不清净。父亲八十年代在道林水管站工作时,一条黑蛇(乌梢蛇,无毒)与他共床共枕半年有余,直到那条蛇在他枕头底下生下一窠蛇崽他才发觉。最多的蛇还是“菜花蛇”(王锦蛇),这种蛇是屋场蛇,几乎每家每户都住着一条,专门吃老鼠的,无毒,长得很漂亮。八十年代,我曾在石家湾一中的屋檐上见过一条巨蟒似的大蛇,有整个屋檐长,足有五米以上。我想那应该也是一条菜花蛇。
地方上蛇那么多,被蛇咬的也不少。一般草药敷上去,少则三五天,多则半月会好,也有被咬身亡的。但总的来说,蛇毒不过人。蛇不管如何毒,最后都沦为人的盘中餐。
我们小时还常玩“麻鹰抓小鸡”的游戏,却不知这“麻鹰”到底是什么玩意,只知是人人喊打的一个坏蛋。有一种与“麻鹰”一道归为“坏鸟”的鸟,一到夜里就发出赫人的叫声,本地称“毛骨头”(猫头鹰)。村民们很不喜欢,说它一叫就肯定不是好事。对那种不孝顺父母的,村里人就会骂其是 “毛骨头变的畜牲”。就是说,猫头鹰长大后会吃掉父母。
猫头鹰是否会吃其父母我没见过,但人吃猫头鹰却听说过数次。早年,我家邻居八爷就经常到后山去张网抓猫头鹰,先是自己吃,后来卖钱。据他描述,那是一种比麻雀不会大多少的小猫头鹰,后脑壳上还长着一对眼睛,总共有四只眼睛!这种有四只眼睛的小猫头鹰无疑是“领鸺鹠”。
八爷说他还抓到过一次“猴面鹰”(草鸮),翅膀张开有小半个人高,长着一张极似猴子的脸,很凶,把他的手还抓伤了。有人出价两百,买了回去治头痛。当那个头痛的人再要请八爷去抓第二只时,八爷果断拒绝了。因为——他的头也开始痛了。
有一种很喜庆的鸟,我们本地人称“长鸦鹊”(喜鹊)。当年我们放学后,或是上学前,只要看到长鸦鹊站在我家那棵大山枣树上唱歌,我们就很高兴。“鸦鹊子叫,有客来”,并非是我们有多喜欢客人。而是,有客来,家里一定会买肉吃。
大约在九十年代初,我们就再没见着喜鹊了。大概的原因,当时山上遍种经济作物,以花生居多。喜鹊喜欢挖花生种子吃,村民用农药拌种子,喜鹊便中毒而亡。
田头时常有惊喜。“懂!懂!懂!”董鸡总是隐在田中的某处,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懂”,俨然稻田世界里最听话的学生。“禾鸡子”(红脚苦恶鸟)的长腿可真会跑,很少有人能抓到它。有次国哥逮着两只禾鸡子的半大鸟,用一个笼子装着,摆在我家地坪供我们欣赏。我自作主张用自家的一只母鸡换了那两只禾鸡子。晚上母亲收工回来,咦,怎么少了一只母鸡?一顿审问,我如实交代。最后,我哭哭啼啼,提着禾鸡子又去换了那只母鸡回来。
天空一样不寂寞。秋去春来,一队队大雁排队飞过。我们站在田野上,仰头望天,齐声高喊:“飞人字,飞一字;飞一字,飞人字。”而大雁好像也能听懂我们的语言,按照我们的指令改变着它们的队形。我从来不知它们从何而来,也不知它们要飞往何处去。
它们飞过我的童年,又飞过我的少年。遗憾的是,当我再抬头望天时,天空却再也没有它们飞行的轨迹。而我,甚至还没来得及搞清它们到底是何种大雁。
它们,还会再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