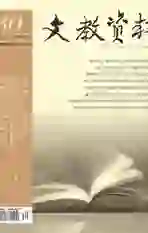西方修辞与英语名著书名汉译
2018-01-15林海梅
林海梅
摘 要: 现行英语名著书名汉译往往有一些被学界主流高度认可的 “经典译名”,从西方修辞视角对其进行反思,这些“经典译名”其实不无问题。本文基于西方修辭“辞屏”与受众理论对这类尚未引起学界重视的“问题翻译”进行反思,提出书名翻译的若干原则与改进。
关键词: 英美名著 书名翻译 西方修辞
书名可谓是作品之窗口,它就像商标一样,人们可以从中可窥见作品的主题和情节的线索。对于读者来说,书名往往是个人选择读物的第一参照。关于英美名著书名中译文本技术层面的方法论探讨,国内学界几近饱和。然而由于对某些现成英美名著书名翻译耳熟能详,国内学界未能与之拉开合理距离,就其翻译对于从未与之谋面的新一代读者(受众)所形成的修辞吸引力进行理论反思,遑论就书名中译对读者阅读书目的选择进行研究与预测。换言之,英美名著书名中译研究中基于受众的反应与接受的西方修辞视角尚付阙如。基于这一缺失,本文拟为这一研究引入修辞①视角,指出当前书名中译存在的若干问题或未曾得到重视的若干经验,并尝试提出几条基于修辞考量的书名中译原则。
一、西方修辞的“辞屏”理论
当代修辞巨匠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提出的“辞屏”修辞理论对书名翻译不无启发。伯克受摄影师使用不同滤色镜拍摄同一个物体获得大不相同照片这一现象的启发,将人们使用的各种象征系统或词汇汇集(terms)称为“辞屏”②(terministic screen)。正如任何一个镜头都难以忠实还原拍摄对象所有特征并且往往只能有选择地凸显某些特征一样,作为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工具,每一套词语或符号构成的独特“镜头”或“荧屏”(我们不妨称其为“辞屏”)所得到的世界图像并非原原本本的“现实”,而只是所用的那一套语言符号允许我们看到的那一维度,因而难免会突出某些特征,掩盖其他特征,乃至于歪曲某些形象。用伯克自己的话说,即便我们说任何词汇都是对现实的某种反射(反映),词汇的本质决定了这一反射(反映)必然是选择性的,因此它同时是对现实的折射(偏离)[1]。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辞屏”是人类只能无可奈何地深陷其中的一个困境,观察和理解非依赖语言符号不可,然而语言符号的应用必然对我们的观察和理解造成扭曲。由是观之,书名翻译不可不慎。但是从修辞的角度看,“辞屏”这一特点恰好为人类进行象征行动提供了一个使能条件。正因为词汇具有内在的“选择性反射”或“折射”功能,其应用才必然具有“劝勉性”和“说服性”,才使得目的和动机能够在象征行动中得以体现和实现,书名翻译也可以根据翻译目的选择恰当“辞屏”促进读者的接受。
二、西方修辞“辞屏”理论观照下的书名中译
英文作品尤其是知名度广流传深远的作品往往有一些被学界主流高度认可的“经典译名”,从西方修辞视角,尤其是在“辞屏”理论对其进行反思,不难发现这些“经典译名”其实不无问题。以下试举数例加以说明。
Charlotte Bronte的Jane Eyre译为《简·爱》,业内好评如潮。类似《简·爱》这样的翻译,在译者看来,前者”简”是女主人公的名字,”爱”又点明是一个爱情故事,既有人名,又有情节,可谓一举两得。然而受“辞屏”的影响,陌生读者很可能顾名思义,将“简·爱”理解为“简单的爱”,误以为这是一部轻阅读作品③。该译名与作品丰富内涵不相称,完全偏离了作品原本设定的厚重与深沉这一阅读预期。又如Robinson Crusoe译为《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讲述的是鲁滨孙乘船前往南美洲,途中翻船被卷到孤岛上生活历经18年才回到英国的故事。这中间的岛上生活艰辛程度自不必说。在当代语境中,漂流几乎都是有充分后勤保障的户外体验运动,虽然不无风险,漂流者在多数情况下掌握主动,主要是娱乐而非冒险。受“辞屏”的影响,当读者看到“鲁滨孙”与“漂流”时,很有可能认为这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外国人漂流的故事,失去与高尚的人谈话从而提升自我的机会。与此相同的例子还有一部美国经典小说Margaret Mitchell的Gone with the Wind,学界主流意见是觉得译为《乱世佳人》十分贴切,但是从“辞屏”角度考量,该译名会在很大程度上引导读者将其想象成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原因不难理解。一方面因为中国话语自古就有“治世”与“乱世”之说,另一方面“佳人”这一“辞屏”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绝代有佳人”及“北方有佳人”等耳熟能详的本土古典表达及相关意象。不仅如此,该译名丝毫无法让人想到原标题Gone with the Wind。“乱世佳人”这一“辞屏”给读者传递的信息与作者的本意南辕北辙,不能不引起译界的反思。
三、修辞受众意识缺乏是“问题翻译”的根本原因
吊诡的是,上述“问题翻译”在国内学界一向不被当做问题看待,甚至被视为佳译反复被引用。“辞屏”理论可以预测及解释读者的反应,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翻译会广受好评。仔细考察相关言论,不难发现书名中译的效果评价存在一个不无矛盾的机制,即评价翻译效果的往往是懂英语,通读英语原著的学者或翻译家,而不是由读完译文的读者根据阅读印象评价书名翻译是否恰当。由于这些评价者本人往往事先阅读过涉及的英语作品原文,对内容的先在把握使得无论翻译所选用的书名“辞屏”在多大程度上偏离原文,主观上总能把它与内容挂钩并为其证当,对于该“辞屏”可能造成的误导主动进行心理过滤(如彭璇,隋长红,2010)[2]。从西方修辞角度而言,修辞受众④意识缺乏是“问题翻译”的根本原因。刘亚猛指出,作为任何修辞行动(本文讨论的修辞行动即书名翻译)的主动发起者,修辞者在诉诸一个由自己选定的受众时无疑认为其成员的见识、态度或行为跟自己所追求的或者服务的一些利益休戚相关,而为了这些利益的实现,又必须促使该受众接受说服,采取某一立场或做出某一决定(本文讨论的即做出阅读该译作的决定)[3](刘亚猛,2008)。因此,决定一个书名翻译妥当与否主要看读者是否理解、认可该书名,是否表现出阅读意愿并决定阅读该作品。
四、名著书名中译原则及其应用
从以上讨论不难发现,为了获得书名翻译所服务的读者的认同⑤,翻译者应该尽量把自己想象成与读者处于相近的外语水平⑥与阅读预期。不能让译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评价书名翻译高下,应该把评判权交还翻译服务的对象---不懂外文的读者。翻译评价应该回到原点,不能以懂外语的读者作为服务对象,如果读者懂外文,则译文显然多此一举。书名翻译可以参照如下三条原则:
1.立足于原标题,忠实于原著。
在可能的情况下,书名翻译要尽量忠实于原文,可以让检验者轻松通过回译(back translation)找到比较接近原文的表达,而不是得到与原文风马牛不相及的回译结果。比如英语名著作品习惯于用主人公的名字作为书名,到中国后有些翻译家就顺其自然把这一习惯沿用。耳熟能详的有William Shakespeare的Hamlet译为《哈姆雷特》、Macbeth译为《麦克白》;Charles Dickens的David Copperfield译为《大卫·科波菲尔》;Nabokov的Lolita译为《洛丽塔》等。这些名著的中文名都是用发音近似且表达本身不具备特别意义的汉字组合进行音译,提醒读者这是一个外国名称,因而比较忠实于原著。
2.以目标读者为导向,追求有效翻译。
书名翻译不能仅仅停留于机械意义上的忠实于原著,同时要注意翻译的效果,能够引起读者兴趣。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言简意赅地增补有效信息,提示读者作品的主题、关键词等,便利读者进行阅读决策。
3.注意发挥“辞屏”的正面作用,避免误导读者。
书名翻译要特别注意发生于译者主观意图之外、客观上由翻译使用语言形成的“辞屏”引发的对读者的误导。比如音译Hamlet为韩木雷,或把Lolita音译为罗丽塔,由于中文原本就有“韩”、“罗”这些常见姓氏,这样的“辞屏”很容易误导读者判断,将其误认为是中国故事。
以下尝试基于这些原则对前文书名进行重译。Jane Eyre如果译为《简·艾》,便容易让读者想到是一个外国人名,“艾”在中国文化中乃是卑微且常见草本植物,有独特药效,与故事主人公特点有互文关联。使用音译法翻译这一书名,并不直白乏味,字形外观清秀隽永,读者读完译作再回想标题,很容易发现标题与文章相称。Robinson Crusoe如果译为《鲁滨孙荒岛求生记》的话就大不相同,让读者见到书名第一眼就耳目一新,不仅贴切传神,有吸引力,而且能跟时下热门的探险类节目荒野求生结合在一起产生联想,更能体会到主人公求生的不易。Gone with the Wind翻译为《随风而逝》既忠实于原标题,又能吊起读者胃口。究竟是什么逝去了?一旦读者的好奇心被激发,就极有可能会促成最终的阅读行为,从而实现书名翻译的最终目标。
五、结语
书名翻译本质上是一种面向受众(读者)的修辞行为,书名的翻译不可能不考虑译者所选用“辞屏”对读者的影响。翻译书名既要对作者负责,又要为读者服务。因此,忠实与有效应成为书名翻译的标准。
注释:
①本文讨论所涉及的“修辞”指的是“通过象征手段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态度,行为的一门实践”(“the practice of influencing thought, feelings,attitude and behavior through symbolic means”) 。关于西方修辞定义的讨论, ,详见:刘亚猛. 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京:三联书店,2004:2.
②关于“辞屏”的论述中文翻译引自刘亚猛,详见: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③国内有酸奶厂家以“简爱”命名其产品便是一个侧面证明。
④受众最好定義为“说者有意通过自己的论辩加以影响的所有那些人构成的一个组合”。详见: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京:三联书店,2004:136.
⑤“认同”是当代西方修辞泰斗伯克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修辞概念,它对于书名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伯克认为修辞的成败事实上系于受众对修辞者的“认同”(identification):只有当我们能够讲另外一个人的话,在言辞、姿势、声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做到和他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同于这个人的言谈方式时,我们才能说得动他。通过奉承进行说服虽说只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说服的一个特例,但是我们却可以完全放心地将它当作一个范式。通过有系统地扩展它的意义,我们可以窥探到它背后隐藏着的使我们得以实现认同或达致“一体”的各个条件。通过遵从受众的“意见”,我们就能显露出和他们一体的“征象”。关于“认同”的论述及翻译引自刘亚猛,详见: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345-346.
⑥不能把读者想象成既会汉语又懂英语的具备双语能力的鉴赏型学者。从逻辑角度而言,这样的读者自己已经具备理解乃至翻译英文书名能力,倘若非要为他们做翻译,那也只是一种语言游戏,而不是为了传达思想或跨文化沟通而进行跨语言转换意义上的翻译。
参考文献:
[1]Kenneth Burke, 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44-45.
[2]彭璇,隋长红.书名翻译的文化策略[J].科技信息,2010(3):771-772.
[3]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京:三联书店,2004: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