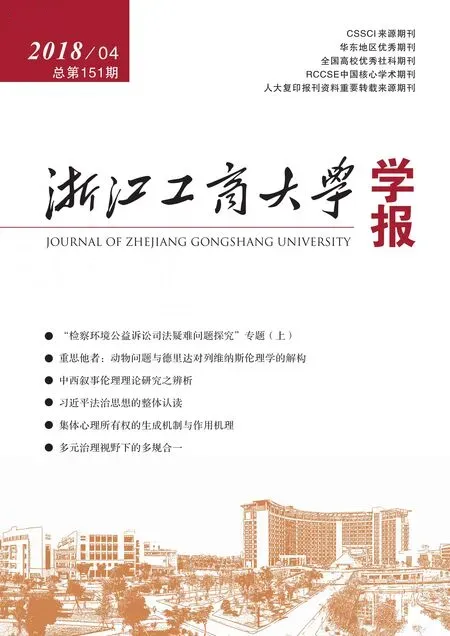空间美学的理论生成与合法性建构
2018-01-15裴萱
裴 萱
(河南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空间美学以“空间”作为美学研究的中介,探究空间元素、空间话语、空间理论等如何生成主体的审美经验,并以美学批判的视角介入后现代文化场景,推动了美学话语的进一步延展。从美学研究对象而言,空间天然地构成主体感性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对空间的“视知觉”感知内蕴审美经验,构成空间美学的研究基点。“美学批评活动的空间总是一个被主观地对象化、感情化‘审视’的场域”[1]。时间和空间作为构建主体生存和人类思维两个重要的方面,塑造了两种基本的哲学人文科学研究路径。从空间性的视角而言,构成了对“时间——历史”线性理论模式的有机调整与补充,成为重塑个体主体差异性、异质性、多元化的良好策略。对空间元素的分析与确证不仅实现了对传统权威话语的拆解,发掘出曾经被边缘化的空间场景,更是建构起全新的主体存在状态和审美感性体验能力。“所谓‘存在空间’,就是比较稳定的知觉图式体系,亦即环境的‘形象’。存在空间是从大量现象的类似性中抽象出来的,具有‘作为对象的性质’”[2]。空间美学也正是在主体的感性能力与空间的审美话语之间,找到了存在的合法性价值。
一、 空间美学的理论萌芽:主体感性认识与空间经验的内在融合
美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主体感性之学的学科形态,其获得自身的场域伦理和合法性价值是一项重要的现代性事件。18世纪以来,认识论哲学逐步占据欧洲的学术场域,主体的理性思维能力、认知自然的能力以及改造神学的能力都获得极大提升,“人”逐步取代了“英雄”和神灵,获得了自我存在和自我认知的权力,并由此带动了一系列现代学科的产生。知识的分化、专业的分工、现代大学与学科教育体系的确立等等,都成为现代性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在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以牛顿、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伽利略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他们以理性认知的方式实现主体对自然和宇宙的探究,延展了主体理性思维的视阈;哲学领域的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唯理论哲学家通过理性建立起主体的启蒙观念。在此进程中,却没有一门单独的学科和知识场域来系统研究主体的感性思维、艺术话语、审美实践以及诗性想象等方面的内容,主体的感性能力被压抑在理性的话语霸权内部。那么,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就重新思索感性思维和审美经验在推动人性启蒙方面的作用,并且要逐步将感性活动从理性的规训下独立和解放出来。“在力量的可怕王国中以及在法则的神圣王国中,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外观的愉快的王国”[3]。系统把主体的感性能力和诗性智慧纳入知识研究范畴的当属意大利启蒙主义学者维柯,他对笛卡尔的理性观念持反思与批判态度,并且将以形象思维为核心的“诗性智慧”视为促使主体全面发展的关键元素,该知识话语被称之为“新科学”。维柯通过对人类学和神话学的研究,认为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是朴素的形象思维和充满感性的诗性智慧,主体以审美想象与感性直观方式实现对外在世界的认知。而“诗性智慧”在维柯的视域中,首先体现的仍然是人与自然外物的关系问题,也正是原初先民把个体情感赋予外物以情感性,并生成审美意蕴丰富的形象过程,其中具有部分空间性和家园回归的因素。“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例如用‘首’(头)来表达顶或开始,……船帆的‘腹部’,‘脚’代表终点或底,果实的‘肉’,岩石或矿的‘脉’,‘葡萄的血’代表酒,地的‘腹部’,天或海‘微笑’,风‘吹’,波浪‘呜咽’”[4]。外在的自然现象和主体的精神感知通过富有形象色彩的词汇进行联系,这不仅确证了主体自由愉悦的生存状态,更是感性能力得到延展的契机。
如果说维柯通过诗性思维的方式重塑了主体的自我启蒙进程,那么德国启蒙运动哲学家鲍姆嘉通则在哲学史和美学史上首次提出“美学”(Aesthetic)术语,系统地建立起美学作为学科的理论范畴和区别于其他学科的自律性价值,并获得“美学之父”的荣誉。由此,美学作为现代性学科分化的产物,终于获得独立于哲学和理性之外的知识内涵,也给研究主体的感性认知领域和审美活动找到了合法的理论空间。“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5]。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通过哲学理论的论述再次确证美学的感性学之义。尤其是将美的鉴赏力判断界定为主观快感的审美愉悦,这就直接确证美感和审美判断与道德活动、理性活动等其他活动的不同,确立了主体审美趣味存在的价值。审视西方现代美学的谱系进程,感性能力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内涵不断得到加强,席勒的“感伤的诗”、黑格尔的“感性显现”与“感性形式”、叔本华的“审美直观”、尼采的“酒神”沉醉和悲剧快感、里普斯的“审美移情”、克罗齐的“直觉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美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等等,都将美学理论同主体的感性思维进行结合。可见,美学自身的学科建构天然地就与主体的感性认识能力、审美实践活动、直观体验意识以及超功利的趣味判断相关,是一种围绕着主体感性审美活动而延展出来的哲学理论。“空间”同样作为主体先验存在的重要维度,也成为主体感性认识的重要方面,并凸显出强烈的审美意识。空间美学形态也由此得以生成。
审视主体对外在自然的感性认知和审美经验,对空间的诗性阐释构成主体认知的重要维度。自然空间的感性体察、生存空间的身体感知、家园空间的审美留恋以及想象空间的艺术表达等等,都一直内化在主体思维活动中,成为确证主体感性能力的重要表征形式。在前现代时期,主体对空间的感性体验还带有朴素本体论的意味,往往将主体的生命和意识视为自然空间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将主体的视觉、触觉等感性体验方式纳入进自然的春华秋实、大化流转的空间进程中,此种古朴的诗性智慧也正是维科所认为的“新科学”与“美学”之义。比如中国哲学典籍《周易》便通过对自然现象和宇宙运动的符号学把握,完成了主体对自然空间朴素的、辩证的感性认知,并且突出浓厚的审美意蕴。“爻辞”中不仅将人类生活与自然运动进行了统摄,更是彰显出浓厚的空间意识,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等都成为度量人类社会的参照。从《周易》开始,通过感性体验和符号形象的路径来描绘空间,成为中国古典时期哲学、文论、画论以及美学思想的重要维度,并且呈现在“超以象外”“天和人和”“无我之境”“神与物游”“神思妙悟”等一系列关键范畴中。《尚书·洪范》中通过“天地大法”和“九州五行”的空间认知,完成了自然空间向主体社会空间的比附;《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和运气学说实现了自然空间和人类身体空间的内化;而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天人感性的神学描绘也凸显出主体在空间中的生存价值。经过哲学层面对空间的朴素认知,审美层面的空间体验逐步也成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表达,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天地自然皆有情愫,讲究尚空、空渺[6],而审美经验的生发则是建立在主体和客体、“心”与“物”之间,并进行同情交流的空间场域。钟嵘在《诗品序》中有云:“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7]在这样一段话中,蕴含了大量的空间因素,出塞的女子、戍边的将士、战死的荒魂、等待丈夫回归的妻子、免职流放的官员,他们对家园的留恋和回归的向往就构成独特的审美情愫,并进而凸显在自然外物的空间感知中。路途艰险,前路茫茫,长河落日,生死未卜,而这些都是在无限的空间中展开,悲凉的空间体验中方能使得诗歌产生并具有感染人的力量。可见,空间不仅构成主体认知世界的重要手段,更是广泛地诉诸于主体的感性力量,成为生发审美经验的载体。
西方古典时期同样也将空间视为主体生存的重要维度,主体可以通过“朴素唯物主义”的方式进行体察,在模仿论和自然神学论的谱系中实现艺术和诗性的延展。柏拉图系统地指出空间和主体感性认知之间的关系,他从理念模仿说出发,认为主体对空间把握正是一种感性的经验,是在对空间的身体占据中完成超验性的体察。“还有第三种性质,那就是空间,它是永恒的、不容毁坏的并且为一切被创造的事物提供了一个住所”[8]。正如《理想国》第七卷中的“洞喻”理论:在黑暗洞穴的狭窄逼仄空间中,受到惩罚的人们必须面壁思过、不能回头,而身后的火光和表演杂耍的演员将虚假的影像投射到墙壁上,犯人所看到的虚假影像仅仅是“美”的复制品和延伸品,真正的“美”是存在于理念世界中。空间就成为美的本质、美的生成以及美的体现的重要载体。而对空间的感性体验和美本体的发掘更多地表现在自然神论的视野中,普洛丁吸取了柏拉图“美在理念”论,主张美存在于超越世俗生活和自然空间的“神灵”和“迷狂”的境地。主体需要用“内在的眼睛”和“灵魂的视觉”来感受美的存在,而这也需要在自然的广阔空间中完成。在文学维度,《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记》正是英雄“归乡”的空间历程,主人公十年海上经历构成叙事的主导线索,其中对空间的体验正是凸显了原始先民的朴素感性意识。但丁的《神曲》同样是在空间的游移和转换中,将个人梦幻般的景象与爱情、友情、赎罪等情感体验进行融合,彰显出空间的“寓言意义”与“哲理意义”。可见,对空间的感性认识与诗性体验构成古典时期美感生成的重要维度,也在“感性”的层面上与美学具有相互通约之义,并促使空间美学具备存在的合法性前提。
二、 空间美学的话语延展:空间诗性伦理的现代美学方案
进入现代与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以来,哲学和美学领域的“非理性转向”和“诗性伦理”愈加明显,感性因素在美学研究中所占据的地位逐步上升。审美直觉、意识流、绵延说、无意识、酒神精神、审美移情、游戏说、存在主义、美学感性批判等等,这些都推动美学进一步摆脱理性枷锁和哲学理论的束缚,呈现出“形而上”的抽象理论与“形而下”的审美实践相结合的美学面貌。在此进程中,主体的感性认识能力和形象直观思维得到进一步强化,美学也在确证主体感性审美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将其上升为促使主体启蒙、实现精神自由的话语表达。如果说主体在古典时期的空间体验仅仅被纳入自然本体论的范畴;那么现代主体的空间体察则是建立在空间本体论与空间实践论基础上,空间不再是被动的、能够被“同情”的外在符号,而是成为属于主体自身创造出来的物质空间或精神空间,已经被浓重地打上了“人学”的印记。由此,建立在感性体验基础上的空间不仅可以传达出审美意识,更是表征呈现出主体在现代性社会中的身体经验,从而具有存在论层面的内涵。感性、身体、经验、存在等关键词都成为考察空间的理论生长点。在现代性社会大生产的语境中,主体经过空间实践,建构起“人化”的空间本体,并由此带来空间压缩、空间失衡、空间流动、第三空间等新形态。这些“外在”的空间变革也带来主体“内在”感性和意识层面的空间体验,再加之哲学领域的“非理性转向”等文化思潮的推动,空间成为主体拓展感性领域、审视自身存在的重要文化表征。“现代艺术的纯粹即艺术的自律,它通过一种距离让自我独立于日常生活世界之外,体现出鲜明的自律性倾向”[9]。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从“时间”和“绵延”出发,最终建构起来属于心理学层面的“绝对运动”观念。外在的物质运动其实是主体的“感性”和“身体”对我们自身的欺骗,而真实的运动只能存在于意识流时间的“绵延”中。虽然柏格森更为看重“时间”的本体化功能,但是空间因素却得到明晰的呈现。柏格森认为,运动本体是一个时间维度连续进行的过程,是不会在任何特定的场景中停止的;那么为什么主体还是会把运动分割成为一段一段的进程呢?这正是因为“身体的惰性”和“空间的错觉”造成的。主体的大脑、身体等都具有物质性存在的特质,那么建立在外在刺激基础上的“知觉”也属于主体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受到外在特定空间的刺激,产生了特定的身体感官知觉,形成了静止化的空间意识,然后再通过大脑的记忆与重构,从而完成一个整体的空间位移——“运动”。“无论运动物体位于空间的哪一点上,我们只看见一个位置。意识在这个位置外之所以还觉得有旁的东西,乃是由于意识把先后个位置保存在心中而对之加以综合”[10]。如果说柏格森通过对主体“意识”和“身体”的二元论来给空间提供了身体化本质,那么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中,空间更是经由身体的运动和感觉,而不断得到彰显。当胡塞尔把与空间相关的其他元素都“悬置”之后,发现身体成为空间生成的“优先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身体综合了主体的触觉、视觉、听觉等多种知觉,能够随时定位自身所处的空间;另一方面,身体的运动以及身体对外在空间的体验,也塑造了新的空间序列、重建了新的空间经验,这被胡塞尔称之为“视域”。静止的身体和单纯的视觉凸显出的是二维的空间“视域”,而身体通过众多知觉的感性综合,完成了空间的动感营造。“而这个处于未规定之中的视域又被同时认为是可能性的一个活动空间(Spielraum)”[11]。由此,现代空间和主体身体就产生了相互融合、相互阐释的关系,空间成为与主体的感性体验与身体话语息息相关的本体化存在。
柏格森和胡塞尔通过高扬主体身体的感性能力和现象学还原的方式,完成了从身体到空间的现代转型,而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则将主体的感性空间经验直接上升至“存在”与“生存”的高度,建构出了一条从经验空间到生存伦理的诗性理论。海德格尔在其存在论哲学中从“此在”和“栖居”两个维度建构出空间在主体、天空和大地间的关系。“此在”强调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所建构出来的空间样态。主体“此在”的存在不仅仅具有时间维度,空间维度更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在世界中存在”其实正是空间自身的“敞开”。如果没有主体的生存与体验,那么空间也只是未被“命名”的、僵化的物质载体;而主体通过对生产工具的使用、艺术的创作、日常生活的介入使空间具有了一种“切近性”,把本来属于外在自然空间的领域更改为“建构性”“配置性”以及“调整式”的主体身体空间。这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讲,被称之为“去远”和“定向”。“去远”是指主体通过身体对空间的改造,把“远处”的空间纳入到自我“切近”的空间中,去除“远”而实现“近”。“去远”正是空间不断向主体“敞开”的进程。“只有在此在与事物打照面之中,一种揭示才是可能的,那么在这种意义上,空间就是一种先天的因素”[12]。海德格尔空间论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栖居”。从“天、地、神、人”四重整体以及建筑、生活等视角来进行审视,主体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必须要占据一定的空间,而且要通过物质性的建筑和精神性的“栖居”共同完成。所以,主体在筑造自身的房屋之时,也在同时构筑着属于自己的“空间”。海德格尔强调了空间感知、空间存在和身体之间的重要联系,并且以“存在”的视角将空间视为延展主体感性经验的重要元素;而梅洛-庞蒂则直接将身体与空间进行结合,认为身体的感性经验、视知觉感触等构成崭新的空间样态。身体不仅仅具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基础,更是以身体的经验、身体的行为和身体的感知表征出“视知觉”,进而促使“物性”与“灵性”的统一。主体的视觉、知觉等活动借助于身体,完成新的主体空间的建构。此种不断被体验、不断被建构出的空间被称之为“深度空间”,从而与“客观空间”进行相互对立的考察。主体在通过视觉对外物进行摄取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深度错觉”,比如焦点、对称、透视、立体、完形等等。随后,主体大脑中的知觉活动会进行“格式塔”式的再整合,最终形成属于主体身体和感性维度的空间序列。梅洛-庞蒂从认识论角度高度肯定空间的功用,主体在认识和感知外物之时,不仅要审视其平面的呈现,更是要通过知觉的体验完成立体化的、深度感的空间体察,构建全新的空间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视知觉通过身体为中介,完成从外在空间到内在精神空间的转型;而身体则通过空间、知觉、世界以及艺术等多种合力的交织,最终营造出独具感性特色的审美话语,形象性、体验性、情感性、直觉性等审美元素得以逐步彰显。“正是通过把他的身体借给世界,画家才把世界转变成了画。为了理解这些质变,必须找回活动的、实际的身体,它不是一隅空间,一束功能,它乃是视觉与运动的交织”[13]。通过以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家的论证与揭示,主体对外在客观空间的感性经验和对内在精神空间的自我重构,成为当代空间理论的主导形式。这一方面呼应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空间实践思想,延续了哲学层面的空间本体内涵;另一方面提升了主体空间经验的合法性存在价值,把空间伦理与现代主体的生存问题、符号意义、审美经验、文化批判等进行互涉,拓展了空间理论的内涵。
可以看出,空间话语和空间经验一直作为主体感性认知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内化于主体的身体知觉内部,成为推动思维认知、确证主体存在的关键话语。美学学科成立的合法性和自身知识场域伦理的建构正是源自对主体感性认知能力的确证,维柯、康德、鲍姆嘉通、尼采、克罗齐等理论家都从“为感性立法”的知识视野完成了美学本体学科的划定。与此同时,空间经验也通过“身体”“知觉”成为主体感性认识能力的重要方面,并且凸显出直观性和审美性特质。那么,“空间”和“美学”便在美学理论体系中有了相互结合、相互阐释的可能。一方面,美学理论在关照主体感性认知能力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其中的空间元素。比如维柯在主体“诗性智慧”的论述中,就涵盖了大地、海洋、河流等自然空间的审美体验;里普斯的“移情论”也充满空间距离的感性经验;海德格尔的空间“栖居”也与艺术的真理表达、诗性的彼岸存在有密切的关联。另一方面,空间经验和空间理论自身也在不断延展,并逐步凸显出审美意蕴。从古典时期建立在“移情论”基础上的自然空间,到现代时期建立在“视知觉”基础上的身体空间与深度空间,内蕴其中的艺术话语表达、外在形式彰显、审美经验体察都一以贯之。无论是美学理论向空间元素的话语辐射,还是感性空间经验的审美观照,都将空间、感性和审美三个关键词密切结合在一起。这也正是空间美学生成的理论契机。同时,空间美学作为现代美学的一部分,其学科与知识形态的成熟也是伴随着现代性进程而展开的。其一,美学为自身划定确定的理论范畴即现代性工程的产物,其本身存在的价值正是源自学科分化。美学自身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知识框架、理论体系等都是知识现代性工程的产物。空间美学作为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知识形态,是伴随着空间理论的延展、感性话语的凸显以及审美自律的推动而产生的,是主体高扬自身空间诗性伦理的结果。其二,空间美学的哲学基础还来自于现代性“空间实践”与“空间压缩”,是经由主体的身体、实践、视觉等建构起来的自主性空间样态,并以激进的姿态表征出现代主体的空间生存与空间体验。“审美实践与文化实践对于变化着的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特别敏感,正因为它们必须根据人类体验的流动来建构空间的表达方式和人工制品。它们始终是‘存在’与‘形成’之间的中间人”[14]。由此,空间美学正是在现代性主体实践与学科分化的场景中,得以逐步生成并得到确定的理论内涵。
三、 空间美学的场域塑形:文本审美实践的推动与美学价值彰显
空间美学的理论生成不仅通过感性与身体把“空间”和“美学”进行结合,更是融汇于文学艺术的知识生成过程,进一步推动美学理论自身的谱系学流变。无论是立体主义绘画的“空间并置”,还是大地艺术的“空间游牧”;无论是后现代元小说的“空间叙事”,还是新传媒视野下的“赛博空间”,都极大增强了文本自身的空间话语,成为对传统单一线性审美观念的结构与重构。文学艺术的空间实践促使美学进行理论层面的总结,并进而考察主体的空间感性能力和空间审美能力。
自20世纪初期现代文学形态逐步成熟以来,空间元素、空间经验、空间叙事与空间结构纷纷构成文学审美经验传达的组成部分,它们在强调主体感性空间经验、推动文学结构调整、尝试叙事时空并置等方面进一步促使文学的现代化转型,可谓以审美实践的方式塑造空间美学话语。比如以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等为代表的意识流文学就消解了传统的“时间——线性”叙事模式,进而以直觉感触和意识流动的方法展开文本,形成一种以主体心理空间为核心的叙事框架。《追忆似水年华》力图避免现实场域的叙事空间,而是以某一个特定场景为核心、以心理空间为主导,展开不同时空的衔接与跳跃。文本中关于“小玛德莲娜”点心的描绘成为审美空间凸显的经典段落,主体在对不同空间的审美体验中,完成了从心理叙事空间向审美空间的升华。“也许因为贡布雷的往事被抛却在记忆之外太久,已经陈迹依稀,影消形散;凡形状,一旦消褪或者一旦黯然,便失去足以与意识会合的扩张能力,连扇贝形的小点心也不例外,虽然它的模样丰满肥腴、令人垂涎”[15]。如果说意识流文学仅仅是在文本中凸显出主体心理空间的话,那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小说”以及之后的后现代文学,通过对空间的游移、拼贴、并置等手法展开叙事就更加司空见惯。空间元素也表征出后现代文学的多元价值取向,新小说、后殖民文学、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戏剧、“垮掉的一代”等等,都进一步破除“时间——线性”话语霸权对文学的统摄,转而通过“空间——并置”等手法去表现从自然空间、叙事空间再到心理和审美空间的文学线索。博尔赫斯在《阿莱夫》中有机借鉴神秘哲学理论和具有东方特质的禅宗思想,通过类似于“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的空间悖论完成“新小说”的创作理念。在《阿莱夫》中,作家通过世界上的不同地理空间展开叙事,各种线索相互交叉,呈现出“迷宫”式的空间场景和叙事脉络。比如《死于自己迷宫的阿本哈坎·艾尔·波哈里》《两个国王和两个迷宫》《釜底游鱼》《阿莱夫》等篇章中都有着独特的空间隐喻。“这个阿莱夫的直径大约为两三厘米,但宇宙空间都包罗其中,体积没有按比例缩小”[16]。在“阿莱夫”的“超空间”表达中,空间中的自然万物、主体视界的包罗万象、心灵场景的复杂变迁等都渗透进此种彻底开放的空间场景,并且契合主体视知觉层面的空间体察,从而凸显出美学层面的意义。新小说派的另一位代表作家克劳德·西蒙也在文本中进行大量空间叙事的尝试,其《草》《弗兰德公路》等小说文本便将现代绘画艺术中的空间因素渗透进语言文字的表述中,通过大量的空间碎片、空间拼贴、色彩描绘等手法凸显出文学语言的立体结构。在后殖民文本中,空间因素得以更加明显的凸显。身份的游离、空间的迁移以及记忆与情感的指向,都在特定的空间中得以彰显。空间一方面成为后殖民文本推动叙事线索的关键,另一方面也和“地方记忆”与“文化认同”相互契合,主体在对空间的诗性留恋中萌发出特定的情感指向。“空间游移的过程其实是通过主体无意识的方式,把全球的经济运行网络空间纳入成为一个整体。康德拉同时也表达,主体行为背后的动机,正是‘冒险’‘英雄主义’等个体化欲望的表征结果”[17]。
空间元素已经成为后现代文学进行叙事形式实验和审美意义凸显的关键符号,并通过主体的身体感知、诗意表达完成了对空间的本体言说。这些都促使美学理论层面对空间进行重新思索。在文学之外,其他后现代艺术也都凸显出对空间元素的重视,比如立体派绘画的空间重构、大地艺术的公共空间营造、小剧场戏剧中“空的空间”,等等,都在艺术本体、艺术媒介、艺术传达等维度凸显出空间的本体性价值。空间不仅构成“内容”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成为变革艺术形式、传达艺术美学的重要策略。“我可以选取任何一个空间,称它为空荡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下走过这个空间,这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18]。文本中空间因素的凸显与主体性的延展、主体间性的交往以及文化的多元共生构成了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关系。因为文本中的空间最终都需要落脚于主体的审美经验之中,成为主体进行审美感知的符号序列,由此,美学意义和美学理论的特质便逐步显现出来。这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的论述:“恰恰是组织空间经验的形式在变化着,它以特有的方式把空间上的近与远连接起来,这是以前的任何时代都没有发生过的。在熟悉与疏远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关联”[19]。
从空间哲学对主体感性审美经验的视域融合,到现代文学艺术的空间审美话语实践,凸显出空间美学本体构建的合法化基础,更推动了美学理论自身的“空间化”转型。从美学理论的历时发展流变而言,经由现代哲学文化思潮的“非理性化”转型和人文主义的推动,美学话语中的感性、意志、本能、直觉、无意识等知识话语得以逐步呈现,并在促使美学获得自身合法性存在的同时,走向审美救赎的生命哲学。而空间元素在美学中却逐步得以凸显,尤其是在现象学、存在论美学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空间成为艺术表达和审美超越的重要元素。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认为,艺术是真理向“作品”和“文本”的自行置入,并向主体进行“敞开”与“呈现”的过程。“美的呈现”促使空间元素以“栖居”的姿态完成了从自然空间到诗性空间的转换。“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的谷物的宁静的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冥”[20]。詹姆逊作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家,在系统阐释审美文化批判的过程中,也将空间性纳入其中。空间一方面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规训主体的必要渠道,但另一方面也是主体通过空间感知进行“认知测绘”的策略,并且通过对空间的感性认知把个体经验与整体文化场景联系起来,促使主体能够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进行重新定位。正如在“航海大发现”时期绘制地图一样,后现代美学也通过对空间的感知与体察,确定主体在“文化空间”中的“地理”定位。“认知图绘使个人主体能在特定的境况中掌握再现,在特定的境况中表达那外在的、广大的、严格来说是无可呈现(无法表达)的都市结构组合的整体性”[21]。可见,在从现代性到后现代美学谱系流变中,主体的空间体验、空间的审美表达以及空间维度的审美批判一直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推动美学不断向前发展的理论资源。空间美学建构的基点源自主体对空间的“视知觉”感知,并由此生成的美感体验。“空间”成为联系主体感性能力和审美经验的重要中介,空间美学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成为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话语。
空间美学诞生于主体的空间感知,拓展于现代哲学的诗性伦理,并最终成为一种关注主体生存的美学样态,这就直接凸显出其主体性、实践性、应用性、价值性特征。主体对空间的诗性体验、文学艺术的空间审美表达、诗性空间的美学批判等,这些都超出美学理论的本体性内涵,进而转向“价值论”层面对主体生存状况的拷问和对后现代审美文化的反思。这些都再次确证了空间美学存在的合法性场域。首先,空间美学的价值体现在对主体空间审美体验的关注和存在论层面的超越。主体在进行空间实践和“人化”空间改造的进程中,不仅生产出供主体持续生活的物质空间,更塑造了全新的主体空间审美体验。空间实践的过程也是主体从精神层面不断满足、不断“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进程。无论是画论中“山水之大,广土千里,结云万里,罗峰列嶂,以一管窥之”[22]的主体空间“散点”游移,还是诗论中的“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23]的心灵空间;无论是“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空间思念,抑或“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空间欣喜,都在审美话语和审美情感的关照中,完成了从空间到主体的生存追问。空间作为主体在世界存在的基本形式,直接规约着主体在感性审美维度的生存体验,也就自然地成为文学艺术实践所重点关注的对象。由此,空间、审美和文艺三者就构成相互融合的关系,并在对生存空间的“诗性”领会中完成了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乌托邦场景。从主体对空间的“人化”实践,到以“空间”为基点形成的审美情感共鸣,美学话语始终围绕着对空间符号的再现、表现、传播、隐喻、象征等进行,最终又再次回到主体诗性的生存之境。空间美学呈现出浓厚的美学“价值论”色彩,它一方面关注现实的审美实践活动,通过对艺术文本空间因素的发掘与阐释,传达出主体的审美心理机制和审美共鸣;另一方面则通过主体自身的空间审美体验,通过空间生存、空间栖居等实现从审美伦理到生命伦理的主导线索。
其次,空间美学的价值论表现在美学公共性和批判性特质的加强。从法兰克福学派到新马克思主义美学,都跳出了艺术自律和美学独立的学科窠臼,将审美视为主体反思历史并且对抗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精神伦理。法兰克福学派通过美学“否定的辩证法”“反艺术”“单面人”等概念内涵进行论述,以激进的美学批判视角完成了从个人精神超越到批判社会文化的理论路径,这就直接拓展了美学的价值功能。空间美学则直接呈现出美学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文化特质,这同样是由于“空间”的本体属性决定的。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空间压缩和空间交往变得更加广泛,呈现出私化空间和公共空间相互交融、共同生长的场景。从网络赛博空间的信息高速流动,到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表达;从大地艺术的公共空间展现,到碎微空间“分形”再聚合的交往奇观,空间逐步成为一个主体进行交流的公共场域,显示出自由平等的意义指向。而空间美学则依托于现实层面的空间交往,以文化符号的形式再造出审美的“共通感”[24],将美学意义从个体主体延伸到公共性的交流中。环境美学、装置艺术、大地艺术、行为艺术等都可以与空间美学产生某种共鸣效应。“空间是一个物质产品,它相关联于其他物质产品,包括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赋予空间一种形式、一种功能和一种意义的人”[25]。比如大地艺术代表人物罗伯特·史密森的《螺旋形防波堤》便通过对盐湖空间的再改造,说明从美学到环境的符号意义指向;本雅明的“游逛者”审美抒写便是在“差异性”基础上生成的城市空间美学话语;福柯的“另类空间”则通过历史与现实、主流与异质的空间辩证法,完成了碎微空间的审美再聚合过程。这些都呈现出空间美学的批判话语和意识形态反思价值。
空间美学作为建立在主体空间感性能力基础上的美学话语,直接高扬了空间的体验性、形象性和情感性特质,成为一种“自下而上”且从审美实践出发的价值论美学[26]。空间美学一方面源自主体空间审美经验的拓展,建构出一条从主体空间经验到空间存在的美学理论脉络。“从空间观点看,在身体内部,感觉所构造的一个有一个层次预示了社会空间的层次和相互关系。被动的身体(感觉)和能动的身体(劳动)在空间里聚合”[27]。另一方面,空间美学也是现代美学自我流变、空间因素不断得到彰显的结果。审视未来的审美文化场景,赛博空间、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脑云端、“超文本”写作、新媒体艺术等都营造出崭新的空间形态。空间美学将进一步凸显出美学理论的实践性和人文性价值,并给美学本体在后现代的发展提供必备的知识学资源,持续关怀主体的审美存在与“栖居”。这正如泰戈尔的诗句:“我们的生命就似渡过一个大海,我们都相聚在这个狭小的舟中”[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