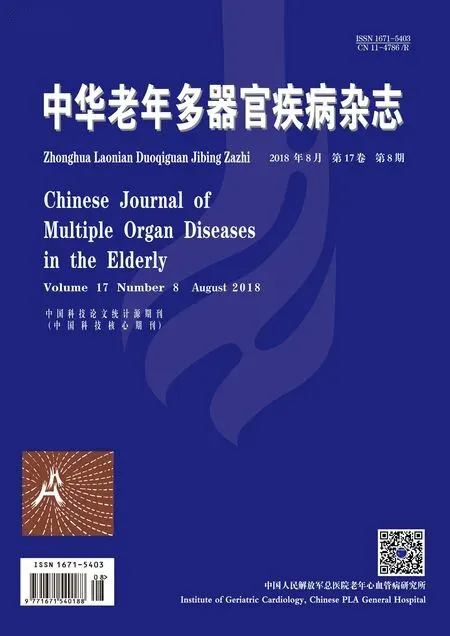巨细胞动脉炎引起下肢间歇性跛行的诊疗进展
2018-01-13吴潇郑月宏
吴潇,郑月宏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血管外科,北京100730)
下肢间歇性跛行是老年患者常见的主诉,主要表现为下肢活动后疲劳和疼痛,短时间休息后可缓解,这一典型症状的出现提示下肢动脉可能存在狭窄。动脉粥样硬化是老年患者下肢动脉疾病最常见的病因[1],面对此类主诉,临床医师易将目光局限于动脉硬化,而忽视引起下肢动脉狭窄的其他原因如巨细胞动脉炎(giant cell arteritis,GCA)。GCA是一种累及大和中血管、以炎性巨细胞浸润为特点的系统性血管炎,可导致下肢动脉狭窄。尽管临床症状相似,但动脉粥样硬化与GCA的治疗完全不同,因此区分它们很重要。
1 GCA的临床特点
GCA是老年患者最常见的动脉炎,发病平均年龄为76.7岁,发生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2],女性的发病率高于男性。亚洲人并不常见,因此临床医师易忽视。
GCA主要累及主动脉及其主要分支,病理表现常为肉芽肿性动脉炎[3],血管内膜在炎症状态下反应性增生,从而导致受累血管狭窄或闭塞。为协助诊断GCA,1990年美国风湿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 ACR)总结GCA分类标准如下[4]:(1)发病年龄≥50岁;(2)新出现的头痛;(3)颞动脉触痛或搏动减弱;(4)红细胞沉降率≥50 mm/1 h;(5)颞动脉活检发现单核细胞为主的炎性浸润或多核巨细胞肉芽肿。符合上述5条标准中的至少3条可诊断为GCA。分类标准并非诊断标准,但由于缺乏更多有效的手段,此标准仍作为诊断依据。作为补充,2010年英国风湿病学学会(British Society of Rheumatology,BSR)/英国风湿病学卫生专业人员协会(British Health Professionals in Rheumatology,BHPR) GCA治疗指南中提到了患者的一些典型症状,当出现如下症状时需警惕GCA[5]:(1)突发头痛;(2)头皮压痛;(3)颌跛行或舌跛行;(4)视觉症状;(5)全身症状;(6)多肌痛;(7)肢体跛行。根据受累血管的分布,GCA可分为颅动脉GCA和大动脉GCA。大动脉GCA因常不表现出上述典型的症状和体征,与颅动脉GCA相比,更易被忽视[6]。另一方面,由于ACR分类标准不涉及下肢动脉,因此GCA累及下肢的患者常不符合标准[7]。
一项针对中国GCA人群的回顾性研究指出,仅2.9%的GCA患者在诊断时出现了下肢跛行症状[8]。发生率较低导致GCA的研究进展较缓慢,但GCA仍是最常累及下肢的血管炎性疾病[9]。总结目前已报道案例可发现,与动脉硬化性跛行相比,GCA引起的下肢跛行更倾向于表现出如下特点。(1)患者缺乏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包括吸烟、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脑栓塞家族史等;(2)症状进展更快,且与踝肱指数(ankle brachial index,ABI)不匹配。GCA患者在几个月内就可进展至下肢静息痛,此时的ABI通常仍>0.4。(3)症状可能具有波动性,时好时坏;而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在治疗前症状逐渐进展。(4)常常累及双侧。动脉粥样硬化常一侧起病,逐渐发展至双腿,而GCA患者更易表现出双侧对称性病变。(5)可能会累及动脉粥样硬化不易累及的动脉,如胸廓内动脉等。(6)除了肢体跛行外,大动脉GCA患者还可能出现主动脉夹层、主动脉瘤、心肌缺血等表现。
此外,急性期GCA患者会出现红细胞沉降率及C反应蛋白等指标水平升高、肝功能异常、碱性磷酸酶水平升高、贫血和血小板增多等现象。这些常见的化验指标异常提示GCA可能,但不具特异性,需进一步进行评估。
2 超声检查
超声检查具有无创、快捷、经济、分辨率高的特点,是欧洲抗风湿病联盟推荐GCA患者首选的影像学检查[10]。为鉴别2种疾病,首先需明确动脉粥样硬化和GCA超声影像的特点与区别。动脉粥样硬化损伤的典型表现为血管内中膜局部增厚、管壁斑块形成。而血管炎由于血管壁的弥漫性水肿,在超声下的典型表现为不被压缩的晕轮征,亦称压缩征[10],即血管壁近管腔侧有环形增厚的低回声区,用超声探头挤压动脉管腔时,此区域不被压缩。此征象往往表现为跳跃性病变[11]。文献报道以颞动脉超声下出现不被压缩的晕轮征用作GCA的诊断,其灵敏度是79%,特异度是100%[12]。除GCA外,其他疾病如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ies,ANCA)相关血管炎、感染性疾病、严重动脉硬化也可出现类似的晕轮征,但非常少见[13]。此方法最常用于诊断颅动脉GCA,而对于大动脉GCA的评估价值有限,因为主动脉在人体较深的位置,超声对主动脉管壁炎症及管腔变化的观察效果不佳。但下肢动脉位于浅表,管径较颞动脉更宽,超声可以更好地识别该处血管炎症。因而对累及下肢动脉的GCA患者而言,超声是首选的检查。如果患者的下肢动脉超声显示出典型的大动脉炎征象,则可证实临床对大动脉炎的怀疑。
超声检查的局限性在于其要求相对丰富的临床经验。由有经验的医师进行多普勒超声是识别GCA是否累及下肢动脉的首选手段,如果超声检查可发现GCA的特征表现,就可避免其他不必要的影像学检查和动脉活检。
3 其他影像学评估
如果超声下未能发现GCA的特征表现,还可尝试进行更复杂的影像学检查,充分评估大动脉的血管损伤。由于磁共振血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和CT血管造影(CT angiography,CTA)具有无创优势,已逐渐取代血管造影。 MRA和CTA的优势在于可评估全身血管,尤其是主动脉等超声难以探测的区域。此外,增强图像可更好地表现管腔形状,表现血管内和管周形态特点。
3.1 MRA
活动期血管炎在T1序列增强像中可表现为管壁增厚、明显强化,T2序列中表现为高信号,提示管壁水肿,如果主动脉或其分支的MRA图像中出现这一征象,则高度提示大动脉炎。非活动期的动脉炎可观察到管腔闭塞和狭窄。高分辨MRA的分辨率已足以用于评估颞动脉,静脉注射钆对比剂还可克服信号强度的限制,增强后的黑血像还可以检测管壁中延迟增强的物质特性。MRA对血管壁和周围软组织的区分要明显优于CTA,在诊断大动脉炎方面,具有和血管造影相似的准确性,但主动脉的病理不易获得。GCA的MRA表现及机制并未得到证实,T2WI序列对血管壁水肿探测不敏感,易产生伪影[10]。钆对比剂不是炎症的特殊标志物,动脉硬化斑块在钆对比剂下也表现出纤维帽和血管壁的强化[14]。因此MRA在区分动脉炎和动脉硬化方面不及超声检查,如果超声可探及受累血管,首先应通过高分辨超声进行鉴别。
3.2 CTA
CTA存在放射损伤,对软组织的分辨力较弱,对血管炎的评估不具明显优势。但CTA对血管结构和钙化斑块的呈现较好,有利于区分动脉硬化和炎症损伤。活动期的动脉炎CTA下表现为动脉壁增厚(>3 mm),延迟像出现双环征(管壁外侧强化,内部衰减),其灵敏度为73%,特异度为78%[15]。
3.3 18F-氟化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GCA患者管壁形成炎症时,代谢活性增高,从非累积放射性18F可用来评估炎症活动度。但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PET-CT)图像有限的空间分辨率不能识别直径<4 mm的血管[16],加之颞动脉邻近生理摄取较高的脑组织,炎症活动易被掩盖,空间分辨率更高的PET-CT可提供更精确的定位信息。
与CTA相比,PET-CT的阳性预测值更高,但不同文献所报道的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差异较大,分别为67%~77%和66%~100%[17]。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动脉炎代谢显像的解读尚缺乏统一标准和客观的衡量指标,加大了研究难度。已有研究将血管壁的摄取浓度与肝脏进行比较,为血管炎症活动度提供半定量结果,并以血管壁摄取浓度大于和等于肝摄取浓度作为诊断GCA的标准之一[18,19]。
由于衰老所致内膜下平滑肌增殖,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血管更容易表现出18F摄取水平升高[20]。而动脉硬化斑块中的巨噬细胞增多也可导致18F摄入水平升高,从而造成误判。因此,PET-CT在老年人下肢跛行中的应用有限,且花费高,不推荐作为诊断的常用手段。
4 GCA引起下肢间歇性跛行的治疗
下肢GCA患者建议按大动脉GCA处理,初始治疗推荐立即给予激素冲击或有效剂量的糖皮质激素[21],初始糖皮质激素剂量推荐1mg/(kg·d),症状改善后依据个体化差异进行激素减量,密切关注疾病是否复发。
许多患者需要长期的免疫抑制治疗,预防主动脉或其他大血管闭塞的不断进展。免疫抑制剂可首选甲氨蝶呤。使用7.5~15.0 mg/周的甲氨蝶呤可减少GCA患者的激素用量和时间,帮助降低复发[22,23]。硫唑嘌呤也可用于GCA的治疗,帮助减少激素用量[24]。而环孢素A的治疗作用则不如其副作用明显[25],不推荐常规使用。
生物制剂中,阿达木和英夫利昔单抗被证明效果不佳[26,27]。在激素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托珠单抗有利于GCA的持续缓解,但其长期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有待评估[28,29]。
炎症损伤可以改善,但纤维化是不可逆的。对于下肢GCA患者,可加用阿司匹林减少缺血事件的发生,但这一治疗方法的获益尚未被证实。此外,对于活动性动脉炎患者,进行手术或介入使血管再通,可能会导致动脉破裂或再狭窄,除非有需要外科干预的严重急性下肢缺血,否则应尽可能避免手术而首选内科治疗。由于血管成形术的再狭窄率高达50%以上,对于难治性或病情反复的下肢GCA患者,旁路搭桥术为标准术式。
5 下肢间歇性跛行的诊断流程
当患者表现出间歇性跛行症状,接诊医师首先应仔细核对病史并进行体格检查,了解其有无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加重动脉粥样硬化的服药史及自身免疫病史,确定有无下肢溃疡、脉搏减弱及动脉杂音,初步判断患者下肢动脉是否有病变。
其次需对血管损伤进行血流动力学的评估,考虑ABI和症状是否匹配。还可完善趾肱指数及ABI运动试验、下肢节段性血压监测,更好地反映下肢缺血的真实严重程度。
对血管形态学的评估,首选超声评估血管壁的形态,根据结果决定进一步的评估方式。如果超声未显示典型的血管炎表现,可通过高分辨MRA或CTA以探测有无管壁炎症。
颞动脉活检是颅动脉GCA的检查金标准,但大动脉GCA常不表现为颞动脉受累,颞动脉活检识别此类患者的灵敏度并不高[6],因此对于下肢间歇性跛行的患者,颞动脉活检并非必需检查。股浅动脉活检对一些患者可能有帮助,接近半数的下肢GCA可通过股浅动脉活检证实。如果有典型的临床症状和检验结果、激素治疗有效或具有典型的超声表现(治疗后14 d内活检有效率不会降低),活检阴性的患者处理同确诊GCA患者[5]。如果临床高度怀疑GCA,但未发现影像学和病理证据,可以经验性静脉给予糖皮质激素[30],观察症状是否有所缓解。
总之,下肢GCA和动脉粥样硬化的治疗方向完全不同,尽早对下肢GCA患者开始治疗有利于在纤维化尚未形成之前逆转症状,因此早期诊断、快速识别下肢GCA患者尤为重要,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外科干预风险。对于以下肢间歇性跛行为主诉的患者,临床医师应保持警惕,不可全部将其归因于外周动脉疾病,而忽视其他相对少见疾病的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