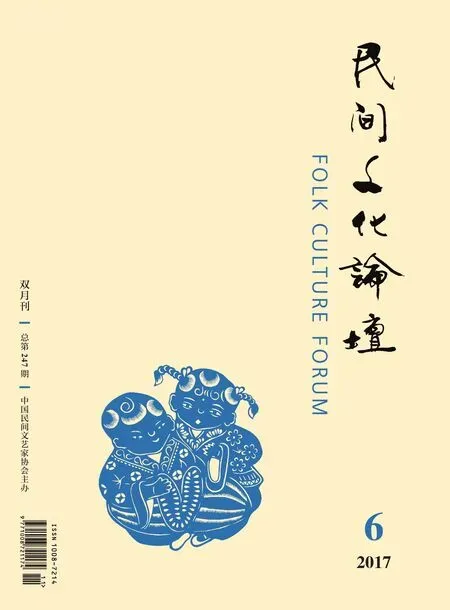传承母体论的问题*
2018-01-02福田亚细男菅丰塚原伸治彭伟文
[日]福田亚细男 菅丰 塚原伸治 著 彭伟文 译.
传承母体论的问题*
[日]福田亚细男 菅丰 塚原伸治 著 彭伟文 译.
由福田氏提出,给后来的民俗学研究带来巨大影响的传承母体论和个别分析法,是对此前(几乎被视作唯一方法)的重出立证法加以批判,作为更加科学的方法被提出来的。它们经常被理解为功能主义,也被认为与功能主义存在同样的问题而遭到批判。那么,福田氏的传承母体论所受到的其他学科的影响都有哪些?
此外,在对现代社会进行考察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将那些未必由传承母体所传承的事象纳入为考察对象?是不是认为不应该将这些事象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进而,近年福田氏提出,今天的民俗学有必要“从个人出发去把握民俗”,但是这看起来与以集体行为前提的的传承母体论很难相容。那么,福田氏对其具体方法是如何思考的呢?
一、传承母体与其他学科有什么关系?与功能主义、共同体论等有什么关系?传承母体是功能主义吗?
二、传承母体与类型论和地域主义有什么关系?
三、传承母体是模型还是理解实态的方法?
四、对传承母体来说,“土地”“历史”“集团”“制约力”全部都是必须的吗?
五、由不能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的主体所传承的事象,是否能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
六、传承母体与个人的理论关系是什么?对个人如何思考,如何研究?
七、如果仅限于传承母体传承的事象,则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将被限定,无法研究的事物是不是会越来越多?那会不会缩小民俗学的可能性?
八、近年,有的意见认为应该将包括以媒体或互联网为媒介的交流在内的,没有“传承母体”的现代问题也作为民俗学的对象,这在福田氏看来是否已经不算是民俗学了?
九、反过来,传承母体论是否存在现代有效性?是否可以应用在文化的所有权、文化现象的权利等问题上?
关于传承母体论的课题
塚原:发言人换了,我是塚原。课题3这部分,就是“传承母体论的问题”这部分由我负责。
首先,我就在课题3这部分打算问些什么问题先整理了一下。福田老师提出的,对后来的民俗学研究给予了很大影响的传承母体论及个别分析法。我的理解是,这是对此前的有人说“几乎被认为是唯一方法”的重出立证法的批判,作为更加科学的方法被提出来的。它们经常被作为功能主义加以理解,也被认为与功能主义存在同样的问题而遭到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曾有人指出它们和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的类似之处,这些理论对传承母体论的建构是否有过影响,有的话又是什么样的影响,希望能够听听福田老师的看法。另外,也有的意见认为,当我们思考现代社会的时候,未必由福田老师所说的传承母体所传承的事象,也有必要纳入考虑范围。老师您本人是否认为这些不应该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此外,近年来老师您提出现今的民俗学“有必要从个人出发去把握民俗”。从理论的角度去思考的话,看起来与以集体行为为前提的传承母体论很难相容。希望听一下老师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方法是如何考虑的。
传承母体的理论
塚原:虽然在场的各位应该都已经知道了,但是作为简单的前提在这里再提一下。福田老师说过:“民俗是有母体的。”如果就其具体内容加以说明的话,以下是从《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①[日]福田アジオ:『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説―柳田国男と民俗学―』,東京:弘文堂,1984。本书中译本《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与民俗学》于2010年7月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关于传承母体论的具体阐述,详见中译本第二篇第六章。在原文中,引用文献出处均为夹注,在译文中统一改成脚注。包括已有中译本的文献在内,所有出处均按日文原题及版本标注。——译者注引用的:“具有这样的制约力,保持着超世代的文化事象的集团,其集团本身也是超世代的存在,原则上有着其成员生而注定归属其中的性质……传承母体超越其成员的生死而存续,是因为其占据着永久存在的特定的大地。”②[日]福田アジオ:『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説―柳田国男と民俗学―』,東京:弘文堂,1984,第259页。继而还写道:“几乎相当于与利益集团相对的自然共同体、与组织相对的地缘共同体。”③同上。将上述内容加以总结的话,也就是福田老师本人所概括的那样:“占据着一定领域的土地,在这个基础上使超世代的生活持续下来的集团,就是所谓的民俗传承母体。”④同上。福田老师从这里出发,对民俗进行了定义。福田老师前面说,自己几乎没有用过“民俗”这个词⑤参见前一篇《民俗学的方法问题》中的相关叙述。(本期第28页)。但是在这里明确写着:“如此,则民俗就是占据着一定领域的超世代存续的社会集团,通过以其制约力让成员承担而传承下来的事象。‘传承’必须这样加以规定。”⑥同上。
菅:啊啊,刚才是这么说了。(笑)
塚原:以上基本上都是从《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引用的内容,也阅读比较了福田老师的其他文章和著作。福田老师在不同地方的表达基本上没有出入,几乎以相同的形式对传承母体进行了定义。也就是说,传承母体由土地、历史、集团、制约力四者共同规定而成,而福田老师还写道:传承母体的代表是可以作为“村”或“部落”加以把握的村落。⑦同上,第260页。因此,福田老师说到传承母体时,最常指的传承母体基本上就相当于村落。
在此不讨论福田老师的具体研究,关于将其他集团作为传承母体,福田老师在《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中也有论述。首先,村落内部还有社会集团,如组、组合、讲、マキ⑧日语发音maki,没有相应的汉字表记。指一个村落内部有本家与分家关系的血缘集团,部分地区也泛指有血缘关系的亲族。——译者注、一同、地类等。此外,还有超出村落,或由数个村落联合组成的单位,较村落更大的事象传承范围,如乡、村落联盟、行政区、学区等。福田老师写过的这些也是传承母体。还有,传承母体扩展到村落以外,涉及了都市范围。老师列举的包括宿场町、门前町、城下町、职人町、住宅区等,指出这些也是传承母体。另外,虽然有所保留,但是书中写道:“新都市的住宅区或小区也具有成为传承母体的可能性。①[日]福田アジオ:『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説―柳田国男と民俗学―』,東京:弘文堂,1984,第261页。”虽然“有可能性”这样的形式稍显消极,没有说“这也是传承母体”,但福田老师还是将传承母体扩大到了这样一个范围。
虽然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福田老师表示过传承母体并不限于村落,但是福田老师在自己的著述中,就应该如何认识村落方面留下了大量成果。其中,被认为最重要的是下面要展示的图,也就是村落领域模式图(图2)。这个图应该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以聚落、田野、山林的形式表示村落领域的模式图,给后来的民俗学村落研究带来了很大影响。福田老师自己在拿出这幅图前后,都引用了柳田的观点。虽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在经过论述后,福田老师写道:“从柳田的观点看来,应该可以将村落领域的构造设定为以下的模式。②[日]福田アジオ:『日本村落の民俗学的構造』,東京:弘文堂,1982,第37页。”然后通过引用柳田的文章,最后做成了这个由三个同心圆构成的图。读了这篇论文的论述,总觉得福田老师的看法是“柳田是这样说的。如果把他的说法模式化的话应该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还有像右边这样一个非常相似的图。(图3)这是由大塚久雄介绍过来的、在日本很多人都读过的一本书上的图,也就是从马克斯•韦伯1924年的《普通社会经济史要论》转载的图③[徳]ウェーバー・マックス:『一般社会経済史要論』(黒正厳・青山秀夫訳),東京:岩波書店,1924(1954,1955)。。这里引用的是大塚久雄在《共同体的基础理论》④[日]大塚久雄:『共同体の基礎理論―経済史総論講義案―』,東京:岩波書店,1955。中转载的韦伯用以说明德国中世纪庄园制的图。福田老师刚才说自己是1959年入学的,在那个时代,大塚久雄的书因为是同时代著作,应该有比较多的人读过。我们主持人的看法是,看到这个图,很难想象福田老师完全没有受它的影响。简短直说,我们认为福田先生应该是受到了个图的影响。

图2 村落领域的模式图(福田 1982)

图3 德国的中世纪庄园制(大塚 1955)
传承母体论的功过
塚原:前面是关于传承母体论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关于“因传承母体论而成为可能的事”,福田老师本人作过总结。首先,将民俗学研究从少数研究者的独占中解放出来。其次,通过从历史的角度究明特定民俗事象在特定地点保持和传承的条件、理由、意义,实现向作为乡土研究的民俗学的回归。此外,虽然在福田老师的研究之前类型论就已经存在,但是传承母体论使其得以刷新。我想应该可以概括如上①[日]福田アジオ:『日本村落の民俗学的構造』,東京:弘文堂,1982;[日]福田アジオ:『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説―柳田国男と民俗学―』,東京:弘文堂,1984。。另外,福田老师在说到自己的研究时,曾经对传承母体论作过以下评价:“对个别的传承母体的民俗相互联系起来进行把握,通过对其进行分析,析出民俗事象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由此成为民俗学的目的。②[日]福田アジオ:『近世村落と現代民俗』,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第9页。”
但是,关于福田老师的传承母体理论,也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其一,有一种意见是,传承母体论是否应该与功能主义或结构功能主义受到同样的批评呢?也就是说,存在实际上村落是向外开放的,但是却将其作为封闭的事物进行理解的问题;其次,像前面说过的那样,传承母体已经以土地+历史+集团+制约力的方式被规定下来了,历史性已经被包含在内,这一点也遭到了批评。
此外,岩本通弥还提出了关于传承母体论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地域主义的批评③[日]岩本通弥:「民俗学における『家族』研究の現在」,『日本民俗学』,第213期,1998,第48—67页。。还有一个疑问就是现代社会的问题,刚才已经说过了传承母体的四个规定要素,那么不满足这些要素的事物怎么办?例如,流动人群、通过媒体进行的信息传递、离开家乡的人群和没有超越世代的人群等,种种情况都会存在。另外,还存在未必会形成集团的,或者不受地域限制的网络。考虑到这些情况,当思考传承母体对民俗学而言,其有效性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应该更有弹性呢?又或者说,不是由福田老师所说的传承母体所传承的事象,是否就不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呢?
例如,福田老师从一开始就没有将都市排除在外,但是如果将其作为传承母体进行把握,则可以被纳入民俗学研究对象的事物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该民俗事象不由集团传承的情况、未必能够被认为是超世代传承的事象等。刚才菅先生也已经提到过了,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虽然福田老师表示过传承母体可以用于都市的研究,但是当研究都市的民俗时,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比如通过媒体沟通的事物,经由互联网实现的交流,团体性质但没有历史性的集团的活动,以及被商品化、被流通和消费的民俗学或“民俗式事物”,这样一些事物也可能会出现。像刚才说的那样,福田老师所说的民俗是由传承母体所规定的。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当遇到上述情况,哪些是民俗,哪些不是民俗呢?
此外,关于从个人出发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福田老师以前在女性民俗学研究会上也讲过,在《近世村落与现代民俗》这本书里所写的,今天的民俗学在村落研究方面应该做的七项工作中,最后也列举了“从个人出发去把握民俗”。但是,传承母体本身,就像刚才说过的那样,是由土地、历史、集团、制约力所规定的,当从个人出发把握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可能的具体方法呢?再者,刚才福田老师说了民俗学应该在超越个人经验范围的层面就对象进行考察,如果是这样,则会产生一个疑问:当对个人的问题进行考察时,有什么可能的方法呢?
其他学科对传承母体论的影响
塚原:接下来进入提问阶段。刚才就问题的背景进行了几个方面的总结,首先我想就“传承母体论的理论问题”方面先提四个问题。
第一,传承母体和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例如,与功能主义、构造功能主义、共同体论等的关系,您自己是怎么看周边学科的呢?此外,从这些学科中您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希望就这个问题得到您的指教。
第二,有人对传承母体论提出过批评,认为与其说它是地域主义,不如说是以对各地的民俗进行类型化并加以比较为前提的理论。请问这个类型论和传承母体与前面所说的地域主义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第三,请问从理论性的问题来说,传承母体是模型还是作为理解实态的方法论提出的呢?
第四,前面已经细致地阐述过,对由土地、历史、集团、制约力所规定的传承母体来说,请问这些确实全部都是必须的吗?
先就以上四点,希望能够听到您的解答。
福田:非常感谢你如此细致地对传承母体这个令人怀旧的词汇进行了整理。
从基本立场来讲的话,简而言之,在思考如何通过现在的生活、文化等事象认识或者重构一定时期范围内长长的历史的时候,飘浮在半空中的朦朦胧胧的民俗事象也许可以模糊地说明过去的样子,但是却无法捕捉其历史过程。简单地说,社会、集团、组织、制度这些事物,由于它是连续性的,因而现在的人们的行为可以成为追溯过去,或者是认识过去的手段,我是从这个思路设定传承母体论的。或者说,我赋予上面说的这些事物以“传承母体”这样一个术语,用来把握它们。
因此,将传承母体当作一个孤立的、僵化的概念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归根结底,“传承母体”这个术语,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要把握一个历史阶段的漫长时间里的世界,不通过传承母体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如果说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那么它确实是严格的。如果说超越世代或者说超越个人与过去相联系,那什么是必要的呢?现在生活着的人们占据着一定的大地,而正因为大地具有连续性所以才可以追溯过去,诸如此类你刚才总结的方方面面,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以过去、历史作为目的,如何通过现在去把握,这样一种方法上的整理和准备,就是我说的传承母体。
另外,不太清楚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还是前面你作为别的问题提到过,所谓共同体论的问题。现在的人在什么地方看到大塚久雄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可能会觉得很高兴吧,但对我们来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是大学一年级二年级,一定会读的书。因为这样,反过来说,我也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样,读的时候第一次想到“原来如此!”但在建构自己的“村落领域论”的时候并没有想起大塚久雄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但是,虽然不像你刚才讲的那样,应该也已经深藏在我的意识里了。《共同体的基础理论》是一本很薄的书,但是对我们来说,确实认真读过,还为此开过研究会进行讨论,从这一点来讲,确实是深受影响。恐怕在这里的很多人也是一样,听到大塚久雄的名字就会想起《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实际上,对大塚久雄来说,他研究的中心并不是这个,但是对我们来说他的研究就是共同体,从这一点来说,你们指出我受到他的影响,我也觉得“原来如此,可能确实是这样。”自己也觉得同心圆式的类型在形式上相一致这一点,可能是从这里来的。虽然受到过影响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关于领域这一观念则未必有什么关联。
归根结底,在思考如何通过现在把握过去的时候,刚好在相同时期,也就20世纪60年代,那时候文化人类学,或者社会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构造功能分析。一个个地区,一个个村落,一个个家族组织,在日本国内,还有当时冲绳研究也很盛行,又或者是国外也以构造功能分析的方式,去探究它的组织、制度的功能性定位。这是人类学的工作。在这当中,我思考的是历史是什么样的,或者说能不能把握它。实际上这是矛盾的。构造功能分析,本来是以批判从摩尔根开始的历史论的形式出现的。构造功能分析在20世纪60年代是重要的理论之一,但它和历史是矛盾的。尽管如此,我还认为由此重构历史的世界是可能的。就这一点而言,传承母体论并不是所谓构造功能主义。构造功能分析这个方法,如今在文化人类学的领域,可能会被说“现在还在说这个啊?”这样一种过时的方法,我是这么认为的。我现在基本上还是使用这种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是不是只能研究封闭的世界而无法用来把握开放的世界这个问题,传承母体本身是从方法上进行设定的概念,根据在具体研究时以什么作为传承母体,是可以应对更广泛的事物的。
这么说并不是要逃避,我只是兴趣点偶然落在村落上,传承母体论就变成了“村落领域论”“村落境界论”。确实,在这种情况下传承母体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没错是建立了一个自我完结的理论。这当然是必须接受批判的地方,但是,我只是尝试将像无脸妖怪一样面目模糊的村落,用一个易说易记的词汇去更加清晰地建构它的整体形象罢了。
村落的类型论式把握
福田:接下来是哪个问题?
塚原:关于类型论的问题,请指教。
福田:我非常喜欢类型论,经常把各种各样的事物类型化,进而像各位知道的那样发展成了“东西论”,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传承母体的必然归结。归根到底还是在各个地方分别进行调查和分析,传承母体是用来描述它们的历史样态的框架。但是同时,仅仅把握个别地区,对我们想要了解的,或者是想要理解的事情来说是不够的,于是我就从类型论进行了另一个方面的把握。我的类型化研究,可能是因为以一般读物的体裁出现,相对来说有更多机会被读到,这方面的形象似乎越来越突出了。但是,我的类型和其他人的类型不同,归根结底还是以在各个地方,简单地说就是作为传承母体的单位进行调查和分析的结果作为类型的基础。在这一点上,我自己认为,和仅仅将要素搜集起来进行类型化的研究是不同的。
塚原:那么说,福田老师在最初以传承母体、个别分析法等形式开始研究的时候,进行类型化,比如说对日本的东西之别进行思考,这些都是并没有想到,而是后来才有了这样的想法,可以这样理解吗?
福田:基本上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写的东西,归根结底是在各个地区,对当地作为现在的生活的民俗分别进行分析,然后去搞明白那个地方的历史形成过程,或者是展开过程,是这么做过来的。
但是,类型也是很早就开始做了,到底还是喜欢啊。只不过在研究类型的时候,有一点是包含在里面的,也就说对我们这代人以前的人所做的类型化进行批判。在我的方法中,有对那种非常单纯的,根据一元化指标进行的分类的批判,我在类型化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我都差点忘记了,我暗自认为这就是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就是若者组①“若”为日语“年轻”之意。若者组是由村落内年轻男子组成的组织,负责村落内的劳动、夜警、消防等,进入现代社会,很多村落组成了与此相当的青年会、青年团等。村内设有若者宿、青年会所等设施作为他们的活动据点,有的地方还将之作为若者组的集中住宿场所。加入若者组的年龄一般在15-17岁,加入时带上酒并口宣规定的词句。若者组内部承认年长者的权威,过去还有成员必须严格遵守的礼仪和规则等。过去作为将年轻人特有的活力统括起来承担村落运营的实际工作的若者组现在基本不存在了,大多转变仅以祭礼或传统活动的继承为目的组织。——译者注的类型设定②福田在初期的研究中,曾尝试以加入资格、加入和退出年龄等几个指标对若者组加以类型化。(福田 1972[1989])方法,虽然没怎么被其他研究者采用。这个方法很朴素简单,但民俗学很少采用这样的步骤。
另外,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讲,不管什么样的学术,都不会始终停留在一个个分别的研究上面,而是将一个个分别的研究综合起来,从更大的面上去把握,纵观整体,将其抽象化,民俗学也是一样的。应该对一个个传承母体进行个别的分析,将这些个别研究的成果积累起来,对其进行综合,或者是类型化,或者是明确地域差异从而展望整体,这样去进行抽象化。但是,民俗学却一直把比较研究当作唯一的研究在讲。
能适用于“新的民俗”吗?
菅:但是,当我们现在想要做这样的研究,已经做不到了吧?
福田:不会,做别的问题就可以,当然若者组是不行了。
菅:但是,要想到作为民俗能够代替若者组的事物,简单地说,就只有新的文化了,因为这些对福田先生来说是不算民俗的。那么,如果说新的民俗产生出来,但这也会造成形容上的矛盾。新民俗产生,这个民俗学一直在说,比如将若者组变化以后的情况进行类型化。但是,说是对若者组变化以后的情况进行类型化,实际现状是消失的压倒性地占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说,问题就是,只有对20世纪民俗学才可能的事,或者说是对20世纪民俗学来说具有可能性,而对21世纪民俗学来说是不可能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福田: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菅:是啊。这到底还是个大问题啊。
福田:这是个大问题。刚才也列举了很多嘛,不能算传承母体的各种组织、关系等等。这没关系啊。对象不能算传承母体,还是要进行民俗学的研究的话,唯一要求的是你通过这个研究要搞清楚什么。我是因为想要搞清楚历史,没有传承母体,就无法捕捉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过去。
菅:实际上,我有时候也想,今后反过来要用一用“传承母体”这个术语。但是对福田先生来说,传承母体和村落是一致的,而正因为这种倾向使它失去了现代的广泛适用性。反过来说,传承这种行为在今后应该也是存在的。简单地说,如果将传承定义为世代间的传递的话,这是总会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事情,现在是,未来也是,应该总会发生世代间的传递。而它的发生场所,或者是这种行为的主体,则未必是村落。然而,将它的主体称为传承母体这件事本身,决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这里列举的各种集团应该也可以用这个术语。但是,这里就必须先去除村落这个限制框架。
福田:基本上,日本的民俗学是以村落作为前提展开的,如果说20世纪民俗学的话,应该就是这样。我对去掉它完全没有意见。关于这一点的可能性,没有半个世纪吧,大概40年前我已经这样想,也这样写过。但现实问题是,在这上面可以做什么样的研究?简单讲,如果让我说传承母体是什么的话,传承母体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把握时间长度而设定的,如果没有这一点,即使用了“传承母体”这个词,我感觉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意义。因此,刚才列举了很多,这个是不是不能算传承母体啊什么的,网络啊信息共享啊等等,如果让我说的话,只要说明白在这里要搞清楚的历史是什么就行了。因此,如果说“历史啊,再见”的话,那就变成完全不同的别的理论了,这么一来,网络上联结起来的人们的信息网啊人际网络啊之类,这些现象或者说事象确实存在,也确实必须对它们进行某种研究。但是,民俗学对它们有必要从认识历史世界的角度来研究吗?因此,如果去掉了历史认识,因为你们一直在努力地想要去掉它嘛,如果去掉了的话,我觉得就是“请随意”,但是如果随意去做的话那不用民俗学去研究也可以,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菅:真是前后一致啊。(笑)
从“个人”出发把握民俗
塚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个人的问题。
福田:关于个人,我一直说必须切实把握个人,虽然我自己没有这样做。首先在实际的行为当中,或者说是故事当中也是,行为也好,故事也好,将它们表现出来的是个人。一直以来的做法是,一边说要从个人出发,但是又将某个地区,或者是我所说的传承母体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大体上,当对传承或者是民俗进行记述的时候,典型的做法是只在括号里标注地名。也就是说,一直以那个地方作为一个整体这样的形式去把握的。与此相对的,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把握的话,在那个社会集团或者说地区,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或者是容许的范围。简单地说,比如过年的活动,可以是过年的仪式,也可以是年轻人的活动或者是游乐,这些行为是被许可的,在容许的范围内有着多样的形式。这不是必须去把握的吗?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这个容许范围的意义可以带来对历史的过去的认识,表现了差异、落差、矛盾、对立、纠葛,又或者在那个社会集团里不被容许的出格现象也可以把握。每个人的行为或者想法虽然是属于其个人的时间范围内的,但是同时个人所展现出来的行为或者想法表现了超越个人时间的传承母体的多种形态。因此,我想个人应该是一定要去把握的。我要说的是,一直以来那种面目模糊的,没有具体人名的访谈记录或者观察之类是不行的。
塚原:是不是说,这与其说是福田老师的研究,不如说是为了将来的民俗学?
福田:是这样。至今为止的民俗学,正是这种没有具体人名的民俗学。具体人名的意思是,必须有个人的存在,研究才会得以丰富。
塚原:非常感谢!
K890
A
1008-7214(2017)06-0031-08
福田亚细男(福田アジオ,Fukuta Ajio),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名誉教授,柳田国男纪念伊那民俗学研究所所长;菅丰(菅豊,Suga Yutaka),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塚原伸治(塚原伸治,Tsukahara Shinji),茨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准教授。
[译者简介]彭伟文,历史民俗资料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讲师。
* 本文译自《超越“20世纪民俗学”:我们从与福田亚细男的讨论中学习什么?》的《课题3》部分。
冯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