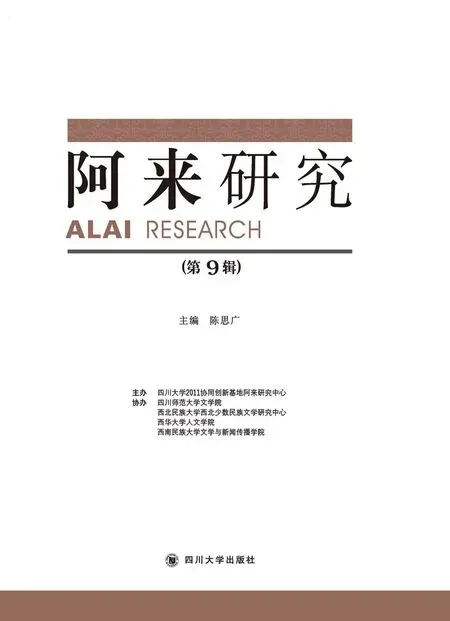民族和性别双重意识的深入掘进
——评徐琴教授 《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
2018-01-01杨荣昌
杨荣昌
西藏民族大学是藏族文学研究的重镇,活跃着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发表和出版了诸多为学界瞩目的学术成果。徐琴教授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多年来,她在藏族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辛勤笔耕,取得了丰硕成绩,尤其在女性文学研究方面,更是用力甚勤。2017年11月,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 《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一书,是多年学术探索的结晶,标志着在该领域的理论建构已初步形成体系,并显露出个人独特的话语风格。
在藏族当代文学历史上,央珍、梅卓、白玛娜珍、尼玛潘多等女性作家均做出过重要贡献,她们在共同的家国和民族情怀的感召下,形成各具特色的创作美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徐琴以极大的学术自觉,集中梳理当代以来的藏族女性文学历史源流,分门别类深入文本世界探究艺术内涵,探析作品背后的作家所担负的那种历史、民族、身份多重因素交织的文化责任;通过解读她们的代表性作品,深入其驳杂深厚的生命景观,爬梳剔抉,去伪存真,在文学作品的民族观念、性别意识、文化理想、价值立场等方面都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深化了学术研究的维度。
首先,关注凸显的民族意识。藏族女性作家善于对本民族历史、传统进行吸收与转化,将丰富驳杂的民间传说、英雄史诗、天人观念等最具深度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明晰的文学表达,以文学的形象性为其他民族的读者所认知。作品打开历史的通道有很多条,如自然物象、民族仪式等,这些民族的意象和符码,透露出作家深层的内心世界。徐琴认为,“作家将藏族人的情感及生活方式进行了内蕴化的提炼。轮回、法鼓、诵经、长磕、赎罪等词汇的使用不再是简单的修辞方式,而是带有藏族人的生命体验和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消融在了藏族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雪域高原上独特的精神信仰和生存状态的表现,离不开宗教书写,它体现在藏族文学的多个维度上。从文学背景来看,雪山、玛尼石、经幡、白塔、佛堂等是常见的场景,烘托了一种宗教氛围;从民间理想来看,对英雄和祖先的崇拜,源于民族史诗的熏陶与濡染;从写作手法来看,常用历史传说、宗教经典、神话故事等作为引言,将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引入当代叙事,勾连起历史与现实的通道。在徐琴看来,即使书写爱情这一人类普遍性命题,作家也无意识地与宗教相联系,“这种杂糅浓郁宗教色彩的爱情书写方式与汉族女性作家的爱情书写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风范”。通过这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意象的抒写,女性作家一次次强化了自己的民族情感,彰显民族身份。她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无疑是值得信任的,研究民族文学,离不开对民族审美意象符号的把握。当下诸多的民族文学批评为何隔靴搔痒,言不及义?原因就是研究者以他者的眼光来观照民族文学,对潜藏在文本中那些动人的精彩细节、隐约的精神秘密无法及时捕捉,而它们往往是作品最核心的艺术细胞。徐琴作为汉族研究者,却对藏族文学中的独特意象有贴己之感,她从藏族独特生产、生活的物象入手,探索这些具象化物质背后的作家自然观、生死观和宇宙观,揭示作家与作品之间在精神同构上的对应关系,从而厘清一条创作的发生学路径。
其次,聚焦女性文学张扬的性别意识。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 “女性写作”不同的是,藏族女性作家几乎共同抵制对性意识和身体经验的描写,她们超越个人身体之萌动,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关注世道人心,传递家国观念,反思民族传统,呈现出一种厚重的艺术经验。在徐琴看来,“藏族女作家的创作较少 ‘小女人’或‘私人化’‘隐私化’写作,也不会哗众取宠,仅仅去关注身体、性以及一己的哀愁与幽怨,她们的写作似乎更有一种历史纵深感,即使是抒写女性个体的苦闷和哀伤,也与整个民族行进的步伐紧密相连”。她们对现实的强力介入,对城乡发展带来的贫富反差和人性变异,尤其对本民族在现代化潮流奔涌中日渐散失的根性传统和难以更改的民族痼疾,更是表现出一种难言的隐忧与伤痛,这是作家责任与道义的表现。如在梅卓等人的创作中,她看到了文学如何从女性狭小的视域中超脱出来,接通更宽广的人文视野,并自觉承担起对民族历史和族性意识的双重反思。梅卓在面对民族文化根性中的痼疾的时候,有着一种感同身受的痛苦和悲哀,以对藏文化的痼疾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建构着自我的民族文化身份,写出了藏文化在强势文化面前的困惑与挫折,企望以惨痛的民族记忆来唤起潜存的豪猛威武的民族精神。藏族女性作家普遍拒绝轻盈浮华,追求深沉凝重,这与这个民族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担负的家庭责任形成一种强烈的呼应。更可贵的是,女性意识的崛起,体现在对一系列带有独立意识的新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她们渴望冲破传统的束缚,在新的时代找到人性的尊严。作家为了深化这类形象,不惜塑造与之相对的男性形象,他们柔弱猥琐、背信弃义,与女性的敢爱敢恨、重情重义形成鲜明反差。而且,在作品中,藏族的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她们身上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和男性一起构成了主导历史的力量。作家们对这类女性形象的塑造与赞美,传递出一种强力的价值观,亦是其女性立场的宣言。她们以女性的视角审视藏民族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挖掘女性在历史发展中潜在的活力,将女性个体的发展纳入民族发展的进程,在女性命运与民族发展之间寻找创作的最佳结合点,展现女性生存困境的同时也展现了民族生存困境。徐琴对这种张扬性别意识的书写给予积极肯定,她认为作家们 “有着对国家、民族和女性个体的独特理解,显示了女性对民族文化的探寻和坚守,传达出了鲜明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再次,饱含忧患的文化思虑。优秀的创作者和研究者都是本民族的先行者,她们独具前瞻性的思考,往往能够穿透历史与现实的帷幕,给人以深沉的启悟与引导。在徐琴的论述中,体现了强烈忧患意识。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家本人对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忧患与反思,二是研究者对于藏族文学发展的反思与批判。前者在书中的表现,在于徐琴深度阐释了作家的反思精神,她们对民族历史进程中女性生存状况的理性思考和对民族痼疾的批判,对被历史所遗忘的女性命运的开掘和关怀,对当下女性生存困境的体认和展现,以女性视角演绎的历史风云和社会变迁,女性的情感困惑和对理想之爱的追寻。如央珍的 《无性别的神》以女性视角观察时代更迭中的风云剧变,对西藏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反思;梅卓的小说在部落兴衰发展中反思民族生存的困境;白玛娜珍小说以女性自我挣扎的个性解放之路,反思民族现代化的困境;尼玛潘多以城乡交织、流变中女性的精神挣扎反思民族困境。这些有成就的作家,均从女性视角出发,着眼点却非个人悲欢,而是整个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她们的写作将自我发展与民族发展相连接,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连接,体现出一种深沉的文化责任。后者是研究者的个体反思。置身于研究的现场,徐琴并未失却自己作为学者应有的辨析与批判能力。在看到这个群体以民族性书写立于文坛的同时,她依然对作品中偏狭的民族观给予批评。她们对他者文化粗暴狭隘的抗拒、对宗教精神性力量不遗余力的张扬,都将削弱作品走向更深沉厚重的力量。没有一种恒定的价值立场和更高远的精神视野而过度地追寻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极容易在自尊与自傲的交织中走向自负,从而矫枉过正,走向另一种认同危机。优秀的民族文化必然要走向现代化,只有对根性传统进行必要的辨析与扬弃,使之符合时代主潮,体现当代精神,才能成为当代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因此,民族文学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费孝通先生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经典论述上来。徐琴关于当代藏族文学发展面临问题的分析,触及问题的症结,不仅对于藏族文学,对于其他除汉族强势文学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学而言,都有极强的参照意义。只是这部分论述在整本著作中显得单薄,优势经验的阐释与固化固然重要,问题困境的分析也必不可少。
最后,积极肯定作家创作技法的提升。藏族作家的成长环境和文化基因,适宜产生伟大的作品,藏地历史与现实的风云激荡、多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深厚根性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都让作家们有着多层面、多维度的表现领域。抛开那些猎奇的描写,仅就对个体价值感的关注和灵魂的书写而言,藏族女性作家的创作便可以有效接通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使西方现代叙事艺术与中国民族传统资源相化合,产生奇异的叙事效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马原的 《冈底斯的诱惑》,扎西达娃的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先锋小说,就是最好的例证。这种带有魔幻色彩的书写,同样体现在梅卓的 《月亮营地》等小说中。先锋的外表,并没有脱离藏民族独特的精神底色。徐琴对藏族女性作家积极吸收现代叙事艺术,对本土精神文化资源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给予热切鼓励,认为这是植根于深厚民族文化传统中创作的作家都应遵循的普遍规律。
文学研究的价值在于抛开那些浮嚣的碎屑,聚拢有益的成分,以研究者的灵性之笔打造出一朵朵最具核心价值的 “金蔷薇”。徐琴的研究,不仅将藏族女性文学放置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背景中考量,勾勒出各个历史时段的文学发展特点与坐标,探索其与中国主流文学思潮之间的异同点,进而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为读者找到评价的参照系。更重要的是,她着力探索、总结和彰显作家们的独特创造,凝聚作品中展露出来的异质性经验和略带陌生化的美学光芒,它们是构成中国文学整体经验的重要因素,缺少这些民族性突出的艺术成分,当代文学的阐释是不充分的。她以民族性和女性的双重视角介入研究领域,力图通过解读文本走进藏族作家的心灵深处,以同为女性之敏感,去感知那些细腻却灵动鲜活的情绪律动,寻找强势文化掩盖下的微弱却倔强发光的美学之源,使之聚集、壮大而成为不容忽视的美学力量。尤其女性文学中强烈的精神性、深厚的家园情怀等,都是当下文坛所稀缺的质素。这是区别于其他族别 (尤其是汉民族)和男性作家的独异的美学,这样的寻找显然是准确而又关键的。同时她又不乏学者的谨严,站在人类共同价值的立场上,诚恳地指出藏族女性文学存在的艺术缺憾,为她们摆脱困境,走向更高远的艺术之境寻找出路。这种既有个性温度又具理性思辨的言说,并且旁及藏族文学整体观感的书写,提供了一种可信的评说参照,对其他民族文学的发展亦有鲜明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