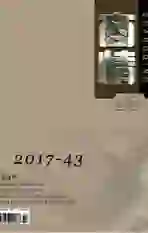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同性恋
2017-12-28张岑怡
张岑怡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以传宗接代作为婚姻的根本目的,以男女异性作为合法婚姻的必备条件;但与此同时,又从未视同性恋为莫大的罪恶而予以严惩,尽管不提倡,却也显示出相当大的包容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是原则性与务实性的统一,体现了古人独特的价值观和智慧。由于后者,使中国的同性恋颇为盛行;但由于前者,又使同性恋无法顺理成章地升级为同性婚姻。
【关键词】同性恋 异性婚 包容性 原则性
2015年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同性婚姻合乎宪法,成为全球第21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时代的趋势表明,越来越多国家的同性恋者站出来,要求实现自己的婚姻权益。2015年12月16日,中国公民孙文林(孙文林,男,中国湖南长沙人,2016年6月23日孙文林和男友两人相约在这天结为配偶。他们前往芙蓉区民政局要求办理结婚登记,却遭到工作人员拒绝。2016年1月5日,芙蓉区人民法院表示,起诉(申请)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决定立案受理。2016年4月13日,该案败诉)和代理律师石伏龙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请求判令芙蓉区民政局为其办理婚姻登记,此举被舆论称为“中国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显然,同性婚姻的实现在中国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然而,提到“同性婚姻”不免会让人想到“性”乃至是一种“变态的性”。我们中国人往往对“性”是讳莫如深的然而,关于“同性婚姻”学术界的研究甚为少见,法学研究仅限于民商法或法理学。为此,本文试图考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同性恋问题。这或许于学术、于现实都不乏启示的意义。
一、源远流长——同性恋的历史演进
提到同性婚姻当然就不可避免地首先要讨论同性恋(homo sexual),它是指对异性不能做出性反应,而对同性产生性爱倾向、性吸引;或对同性产生性爱倾向、性吸引并导致身体接触、产生性快感。人类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自然而然会有性的需求,同性恋则是人性取向之一,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同性恋史。中国同性恋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颇为盛行。在中国古代对同性恋称呼就多达数十种,如“分桃”、“断袖”、“男风”、“磨镜”、“顽童”、“龙阳之好”等。中国同性相恋史可以追溯至文明之初,清代纪晓岚所著《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载“杂说称娈童始黄帝”,《尚书·伊训》有所谓“三风十愆”(“三风”包括“巫风”、“淫风”、“乱风”,都与性有关系,其中“乱风”中还有“比顽童”一项)。对两种说法的解读至今仍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皆不可靠,不足为据。但根据《逸周书·武称》有关“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的记载,可以肯定商周时期已有同性恋。民间诗歌中,也有许多赞美男风之词,如《诗经·郑风》中的“子馻”一章有不少内容经后代学者考证,都认为是“两男相悦”之词。
先秦至秦汉时期史料记载的同性恋多与帝王诸侯有关,往往称作“外宠”、“侯幸”。汉朝几乎每个皇帝都是同性恋者,并被记入正史。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性恋由宫廷扩散到民间,史载:“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炽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皆相仿效。”魏晋南北朝男子普遍重仪表,乔装打扮,蔚然成风:“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且士族崇尚玄学清谈,妙趣言辞,放浪形骸,回归自然,无视礼教,形成一个排除女性的士人活动圈。隋唐特别是唐朝,不仅政治、經济、文化臻于鼎盛,社会也非常开放,竟然出现了“小倌”以从事男妓职业(作为男妓从事的“小倌”职业,虽然不限于男性间的同性性活动,却也不能排除它),同性性行为愈发普遍化和民间化。宋代的社会更加活跃,“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或许也是针对同性恋而发,但无法从根本上抑制住人们的性需求和性生活,自然也不能从根本上逆转男风。
明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个王朝,记载同性恋的资料大为增加,有小说、剧本与笔记等各种载体,同性恋更为平民化,所覆盖的人群之广泛为前所未有。同性恋作为一种性爱的形式在半个世纪的时期里几乎与异性恋并驾齐驱,官员士大夫趋之若鹜,以致形成了“不重美女重美男”、“有歌童而无名妓”之风气。
但到清朝末期,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他们耻笑中国人“丑陋”、“野蛮”、“文化落后”,并以西方的习俗、观念来改变中国。基督教盛行的西方国家对同性恋的态度是迫害、禁锢,甚至定为重罪,予以严惩。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同性恋受到外来文明的强烈冲击。尤其在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帝制的瓦解,中国融入世界主流社会,同性恋者更受社会的鄙视,进而转入隐秘状态。
二、有容乃大——同性恋的立法与宽容同性恋的原因
(一)宽松的同性恋立法
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就提倡禁欲主义,而早期基督教中更充斥着大量原始禁忌和禁欲主义的戒律,视同性恋为一种邪恶或罪行,直至处死。如《圣经》记载:“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与其相反,中国社会则从没有过这类的思想和做法,当欧洲对同性恋者处以死刑时,中国同样未发生过类似的事,甚至对同性恋习以为常,表现出很大的宽容性。通过史料和历代律例的记载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对同性性行为的干预相当有限。到了宋朝,时人陶谷所撰《清异录》对北宋京师汴京男风大盛的情形作出这样的描述:“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而北宋王朝对此情形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至政和年间才立法禁止:“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者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这似乎是迄今所知中国法律史上最早的关于同性恋的立法,但其所针对的主要是男性卖淫,当然也不能排除卖淫于男性。国家虽然立法禁止,但处罚也不算重,到了南宋这一禁令便不了了之了。
明代嘉靖年间制定条例,第二次对同性恋进行立法。《大明律例附解·附录》:“将肾茎放入人粪门内淫戏,比依移物灌入人口律,杖一百。”单就条文本身来看,似乎是对同性性行为的刑罚,但其实只是针对侮辱、侵害他人人身的鸡奸或强奸行为,至于合意行为并未作出惩罚性规定。endprint
直至乾隆五年(1740年)修律时才对自愿的同性性行为作出了惩罚的规定:“如和同鸡奸者,照军民相奸例,枷号一个月,杖一百。”[5]这与同时代欧洲对同性恋的惩罚相比可谓“薄惩”,惩罚非常轻,欧洲直到19世纪,许多国家还依然有反鸡奸条例,且处以极刑,如1835年英国还公开绞死了两个同性恋者詹姆斯·帕瑞特和约翰·史密斯。
通过前文对中国同性恋历史沿革和立法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古代的同性恋是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下生存发展的,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同性恋者没有受到法律的严厉禁止和社会的强烈排斥,甚至是被广泛接受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那么,其中的原因有哪些?
(二)同性恋盛行的成因
(1)上行下效。据《史记》、《汉书》记载号称“大汉雄风”的汉朝几乎每一代皇帝都是同性恋者,如高祖的籍孺,惠帝的闳孺,文帝的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的周仁,昭帝的金赏,武帝的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的张彭祖,元帝的弘慕、石显,成帝的张放、淳于长,哀帝的董贤等,可谓书不胜书。到了南北朝时期,陈朝的美男韩子高,他深受皇帝的宠幸,虽无皇后之名却有皇后之实,被后世称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男皇后”。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皇帝如此,士大夫阶层则纷纷效法,非但不以为耻,反倒津津乐道,以为美谈。前文曾总结过中国古代的同性恋经历了由宫廷到官场再到民间的发展过程。明清时期,闽南一带产生了“契兄弟”的风俗,“男风”也因此有了“南风”的别称,一对契兄弟年纪大的叫“契兄”,年纪小的叫“契弟”。“契兄”到“契弟”的家时,其家人会像对待女婿一样款待。关系确定后,“契弟”日后的生计就成了“契兄”的责任,他们感情真挚,如同夫妻一样共同生活。根据明代沈德符《敝帚斋余谈》记载,福建的男风已经实现了契约化,得到道德风俗等方方面面的认可,甚至建立起被家族接纳的稳固家庭。清朝康熙年间还产生了最早出现的同性婚姻:“有通州渔户张二娶男子王四魁为妇,伉俪二十五年矣。”
(2)宗教势力薄弱。西方国家长期歧视甚至敌视直至迫害同性恋者,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很大原因是基督教的广泛传播。我国古代并没有浓重的宗教信仰情结,除了西汉末年产生的道教,其他诸如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都属于舶来品。同时,无论是本土的宗教,还是外来的宗教,其影响力都是有限的,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也不允许任何宗教的过分传播以动摇帝王的统治。总之,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宗教,却始终是世俗国家,而不是宗教国家。中国既不重视来世,也不向往天堂,而是尊重历史,关注当世,讲究实际,是一个几乎没有神权法的世俗社会。在这样的传统下,国家更强调个人操守与道德自律,而不是强加于人的外在法律规范,因而以一种大度与宽容的姿态对待同性恋。
(3)节欲的礼教文化。中国的礼教提倡节欲,特别是自宋代开始,程朱理学阐发“存天理灭人欲”、“万恶淫为首”、“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思想,并在统治者的推动下逐渐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然而,一方面礼教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是节欲,不是禁欲,正如荀子《礼论》中所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另一方面在男女大防的礼教约束下,出于人的生理心理需要自然地转向同性恋。此外,与中国人的生死观有密切联系。长期以来,中国人坚守好死不如赖活的信条,甚至想方设法地修炼成仙,孜孜不倦地追求长生不老,并认为男女之间贪欢纵情会有害于健康,甚至会损阳减寿。这就为同性恋提供了思想认识和价值理念上的依据。
(4)私法自治。与西方发达的私法文化不同,中国古代的法典基本上是刑法典,是“罪名之制”,相反,民法作为最重要的私法却始终没有制定出成文法典。然而,中国虽然没有国家制定的民法典,却不乏调整民事关系的民间法,或许中国的民间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法。正因为有民间法,所以国家刑律对于“钱田户婚”一类民间琐事细故,不仅规定简略,也比较宽松,而在实践中又采取民不告官不理的消极态度,州县官既不愿意也没有精力和条件去过多地干预民间生活。因此,大量民事纠纷不是通过官府依照国法处理,而是通过家法族规乡约以民间私法自治的方式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很少通过法律的方式规制同性恋,即便规制也远不如现代化以前的西方严厉。
三、不越雷池——同性恋的婚姻红线
尽管同性恋是源远流长的历史现象,而且中国古代对同性恋的态度一直比较宽容,然而却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同性婚姻。號称唯—“男皇后”的韩子高只有同性恋之实,没有同性婚之名,并且死后下场悲凉。闽南一带的契兄弟与其说是“同性婚姻”,不如是说同性伴侣,而且契兄与契弟最终往往会娶妻生子,各自组成家庭。而康熙年间最早的同性婚姻也不外是事实婚姻,而且纯是偶然的个案,并不是普遍性的法定婚姻,官府最终宣布无效并处以刑罚:“王抱义子养之,长为娶妇。妇归,语其父母,告官事乃发觉。解送刑部,问拟流徒。”在看似宽容的氛围里,同性恋本可以发展为同性婚,然而事实上却没有迈上同性婚的台阶,这是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考察对同性恋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婚姻观念和制度。
(一)同性恋的从属地位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毫无疑问也是基于人性、基于性爱、基于性爱者的个性,但并没有因此而发展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意识,也自然不会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争取实现这种权利,更不可能将这种权利上升为法律,从而建立起同性婚姻制度。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者同样娶妻生子,同样承担着传统文化所赋予的性别角色和家庭责任,因此对家庭伦理没有造成致命的冲击,或者说没有突破家庭伦理的红线。家庭伦理是同性恋的基本原则,这其实也表现了中国古代同性恋的本质。实际上,中国古代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同性恋”,所谓的“同性恋”只是婚姻家庭生活中一种无伤大雅的“佐料”或调节剂,始终处于从属地位,绝不能与婚姻平起平坐。正因为同性恋是婚姻家庭伦理的补充,并不威胁婚姻家庭伦理,所以古人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不视其为伤天害理的大罪。这里充分体现了经与权、严与宽、原则性与务实性相统一的智慧。因为务实性才使同性恋颇为盛行,但由于原则性,同性恋不可能发展成为建立在个人自由权利基础上的同性婚姻。
(二)同性恋不可逾越的婚姻红线
中国古代对婚姻的认识绝不同于今天,因此把今天的婚姻观套用到古代显然是不合适的。今天法律意义上的婚姻是一种契约关系,是一男一女合意以结为夫妻并终生共同生活为目的。然而儒家经典对婚姻的权威界定是:“婚姻者,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从这句最古老也是总结最到位的定义中可清楚看到,婚姻是手段,是夫妻双方不可推卸的义务,是连接男女双方两大家族的纽带,其根本目的在于传宗接代。中国古代婚姻首要任务是生育,而生育一是敬祖尽孝,二是壮大家族,使家族后继有人。所以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又因为无后是最大的不孝,所以他接着说:“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9]古代婚姻的目的、性质、功能、意义是根本性法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它决定了人人都必须结婚,而且人人都必须为繁衍后代而结婚,因而也都只能是异性为婚,进而也决定了同性恋不可能成为合法的婚姻。可以说,由于中国古代特定的婚姻价值观念和制度,所以不管对同性恋多么包容乃至宽容,也不管同性恋的历史多么悠久且盛行,都永远无法迈入合法婚姻的殿堂。只要有这种价值观和制度存在,同性恋就永远是同性恋,就一定被拒之于婚姻的大门之外。中国古代既包容同性恋,又厉行异性婚,决不允许同性恋升级为合法婚姻。对前者颇有灵活性、实用性、开放性,对后者则严防死守,绝不含糊、动摇、让步。这既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更蕴含着独特的思想价值观念。
对比中西方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颇有趣且极值得深思的现象:在中国,虽然包容同性恋,却彻底堵死了同性恋通向同性婚的道路;而在基督教世界,虽然视同性恋为邪恶而予以严惩,然而却柳暗花明,领先进入同性婚合法化的时代。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基督教文明里有个人、自由、平等的种子,只要这些种子发芽长大,同性婚就自然成了个人的自由选择;而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里无视个人的存在和意义,过于重视家庭、家族乃至家天下,奉行的是家族或伦理本位,恰恰缺少个人、自由、平等等基因。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