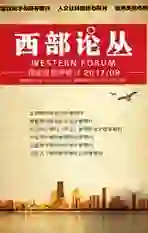继承法上特留份制度的法律问题研究
2017-12-27刘夏安
刘夏安
摘 要:特留份制度作为继承法上的一项制度,被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继承法所采用,但我国继承法上并无此项制度。我国《继承法》第19条规定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是必留份制度,与特留份制度存在差异,但很多时候在概念上常为人所混淆。本文从特留份的规范目的、历史变迁等角度对特留份制度作了梳理,并认为其制度仍然具有制度意义和活力,因此我国在编纂《民法典》时应当构建特留份制度。
关键词:特留份 必留份 历史变迁 规范目的
一、特留份与必留份规范目的不同
特留份,是指遗嘱人必须为特定的法定继承人预留的,不能借用遗嘱予以剥夺的份额。[1]特留份权是立法者在法定家庭继承和遗嘱自由之间作的一项妥协。被继承人可以经死因处分剥夺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但一般无法剥夺其特留份权,从而保障近亲属能在最低限度上分享遗产。关于特留份制度,仅从概念上难以看出其實质内涵,或者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表述表达其完全周延的内涵。若仅从概念上看,似乎我国《继承法》第19条规定的必留份制度也符合该概念的表述,必留份同样是遗嘱人必须为特定的法定继承人预留的,不能借用遗嘱予以剥夺的份额,甚至预留份制度也能统摄在这一概念下。
必留份制度在我国《继承法》体系上虽然被安排在“遗嘱继承和遗赠”这一章,但其规范目的是为了使得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能够获得一定的遗产以维持生活需求,其与《继承法》第14条酌情分得遗产权的规范目的有相似之处,都是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的一种照顾,只是前者适用的对象是继承人,后者适用的对象是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举轻以明重,连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都应当在继承遗产时得到照顾,继承人中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都应当在继承遗产时更应当得到不低于前者的照顾,但考虑到第19条条文文义是针对遗嘱作出的规范,在法定继承中应当采用类推适用的方式,类推适用第19条。之所以得以类推适用的原因是因为必留份制度是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一种照顾,给予其必要的遗产份额不会因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不同产生差别。而特留份制度则不然,特留份制度是建立在被继承人有完全的自由处分自己的遗产和对遗嘱的充分尊重的基础上的,这一制度特点在各国含有特留份制度的继承法中均有所体现,特留份制度和遗嘱继承制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被继承人无法通过或没有通过遗嘱继承的方式安排自己的遗产,则出于对被继承人遗嘱进行限制的特留份制度就失去了其制度价值和规范目的。
二、从对遗嘱进行限制的角度看特留份制度的历史变迁
(一)罗马法上的义务份
有学者认为罗马法中的“义务份”的起源是为了实现家庭中赡养老人和幼子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继承法上的必留份制度更贴近于罗马中的早期的“义务份”制度的规范目的,均有保障继承人中缺乏劳动能力且没有生活来源的老人和幼子的生活保障功能。罗马法上的继承制度以遗嘱继承为主,法定继承为辅,到查士丁尼一世时,正式形成了“遗嘱逆伦诉”,凡是不合情理的遗嘱,遗嘱人的近亲可以向法院提起“遗嘱逆伦诉”。可见随着罗马法中“义务份”制度的扩展,最初的有权利提起诉讼的人从被继承人的直系卑血亲或直系尊血亲扩展到了兄弟姐妹等近亲属,此时“义务份”制度承担的不仅仅是实现家庭中赡养老人和幼子的目的,它更多是因为遗嘱违反了遗嘱人对家庭和亲属的一种自然义务。因此应当看到,罗马法上的“义务份”制度存在一个衍变的过程,它的规范目的也存在漂移,不是一开始就是“特留份”制度的起源,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有了与特留份制度相近的内涵。
(二)日耳曼法上的期待份和对罗马法的继受
在日耳曼法中,同样有特留份制度的雏形。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日耳曼人没有遗嘱制度,只是在没有亲属继承的事后才能在生前指定他人为自己的继承人。[2]在遗嘱制度和“期待份”制度之前,日耳曼法有死者份制度,即死者生前所用的物品随死者埋葬或焚烧。随着天主教的影响,死者开始将其可以处分的财产捐助教会,因此死者分开始转变为“供养分”,即有供养教会之意。但此时的供养分仍然限于教士之中,随着这种方式的财产移转方法为世俗法所承认,日耳曼法上的遗嘱制度因而成形。[3]由此可见,日耳曼法上的遗嘱制度从无到有,有其自生之土壤。在所有法律制度中,继承法是最能体现民族特征的,因此作为继承法中的遗嘱制度,并非源自罗马法,而与遗嘱继承制度相伴而生,作为对遗嘱继承制度进行限制的特留份制度,即便罗马法上与日耳曼法上均有相似制度,也并非起源与更新的关系。
特留份制度在日耳曼法中最初出现,就表现出很强的对遗嘱的自由处分进行限制的基因,即被继承人只能将遗产中很小的一部分通过遗嘱的方式自由处分,而大部分财产要受到特留份制度的制约,由法定继承人继承。与其说特留份制度是对自由处分遗产的遗嘱制度的限定,不如说遗嘱制度是对限定处分遗产的日耳曼法继承制度的松绑。因为“团体主义”的日耳曼法中,一开始并没有继承制度,也没有自由处分遗产的基因。尔后,随着社会发展,遗嘱制度渐起,对财产的自由处分权限增多。随着文艺复兴之后,罗马法的兴起和伴随着日耳曼对罗马法的继受,意志自由的基因在法律制度中的增多,日耳曼法中合乎意思自由的遗嘱制度和和对遗嘱中的意思自由加以特留份制度也逐渐成型。可见相较于罗马法,日耳曼法中的“期待份”制度最初最多只能算“特留份”制度的雏形,真正作为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的“特留份”制度尚未成形,直到继受了罗马法“私法自治”的核心后,特留份制度才逐渐发展为今天的样子。
(三)德国和法国的特留份制度
1、德国民法中的特留份
德国法上,专以一章对特留份制度加以规范,包括特留份数额,解释规则,特留份的补足、限制、计算等规则。其中在遗赠的给予及其与特留份之间的关系上,给予特留份权利人以充分的自由选择请求特留份还是接受遗赠的受益。为了充分保障特留份权利人的权利,继承人承担有一定的法定义务,如确定义务、答复咨询义务等,以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对特留份权利,被继承人也可以在一定情况下对其进行限制。[4]
2、法国民法中的特留份
法国法上,对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限定较严,不仅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定,对被继承人通过生前赠与方式处分其财产的自由也加以限制,且被译成人可以自由的财产份额受到很大约束,被继承人不可以处分的财产部分即为特留份。其特留份份额保留较德国法上为多。法国法上对继承人的利益保护更为严格,可以通过生前赠与方式或遗嘱赠与的方式处分财产的份额被严格限制,在被继承人存有子女的情况下,可以自由處分的财产仅在一半甚至更少。
三、我国继承法上的特留份制度建构
从前述特留份制度的规范目的和历史变迁可以看到,我国《继承法》上第19条确定的必留份制度并非特留份制度,其与特留份制度的规范目的有所不同,也并非源自特留份制度的历史变迁,我国并无特留份制度,目下一些法条编纂中将该条列为特留份实为以讹传讹。既然我国并无特留份制度,值此民法典编纂之时,是否应当在继承编中移植特留份制度呢?就我国目前的《继承法》而论,对遗嘱自由的限制是非常少的,除了必留份制度、和预留份制度有所限制外,别无他限,且前述制度与特留份制度之规范目的有很大不同,由于遗嘱自由带来的一定伦理问题,法官审判时均只能借助于公序良俗原则裁判,使得遗嘱归于无效。但遗嘱全然无效,同样与被继承人之意志相违背,借用公序良俗原则裁判,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欧陆各国的特留份制度对解决上述继承法领域的伦理问题,践行优良的传统道德伦理,有很大裨益。
从欧陆立法例来看,特留份制度的存在有其客观作用,即保护家庭亲属利益。从罗马法上的“义务份”到日耳曼法上的“期待份”直至今日德法的特留份制度,尽管制度形式、规范各有不同,但是其中内涵同一,即限制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保证被继承人血亲的继承利益。所不同者,基于立法的出发点不同,对待遗嘱自由的态度各不相同,大抵为两种,一种是如罗马法上那般,以遗嘱继承为主,法定继承为辅,对遗嘱自由持宽容态度,对其限制较少,对被继承人的自由意愿尊重为先,以德国法为代表。一种是如日耳曼法上那般,遗嘱继承是对法定即成的松绑,对遗嘱自由持审慎态度对其限制较多,对继承人的利益保护为先,以法国法为代表。各国均各有民法典,特留份制度的具体规定或有不同,但其规范精神并没有超过这两者的藩篱。我国要继受特留份制度,应该以哪种制度模式为范本呢?从现行继承法的实践来看,我国对遗嘱即成自由度很高,民众于习惯上也更愿意接受以德国法为代表的特留份制度,且我国民法学说也多以继受德国法为主,故采德国法模式为好。
参考文献
[1] 宋宗宇、姜红利、王琳,《特留份制度及其在我国的法制构造》,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11期。
[2] 参见李宜琛著,《日耳曼法概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214页。
[3] 参见李宜琛著,《日耳曼法概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221页。
[4] 参见陈卫佐译,《德国民法典》(第四版),法律出版社年2015年版,第638-6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