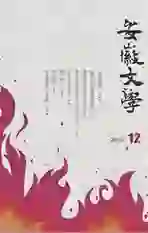赣水之城
2017-12-25詹文格
詹文格
一座被反复命名的城
面对遍地拆迁,众生奔跑的时代,我不知该如何去谈论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依然沉浸书斋,用一種呓语般的文字去赞叹歌吟,无疑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就如一个涂粉抹脂,眼神暧昧的女人,假扮清纯,那般忸怩作态的表情不合时宜。
当刀剑般的高楼将天空分解切割之后,我看到了铲土车、挖掘机、工程车的阴谋。曾经掘走的每一截砖头都是记忆,每一块瓦片都是历史,一场颠覆性的改造清空了城市的所有记忆,让大城小市一贫如洗。
纵观历史,与诸多城市一样,在大浪淘沙的时代更迭中,南昌也避免不了被反复更名的命运。“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从王勃闪光的序言里可以觉察到不变的定律。历朝历代,地名更改一直没有停止。南昌从秦代归属九江郡,汉朝豫章郡,灌婴平定豫章,设官置县,首立南昌县为豫章郡之附郭,取吉祥之意“昌大南疆”“南方昌盛”为县名。隋唐时期将豫章郡改为洪州,设总管府,唐朝中后期又先后改为都督府、江南西道。五代南唐中主李璟于交泰元年(公元959年)升洪州为南昌府,并于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将都城从建康迁往南昌,号“南都”。明代先后称南昌为洪都府、南昌府。民国初年立豫章道,1926年北伐之后设南昌市,1927年,一声枪响,使这个城市从此有了开天辟地,一鸣惊人的气象。
一些看似平常的事情,其实并不平常。每一次地名更改,称谓变化,都隐藏着强大的风暴。我们无法理解史上每一次更名的代价,因为面容枯瘦的历史删除了血腥的细节,所以胡适才把历史比拟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惜墨如金的史官摒弃了所有的修饰,把僵硬的文字刻写在冰冷的竹简里,保存在线装的古籍中。像我这类乡土的逃离者,在漂泊中哭泣,城市始终与我隔着遥远的距离。
掩藏在湘鄂赣三省边界的家乡,是一个豆粒般的圆点,在圆点的周围有南昌、长沙、武汉三个省会城市,这三个城市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从家乡出发,三个省会城市均在两百公里以上。这样的距离如同相互制衡的星座,像一个意志不坚的恋爱者,对三个城市都存在着欲说还休的感情。见过世面的乡邻,谈起长沙马王堆,橘子洲、岳麓山;武汉黄鹤楼,汉正街,六渡桥,眉飞色舞。说起湘鄂各地的风味小吃,更是令人馋涎欲滴,反而对于南昌语焉不详,少有提及。
一个城市的地理方位,决定了它的命运走向和功能地位,就像香港之于深圳,澳门之于珠海,唇齿相依,直接影响着两个城市的发育。学界认为,城市历史地理是人文历史地理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城市是地理实体。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城市的兴起、发展与变迁离不开地理环境,这是众所周知的。比如城址选择,必须考虑具体的地理特点,即傍河还是靠山,背原还是面水,环湖还是沿河,平地还是丘陵等。有些是以单一的地理特征为主,有些则是多种地理特点共同起作用。城址的选择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古人在选址建城时都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既要考虑其地理优势、山水优势,又要考虑交通优势。赣江之滨的南昌,地处鄱阳湖和长江,两江一湖的交汇地带,“襟三江而带五湖”,洪州与水相关。古人选址造城对水系都有远见思考。楼兰古城的消亡与水的流失应该有密切关系,并非选址不对,而是生态恶化,地理剧变,加之战争影响。
当年高速公路未建,京九铁路也尚未开通时,家乡如潮的务工者就是从邻省的长沙南下去往广东寻梦。南昌虽是管辖家乡的省城,但走近它的次数却十分有限,对这座城市我一直深感陌生。挨江靠湖的城市形成了特殊的气候,冬天江湖来风彻骨寒冷,夏天火炉一般闷热难耐,我至今留宿最长的只有三天。三天,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还描绘不清它的背影,但我在这三天中却感觉到了一种少有的透彻。
通行于司马庙立交,上下几层的车流,让我看到了上海某处街区的影子。其实建筑最能体现人心的物化与外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的个性正日益缺失,从局部到整体,似乎可以用一条街道来观照天下,拿一个小区来遍察世界。城市迷失了自我,消解了特色,模仿抄袭各种设计方案,克隆了众多的孪生兄弟。一幢高楼与另一幢高楼;一条街道与另一条街道;一个小区与另一个小区,它们除了外在不同的名称,相同或相似的东西实在太多,有的简直成了一道复制的程序,让你惊讶他乡就是故乡。公交车同样拥挤,等车的男女同样匆忙,咖啡屋,麦当劳里的食客依然不紧不慢,出入美容院的高傲女郎拒绝素面朝天。
在我见过无数种相似之后,渴望南昌这座被反复命名的城市能留下一点独特记忆……
一座色彩变幻的城
我站立于高楼之间,清晰地目睹赣江带着不少的沉重和凝滞向前流淌。也许是江水承载着这座城市以及城市之外的太多欲望,当年“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也是望见这样的一江流水吗?也是因这些江水而引发了如涌的文思?
赣江蒸腾起一片烟岚,飘浮在吃水很深的船只间,透过滩涂,传来嘈杂的市声,江的此岸与彼岸在对应中,一切又好像并不真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虚构还是写实?千百年来,对于滕王阁这座江南名楼来说,是滕王阁成就了王勃;还是王勃成就了这座名楼?这一点恐怕连那位山西才俊自己也未必能准确地道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跟今天电视广告中的名牌与名人效应颇为神似。
第一次以游人的身份走近重建的滕王阁,金碧辉煌,但不一定就能再现当年名楼的气魄和神韵。游人自然不是来重温历史的,而是来欣赏现代美景和风光的,不管风景背后包含着怎样的历史,在游人眼里都只是个普通的景点,除了用各式相机记载到此一游外,别的都无关紧要。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看来是动物间的通病,没有高级与低级之分。这一点倒让人想起长城,将那些古老的秦砖刻得遍体鳞伤的赵钱孙李之名,游人用力雕刻上自己某年某月到此一游,天南地北的游人都有这浅薄的想法,妄想把这一刻变成永恒。
《滕王阁序》的骨子里无法排除恭维与吹捧的成分,算是一篇传世的应景之作,它与《兰亭集序》《岳阳楼记》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线。王勃的过人才华竟被自己无意间给蒙蔽了。
毫无疑问,在那种场合,才华横溢的王勃,一定会把洪都新府描绘得金光四射,耀目辉煌。
游完名楼,心中没有太多的感觉,而当我购买门票進入青云谱八大山人纪念馆时,胸腔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感慨。近年不知有无改变,反正前些年滕王阁的门票要比青云谱贵一倍。文化与文化之间竟然有如此惊人的差异,使人想到传统与时尚,通俗与高雅的最终归宿。市场经济让我们看清了热闹与华丽的显赫价值,体悟到了孤寂与清贫的本质和成因,看来文人的困惑在久远的历史时空中早已有之,所谓的历史就是当下史。
手上捏着面值不同的门票,我不好轻易地拿滕王阁与青云谱作肤浅对比,只是思绪被一位奇人牵引,他就是皇室后裔——朱耷。这位八大山人,应该是这座城市的骄傲。他是明末清初画坛上的一位旷世奇才,他身为贵族,在中国写意花鸟画上用平民化的眼光开辟了一代先河,承前启后,无可阻挡,影响画坛数百年。
明崇祯十七年(1664),清兵攻占京城,推翻了明王朝。此时的朱耷只有十九岁,生活的急剧变化,使他体味到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巨大落差。国破家亡,清廷追杀,于是他隐姓埋名,遁入空门,装聋作哑。
后来在青云谱修筑道院,他历经坎坷,性格倔强奇傲,一生扮演着悲剧角色。甲申之变彻底改变了八大山人的命运,清初的八旗劲旅能征善战,当权者用刚柔并进的统治手段,招降纳叛,逐个击破,明王朝复国已毫无指望。一个落魄王孙,能否借用佛家空与无的教义来稀释蓄积于心的痛楚?但空门的因果轮回无法取代孔孟的纲常伦理,八大山人只好在他的诗画中长歌当哭。
他平日大书一“哑”字置于门上,从不与人开言,也不再与任何权贵往来。数年后,有一个叫邵长蘅的文人,拄杖冒雨进山,寻访山人。空山古寺,风掀起阵阵林涛,两人正面对坐,不交一言,只在书桌上以纸笔相问对答,直至午夜。就是这次奇特的对话,让人们走进了八大山人的内心世界。他闭上嘴不向人发言,是为了寻找另一种表达自己内心的方式;他向喧嚣浑浊的世界闭上眼睛,用心的感应与尘世以外的无限事物交流。山人画鸟多独立,白眼朝上,写字苍茫高古,超尘脱俗,而落款则把八大山人四字书写成哭泣之状,墨点无多泪点多。在那样的时代,支撑他信念与生命的东西本身就是个谜,他的艺术也像断线的风筝,是精神漂泊与生命苦旅的最后结晶。在八大山人的眼里,天地是灰色的。
走出屋外,我感觉自己在剧烈喘息,一阵旋风吹来,卷起地上一只黑色垃圾袋,就像山人画中一叶残荷,渐渐漂离了我的视线。
无论是在过去和现在,一个人想真正读懂另一个人,那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情,何况是一个紧扣心扉的人。正如一处景观与另一处景观无法比较,风景亦和人一样,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个性、内涵、遭际与命运……
乘车回城,远远看到那个塔尖,古矛一样刺向天空。那是一座名为绳金的古塔,很多年前就在农历通书上见过这个地名。它立于古城进贤门外,始建于唐天祐年间(公元904~907年),相传建塔前异僧惟一掘地得铁函一只,内有金绳四匝,古剑三把(分别刻有“驱风”“镇火”“除蛟”字样),还有金瓶一只,盛有舍利子三百粒,绳金塔因此而得名。传说可以丰富景点内涵,拥有历史的城市,不仅有华丽的外衣,还有绵密的羽毛。
当旅游成为产业的时候,所有的城市景点都被连接贯通。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访的古迹,很多远道而来的游客都想一睹王侯的墓葬。2011年3月被发现的海昏侯墓,经专家考古发掘,2016年3月2日最终确定墓主为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成为目前我国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等级墓葬,并入选201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南昌海昏侯墓已出土万余件(套)珍贵文物,仅金器就有478件,重量超过78公斤。其中大小两种马蹄金33枚,麟趾金15枚,分别刻有“上”“中”“下”三种文字。通过对这些铭文的考释,将楷书的产生时间推到西汉,使研究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梳理中国书法史、中华文明史。可见从考古中推断的历史,永远不会终结。
时光从古迹中穿过,投下巨大的影子,城市的背面一片荒芜。走马观花者,看过南昌的古迹之后,应该用心去关注一下英雄城的历史。这片血色浸染的土地,注定成为一座红色的城市,朱红成为它的底色和基调。1927年8月1日,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一座城市立起了建军大业的理想,南昌由此以“英雄城”而驰名天下。在城市的中心人民广场南端,矗立着一座45.5米的长方体,那就是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塔身由“宣布起义”“攻打敌营”“欢呼胜利”三幅大型花岗岩浮雕组成,再现了当年枪林弹雨的场景。为纪念这个历史性的一幕,1957年在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上建成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作为起义的指挥中心,陈列着大量有关起义的文献资料、照片、图表、绘画和文物。
历史已经走远,遗迹归于安静,纵情于物质之上的享乐主义,推动着汹涌的人流奔向另一个方向。长久的和平让人们忘记了苦难与艰险,城市已沉迷在亮丽炫目的光环中。出入此地,人们大都浮光掠影地只看到表面的水花,而忽略了沉淀在时光深处的事物。当四季轮回,色彩变换的时候,有人会记起,这里曾传递过怎样的理想誓言!
面对未来,这座英雄的城市不断变幻色彩,显现了不同的时代历史和生命轨迹。在万物葱茏的季节,我看到南昌满城的苍翠,那种清新的色彩,包含了匡庐云雾,井冈翠竹,瓷都窑火,赣南杜鹃……
一座延伸的城
一座城与另一座城,在时间与空间中能完成内在的对接。当功能齐全的红谷滩新区建成后,南昌的城市规模迅速扩大,跨越赣江的几座大桥,像主动脉,日夜不停地奔腾。每当从省城退回家乡,我就会细心去比较或者寻找,大城与小城究竟存在怎样的差异。我固执地认为,乡村是城市的祖宗,解读城市应该从乡村开始,因为是乡村的存在才衍生了市井,建立了城门,萌生了交易,出现了算计。
从泉水到溪流,溪流到小河,小河到大河,这是大海的孕育过程。同样从乡村到小镇,小镇到县城,县城到省城,这是城乡的认知过程。一座包罗万象的城市,不应该千人一面,它的丰富与复杂应该就像《哈姆雷特》,千人阅读,千种答案。官人看见政治与权力;商贾看见竞争或买卖;民工看见建筑和工地;学生看见校舍与教育;食客看见酒肆与饭局……
这些年,城市留下的只是模糊的脸庞,比起沾满露水的菜地,满园乱飞的鸡鸭,垛满禾草的乡村要乏味得多。
别看这小城山重水复,它也学会了模仿,从遥远的时代就与南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而小城却是秋收起义的策源地,近代革命史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并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三大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秋收起义部队在修水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在这里设计制作出第一面绣有镰刀锤子的军旗。
可惜乡村太过闭塞,直到进城读书之后,我才知道一些或远或近的历史。家乡在北宋时期就出过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所以从那时起我就认定,知识、智慧、权力和欲望都是生长在城里的东西……
黄庭坚乃江西诗派始祖,而南山崖则是他读书思考的地方。一座瘦削的孤崖,古木参天,藤萝蔓延;崖下河水翻滚,舟楫往来。站在山顶眺望,楼台街巷,尽收眼底。那个读书少年竟然选中了宝地。他聪颖过人,早在七岁时就显露了过人天赋。少年老成的诗人,不经意间吟出千古绝唱:“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如今,已近千年,往来的都是平庸的游人过客,他们把南崖、双井和省城南昌的景点,用一根线条连接起来,人们不再借助缓慢的舟船官轿,而是乘坐风驰电掣的汽车。
逆流而上,只是眨眼工夫,明月湾头就张开了怀抱,这个名为双井的古村,就是诗人故里。在这个黄姓的村落里,读书出仕,早成风气,仅宋代就出了48名进士,被誉为“华夏进士第一村”。
接下来还有名声遐迩的桃里竹段陈家老屋。这个培养了陈门五杰的家族(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像一团耀目的星群,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响。然而对于這个家族来说,南昌西山是他们永世的疼痛,在资讯泛滥的年代,无需赘述,熟悉那段历史的人,自会知道个中原因……
翻开地方史志,看源远流长的历史该如何延续,记忆该怎样留存?当下的城市规划者,以为现代化的水泥、钢筋是无坚不摧、无所不能的物质,其实在时光的较量中,钢铁战胜不了陶土,权力遮蔽不了文化。
从县城往东南行驶36公里,那里有一处新石器时期遗址,称为山背文化,距今大约有4300年历史。那些磨光的鼎、鬶、豆、簋、壶、罐、钵,沙灰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和黑皮陶,被制作成扁平、圆锥和羊角的造型,留下了远古时期的无限想象。而距离其二百公里的南昌莲塘,亦有多处新石器时期遗址,这样的历史交汇与重叠并非无意中的巧合,而是一座城市经济文化的辐射,一种精神传递或远游,它留下了延伸迁移的轨迹,留下了繁荣昌盛的记忆。
责任编辑 李琪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