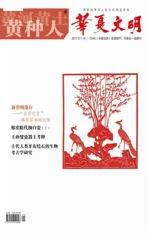论“西泠精神”的核心价值及时代特质
2017-12-25陈博君周斌
□陈博君 周斌
论“西泠精神”的核心价值及时代特质
□陈博君 周斌
西泠印社是闻名海内外的著名印学社团,是中国研究金石篆刻的一个百年传统学术团体,至今已有111年的光辉历史。西泠印社的创立与发展,对继承和弘扬篆刻这一国粹艺术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因而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金石篆刻艺术领域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天下第一名社”。
如今,当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回望这一传统印学社团的发展历程的时候,我们不仅骄傲地看到了西泠印社对篆刻艺术的巨大影响力,而且还真切地感受到了蕴含在这个百年印学社团肌体里的一股强劲的精神力量。这股精神力量由“爱”发端,呈现出无比开放的时代特质,并且凝聚成一个完整的精神体系——“西泠精神”。因此,对“西泠精神”的传统核心价值和时代发展特质进行必要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这一特殊精神力量的实质内涵,更好地继承和弘扬“西泠精神”的优良传统,同时,对其他传统社团的建设与发展,也都具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西泠精神的传统核心价值
所谓核心价值,就是一个组织拥有的区别于其他组织的、不可替代的、最基本最持久的那部分组织特质。纵观西泠印社的创立和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核心价值就在于西泠印社的同人乃至热爱和支持这一艺术社团发展的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都有着非常坚定而执着的共同理想,这个理想就是矢志振兴和弘扬篆刻这一国粹艺术;都有着强烈而浓郁的民族情怀,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勇于担当;都有着为了印社发展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印社的大爱。概言之,就是对艺术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印社的热爱。这些源自“爱”的精神品质,成为西泠精神的传统核心价值所在。
1.爱艺:执着坚定的共同理想。西泠印社作为一个研究金石篆刻的学术团体,其最初的萌发和诞生,就是源自一群年轻人为了追求共同的艺术理想而做出的不懈努力。晚清时期,八千卷楼楼主丁丙在孤山西侧移建数峰阁,吸引了当时杭州的文人墨客前来参加探讨艺术的聚会。此风后被丁仁、叶铭、王禔、吴隐等几位对金石篆刻有着共同爱好的年轻人传承发扬,他们在孤山之地频频聚会交流、研讨印学。20世纪初,受西方文化冲击,我国传统文化走向衰微,篆刻也江河日下。这些有着远大理想的年轻人在切磋技艺的同时,又忧心于印学之将湮没,便萌生了创立印社的想法。为继承和弘扬这一中华国粹,这群年轻人于1904年提议结社,提出了“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明确宗旨[1],并各出私产,聚资在数峰阁旁买地,并联系了更多有着共同理想的印人出资出力营建印社,由此开始了一段执着而坚定的篆刻艺术振兴道路。
为了实现振兴篆刻这一崇高的艺术理想,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间,西泠印社的历代同人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支撑着西泠印社走过无数条坎坷的道路,最终发展壮大成为百年名社。譬如,1937年11月,侵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丁仁、叶铭和王禔三位印社创始人在离杭避居上海时,仍不忘对印社的保护,一方面委托叶秋生一家留社看护,另一方面竭力凑集生活费托人带往杭州。叶秋生一家也恪尽职守,尽最大的努力封山门护印社,使印社在日寇横行的危难时期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印社的其他骨干成员王个簃、叶璐渊、张鲁盫、黄宾虹、张大千、朱屺瞻、钱君匋、傅抱石、诸乐三、商承祚、沙孟海、高式熊、张宗祥等,也都在抗战的逆境中不断发奋,为振兴国学而不懈努力。又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印社遭遇冲击,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之时,印社的员工们自发组织起来护社,他们在杭州书画社的门市部里撕毁一些无价值的字画,以表明其主动破四旧的态度,避免了外来造反派进库房毁损文物的行为。员工们还将印社中有价值的碑刻卸下转移到室内保存,不能转移的碑刻就用石灰涂抹覆盖,并且在存放有珍贵文物的汉三老石室大门上张贴主席画像和语录,终于使印社的文物躲过了那场浩劫,幸运地得以保存。
2.爱国:勇于担当的民族情怀。西泠印社虽只是一个研究金石篆刻的学术团体,但这个社团的每一位成员都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怀和浓厚的爱国热情,当祖国和民族的利益遭遇危险的时候,他们不是袖手旁观、宅室究艺,而是纷纷挺身而出,勇于为祖国、为民族分忧和担当。印社创立之时,正值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对我国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宝藏进行着疯狂掠夺,在此危难关头他们明确提出“保存金石”的建社宗旨,正是忧国忧民的印人们针对时弊发出的呐喊,他们用行动向世人宣示了中国文人对祖国、对民族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
在西泠印社的孤山社址,有一座非常独特的全石建筑汉三老石室,里面珍藏着的一块距今已有1900多年历史的 “三老讳字忌日碑”,它见证了西泠印社同人们强烈的爱国爱乡的民族情怀。这是浙江出土的唯一的一块东汉刻石,被誉为 “浙东第一石”。1921年秋天,这块碑石从浙江余姚辗转流入上海市场,被丹徒陈渭亭购得。洋人获悉此事后垂涎不已,欲以重金将此石买走并运往国外。沈宝昌、姚煜等浙籍文人获悉后,立即联系西泠印社。吴昌硕、丁仁等迅速行动,联合浙江同乡四处奔走,发起募赎石碑的活动,得到了印社内外人士的积极响应,最后以8000块大洋的高价将碑赎回,运至西泠印社,并专门修建石室永久珍藏,使这一价值连城的国宝得到了最好的保护[2]。
西泠印社的社员们虽然都是身怀传统技艺的文人,但在面临国难之际,他们有气节、勇于担当,呈现给大家的却是一副副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抗日战争期间,身在上海暂避战乱的丁仁为了保护珍贵的印学历史资料,专门让儿子冒着危险潜回杭州,抢救出了大部分西泠八家印章,并将这些珍贵的印章编印成《西泠八家印选》。另一位印社创始人王禔,则以“历劫不磨”为题专门篆刻了一方印章,并且编印《丁丑劫余印存》,以示劫难中的坚韧不拔。还有一位印社的骨干方介堪,为避战乱回到老家温州后,因篆艺精湛竟引来了日伪的注意,伪军带着日军的要求前来求印,他断然拒绝了日伪的要求。宁愿忍受战乱、沦陷之苦,也绝不向侵略者及卖国卖乡的汉奸走狗低头妥协,西泠印人的民族气节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3.爱社: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西泠印社的创立乃至发展,都离不开印社同人们的无私奉献。在创社之初,一大批早期社员和赞助社友都为印社的诞生付出了努力、贡献了财物,尤其是四位创始人,更是大公无私,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印社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丁仁醉心于金石,继承祖风,将数峰阁等祖业辟为印人聚会研讨金石篆刻的公共场所,且斥资修建鹤庐,永为社产,不私所有。又如吴隐,经常捐资协助印社建设,并于1915年修建遁庵、筑味印亭,且导渠为池成潜泉,并将属地及房屋全部交给印社,规定子孙只能在此祭拜祖先,平时皆归印社使用。
印社同人们这种热衷公益、公而忘私的精神,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印社刚立,新成立的民国政府答应归还部分地产给洋务运动家盛怀宣,其中包括孤山西麓大片地产。盛家欲在此建祠堂,发现宝山印房、山川雨露图书室等建筑已侵入其地盘,于是提起诉讼。后来,盛怀宣得知西泠印社不是营私,而是为了有潜心学问的固定场所,每笔开支都记录、公开,竟为印社的文人情怀所感动,亲自干预并将地产捐赠给西泠印社[3]。1911年,湘阴李庸奉父命将小盘谷捐给西泠印社,吴兴张均衡又捐资建闲泉;1915年冬,常州天宁寺冶开法师向西泠印社捐赠“金砖”……
此后,这种为了印社的发展而不惜奉献的精神得到了大力弘扬,并且从最初的捐地建社,逐渐转向了捐献珍贵藏品。1957年,西泠印社筹建“吴昌硕纪念室”,吴昌硕后人吴东迈捐出缶翁金石书画作品及相关资料数十件,其孙吴长邺也捐献缶翁常用田黄印章及其他书画文物数十件。1960年,社员高络园首献铜印500方、晋铜鼓2只、汉晋纪年砖300余块。1962年,张同泰掌门人张鲁盫的后人捐出望云草堂明清印谱493部和1500余方战国、两汉和明清印章;同年,71岁的平湖社员葛昌楹捐献明清印章43枚,其中不乏文彭的 “琴罢倚松玩鹤”、何震的“听鹂深处”、邓石如的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等印林瑰宝。此后,王禔、王个簃、陈叔通、钱镜塘、吴振平、张宗祥、沈尹默、杨鲁安、刘创新、戚叔玉、丁利年等众多的印社同人或印人的家属后人,均先后向西泠印社捐献了大批珍贵的文物藏品,为西泠印社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西泠精神的时代发展特质
如果说,西泠精神是一个完整的精神体系,是一个系统的精神宝库,那么除了“爱艺、爱国、爱社”这三大传统的核心价值外,西泠精神显然还包括了其他一些精神特质,如谨而不拘的学术态度、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不断创新的发展意识。这些 “开明、开放、开拓”的精神特质,是西泠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历经了百年发展之后,这种开放精神已成为西泠印社独特的时代发展特质。
1.开明:谨而不拘的学术态度。西泠印社在《社约》中开宗明义地阐明了“本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的观点,充分表明了印社同人们在中国印学研究方面的信心和决心。与其他很多学术团体不同的是,西泠印社在学术方面不仅继承了传统朴学严谨细致的作风,更具备了一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明胸襟和气度。正如胡宗成的 《西泠印社记》所言:“汇流穷源,无门户之派见;鉴今索古,开后启之先声。”[4]
西泠印社地处浙江杭州,在印社成立之初,创始人丁仁、叶铭、王禔、吴隐等人的治印风格都有着十分明显的浙派特征,但是他们并未以一地一艺自囿,而是对各种风格流派的篆刻艺术一视同仁。在西泠印社的孤山社址,同时矗立着浙派篆刻鼻祖丁敬和皖派篆刻鼻祖邓石如的石雕立像;在印社仰贤亭的壁上,亦同时嵌刻着28位不同流派的印人先贤像,这些都充分显示了西泠印社以传承印学为重、不存门户之见,严谨而不拘泥的学术态度。
艺术是相通的,相互之间的学习与交融非常重要。西泠印社虽是印学团体,但并没有将自己的学术范围框死在金石篆刻艺术一艺,而是“兼及书画”,将书画、鉴赏、考古、诗词、文字等诸多与篆刻相关的领域的顶级人才尽力吸纳过来,以他们的艺术修为来滋养和润泽金石篆刻艺术。印社在竭力收藏金石作品的同时,广泛收集其他艺术门类的珍品,从中发现和提炼艺术精华,丰富印学思想,充实印社内涵。
2.开放: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西泠印社虽然是以弘扬国粹艺术为己任的传统学术团体,却有着非常开放的心态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不仅在艺术上非常开明地兼收各家各派所长,在印社的组织建设和发展上也体现出了极具包容的开放姿态。
印社社长是团体组织的核心人物,西泠印社在社长的推选中,一直保持了一种大气开放的姿态。印社创立的时候,正是浙派篆刻声名最为显赫的时期,而直接诞生于浙派篆刻的西泠印社却敢于打破门第观念,推举吴昌硕为第一任社长。吴昌硕虽为浙人,曾初学浙派,但其后自创出雄浑厚重的一派印风,与浙派风格大相径庭。而当时的社员们却能明大势、识大体,共推当时在金石书画界极富影响力的吴昌硕先生来统帅印社,这种博大的胸怀实乃大气开放的表现。1992年,当西泠印社的第四任社长沙孟海辞世后,这个社团进一步打破社长必须是浙籍人的无形约束,将赵朴初推选为第五任社长。这位非浙江籍社长的诞生,标志着西泠印社的影响力进一步从浙江走向全国,呈现出更加大气、包容的发展态势。2011年,久居香港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当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这一开放的社团以更加博大的胸怀,走上了新的振兴之路。
吸收海外社员,是西泠印社大气开放的另一个表现。印社成立伊始,不仅凝聚了国内众多文人志士,甚至还吸引了日本的河井仙郎和长尾甲慕名前来申请入社。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西泠印社更是迈上了面向国际吸收会员的发展道路。相继吸纳了日本的小林斗盦、梅舒适和韩国的金赝显之后,又有一批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美国、加拿大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印人被吸收入社,基本囊括了海内外篆刻界的中坚力量。
3.开拓:不断创新的发展意识。西泠印社是一个开放的社团,更是一个发展的社团,在其一百多年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发展意识。这是印社得以在全国乃至世界众多艺术社团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西泠印社成立之前,篆刻是依附于书法和绘画而存在的,并没有自己独立的艺术地位。印社的创始人极具开拓意识,他们把篆刻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专门提出了“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响亮口号。这种不因循守旧、敢于创新的思维模式,为中国的篆刻艺术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成为中国文人在艺术道路上勇于开拓创新的楷模。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西泠印社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了空前的壮大。但是印社同人们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以更加崭新的思维,继续不断创新发展模式,使西泠印社跨上了与时代同步的快速发展轨道。1999年建成并正式开放的中国印学博物馆,正是西泠印社审时度势、跨越发展的产物。博物馆集文献收藏、文物展示、学术交流于一体,向人们系统地展示印学发展史及中国的印文化,为印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推动中国印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03年,西泠印社对自身的体制机制进行大胆的改革与创新,同步推进了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整体改革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转企改制,为印社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04年,西泠印社导入市场机制,成立了拥有国家第一类文物拍卖经营资质的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秉持着“真乃居先,诚为业本”的从业精神,通过定期举办春季、秋季大型拍卖会及特别专场,不断发掘艺术品的深层价值,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拍卖活动之一。自2004年起,西泠印社又在社员发展中引入极具时代感的海选方式,面向全国乃至全球采用“无门槛”的方式公开选拔新社员,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5]。
三、西泠精神对传统社团建设发展的启示
以“爱艺、爱国、爱社”为传统核心价值和以“开明、开放、开拓”为时代发展特质的“西泠精神”,不仅是西泠印社历经风雨坎坷、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更为其他传统民间学术社团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1.要高瞻远瞩,传统社团眼界高才能有大发展。西泠印社的创立,尽管最初源自几位志同道合、热爱金石篆刻艺术的年轻人的艺术追求,但是这些年轻人并没有单纯地把交流心得、切磋技艺作为成立印社的最终目的,而是站在一个保护和弘扬国粹艺术的高度,发出了“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响亮呼声,从而赋予了西泠印社重大的历史使命,使得这个初生的印学社团“出手不凡”,诞生伊始便拥有了有别于其他一般学术团体的“气质”。四位创社元老,为了表达这种崇高的追求和理想,默默付出,无私奉献,却相约不当社长,一致同意推选更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来担任,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坚持不懈,直到建社十年之后,方才推选出第一任社长吴昌硕。也正因为有了这种高瞻远瞩的发展眼光,西泠印社在正式成立之初就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管理规范,他们刻制社员名、制定社团章程,甚至把印社的每一笔捐款和开支悉数记录在案,以供核查。他们还以社约的方式,将社团的雅集活动明文规定下来:“本社以清初黄山诸家及西泠八家为最备,同人各有所藏,兹合议于每年春秋时分别陈列社中,以资眼福,而助清兴。”并且约定:“本社同人集会之时,各携所藏。凡吉金乐石、法书、名画、雕刻、匋冶、图籍、文玩皆属之。”“本社收藏各印,均分门别类,附拓边款,精印成谱,如有同好者,尽可到社索阅,获观摩之益。”[6]传统社团应摒弃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和地域门派为重的陈腐观念,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统筹谋划社团的建设。唯此,才能取得稳健而快速的发展。
2.要独善其身,传统社团必须保持艺术上的独立性。艺术家不能人云亦云、跟风造作,必须独善其身,独立思考,保持艺术上的独立性。只有如此,方能真正创造出具有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艺术作品。传统艺术社团同样需要拥有独立的艺术观,并凭此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艺术之林大显身手、有所作为。西泠印社对中国篆刻艺术的一大贡献,就是将篆刻从传统的依附于书法绘画艺术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而这一创举,正是得益于印社同人们拥有了独立的艺术观。关于印艺,宋代的米芾,元代的赵孟頫、吾丘衍,明代的文彭、何震等,都提出过不少独到的印论见解,但他们都仅限于个人的艺术感悟,并没有上升到印学研究的高度。而西泠印社的发起者和创始人,却没有被传统思维完全困囿,他们在大力传承先祖先辈优秀的篆刻艺术的同时,独立思考、积极探索,大胆地提出了富有自我见解的印学艺术观,从而使“保存金石、研究印学”成为了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主观艺术实践行为。这是西泠印社取得成功的一大因素。传统艺术社团只有像西泠印社这样,拥有自己独立的艺术观,才能在艺术上取得重大突破,进而为自身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和更高的地位。
3.要审时度势,传统社团善于借力才能不断壮大。有些传统社团认为,自身要保持艺术上的独立性,不能成为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社会力量,尤其是涉及经济利益组织的“合作者”。其实,艺术上的独立与其他方面的合作并不矛盾,民间社团既然存在于社会之中,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超脱者,只要处理得当,传统社团不仅不会因与其他组织合作而丧失自我,反而会由此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动力。事实上,在西泠印社的百年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印社与政府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常良好的互动关系。1905年,在丁仁、叶铭、王禔、吴隐等发起成立西泠印社的第二年,他们就联合了很多在杭爱好金石的同人们给官府写呈文,要求置地建社,并且获得了批准。1912年2月,民国政府颁布法令收回所有属于清政府的公产,西泠印社位列其中,情急之下,丁仁、王禔等将身为社员的辛亥革命烈士底奇峰的遗像供奉于社内,使西泠印社成了革命先烈的专祠,从而巧妙地保住了印社的产业。1927年,宋美龄游杭,建议把孤山改为中山公园,为了保住西泠印社的社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理事马衡的支持下,印社采取增挂“古物保管委员会浙江分会”牌子的办法,成功地自我保护。新中国成立之初,病榻中的丁仁嘱咐王禔将印社交给共产党,正是这一英明的决策,为西泠印社带来了新的发展曙光[7]。改革开放后,西泠印社更是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善于审时度势,借助政府等其他社会组织的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自我。西泠印社的经验值得民间社团学习和借鉴。
4.要与时俱进,传统社团才能永葆发展活力。西泠印社是一个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己任的传统学术团体,但是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个社团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印学研究上,他们一直紧跟时代的发展,不断地与时俱进。在创社初期,印社就积极借鉴西方的展览模式,通过不断充实雅集的内涵,使之成为分门别类、陈列雅藏、以资眼福的作品展览,从而开了篆刻作品展览之先河。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之后,西泠印社都一次次挺身而出,担负起对外交流的重任,不仅将中国的篆刻艺术推向了世界,也由此架起了中外友谊的桥梁。1985年,印社面对亟待振兴的篆刻文化,创办了社报《西泠艺报》,从而开辟了印学文化交流的新阵地。同时,印社还连续举办了全国乃至世界篆刻作品展评活动,以及多次“印学讨论会”,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印学研究的发展。2003年,印社实行体制改革,成立了社委会,机构升格后,印社不仅实力大增,还首次提出 “印文化”概念,召开印社产业发展新闻发布会,连续举办博览会,成立拍卖公司,西泠印社由此走上了一条更为宽广的发展道路。2009年10月,经过印社全体同人和社会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以西泠印社为主要申报单位和传承代表组织的“中国篆刻”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通过,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泠印社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传统社团才能永葆活力。
[1]陈振濂主编:《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3年。
[2]魏皓奔主编:《西泠印社》,杭州出版社,2005年。
[3]杨光繁:《核心价值的形成及清晰》,同心动力文库。
[4]刘 江:《弘扬西泠印社精神——纪念西泠印社创立九十五周年》,《西泠艺报》第152、153期。
[5]孙晓泉:《西泠情愫》,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
[6]林乾良:《西泠群星》,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年。
[7]王佩智:《回望西泠六十年(1949-2009)》,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
(作者单位 中国湿地博物馆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孟昭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