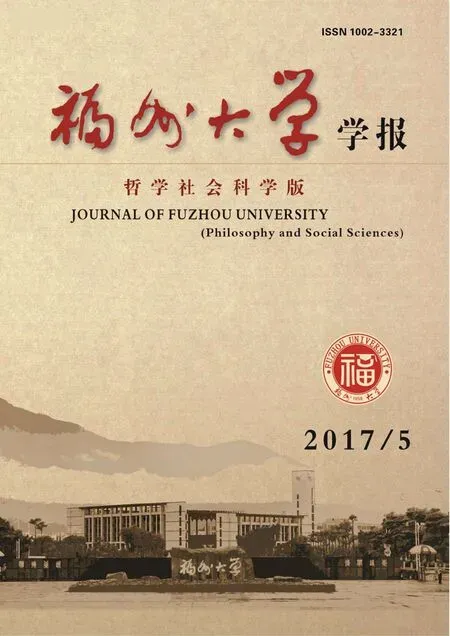行业跨越对中国跨境投资企业的创新能力影响研究
2017-12-20郑云坚
郑云坚 赵 淼
(1. 闽江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2. 国家开发银行, 北京 100031)
行业跨越对中国跨境投资企业的创新能力影响研究
郑云坚1赵 淼2
(1. 闽江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2. 国家开发银行, 北京 100031)
立足于国际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使用数据挖掘手段构筑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行业跨越经验相关数据库,利用面板数据系统两步法广义矩估计模型对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行业跨越经验的影响、调节条件和理论依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行业跨越所带来的相关经验能够对企业创新绩效带来显著的影响。成长期企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会获得更多的商业、政策支持。政府应当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据市场规则跨国、跨行业投资,提升其创新能力水平;同时,也应当主动提供行业跨越相关的信息技术支持,警示过快、过于分散的跨行业投资企业可能面临要素资源支撑不足的风险。对于企业而言,在海外投资中不但需要注意培育自身跨行业学习能力,也要注重增强其基础性的资金、技术、人力和管理保障能力,使对外投资过程中的创新能力始终处于正向增强状态。
对外投资; 创新能力; 行业跨越; 制度跨越
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出三大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为了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战略计划,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以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扶植等,这就对学术界研究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中产业跨越的创新绩效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
某一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揭示了各产业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数量关系,也能够体现不同行业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的差异。由于产业关联分析能够基于投入产出表,从数量上分析产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尤其是详细探究产业间的单向与多向联系、顺向与逆向联系、直接与间接联系,因此其分析结果对于政府制定政策和企业进行投资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不论境内或者境外跨行业投资,企业行业跨度策略研究都对企业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一些企业如首钢集团的国际投资业务广泛分布于地产、食品、健康和互联网等领域,虽与原有主营业务行业跨度巨大,但通过创新取得了业绩的提升;也有一些企业倾向于立足本行业和近似行业发展投资业务,如奇瑞汽车,主要的国际投资业务集中于汽车制造、新材料等近似行业,业绩不俗。当然失败的案例也不少。企业投资行为中的行业跨度决定了企业跨行业吸收、学习其他行业的知识水平和创建独特的资源基础的能力,有利于企业在供给环节中提供高质量、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对于实现供给侧创新具有决定性意义。
因而,不论从理论构建还是实践需求方面,都有必要根据最新的企业对外投资行业数据并利用动态广义矩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发现行业跨越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并且对上述影响的边界条件即相关经济变量的调节作用进行研究。
一、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在管理学领域,企业对外投资所带来的正向和逆向创新水平和企业业绩溢出效应受到了学者广泛的关注。不论外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还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都会带来知识传递和技术、资金、管理能力的显著溢出,并且最终有利于所在国或者投资企业的创新能力水平建设和业绩增长。[1][2]对于企业对外投资的知识溢出影响,学者首先关注的是对外投资行为对投资目的地国家相关企业和社会整体的技术和知识溢出作用。[3]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经济学研究成果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相关行业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4]在相关中国地区行业技术、知识能力、基础设施和制度条件的配合下,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很好地提升当地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和企业业绩。[5]另外,理论界也将研究视角投向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所带来的“逆向知识溢出”对企业自身和所处行业、区域的创新、业绩等影响。[6]李梅和金照林利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发现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对发达地区存在明显的技术推动作用而对欠发达地区投资带来的影响并不显著。[7]除了从宏观政策视角考察企业投资尤其是企业研发投资对于其他行业的带动性影响,从而识别对于国民经济起到关键带动性的产业,还可以从微观企业视角探究企业自身在进行多元化选择时产业间距离对于多元化有效性的影响,为企业多元化过程中的行业选择提供指导建议。[8]
理论界对企业对外投资的行业跨度策略有着相互矛盾的解释。有的学者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认为企业依据本行业特点所具有的各类资源能够很容易地适用于本行业或者近似行业的对外投资,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效率;而过为大的行业跨度,可能使企业现有资源无法匹配导致创新效率低[9][10];有的学者基于组织学习理论,认为更大行业跨度的企业投资,使得企业能够组织化地接受更为新颖的技术和取得更为广阔的创新空间。[11]但是上述理论并不能解释错综复杂的跨行业对外投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上述研究的结论往往相互矛盾,难以被有机地统一到一个稳定的理论框架之中,所以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融合上述理论的合理内核,创立更新的理论研究支点。
本文还将讨论行业跨越创新作用的边界条件。中外理论界均广泛地利用两个国家之间的制度评分和制度评分差异计算国家间的制度距离,并利用上述制度距离对FDI的制度跨越问题进行研究。[12][13]不论针对宏观变量如行业技术水平还是针对诸如企业业绩等微观变量,上述制度跨越对于投资母国行业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投资母公司创新能力、业绩水平的提升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Brouthers和Brouthers探索了制度跨越与海外投资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面对投资目的地国家与投资母国较大制度的环境差异,需要进行较大跨度的制度跨越时,其倾向于选择合资方式。[14]Chao和Kumar则指出对于制度跨越的相关公司业绩影响需要进行特定化的实证分析。[15]
生命周期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Vernon提出的。他从产品生产的技术变化出发,分析了产品的生命周期以及对贸易格局的影响。他认为,制成品和生物一样具有生命周期,会先后经历创新期、成长期、成熟期、标准化期和衰亡期五个不同的阶段。[16]生命周期理论随后被广泛地引入到公司治理、创新创业相关研究和跨国企业研究中来。[17]主流学术观点认为,在成长期的企业更为倾向利用企业和行业内部创新动力推动企业创新能力和业绩的双重增长,而在衰退期的企业其创新能力的提升更加依靠其他行业或者外部动因的推动。[18]与生命周期理论相同,国家战略产业定位也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行业跨越的创新绩效,国家制定的战略产业政策和划分的战略产业不仅仅意味着上述产业的企业具有一定的战略发展潜力和带动效应,也意味着政府和社会将会对企业提供更为充分的资金、技术、人力和管理资源,协助企业的对外投资扩张以及跨行业投资行为。[19]
虽然上述因素对于企业创新和业绩的影响已经被学术界广泛研究,但是,有关上述因素对于企业对外投资行业跨越的相关影响和影响机制却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究其原因,第一,直到最近理论界才形成成熟的上下游距离评价体系。第二,相关行业跨越溢出的理论基础存在多个混淆和矛盾之处,难以从理论层面分析上述因素的调节影响。因此,本文将基于最新的生产链行业距离相关研究成果,并糅合相关矛盾理论,对上述因素的行业跨越调节影响进行分析。
二、实证分析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研究提出问题,使用数据挖掘技术收集在A股上市的企业跨境投资相关数据形成上市企业对外投资面板数据库,基于上述数据库,利用实证分析模型进行分组回归分析,从而发现不同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最后将相关研究结论运用到现实问题的解释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实践建议。
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根据公式(1)进行回归分析:

(1)
其中:DVit为因变量,IDVsit为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controlsit为控制变量,εit为模型残差。
该方法主要是在一定假设条件下将估计方程的一阶差分变量设定为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从而得到差分GMM 估计量,有效解决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但差分 GMM 方法的缺点在于会损失一部分样本信息,而且解释变量的时间连续性较长也会减弱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小样本情况下尤其如此。因而我们采用系统GMM 估计方法。它是在差分GMM 估计方法上再引入水平方程,将滞后差分变量增加为水平方程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从而使得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大为提高。另外,采用系统 GMM 两步法估计可以消除异方差的干扰,所以,本文使用系统 GMM 两步估计方法来对模型做回归分析。
(二)数据样本
本文依据Wind数据库中2006-2015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20]Wind数据库提供了中国上市企业上市之后根据证监会和其他机构要求应当刊载的信息和企业主动刊载的公司财务、人力、技术相关信息。本文所依据的主要因变量和自变量均基于Wind数据库。
同时,本文借鉴毛其淋和许家云的研究[21]并利用商务部发布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名录》匹配相应的中国上市企业对外投资信息。由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名录》中仅仅收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母公司全称,所以还需要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利用工商登记系统查询相关对外投资母公司是否属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并对其进行数据挖掘和数据匹配。
为了收集和整理相关对外投资数据,本文首先对对外投资母公司企业工商登记信息进行数据抓取。使用PHP软件作为主要数据挖掘方法,从企业信息端口中挖掘《中国对外企业投资名录》中对外投资母公司的全资母公司和控股母公司全称,再加上对外投资母公司全称,匹配上市企业全称,确定上市企业2006-2015年对外投资情况。
最后,本文借鉴Antràs等基于2002、2007和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input-output tables)提出的比较完善的产业位置测算方法[22],测算出全国40个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处的产业链相对位置,并以0与1之间的数值大小加以表征。
首先可以明确投入产出表中的一个基本恒等式:
Yi是i行业的总产出,Fi是i行业产出中直接流向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的部分,而Zi为i行业产出中被用作其他行业消耗的部分。在一个拥有N个行业的国民经济体系中,上述等式可以进一步被阐述为:
基于公式(3)所建立的关于产业链位置的第一种测算方法为:
公式(4)中的[I-D]^(-1)通常被称为莱昂列夫逆矩阵。
关于产业链位置的第二种测算方法为:

(5)
通过上述两种方法测算出的产业链位置评分均落在[0,1]的区间之内。某行业的评分数值越大,说明该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越处于下游位置。以上测算方式在提出以后,引起了经济学领域学者的极大关注,并已经有部分学者基于上述测算方式开展宏观层面的研究。本文创新性地将上述测算方法引入到研究中来,将投入产出表与企业微观数据相结合,从而拓展了投入产出表及上述测算方法的使用场景。基于公式(5)产业链位置评分测算方法,本文进一步以差值的方式测算出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行业距离大小,仍然以0与1之间的数值大小加以表征,并且利用上述2006-2015年行业距离编制相关的变量。本文还利用了世界银行制度条件指数编制制度跨越相关变量[23],并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编制战略新兴产业相关变量。
综上,本文在删除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名录》中无对外投资数据(或无对外投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企业之后,整理出761个企业2006-2015年10年间5178条数据所组成的数据库,并利用动态面板数据系统广义矩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三)变量测算方法
因变量:学术界衡量企业创新能力一般运用企业专利申请、专利获得或者专利被引率等专利数据。[24][25]然而,Smith指出虽然从科学技术创新角度,专利相关变量能够很好地衡量创新业绩的大小,但是无法衡量非科技类的其他创新模式和创新企业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在研究相关创新能力溢出的学术情境下,管理、人力、制度方面的资源储备和组织学习可能更能解释溢出效应的实际情况。[26]因此,本文根据Smith的研究成果并基于Wind数据库披露的上市企业财务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因变量。此外,为了衡量中国上市企业对外投资中行业跨越行为对企业业绩的整体影响,本文在利用资产收益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同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本文利用公式(5)所编制的行业评分,测算每一次对外投资上市企业所属行业与上市企业对外投资行业的上下游评分差异的绝对值,作为投资的行业跨越距离。借鉴Zhou和Guillén的研究成果[27],本文利用公式(6)构造上市企业年度制度跨越经验变量:
其中:IDDikt代表一次对外投资行为的行业距离,Ait代表此次投资行为在当前年份相隔的时间(年),Tit指该企业首次进行对外投资到当前年度相隔的时间。
调节变量:本文根据Zhou和Guillén的研究成果[28],利用公式(7)测算企业制度跨越经验:
其中:IIDikt代表一次对外投资行为的国家制度距离,Ait代表此次投资行为在当前年份相隔的时间(年),Tit代表该企业首次进行对外投资到当前年度相隔的时间。
本文根据Kravet的研究成果[29],测算企业生命周期指数,并且按中位数将数据分为成长期企业和衰退期企业,生成生命周期虚拟变量,成长期企业为1,衰退期企业为0。
最后,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本文对照各个上市企业国内主营业务,生成战略产业虚拟变量,其主营业务属于战略新兴产业的赋值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根据Peng和Luo的研究[30],上市企业年龄、所处行业增长率、公司规模(公司员工数量对数值)都能够影响上市企业的创新水平和业绩水平,因此本文加入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Li,Poppo和Zhou还指出行业不确定性能够明显地影响企业的业绩。[31]因而,本文根据Li,Poppo和Zhou的研究方法[32]编制了行业不确定性变量(对数值)控制相关的影响。Liu等指出企业所有制结构对创新能力具有较高的影响。[33]因此,本文按照Liu等的研究[34]设置所有制虚拟变量,国有企业为1,非国有企业为0。Galindo和Méndez也指出,企业研发投入占总年度投入的比值,以及企业所处省份GDP(对数值)均会对企业创新业绩产生明显的影响。[35]所以本文加入研发投入比和企业所在省份GDP对数值作为控制变量。变量统计特征见表1。

表1 变量统计特征
续表1

变量名称MeanS.D.MinMax4.制度跨越经验20.8265.7255.13645.4275.生命周期指数虚拟变量0.4970.500016.战略产业虚拟变量0.3050.460017.公司年龄15.4114.9343378.行业增长率0.1051.520-5.58322.3339.公司规模7.8221.2152.39812.18610.行业不确定性10.4620.7096.18811.39111.所有制虚拟变量0.4420.4970112.企业研发投入比0.1472.1540133.37613.企业所在省份GDP6.1671.1470.5887.410
(四)实证结果和分析
本文利用STATA提供的xtdpdsys命令,运用系统两步法广义矩估计模型(GMM)对中国上市企业对外投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36]所建模型都能够满足Sargan检验和序列自相关性检验的通过标准。根据前文分析,在组织学习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理论的指导下,企业行业跨越对创新能力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为了厘清其中的影响机制,本文借鉴Haans和Pieters的研究成果[37],在解释变量中加入平方项进行模型回归,同时分析企业行业跨越对创新能力的U型或者倒U型影响。最后,本文还将根据Peng和Luo、Deng和Wang的研究成果[38][39],按照调节变量中位数对模型进行分组,检验上述变量对企业行业跨越创新能力影响的调节作用。主效应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主效应回归结果
续表2

模型1模型2模型3公司规模-0.010***(0.001)-0.011***(0.001)-0.010***(0.001)行业不确定性-3.05e-04(3.47e-04)-3.05e-04(3.27e-04)-3.19e-04(3.88e-04)所有制虚拟变量0.030***(0.011)0.028***(0.009)0.030***(0.010)企业研发投入比3.82e-04***(1.31e-04)4.29e-04***(1.59e-04)0.001***(1.74e-04)企业所在省份GDP0.003(0.002)0.004(0.004)0.003(0.002)工具变量数151618AR(1)-1.560-1.433-1.376AR(2)0.4490.4320.319Sargantest1.8770.5460.452Waldchi2(15)13.87534.55528.04企业数761761761观测值数517851785178
注:(1)因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2)*,**,***分别表示z统计量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3)模型使用滞后期为三期,工具变量引用一次;(4)所有数值均保留三位小数,但转折点以未四舍五入的回归系数数值计算。
回归结果发现,中国上市企业对外投资行业跨越经验并非单调线性地影响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创新能力,而是呈现倒U型曲线模式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影响。[40]在对外投资初期,跨行业投资能够为企业带来组织化的学习其他行业先进技术、经验的机会,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所带来的创新能力正效应不断加强,边际效应递增。但是本文也发现,企业自身的基础性资源,如技术、资金、人员和管理能力等,如果不能随着企业的行业扩张迅速地适应企业组织化学习的需要,跨行业投资对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所带来的创新能力会发生变化并出现“拐点”。本文发现行业跨越的转折点是0.411左右(这一数值稍大于本文样本的平均值),最终企业跨行业经验的创新边际效应逐渐递减。
为了进一步研究企业对外投资行业跨越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形成机制,本文根据Deng和Wang的研究成果[41]分别利用制度跨越经验中位数、企业生命周期和战略产业虚拟变量进行分组回归,比较回归结果,研究上述变量的调节作用。全部回归结果都经过模型Sargan检验以及序列自相关性检验,并且各组间差异都通过了Z值检验。回归结果见表3(为了表格简洁本文省略了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回归结果和统计量的输出)。

表3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续表3

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模型8模型9Sargantest0.7010.5490.6260.7130.5940.498Waldchi2(15)501.75487.23449.36490.17519.89420.30企业数459390471493302459观测值数255826202606257020103168
注:(1)因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2)*,**,***分别表示z统计量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3)模型使用滞后期为三期,工具变量引用一次;(4)所有数值均保留三位小数,但转折点以未四舍五入的回归系数数值计算;(5)模型分组回归中同一企业存在在不同年份归属于不同组别的情况,因此企业数各组相加可能会大于761家。
最后,本文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即利用企业资本收益率替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因变量对数据库中的全部企业和各种调节变量分样本企业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

表4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注:(1)因变量为ROA;(2)*,**,***分别表示z统计量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3)模型使用滞后期为三期,工具变量引用一次;(4)所有数值均保留三位小数,但转折点以未四舍五入的回归系数数值计算。(5)模型分组回归中同一企业存在在不同年份归属于不同组别的情况,因此企业数各组相加可能会大于761家。
根据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利用企业资本收益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的稳健性检验与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相一致,企业对外投资跨行业经验对企业经营业绩也有着倒U型影响,企业制度跨越经验、生命周期和企业战略产业定位对上述影响都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通过Z值检验)。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立足于国际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使用数据挖掘手段,构筑了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行业跨越经验相关数据库,并且利用面板数据系统两步法广义矩估计模型对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行业跨越经验的影响、调节条件和理论依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行业跨越所带来的相关经验能够对企业创新绩效带来显著的影响,具体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在行业跨越初期,通过学习跨国、跨行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开拓企业市场和发展战略视野,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边际递增的正向增强。但随着企业在本国本行业内积累的资金、技术、人力和管理基础资源越来越难满足过于分散的行业跨越的需求,行业跨越会降低企业创新拓展的能力,创新影响边际递减。
第二,丰富的海外制度跨越经验能够有力地促进行业跨越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企业长期在不同制度、不同市场环境和不同文化特征条件下进行投资经营所获得的经验能力能够激发企业组织学习能力,增强企业获得关键性的技术、资金、人力和管理基础资源的能力,从而有效地配合企业行业跨越所带来的组织学习效果,抵消企业基础资源局限和不足。
第三,成长期企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会获得更多的商业、政策支持,有机会以快捷和低廉的方式获得必要的基础资源。这类企业在海外投资中有机会和更强的能力进行行业跨越性投资,并且因之激发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企业可以尝试不同的产品和经营模式,寻找机遇,学习科技和管理经验,最终达到创新能力和业绩水平的共同提升。
(二)研究启示
第一,对于政府而言,应当意识到企业对外投资行业跨越的重要作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的经济背景下,对外投资不仅应当聚焦本行业或者近似产业的创新动向,还要把握不同行业的投资机会,从其他行业的经验中学习和提升创新能力。政府应当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据市场规则跨国、跨行业投资,提升其创新能力水平。同时,也应当根据企业海外投资制度跨越经验、成长阶段和经营条件,主动提供行业跨越相关的信息技术支持,警示过快、过于分散的跨行业投资企业可能面临要素资源支撑不足的风险。
第二,对于企业而言,要把握在海外投资中跨行业投资的适度性。过于局限于本行业或者接近行业的投资策略可能会错失投资机会,而过于分散的对外跨行业投资策略则可能因为资源基础无法衔接,导致其创新能力提升无法摆脱倒“U”字型的宿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不但需要注意培育自身跨行业学习能力,同时也要注重增强其基础性的资金、技术、人力和管理保障能力,使对外投资过程中的创新能力始终处于正向增强状态。
注释:
[1] Chen V.Z., Li J., Shapiro D.M.,“International reverse spillover effects on parent firms: Evidences from emerging-market MNEs in developed markets”,EuropeanManagementJournal,vol.30,no.3(2012),pp.204-218.
[2] Wang C.C., Wu A., “Geographical FDI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innovation of indigenous firms in China” ,InternationalBusinessReview, vol. 25, no. 4(2016),pp.895-906.
[3] Meyer K.E., Sinani E., “When and where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enerate positive spillovers? A meta-analysis” ,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vol.40,no.7(2009),pp.1075-1094.
[4] 陈继勇、盛杨怿:《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5] 赵 勇、白永秀:《知识溢出: 一个文献综述》,《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6] 李 梅、柳士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管理世界》2012年第1期。
[7] 李 梅、金照林:《国际R&D、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 2011年第10期。
[8] Buckley P.J., Wang C., Clegg J., “The impact of foreign ownership, local ownership and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on spillover benefit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Internationalbusinessreview,vol.16,no.2(2007),pp.142-58.
[9] Jensen M., “The role of network resources in market entry: commercial banks' entry into investment banking, 1991-1997”,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vol.48,no.3(2003),pp.466-97.
[10] Melitz M.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Econometrica,vol.71,no.6(2003),pp.1695-1725.
[11] Garriga H., von Krogh G., Spaeth S., “How constraints and knowledge impact open innovation”,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vol.34,no.9(2013),pp.1134-1144.
[12] Ahammad M.F., Tarba S.Y., Liu Y., Glaister K.W., “Knowledge transfer and cross-border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stance and employee retention”,InternationalBusinessReview,vol.25,no.1(2016),pp.66-75.
[13] Siegel J.I., Licht A.N., Schwartz S.H., “Egalitarianism, cultural distanc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new approach”,OrganizationScience,vol.24,no.4(2013),pp.1174-1194.
[14] Brouthers K.D., Brouthers L.E., “Explain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paradox”,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vol.32,no.1(2001),pp.177-189.
[15] Chao M.C., Kumar V.,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diversity-performance relationship”,JournalofWorldBusiness,vol.45,no.1(2010 ),pp.93-103.
[16] Vernon 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InternationalEconomicsPoliciesandtheirTheoreticalFoundations,vol.80,no.2(1982) , pp.307-324 .
[17][29] Kravet T.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Managerial risk-taking: corporate acquisitions”,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vol.57,no.2(2014),pp.218-240.
[18] Lumpkin G.T., Dess G.G.,“Linking two dimensions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o firm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 and industry life cycle”,Journalofbusinessventuring,vol.16,no.5(2001),pp.429-451.
[19] Zongyi Z., Long C., “Empirical Study on Impact of Government Subsidy on Internal R&D Invest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in China” ,TechnologyEconomics, vol.27,no.27(2013),pp.1089-1093.
[20] 王克敏、杨国超、刘 静、李晓溪:《IPO 资源争夺、政府补助与公司业绩研究》,《管理世界》2015年第9期。
[21] 毛其淋、许家云:《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世界经济》 2014年第8期。
[22] Antràs P., Chor D., “Organiz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Econometrica,vol.81,no.6(2013),pp.2127-204.
[23] 李雪灵、张 惺、刘 钊、 陈 丹:《制度环境与寻租活动: 源于世界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1期。
[24] Boeing P., “The allo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R&D subsidies-Evidence from listed firms”,ResearchPolicy,vol.45,no.9(2016),pp.1774-1189.
[25] Boeing P., Mueller E., Sandner P. , “China's R&D explosion—Analyzing productivity effects across ownership types and over time”,ResearchPolicy,vol.45,no.1( 2016),pp.159-176.
[26][36] Smith S.W., “Follow me to the innovation frontier? Leaders, laggards, and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imports and export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vol.45,no.3( 2014),pp.248-274.
[27][28] Zhou N., Guillén M.F., “From home country to home base: A dynamic approach to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vol.36,no.6(2015),pp.907-917.
[30][38] Peng M.W., Luo Y.,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vol.43,no.3( 2000),pp.486-501.
[31][32] Li J.J., Poppo L., Zhou K.Z., “Do managerial ties in China always produce value? Competition, uncertainty, and domestic vs. foreign firms”,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vol.29,no.4(2008),pp.383-400.
[33][34] Liu D., Gong Y., Zhou J., Huang J.C., “Human Resource Systems, Employee Creativity, and Firm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irm Ownership”,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 vol.60,no.3(2017).
[37][40] Haans R.F., Pieters C., He Z.L., “Thinking about U: theorizing and testing U‐and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s in strategy research”,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vol.37,no.7( 2016).pp.1177-1195.
[39][41] Deng Z., Wang Z., “Early-mover advantages at cross-border business-to-business e-commerce portals”,JournalofBusinessResearch,vol.69,no.12( 2016),pp. 6002-6011.
2017-03-10
郑云坚, 男, 福建福州人, 闽江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高级经济师、 新华都商学院硕士生导师, 管理学博士;赵 淼, 男, 北京人, 国家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师, 经济学硕士。
U448.34
A
1002-3321(2017)05-0048-09
[责任编辑:黄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