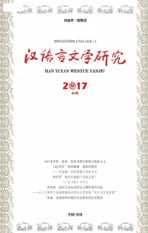废名小说的“文章之美”
——以《桥》为中心
2017-12-10张丽华
张丽华
废名(1901-1967)是现代文学作家中“读者缘”颇为奇特的一位,其作品在当时即被公认晦涩,是“第一名的难懂”①岂明(周作人):《枣和桥的序》,王风编《废名集》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10页。下引《废名集》版本皆与此相同。;然而,正如其好友鹤西所称,“废名君的文章,以难懂出名,可是懂了一点就必甚为爱好”②鹤西(程侃声):《谈桥与莫须有先生传》,《文学杂志》1937年第1卷第4期。。周作人、朱光潜、李健吾、施蛰存等同时代的评论家皆是废名文章的爱好者,对其作品赞赏有加,且颇有会心之理解。废名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少“破天荒”的小说作品,如《桥》(1932)、《莫须有先生传》(1932)、《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1948)等,这些作品在小说史上颇难定位,但直到今天,它们仍然不断激起“懂了一点就必甚为爱好”的读者和研究者孜孜解读的兴趣。
周作人曾将废名的晦涩,归结为文体的简洁生辣,将之比附于明末以文风奇僻著称的“竟陵派”,又称“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③岂明(周作人):《枣和桥的序》,《废名集》第6卷,第3410页。朱光潜在对废名《桥》的评论文章中则写道:“看惯现在中国一般小说的人对于《桥》难免隔阂;但是如果他们排除成见,费一点心思把《桥》看懂以后,再去看现在中国一般小说,他们会觉得许多时髦作品都太粗疏浮浅,浪费笔墨。”因此,“读《桥》是一种很好的文学训练”。④孟实(朱光潜):《桥》,《文学杂志》1937年第1卷第3期。将大多数读者与废名隔绝开来的,大概并非废名作品本身的困难,而是如朱光潜所说,源于现代读者“安于粗浅”的小说阅读习惯。假如我们打破“小说”的形式成规和阅读期待,从周作人所说的“文章之美”的角度进入,或许可以找到打开废名奇僻幽微之文学世界的另一条通道。
一、废名小说文体略识
废名在文坛初露头角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其时他尚未“废”去名号,署的是本名“冯文炳”。废名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升入北京大学英文学系,《竹林的故事》所收的14篇短篇小说,即大致创作于这一时期。这部小说集中的作品,虽然最早的几篇还残留着模仿的痕迹,但很快便显示出废名独特的个人风格,已约略可以见出日后《桥》《莫须有先生传》的文体端倪。1935年,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从《竹林的故事》里选了三篇作品——《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作为废名小说的代表。为便利起见,我们先以这三篇作品为例,对废名小说的文体特质略作分析。
《浣衣母》写于1923年8月,这篇作品从文体到主题,皆可见出模仿鲁迅的痕迹。小说的主人公“李妈”是一位住在城外河滩上替人洗衣的普通妇人,原本受全城人的尊敬,但一位卖茶的单身汉的寄住,引起了乡村的骚动与谣言。小说开头便是以倒叙的方法从这一“谣言”写起:
自从李妈的离奇消息传出之后,这条街上,每到散在门口空坦的鸡都回厨房的一角漆黑的窠里,年老的婆子们,按着平素的交情,自然的聚成许多小堆;诧异,叹息而又有点愉快的摆着头:“从那里说起!”①废名:《竹林的故事·浣衣母》,《废名集》第1卷,第50页。
这种对于乡村谣言的传神描写,即颇有鲁迅的笔法;而从“年老的婆子们”的议论中引出主人公“浣衣母”的间接写法,亦是鲁迅小说《药》和《明天》中的典型技巧。此外,小说中写到李妈的女儿“驼背姑娘”的死,“一切事由王妈布置,李妈只是不断的号哭”,这一情节也与《明天》中单四嫂子失去孤儿的情景,似曾相识。废名自己后来回忆说,在这篇作品中,“一枝笔简直就拿不动,吃力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②废名:《〈废名小说选〉序》,《废名集》第6卷,第3269页。。所谓“吃力”,显然和他的小说技巧尚不成熟、还处于模仿阶段有关。尽管从文体到主题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与鲁迅的作品相比,废名在《浣衣母》中的表达要冲淡许多,无论是寡妇孤儿的悲哀,还是礼教的迫害,都笼罩在一种小说无意中所展露出的人情之美中,批判的锋芒被稀释了不少。如果将鲁迅的小说比作木刻画,那么废名的作品一开始便呈现出铅笔素描般的轻淡之感。
除了《浣衣母》,《竹林的故事》集中其他几篇早期作品,也存在或多或少的模仿痕迹。不过,废名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个人风格,这在写于1924年的《竹林的故事》中即已明显表现出来。这篇后来被用作小说集题名的作品,很有废名的特色,小说几乎没有情节性的故事,所写的只是平凡的乡村生活,作者意在借竹林的主人公“三姑娘”这一美好的少女形象,来表现乡村的人情之美。废名在此所塑造的淳朴美好的乡村少女形象,对沈从文有着显著的影响。在“三三”“翠翠”这些沈氏笔下著名的少女形象中,我们不难看到“三姑娘”的影子。不过,和沈从文的写法相比,废名的文体更具含蓄的古典趣味。“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这是《边城》里的名句,沈从文对翠翠的描写,从肤色到眼眸,颇为详尽,接近西方小说言无不尽的写实传统。相比之下,废名对“三姑娘”的描写则要含蓄得多:
三姑娘这时已经是十二三岁的姑娘,因为是暑天,穿的是竹布单衣,颜色淡得同月色一般,——这自然是旧的了,然而倘若是新的,怕没有这样合式,不过这也不能够说定,因为我们从没有看见三姑娘穿过新衣:总之三姑娘是好看罢了。③废名:《竹林的故事·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1卷,第123页。
在废名这里,少女相貌的美好似乎是不可写的,只好用饶舌的方式写上下四旁的衣装:旧衣也好,新衣也罢,总之“浓妆淡抹总相宜”——至于如何“好看”,则作为空白,留给读者去想象。这种“留白”的技巧,后来成为废名小说中十分常见的修辞艺术。
从《浣衣母》到《竹林的故事》,再到《河上柳》,废名在小说中对故事情节的放逐,愈发大胆。写于1925年4月的《河上柳》,不要说没有情节,连故事也几乎消亡殆尽,整篇小说所表现的只是“陈老爹”如意识流般的心理活动:从衙门禁演木头戏后的失落,到对于亡妻曾经在杨柳树上点灯的怀念,再到大水淹没杨柳的回忆……值得注意的是,在表现陈老爹内心意识的流动时,“河上柳”这一“风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老爹突然注视水面。
太阳正射屋顶,水上柳荫,随波荡漾。初夏天气,河清而浅,老爹直看到沙里去了,但看不出什么来,然而这才听见鸦鹊噪了,树枝倒映,一层层分外浓深。
(中略)
接着是平常的夏午,除了潺潺水流,都消灭在老爹的一双闭眼。
老爹的心里渐渐又滋长起杨柳来了,然而并非是这屏着声息蓬蓬立在上面蔽荫老爹的杨柳,——到现在有了许多许多的岁月。①废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废名集》第1卷,第126-127页。
这里,风景并非客观之物,而是存乎主人公的眼与心——注视水面可见柳荫荡漾,闭眼则外物消失;而心里滋长出的杨柳——回忆的经验世界,同样也是“风景”之所在。正是基于这一对于“风景”的理解,小说以“老爹的心里渐渐又滋长起杨柳来”为过渡,从主人公的现实生活悄然切换到了回忆世界——紧接着这一段引文,便是陈老爹对于过往岁月中与杨柳有关的回忆。这种对于风景与人物内心之关系的处理方式,以及在现实世界与回忆/幻想世界中的自由穿梭,开启了废名后续诸多小说的先声。
以上三篇经鲁迅选入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废名小说,的确代表了三种特色,同时也能见出废名的小说创作从模仿到形成个人风格的过程,可见鲁迅眼光之敏锐。在《小说二集》的导言中,鲁迅对废名《竹林的故事》之后的小说评价不高:“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了,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样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②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所谓“率直的读者”,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以“小说”的形式成规和期待视野去阅读的读者。假如我们换一种眼光,从文章的角度来看,或许会另有发现。
在1937年的评论文章《一人一书》中,施蛰存将废名视为中国新文坛中“第一名”的文体家,在他看来:
在写《竹林的故事》的时候,废名先生底写小说似乎还留心着一点结构,……但在写作《枣》的时候,……似乎纯然耽于文章之美,因而他笔下的故事也须因文章之便利而为结构了。……看废名先生的文章,好像一个有考古癖者走进了一家骨(古)董店,东也摩挲一下,西也留连一下,纡徊曲折,顺着那些骨(古)董橱架巡行过去,而不觉其为时之既久也。……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起来,也就是所谓“涉笔成趣”。③施蛰存:《一人一书》,《宇宙风》1937年第32期。
在废名的小说中,故事“因文章之便利而为结构”“涉笔成趣”之作,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1932年出版的《莫须有先生传》。
《莫须有先生传》是一部自叙传式的小说,它以废名1927年前后隐居西山的生活为底本,“莫须有先生”即废名自己的投影。这部作品与《桥》出版于同一年,可是风格却截然两样。《桥》的风格是简洁而凝练的,而《莫须有先生传》却来得恣意汪洋。卞之琳说:“废名喜欢魏晋文士风度,人却不会像他们中一些人的狂放,所以就在笔下放肆。”④卞之琳:《序》,《冯文炳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用“放肆”来形容《莫须有先生传》的文风,可谓恰如其分。尽管风格两样,但在联想的跳跃、情文相生的语言机制上,《莫须有先生传》与《桥》却有着内在的共通之处。《桥》且按下不表,这里先来看《莫须有先生传》的文风:
莫须有先生蹬在两块石砖之上,悠然见南山,境界不胜其广,大喜道:
“好极了,我悔我来之晚矣,这个地方真不错。我就把我的这个山舍颜之曰茅司见山斋。可惜我的字写得太不像样儿,当然也不必就要写,心心相印,——我的莫须有先生之玺,花了十块左右请人刻了来,至今还没有买印色,也没有用处,太大了。我生平最不喜欢出告示,只喜欢做日记,我的文章可不就等于做日记吗?只有我自己最明白。如果历来赏鉴艺术的人都是同我有这副冒险本领,那也就没有什么叫做不明白。”
“莫须有先生,你有话坐在茅司里说什么呢?”①废名:《莫须有先生传·这一回讲到三脚猫》,《废名集》第2卷,第701页。
这一段是小说第六章 《这一回讲到三脚猫》的开头,写的是莫须有先生出恭的神态。莫须有先生坐在茅司里自言自语,他的思绪十分跳跃:从山舍的命名,到写字,到印玺,再到告示,日记,文章,最后讲到艺术的赏鉴,各个联想物之间有一点微弱的联系,但背后却没有总体的指涉,类似于在能指层面不断跳跃的成语接龙游戏。在这个滑稽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场景里,作者还插入了一句“悠然见南山”,这既是对陶渊明诗句的引用,同时又是对莫须有先生真实动作的描摹。这种在文本中随时插入古诗文的情形,在 《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中都很常见。这些诗文皆是未经剪裁、长驱直入的,废名并没有有意识地将诗文典故与当前文本的语境加以协调,而是如庾信一般,“以典故为辞藻,于辞藻见性情”②废名:《谈用典故》,《废名集》第3卷,第1461页。;当典故的历史含义与当下的文本语境产生落差时,便造成这种特殊的又热闹又嘲讽的效果。
周作人曾形容《莫须有先生传》文章的好处道:“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③岂明(周作人):《〈莫须有先生传〉序》,《废名集》第6卷,第3414页。这段关于流水的比喻很贴切,与施蛰存所说的如考古癖者在古董店中巡行的感觉,颇为相似。诗文典故以及自由联想中的各个物件,在废名的文章中,类似于流水所遇到的汊港弯曲、岩石水草,被披拂抚弄一番之后,文章又继续前行了。这种流水般的文脉,不仅是废名文章局部的文体特色,也可以用来形容《莫须有先生传》的整体结构。莫须有先生在西山的奇遇,如同堂吉诃德的漫游,其间的偶然和巧遇,似乎皆非行程的主脑,但除去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换言之,莫须有先生的故事,没有任何先在的目的性,亦不指向一个外部的现实世界,仿佛是文本内部一种自足的生长和蔓延。如果借用浪漫主义的一个批评术语,这种文本的“不及物性”④关于浪漫主义美学中语言“不及物性”的概念,参见[法]茨维坦·托多罗夫著,王国卿译:《象征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1-226页。,与其“文章之美”恰好构成了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关系。
二、《桥》的文章与意境
废名的小说 《桥》1932年4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分上下两篇,计四十三章。这部小说的写作始于1925年11月,上篇各章在结集出版前,曾经过废名的大幅修订。开明书店的单行本出版之后,废名又开始续写下卷。⑤下卷未结集,收入王风编《废名集》第2卷。这里的讨论以开明书店已出版的单行本为主。因此,后来他戏称自己是“十年造《桥》”。 《桥》既是从《竹林的故事》到《莫须有先生传》之间的过渡,也是废名小说文体的集大成者。
《桥》的情节构造十分松散,上篇十八章写小林与琴子的儿时生活,下篇二十五章写小林长大后的回乡及其与琴子和细竹之间微妙的爱情。小说的主要人物只有三位:小林、琴子和细竹,琴子与细竹是堂姐妹,小林与琴子自幼定下婚约,而回乡后的小林对长大了的细竹姑娘,亦萌发爱意。整部小说即围绕这小儿女的微妙爱情与田园诗一般的乡村生活而展开。实际上,这一故事线索,对于理解《桥》并不重要。《桥》的各章最初在《语丝》上刊出时题作《无题》,其发表的先后并不遵循原稿的顺序。而按照当时发表的顺序,《语丝》的读者显然无法读出小说的时间线索。对此,废名早有自觉,他在1930将《桥》的上篇各章修订之后揭载于《骆驼草》时,便在《附记》中声明道:
无论是长篇或短篇,我一律是没有多大的故事的,所以要读故事的人尽可以掉头而不顾。我的长篇,于四年前开始时就想兼有一个短篇的方便,即是每章都要它自成一篇文章,连续看下去想增读者的印像,打开一章看看也不致于完全摸不着头脑也。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时常姑且拿到定期刊物上发表一下。①废名:《附记》,原刊1930年8月11日《骆驼草》第14期,《废名集》第1卷,第340页。
1935年,周作人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时,则干脆从《桥》中选了六篇作为小品散文的代表,并称“废名所作本来是小说,但是我看着可以当小品散文读,不,不但是可以,或者这样更觉得有意味亦未可知”②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2页。。由此看来,废名的《桥》甫一问世,即打破了“新文学”刚刚建立起来的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乃至小说和散文之间的文类界限。
对于这部情节松散、“文章”大于“故事”的小说,周作人的观感是:“仿佛是一首一首温李的诗,又像是一幅一幅淡彩的白描画。”③周作人:《〈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94页。在诗与诗、画与画之间,并不需要连贯的线索,因此,结构的跳跃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废名自己在《桥》的序言中也交代:“上篇在原来的计划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写,因为我写到《碑》就跳过去写下篇了,以为留下那一部分将来再补写,现在则似乎就补不成。”于是主人公十年的光阴,便以小说上下篇之间“一叶的空白”的形式而存在了。对于这一结构上的空白,废名说:“从此我仿佛认识一个 ‘创造’。真的,我的《桥》,它教了我学会作文,懂得道理。”④废名:《〈桥〉序》,《废名集》第 1卷,第 337页。这句话似乎语带禅机。的确,这种“跳跃”和“空白”的美学,不仅存乎《桥》的结构,在《桥》每一章的行文中,亦比比皆是——而这也正是造成废名小说令人感到“晦涩”的重要缘由。
废名在1927年所写的《说梦》一文中,曾论及其小说的“晦涩”,并为自己辩解道:
有许多人说我的文章obscure,看不出我的意思。但我自己是怎样的用心,要把我的心幕逐渐展出来!我甚至于疑心太clear得利害。这样的窘况,好像有许多诗人都说过。
我最近发表的《杨柳》(无题之十),有这样的一段:
小林先生没有答话,只是笑。小林先生的眼睛里只有杨柳球,——除了杨柳球之外虽还有天空,他没有看,也就可以说没有映进来。小林先生的杨柳球浸了露水,但他自己也不觉得,——他也不觉得他笑。……
我的一位朋友竟没有看出我的“眼泪”!这个似乎不能怪我。⑤废名:《说梦》,《废名集》第3卷,第1153页。
《杨柳》即《桥》的下篇第七章,这一段写的是小林在河边看细竹为小孩子扎杨柳球时的观感。假如没有废名自己关于“眼泪”的解释,这段文字的确令人费解。不过,由“眼泪”的解释作回溯式的阅读,我们却不难解析出废名文章典型的组织方式,并由此获得解读其“晦涩”之文的某种“密码”:“小林先生的眼睛里只有杨柳球”这一句是实写,指的是小林被细竹所扎的“一个白球系于绿枝”之上的杨柳球所吸引;而接下来“小林先生的杨柳球浸了露水”,则跳跃到了隐喻的层面——“浸了露水”的“杨柳球”,而且是在小林的眼睛里,这一眼睛里湿润的球状物,喻指的似乎只能是 “眼泪”,而破折号后面 “他也不觉得他笑”,则再次从“哭”的角度暗示了“眼泪”这一喻旨。从这一角度来看,废名的确是“用心”地要把自己的“心幕”逐渐展开来,以便贴近他想要表达的对象。
这种表现手法,其实是废名小说中常见的技巧,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竹林的故事》与《河上柳》中,已略见一斑:首先,不直接说出想要表达的对象,而是从上下四旁去描写,最终将对象(如三姑娘的“好看”、小林的“眼泪”)烘托或者暗示出来——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空白”的美学;其次,在实写与隐喻或回忆之间,缺乏明显的过渡,同一景物或物件可以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自由驰骋,这里的“杨柳球”与《河上柳》中的“柳树”其实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跳跃”的艺术。这种“空白”与“跳跃”,并不是一味的削减、经济,而是一种间接而有力的美学手段。这一技巧在《竹林的故事》《河上柳》中还只是初露端倪,《桥》则将这一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
我们不妨再来看《桥·花红山》中的一段:
琴子微笑道:
“火烧眉毛。”
细竹听见了,然而没有答。确乎对了花而看眉毛一看,实验室里对显微镜的模样。慢慢地又站起身,伸腰——看到山下去了。
“你喜得没有骑马来,——看你把马拴在什么地方?这个山上没有草你的马吃!”
她虽是望着山下而说,背琴子,琴子一个一个的字都听见了,觉得这几句话真说得好,说尽了花红山的花,而且说尽了花红山的叶子!
“不但我不让我的马来踏山的青,马也决不到这个山上来开口。”
话没有说,只是笑,——她真笑尽了花红山。①废名:《桥·花红山》,《废名集》第1卷,第514页。
这是琴子和细竹在清明节后游览花红山,见到了漫山的杜鹃花(映山红)之后的对话。太阳之下杜鹃花的盛开,似乎没有恰当的语言可以直接描摹,因此,废名借用了姐妹俩的对话来表达:琴子的“火烧眉毛”形容花的颜色——火红;而细竹的 “这个山上没有草你的马吃”则形容花的密集——满山是花,没有草的生长之地。这里,琴子和细竹似乎变成了练习联句的诗人,将她们的对话拼贴起来,便如同近体诗中的对句,从不同的角度互文式地描摹了花红山花开的盛况。
有意思的是,在这段对话中,姐妹二人对对方话语的反应,又类似针对对方“诗句”的评论,如细竹的“对了花而看眉毛一看”,琴子觉得这几句话“说尽了花红山的花”;这些嵌入在小说叙述中的评论,则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到“诗作”的字面上来——如“眉毛”“马”,而叙述的脉络竟由此跳脱和衍生开去——琴子接着便由细竹的“没有草你的马吃”联想到“不让我的马来踏山的青”。换言之,在废名这里,用来烘托和描写那似乎不可言传之对象的文字本身(能指),也具有传达美感和衍生意义的可能。这种由“能指”衍生出跳跃式联想的方式,与中国近体诗在文字上进行对偶相生的艺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1950年代的《杜诗讲稿》中,废名提出了一个“文字禅”的概念。所谓“文字禅”,指的是诗句中的意象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而是“从写诗的字面上大逞其想象,从典故和故事上大逞其想象”。②废名:《杜甫的诗·夔州诗》,《废名集》第4卷,第2206页。如杜甫的 “有猿挥泪尽,无犬附书频”,“猿”有现实的所指,“犬”却是因对仗而起的联想,是从“黄犬寄书”的典故而生的想象;又如李商隐的“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驻马”是写实,“牵牛”则是由上联对应的字面(“马”)而来的想象——李商隐的诗句原本表达的是凄怆之情,但因为对仗的关系,字面上却显得热闹非凡,仿佛有六七牛马在欢笑似的。近体诗的对仗机制,为这种由字面(能指)而不断衍生出新的联想和意义(即废名所说的“文字禅”),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这也正是中国诗“以少写多”“说尽了而又余音不绝”③废名:《杜甫的诗·秦州诗风格》,《废名集》第4卷,第2169页。的奥妙所在。废名笔下共同作诗、互相评诗的琴子和细竹,显然深谙这一中国诗文的传统。④关于废名小说的语言艺术与他所阐发的杜、李诗歌之“文字禅”的关系,可参阅张丽华:《废名小说的“文字禅”:〈桥〉与〈莫须有先生传〉语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废名自己曾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是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⑤废名:《〈废名小说选〉序》,《废名集》第6卷,第3268页。所谓 “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并不意味着文字的简洁,或是在小说中追求唐人绝句般的意境,而是一种对于意在言外、以简驭繁的表达技巧的锤炼。上文所分析的《杨柳》《花红山》中的例子,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废名所说的“用写绝句的方法”来写小说的真正意涵。实际上,废名此语,不仅是他的创作谈,更是可以作为一种阅读技巧来把握:《桥》的每一个章节,亦可当作一首古典诗词来阅读——这要求我们不再用读小说的方式去追踪线性的故事情节,而是需要来回扫描其结构布局,关注其中的前后照应、暗示与烘托,以读诗的方式来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对象与主题。《桥》最早在《语丝》中连载时,不仅整部小说尚无名目,各章的小标题也处于待定状态,只好一律以“无题”相称;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废名后来为《桥》各章所加的小标题,尤其是下篇的各章,如 《灯》《棕榈》《沙滩》《杨柳》《黄昏》《灯笼》《花红山》……等等,便不难发现,它们不仅标识着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同时也是各章的“题眼”。抓住这一“题眼”,废名从上下四旁进行的烘托和暗示,也就庶几可解了。
废名在北大读的是英文系,他这种对于“中国文章”的理解,最早其实是由西洋文学启发而来。他在1930年代曾说:“我读中国文章是读外国文章之后再回头来读的。”①废名:《中国文章》,《废名集》第3卷,第1371页。在1957年的《〈废名小说选〉序》中,更是明确指出:“就《桥》和《莫须有先生传》说,英国的哈代,艾略特,尤其是莎士比亚,都是我的老师,西班牙的伟大小说《吉诃德先生》我也呼吸了它的空气。”②废名:《〈废名小说选〉序》,《废名集》第6卷,第3269页。而朱光潜在评论废名的小说《桥》时,则将它与普鲁斯特与伍尔夫夫人的作品相提并论:
它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而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这种文章;它丢开一切浮面的事态与粗浅的逻辑而直入心灵深处,颇类似普鲁斯特与伍而夫夫人。(中略)普鲁斯特与伍而夫夫人借以揭露内心生活的偏重于人物对于人事的反应,而《桥》的作者则偏重人物对于自然景物的反应。他们毕竟离不开戏剧的动作,离不开站在第三者地位的心理分析,废名所给我们的却是许多幅的静物写生。③孟实(朱光潜):《桥》,《文学杂志》1937年第1卷第3期。
朱光潜的评论并非特例,温源宁也有类似的看法,废名表示自己虽然“当时只读俄国十九世纪小说和莎翁的戏剧”,但 “后来读了点吴 (尔夫),艾(略特)的作品”,认为“确有相同之感”。④朱光潜等:《今日文学的方向——“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记录》,原刊1948年11月14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07期,《废名集》第 6卷,第3394页。这意味着,在废名小说中,其“中国文章”的形式背后,实有着西洋文学的灵魂——这是一位“用毛笔写英文”的作家。
在《桥》中,废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呈现和分析方式,已颇具现代意味,的确非中国的“旧文章”所能涵盖。我们来看《桥·灯笼》中的一段描写:
这时小林徘徊于河上,细竹也还在大门口没有进来。灯点在屋子里,要照见的倒不如说是四壁以外,因为琴子的眼睛虽是牢牢的对住这一颗光,而她一忽儿站在杨柳树底下,一忽儿又跑到屋对面的麦垅里去了。这一些稔熟的地方,谁也不知谁是最福气偏偏赶得上这一位姑娘的想象!不然就只好在夜色之中。
“清明插杨柳,端午插菖蒲,艾,中秋个个又要到塘里折荷叶,——这都有来历没有?到处是不是一样?”史家奶奶说。
“不晓得。”
琴子答,眼睛依然没有离开灯火,——忽然她替史家庄唯一的一棵梅花开了一树花!
这是一棵蜡梅,长在“东头”一家的院子里,花开的时候她喜欢去看。⑤废名:《桥·灯笼》,《废名集》第1卷,第492-493页。
这一段所极力描摹的是琴子的“心不在焉”。小林徘徊于河上,细竹还没有回来,琴子在灯下与奶奶闲谈,虽然人在屋内,但思绪却全在小林身上,因此是“一忽儿站在杨柳树底下,一忽儿又跑到屋对面的麦垅里去了”(即猜测小林此时的所在地)——这里,“站”和“跑”的行动主体,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琴子,而是琴子的意念。再到后面,“忽然她替史家庄唯一的一棵梅花开了一树花!”这是很拗口的一个句子,意思是,琴子的思绪又飘到了下文所交代的“东头”一家(即细竹家)院子里的梅花上了。文章表面上是由奶奶所说的清明、端午、中秋,按照四季更替的顺序,琴子接着就联想到冬天的梅花,可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是少女之心的飘忽不定、暗自担心。这种对于人物内心活动的呈现方式,的确如朱光潜所说,乃是“丢开一切浮面的事态与粗浅的逻辑而直入心灵深处”,颇具普鲁斯特与伍尔夫夫人所代表的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于人物内心活动的分析和展示,废名并没有直接从普鲁斯特和伍尔夫夫人的作品中获得灵感,他有他自己的“创造”。我们再来看《桥·诗》中的一段:
他要写一首诗,没有成功,或者是他的心太醉了。但他归究于这一国的文字。因为他想像——写出来应该是一个“乳”字,这么一个字他说不称意。所以想到题目就窘:“好贫乏呵。”(中略)
一天外出,偶尔看见一匹马在青草地上打滚,他的诗到这时才俨然做成功了,大喜,“这个东西真快活!”并没有止步。“我好比……”当然是好比这个东西,但观念是那么走得快,就以这三个字完了。这个“我”,是埋头于女人胸中呵一个潜意识。
以后时常想到这匹马。其实当时马是什么色他也未曾细看,他觉得一匹白马,好天气,仰天打滚,草色青青。①废名:《桥·诗》,《废名集》第 1卷,第 526-527页。
如果说上引《灯笼》一节写出了琴子的“心不在焉”,这里写的则是小林在面对细竹“少女之胸襟”时的“心猿意马”。如同《花红山》中的琴子和细竹一样,小林在此也成了一位诗人——这里更为显豁,因作者直接交待“他要写一首诗”。引文中略去的部分,是小林为写出这首“诗”所想到的典故和意象——“杨妃出浴”的故事、红桃、月中桂树等,然而这些都不能令人满意;直到有一天,看到“一匹马在青草地上打滚”,小林(或者说作者废名)才找到了恰当的形象,以表现心中的诗思。
朱光潜认为,与普鲁斯特和伍尔夫夫人相比,废名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特色在于侧重人物对自然景物的反应;如果更加具体一点来说,在废名的小说中,如上引《灯笼》和《诗》中的例子,主人公的意识之流动,皆是以一种意境化的方式来表达的,即以自然景物中的具象来表达人物内心的意念。②吴晓东在《意念与心象——废名小说〈桥〉的诗学研读》(《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一文中,主张用“心象小说”来概括《桥》的诗学特征,强调废名善于在小说中营造一种拟想的具象性的意境。这种以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抽象的、不可捉摸的意念的方式,颇具朱光潜在《谈美》中所说的“寓理于象”的“象征”意味③朱光潜:《谈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07页。。这一象征手法,与《诗经》中的“比”不同,而是更接近于“兴”的手法,因为在作为能指的具象(如“梅花”“白马”)和作为所指的意念(如琴子的心不在焉,小林对细竹之胸襟的遐想)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有理据的联系。从《诗》中所展示的小林做诗的过程——如放逐掉“杨妃出浴”“红桃”等与“少女之胸襟”更具关联性的意象来看,废名其实是在有意避免具象(能指)与意念(所指)之间的相关性或相似性。
对于这种意境化或者说“象征”的技巧,废名后来在《谈新诗》的《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一节中,通过对温庭筠和李商隐诗词艺术的分析,有着精彩的阐述。在废名看来,温庭筠的词,因其“具体的写法”以及对具象的频繁使用,堪称“视觉的盛宴”;而李商隐的诗则借典故来驰骋他的幻想,其典故亦是“感觉的联串”,这种不具逻辑性的“上天下地的幻想”,以及对于具体的形象、感觉与经验的重视,蕴含着突破已有诗歌形式(如腔调、文法)的内在力量,乃是以自由表现自己为诉求的“新诗”所应取法的资源。在论述温庭筠词的“自由表现”手法时,废名举了《花间集》的几首作为例子,并称其“写美人简直是写风景,写风景又都是写美人”。如《花间集》的第二首《菩萨蛮》: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在废名看来,前两句是写幻想中的美人闺房里的情景,可是接着“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一下子就跑到闺外的风景里去了,闺中的“暖香惹梦”与闺外的“江柳残月”之间,并没有任何理据性的关联。废名说,这就是幻想,如此落笔,温词中处处皆是,而这也正是温庭筠最令人佩服的地方——“上天下地,东跳西跳,他却写得文从字顺,最合绳墨不过”①废名:《谈新诗·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废名集》第4卷,第1640页。,“仿佛风景也就在闺中,而闺中也不外乎诗人的风景矣”②同上,第1638页。。我们很难说究竟是温庭筠的词启发了废名《桥》的写作技巧,还是通过《桥》的写作,使得废名“学会作文,懂得道理”,因而对温词有着别有会心的领悟。无论如何,在《桥》的意境化或是象征化的表现方式与废名对于温词的阐释之间,我们能够看到一种鲜明的互文关系。
《桥》的这种文章与意境,在现代小说中似无后续,却意外地在卞之琳一派的新诗中得到了回响。卞之琳诗歌的以小写大、以具象写抽象,与《桥》的意境化和象征化的技巧,颇有会通之处。卞之琳自己也曾说:“我主要是从他(按:废名)的小说里得到读诗的艺术享受,而不是从他的散文化的分行新诗。”③卞之琳:《序》,《冯文炳选集》,第8页。这里我们引用一首卞之琳的《无题一》,以见一斑:
三日前山中的一道小水,
掠过你一丝笑影而去的,
今朝你重见了,揉揉眼睛看
屋前屋后好一片春潮。
百转千回都不跟你讲,
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载你
你的船呢?船呢?下楼去!
南村外一夜里开齐了杏花。④卞之琳:《无题一》,《十年诗草 1930-1939》,桂林:明日社,1942 年版,第 108-109 页。
在这首诗中,诗人以水自居,描写爱情从萌芽(“一道小水”)到生长(“春潮”)、泛滥(“水愿意载你”)的过程。最后一句“南村外一夜里开齐了杏花”,似乎是从《桥·灯笼》中的“忽然她替史家庄唯一的一棵梅花开了一树花”化用而来,其功能则类似温庭筠词中的“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从闺中不可言传的情思,突然转向了闺外的风景,虽然“上天下地,东跳西跳”,却又似乎“最合绳墨不过”,爱情的生长、绚烂,似乎非“南村外一夜里开齐了杏花”不能表达。
三、《桥》的诗学与哲学
通过上文的分析,《桥》的诗学特质可大体概括如下:首先,“空白”“跳跃”的文体特征背后,是一种与中国近体诗的描写技巧以及文字上的对偶相生颇为类似的美学;其次,废名对人物内心活动的开掘,糅合了西方小说与温(庭筠)李(商隐)诗词的传统,开辟了一条独特的以具象写抽象、以心象写意念的“象征”手法。这可以说是废名在现代小说文体上的独特贡献,也是他的文章至今仍然值得一读再读、难以超越的地方。李健吾说,废名有“具体的想像”⑤刘西渭(李健吾):《画梦录——何其芳先生作》,《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192页。;朱光潜则称,《桥》“没有成为‘理障’,因为它融化在美妙的意象与高华简练的文字里面”⑥孟实:《桥》,《文学杂志》1937年第1卷第3期。。这两位评论家皆堪称废名文章的知音。
《桥》的这一诗学特质的背后,蕴含着废名作为一位小说家对语言与事物之关系的独特思考。《桥·黄昏》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一年前,正是这么黑洞洞的晚,三人在一个果树园里走路,N说:
“天上有星,地下的一切也还是有着,——试来画这么一幅图画,无边的黑而实是无量的色相。”
T思索得很窘,说:
“那倒是很美的一幅画,苦于不可能。比如就花说,有许多颜色的花我们还没有见过,当你着手的时候,就未免忽略了这些颜色,你的颜色就有了缺欠。”
(中略)
T是一个小说家。①废名:《桥·黄昏》,《废名集》第1卷,第491页。
这里的N和T皆可视为废名自己的化身。所谓“一落言筌,便失真谛”,N和T的对话,所表达的正是这一对于语言表达限度的体认。对此,禅宗的方式是“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然而,作为一个小说家,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悖论:如何以有限的颜色,来表现“无量的色相”。在《桥》中,废名示范了一些方式,其文体的“空白”与“跳跃”,以及以象征化的方式对人物内心活动的呈现,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有与无、繁与简之间的辩证。
废名在《桥》中所实验的这种文体和手法,与他的艺术观亦息息相关。对此,废名在《桥》中也有不少自我指涉之处。《桥》上篇写的是小林儿时的生活,废名多次想表达的一个观念是,在儿童的世界里,艺术与现实的界限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可以轻易跨越的。如《井》中,小林的姐姐埋怨他在扇子上画的石头是“地下的石头,不是画上的石头”,小林则回应道:“那么——它会把你的扇子压破”;又如《“送牛”》中,小林试图偷拿寿星面前的供桃,被姐姐窥破后,则辩称“我要偷寿星老头子手上的桃子”。在儿童的思维里,画中的世界(连同影子里的、夜里的、梦中的、镜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并没有划出鲜明的界限,二者之间似乎可以来去无碍。如果我们联想到废名在《说梦》一文中,曾将文章和艺术的世界比作“梦”的世界,那么,他在《桥》中所表露的这种“艺术观”,可以解释他对于“文章之美”的偏爱,即他的文章并不追求对于现实世界的“及物性”,而是更为关注文字或者说文章本身的美感与自足性,因为“文章”的世界,并不比现实世界缺少生动性或真实性。
《桥》的下篇写的是成年之后的小林,但小林本质上乃是一位诗人。我们可以看到,他特别钟情于一些临界的意象,如时间的临界——黄昏,空间的临界——坟、塔、桥,等等。这些对于临界意象的描写,是《桥》中格外迷人的段落。如写到“黄昏”:
天上现了几颗星。河却还不是那样的阔,叫此岸已经看见彼岸的夜,河之外——如果真要画它,沙,树,尚算得作黄昏里的东西。山——对面是有山的,做了这个horizon的极限,有意的望远些,说看山……②同上,第489页。
又如“坟”:
小林又看坟。
“谁能平白的砌出这样的花台呢?‘死’是人生最好的装饰。……坟对于我确同山一样是大地的景致。”③废名:《桥·清明》,《废名集》第1卷,第500页。
“黄昏”是日与夜的临界,废名却从空间上着眼,从河两岸的景色写起;而写到“坟”这一空间意象时,却又带入了时间的维度,即生与死的临界。
很明显,对这些临界意象做出诗人般冥想的小林,同样是作者废名的化身。废名自己对于“黄昏”“坟”这些临界意象,亦有着特殊的迷恋。在《说梦》中,废名曾说,“我有一个时候非常之爱黄昏”,其《竹林的故事》即原拟以“黄昏”为名,并以希腊女诗人萨福(Sappho)的歌作为卷头语:“黄昏啊,你招回一切,光明的早晨所驱散的一切,你招回绵羊,招回山羊,招回小孩到母亲的旁边。”④废名:《说梦》,《废名集》第3卷,第1154页。而在《桥》的序言中,废名也曾指出,这部小说他一度拟题为《塔》——埋葬佛骨的塔,与坟一样,亦是以“死”来装饰“生”的“大地的景致”。废名最终作为小说题名的“桥”,则是此岸与彼岸的交界。在《莫须有先生传》中,废名曾借莫须有先生之口道出他对“桥”的特殊感情:
好比我最喜欢过桥,又有点怕,那个小人儿站在桥上的影子,那个灵魂,是我不是我,是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殊为超出我的画家的本领之外了。①废名:《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看顶戴》,《废名集》第2卷,第698页。
《桥》所描绘的,正是这样一个能够在现实与幻想、日与夜、生与死、此岸与彼岸之间自由穿梭的儿童和诗人的世界。在1935年的《诗及信》一文中,废名有一首和鹤西的诗,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梦与醒、死与生两个世界同时共存的奇妙想象:
我是从一个梦里醒来,
看见我这个屋子的灯光真亮,
原来我刚才自己慢慢的把一个现实的世界走开了
大约只能同死之走开生一样,——
你能说这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么?
我的妻也睡在那壁,
我的小女儿也睡在那壁,
于是我讶着我的灯的光明,
讶着我的坟一样的床,
我将分明的走进两个世界,
我又稀罕这两个世界将完全是新的,
还是同死一样的梦呢?
还是梦一样的光明之明日?②废名:《诗及信》,《废名集》第3卷,第1328-1329页。
在此,诗人成了梦与醒、死与生、幻想与现实两个世界之间的“通灵者”;而“黄昏”“坟”“塔”“桥”这些连接日与夜、生与死的临界意象,则可以视为作为“通灵者”的诗人再好不过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废名的小说《桥》,同时也可以读作作者的一部诗学宣言。
在《桥》的下篇,废名曾借小林之口说道:“我感不到人生如梦的真实,但感到梦的真实与美。”③废名:《桥·塔》,《废名集》第1卷,第564页。这句话通常被视作《桥》的诗学纲领。对此,废名后来在《阿赖耶识论》中还有一番哲学式的表述:
其实五官并不是绝对的实在,正是要用理智去规定的。那么梦为什么不是实在呢?梦应同记忆一样是实在,都是可以用理智去规定的。梦与记忆在佛书上是第六识即意识作用,第六识是心的一件,犹如花或叶是树的一件。……梦与记忆都是可经验的对象,不是“虚空”。④废名:《阿赖耶识论·序》,《废名集》第4卷,第1836页。
所谓“阿赖耶识”,在废名这里,即是包含了第六识在内的“心”的代名词。在废名看来,梦与记忆的世界,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感官所感知的世界,具有同样的“实在”性。这番关于“阿赖耶识”的“实在”论,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桥》的诗学特质:在废名这里,无论是五官所见的实象,还是梦与记忆中的虚象,皆是作为“实在”来描写的,不是“虚空”。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常常是实象与虚象交叠共存,并互相濡染,产生交互感应——这正是其小说中意象 “东跳西跳”的内在逻辑,亦是其象征手法的理论依凭。在这个意义上,废名小说的“文章之美”,也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形式的概念,它本身就是“实在”的内容与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