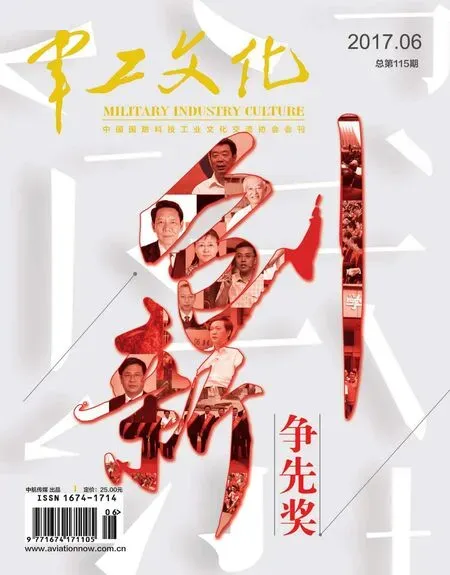一张 黑白照片的辉煌记忆
2017-12-07吴明静
文/吴明静
一张 黑白照片的辉煌记忆
文/吴明静
第一颗氢弹洁白的蘑菇云升腾之后50年,仅以此照片,邀请所有的爱国之士,共享核武器人骄傲而坚定的牺牲,共享这一份隐秘而博大的幸福。
有一张老照片,叫《14号楼灯火辉煌》,这是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科研人员很熟悉的照片。在暗黑的天幕下,一个个方形的光块勾勒出一幢极普通的四层办公楼。整个画面只有黑白二色,没有人物,也不见花草树木或者什么园林景致,一眼看去,这张照片可以说是平淡无奇。
这张不起眼的照片背后蕴含着令九所人为之自豪的一段史实,它记录了1965年氢弹理论攻关时期的九所。
今年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人们总是赞叹,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在五个核大国中速度最快。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氢弹理论突破过程异常艰难,各方面的科研工作非常艰辛枯燥。照片记录的1965年,正是理论研究最为艰难的时候。
照片中的14号楼就是当年九所的科研办公楼。曾在这幢楼里工作过的李德元先生至今清晰地记得,1965年的北京,北太平庄以北还很荒凉,夜深了,九所人还在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灯火通明的14号楼,从很远处就可以看见。作为亲历者,每每想起这灯火辉煌的一幕,这位耄耋老者都激动不已、感慨万千。

↑《14号楼灯火辉煌》
在这张照片拍摄前一年,我国刚刚实现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毛主席说,原子弹有了,氢弹也要快。可是氢弹和原子弹不一样,原子弹是裂变反应,氢弹是聚变反应,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制造技术上,氢弹都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而且,不同于原子弹研制初期还得到过苏联人的一点帮助,氢弹的研制可谓披荆斩棘、白手起家,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当时,在彭桓武先生的带领下,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三位科学家,各自率一个研究小组,从不同方向对氢弹原理展开猛攻。人们提出过很多设想,可惜一条条道路,一时间都没打通。
当年,14号楼前,经常会停着一辆红色的奔驰牌小轿车,九所人一看见这辆当时很少见的小轿车就知道,西尧部长又来了。
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西尧,几乎每周都会来九所实地了解科研进展。
研究进展不畅,刘西尧副部长很着急。一次西尧部长在会上大声说“各人把兜里的东西掏出来!”可是,没有就是没有。坐在西尧部长面前的,是一批十分严谨的科学家,没有可靠的论据,谁也不会在领导面前夸夸其谈,显摆自己。
有一天,红色奔驰车又停在了楼门口,刘西尧副部长专门来组织学习会,理论部的主任、副主任以及各研究室主任都要参加,学习内容就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大家试图用哲学引领科研工作走出困境。后来,实践论和矛盾论果真在核武器理论研究和工程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前进道路上的拦路石如此庞大,但在1965年,九所人攻坚克难的意志极其坚定,大家憋足了劲,要赶在法国人之前爆炸氢弹。
遇到困难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发扬学术民主、集中集体智慧。这也是九所突破掌握第一颗原子弹原理的成功经验。
那时,号称“鸣放会”的学术讨论会经常举行。在14号楼的三楼、四楼的大会议室,几乎每天都有讨论。不论大专家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每个人都可以走上台去发言,每个人也可以对别人的设想提出不同意见。彭桓武等大科学家特别鼓励年轻人发表不同看法。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副院长孙锦山刚刚参加工作,就某个部件的构型大胆发言,赢得专家表扬,说新来的同志有想法,很好!
除了民主大讨论,部领导还安排专家讲课,目的是进一步提高科研人员理论水平。彭桓武、邓稼先、于敏、周光召都为科研人员作报告,在所内掀起了空前热烈的学习热潮。邓稼先等人在那个时期撰写的等离子体物理的讲义至今还留存在九所档案室。刘恭梁记得,于敏的讲座尤为受欢迎,他第二天讲课,头天晚上就有人搬椅子占座位。
所以,无论白天黑夜,14号楼总是洋溢着一股工作热情。科研人员加班加点,争分夺秒,以至于当时的室主任和支部书记有一项重要任务:晚上十点,一定要规劝科研人员下班。
每天晚上,室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一间办公室一间办公室巡视,苦苦劝说科研人员早点回家休息。许多人却不过情面,假装离开了,在楼下转悠一圈,瞅个空子,又回到办公室继续挑灯夜战。
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试验的圆满成功,九所人要严守保密纪律,只能压抑住心中的激动,但有一些北京航空学院的师生跑到九所大门口,悄悄写下:祖国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
贺贤土院士和刘恭梁研究员当年都是经常和室主任玩捉迷藏的年轻人,回忆往事,他们异口同声说:不觉得累啊。
就在这一年的10月,于敏率领研究小组到上海出差,利用上海的计算机资源继续攻关。于敏先生对计算结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深厚的学养使他敏锐察觉到氢弹原理突破的关键,在后来的三个月里,他带领科研人员多方计算,反复讨论,终于形成了一套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理论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好消息传到北京,14号楼里群情振奋!大家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立即调整研究方向,组织了新的攻关——那时的科研人员没有门户之见,更没有名利纠葛,人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奋斗,真正将个人融入到集体事业中。
但是理论方案毕竟还是纸上的,还需要经过试验验证。1966年12月底从隆冬严寒的罗布泊传来又一个喜讯。九所人欢欣鼓舞,因为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氢弹全当量试验就有把握了。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贺贤土清楚地记得,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试验的圆满成功,人民日报两次发号外,外边街道上群众欢呼雀跃,自发游行,研究所内却平静如常——因为九所人要严守保密纪律,只能压抑住心中的激动,装作若无其事。但有一些北京航空学院的师生跑到九所大门口,悄悄地在水泥地面上写下粉笔字:祖国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
另一个十分现实的情况是:自九所诞生之日起,一项又一项重大的国防科研任务总是安排得十分密集。氢弹原理突破了,九所科研人员立即转向了新的研究任务。6月17日的胜利带来全国又一次狂欢庆祝时,包括于敏先生在内的一批科研人员,已经安坐书斋,埋头于新的更为艰巨的工作。

↑《灯火辉煌,北京花园路三号院,1965年》
1965年的艰难攻关完美体现了九所的精神气质,氢弹突破固然令人狂喜,这张黑白照片所隐含的胜利曙光到来之前的勃发张力更令人血脉沸腾。
李德元先生后来担任过九所所长,他曾经不无感慨地说:九所做理论研究,讲起来很激动人心,很高大上,但实际上很枯燥单调,那是一帮子耐得住寂寞的人。他们无非整天就是埋头“算题”,然后把计算结果细心地、一点一点地点在坐标纸上供大家讨论,很难产生一般电视剧和电影所追求的戏剧效果。
从照片上也可以看出,14号楼谈不上有什么建筑特色。因为保密的缘故,九所办公楼的样式类似厂房。五十多年前,从单位大门口往里面看,第一眼所见是一个高高的烟囱,颇能迷惑和遮挡视线。
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席卷到九所时,狂热的政治空气重压在14号楼,黄祖洽、秦元勋等理论部副主任相继被打倒,他们每天早早站在楼洞门口,接受群众批斗。不过,等上班时间一到,他们就摘下身上挂着的沉重的大牌子,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和精神,立即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
李德元也遭到批斗,造反派让他去打扫十四号楼三楼的厕所。李德元很得意地说:我打扫厕所又快又干净,然后我就在楼梯口的一张旧桌子上写检查,检查写完了我还继续算题。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压不弯,折不断,背负重担也要挺直向上。他们用坚定执着、用埋头苦干回答了什么叫无所畏惧、什么叫一往无前。
回忆过去,李德元十分感慨:氢弹研制能够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获得重大突破,中央专委的决策太关键了,西尧部长的当机立断太重要了,1965年的加快攻关太及时了。
他认为,1965年的艰难攻关完美体现了九所的精神气质,氢弹突破固然令人狂喜,这张黑白照片所隐含的胜利曙光到来之前的勃发张力更令人血脉沸腾。
那真是一段慷慨激昂的往事,一种奔腾火热的生活,一份舍我其谁的责任与担当。
楼仍在,人常新。如今,一代代科研人员接过 “两弹”事业的旗帜,继续默默坚守武器研究。50年来,尽管时代变迁带来了多元价值理念的冲击,禁核试后,九所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但是,彭桓武先生“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的赠言为九所科研文化打牢了坚实的根基。九所人传承了前辈科学家科学求实的风范,团结协作,报效祖国,履行使命。科技强国、科技强军,始终是九所人的目标牵引。
为氢弹理论突破立下最大功绩的于敏先生,谢绝“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号。他在九十高龄之际,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这位睿智的学者谦虚地说:核武器是千千万万人共同的事业,我只是献出了自己微薄的力量,国家选择了我,我很幸运。
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表示:这件事(核武器)做成功了,我为它死了都值得。
人,要为理想和信念活着。人生如何没有遗憾?什么事情算得上“值得”?“两弹”事业前辈们用自己的一生做出了最真切的回答。
第一颗氢弹洁白的蘑菇云升腾之后50年,仅以此照片,邀请所有的爱国之士,邀请所有国防科技战线的从业者,共享核武器人骄傲而坚定的牺牲,共享这一份隐秘而博大的幸福。
2017年5月,九所采取图片处理技术,重新创作摄影作品《灯火辉煌,北京花园路三号院,1965年》,纪念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50周年,还原历史细节,传承两弹精神。
(作者单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猜你喜欢
杂志排行
军工文化的其它文章
- 长大后,我就成为了你
- 文苑
- ——我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试爆成功的故事">炫目的"太阳"
——我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试爆成功的故事 - 奠定国家安全与大国地位的基石『两颗』研制的故事
- 我送祖国第一颗卫星上天背后的故事
- 领航,在民族工业复兴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