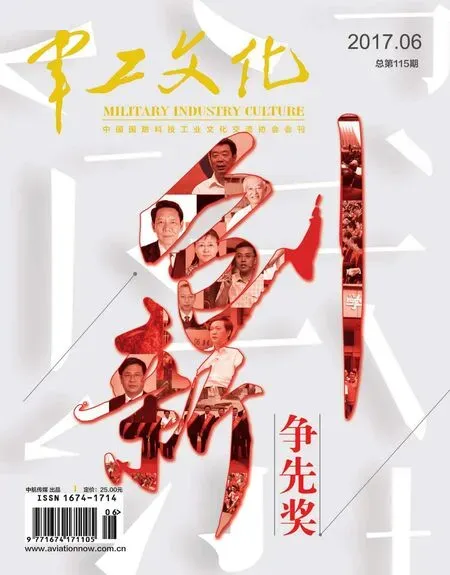炫目的"太阳"
——我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试爆成功的故事
2017-12-07杨新英
文/杨新英
炫目的"太阳"
——我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试爆成功的故事
文/杨新英
我们不可忘记今日的和平环境,民族魂的不屈意志将会激励我们挺起脊梁,坚定前行。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原子弹的试爆成功,只是中国“两弹一艇”强国梦的首幕。
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计划设想的汇报后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于是,一个攻克氢弹研制技术的任务,就摆在了核工业科研人员的面前。
一片空白造氢弹
如果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曾借鉴了苏联的一些技术和经验的话,而氢弹的研制则完全是自力更生、从头摸索。
1960年12月的一个早晨。钱三强办公室里来了一位30岁的年轻人。他叫黄祖洽,是原子能研究所的第四研究室的一个组长。
钱三强用信任的目光看着这位1950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物理学家,平静的语气中透几分严肃:
“小黄,今天叫你来,是要告诉你部党组的一个重要决定。为了早日掌握氢弹技术,我们要组织一个轻核理论小组,先行一步,对氢弹的作用原理和各种物理过程,可行的结构进行探索、研究。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啦!”
黄祖洽专注地听着钱三强的叮嘱,不由得挺起胸膛。
钱三强又特意叮嘱说:“你原来那个组叫47组,这个轻核理论组就叫470组吧,要特别注意保密。”
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一群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
1961年初,于敏加入氢弹探索的行列。这对于于敏来说,是又一次改行。
1951年,于敏从北京大学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变自己追求几年的“量子理论”的研究,从头学起,去搞原子核理论。十年寒窗,于敏发表专著、论文20多篇。钱三强说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从一个基础性很强的科研领域,突然转到氢弹原理这个应用性很强的领域,于敏很快就显示了新的才华。
一次,国外刊物报道了一种新的截面,这个截面的数据非常理想,大家都很感兴趣。但要重复这个实验,不仅需要几百万人民币,还要花两三年的时间。
于敏苦苦思索了两天,做了详细的分析,得出了结论。他对同事们说:“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么个截面,而且任何其他反应截面都达不到这个数。我们根本没必要用那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去重复这个实验。”
过了一段时间,外刊又报道,有实验证明那个报道是假的。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这些年轻的探索者出发的阵地只是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他们手中的主要兵器只是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和一块黑板。
探索者的队伍不断扩大,最多时曾达40多人。这期间,钱三强又委派黄祖洽兼任九所物理理论部的部分工作。钱三强说:“这里的情况你可以带到那边去,但那边的情况不能带到这里来。”因此,人们称黄祖洽是个“半导体”。
一篇又一篇论文交到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山头被绞尽脑汁、呕心沥血的科学勇士攻克。4年中,黄祖洽、于敏和同志们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
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热火朝天的年代,位于北京花园路5号的核武器研究所那座灰楼里,灯火通明。从老一辈科学家到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人人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1965年1月,为了加强氢弹理论的攻关力量,二机部决定将原子能研究所的黄祖洽、于敏等31人调到核武器研究所。这样,氢弹的理论研究队伍汇聚一起,形成了强有力的科研攻关拳头。
这些年轻的探索者出发的阵地只是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他们手中的主要兵器只是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和一块黑板。一篇又一篇论文交到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山头被绞尽脑汁、呕心沥血的科学勇士攻克。

↑待装氢弹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刘杰向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汇报说:“三年到五年能爆炸氢弹。”周恩来说:“三年才能爆炸氢弹,太慢了,要快!”周恩来指示二机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并注意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研制和试验的关系。
1965年2月,中央专委批准了二机部报的计划,确定力争 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爆炸试验。在朱光亚、彭桓武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科技人员总结前一段的研究工作,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工作的大纲;第一步继续进行探索研究,突破氢弹原理;第二步完成质量、威力与核武器使用要求相应的热核弹头的理论设计。
准确完整的核数据,是核装置设计的重要依据。核武器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在文献研究中发现记载数据很不一致。原子能研究所何泽慧率领30余名科技人员,在丁大钊等曾进行过的关于轻核反应的科研工作基础上,经过半年左右的实验研究,对热核材料的核反应截面进行了测量,获得了可靠的实验数据。
手里是价值千百倍于黄金的珍物,面前是生命和荣辱都系于那一响的千军万马,背后是领导信任的目光,好像整个国家的份量都压到了他们的背上。他们的心脏究竟有多大的承受力啊!

↑氢弹投放靶心
1965年9月,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赴上海华东计算所研究所,利用该所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进行“加强弹”的优化设计,争取通过加大尺寸,多装热核材料,达到有一定聚变比的百万吨级当量威力的核装置。
到达上海后,为了争取时间,搞物理的、搞数学的,还有科研辅助人员,混合编组排班,昼夜不停,轮流在机房工作,很快计算出一批模型。从计算结果看,威力可以达到百万吨级梯恩梯当量,但是聚变份额都比较低,说明其中的热核材料并没有得到充分燃烧。
面对这批计算结果,考虑到此次来上海的不少年轻人,缺乏有关氢弹的基础知识和科研工作的实践经验。于敏从现象到本质,分析了热核材料不能自持燃烧的外因和内因。认识到温度只是热核材料燃烧的外因起的作用,而要热核材料自持充分燃烧起来,必须依靠增强热核材料密度这个内因发挥作用才能做到。研究工作重点从提高温度转到增强密度上来,利用原子弹的辐射能压缩热核材料,达到理想的密度,形成了氢弹的新原理,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基本完整的方案。
经过了100来天的奋战,一个有关能量的关键点有了突破。于敏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
20多年后,当人们问于敏是怎样攻克氢弹原理的,于敏回答:“研究氢弹原理是一批科学工作者,参加设计、实验的人就更多了。要说攻关,是集体攻关,我只是其中一个卒子。”
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
1966年12月28日12时,在聂荣臻元帅亲自主持下,氢弹原理试验装置按时起爆,国外报道爆炸威力达到20~30万吨梯恩梯当量,实际这是一次低威力氢弹地面试验,试验完全成功,表明中国已经掌握了氢弹原理。
随着强烈的闪光,蘑菇云翻滚着直冲九霄。
于敏院士后来回忆说:“看到蘑菇云了,知道爆炸当量是不错的,但心仍然是悬着。我跟着唐孝威、吕敏他们,用挑剔的眼光看他们速报测试结果,可就是挑不出刺来,各种干扰的因素都想到了,排除了,这时我才完全信服了,我们的氢弹试验成功了!
我到罗布泊不下十次,每次做这种试验,成功不成功?牵涉那么多人,花那么多钱,政治上影响那么大,心总是提在嗓子眼上。记得有一次试验,当量当时知道了,在第二天才能知道物理试验的具体结果,会不会没有结果呢?那一夜睡不着,翻腾得厉害。真担心啊!心慌、心跳、紧张、不安,非常之难受!我躺在床上也不好意思叫人,强忍着,现在想起来真后怕,那时我是40多岁,如果晚几年,心脏就会受不了。第二天,还好,大部分成果还是拿到了,心脏也好了……”
几十年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手里是价值千百倍于黄金的珍物,面前是生命和荣辱都系于那一响的千军万马,背后是领导信任的目光,常常是好像整个国家的份量都压到了他们的背上。他们的心脏究竟有多大的承受力啊!
九死不悔的忠贞,舍生忘我的献身,这就是涌动在中国核科学家身上的血脉,这是一种比核爆炸更强大的力量,这是一种比原子弹的影响更为久远的精神。
“给赫鲁晓夫发一吨重的勋章”
1967年6月14日清晨,北京西郊机场一架飞机腾空而起,向西北飞去。下午1时50分,飞机降落在新疆的马兰机场。
这是聂荣臻在八个月的时间里第三次飞往罗布泊核试验基地。此行他正发着烧,是抱病执行任务的。
这时的新疆马兰机场,笼罩在紧张而忙碌的气氛中。担任氢弹空投试验任务的轰-6甲型飞机静静地停在停机坪上。

↑氢弹烟云
6月16日晚上,聂荣臻赶赴核试验场区,住到场区的开屏村,这里离指挥所约30公里。秘书回忆说:“我们赶到白云岗快到10点了,但天还没有黑,我们出去散步。他们讲那里蚊子厉害,盯上你后,无论如何都赶不走,非要咬你,除非你把它打死。
张蕴钰、张震寰、李觉等领导向聂帅汇报了有关情况。随后,他们向聂帅建议,正式试验定在17日上午8时整,聂帅表示同意。
第二天凌晨7时,天还没亮,聂师便乘车来到指挥所,指挥所设在距爆心西55公里的白云岗。到达指挥所时,天已破晓。早晨的天气一片晴朗,确是试验的难得的好天气。试验场上,一切准备就绪,人们都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期待着即将发生的一切。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飞机起飞。
担任这架飞机机长的徐克江回忆说:“那一天晚上我们都没睡觉。上级命令让我们提前睡觉,好好休息,可是我和同志们躺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4点钟,天还不亮我们就起床了,来到机场,一遍又一遍检查飞机上的相关设备,默念自己的操作程序,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上午7时,担任空投任务的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轰-6甲型飞机从马兰机场起飞,开始了氢弹空投试验。
聂荣臻元帅始终站在参观场最高的山丘上。他不时地看看手表,又看看蓝天。
8时整,徐克江驾驶飞机进入空投区。
指挥员立即发出清亮而庄重的报时令:“……5、4、3、2、1,起爆!”
……
半分钟过后,仍无声响。
飞机在空中盘旋。
氢弹没有投下。
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是第一领航员孙福长,后来在接受电视片《共和国之恋》摄制组采访时说:“一是由于当时我的心情比较紧张,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没能在预定的8点准时投下……”
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从电话中得知这一情况,随即指示罗布泊指挥所:“请告诉飞行员,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
机长徐克江要求再次投弹。
徐克江回忆说:“关键是要稳定大家的情绪,互相提醒,不要紧张,不要再忘动作。我重点是协同、进入,保持高度;第二次一定要投好。”
试验场的上空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圆柱体——这就是中国第一颗氢弹——它在湛蓝的天空中被高速飞行的飞机抛出,犹如蔚蓝色海洋中一个浮沉着的深水炸弹;它使劲地拽着降落伞,摇晃飘飞,寻觅,滑行……越来越远,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白点,一个只能凭感觉而不能凭视觉捕捉的白点。突然——白光!白光,无所不在的白光,亮彻天宇的白光!
就在人们因强烈的亮光不得不眯起眼睛的刹那间,白光中现出了金色,犹如一个新生的更为壮观的炫目的“太阳”。火球的上方渐渐出现了草帽形的白色云团,云团悠悠地旋着、旋着,变成了一朵白色的蘑菇云。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我国只用了2年8个月时间。
氢弹爆炸成功后,毛主席在接见军训会议代表时高兴地说:我们搞原子弹、导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要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我们不可忘记今日的和平环境,是大国工匠英雄们毕生的付出,尊重英雄,传承英雄……民族魂的不屈意志将会激励我们挺起脊梁坚定前行。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
那山、那水、那人、那事、那一切动人的故事,都将成为美丽的传奇。
(作者单位:《中国核工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