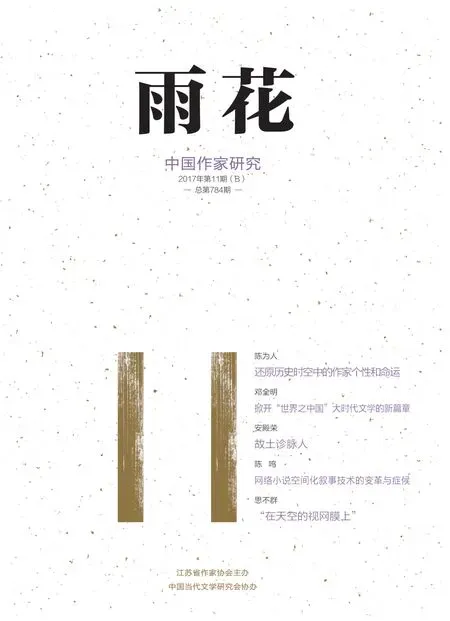“在天空的视网膜上”
——论杨隐诗歌
2017-12-01思不群
■ 思不群
杨隐是我的多年同窗。在诗歌写作上,他又是我多年相伴而行的同道诗友。人生本无趣,但因为有了朋友,有了同行者,这难挨的时日便多了一份快意,多了一份醇味。当我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十年前我们在苏大后庄谈诗论文、谈古论今的一个个瞬间又浮上了心头,它们构成了我三年研究生读书生涯最值得回忆的片断。那时我们还是研一,正在大量恶补理论著作和经典作品,一次次从图书馆搬回一摞摞著作。我们读累了、读烦了,就跑到隔壁对方寝室,交流各自喜欢的诗歌、最近读到的佳作,有时也拿出自己新写的诗作请对方品读、挑刺。我们往往是对方诗作的第一读者,因此,他的绝大多数诗歌我都耳熟能详。杨隐在诗歌写作上是虔诚的,也是勤奋的,他像琢玉者一样,既善借他山之石,又苦练内心之力,孜孜以求,用那些仔细打磨后纯美反光的语言,向我们呈现出汉语之美、诗歌之美。
一、细节的暴动
杨隐是一个多愁善感、略带忧郁的诗人,这种忧郁为他的诗歌带来了一种基调,一种罩着旧时光的美。这个忧郁的人,睁大了眼睛,静观这世界的变幻和人世的悲欢。他的眼睛总是看向低处,看向细枝末节,在一朵花的生长过程中,他只关注“它在一微米一微米地喝水”的样子,“在一整条河里,唯独对这一滴水一见钟情”(《一滴水在流》)。在这个大规模、大数据、大狂欢的时代,杨隐却情愿把眼光放低,专注于那些小小的灰尘,独自品味记忆中那些笑脸和汗水、那些思念与眼泪。南朝齐王僧虔在《笔意赞》中曾说过:“纤微向背,毫发死生”,虽然他说的是书法,但是我认为它适用于所有的艺术。正是那些幽微末节,显现出一个艺术家的与众不同之处,显现出他独到的眼光和品质,甚至能让人将他从众人中识别出来。诗人都是回忆的俘虏,容易被过去的声音和瞬间所带走。诗人消失了,一个个画面从深海浮出了水面,披泻着月光散发出美丽和召唤。然而,月亮带来了潮起潮落,带来了一次次的冲刷内心崖岸的波浪。在那些不可避免的决堤的时刻,他捉笔成文,如一个鬼魂附身的首领,发动那些沉睡的细节举起草籽与麦芒,联手发起了暴动,一举将诗意收入囊中。在这些诗歌中,他用语言的冰块冻结了时间,并用触觉的镊子将时间无限拉长,然后在感叹与祝酬中将它编织成一个密致、结实的结晶体。
故乡
首先你得把这个词
从泥土里拔出来
慢慢的
不要太用力
再用贴身的小刀轻轻赐净根部
注意:要绝对干净
残留一粒泥土也足以击瞎你的眼睛
然后你坐下来
用一盆清水覆盖它
看它舒展开身体,慢慢沉下去
这时候,你不要说话
像另一个溺水者
沉默,足以化解你们与生俱来的敌意
《故乡》这是一个怀乡病者的自我解剖实验,他将这些用童年、回忆、亲情配制而成的“故乡”放在显微镜下,让我们看清它的根须和叶脉。故乡深埋,那些回忆的泥土层层覆盖,从三十年的泥土和三千里的马蹄声中慢慢“拔出”,怀乡病者惊声尖叫,“溺水”的恐惧阵阵袭来,在异国他乡的手足无措中,他独自抚摸着这温润的“实验品”,陷入了沉默。“故乡”不是一个地方,也不是一个心理空间,而是一个时间的储存器,一念孤悬地垂挂在记忆的底部,当我们快步向前时,在不经意间,就会晃动它,甚至在一阵不期而来的创痛中将它连根拔出。幸好,这时止痛药已经来到:
桃木梳子
从你捉住梳子顺发的那一瞬
往后退三个月
那时它还在木匠手里
往后退三年
那时桃花盛开,红颜遍地
往后退三十年
还没有你我
它只是一粒种子,在泥土的胎中分娩
诗人多半都是神秘主义者,他们相信臆造的必然,相信身不由己,相信一只隐形之手最初的安排。当初的相遇或许是偶然,但诗人从心灵出发推导出必然的路径。正如沈从文在《边城》中说的“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在这首诗中,诗人代替上帝出现,说出了爱的秘密,说出了爱的必然来到。站在今日的晨光中,诗人在一步步地回首,“三个月”前、“三年”前和“三十年”前,一个个瞬间忽闪而过,那仿佛是丘比特写给他的一封封确认函,并由此回溯,成功地从上帝手中获得了首肯。诗歌本身很简单,随着时间的倒退,那是根据剧情需要进行的重新编排,一帧帧画面缓缓推出,在最后所到达的地方却仿佛与出发点天然相连。从诗歌技巧上来说,它是充足而有效的,让我们在陪同诗人颔首回望中同样获得了爱的充注与照耀。2009年我曾写过一首《童年瓮》,与此有相似之处:
从三十岁开始往回
倒退。退一次
探瓮取滴原初之蜜,
死皮掉一层,茶味
浓一层。
退到年方二八,总角相伴
天朗气清,春溪奔流。
或者相反,退到五十岁,风平浪静。
到最后,速度越来越快。
被一次次掏空的
将瓮浓浓地充满。
《桃木梳子》因为爱的自信给予了诗歌一种正向的力量感和顺利到达的畅快感,而《童年瓮》因为一种内心的纠缠、因为经验相互之间的胶着,呈现一种混杂的景象。但是,由于时间的介入和沉淀,两首诗最后都力求达致一种内在的充盈和满足。杨隐曾在读到陈先发的《茅山格物九章》时说:“诗歌就是要说出一些神秘,在情绪、思想的幽微之处发端。”这是杨隐诗歌的特点,他总是从细节出发,在细部慢慢积蓄力量,在细节的相互拱卫、联结和抬升中,忽然将一种崭新的诗意端现在人们面前。比如写那些在街头揽活民工的《在太平街》:
一张一张被生活擦旧的面孔
聚在太平街的边上
扁担、铁锹、大锤子
以及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以及憨厚的微笑
一丝不苟的
在这个清冷的早晨
等待包工头的挑选
这一节的白描很平实,不动声色,一个平常的早晨,小镇的街头就这样展开。这仿佛是一幅古典的风俗画,画家远远地隐在后面,只有一些微微的体温,隔着纸背传来,需要敏感的心灵温度计才能测度。但当波浪一层一层推涌,它速度越来越快,瞬间就到达了顶峰:
他们站着
有时倾斜,像一片片快要被风吹走的树叶
有时笔直,像一枚枚未及被敲进泥土的钉子
卡尔维诺曾在《未来文学千年备忘录》一开首便详细论述了“轻逸”的价值,他所说的“轻”是“一种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它是“超脱了世界之沉重哲学家诗人那机敏的骤然跳跃”。我以为这几句诗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它是建基于沉重和洞悉之上的轻,从“扁担、铁锹、大锤子”中抽身而出,从“等待”中突围而出,在一棵树的枝头,一种生命之轻哗哗作响。当我们读诗时,不仅仅是在读眼前的诗作,我们还会不自觉地调动所有的经验、回忆与想像来对比、确证或者区分。所以瓦雷里说:诗歌要像一只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羽毛。这不仅仅是质感和想象力,还有经验和回忆。在这首诗里,杨隐直接越过了羽毛,将风中的鸟儿呈现出来。
二、诗歌相对论
爱是直接的,而时间和空间总是相对的。推广开来说,你与我是相对的,青山与大漠是相对的,沉默与哭泣是相对的,怀念与拒绝也是相对的。由于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刻度,有了相互的记录和回放,我们每一个内在的小宇宙,在空间和质量的相互作用下,也有着自己大爆炸的时刻,有着从未止息的核聚变和燃烧的火焰。这是灵魂的广义相对论。
一个相对论的中午
灰尘一样,这是我小小的爱
一个中午,我看着它们
在光线里跳舞
那么欢快,那么恣意,那么
不顾一切
像宇宙洪荒,那么多破碎的星球
在大爆炸后旋转
牵引它们的力量,无限大
阅读这首诗我们需要天文望远镜,从聚焦于一个点、一个原子核,忽然大踏步后退,退出宇宙,站在宇宙的起始点上,静观那些碰撞的焰火,自我的爆裂,恒星在坍缩后一举将行星吞没。帕特里克·莫迪亚克曾在《地平线》中写道:“他清楚地感到,在确切的事件和熟悉的面孔后面,存在着所有已变成暗物质的东西:短暂的相遇,没有赴约的约会,丢失的信件,记在以前一本通讯录里但你已忘记的人名和电话号码,以及你以前曾迎面相遇的男男女女,但你却不知道有过这回事。”那些灰尘、那些暗物质,就是我们破碎心事的前身,就是我们独自站在星空下,对着遥远的天穹默默无言中咽下的口水。那些暗自握紧双拳的忍耐,那些胎死腹中的莫名冲动,只有口水咽下时咕咚做响的喉咙知道,并记下了每一个时刻。“小小”的灰尘之爱,却受到巨大天体的“牵引”,高速运转和飞行,仿佛不由自主,仿佛遽然而逝。在优雅、腼腆的另一面,杨隐自有他的力量和手段。然而,在目睹宇宙洪荒、尘埃飞舞之后,我们仍然会把眼光收回,重新注视起那小小的爱的星球。而这时,由于有了遥远的广大背景,有了那些朦胧存在的信息,我们再注视的眼光变得不一样了。这是语言牵引的力量,这是诗歌的相对论。卞之琳的《断章》是诗歌相对论的经典之作,那是两两相对、智性静观中生发出的时空倒错,它是快乐的智性游戏。太白则是诗歌相对论的王者,《独坐敬亭山》与大块对坐,与山川对谈;《月下独酌》更进一步,用想象塑造出一个通灵通神的相对者,“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几乎不需要对待之物,他强大的分身术,可以无中生有,隔空取物,对月祝酬,天地星月,流云花影,都被他随手取来,借酒之杯,浇己之怀。而杨隐也写出了另一种相对论:
在西湖
夜色沉沉,运送鬼魂的棺木还在路上
白茫茫的湖水现在看不见了
但我知道,它还在,就在它原来在的地方
容颜不改
独自站了很久,安静得像近旁睡着的一株细柳
天光将至,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事物
马上就要现身了
我一直有个偏见,认为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在艺术效果的呈现方面远远高于其他艺术。因为汉字不仅有音、形、义,具备了音乐的流淌性、建筑的建构性特质和基本稳定的内涵,而且每一个汉字、每个词语身上都背负着多重暗影,都有自己的历史,当它被安排在某一句诗中,这些历史的影子争相走出,仿佛是一场角色众多的戏剧,在相互激发、对质与妥协中,一种崭新的意义被呈现出来。这首诗通过水墨的淡笔细描营造了一种幽魅、神秘的心理氛围,但是诗人的战术是坚壁清野,是围而不打,他没有从正面讨战,而是将那些靠近中心的语词和意象一个个排队出场叫阵,围着那中心不断打转、打转,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那一再隐身者终于坐不住,“马上就要现身了”。而有时,那震惊我们的,正是那现身者:
断章
在天空的视网膜上
月亮的瞳仁放大
又缩小
因为内心的光线
天空因其大而显出月亮之小,天空因其沉静不变显出月亮内心的忧戚、不安。这时我们看见的仿佛是天空巨大的瞳仁,它总是在上面静静的注视,但又时刻准备着用它巨大的云团把月亮的瞳仁紧紧包裹,而们的心灵也随着“放大”又“缩小”的节奏在内心同频共振。这首诗在高度简洁概括中实现了静与动、安宁与不安、抽象与具象的完美凝合。
三、与古人对称
有时,我们的写作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另一个人,那甚至是一个古人,我们的写作就是为了与他对称,为了让他们在今天被重新唤醒,再次介入我们的生活和思考,与我们饮酒、吃茶、谈诗、论文。于是,有了里尔克写给波德莱尔的诗歌,有了布罗茨基要“取悦一个影子”的尝试,有了海子向荷尔德林的致敬之诗。而杨隐则写下了给嵇康的《白玉兰》:
一片一片,白里泛黄,像被美人
手掐过,她们剪掉的小指甲仿佛锈掉
慵懒,随意,漫漫地推开云烟
相隔一夜,玉山崩毁得面目全非
不可断绝的仅仅是魂魄,一寸一寸
与风雨肝胆相照。这样的时辰,醉与不醉
又有何区别?大杯是年,小盏是月
“叔夜兄,请再浮一大白”
读到最后一句,我忽然想起了陈先发的《前世》中那句“梁兄,请了/请了——”。杨隐很喜欢陈先发的诗,这首诗可能受到他的影响,但这并没有减少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的惊喜和激动。除了它,还有《失魂引》:
泡桐开裂,第一个看见它内部的人必成瞎子
大罗山以北,清水一线天,有墓碑一截
两座坟,有龙柏一株,大悲咒一部
饭叶露洗喉的斑文鸟在念
……
“知其白,守其黑,而后因果可成”
在这无人之地,枯云是薄暮的灰烬
躺,是站的灰烬
这些散发着浓郁的历史墨香的诗歌以前他没有向我出示过,这代表着杨隐已经沿着传统文化的河流逆流而上,不断深入文化的源头。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总有一天会走到这一步,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把它作为成熟与否的标志。作为嫁接品种的新诗,它与母系水土的关系始终没有很好解决,时至今日,从写作到批评,我们所操持的语言和理论、思维,仍然是西方传过来的那一套,仍然与我们的文化母体是隔膜的。关于传统,布鲁姆认为是一种“影响的焦虑”,这种“焦虑”是顺时传递的。而T·S·艾略特则认为不仅传统对个人产生影响,相反个人也在参与传统的生成,也会对传统产生影响,使传统的面貌发生变化。在今天T·S·艾略特的这一观点尤其重要。由于20世纪后半叶传统文化的断裂,我们平常所谓的传统其实往往就是呈现出来的传统,是我们所看到的传统,那些没有呈现出来、沉在水面之下的,也许将不再成为传统,或者说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它们并不存在。当然,在新诗写作史上,重返文化母体的探索从未停止,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大批诗人遵从内心的召唤,以自己具体的写作去重新接续传统文化的血脉。比如于坚、杨键、陈先发等诗人,就在自己的诗歌中力图恢复汉诗传统的光彩。杨隐的一些带有古典韵味诗歌的写作,正是对这些前辈诗人努力的呼应。种种迹象表明,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正在苏醒,传统在我们文化和文学中的面目将会越来越清晰。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传统的普照之下,我们所意识到的时间都是传统里的时间。因此,杨隐在诗歌写作上寻求与古人对称的自觉努力,向古典文学源头靠拢,显示了他的诗歌写作的自觉。
萍水相逢
那一年,身负箧囊,手持布伞
行走于江湖
有花折花,有酒饮酒,有朋友交朋友?
亲近一夜明月,只为几句玩笑
如今,“众鸟高飞尽”
我们学会收拢袖筒,放走清风
不伤春,不感冒
如隔水之岸,两不相欠
1932年克罗齐在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美学”条目时写道:“如果拿出任何一篇诗作来考虑,以求确定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人判定它之所以为诗,那么首先就会从中得出两个经常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即一系列形象和使这些形象得以变得栩栩如生的情感。”这首诗从古典情怀入手,但是在整体风格上仍然保持了杨隐一贯的洒脱而又略带伤感的调子。全诗读罢,竟有梁祝同窗共学之感,杨柳清风,河水之渡,潇洒意兴,共趁诗酒年华。“众鸟高飞尽”及时嵌入,妥帖,及时,以一当十,情感与形象二者无间地融合到一起。
在并不算长的十年写作生涯里,杨隐的诗歌追求在一种纯粹、简练而又平和的语言背后,通过独具个人匠心的意象的打磨塑造,在“天空的视网膜上”呈现出最为丰富的诗意。他的写作进步之快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的诗歌面目也愈来愈清晰。当然,杨隐的诗歌写作也有隐忧在,那就是延续多,变化少,没有打开自己写作的多方面的可能性。从我们相识时起,一直到现在,他的诗歌在技艺上进步很大,更圆润、饱满而丰富,越来越呈现出繁复、综合性的一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辨识度。但是他的诗歌在风格上变化不大,总体诗风偏柔、偏软;从内容来说,则偏重于个人情怀和内心的书写,较少关注外部世界和历史纵深。不过,杨隐是聪慧的,他自己也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在尝试进行改变和突破。前不久他发给我一首新作《“给铁犁和诗人的声音镀银”》,这首诗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与他此前的诗歌风格上变化较大,将一种饱满的历史感和人性力量揉合在一起,再辅以他擅长的细节和意象的吸引,有一种深沉的艺术感染力。
我期待着读到杨隐更多更好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