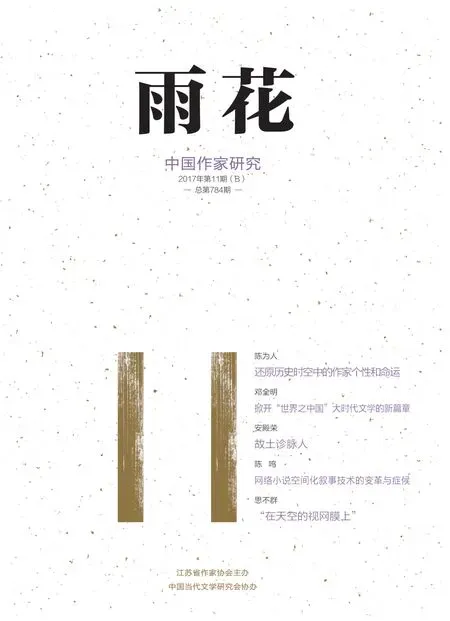“返观与重构”
——评丁帆《中国新文学史》
2017-12-01殷鹏飞
■ 殷鹏飞
钱理群曾在世纪之交的一篇文章中对于21世纪的文学史写作做出这样的预测:“现代作家与作品不可避免的要面临新的严格的筛选;这首先是美学的筛选,对作品内容的历史评价也将更注重其超越意义与价值。”并期待出现“带有强烈个人性的,不受‘趋向’、‘潮流’限制的研究。”①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所做出的努力显然与钱理群十多年前的展望不谋而合。在“彰显治史者个性”的自我期许之下,《中国新文学史》的写作就必然是要以打破既有的文学史论述模式为前提的,同时,也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文学史叙述模式。长时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大多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左翼文学史观下展开各自的论述。尽管,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背景下,特殊历史条件下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似乎随着“重写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一系列“去政治化”的文学研究“事件”的出现得以漂洗和稀释,但是,所遗留下的“鲁郭茅巴老曹”经典作家作品的文学史论述体制却伴随着大量文学史的出版,反而加强了。这并不说1949年后左翼史观下构建的经典文学史叙述模式没有价值,而是说随着这一论述模式的不断重复,成为一种“常态化”的体制之后,其原有的“革命性”的意义便随之消解,文学史写作也就在这样的价值“窄化”中无形间缺失了写作主体的能动精神以及左翼史观原生的内在批判意识。正因如此,《中国新文学史》所提供的经验才格外值得注意,这不仅仅是新的文学史叙述架构所带来的新的写作模式的转变,更是新架构背后所凸显的新的价值问题的展现。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推进和积累,早在30多年前,便已有人感叹“现代文学,拥挤的学科”②,如何在“返观”既往文学研究成果的之余,“重构”新的文学史观便成为《中国新文学史》的当务之急。面对原有的“唯政治”化的文学史观,丁帆先生并没有以80年代“纯文学”氛围下的“去政治化”回避政治,而是以一种更为鲜明价值态度取代原本的“后设”史观,尽量避免由于价值“窄化”造成的对于历史的抹擦,将文学还原到动态的场域之中,力争在“了解之同情”之余,把握价值思考的契机,这便是《中国新文学史》所做出重要尝试。当然,一部“新”文学史的写作必然“牵涉到意识形态、教育制度和学术体制等诸多方面,其中任何一方面的问题,都可能根深蒂固”③,在此意义上讲,《中国新文学史》的写作不仅仅是“新”文学史写作,也是一场看待历史和现实的整体性的观念的变革。
一、“1912作为起点”
1924年,鲁迅在《忽然想到(三)》写道: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④
鲁迅在此想要表达的是对民国建国精神的肯定,以及对民国建政后混乱不堪局面的激愤和无奈。在此,鲁迅是将政治理念与具体的政治实践分开看待的。而《中国新文学史》以中华民国成立作为新文学起点,认为“只有在民国成立之后,西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以‘人’为旨规的价值观,才正式进入到制度层面,确立了合法性,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新文学的核心观念。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发现并正确体认‘人’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反抗‘非人’境遇的历史。”⑤丁帆的野心在《中国新文学史》的开头综述部分其实就已昭然若揭,以中华民国建政作为起点是虚,以民国肇始的精神打通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的筋骨是实。有论者曾对“民国文学”的论述提出批评,认为:“‘民国时期的文学’不仅不等于‘民国文学’,往往还是‘反民国的文学’。”⑥这种论调实际上是将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制度具体实践两者混为一谈。制度设计的理念往往是某一价值的“理想国”,而制度的具体实践则会因为现实情况而对价值做出让度。因此,这位批评家所说的“反民国的文学”实际上是“反民国制度实践”的文学,而非“反民国价值理念”的文学。否则,鲁迅也不会“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作为昔日“民国敌人”的中国共产党更不会肯定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⑦分清楚这两点,便不难发现,《中国新文学史》对1912这一历史起点的选择意涵,恰是像陈晓明、丛治辰二位先生点出的那样,“以当年的纸面象征作为当下重塑精神的号召。”⑧尚需补充的是,这种以鲜明的启蒙立场贯通现当代文学的做法并非丁帆先生首创,这一努力其实早已预伏于许志英、邹恬两位先生当年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当中,这本文学史著作中不仅将“五四”以来的文学统称为“现代文学”,更是在对新时期文学的论述上与“五四”新文学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自一九七六年四月开始的新时期文学,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复兴。”⑨虽然,受制于当年的言论环境,很多论述并没有充分展开。但是,联系两本文学史不难看出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的志趣所在。不同的是,相较于《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中在论述上做出的诸多妥协,《中国新文学史》在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则显得相对“苛刻”,尤其是对一些已有“公认”评价的经典作家作品上显得格外具有批判色彩。如在对茅盾《子夜》的评价上,《中国现代文学主潮》只是委婉点到“即使是成功创作了《子夜》的茅盾,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友人‘开口讲艺术(技巧)’,他却‘开口讲社会问题。’”,“一部分左翼都市文学则由于过分疏离了形式艺术的讲求而误入了另一条歧途。”⑩而《中国新文学史》则毫不客气地批评茅盾这种“科学家写论文”式的创作方法,“这种写作方法造就的人物,其性格由若干方面、层次的特点组合而成,可能有复杂之处,但因为过于定型化,远不能展现现实中人应有的丰富、流动的个性。可以说,‘科学家’的理性(以及政治家的意识形态)遮蔽住‘文艺家’的感性,导致了《子夜》艺术上的失败。”⑪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中国新文学史》的价值判断相较于《中国现代文学主潮》更为鲜明,这不仅仅是因为言论环境的“宽松”所致,也是因为将民国肇始作为新文学起点后,已没有了《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模糊空间和余地。正因如此,《中国新文学史》的写作何尝不是一场“以1912作为起点”的冒险实验?
首先,“1912作为起点”很好地连接起了“晚清”与“五四”之间的关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写作总是陷在“顾此失彼”的困境当中。一方面,由于“左翼”史观的禁锢,使丰富生动新文学史变成红彤彤的左翼文学的抗争史;另一方面,80年代“新启蒙”思潮下,五四“启蒙”史观的高扬,不知不觉间也压抑了对于晚清“众声喧哗”的文学现场的关注。在后者的视阈下,旧体文学被当作“旧文学”被文学史家抹擦,“五四”“新文化运动”则被描述成一个突兀的历史事件,而忽略了晚清以来社会风气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史》的作者试图告诉我们:历史并非是一个突变的过程,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离不开晚清仁人志士的努力,与之相关的民国文学也并非横空出世,而是与晚清的各种因素息息相关。因此,《中国新文学史》花费了整整一章的笔墨用来论述“新文学三十年的晚清因素”,对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刘鹗《老残游记》、韩邦庆《海上花列传》评述不吝笔墨,“草灰蛇线,伏脉千里”,隐伏在背后的仍然是民国文学中所凸显的“人”的价值,这样的文学史论述或许会带有某种历史后设视角的嫌疑,但必须肯定的是,这样的努力无疑将之前充满争议的晚清文学整合入新文学史的视野当中,使民国文学的整体论述不至于突兀,而是有迹可循。
其次,“1912作为起点”注意到了晚清以来,民国成立后所确立的社会机制对于新文学的影响。作者没有对民国体制下成立期刊、书局进行非常详尽的专章论述,而是穿插于作家作品之间以节或是贴士的形式呈现。如在第一章“新文学三十年的晚清因素”中对“四大小说期刊”的介绍,第二章“新文学潮”中对《小说月报》的介绍,第四章“‘京派’与‘海派’”中对《大公报·文艺》副刊和《现代》杂志的介绍等等,这些论述看似闲笔,实际上营造了文学史当中的“感觉结构”,将民国文学之“风”的生产机制托出,使文学史不至于变为作家或者作品的简单罗列,而是放置在民国的具体情境中去理解新文学的多元共生的历史情态。尽管有学者曾指出:“《临时约法》当然具有民主意识,渗透着中华民国‘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理念,但民国伊始即大权旁落,《临时约法》沦为一纸空文,亦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所谓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对“大写的人”的尊重无非是空洞的象征而已。”⑫但是,是时国民政府的“弱势独裁”在客观上也造成了某种“宽松”的氛围,拓展了一些相对“自由”的批评空间,形成了民国文学特有的生产机制。在此,“1912作为起点”,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召唤历史,以反思、批判当下的文学史写作模式,也是以民国立国的基本价值去不断“返观”历史中的民国,在高扬民国立国价值的同时,也对民国的现实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如在对左翼文学发展的背景进行描述的时候,作者写道,“北洋军阀统治初期,握有实权的各方军阀形成均势,新文化运动在权力无暇顾及因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展开,取得了重大进展,待到权力纷争告一段落而某一派势力占据优势之后,均势被打破,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就重新遭到干涉与阻碍。”⑬民国复杂的社会肌理和运行机制显然不是一本文学史所能容纳,但作者却尽力将这一点展现给读者。在高扬了民国以“人”为指规的价值的同时,对于民国也不盲目吹捧,字里行间保持了一位知识分子对于历史现实可贵的清醒和独立的批判意识。
最后,“1912作为起点”可以将台港文学史较为有效地整合入中国新文学史中。长期以来台港文学史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常常难以整合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因为现代文学史往往以“五四”或与“五四”息息相关的“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因此,台港文学在进行论述时也必须延续这一整套“大陆史观”,而被简单粗糙地论述为由边缘心向中央的文学,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台港文学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学的“地方性”以及作为另一种政治文化体系与大陆文学相对所呈现出的“异质性”。以“1912作为起点”的中国新文学史虽然也未能完全从过去文学史对台港文学论述的窠臼中跳脱出来,但是,《中国新文学史》不论是在台港文学史论述框架的搭建还是具体的操作方面都力避过去文学史简单粗暴的“硬写”,而是希望通过较为细腻的梳理,将台港文学理解为“是中国现代文学此一时期在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延伸和发展,但同时,它们又因为与大陆存在不尽相同的政治状况和文化机缘,又形成了一些自有其特殊性的若干文学命题,并在现实中具有相应发展的发展形态。”⑭较为可惜的是,不论是在作家作品的选取,还是在与大陆文学的关系的论述方面都没有达到概论部分的自我期许。《中国新文学史》选取的多是大陆地区研究比较成熟经典作家,但是近十多年来在整个华语文学圈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王鼎钧、龙应台、施明正、齐邦媛等作家都没有纳入到考察范围当中,这与《中国新文学史》中当代文学作家作品选取的“当下性”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因而台港文学部分的文学史写作稍显不足。另外,如台湾经日本到大陆的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抗战时期香港的“南来作家”群,1949年移居台港或海外的作家等等,这批作家的创作因为横跨多个时空,各个阶段的创作又呈现不同特点,如何整合入大陆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离散写作的文学史论述格局无疑是需要学界同仁继续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二、“民国作为方法”
如前文所述,“1912作为起点”不仅是对新文学史的一次重构,也是以民国肇始的立法精神对于历史和现实的一次“返观”。《中国新文学史》以“民国作为方法”跨越传统文学史的框架,以此作为反思当下文学主体性的价值起点。换而言之,“民国”依然是一个能够召唤出现实力量的尚未完成的“事件”,它所承载着历史的价值与势能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华语文学的生态。现实政治层面上看,“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国家一息尚存,即使是在大陆的政治话语层面,也不否认“两岸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⑮这一政治现状。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必然是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作为其合法性的前提而存在。而在更为广阔的文化层面,“民国文学”如“落地的麦子不死”,在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生根发芽,繁体文学依然呈现活跃的状态;与之相对应,1949年后中国大陆所开启的共和国文学中,“民国文学”则作为一个批判的对象而存在,实际上未能脱离一种回应性的模式。所以,以“民国作为方法”实际上是以一种对当下介入的态度,以返观今日文学所面临的诸多困境。
《中国新文学史》以“民国作为方法”首先是针对于中国当下文学存在诸多问题反思意识,力图把握历史深处的价值,以此作为关照当下文学困境的契机。因此,《中国新文学史》在对1949年中国大陆文学史的处理上放弃了细密的历史论述,放弃了用繁杂的史料去编织当代文学的“存在之由,变迁之故”;也没有“再解读”的藉由西方现代性理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式的革命“叫魂”,而是用更为鲜明的价值去重估当代文学文学价值,试图理出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因此,相较于其他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对于当代文学发端的“十七年文学”评价显得有些“苛刻”,“所以,在缺乏世界文学参照且被迫斩断‘五四’新文学启蒙传统的环境中,那些曲折表露个人真实境遇、思想和体验的创作就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它们代表着‘人的文学’所追求的‘人的生活’的肯定与呼吁。”⑯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是在集体意志之中,对于个人价值的坚守。因此,在作家作品的选择方面,选择的主要是能呈现鲜明个人色彩,或是能带有个人与集体之间张力的文学作品。即使是涉及极富政治意识形态意涵的“样板戏”,也不忘点出其中“隐含有日常生活、人伦情理、传奇色彩等成分”⑰。而在对新时期文学的评价方面,也没有陷入到过去文学史“非此即彼”的模式之中,清醒地意识到“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所造成的审美惯性,对于“刻奇”(Kitsch)式的抒情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呼唤的仍然是以“民国”作为参照点的个人审美话语。也是在“人性的,审美的,历史的”标准之下,《中国新文学史》在“以论理史”的过程中更为突出“问题”(problem)意识,凸显批判性的同时,并不寻求某种确定的对问题的“解决”,取而代之的是,阅读后的苍茫感和荒芜感。如在对于80年代北岛诗歌美学的评价方面,并没有因为诗歌中的“反抗”姿态,而对其有过分的偏爱。相反,指出北岛与其“反抗”对象之间在美学上的趋同,北岛的“反抗”是拾起对方武器的“反抗”,认为“北岛的文学努力,在80年代初并没有树立一种反叛文化,因而其文学不具有充分的先锋性”,“有政策限度的政治意识,诞生了独特的北岛诗歌美学。他的诗歌中一直未中断过斗士情绪,常形成抗争的阵列,有强烈的对立结构”,“北岛将诗歌胜利的辉煌写于一瞬,而将诗歌溃败和救赎的悲壮写于一生。”⑱这一评价所折射是对80年代所形成美学现象的清醒反思,是以一种“走出80年代”的姿态回望当下文学的来时之路,是以今日之我对于当年之我的“再解读”,其中蕴含的自我批判意识在当下的文学史写作中显得难能可贵。
其次,在“民国作为方法”鲜明的价值取向之下,使《中国新文学史》的写作打破了原有文学史中列传式的“史体”,以期更好地展现史家对于历史“风势”的观察,凸显治史者的价值取向。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曾批评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单倘有据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⑲历史学也好,文学史也罢,自不仅仅是史料学,局限于材料的归拢和整理,晚清学者刘咸炘就认为,“‘史’不应该有定体,应该根据所要创设的‘风’,而创设新的史体。他认为要捕捉‘风’的史体要能兼顾‘上下’和‘左右’。所谓‘上下’就是要贯穿,不能以一个朝代为限,往往要看三五百年,所以要‘纵’观,要种时风。但他同时也将左右,讲‘横’观,讲‘土风’,一个地域的‘风’。”⑳所以,从《中国新文学史》的“史体”来看,显然是带有“观风察势”的野心的,力图从文学史的剖面入手,观测出时代之“风”的变化,在风势的起落中加深读者对于当下时空的理解。这突出表现在章节的设置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史既有写作模式,代之以“新文学三十年的晚清因素”“新文学潮”“鲁迅与‘五四文学’”“‘京派’与‘海派’”“传统与现代的审美融合”“知识阶层形象谱系”“‘文革’后的诗歌美学建构”“文化意识与审美意识的深化”“历史病症的文学呈现”等等这类以回归文学审美特征为导向,以知识分子的启蒙价值为旨归的章节设置,惟有“格式的特别”方能实践其人道主义关怀的“表现的深切”。稍显不足的是,和传统文学史一样,《中国新文学史》没有刺破现代、当代之间的壁垒,书中很多有价值的观测点未能做到“上下”贯通,这个角度上看其实还稍嫌“保守”。如上册“知识阶层形象谱系”一章中对于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精神困境的探讨,在下册第一章第一节“在规训与疏离之间:集体姿态与个性立场”与第七章“历史病症的文学呈现”中似乎若隐若现,如果单刀直入的进行讨论,这一话题将显得更为饱满和富有张力,其折射的将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精神困顿背后的整个社会公共空间的收与放,启蒙的张扬与压抑等一系列问题。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传统与现代的审美与融合”和“眩惑的文学形式”、“废名、沈从文与‘田园牧歌’乡土小说”和“各具特色的乡土小说”等等上下册中存在互相相对应的章和节中。当然过份凸显对问题的关注,则又必然打破“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的整体结构。张扬史观必然以切削史实为代价,亦步亦趋于线性前进的历史则无以凸显其中的问题意识,如何把握其中的平衡考验着治史者的功力,在此也不难理解丁帆先生后记所陈心曲,“要想撰写一部真正能够表达自己内心世界感受的新文学史真不容易!”㉑
最后,以“民国作为方法”与其说是在学理上“大胆假设”的一次实验,不如说是彰显治史者价值观的性情之作。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校注》中曾言,“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和从者是也。”㉒将个人性情熔铸于学术研究之中,在《中国新文学史》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丁帆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就“民国文学风范”有过深入的探讨,表达了“即便民国不在,民国文学风韵犹存”的感喟,而在《中国新文学史》的“绪论”部分也不吝笔墨地重复着自1912年至今在社会中已被普遍接受进而形成“共识”的某些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在这些看似是“常识”的价值上重新出发,其暗含的是对现下的文学乃至社会价值失范的思虑和关照。因此,《中国新文学史》在进行文学史叙述时,时刻存在着一个难以压抑的是治史者的声音,其对于个人价值的高扬,对于启蒙理念的贯彻,也远比其他文学史要来得更加“坚定”。如对于受大众热捧的两部小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余华的《活着》,在评价的时候保持了知识分子可贵的清醒,“对历史和现实的模糊认识和对农民人生奋斗图景的景仰与讴歌,使路遥的作品民间情感有余而历史省察不足……在路遥身后,暴发户的精神荒原和挣扎在生存最底线的人生惨剧,已经使一代农民人生奋斗的理想主义,幻化为更耐人寻味的悲剧意味。……在路遥之前,乡间的苦难从未获得如此‘瑰丽’的诗情呈现,这也使他的作品对于缺乏问题意识与悲剧感的普通读者具有长久的吸引力”㉓“整体来看,福贵们的苦难耐受并没有中止在亲情层面,而是穿越生命伦理的底线,以全部尊严感的丧失为代价,呈现为一个裸露的生存本相,一个可以接受任何戕害的无机躯壳。福贵与许三观的生与死在这样的呈现中具有鲜明的代码特征:余华在其中所铺张的生命耐受力的夸张变形的书写,则能引起更多通俗文学性质的阅读共鸣。”㉔这样的评价一方面充满着对于底层苦难生活的同情,对于另一方面则对于造成苦难的原因,对于作家醒觉的限度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即对评价对象保持“理解之同情”,也不失时机地亮明自己的观点,显示了治史者对于自己所秉持价值的自信。也是基于这一自信,使得《中国新文学史》的文字呈现充满了个人的风格,追求表达的平实准确之余,也不失语言的优美。灵动的文字激发起人的阅读欲望,使文学史真正成为了一部“文学”的文学史。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当今社会面临着价值的缺位等诸多问题,文学在社会之中也似乎愈发边缘化,但是,人类对于人性、审美、自由、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乃是亘古不变。文学、文字也许是无力的、边缘的,但是,正如那木铎之声,其音清远,在黑夜中穿过,温暖着清醒者们的心灵。
注释:
①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5页。
②许子东:《现代文学,“拥挤”的学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
③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8页。
④鲁迅:《鲁迅全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17页。
⑤丁帆编:《中国新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9页。
⑥郜元宝:《“民国文学”,还是“‘民国的敌人’的文学”?》,《文艺争鸣》2015年08期。
⑦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1月11日)。
⑧陈晓明、丛治辰:《启蒙理念与文学史叙述——评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04期。
⑨许志英、邹恬:《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⑩许志英、邹恬:《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8页。
⑪丁帆编:《中国新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17-318页。
⑫陈晓明、丛治辰:《启蒙理念与文学史叙述——评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04期。
⑬丁帆编:《中国新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94页。
⑭丁帆编:《中国新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62页。
⑮《习近平与马英九致辞全文》,http://news.qq.com/a/20151107/028783.htm
⑯丁帆编:《中国新文学史》(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⑰丁帆编:《中国新文学史》(下册),高北京: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6页。
⑱丁帆编:《中国新文学史》(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3-126页。
⑲鲁迅:《鲁迅全集》(1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2-103页。
⑳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1页。
㉑丁帆编:《中国新文学史》(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45页。
㉒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14年,第161-162页。
㉓丁帆编:《中国新文学史》(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87-188页。
㉔丁帆编:《中国新文学史》(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