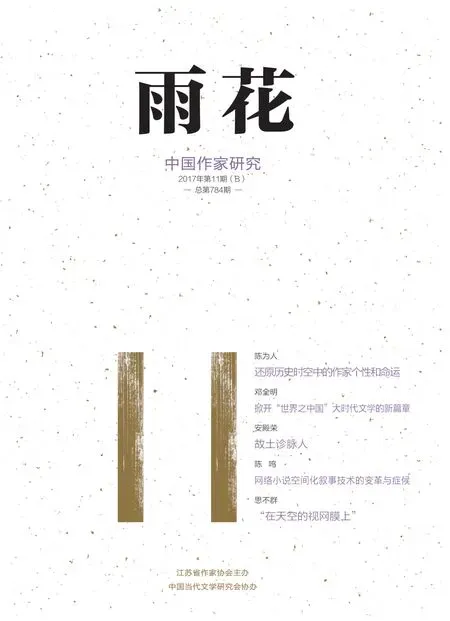还原历史时空中的作家个性和命运
——在沁水赵树理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7-12-01陈为人
■ 陈为人
已经开过了难以数计的关于赵树理的研讨会。
为什么要一次次地花费人力物力去召开呢?如果就是炒馊饭旧调重弹人云亦云老生常谈吃别人嚼过的馍,那样有什么必要和意义呢!
我们说一个时代标志性的作家,必然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与交结,这是一种盘根错节的联系。正是因为这种复杂化的关系,使得后人能够常读常新,不断从他身上发现作家个性与命运的时代根源,社会原因,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局限。当然,这不是配合当下政治形势的“与时俱进”,而是把一个作家还原到他生存的特定历史时空中,做出更加符合人物真实面目的界定。
2011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作为“新史学丛书”中的一家,推出我撰写的赵树理传记。动笔之始,意在笔先,我想:仅自己目力所及,已经看到过十几部赵树理的传记,还需要我画蛇添足抑或狗尾续貂地再来写一部赵树理的传记吗?
我把赵树理的传记命名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赵树理自己的命名,由此可见赵树理对自己文学史上的定位是心存迷惘的),因此而引出我的副标题——“重新解读赵树理”。
书出版之后,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和反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评价说:“赵树理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是相对成熟的,但本书在材料的搜集和事实的叙述方面还是多有新意,特别是作者与研究对象可能涉及的历史比较熟悉,所以在分析和判断方面较以往的研究更有启发。另外本书吸收了近三十年来赵树理研究的主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是近年来赵树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赵树理的儿子赵二湖在看过本书后说:“出过很多种赵树理的评传了,因此有了很多个面目各异的赵树理。我不是专家,无从评论这些专著的好坏,作为儿子我只能评判像与不像。感谢陈为人先生写了这么一本好书,还原了一个我熟悉的父亲形象。”
钱理群先生在《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最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是本书《尾声》所讲述的赵树理的当下命运:他的形象“与时俱进”,却“面目全非”;他被安置在殿堂、广场,以至荧幕,供人瞻仰;“毫不相干,强加给他的塑像”竟有八处之多,他的儿子也只能自嘲而无奈地说:“人家说他是我爹”。——在这样的氛围下,被呼唤而出的“后赵树理写作”,会是什么模样,实在令人担忧……而在我看来,提供这样一个模糊的,难以作出简单、明确判断的赵树理,而且引发我们许多想不清楚的思考:关于赵树理,关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农民,关于赵树理生活的、以及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国家,民族……最后所有这些思考,都会归于对历史,对人的命运、存在的追问,却又没有结论:这正是本书的真正价值与贡献。
钱理群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陈为人先生:前一段一直在赶写一篇文章,这两天才开始拜读大作,确实受到了震动,也引发了许多思考,但一时无法理清楚,只能赶写出这篇《读后》……我原来有一个写‘1949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大的写作计划,我赶写的文章,就是写胡风与舒芜的(还没有写完),赵树理也是我想写的。读了大作,更激发了我写作的冲动,许多方面,大作已经写得很好了,我再要写,可能就是《读后》里提到的赵树理引发的思考……”
2014年10月,我正在上海陪伴已经九十三岁高龄的父母,钱理群先生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我写了关于赵树理的七万多言的文章,从大作中多有吸取,特致谢意,也很想听听你的意见。”于是我得以先睹为快,看到了钱理群先生关于赵树理研究的最新成果:《赵树理身份的三重性与暧昧性——赵树理建国后的处境,心境与命运》。钱理群先生在文章中写道:
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包括本书(《岁月沧桑:1949——1976知识分子精神史》)写作的追求:写出一个又一个的“难以作出简单、明确判断”的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史,以激发“对历史,对人的命运、存在的追问,却又没有结论……我在1998年即十六年前第一次研究赵树理时,就注意到了他的“双重身份”:“赵树理把他自己的创作追求归结为‘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正是表明了他的双重身份、双重立场。一方面,他是中国革命者,中国共产党员,要自觉地维护党的利益,他写的作品必须‘在政治上起(到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国农民的儿子,要自觉地代表和维护农民的利益,他的创作必须满足农民的要求,‘老百姓喜欢看’。”正确地理解赵树理的这两重性是准确地把握赵树理及其创作的关键。
现在有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赵树理的学者,都刻意指出赵树理与其他“山药蛋派”的不同,其实,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自觉做党的宣传员这一点上,他们都走在同一条《讲话》指引的“金光大道”上。
马烽在某次创作谈中,关于一个作家能不能只要是现实中曾发生过的真实事,就可以不加选择地写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有的题材要自觉地不去写,因为写出来没有好处,没有用。除了使人们看到社会上一片黑暗之外,没有其他作用。有些题材不能写,如涉及到国家机密的问题就不能写。也有些题材当时不能写,现在能写。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党的地下工作,当时不能写,一写就暴露给敌人,但现在能写。所以不是什么题材都可以写的,要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赵树理在一篇《若干问题的解答——写戏、改戏的标准》的创作谈中也说了一番与马烽类似的话:“有的戏,有时能演,有时就不能演,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要看具体情况。假如到灾区慰问演出,我们演的是因天灾人祸而引起暴动的戏,这戏对灾区农民有什么好处呢?对人民对革命负的什么责呢?又如,在欢送新兵时演出《四郎探母》,这又起什么作用呢?问题在于是自己对农村、对革命负责了,自己就会发现,并进行批判。”
把赵树理与马烽的话比照着读,不是正深刻揭示出了共和国文学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吗?
在1947年召开的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赵树理被确认为是贯彻执行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方向。陈荒煤在评价到“赵树理方向”的政治意义时,一针见血地指明:“赵树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深刻认识,最集中地表现在他说的‘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两句话上。这两句话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最本质的认识,也应该是我们实践毛主席文艺方针最朴素的想法,最具体的作法。”
赵树理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他说自己的创作是“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而从《万象楼》起始,我们从赵树理的一系列作品中,都能感受到赵树理创作观中配合政治任务的倾向。
马烽与我谈起过他对赵树理的记忆:“我认识赵树理,是在全国解放初期,那时候我们都到了北京,虽然不在一个单位,但常常见面,工作上也有一些往来。那时北京市成立了一个业余的‘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要任务是团结一些过去写章回小说的作者以及曲艺界的朋友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研究会’还创办了一个叫《说说唱唱》的通俗刊物,主编是老舍,赵树理是副主编,我是编委之一。……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50年夏天,正是大力宣传婚姻法的时候,刊物急需发表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但编辑部却没有这方面的稿子。编委会决定自己动手写。谁写呢?推来推去,最后这一任务就落到了老赵头上。这是命题作文章,也叫‘赶任务’。一般的说来是赶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老赵却很快‘赶’出了一篇评书体的短篇小说《登记》。这篇小说曾轰动一时,很快被改编为戏曲,改名为《罗汉钱》,搬上了戏剧舞台。……我当时曾这样想过:如果这任务落在我的头上,即使给我半年时间专门去搜集材料,也不可能写出这样动人的作品来。”
赵树理对于配合政治形势,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有着高度的自觉性。赵树理在《谈“赶任务”》一文中,就把自己的创作是积极主动自觉自愿地去配合政治的态度说得更为明确:
每当一个事件或运动来了之后,会有新的任务摆在作家们面前,就是平常所说的要“赶任务”……
“赶临时任务”这个名词本身已经不妥当。……如果本身生活与政治不脱离,就不会说临时任务妨碍了创作。因为人民长远的利益以及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才是第一位的,只是带着应差拉夫的心情去“赶”,而是把它当作长期性的任务去完成。情绪与工作统一起来,不是随随便便的应付。
认为临时任务一来,妨碍创作,原来大作就永远不能完成了,这种错误观点的产生,基本上就是因为生活与政治不能密切配合,政治水平还不够高。所以当上级已将任务总结指出之后,应该是感激才对,因为自己不能认识到是中心任务,而别人已替自己指出来,如果认识不足,仍然认为是赶临时任务,那么这是应该放下手头的创作去赶,赶总比不赶好,只要没有大错误,赶得多总比赶得少好,写得好总比写得坏更好。……临时任务根本不能赶好,也不见得,看作临时任务也可以写好的,只看怎样写。写出来不好还不是最大失败,写总比不写好。
自己过去有些创作在写的时候就与当时任务统一,有的是写过之后与任务碰上了头,有的则是“赶任务”赶出来的。例如《李家庄的变迁》是经上级号召揭发阎锡山统治下的黑暗之后才写出来,材料早已有,但当时没有认识到揭发的必要,直至任务提出后才写。
写作品好比种庄稼,江南为橘,江北为枳,植物与其生长的土壤有很大的关系。在黄土高原上,很难指望生长出椰子芭蕉,而只能是“满山遍野的土豆高粱”。赵树理的局限性也无法超越他生存的这块土壤。
韩文洲曾多年担任赵树理家乡晋东南地区的文联主席,后又成为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称得上是得赵树理真传的“第一人”。 1962年在中国作协召开的那次著名“大连会议”上,树起了一个标兵三个样板,标兵是赵树理,其中一个样板就是韩文洲的《四年不改》。赵树理对韩文洲的作品极为欣赏,他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中说:“韩文洲写的小说虽然有他自己的风格,但跟我的风格很接近。如果韩文洲的小说不写韩文洲而换成赵树理,读者不会说不像的。”韩文洲以自己对赵树理的了解,在我对他的访谈中,这样说到赵树理和马烽的区别:“马烽和赵树理不是一回事。马烽从来是站在党的立场,是党领导文艺的干部;而赵树理从来都是站在农民的立场,是个农民的代言人。文革中有一句批判老赵的话,说赵树理成了落后农民的尾巴。”
当年批判赵树理的还有一个观点:“反映落后农民观点的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意见。”
当年山西的省委书记王谦,对先后为“山药蛋派”代表人物的赵树理、马烽有一个极为准确的概括和评价:“马烽和赵树理不一样。马烽是为党而写农民;赵树理是为农民而写农民。所以当党和农民利益一致的时候,他们俩人似乎没什么差别。而当党和农民的利益不一致时,马烽是站在党的一边,而赵树理是站在农民的一边。”
我一直以为,王谦的话是对赵树理的夸赞。在对赵二湖的访谈中,赵二湖却对王谦的这段评价,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见解。赵二湖说:“王谦对赵树理的评价,其实内里含有的是批评意味:即在关健时刻不能与党保持一致。
在赵树理的主观愿望上,是心甘情愿做一个“为革命拉磨”的牛马。但他那爱尥蹶子的“毛驴脾气”,又往往使他在关健时刻,不能与上级领导保持一致。
赵树理说:“我是一个农村干部,就得对农业生产负责,不能叫老百姓没有口粮,牲口没有饲料。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得对党负责,不能说假话,下级欺骗上级,地方欺骗中央。”
赵树理还说:“我看到由于种种不合理的措施,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和给群众带来的灾难,我不能熟视无睹。向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等人提出,可是说不服他们,为这事,我日夜忧愁,念念不忘,经常奔上奔下,找领导想方法。但他们都认为我是一种干扰。”
赵树理的奔走呼号,面折廷争,招致社、乡、县三级干部的反感,认为赵树理是多事,挑毛病,神经病。
赵树理自己还说过这样一个情节:“过去我有老母,借此探亲,能了解到许多真实事情。但我的脾气急,性情直来直去,知道后就向上级党委反映,提供基层情况。后来人家发现了我这个秘密,回家后没人给我说实话了。这些事我也苦恼过。为了他们,他们还避忌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怕报复、受治。我得了教训,学了点乖,再接触知情人,就讲究些方法。”
钱理群先生在《赵树理身份的三重性与暧昧性——赵树理建国后的处境,心境与命运》一文中写道:
这样的双重性,自然也是我十六年后的新研究的基本视角;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在其他研究者的启发下,我又注意到了赵树理的第三重身份,即“知识分子的身份与立场”。这样,“党——农民——自我主体(知识分子)”就构成了赵树理精神与心理结构的三个层面,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纠缠,矛盾,张力,又造成了赵树理身份与立场的暧昧、模糊,背后是党和农民,作为特殊的知识分子个体的赵树理和农民,以及赵树理和党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别有意味的丰富性……
现在人们在评议到赵树理的创作时,几乎异口同声地强调一点:“深入生活”。马烽在《忆赵树理同志》一文中说:“赵树理同志是我所尊敬、所热爱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的主题,也正是当时根据地农村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后来我读了一些介绍赵树理的文章,逐渐懂得了:“他所以能够写出这样好的作品来,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长期深入生活,熟悉农村中各种各样的人物。”
马烽还说:“赵树理在一些谈创作经验的短文里,或是在和青年作者的谈话中,总是一再强调深入生活的重要性。而首先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毛主席指示‘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楷模。”
于是,深入生活,建立自己的“生活基地”,成为“山药蛋派”作家们共同遵循的一条铁律。
赵二湖说:“说起来是一个奇怪现象,我父亲这么一个紧密靠近政治的作家,这么个不怎么‘文学’的作家,恰恰没有陷进许多作家都掉进去的‘高大全’、‘假大空’的概念化泥潭,没有成为看风使舵随波逐流的‘跟风派’,去写粉饰现实的作品。反而在这时用沉默和反抗凸显了他的文学价值和人格魅力。”
赵树理在某次谈创作体会时,“一语道破天机”地说出了其中的奥秘:“材料的来源,非从生活中来不可,任何作家,不管是戏剧、小说、诗,离开生活不能写东西。在生活中,细心观察人和事,在我看来,这是次要的。作为旁观者,作为观察员是这样,作为生活的主人不是这样。”
赵树理关于“生活的主人”的说法,真是画龙点睛之笔。
马烽谈到对赵树理有这样一段回忆:“我没有和赵树理同志一起下过乡。1971年我获得‘解放’后,曾在他蹲过点的一个村庄附近的另一个村庄插过两年队。他蹲过点的那个村庄我也去过,提起赵树理来,大人小孩都熟悉。他们告诉我:老赵在这里蹲点的时候,正是大办农业社的那阵子,他不仅参与办社的大事,连改革农具、修补房屋,调解家务纠纷等等他都参与,而且是认真地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吃饭时候,他常常是端着饭碗在饭场上和农民聊天,也常常和喜爱文艺活动的人们一起唱上党梆子。谁也不把他当作家看待,而是看作他们中的一员。……”
高捷等著的《赵树理传》,还记载了赵树理这样一个细节:
盛夏某日午后,作协开一个小型会议,主持者邵荃麟正在发言,外面天色渐晦,继而黑云压城、雷鸣电闪,暴雨夹着雹子砸下来。只见赵树理起身,怔怔望着窗外,嘴里还念念有词。邵荃麟一心专注地发言,忽然看见赵树理不听他的话,跑到窗前看下雨去了,以为老赵有什么意见,不耐烦听他说了。便说:“老赵,你坐下谈谈你的意见吧!”不想赵树理头也没回,气狠狠说道:“该死!”在场的人都惊奇起来,邵荃麟问道:“老赵,你怎么回事?”赵树理这次似乎听到了邵荃麟的话,才转过身来朝外指了指:“麦子完了!”
这个细节形象而生动地反映出赵树理心之所系。
立足点成为分水岭。
冯翼惟象,差之丝毫,失之千里。鲸鱼不是鱼,形同质不同。正是这一“生命基因”的不同,使赵树理超越了“山药蛋派”的局限,完成了人格精神的“化蛹为蝶”。
正是基于对赵树理命运的深刻研究,钱理群在文章中提出了“赵树理身份的三重性与暧昧性”。
看过钱理群先生的《赵树理身份的三重性与暧昧性——赵树理建国后的处境,心境与命运》,激动之中与他有一次长时间的通话。在通话中,钱理群先生向我披露: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将分为三部曲:第一部是《1948:天地玄黄》,写共和国之前的知识分子精神状况;目前正在进行的《岁月沧桑:1949——1976知识分子精神史》一书是第二部,写上个世纪后五十年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困境;最后完成《精神自传》,从自己人生经历中心灵的历程和轨迹,挖掘和丰富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通话后,我意犹未尽又回复一信:
您的大作把赵树理由一个人们定位为“农民的代言人”的作家,升华为“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思考者”,“农村社会理想的探索者与改造农村的实践者”,并深刻指出:“赵树理正是这样的中国式(又是现代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文学’培育出来的‘农民作家’。在他这里,写作与农村变革实践,是合一而且可以随时相互转移的。这确实是几乎不可重复的社会历史和文学现象”。这就使得赵树理超越了自身生命而使后来者从其生存经历中不断获得“常读常新”的长久魅力。另外,关于赵树理与党的关系的分析也是准确且深刻的……
钱理群先生的研究,十分重视文学史中的“时空距离”。他认为,“历史人物”是留存于“彼岸”,而撰写者是生存在“此岸”,阴阳两隔着岁月的流水。所谓历史写作就是一个不断往返的双向运动过程:既要由此及彼设身处地,努力进入历史情境,又要进入角色,“南海北海,心理悠同”,感同身受于笔下人物做出这样那样选择的思维背景及心理逻辑。人的选择都是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选择,人因为选择而成为自己。把“隔岸观火”的旁观者的隔膜,转化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当事者的共鸣。由此及彼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体察笔下人物选择中的痛苦与矛盾,从而产生具有历史深度的命题。毫不回避地正视与揭示在选择(命题)展开与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严峻而复杂的史实,这些后果是当事人所不可能预知的,从而提出把“设身处地”与“正视后果”作为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基本原则。追求“历史与现实”、“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结合和贯通。
钱理群对赵树理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更深的层面。
我们研究一个作家,一定要把他还原到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展现“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以此确立他在时代中的身份和地位。这大概也是我们不断召开一个作家纪念会研讨会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