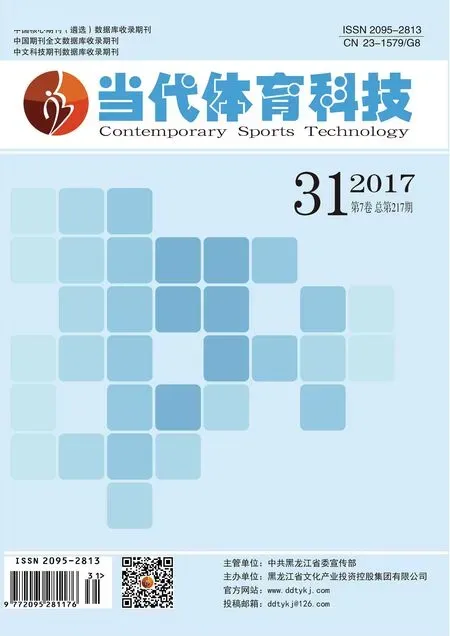契丹人传统体育活动的文化学分析①
2017-11-27苏楠
苏楠
(内蒙古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北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研究所 内蒙古通辽 028000)
契丹人传统体育活动的文化学分析①
苏楠
(内蒙古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北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研究所 内蒙古通辽 028000)
采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主要基于《辽史》中的史料,对辽代契丹人所进行的传统体育活动进行考证分析。主要结论:契丹人传统体育活动源于祭祀,射鬼箭体现了原始崇拜的宗教特点,受政治体制影响具有多样性特点包含了“射猎”、“渔猎”方面的内容,角觝、击鞠等体育活动被辽代皇族所钟爱,常作为接待使臣举办国宴的礼仪,契丹传统体育活动具有全民参与的文化色彩。
契丹人 体育活动 文化学
契丹族是中国北方少数游牧民族,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正式称帝建国号契丹,947年建国号辽,直到1125年被金所灭,契丹族有着两百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民族发展过程中,契丹人在本民族的先源文化基础上学习了汉唐文化并发展突厥文化,进而开展各式各样的体育活动,比如射柳、击鞠、角觝、双陆、头鹅宴等,并最终形成了丰富且独具游牧渔猎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
1 契丹人传统体育活动的宗教性
契丹人信奉萨满教认为万物皆有灵,赋予大自然万物以神性,信鬼神崇拜自然。举凡军国大事皆举行祭天地仪式,“辽国以祭山为大礼,服饰尤盛”,“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日,东向而拜日……”,“辽俗好射麃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契丹人的这些富有宗教色彩的原始崇拜已经融入民俗生活中,有些传统体育活动源于祭拜仪式,具有很强的宗教性。
惊鬼,“正旦,国俗以糯饭和白羊髓为饼,丸之若拳,每帐赐四十九枚。戊夜,各于账内窗中掷丸于外,数偶,动乐,宴饮。数奇,令巫十有二人鸣铃,执箭,绕帐歌呼。账内爆盐垆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居七日乃出。”契丹人在农历新年的第一天,举办驱鬼祭祀活动,将糯米和羊骨髓做成的丸子扔出窗外,偶数代表吉祥众人宴饮;奇数就需要巫师执箭绕帐,通过声音惊醒各路鬼神,祈求平安。
射鬼箭,“凡帝亲征,服介冑,祭诸先帝,出则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方,乱失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师,则射所俘。后因为刑法之用。”皇帝率军出征前,进行“射鬼箭”仪式,祭拜先祖后将死犯绑在柱子上,乱箭将其射死以祈求胜利。“太祖七年问诸弟面木叶山射鬼箭厌禳”,后来用作辽朝刑法。
2 契丹人传统体育活动的多样性
受辽代“因俗而治”的政治体系影响,一年之中契丹皇帝随着季节的变化进行春水、避暑、秋山、坐冬,以保持本民族传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渔猎生产及生活方式,契丹人的传统体育活动开展按四季变换形成游牧射猎、渔猎宴饮的多样性特点。
2.1 “游牧射猎”的体育活动
射柳,据《辽史·礼志》记载:“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质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又翼日,植柳天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稗荐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皇族、国舅、群臣舆礼者,赐物有差”作为一种祈雨仪式,皇帝射柳两次,随后才由子弟大臣依次射柳,整个活动中双方以衣帽作为抵押,以是否射中分胜负,负方要向赢者进酒。第二天在天朋东南面种植柳树,由巫师祭祀神灵帝后行礼,子弟依次射柳,参与的大臣会接受不同的赏赐。三天后如果下雨则赏赐北面官敌烈麻都,马4匹,衣物4套。据《辽史·游幸表》记载太宗时期共举行射柳活动5次;景宗时期3次;重熙年间1次,活动多在每年的4、5、6月举办,求雨目的明确,只有雨水充沛才能保证契丹人赖以生存的草原水草丰茂,整个射柳活动从皇帝到群臣集体参与其中,也体现出了契丹人“挽强射生”的民族特点。
射木兔,契丹语“陶里桦”,陶里谓兔,桦谓射也。“三月三日国人以木雕为兔,分两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其负朋下马跪奉胜朋人酒,胜朋于马上援杯饮之”。人们分为两组,把木头雕成的野兔放在适当位置,举行走马射箭比赛。这项体育活动以竞技娱乐为主要目的,要求竞赛者有高超的射术和精湛的骑技,主要比拼的是谁先走马射中木兔,先中者为获胜方,输了的一方要下马向胜者跪着敬酒,胜者在马上接杯饮下。三月三为上巳节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流行,唐代诗人杜甫在《丽人行》中用“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来描绘节日的胜景。辽兴宗于重熙5年在皇后弟弟萧无曲的府邸内进行曲水泛觞赋诗的活动,可见契丹人在沿袭汉人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文化习俗上,加入了本民族特色活动举办走马射兔比赛,并以木头雕刻的兔子为靶,体现出了一种生态保护理念,春天为鸟兽慈孕之时,辽朝明令禁止在这一时期进行捕猎活动,以此爱护动物的成长,维持草原的平衡。
呼鹿,即“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辽史·营衛志》鹿性喜盐,将盐撒在河边鹿饮水时会舔舐盐,这时埋伏好的契丹人弓箭射之;或是“常作鹿鸣,呼鹿而射之”。模仿鹿的叫声,并穿与鹿皮颜色相近的衣物头戴鹿头靠近鹿群,最终完成捕射的目的。“辽俗好射麃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据笔者统计《辽史·游幸表》穆宗至天祚帝期间共记录了35次射鹿,包括射鹿以及射舐碱鹿或呼鹿射之。《辽史·皇子表》道宗儿子耶律濬的功绩为:“幼能言好,学知书。文帝屡曰‘此子聪慧,殆天授’七岁从猎连中二鹿谓左右曰:‘祖先骑射绝人,威震天下,是儿幼,当不坠祖风’。”道宗十年7月,“猎于赤山,以皇太后射获大鹿,设宴。庚寅,猎,良王濬遇十鹿,射之得九。帝大喜,后设宴。”这两段记载不难看出契丹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挽弓射箭捕获猎物,而射鹿的行为也是其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凿冰钓鱼”的渔猎宴饮活动
头鱼宴,在辽朝正月上旬至四月中旬这个期间,正值冰雪未化,河床结冻,寒风刺骨的时节,皇帝大臣们的娱乐项目就变成了“卓帐冰上,凿冰取鱼”,“藩俗喜罩鱼,设毡庐于冰河之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窃,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钓竿,罕有失者。”皇帝在冰面上设下大帐,前面的士兵凿冰眼,下游的士兵侍从抡开大锤,下杆布网防止大鱼逃脱,专门有士兵在凿好的冰眼前观望,若发现有鱼游来及时报知皇帝,辽皇帝亲自施钓,头鱼既得,接下来就移入别帐开始了头鱼宴的欢庆活动。这种捕鱼方式使契丹人在寒冷的冬日也能获取食物,皇帝的春季捺钵也在这个时候结束,启程到下个营地。
头鹅宴,“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槌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位。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位近者,举锥刺鹅,取鹅脑饲鹘。皇帝德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据史料记载,辽朝皇帝在“春捺钵”行营接见各部首领、外国使臣时,就会举办“头鹅宴”等渔猎宴饮活动,辽朝萧总管所作的《契丹风土歌》中提到“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说明当时获得头鹅者可得重赏。
2.3 益智娱乐的博弈活动
双陆,两人面对面而坐,棋盘在两人中间,棋盘上刻有对等的12条竖线,黑白两种棋子,掷出骰子,按照显示数字走动棋子,白色自右向左,黑子自左向右,棋子先走进对方刻线内为胜。按提前约定赌注进行奖惩,其中赌注下的最大的要算辽兴宗,在与其弟耶律重元对弈双陆棋时竟将居民城邑作为赌注,“帝屡不竞,前后已偿数城……”后来还是其身边的伶人罗衣轻指其居曰“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顿悟停止了游戏。辽代宫廷之中盛行双陆棋“丁酉,皇太后幸韩德让帐,厚加赏贡,命从臣分朋双陆以尽欢”,出土的文物中也屡见辽代双陆,1974年,辽宁法库县叶茂台7号辽墓,首次出土了一套漆木质地的辽代双陆,包括棋盘和棋子。棋盘为木质,长方形,在两个长边各雕出1个月牙形纹样和其左右共12个圆形凹陷,盘上排列着30粒棋子,黑白各15粒。2004年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博物馆征集到一套完整的辽代双陆棋,包括棋盘和32枚棋子。这些文物也佐证了契丹人不仅精于骑射渔猎等尚武的传统体育活动,日常生活中也会进行益智娱乐的体育项目,形成“本土与结合”的文化特点。
3 契丹人传统体育活动的贵族性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政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以契丹贵族为主,联合一部分汉族地主和其他各族上层分子组成的政权。因此其体育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也体现了其贵族宫廷特征。辽在接受附属国的朝贡或使臣来访之时多会举办宴会观看角觝或进行击鞠,以展现契丹人勇猛强悍的尚武品质。
角觝,在辽代多做娱乐表演节目以展示契丹人的勇猛,规则与今天的摔跤类似。《辽史》中最早关于角觝的记载出现在《太祖纪》:“有司所鞫逆党三百余人,狱即具,上以人命至重,死不复生,赐宴一日,随其平生之好,使为之。酒酣,或歌、或舞、或戏射、角觝,各极其意。”太祖赐即将行刑的叛党一日宴会,这些契丹叛党喜欢的娱乐项目中就有角觝,可见早在辽建国之初就有角觝,是契丹人的传统体育项目。太宗天显四年春正月“宴群臣及诸国使,观俳优角觝戏”这段记载说明到太宗时期角觝已经正式进入皇族宴会之中以娱乐群臣。辽兴宗重熙十年“以皇子胡盧斡里生,北宰相、驸马撒八宁迎上至其第宴饮,上命卫士与汉人角觝为乐。”在庆祝皇子出生的宴会上,参与角觝的不只是契丹人,汉人也参与其中,双方进行较量,说明这项体育运动已被广泛接受,是全民参与的体育运动。后来更是将角觝作为娱乐项目写入皇帝纳后仪中,“宴后族及群臣,皇族、后族偶饮如初,百戏、角觝、戏马较胜以为乐。”不难看出角觝已成为国礼中的一项内容,是皇家娱乐的必备演出。
击鞠,也称击毬,是骑在马上用月杖击球的一种运动。契丹人对击鞠的喜爱程度来看可以将其称为“国球”。辽圣宗统和元年七月“上与诸王分朋击鞠”,统和四年十月“上与大臣分朋击鞠”也就是说从皇帝到各部落诸侯及王公大臣都会击鞠。《辽史游幸表》记载从穆宗应历六年开始有击鞠活动,兴宗时期最盛共记录16次(五年2次,六年2次,七年2次,八年2次,十一年1次,十六年2次,二十一年2次,二十三年3次)击鞠活动(包括2次观击鞠)。因圣宗过于喜爱击鞠,大臣马得臣担心皇帝在击鞠中受伤而上疏“……臣望陛下念继承之重,止危险之戏。”求皇上停止参加这样危险的游戏,“大嘉纳之。”同21《辽史》复见击鞠的记录是在辽兴宗太平十一年七月“皇太后率皇族大临于太平殿……上召晋王萧普古等饮博,夜分乃罢。丁末,击鞠”,重熙七年12月“召善击鞠者数十人于东京,令与近臣角胜,上临观之。”同22,221页直到辽兴宗重熙十年四月“驰东京击鞠之禁”正式下达解除在东京禁止击鞠的规定,击鞠重新在皇族中流行开来,重熙十五年辽兴宗下诏规定“禁五京吏民击鞠”同23,233页说明辽兴宗之后的平民是禁止进行击鞠游戏活动的,也更加确定了击鞠在皇朝贵族中地位。
4 契丹人传统体育活动的全民性
契丹人的传统体育活动一直在其传统节日、宫廷活动、民俗活动中开展,参与人群广泛具有全民性特点。依靠弓马建国的契丹人兵制为:“辽国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每正军一名,马三疋,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也就是说15~50岁皆为兵,每军必备马三匹、弓四张、箭四百及其他武器装备,人人会骑射,苏辙在《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虏帐》中说:“弯弓射猎本天性”,走马射猎为契丹人的的生存之本,自然在社会生活中演变,民族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狩猎娱乐的民族体育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契丹女性也一直参与多种形式的传统体育活动,上至皇后嫔妃下至一般妇女大多数善于骑马射箭和行军打仗,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后简重果断,有雄略……行兵御众,后当与谋。太祖当渡碛击党项,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袭之;后知,勤兵以待,奋击,大破之,名震诸夷。”;“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辽史》的这些记载说明,契丹女性同男子一样参与各项体育活动。
5 结语
综上所述,契丹人传统体育活动源于宗教祭祀,射鬼箭体现了萨满教的宗教特点。在长期生产生活与社会实践中得到发展,受政治体制影响具有多样性特点包含了“射猎”、“渔猎”方面的内容,角觝、击鞠等体育活动被辽代皇族所钟爱,常作为接待使臣举办国宴的礼仪,契丹传统体育活动具有全民参与的文化色彩。
回顾辽朝200余年历史,辽太祖建国初期契丹人以射猎游牧为生,体育活动多为骑射项目如射鹿、射柳、射木兔,在征战外国平定内乱的过程中这些体育活动作为武备训练手段必不可少,有助于国人凝聚力的提高,促使契丹人骁勇善战擅长“骑射”的尚武风气形成。辽景宗统治期间契丹内部政局稳定,农牧业兴旺经济得到增长,辽圣宗时期“澶渊之盟”的签订,保证了契丹人的生产物资不再只依靠骑射渔猎获取,使者往来、互市的开放加强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促使契丹人的传统体育活动发展趋向于重娱乐的击鞠、头鹅宴、头鱼宴、双陆等宴饮活动,加快了体育文化的变迁与发展。
[1](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宋)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2702.
[3]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117.
[4]丛密林.辽代击鞠考略[J].体育文化导刊,2016(1):1172-1176.
[5]刘晶.辽代契丹人勇武精神嬗变研究[D].辽宁大学,2013.
10.16655/j.cnki.2095-2813.2017.31.198
G80-32
A
2095-2813(2017)11(a)-0198-03
内蒙古民族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辽代民俗体育的文化研究(项目编号:NMDYB1418)。
苏楠(1982—),女,内蒙古通辽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