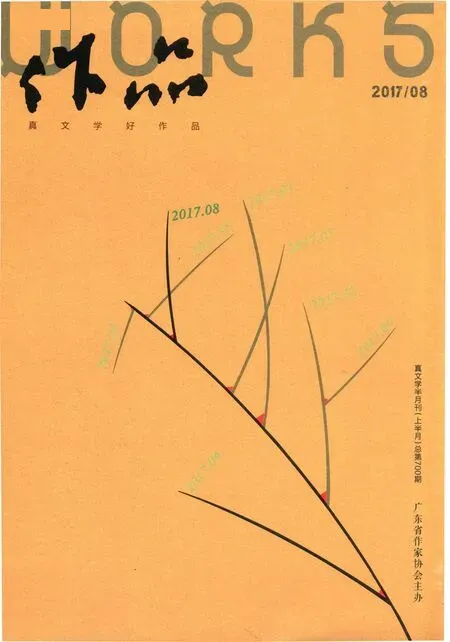林旭,走失的文学英雄
2017-11-25曾念长
文/曾念长
林旭,走失的文学英雄
文/曾念长
曾念长1978年生,福建漳平人。社会学硕士,文学博士,主攻现当代文学思潮和思想史,兼从事文学创作,以评论和散文为主。出有《断裂的诗学》 《中国文学场》等若干专著。现供职于福建省文学院。
一
像我这一代人,倘若对林旭尚有一丝印象,多数是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获得的。在写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时,这个陌生男子终于被捆绑在“戊戌六君子”的名单里,挤进了历史通识课本的花名册。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毕竟是有名有姓的,如一枚确凿无疑的钉子,打进了一个民族记忆的墙面。不过我依然疑心,那些经历过高考锻压的学子们,事隔多年之后,是否还真的记得有一个叫林旭的历史人物。这个名字太过平凡了,以至于失去了让人产生兴致的记忆点。相比之下,在戊戌变法的人物名单里,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的名字皆是极具识别性的,似乎让人看上一眼,就舍不得忘掉。即便是刘光第,其名也是要比林旭给人印象深刻。后来我试图去解读林旭,才知道其名为旭,字为暾谷——其字虽然貌似生僻,多少总算是恢复了些个性,隐藏在名字背后的历史形象,也变得鲜明一些了。
当然,将一个历史人物的命运压在一个名字上面,不仅偏执,而且主观,近乎迷信。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出更加充足的理由,来说明林旭之所以容易被忽略,是因为历史对他太吝啬了,不曾拿出足够的叙事篇幅,就像对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一样,给予浓墨重彩的书写。于是,当我试图为林旭重新做一次历史定位的时候,不免生出了非分之想:即便他不能与康、梁相提并论,也应该和谭嗣同并列,获得对等的历史待遇吧!康、梁是戊戌变法的主谋,却逃脱了被慈禧太后诛杀的命运,因而在后来的岁月里,尚可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历史解释权。而谭嗣同属于另外一种情况。他是血溅刑场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与林旭、刘光第、杨锐、杨秀深、康广仁同时被杀于北京菜市口。他们的生命终结于戊戌年八月十三日(公历9月28日),似乎有命运主宰之手,对他们同时按下了死亡计时器。
但历史还是偏心了,给予谭嗣同的记忆闪光点,要远远多于林旭,也多于“戊戌六君子”的任何一个受难者。别的且不说,谭嗣同留下的绝命诗,其中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句,至今是广被传诵的。林旭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几乎没有人可以脱口而出林旭写过的某一句诗,或者说过的某一句话。哪怕是一句口号也行啊。事实上,林旭也是写过绝命诗的,题为《示复生》。复生就是谭嗣同。
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
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短短一首诗,多处埋设了典故和暗喻,要想脍炙人口,自然是很难的。即使将这首诗翻译成大白话,也无法被口口相传。它太像一首诗了,以致于失去了口号般的社会性广度。然而也正是通过这首诗,后人可以看到,林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段恢复了一个诗人的本色。他是低回的,内省的,悔悟的。甚至是有所畏惧的。诗人有可能会成为英雄,却天然不是英雄,而是在精神形态上比英雄软弱且纠结的纤细个体。他们在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双重召唤之间踌躇反复,在光明与黑暗的边界无地彷徨,因而通常仅在纯粹的精神界限之内成为一个受难者。英雄却不是这样的。英雄服从于某种集团性目标的指引,将内心世界毫无保留地托付给外在世界,在遇到生命危机时,则视死途为星光大道。
谭嗣同就是这样一位英雄。维新变法陷入绝境,他临危而不退。慈禧太后下捕杀令,梁启超劝逃,他誓言变法需流血,“请自嗣同始”。至于他在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更是像极了历史正剧里的典型人物,似乎在历史帷幕之后藏着一个导演,在戊戌年的这一天安排了一个如此入戏的角色。
相比之下,林旭要暗淡得多了。
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延揽人才,推行变法。是年七月二十日,经翰林学士王锡藩举荐,林旭获得光绪皇帝擢拔重用,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四人同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军机章军,又称“小军机”,是清帝国权力中枢军机处的组成部分,由皇帝直接掌控。这也就意味着,林旭一夜之间平步青云,且身临君侧,直抵圣意。此时,林旭虚岁二十四,刚刚经历了两次会试不中的沮丧,并将这种沮丧转化成一种外部狂热,呼应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
大概林旭自己也不曾想到,皇宫大门会如此意外地向他敞开。如果做时空换算,四品卿衔,相当于今天的厅局级政治待遇了吧?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今天又能做什么呢?大学毕业不久,或许正因求职而四处碰壁,或许运气好一点,已经考中了公务员,但也只是一个普通科员而已。以今天的官僚制为参照,几乎没有任何一条特殊的通道,可以让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步入与清代四品官阶相当的权力层级之中。在林旭那个时代,这样的奇迹也是不多见的。想到这种概率之小,他必然生出了“一夜看尽长安花”的人生快意,且发誓一定努力,不负圣恩。
林旭的确是一个勤奋且高效的办事人员,据说光绪颁布的变法上谕,不少出自其手笔。光绪既因变法而识用于他,他也就必然要在变法主张上特别用力,恰如杨锐对其评价道:“日夜谋变更一切甚亟”。有多种不同角度的史料可以说明,林旭行走军机章京,在变法主张上表现出一种激进姿态。回过头来看,如果变法不是这么快就遭遇颠覆性挫折,以林旭的做事风格,确有可能施展一番抱负。可是从七月二十日入朝,到八月初九日被捕,在短短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他的一腔热情又能付诸多少现实呢!历朝变法,必然遭致守旧势力的绝地反击,而当变法面临绝境之时,林旭的激进则变成了章太炎眼中的“佻达”,“先逮捕一夕,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章太炎的说法多少让人起疑。通过郑孝胥的日记可知,林旭被逮捕的前夜不是去了教堂,而是去了郑孝胥住处(当然,也有可能两个地方都去了)。
夜,月明,与谅三谈。既寝,暾谷忽至,复起,谈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
戊戌年的北京秋夜,没有雾霾,空气清澈而冰凉。但我能想象得到,此时的林旭一定是内心深锁浓雾,四顾茫然。他深夜去访“乡党”郑孝胥,是要寻求解脱之法,试图与“康党”撇清关系。
挖出这些历史细节,并不是要奚落一个多少还蒙着一层面纱的历史人物。我只是从中看到了平凡的真实。一个再有抱负和雄心的人,也是可以有怕的。事实上,从一个凡人的角度来看,林旭要比谭嗣同来得更加真实一些。八月初五日,他到郑孝胥处,说到太后欲“清君侧”,“上势甚危”,并与郑孝胥商讨避祸之法。由此想来,他似乎还有临阵逃脱的时机和可能。然而,他终究还是正视了死亡的来临。可以确信,他还想活,不甘愿就这样断送了性命,但他也知道报答圣恩的重要性,以及在污名中苟活的代价。正是这种左右为难的复杂性,使得林旭与一个纯粹的英雄相去甚远,也与谭嗣同拉开了距离。
林旭少孤,但在各种似是而非的传说中,他却是一个胸怀凌云志的少年。的确,通过林旭遗留下来的一百多首诗,依稀可见那种不能抑制的抱负,以及一般儒生都会有的感时忧国的情怀。但我理解,林旭的人生理想,更多是代表了一种顺从式的世俗逻辑,不仅要功成名就,而且要荣归故里,现世安康。世人嘉许的大志,是以俗世功名为坐标的,倘若一个少年立志为理想赴死,这样的大志不仅不被俗世理解,而且难免沦为“短命鬼”之类的流言谶语。林旭两次会试不中,留在京城寻求政治机会,在我看来并不是为了当英雄,而是为了干大事。当英雄与干大事,似乎都朝着一个宏大目标而去,但终究是错位的。前者的追求止于自我的毁灭,朝着一个绝对理想的、甚至是虚无的世界冲去;而后者的追求止于功德的圆满,将功成名就定制成平凡的人间目标。
这么说来,将林旭列在“戊戌六君子”之中,多少是有一点历史误会的。我翻阅了不少史料,并不曾见到林旭有着舍我其谁的豪情与执念。而他对待康有为及其变法主张,在态度上也并非始终如一。丁酉年十一月,林旭致信好友李宣龚,谈及康有为,言其“日有是非”,而自己“欲避未能”。可见他对身陷舆论漩涡的康有为是被动接受的,近乎半推半就。但林旭是想做大事的。一个想做大事的人,碰到了一个有政治野心且极富煽动力的意见领袖,情形就可想而知了。他最终成了康、梁变法主张的追随者之一。但很难说,他对变法能有几分主见。百年之后,有一部堪察颇详的资料汇编,以日为单位,密密匝匝地记录了戊戌变法当事者和旁观者的言行。我希望能在其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证明林旭是有所作为的。但是涉及林旭的资料极少,明确出自其手笔的文献,更是几近于无。经过百年淘洗,时间并没有真正选择这位多少有点冒进的男子作为“戊戌变法”的历史代言人。而他匆匆被斩,在官方口径中也不是被赋予维新变法的崇高名义,而是被冠以“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的罪名。如此接二连三的命运错位,不是林旭预料得到的,也不是他愿意接受的。
重新打开“戊戌六君子”的标签,我们看到的,是一次匆忙的历史打包行动。慈禧太后根本无心审讯,一声令下,将六个各怀心思的角色推向了刑场,就像一个在家闹翻了的主妇,将各种家什一股脑儿抛出了窗外。在这一刻,天下子民见识到了一个女人的雷厉风行的威力,也目睹了历史的粗暴逻辑对个体生命的无情摧毁。以“康党”之罪论处“六君子”,林旭不算是最冤的。他不像杨锐与刘光第,对康氏学说颇为不屑,甚至厌恶,只因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就被打包问斩了。林旭确实与康有为有着难以撇清的关系,死罪难逃。前期尚且只是附和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属于政治维新,不致于死。到了后期,“康党”意图在颐和园围杀慈禧太后,其性质已演变成一种夺权革命了。革命必然是要流血的。但若因此论断,林旭留京谋职是冲着变法或革命而来的,同样是一种误会。在各种与林旭有关的历史脚本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个手勤脚快的年轻人,在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之间来回穿梭,就像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他不过是想通过某种勤勉的付出,来赢得宏图大展的现实人生,不料倏忽间误入迷局,最后葬身在一次政治风暴之中。
时代的风暴就这样匆忙带走了一个年轻的配角。风暴平息之后,康、梁开始塑造“戊戌六君子”的形象丰碑。但是出于历史叙述的简便,丰碑上的主角只能有一个,他就是谭嗣同。按照今人对史料的分析,谭嗣同留下的绝命诗,其中最被传诵的两句并非谭氏原创,而是出自康、梁的篡改。只有这样,才有助于谭嗣同的英雄形象飞翔起来。康、梁如此重视谭嗣同的形象修饰,不全然是偏心,而是因为在“戊戌六君子”的历史原型中,唯有谭嗣同最接近理想类型的主角。他不仅是有主见的维新者,也是九死而不悔的革命者。而林旭呢,他只是一个配角。当然,配角也不可缺少,那就以康有为的追随者来定位吧。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日复一日的意义再生产中,主角的形象愈发丰满,而配角的形象则日渐萎缩,就像墙上的那枚钉子,在时间的氧化中被锈蚀,在被遗忘中自我遗忘。
在汗牛充栋的戊戌变法史料中,似乎找不出几许材料,可用以钩稽一个稍微完整的林旭形象。我也不曾见到,有哪个好事者,愿意以林旭为主角,重新叙述一段有声有色的戊戌变法史。直到我读到南帆的《戊戌年的铡刀》,那个面孔斑驳的林旭才开始恢复了些许血色,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丝生动的气息。
一个地道的福州人写另外一个地道的福州人,即便不做考证,但凭精神嗅觉,也有可能抓住他人无法轻易抓住的可靠的线索。让我尤其感到过瘾的是,南帆采用了一种在他看来最可信赖的文学叙事方法(而不是史学叙事方法),让一个在僵化的历史范畴中陷于绝境的人物得以复活。在南帆笔下,哪怕是那些流播于福州乡亲之间的传说,也可采撷为原料,用来修补林旭的多重面相,重新假设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的确,历史不是一条线,而是人类表情记忆的魔法包,内含多重皱褶的构造,每一重皱褶里都隐藏着不同的历史面孔,恰如黑格尔曾经分类过的,历史可以表现为原始的、反思的、哲学的不同形态。我略微感到不满足的是,黑格尔不曾为“文学的历史”确立一个应有的位置。这种历史建立在想象性叙事之上,其初级形态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小说,恰如班固定义的,“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它是虚构的,无中生有的,甚至是添油加醋的。但它也是真实的,代表了一种由旁观者的隐性态度构建起来的客观历史。
二
南帆写道,沈瑜庆回闽扫墓省亲,在一位私塾先生的手里读到林旭的诗文,打心里喜欢上了这个青年的大气之象,因此当即决定将其大女儿沈鹊应许配给林旭。这个才子佳人式的故事,当然不是南帆首创,而是在不同的历史脚本中有着相似的记录。不过,当南帆说到“沈瑜庆就是看上了林旭隐藏在笔墨之间的雄心大志”时,则是发乎一己之想象了。这种想象当然是合乎常识的,可以在一般的俗世逻辑里找到充分依据。沈瑜庆是晚清重臣沈葆桢第四子,系出当时福州最富名望家族之一,且大半生行走于帝国官场之间,晚期一度官至江西、贵州巡抚。他能称心的女婿,自然应是栋梁之材,必合经世致用之标准。可是,如果想象是被许可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斗胆猜测另外一种可能呢?就让我们想象,沈瑜庆仅仅是发现了林旭的文才禀赋,“异其博赡”,就已心满意足了。别忘了,沈瑜庆虽为食君之禄的帝国官员,但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同光体”诗人。
在新旧文学交替之际,“同光体”算得上中国旧文学的最后一枝新芽,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守旧诗人中间,一度也光鲜绽放了几十年。这一派诗人,主要集中在闽、浙、赣三省,但首倡者在闽,集大成者亦在闽,其精神发源地就在福州三坊七巷之内。三坊七巷是个古老街区,三条坊和七条巷分列在一条中轴街两侧,呈鱼骨型布局。中轴街南北走向,名叫南后街。街西侧连接三条坊,自北向南依次是衣锦坊、文儒坊和光禄坊;街东侧连接七条巷,依序是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和吉庇巷。在光禄坊内,有一处高地,名为玉尺山,原本为乌山余脉,高不足层楼,如今四周皆为平地,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土丘了。土丘之上有亭台,亭台边上有一块巨石,上刻“光禄吟台”。据传,北宋时这里是一座寺院,由于时任福州太守的光禄卿程师孟常来此地吟诗雅集,从此成了一个重要地标。至于那座寺院,几经兴废,最后也变成了在名流之间辗转相传的深宅私府,名叫“玉尺山房”。我的思绪在这里停留了许久,仅仅是因为,当“玉尺山房”在同治年间落在一个名叫李端的富商手中,谁也不曾预料到,这里竟然成了“同光体”诗派的发源地。
李端出身盐商世家,并无诗文建树。但他四个儿子的其中两个,大儿子李宗言和二儿子李宗袆,却热爱捣腾一些与诗歌有关的事。他们以“光禄吟台”为基地,成立“福州支社”,每月组织诗会四五次,坚持达十数年之久。据说诗社成员有十九人。这个数字准确与否,具体都是哪些人,我没有做过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其中有几个人,包括陈书、陈衍、郑孝胥、陈宝琛、沈瑜庆等,都是“光禄吟台”的常客,后来都成了“同光体”诗派的中坚力量。当然,还有林纾,他似乎并不怎么认同“同光体”,但也是这个诗社的重要成员之一。“同光体”这个说法最早是谁提出的,已无法定论。一说是陈书,一说是陈衍。他们两个其实是兄弟。无论如何,真正把“同光体”推向全国的,是陈衍和郑孝胥。那已经是光绪九年之后的事了。当年纯粹为诗歌而聚的青年,心中已被更多事务占据。他们多数外出求取功名,水流云散,“光禄吟台”也不复往日热闹了。但不能说这就是诗社的终结。当陈衍、郑孝胥在北京鼓吹“同光体”时,当年在那个土丘之上反复切磋出来的火花,已经开始向全国诗坛蔓延了。
此时,林旭来得正是时候。他已成长为慧颖特出的少年,“出语惊其长者”,并且被“同光体”诗人沈瑜庆盯上了。试想,如果沈瑜庆不爱诗文,他光顾私塾的概率就要小很多,林旭被他赏识的可能性也就更小了。至于他们最后建立了翁婿之关系,确实不能忽略了诗歌给予他们的缘份。其时沈瑜庆正处于事业上升期,辗转奔赴于江淮、湖广各地,随行人员不少,其中陈书、李宣龚、林旭和沈鹊应皆能诗。在处理政务之余,沈瑜庆没让一行人闲着,而是“日课一诗”,不数月成一集。通过这种方式,沈瑜庆搭建了一个移动的“光禄吟台”,所到之处,必有“同光体”同仁应酬唱和,不管是身在他乡的福州老诗友,还是外省的新诗友。而林旭呢,无疑是这个文学社交平台的最大受益者。他在二十岁左右就开始出入于名流圈,且颇受器重。
说这些,是因为在“戊戌变法”之外,我看到了林旭的另一个人生剧场,和另外一种剧情的可能。这个剧场的中心不再是北京的皇宫,也不是菜市口,而是福州的三坊七巷。在这里,一个庞大的姻亲家族,试图通过诗文传承的方式,来延续一种古老的美学趣味和光荣梦想。这个家族以沈家为中轴,以姻亲为纽带,形成了延续两代人的“同光体”诗群。第一代有陈衍、陈书、郑孝胥、陈宝琛、沈瑜庆、何振岱等,第二代有林旭、沈鹊应夫妇,以及李宣稠、李宣龚兄弟。无论是当时的人来看,还是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林旭在这个群体中的位置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就处在纵向传承的中轴线上。我猜想,沈瑜庆如此看重林旭,一方面固然是识才,另一方面极有可能是因为林旭早孤。按照民间的一般经验,沈瑜庆招了一个女婿,实际上等于多了一个儿子。因此,我宁愿相信,沈瑜庆视林旭为己出,是把他当作沈家的继承者来扶持的。我对沈瑜庆的政绩,并无深刻印象。倒是他的厚道勤勉,以及对诗歌的热爱,在我的脑海中极为生动。他自己爱诗,而且竭力把这种热爱传递给子女,因此让沈鹊应自小跟从陈书、陈衍习诗。后来招林旭为婿,自然也是这般培养他的。
林旭生前留下了一百多首诗,大多是在跟随沈瑜庆之后创作的。他没能多写一点,确实可惜了。但仅凭这一百多首诗,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林旭都得到了同行的足够重视。褒贬倒是要另当别论。挺林旭者自然不在少数,甚至有人认为,林旭“年少能诗,卓然可传者”,可与唐李贺、宋王逢原相提并论。也有人对林旭的晦涩诗风极有意见,就连颇为赏识他的陈衍,也只能带着一点遗憾说道:“在八音中多柷敔,少丝竹, 听之使人寡欢。”我以为,这些意见未必说得到位。批评林旭的诗苦涩幽僻者,不应忽略其具体成因。姑且不说林旭少时失去双亲的晦暗心境,单论习诗这一点,他起先师法宋代诗人陈师道—— 一个经常闷在被窝里苦吟的诗人,不涩不僻才怪呢!况且“同光体”以宋诗为宗,而林旭野心极大,对宋诗诸家多有兴趣,“在乎能驭众派”,因此在早期阶段难免用力过猛,写得磕巴一些。至于将林旭与李贺、王逢原相提并论,则近乎浮夸了。我倒不是怀疑林旭,而是怀疑“同光体”。这一派诗人主张学步宋诗,策反明清诗人“诗必盛唐”的主流陈见,多少显示了一种革新精神,但终究是在旧诗的框架里作一种无谓的挣扎,其实是不具有时代预见性的。“同光体”闽籍诗人中,最有成就者,当属陈衍和郑孝胥。但是放到整个古典诗歌史里,他们的作品就没有让人记住的理由了。历史更愿意记住的,是陈衍的诗论,还有郑孝胥的书法,以及他的伪满洲国总理的身份。不是因为他们缺乏诗歌才情,而是时代不再给他们机会。
要让林旭在“同光体”的框框里捣腾出多大的诗歌成就来,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但我并不怀疑,林旭可以在另一个层面创造出杰出的文学成就。我读他的诗,有一个总体印象,就是林旭擅论。换句话说,林旭是为讲理来写诗的。他在狱中写下的《示复生》,就是“讲理诗”的典范。诗人身陷牢狱,有悲愤,有悔恨,但这些情感都被抑制在表面修辞之下,呈现在文字上面的,则是一种理性的议论:复生啊复生,你当初真该听我的,袁世凯是不可靠的,如果请求董福祥的援助,结局或许就不是这样了。根据看管林旭的值班狱卒回忆,林旭在狱中极为镇定,美秀若处子。这个细节虽然不能得到更多史料的印证,却是可以和林旭的那首“绝命诗”相匹配的。在天旋地转之际,林旭尚且能够如此克制情感,不是谭嗣同的慷慨激昂,也不是康广仁的以头撞壁。那么林旭的夫人沈鹊应呢?她是林则徐的曾外孙女,沈葆桢的孙女,沈瑜庆的大女儿,自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面对丈夫的死亡事件,她是如何反应的?
绣佛旧妆楼,我已君休。
万千悔恨更何尤。
拼得眼中无尽泪,共水长流。
沈鹊应作词,是不讲理的。但她也不做英雄状的抒情,而是向内诉诸衷肠,曲折委婉,却毫无保留,直至最后情感透支,容毁身亡。林旭、沈鹊应向陈书习诗词,陈书因材施教,与林旭言诗,与沈鹊应言词,并做了一个预言:“夫二子者之作, 必传无疑。”这个预言是否下得太早,暂且不论。但陈书以诗、词分别施教于二者,当真是有过人眼力的。林旭擅论,沈鹊应有情,二者之区别,恰恰也是我们识别宋诗与宋词的重要依据之一。诗乃各种文学体式之正统,在理学兴盛的宋代,已被士大夫赋予了空前强大的载道功能,在诗中说理的气氛也就特别浓厚了。而那些被诗歌排挤出来的俗世里的欢娱与苦痛,只能寻找一种新的载体,于是也就有了宋词的兴起。陈衍说林旭的诗“听之使人寡欢”,其实不是林旭个人的品格,而是宋诗无处不在的基调。被说理气氛包围的宋诗,必然是一幅过于老成的面孔,丧失了感性和浪漫的生气。因此,胡云翼有论,宋诗缺失了唐诗的“活泼浪漫气”,“俨然少年老成”。
林旭以诗讲理,当然不像现在的一些官员,赤裸裸地直喊口号或直发议论,而是如儒生论道般,铺设各种典故,通过案例分析来呈现观点。本质上,这是一种论文写作,其文本框架由论点、论据以及被省略了的注释构成。《示复生》这首诗,一度被怀疑是否出自林旭之手。陈衍为其辩护道:“千里草二语,实有论议而主张之者。但以诗论,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乃追溯未败之前,吾谋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不用之咎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时揣摩后山(陈师道)绝句深有得者,岂能为此,舍暾谷无他人也。”陈衍的说法,当然也不能证明那首诗就是林旭的作品,但至少说清楚了林旭写诗深得论理之章法。
讲理抑制了诗人的情感流畅性,因而有涩、僻等问题的产生。但这又未尝不是另外一件好事,足可让人预见林旭的天性中还有得天独厚的一面。我隐约觉得,倘若林旭笃志于文学,极有可能始于诗,成于诗论。这个辉煌的文学过程,最后由他的“同光体”前辈陈衍完成了。在新旧文学交替的时代,陈衍的诗在中国旧诗人中可谓风光无限,但是毕竟雨打风吹去,虽勉强守住了古典,却没有创造出经典。但他的诗论,单凭那一本厚厚的《石遗室诗话》,却在文论史上树立了一座高峰。钱基博称赞陈衍是“并世文章之雄”,倘若没有其诗论作支撑,这样的高度评价恐怕要轰然倒塌。再往大一点说,若是没有陈衍最后集理论之大成,“同光体”在整个文学史上的份量也是要大大缩水的。我读《石遗室诗话》,深为叹服陈衍的专业识见,且颇为他的新鲜意见所打动。他虽以旧诗遗老自居,却对传统文人喜好的“模糊惝怳欺人之谈”甚为不屑,往往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旧诗的问题,颇有一些现代人的头脑。在此意义上,他不再是守旧者,而是推陈出新者。陈衍对文学史的最大贡献,或许就是挑动了唐宋诗之争,从而推动了二十世纪宋诗研究传统的形成,这其中卓有成就者,就包括与他有过师生缘份的钱钟书先生。我常想,在这个代际推衍的文学基因链条里,林旭应该是重要的一环。他与夫人沈鹊应都跟从陈衍习诗,且与陈衍一样,他也拥有一个擅长说理的头脑,其实是最有可能把“同光体”带到新的时代语境里去。
戊戌年春天,林旭曾与林纾同游杭州。闻京城出现了维新变法新机,他毅然北上,而林纾则因刚刚续娶娇妻,留在了杭州温柔乡。从此天地两隔绝。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南帆从中看到了两个人的政治命运的相互观照。他说,林旭固然早死,林纾却没有走得更远,而是成为与时代潮流相悖逆的大清遗老。这是从大历史观中必然得出的一个结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线性时间,将历史滚滚向前推进。但我以为,一个人的文学生命,却未必要受到这种线性时间的裁决。“诗比历史更永久”。林纾虽然在政治上走向极端守旧,却不防碍他成为英雄式的文学巨星。陈衍也是。事实上,“同光体”大部分代表性诗人,在大清王朝覆灭之后,均以遗老自居。如果林旭不死,大概也难逃此中圭臬吧?但我依然相信,如果林旭继续在文学剧场里演绎自己的人生,他是有望成为一个文学英雄的。
但时代终究没有给林旭这个机会。事实上,我的假设一开始就不成立。沈瑜庆确实热爱诗文,并且希望通过诗文传承的方式,为一个家族的持续繁荣注入精神活力。然而,临到头,这些都只是一场幻觉。如果这种幻觉一开始尚且是可靠的,那是因为在古代中国的官僚体制里,通过科举取士这样一种精密机制,有用的政治和无用的诗文被巧妙地捆绑在一起。但是,一旦落到俗世处,政治总是要先行的。林旭两次会试不中,沈瑜庆就为他捐了个官,在京城里呆着,等待更大的政治机会。后来,就在林旭被召入宫前不久,沈瑜庆又通过曲折途径,将其荐入直隶总督荣禄幕府。瓜尔佳·荣禄,满洲正白旗人,出生于福州,会讲福州话,对福州籍士子颇为优待。他本该好好栽培林旭的,但他是慈禧的宠臣,最后也是他,奉命捉拿林旭,“骈而戮之”。沈瑜庆一定是悔不当初啊。但这又岂是沈瑜庆自己能左右的宿命?走进三坊七巷,在每一条坊或巷的路口,游人都可见到一块导游牌,上面介绍说,某某年,这里出过某某官员,这条坊巷因他改名,又过多少年,这里又出了一个更大的官员,坊巷再一次改名。那些天真而好奇的游人啊,有谁读懂了这其中的洗牌逻辑呢?
或许,林旭和他的岳父沈瑜庆,都曾经对着某条坊巷出过神,甚至生出了一种预感,某条坊,或某条巷,将有一天因他们的存在而改名。但这只是一种幻影,明白过来时,已物是人非。林旭在郎官巷的故居,至今是一个谜。有人说是在巷东头,也有人说是在巷中间,即后来被福建督军李厚基购买下来转赠给郑孝胥的那座宅子。但无论如何,他在郎官巷出生和成长,大抵上是不会有错的。我曾无数次走进这条巷子,却不曾见到哪个院落的门口挂着“林旭故居”的牌子。想到这个曾被我反复疏忽的空白,我突然间对“人去楼空”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
林旭故居不可考,实则是一种深刻的民间遗忘。在闽地社会,一个人短命,或非正常死亡,都是被极端忌讳的。林旭被斩后,残尸运回福州,但不入家门,而是停放在东郊的地藏寺。从此多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被隔绝在生者的世界之外,甚至被极力抹除曾经有过的生活痕迹。如果林旭不是喋血刑场,而是以诗人或诗论家的身份老死,他与故居的联系,恐怕不会这么轻易消散吧?
三
林旭生涯虽短,却有幸身后留名,被打包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档案夹里面。一个档案夹叫“戊戌变法”,一个档案夹叫“同光体诗派”。联系到他的个人命运,这两个档案夹实则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一种是政治,一种是文学。然而不幸的是,无论在哪一条道路上,林旭都没有成为自己的命运主宰。如果历史允许再做假设,林旭或许可以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更长远,就像他的前辈陈衍,或者像他的后辈钱钟书,成为一个文学英雄。这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同时也是自我设限的英雄。这个英雄以文字为囚,在纸上寄托对俗世的关怀,最多也只能在书斋里闹闹革命罢了。可惜,这个可能的文学英雄尚未形成气候,便在一次偶然迈出书斋的远行中走失了。他走进了另外一个历史档案夹,卷入一个时代的风暴之中,很快被摧毁了。
我试图通过一种想象性叙事,来复原这个走失的文学英雄。但在事件史层面,这个名叫林旭的文学英雄并不曾真正存在过。就连他的走失,也只是一种虚构出来的隐喻。但我相信,这也不是无稽之谈。因为在观念史层面,这个被虚构出来的文学英雄,恰恰代表了一种历史真实。一种有关于态度的历史真实。这种态度并非是肯定性的,或者否定性的。准确地讲,它是试探性的。它的具体含义就是,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人生道路,其可能性在哪里,其限度又在哪里。
我猜想,林旭不曾思考过这种可能性及其限度。不仅仅是因为他走得匆忙,还因为时代不曾赋予他这方面的问题意识。但我们不能说,林旭就不曾对这样一条独立的人生道路有过朦胧的向往。这种向往也不是毫无依据的。在他之前,在孔子之后,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人生理想,一直若隐若现,绵绵若存。当曹丕说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是说文章可以经国,而是说文章的重要性不输于经国之大业。杜甫本出经学世家,却误入文学歧路,被时人指责不务正业,以致他在晚年不得不为自己辩解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某种意义上,曹丕和杜甫都试图为文学这个可能的独立王国立法。但以往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终究是小道。只有通往政治,汇入大流,直至成为俗世里的水乳交融的部分,它才有可能成为大道。当杜甫说出“法自儒家有”时,其实已经暴露了他对文学的不自信了。文学固然有其独特之法,却必须源自“儒家有”。这便是杜甫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吧。如果杜甫一生仕途得意,他的才华或许将损耗于事功之学,其文学成就也就要大打折扣了。这么说来,他的诗圣之名,其实是一种被动的产物,而非自觉的成果。
这是杜甫的侥幸,林旭却没有。
在初到北京的几年,林旭虽已不常在沈瑜庆身边,但写诗在他的生命中已然占有习惯性的重要位置。他写出了两次会试不中的个人抑郁,和国势衰颓的感伤。但他终究抵挡不住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煽动力。梁启超劝说道:“词章乃娱魂调性之具,偶一为之可也。若以为业,则玩物丧志,与声色之累无异。方今世变日亟,以君之才,岂可溺于是。”林旭真是求成心切啊,“幡然戒诗,尽割舍旧习”,转而跟从康有为学习经世致用去了。其实林旭还是心有不安的。所以他才会写信给李宣龚,说自己实在是逃不过康有为的灵魂渗透。他甚至觉得自己对不起李宣龚,“深愧吾友闭门之贤”。所谓“闭门之贤”,正是一种自我设限的人生世界,一种独立的人生道路。李宣龚识得这条路径,林旭岂能不曾领会?
陈衍曾对林旭的诗作下过一个精辟论断:春夏行冬令。按照中医的理解,时令错乱,实非常道。后人据此更是确信,林旭的诗乃为涩体,晦暗难解。但我理解,这话还可以有其它的含义。春夏当勃发,冬乃藏。在我看来,春夏行冬令,恰到好处地体现了林旭胸有豪情却隐而不发的精神品质。这是一种自我设限的德行,倘若转化为文学的志业精神,是可酿成大气候的。
但林旭终究没有守住这个界限。
在他那个时代,读书人固然晓得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美德,但这种美德不是目标,而是手段,一俟走出书斋,则如鱼入水如鸟腾空,必然深深迷恋于另一个天地的广阔,对现实的野心,对致用的渴望,也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即便是林旭的“同光体”前辈陈衍,虽毕生功成于诗论,但他终究也只是一个传统士大夫,不曾明确意识到,文学也可成为一种志业,虽为务虚,却有自己的边界,且可开拓出一条独立的人生道路。在戊戌变法前后,他畅言变法,应试“经济特科”,实非出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志业意识,而是呼应了传统读书人的功名意识的召唤。他对钱钟书的治学方向虽有至深影响,却不能说他培育了钱氏的志业精神。1935年,钱钟书留学英国,陈衍大惑不解,说国内已有文学,何须舍近求远?他当然不明白,国内虽有文学,但以文学为志业之精神,依然稀薄。钱钟书留学欧州,固然也不是冲着某种明确的志业精神而去的,但最后,也许是一种意外的收获,他必然受到了这种精神的熏染。此时,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发表《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两次著名演讲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以志业为根基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在欧洲已渐成气候。我常想,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志业精神,隐含着某种认知自我和世界的独特方法,使得钱钟书回国后,不曾在极端年代的政治狂流中迷失了自己。我又想,倘若钱钟书早生一个时代,其人生轨迹是不是也如林旭一样,虽不致死,却也是功名累身呢?
这么想来,我倒是叹息林旭生不逢时了。他确实有望如钱钟书这般,不为时务所惑,成为一个自我囚禁的文学英雄。
(责编: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