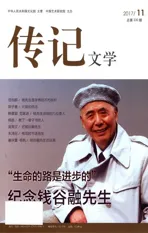一部“个人”的史诗
——传记电影《戏梦人生》评析
2017-11-20黄亚利
黄亚利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台湾“新电影”在1980年代兴起并引人瞩目,以侯孝贤、杨德昌、王童为代表的导演及其作品不仅引起台湾影坛的变革,也成为世界电影的财富。他们放弃了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着力于讲述普通人自己的故事,微观呈现生命个体在历史时空中的不同命运及遭遇,或者去揭示历史遗留给后世的种种困扰。侯孝贤的《戏梦人生》《童年往事》和王童的《红柿子》等传记电影,都将镜头对准历史洪流中的普通人,呈现随着历史的沧桑变化,人也随之迁徙、漂泊最后落地归根的个体命运。
侯孝贤电影“悲情三部曲”之一的《戏梦人生》讲述了台湾布袋戏表演艺术家李天禄的前半生(1910-1945)历程,包括他的成长、家庭、事业和爱情,记录了李天禄及其家庭在时代潮流中的命运沉浮,不仅反映了台湾日据时代普通民众的境遇和心理,也通过个人历史经验折射出台湾殖民地时期的历史风貌与社会变迁。影片在叙事上采用了传记人物口述与戏剧性演绎相结合的手法,虚实间实现了历史时空和现实时空的对望。散文式长镜头的影像特点,延续了侯孝贤一贯的纪实风格,又透露出浓浓的诗意。
值得一提的是,由侯孝贤策划,根据李天禄的口述回忆还完成了著作《戏梦人生:李天禄回忆录》(曾郁雯,台湾远流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音乐专辑《戏梦人生》(陈明章,1993年)。电影《戏梦人生》在1993年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李天禄和侯孝贤一起参加了颁奖典礼,李天禄戴着墨镜出席,魅力无限。

传记电影《戏梦人生》海报
一部“个人”的史诗
李天禄作为布袋戏表演艺术家,在戏台上一直是扮演他人的人生和故事,而在电影《戏梦人生》中,他成为主人公,在镜头前娓娓讲述自己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1910年,李天禄出生于台北一个布袋戏世家,父亲是华阳台布袋戏剧团的团长。李天禄8岁开始学习布袋戏,由于天资过人,领悟力强,14岁便出师担任主演。20岁时入赘陈府,娶妻生子。22岁独立门户自组“也像生活”剧团,四处演出,在台中邂逅了妓女丽珠。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殖民当局下令禁止台湾所有户外演出,只准演出日本戏。受此影响,李天禄不得不暂时封箱,改行做生意,也曾到歌仔戏团、客家戏团当导演。而后,为了维持生计,应日本课长川上之邀,加入日本政府的宣传剧团“英美击灭催进队”,演出日本戏,后因与一名日本警察产生矛盾辞职,这也成为李天禄日后受到争议的一段经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局势影响,布袋戏无法再进行演出。台湾光复的前一天,在疏散过程中,李天禄的岳父和小儿子因感染痢疾相继离世。在这之前他也经历了与祖父母、父母的生离死别。台湾光复后,李天禄重新开始演出布袋戏。电影《戏梦人生》到这里戛然而止,令人怅惘。
电影《戏梦人生》所表现的李天禄的前半生恰巧与1895年日本割占台湾到1945年台湾光复这一时间段相重合。因此,以李天禄的命运轨迹为索引,不仅反映了台湾日据时代普通民众的境遇和心理,也呈现出那个时代的历史风貌。“民间历史一旦进入电影,其内隐的召唤结构必将激起民众的集体记忆,从而建构起与官方不同的民间历史。”《戏梦人生》中多视角和多语境的“个人”史诗化表现,一方面丰富了台湾电影关于历史与现实的探索,另一方面也从多种视角反映了台湾身份认同问题的困境和努力。个体历史经验是构成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因素又是外在表现,因此,传记电影“个人”史诗的叙述范式,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

传记电影《戏梦人生》剧照
虚实结合的叙事
《戏梦人生》作为传记电影出现了两个李天禄,一个是真实的李天禄,一个是虚构的李天禄。真实的李天禄以纪录片受访者的形式出现在影片里,结合导演编排演绎的李天禄故事,呈现出“纪录片与剧情片、传记与自传、呈现与再现”相融合的独特叙事模式。传统的电影叙事、李天禄本人的口述回忆(画外音和访谈)、戏剧舞台的表演(布袋戏和歌仔戏)三条叙事线索交织并行,互为推进和补充。故事扮演和现身说法的结合,使得电影所能承载的意义被放大,多视角和多语境的电影表现,体现出历史的复杂与难以言说。
影片中共出现九段李天禄的自述,李天禄每次在镜头中出现时,身后的场景都不尽相同。或是儿时学艺时住的木屋前,或是在台中和丽珠吃饭的桌子旁,或是颠沛流离中棺材房的床边。暮年的李天禄,身穿中式汗衫,戴着宽边圆礼帽,坐在电影故事中“李天禄”生活的场景里,缓缓地讲述自己的一生,不悲也不喜,像是往事太久了,过去的沉重都已云淡风轻。“因此我想一个人的运气,是不可能改变的,仅仅是因为在战争的最后一天我们被疏散,我的岳父死在奥李附近,我的小儿子毛里,在吃他妈妈的奶时就已得了这种病,当我回家时,我发现我的妻子在哭,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毛里在日落时分死了,我说那是他的命,他不想继续跟我吃了,我买了一些木板,钉了一棺材。我们请了一道士来埋他,以便他能再生。”真实与演绎、现世与历史的不断交错,带领我们穿梭在两个时空中,感受时间的变化和方向,在纪实与虚构之间,寻找时间的影子。
李天禄自传式的讲述,在影片和观众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在时空之间设立关卡,“可防止观众完全沉浸于封闭的虚构叙事和幻觉中,从而营造一种‘客观’的视听描摹与‘主观’的口头评述(或反之)、观者与被观看的文本之间的距离感和弹性”。同时,主人公的旁白,填补了影像表现的微妙细节和情感,突破了电影的时空限制,虚实间实现了历史时空和现实时空的对望。
此外,这种多视角和多元语境的杂糅互动、纪录片的特征与传记电影的叙事结构、自传式回忆与影像再现的电影手法,在传记电影表现中独树一帜,也是电影美学上的一次实验。

出现在电影镜头中的暮年李天禄
诗意的银幕时空
影片《戏梦人生》中沿用了导演侯孝贤一贯的影像特点,凝视般的长镜头、固定机位和全景拍摄。两个半小时的电影只有一百个固定镜头,(除了五个摇镜头)平均每个镜头长82秒,可以说“一场一镜”。影片的第一个镜头便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的固定长镜头(02:47-05:07),表现了李天禄的出生以及家庭状况。画外音是李天禄本人的回忆,讲述了自己名字的由来。这不禁让人想起侯孝贤的另一部电影《海上花》开头“吃饭”的长镜头段落。长镜头发挥了摄影机的“历史纪录”功能,最大程度上地还原了生活的本真。
《戏梦人生》在影像上的另一个特点便是散文式的电影节奏,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导演侯孝贤的文学素养,他曾讲到沈从文对他有比较深的影响。影片随着李天禄的口头讲述,将李天禄各个时期的人生境遇串联起来,“像云块的散布,一块一块往前叠走,行去,不知不觉,电影就结束了”, 片段式的影像呈现像记忆碎片一样散落在时光之河里。这种叙事模式和节奏不像传统传记电影那样,讲求叙事的起承转合,在情节和事件高潮中讲述人物传奇的一生,而是让观众随着传记主人公本身的回忆,去拼贴、抚平历史的残缺和褶皱。
《戏梦人生》中最突出的是对琐碎生活的描写,文学笔触的影像书写,弱化了电影的戏剧性。除了主人公李天禄以外,电影中的其他人物都十分模糊,缺乏连贯的命运交代。一些配角人物更是看不清楚样子,远远的只有一个剪影。镜头前的李天禄在讲述时,说的最多的是生离死别和宿命。在讲到母亲的死时,画面上呈现的是一些简单的生活场景:远山、行人、做买卖的大叔、扫地荡起的尘土。讲到祖父摔下楼梯过世时,画面内是远处的房子、行人的身影、燃烧麦秆飘起的浓烟。侯孝贤在表现生离死别时,没有刻意表现亲人的痛苦和挣扎,而是以白描式的手法表现了琐碎的日常,生离死别即生活本身。
侯孝贤曾说:“到后来才慢慢知道,电影其实就是某种情感时间和空间的凝结。”银幕时空与现实时空的界限逐渐模糊,情感的积淀散落在对琐碎生活的记忆中。
多重视角下的“日据时代”
影片在表现李天禄(1909-1945)前半生历程的同时,也借家庭和个人的历史横截面,反映了整个台湾在1945年之前的沧桑历史变化。李天禄个体命运的颠沛流离,及其亲人一个个逝去的无奈与忧伤,映射了殖民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命运变迁。
在对日本殖民历史的表述上,影片既没有像《一八九五》《赛德克·巴莱》那样呈现台湾民众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或日本殖民者的残暴镇压,也没有像《稻草人》《无言的山丘》那样着意渲染殖民统治下普通民众生活的悲苦。导演在表现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时,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多维度的关系。影片开头不久,当李天禄还是孩童时,日本警察来到他家里,要求所有人剪掉辫子,不过并非是强盗式的威胁恐吓,而是以平和的口吻提出,同时还给他们发戏票,邀请他们看戏,整个场景非常生活化。而在殖民后期,因战争局势的影响,日本加紧了对台湾的管制,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本土的布袋戏被禁止演出,进而建立宣传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英美击灭催进队”等宣传剧团,以及收编台湾戏剧艺人为日本服务。
此外,在对人物的刻画上也没有公式化,比如电影里的日本课长川上,他始终表现得彬彬有礼、平易近人,跟以往电影中粗鲁残暴的“鬼子”形象截然不同,对李天禄更是礼遇有加,将其视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并给予他丰厚的待遇,不仅给他很高的工资,还承诺保障他家庭的生活问题。而当李天禄决定辞职时,他也并无勉强,还邀请李天禄到其家中做客,袒露真情:“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见到你真是我的福气。”川上和李天禄的关系,在侯孝贤另一部电影《悲情城市》中也有所体现(宽美兄妹和静子兄妹之间的友谊),表现了导演对台湾/日本关系的思考:“国仇”不一定催生“家恨”。另一种日本人形象则是影片中终日酗酒的日本宣传兵库柏塔,他在台湾已经呆了10年之久,仍对台湾人充满芥蒂。他对李天禄的高薪待遇心怀不满,始终以日本人的优越感来看待周围的台湾人,在他看来李天禄始终是殖民地的居民,是低等的“第三阶层市民”。可以说,这两类日本人在当时都是客观存在的,由此也体现出侯孝贤导演对历史的客观把握。
影片所讲述的故事在日本投降的1945年结束,“台湾终于从日本中解放出来了”,普通老百姓把战争时留下来的飞机砸烂,变卖钢铁、金属,为的是筹钱请李天禄演出布袋戏,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神会给我们答案”。生活对于普通人而言,无论在战争年代亦或是和平年代,无论谁做统治者,都只是简单的一日三餐、四季更替和生死轮回。

导演侯孝贤
戏·梦人生
布袋戏在电影《戏梦人生》里具有多重的意义。“木偶”本身就具有极强的隐喻意义,其被操作的命运,在电影里是李天禄人生的隐喻,是台湾社会的隐喻,也是生活本身的隐喻。
木偶演的是人的生活,是木偶表演者李天禄的生存手段和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李天禄自己。影片开始时李天禄就讲到,他出生的时候,算命先生说他命太硬,为了改变福祸,他只好改叫自己的父亲为叔叔。人一落地,就跟命运联系在一起,人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生是,死亦是。青年的李天禄为新成立的剧团起名为“也像生活”,他认为“表演中的木偶就像人们,所以木偶剧也像生活”。侯孝贤说:“它代表的不只是李天禄对人生的态度,同时也包括我,或者说所有中国人民的情感。这部影片的结构是这些感情的具体表现形式,就像李天禄的木偶是他精神的具体化形式一样。”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进入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历史时期。布袋戏作为极具文化特色的戏剧形式,在台湾历史的流变中也经历了沧桑变化。戏剧表演(布袋戏和歌仔戏)在电影《戏梦人生》里多次出现,占据电影很大的篇幅。如果注意的话会发现,每次的内容和形式表现都有所变化,从《三仙贺寿》到《白蛇传》,再到《三藏出世》《五侠女大破龙潭寺》《七侠十三剑》。“皇民化”时期,日本人禁止台湾社会演出布袋戏,而只能改演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日本戏,表现台湾风情的布袋戏变成日本戏。李天禄为了生计不得不辗转于剧团之间,而后还加入日本宣传剧团“英美击灭催进队”,暗示了时代历史对文化的影响、对个体命运的影响。
木偶被操作的宿命似乎在暗示着无论是台湾社会、还是个体亦或是文化,都难逃被历史裹挟的命运。木偶戏(布袋戏)是生活,电影也是生活,也同样反映了导演侯孝贤的人生观和电影观。人生、戏、电影,戏梦人生在电影内外有了双重的含义。
电影《戏梦人生》与传统传记电影不同的地方在于,导演侯孝贤没有动用所有影像元素塑造李天禄这个银幕形象,而是将李天禄与布袋戏、历史、生活、影像融合在一起,于虚与实、写意与留白之中糅合成一个时空的镜像,如影似梦。“生者/死者、台湾/日本、戏台/人生,也只是天地推移的自然轮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