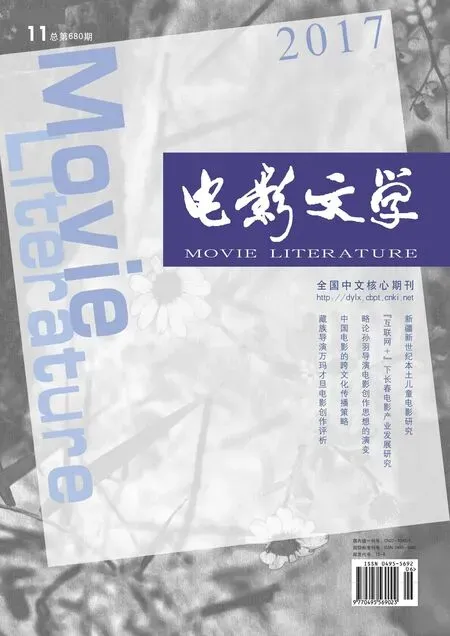论《荒野猎人》的殖民叙事
2017-11-16司方维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南许昌461000
司方维 (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电影《荒野猎人》的故事主线是格拉斯荒野求生为子复仇,故事却是以皮毛生意——欧美对北美的殖民为背景。殖民并不是这部电影的核心关键词,但电影回避不了的殖民叙事,也不仅是无关紧要的背景,白人主人公格拉斯一直在以殖民为网结勾连成的人物关系网络里挣扎,经历了身份的解构与重构。
一、殖民者视域下的殖民罪恶
皮毛生意之于当时成群结队涌入北美的欧美人而言,是充满冒险精神的西部拓荒史的一部分。《荒野猎人》原著小说的作者写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西部精神的向往,电影的主核也仍是求生与复仇,但并没有回避殖民的罪恶。
电影中的殖民罪恶集中在三个人物身上:格拉斯的混血儿子霍克、里族头领的女儿普瓦卡与格拉斯求生路上遇到的不知名的波尼族人。霍克是西进军队屠杀波尼族村落的幸存者,电影伊始就遭到了菲茨杰拉德的言语羞辱。被称为“野人”的霍克眼神中充满仇恨,他要反击却被格拉斯训斥。霍克的死亡并不是起于种族歧视的蓄意谋杀,而是源于人性自私的意外,如果霍克没有恰好回来看到菲茨杰拉德杀害格拉斯并反击,并不会被杀。但若不是因为他混血的身份,菲茨杰拉德也不会如此轻易下杀手。普瓦卡被法国人劫持为性奴的经历,是殖民与男权的双重悲剧。不知名的波尼族男人邀请重伤的格拉斯同行,为他治病,为他搭盖棚子遮挡暴风雪。风暴过后的白桦林,如此静穆与美好。镜头一转格拉斯就看到了被吊死的波尼族人,身上挂着“我们都是野蛮人”的牌子。这是无理由的种族残杀,电影还借里族头领之口说出:“你们的东西都是从我们那里偷的,所有的东西。”
殖民的罪恶非常清晰,但这并不是电影主要强调的。霍克的悲剧还没展开就以死亡告终;普瓦卡的悲情多在父亲的口述中,唯一的被强暴镜头也因为格拉斯的解救半途中止。波尼族男人的死亡最具震撼力,但用的也是较不血腥的吊死的方式。从格拉斯生吞牛肉、剖马腹取暖等情节看,这显然不是部风格内敛的电影。那么如此安排,还是与电影的叙事视角有关——“殖民者”。
这部电影的殖民叙事重点并不在控诉当年西进运动中白人对印第安土著人的残暴杀戮,也不在殖民文化冲击下印第安土著人的身份认同。霍克作为一个混血儿,其实是印第安文化与西方文明冲突的极佳代言人,但就像面临外敌的强势入侵印第安人还在自相残杀一样,电影对被殖民对象的问题点到即止。一部电影不可能面面俱到,《荒野猎人》的关注点在格拉斯——这个特殊的“殖民者”,在一系列人生悲剧的冲击后,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
二、殖民者的身份重构
如若说“被殖民者”这个曾在殖民者文化中被严重丑化的他者,其实并不是一无是处的“野蛮人”,那么“殖民者”这个自我在褪去了“文明”的光环后,也不是只有一个“残暴”的标签,尤其是当历史大叙述还原为具体的个体时。
电影有一个场景是格拉斯与儿子在丛林中猎麋鹿,轰然枪声打破了丛林晨曦的安详宁静,只剩下剥皮的血腥。这些猎人面对麋鹿这样温顺的动物时是强者,转眼却被印第安人偷袭,死伤惨重。后来,格拉斯又被凶残的灰熊所伤,性命垂危。这是很有意思的位置转换,以这些皮毛商人为代表的西方人对北美进行了无节制的掠夺,但因为个体生命的脆弱,又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与土著的追杀中扮演了“弱者”的角色,他们一样有背井离乡之苦,一样有性命之忧。即使无耻如菲茨杰拉德,也曾在里族人戏耍般的割头皮中体会死亡之恐惧。
格拉斯的境况更为复杂,他因为娶了波尼族妻子并生了混血儿子,还要遭受来自白人内部的恶意与伤害。菲茨杰拉德的种族观是当时白人的普遍看法,不然格拉斯也不会训斥儿子想活命就不要说话,因为没有人会听他说什么,而只会看他的肤色。格拉斯要带着霍克融入白人族群非常艰难,队长亨利同情霍克,也认为他将来最好回到母亲那边。格拉斯娶波尼族妻子的始末电影没有交代,也许也像当时很多白人一样,是为了方便与印第安人做生意,但他为儿子复仇的执念与一直出现在他梦境中的妻儿都说明他爱他的家人。但深爱的妻儿先后被“同类”杀害,他自己也被“同类”抛弃于荒野,这比灰熊的袭击与里族人的追击更让格拉斯痛苦,极大地冲击了格拉斯身为“白人”的身份认同。一直以来带给他伤害与仇恨的都是他的“同类”,反而是“非我族类”的妻儿带给他家庭的温暖,素不相识的波尼人救他性命,一直追杀他的里族人也在误会解除后停止了杀戮。
“身份绝不是‘首要的’,而是关系的产物。”[1]白人作为殖民者的身份建构中向来缺少被殖民者这个他者,格拉斯正视印第安文化,在具有“冒险精神”的文明人与亲近自然的“野蛮人”的矛盾冲突中,格拉斯倾向后者。他认同印第安文化,复仇结束后走向了波尼族妻子引领而去的灵魂栖息地。
三、人性:殖民与现代文明的交锋
格拉斯代表了一种打破种族歧视、跨越文化差异的种族观,在复仇的考验中重建了自己的身份。但若说格拉斯身份的重建是背叛了他原属的族群与文化,又不尽然。格拉斯的梦境中曾出现教堂的残壁断垣,残破的教堂表面上是西方文明的坍塌,尤其在教堂遗址中格拉斯还拥抱了霍克,似乎是在暗示他在西方文明与印第安文化中二择一。但细究格拉斯的人生抉择,他其实并没有完全背弃他的族群,他背弃的是殖民罪恶,是人性丑恶。
电影中没有交代格拉斯加入西进大军之初对印第安文化是何想法。就电影中展示的部分,格拉斯向印第安文化的靠拢,一部分原因是与印第安人长期共居所受的感召;另一个原因则是同类的逼迫。妻子死后,格拉斯在深知混血儿子受歧视的情况下,还是继续为白人工作,也朝进犯的里族人开枪。在复仇之旅的后段,他回到了基地,接受了队长亨利的帮助,并与其联手追杀菲茨杰拉德。格拉斯的回归是因为其他猎人并没有伤害他,吉米虽然软弱,却一直保留着人性中最善良柔软的部分;亨利作为领导者虽然魄力不足,但信任同情格拉斯父子,他不得不放弃格拉斯时还悬赏三百美元寻人为他送终。菲茨杰拉德则不同,他自私、残忍、贪婪、无耻,是人性恶的代表。格拉斯的复仇,针对的是有杀子之仇的菲茨杰拉德个人,而不是西方白人群体。
电影试图加入人性这一标尺为殖民者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重新塑像。这种叙事策略将所有人以人性为基准分类,而不是无理由的肤色,无声消弭了种族间不可跨越的屏障。正如格拉斯在自己性命难保时还想办法救了一个被法国人性侵的印第安女子,吉米也悄悄留了食物给他们经过的村落幸存者,那位幸存女子拿到食物后眼睛中不再有惊惧。但这种叙事策略又极容易滑入消解殖民罪恶的陷阱。如果只是法国人用心险恶挑拨离间,只是丧心病狂的个人滥杀无辜,难免有美国人自我洗白的嫌疑,毕竟那些善良如吉米的美国人也未停止掠夺北美,亨利也在等莱文沃恩中尉的军队用“文明”扫荡里族人。他们的善行都是出于人性的善良,都是个体对个体,而非白人对印第安人。
另一方面,这种叙事策略让格拉斯的身份重构从殖民冲突转换到了人性冲突。除上述问题,格拉斯最终皈依印第安文化也由此带上了乌托邦的意味。当现代文明生出菲茨杰拉德这样的毒瘤,“野蛮”的印第安文化能够疗救吗?这就像乡土电影往往最终把现代文明负面倾向的救赎希望寄托于传统农业文明一样,传统文化本身也是个复杂体,“种种有机社会仅仅是用以谴责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商品化生活的种种方便的神话”[2]。印第安人就如同电影中的野牛群,它们看似强大却在体形较小的狼群攻击下四散逃命,对落单者置之不理,逃走后的最终命运也是加入格拉斯梦境中的野牛头骨堆。印第安文化在殖民与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双重冲击下,也必然不可再回归。
四、家庭:殖民历史的重叙
队长亨利问格拉斯是否真的杀过一位中尉,格拉斯回答说:“我只是杀了一个要杀我儿子的人。”格拉斯如此回答,不难看出杀白人之于他还是有压力的。但相比白人至上论,他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信仰——家庭。家庭,是人性之外,格拉斯融合种族差异的重要黏合剂。
格拉斯与霍克被菲茨杰拉德辱骂后的第二天凌晨,格拉斯喊霍克起床探路,霍克并没有马上起来,格拉斯让他再躺会儿并走上前拉上被子,摸着霍克的头说了两遍:“你是我的儿子。”作为父亲,格拉斯深知霍克的恨与痛,他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不允许他反抗,即便是言语的,他用以抚慰儿子的是血缘亲情,是他对儿子不离不弃的爱,正如他自己的梦境中一直是死去的妻子与儿子。梦境中的妻儿一直与树这个意象连接在一起。枝繁叶茂的大树,沉稳坚定,是个体对家庭的重视,也为家庭成员提供坚实的后盾与心灵的宁静。大树也是他们家庭精神的象征:再大的风也吹不倒根深的大树,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坚持战斗。正是这种信念,促使格拉斯反省西方白人与印第安人的种族关系,支撑着格拉斯走过最后的复仇之路。
也是因为家庭、亲人,格拉斯获得了与印第安人和平共处的可能。波尼族男人遇到格拉斯时,先是因为语言相通放下了武器,这有赖于格拉斯与波尼族人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后又因为相同的遭际而结伴同行,不是因为亲人遇害的共同悲痛波尼族人不会轻易邀约陌生白人共骑马匹前行。里族人最后再相遇时没有杀格拉斯,也是因为头领的女儿平安归来。虽然只是马背上冷漠的一瞥,已是良好的开端。“身份认同从来就不是一种单一的构成,而是一种多元的构成。”[3]对普通个人而言,与国家、种族、民族等宏大理念相比,显然家庭是身份认同更重要的维度。个体的价值应该得到肯定,把每个个体的故事从历史书的笼统叙述中发掘出来,也让冷冰冰的文字多了温情。
与人性叙事策略相类,突出个体在殖民历史中的位置,也是把双刃剑。格拉斯以父亲的身份而不是白人的身份杀死了白人军官救儿子一命,也是以父亲的身份杀死菲茨杰拉德为儿子复仇,两次针对白人的对抗行为都是为了“儿子”,而并不是为混血儿,不是为印第安人。格拉斯能以最朴素真挚的情感爱家人、护弱者已是不易,要求他有反殖民的思想觉悟是苛求。但也正是他以妻儿乃至自身死亡换来的觉醒,喻示了“殖民者”内部反思殖民、重建种族观的不易。而且电影还在里族人对猎人团队的追杀原因中突出了“女儿”因素。头领对于白人的残暴掠夺明明十分清醒,却未将种族认同纳入他的战争缘由。这是一种非政治视角的历史观,以个体碎片化的经验还原了历史丰富的原生情态,但也让头领与殖民白人的冲突变成了私仇,弱化了印第安人反抗殖民的正义性。
海登·怀特认为曾经存在的过去“现在呈现的只是遗迹、碎片和混乱”,“为了从中抽取一些可理解的信息,我们必须先给这些遗存强加某些秩序、提供某些形式、赋予某种模型、确立它们的连贯性,以作为现今已分裂的整体各部分的标示”[4]。《荒野猎人》对格拉斯原型真实故事的改编,就是在用当下白人殖民观串联历史的碎片,重组出格拉斯这样的殖民者形象。这个“改编”也是今人对自我的认识。殖民主体的重建已不再完全缺失被殖民者这个他者,但殖民历史却遭逢了普世价值虽非恶意却强力的稀释。当种族歧视不再是需要争辩但仍然存在的问题,在多元文化中重建身份认同,仍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