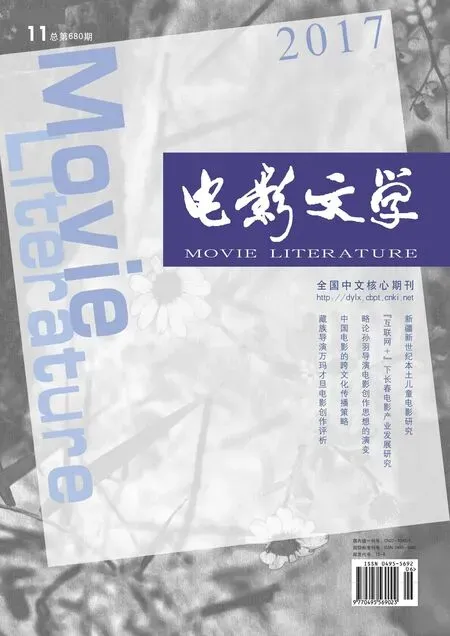《生命之树》的视觉审美风格
2017-11-16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河南郑州450000
刘 华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美国导演泰伦斯·马力克(Terrence Malick,1943— )无疑是当代世界影坛中的一位极具个性的导演,在其40年的从影生涯中,仅仅拍摄了五部影片。而第五部便是在2012年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异彩的《生命之树》(TheTreeofLife,2011)。由于这部电影在叙事方式上大胆地采用了“意识流”理念,使得整部电影的故事支离破碎,并且叙事的背后灌注了导演本人的神学思考,导致电影在问世之后得到了两极化的评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一贯特立独行的马力克再一次地解构了人们的审美习惯。从电影的主题以及表现手法来看,《生命之树》与希腊电影大师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永恒和一日》(EternityandaDay,1998)有很明显的共通之处,两部电影思考的都是极为严肃的生命问题。而二者的区别恰恰就是在视觉审美风格上。当安哲罗普洛斯采用一种朴素无华的视觉风格时,马力克却呈现给观众一种实验性的影像。与《生命之树》零散、打破传统的叙事相对应的,是马力克使用各种美轮美奂甚至是带有悲悯色彩的画面来突出他宏大的生命主题,大量的画面是带有抒情性质、富有诗意的空镜头,在看似不合理的背后孕育精妙的哲思与隐喻。可以说,《生命之树》的画面炫目多姿、超拔而不失细腻,本身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美学高度,同时,对其的解读又有助于人们了解该电影极具挑战性的、怪异的叙事,从而在整体上把握马力克的匠心独运。
一、视觉的穿梭与跳跃
如前所述,《生命之树》和《永恒和一日》之间是有一脉相承关系的。两部电影就叙事而言,都使用了多个时空,不同时空共同形成了一种诗歌性的表达形式,只是安哲罗普洛斯更倾向于让情感汩汩流淌于平实的细节中,而马力克则大量使用了意味着情感喷涌、爆发性的空境画面,这些与主人公普通,甚至对情感有所压抑的日常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就使得观众在欣赏《生命之树》时,其视觉一方面要穿梭、跳跃于不同的时空中,另一方面则要穿梭跳跃于多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氛围中。
首先,就时空的穿梭跳跃而言,电影中承担叙事责任的视觉画面来自于对一个五口之家生活的表现。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主人公杰克人到中年以后的回忆甚至想象,为了体现回忆的跳跃性、选择性,剪辑时有意采用了一种意识流式的拼接手法。如刚表现了19岁的弟弟死亡,时空就切换到母亲刚怀孕时父母的喜悦;又如刚表现了一个男孩子不幸溺水身亡,大家极为悲哀,下一个镜头便是兄弟们无忧无虑地玩闹等。传统电影中的起承转合,各时间、空间之间的逻辑连接退居末席,观众所看到的是主人公小时候印象深刻的一个个片段,这些画面是突兀出现,具有瞬间美感的。而时空和时空之间的断裂就意味着一个个留白,这些留白能够调动起观众对电影叙事的参与性。
其次,就情感的穿梭跳跃来说,电影中所要表现的感情是复杂的,这主要体现在一种情感是属于一个微观的、普通的家庭世界,而另一种情感则属于宇宙这一杳渺无极的宏观世界。两个世界在电影中以人和上帝的对话作为连接点,相互呼应,交织为一体,形成了一种结构上的对称美。在微观世界中,三兄弟手足情深,相依相伴,杰克在三人之中是最成熟的大哥。在青春期阶段,杰克还曾经潜入一个女孩子的家中偷走了她的丝绸睡裙;母亲温柔善良,笃信宗教,在三兄弟的成长中扮演了一个典型的“慈母”角色,她也是身体力行地向杰克传达何为爱的最重要的人。甚至观众可以感受到杰克心中的俄狄浦斯情结;而父亲则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严父”,他总是保持着严肃的面孔,强硬地教儿子们打拳,甚至不允许孩子们叫他“dad”,而使父子间的对话往往都是以儿子说“Yes, sir”结束。这都是因为父亲坚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父亲在工作上遇到不愉快时,他便会突然对家人爆发情绪,痛斥儿子,甚至对妻子动手,逼得妻子泪流满面。这样令人窒息的环境下,长子杰克对父亲有着深切的恨意,这甚至使得他成年之后的生活也并不愉快。这种情感是真挚感人、贴近观众的。而在宏观世界中,一种震撼人心的情绪却扑面而来。大量自然意象(如阳光、河流等)堆叠,繁杂而丰富,令人眼花缭乱,它们都直指“生命”这一关键词,最后结合兄弟的死让观众产生一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悲怆与无奈。观众能从两种一小一大的情感变换中得到一种经由视觉,再至心灵的双重错愕,令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宏观世界传递出来的情感并没有对观众理解微观世界的情感带来干扰,后者是主人公杰克叩问宇宙、与神明对话的产物。
二、视觉的譬喻与表征
马力克在思想上曾经深受基督教以及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海德格尔的影响。整部《生命之树》中,马力克一直试图超越生死的界限,表现徘徊于生命边缘的灵魂,来对曾经困惑过自己的问题进行总结。但并非所有人都曾直面生死,也并非所有人都对存在主义哲学、基督教文化以及马力克的个人经历(如电影中死去的弟弟很大程度上对应的是马力克自己死在西班牙的弟弟,弟弟的死让他第一次对上帝产生了怀疑)有所了解,并且这些内容很难以非文字的方式杂糅于一部电影中,为此,马力克选择了制造多种视觉上的譬喻与表征。
首先,在色彩和场景设置上,马力克在表现杰克的童年时期时,多采用清新、丰富、温馨的色调与物象,如草坪、树木、带有暖意的黄灯、金色的袋鼠玩具等,观众可以感受到,在一个对孩子投入了全部爱的母亲的照顾、庇佑之下,杰克的童年大体上是幸福的;而在其成年之后,工作上蝇营狗苟,婚姻上也并不顺利,母亲也去世了,这时候充斥观众眼球的则是大片白色的、冰冷的建筑与家具,生活于此间的杰克衰老而疲惫。
其次,在具体的物象设置上,马力克也在其中赋予了值得解读的深意。以电影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恐龙为例。电影中第一次出现恐龙时可以理解为表现的是自宇宙大爆炸、星云变化后,地球上生命的孕育发展情况。而恐龙第二次出现时情形则产生了变化,画面上出现了一只濒死的恐龙,身旁还有另一只恐龙,它无能为力地走开了。这里那只奄奄一息的恐龙无疑隐喻的便是杰克早逝的弟弟。对杰克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来说,弟弟的死亡无疑就相当于宇宙进化中的一个重要物种的消亡。
但必须承认的是,大量的譬喻与表征并不意味着电影就是含蓄的。在《生命之树》中,视觉审美上的缺憾并不在于马力克频繁使用的各类意象画面,而是在于马力克为了向观众申明主旨,在电影结尾反复用多个视觉意象来表达一个内涵:爱。如宁静的海涛、布满向日葵的山谷、反复敞开的门、夜空、透过树枝的阳光等。这就未免使得这一部分给观众的独立思考空间较小,与之前引用各种绚烂画面时的举重若轻形成了对比。然而这毕竟只是白璧微瑕,并无损于电影在视觉审美上的品质。
三、视觉的写实与虚拟
《生命之树》的一大视觉审美特征便是其画面游走于写实与虚拟两种风格之间。甚至可以说,马力克在这方面做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探索。写实被视作电影基本功能以及初始形态,比尔·尼科尔斯甚至认为所有的电影实际上都是纪录片,而巴赞则更是在其本体论思想中提出了电影的照相本性。从艺术表现力而言,电影相较于文学、美术等艺术显然要更受技术变革的影响,如合成镜头、数字技术等就曾大大地拓展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力。
就实与虚的关系而言,《生命之树》中的影像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便是在讲述杰克的中年、青少年、童年生活时,这一类影像在视觉上是最符合观众审美习惯的,也是观众最容易接受的。观众可以很轻松地在其中捕捉到导演要传达的信息,如父亲对着巴赫的黑胶唱片双目紧闭,双手做出指挥的样子;又如父亲在弹琴,儿子则在一旁倾听等,这代表着父亲是一个极具音乐天赋的人,然而因为种种原因父亲从事着与自己的天赋毫无关系的工作,而数十年后,成年的杰克实际上也在重复父亲的命运。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部分的镜头马力克并不纯粹是以“记录”态度进行拍摄的。即使是在这部分高度写实的画面中,马力克都采取了一种“非常”的视觉角度,这部分几乎没有一个镜头是以正常的人类视角进行拍摄的,摄影机位置不是过低就是过高(比如母亲在草地上逗幼儿玩耍时,摄影机位置甚至要低于幼儿),并且会有故意制造梦幻效果的摇移。马力克用这样的方式来为观众制造一种“上帝视角”或“昆虫视角”,降低画面的写实性。
第二类影像显然是为了体现一种虚幻、玄虚感,其中一部分尽管是实拍,但是就逻辑而言显然是非现实的。如在电影的结尾,杰克一家人在雨过天晴的海滩上重逢,除了他们一家还有许许多多观众陌生的脸孔。这次重聚为电影点明了“爱”与和谐这一主题。西恩·潘饰演的老年杰克看到了死去的弟弟,也看到了年轻美貌的母亲。这并不能单纯理解为弟弟和母亲的“复活”,而是因为在杰克的记忆中,弟弟和母亲最为清晰的形象便是这样年少如花。一部分来自虚拟技术而非实拍,如恐龙从沙滩上抬起头来,熔岩的喷发,卵子的受精,还有不断出现的影影绰绰的火焰等,这一类镜头是服务于电影置于片头的《圣经·约伯记》中的那句“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的,它们共同表意上帝注视下万物的起源。
还有一部分画面则有所不同,其承载的是与上述镜头一样的功能,观众也很容易将其误认为是数字技术的产物,但实际上,这一类画面中的景象却是真切的实景。如电影中的宇宙景象,其实是哈波望远镜中的宇宙。在《生命之树》中,早有相关纪录片向人们展现过宇宙的神秘与浩瀚。马力克的宇宙观也是属于当下时代人类的普遍宇宙观的,但马力克将宇宙与人类自我认知联系起来。观众在目睹宇宙的实景画面时,并不能将其与虚拟画面分辨开来。对观众来说,宇宙的真实或虚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几乎无法影响到人类的现实生活,这恰恰就是人类的局限性。在电影中,马力克多次强调人类的无力,在面对生命中的种种意外(如家庭成员的离去)时,人类是渺小的、束手无策的。在面对宇宙时也是一样,绝大多数的人类对此是陌生的、无法把握的。就这一点而言,马力克的功绩并不仅仅在于结束了科幻电影对宇宙形象的垄断上。
电影艺术具有直观性,高度依赖或者说得益于技术的形式使电影具有优势也具有劣势,也使得大批电影人前赴后继地开拓着电影体裁。部分人选择了将电影打造为思辨的工具,然而其尝试大多以失败告终。客观来说,就思辨力而言,影像终究无法与语言文字相媲美。但至少对于有思想的电影人来说,电影绝不仅仅是增添了声色的动感小说或连环画。泰伦斯·马力克用一部具有诗意哲思视觉审美(以及天籁般的配乐)的《生命之树》完成了对生死、成长、离合等问题的思索。电影在视觉审美上的独树一帜,与电影有意背离前因后果逻辑的叙事相得益彰,使观众得以与马力克一起从生命的最细微之处飞翔于宇宙的最广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