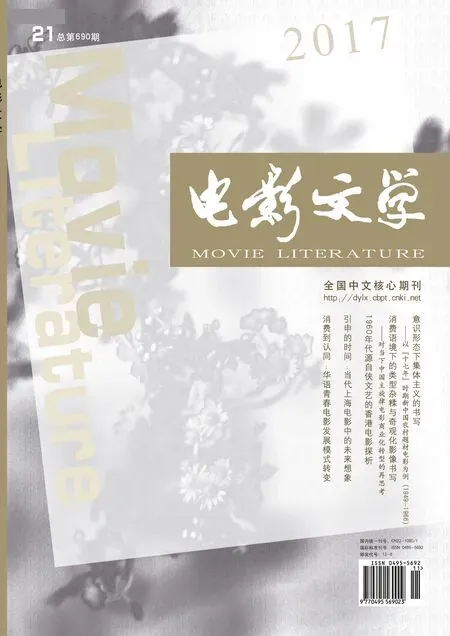姜文电影的存在主义
2017-11-16赵晓菲郑州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河南郑州450000
赵晓菲(郑州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存在主义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经过克尔凯郭尔、叔本华、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不断健全完善后,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存在主义提倡的是恢复人性的本真,关注人的自由,它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哲学的圈子,而进入文学、电影等领域中。中国导演姜文原本出身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自将他所极为重视的小说《动物凶猛》改编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在国内外造成影响后,姜文就已经不再只是作为“演员姜文”而是作为“导演姜文”为人们所熟知了。在姜文之后推出的几部电影中,可以看到其中都带有属于姜文的独一无二的思想烙印。而存在主义便是这种思想烙印的成色之一。
一、姜文与非理性
存在主义的出现本身就有着某种对理性的反拨。存在主义称不上是一个壁垒鲜明、定义清晰的哲学阵营,不同的存在主义者所持有的哲学理念也各有不同,这种分歧甚至包括了雅思贝尔斯等人的有神论和萨特等人的无神论的区别。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对外部世界有着一种抵触的情绪。在存在主义诞生之前,哲学用以探究世界本源的途径便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这两种思想,存在主义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尤其是诞生于17世纪的英法唯物主义与黑格尔提出的理性辩证法,都为叔本华、尼采等人否定。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在唯物主义中服从于理性,从而只关注外部世界而忘却自身,最终失去自由。以叔本华为例,他就曾经提出支配世界的是意志,意志应该拥有高于理性的位置。
在姜文的电影中,尽管我们并不能论定姜文是一个反对唯物主义的导演,但我们可以窥见姜文对“非理性”的尊崇。并且在这种“非理性”中,姜文关注的正是人的内心世界。例如,在可以被称为“荒诞派戏剧”的《一步之遥》(2014)中,真实与魔幻、清醒与荒诞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这也是大部分习惯了理性的观众难以接受这部电影的原因之一。如在影片开头的马走日的旁白,以及结尾时重新出现的马走日旁白,都说明了整部电影实际上都是马走日的临终回忆,这种回忆自然不可能是完全贴合现实的,它掺杂了马走日的主观思维。为了提醒观众自己选择的非理性路线,电影还在视觉上运用了大量舞台语言:硕大的月亮、浮华怪诞的舞台、艳俗得甚至显得虚假的建筑,以及最后马走日临死前出现的风车以及漫山遍野穿着结婚礼服的新人,乃至覃老师开机关枪向武六和马走日扫射的场景,都是在标举电影的超现实主义特征。
可以说,《一步之遥》是姜文拒绝附庸于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一部典型之作。
二、姜文与人的自由选择
人的自由选择问题可以视作是存在主义核心问题之一。在经典存在主义中,自由被认为是人最重要的属性,甚至是人的本质之一。脱离了自由的状态,人是无法被视作真正的存在的。存在主义以人的自由来反抗世界上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威包括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以致上帝等宗教。在存在主义看来,人如果在思想和行动上服从于具体的客观规律或文化,如果屈从于上帝,那么人便会失去自由,无法称作真正的人。
在姜文的电影中,人的自由选择问题并没有被上升到这样一种绝对的高度,姜文并没有如克尔凯郭尔所强调的那样,将人的自由定义为神秘的某种意志自由中。如此深奥以及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难以接受的理论也是很难被影像化的,尤其是在需要兼顾市场回馈的情况下。但是综观姜文的电影不难发现,自由是他始终关注的,拍电影本身也是姜文走向个人自由的一种方式,尽管这种自由是“戴着镣铐跳舞”式的。姜文也同样肯定人生而自由,拥有自我选择的权利,在意识和人身上都应该得到自由创造、自由发展的空间。例如,在《让子弹飞》(2010)中,张牧之原本是蔡锷将军手下的手枪队长,在革命理想破灭之后选择了当麻匪,这是他做出的自由选择。而在当上麻匪以后,化名张麻子的他也并没有满足于只过打家劫舍、朝不保夕的生活。在结识了假称师爷的马邦德后,张麻子决定带上师爷的委任状以马邦德的身份去鹅城赴任。在抵达鹅城后,张麻子又开始了和当地一霸黄四郎的斗智斗勇。经历过辛亥革命的张麻子深切地知道开启民智的不易,因此他在和黄四郎的斗争中一再强调要师出有名。甚至在最后,孤家寡人的张麻子看到火车上黄四郎一闪而过的身影,依然选择了纵马跟上,尽管兄弟和百姓让他失望,但他依然要战斗到底,给他人自由的同时也为自己争自由,这便是张麻子的自由选择。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自由的追寻又是与主流意识形态中的追求自由有所区别的。在存在主义中,自由主义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如萨特曾经指出:“自由正是通过分泌出它自己的虚无而把它的过去放在越位位置上的人的存在。”换言之,萨特认为,人争取自由是没有过错的,为了自由而反抗极权也是合理的,但是自由主义者有其软弱的一面,在其反抗过程中,他们所收获的实际上是新的虚无。随着这种虚无的不断增加,人的焦虑感也就会越来越强烈。例如,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在主流语境中意味着“黑暗”的“文革”时期在电影中呈现的是一派玩乐、轻松、自由的场景,革命浪漫主义气息在电影中无处不在。在他们之上,依然有威权的存在,从警察将马小军骂得回家大肆发泄的那一段话中可见一斑:“瞧你这德性,还镇王府井,镇动物园,镇地安门,告诉你,公安局全镇!”马小军等少年在电影中不谙世事、衣食无忧,又因为成年人的“闹革命”而失去了学业上的压力,他们偷窥他人,打碎玻璃,在老师帽子里放煤球哄闹课堂等行为,都是他们追求自由、挑衅威权的一种表现。但这种对自由的追求最后引向的是一种空虚。马小军在米兰面前扮演着一个和自己年龄并不相符的角色,然而他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假的,甚至在电影中出现的大量在强烈阳光中他和米兰相处的画面只不过是他在偷窥米兰之后的幻想。
但即便如此,姜文也不认为我们应该回避对自由的向往,尤其是在社会上阶层压迫日益严重、生存压力日益加大的当下。以《让子弹飞》为例,在电影中,人们对黄四郎的反抗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最后这种反抗变成了以黄四郎曾经最为骄横的奴隶带头的肆意的打砸抢,这对观众来说是违背传统审美习惯,也是有着警醒和讽喻意义的。这一点有着非常明显的存在主义名著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TheNakedandtheDead,1948)中的意味。一方面,过强的、无法无天的极权统治是不可能持久的,而另一方面,由于人已经在这种极权压迫下丧失了主体性,一旦反抗成功就会走向同样无法持久的无节制的自由放纵,最后人们正如孤身一人的张牧之一样,面对的是一片虚无。
三、姜文与悲观性
叔本华在建设存在主义时代入了强烈的悲观主义情怀。在叔本华看来,人生为源源不断的欲求、痛苦和不幸包围的。这种悲观也影响到了后来的如尼采、克尔凯郭尔等存在主义者。克尔凯凯尔认为人是“孤独的个体”。人在世界上其实只与自我发生关系。在海德格尔和雅思贝尔斯等人来看,人的存在状态主要就是悲伤、恐惧、忧虑等。而萨特更是对“恶心”进行了重新定义,萨特认为,恶心并不仅仅是一种引起人想呕吐的胜利性厌恶,而是一种人们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方式,正是因为人有着不可克服、痛苦的恶心感,人才能揭示自己的身体。恶心是人自我觉醒的前提,但它也意味着人要生活在对内在世界的恐惧和对外在的荒诞世界的无尽痛恨之中。
在姜文的电影中,可以看到叔本华等人消极的人生观:首先,人的生存形势是严峻的,不仅生命受到威胁,人的尊严、个体价值等也不断遭到践踏。例如,在《鬼子来了》(2000)中,一方面,河北某乡村的村民,在抗日战争时期本身就面临着日军占领后的生命威胁。姜文就曾在采访中说过,他的老家唐山就曾经发生过日本军人屠杀中国平民的惨案。而另一方面,这些处于偏僻山村挂甲台的村民又在以为自己能够在日军统治之下过上相对平静的生活时,意外地结识了日军花屋小三郎和汉奸翻译官董汉臣。然后村民们在粮食的诱惑下与日军签署了安全送走花屋的合约。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村民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处死花屋和董汉臣,还是依照董汉臣的建议将花屋送归宪兵队,他们的生命都是掌握在日本人手上的。
其次,人和人的关系是被异化了的,整个社会存在大量难以克服的矛盾与对立,人很难得到应有的慰藉和安抚。例如,在《太阳照常升起》(2007)中,在讲述年轻时和“最可爱的人”李不空之间的故事时,一开始疯妈认为穿着军装的李不空“像个英雄”,然而后来疯妈的叙述却是这样的:“你爸来找我,还带着枪,我说:‘不!’你爸说:‘我知道,我知道……’”单纯从疯妈散乱、零碎的叙事中很难补全事实的真相,但从疯妈当时回忆这件事时痛苦的表情推测,最有可能的是李不空凭借武力强奸了疯妈。而更为可悲的是,疯妈从此就因为“不怕记不住,就怕忘不了;忘不了,太熟,太熟了就要跑”而跟李不空走了。而后来李不空的军衔越来越高,在疯妈怀孕时,李不空则在新疆服役,从李不空搜集的各种颜色的辫子中不难看出,他在利用职务之便继续染指其他女性。然而疯妈一直深爱李不空,以至于一直不愿意接受李不空死去的事实。
而姜文电影始终有着较为可观的票房成绩,除了《太阳照常升起》外,观众基本上都愿意为“姜文”二字走入电影院,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姜文习惯于在绝望悲观的外面包裹一层叙事的灵动、戏谑外衣,使电影本身并不失去娱乐性。例如,在《鬼子来了》中,花屋小三郎为了激怒村民求死殉国,让董汉臣教他几句骂人的中国话,而董汉臣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却教了花屋几句奉承讨好的话,于是花屋横眉怒目、视死如归地说出:“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观众便很容易感到一种喜剧性。这些都让观众在观影时尚处于一种沉迷于流动的剧情的状态,而在观影结束,对电影的内核进行思考时,才会发现电影中各种罪恶、压抑现象实际上并没有离我们远去,相反,某种荒谬性其实是不仅仅体现在台词语言上的。可以说,观众一般以一种较为轻松、愉快的感情来欣赏姜文的电影,而如果对姜文电影稍加咀嚼便可以感受到其中人所承受的深重的苦难。
存在主义这一哲学思潮高度关注精神的存在,视心理意识为唯一的存在。姜文的电影尽管并不是彻底的存在主义电影,但是处处可见导演在用存在主义的语言来说话。姜文对人的自由追求有着强烈的关怀,对社会和人生则有着较为悲观的认知,在他的电影中,社会存在被与个人的生存状态对立起来,人生的荒诞与痛苦往往被姜文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尽管就具体电影的艺术价值和政治隐喻而言,姜文电影面临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但是他在电影中所呈现的存在主义思想和艺术表现方式,却是饱含了否定和自我否定意义的,对于当代国产电影的创作和批评是有着积极作用的。